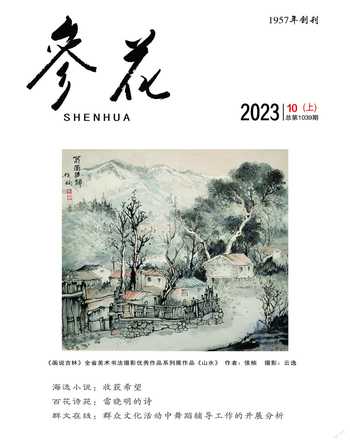与面食有关的记忆
多年来,我一直对面食情有独钟。
我更偏执地认为,美食也会隐于市。在偏僻的角落,不经意间我们会与当地的特色面食来个不期而遇。有机会外出时,我总喜欢在城市的老街道转悠,一边从最原始的建筑中阅读这个城市的过往,一边寻找自己心心念念的手工面食。
我钟情于面食,最主要的缘由可能与小时的生活有关。那时候主要以粗粮为主,“白面饭”就成了一种奢望。“白面”是家乡人对小麦面粉的俗称,相对于粗糙的杂粮面而言,小麦面粉细腻,营养价值高,是当时人们眼里的上等面。或许胃和人一样,容易对面食形成独特记忆吧,只要有面食,胃就会被唤醒。面对各种面食,我的胃很难经受住特有的味觉诱惑,人也会自然而然地停在面食前。
面食也是一种文化传承。从最初的“汤饼”到现在的五花八门,基本是中国人最为地道、最为经典、最为难以舍去的饮食文化。最初所有面食统称为“饼”,面条被称为“汤饼”,后来,又有“索饼”“水引饼”之称。据考证,宋代的面条品种多达十几种,早在元朝时就出现了能长期存放的挂面;明朝的拉面、刀削面也声名远扬;清代的伊府面要经过煮、炸工序后再加入各种菜焖熟后方能食用,那时候人们把面食和菜肴就已经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了。正因为面食有着独特而悠久的历史,才会让我更加痴迷。有时候暗自窃喜,自己钟情的不仅是美食,还是文化,是历史。先辈们千百年来在广袤的大地上用双手和汗水书写了一本本厚重的味觉之书,奈何我们仅是用舌尖怎能体会到其中的辛劳。每每想到这里,吃完饭后的惬意中又夹杂着难以言说的愧疚。
在我吃过的面食中,甘肃灵台的手工面可算得上一绝。去年,有机会和朋友去了趟灵台。为了早一点能够品尝到心仪已久的手工面,车到灵台县城,我们顾不上休息,直接前往邵寨镇。我早就知道,那的手工面最地道。
邵寨家家户户都会做手工面。在当地,又把手工面称为“长面”,言下之意,面条以长为主。不管是近亲还是远客,只要进入家门,邵寨人都会用最地道的手工面以表诚意、以示欢迎。我和朋友还在村子的林间转悠时,主家便在门口招手吆喝:“饭成了!”听到这么直接又满是诚意的招呼时,我们几乎是小跑过去的。想来也挺好笑,几个大人为了一顿面食而如此奔波,或许是很难再有什么饭菜能让人的心情如此迫切吧!
走到餐桌前,我们几个人面面相觑。比拳头略大一点的小碗,只盛了八分满。毫不夸张地说,十来岁的小孩子都能一口吃完,更不用说成年人了。主家看到我们面露难色,笑着解围说:“吃吧,还有哩!”一句话便瞬间化解了尴尬。坐定之后,主家向我们介绍了手工面的独特之处。看似碗小,实则面多。最先盛给客人的是“汤细”,面薄如翼,纤细如丝。配上五色酸汤,撒上葱花、蒜苗,吃一口面,喝一口汤,面条劲道十足,面汤酸香可口;紧接着是“汤宽”,汤还是原来的汤,只是把面条切成手指般的宽度;还有“宽干”,配以农家特制的小菜、食醋,加上肉臊子,一小勺辣椒油,让人食欲大增,胃口大开。
第三小碗还没有吃完,“汤细”“汤宽”“宽干”又轮番端上餐桌。说实话,这样的吃法还真是第一次见到,确实是碗小面多。面条被主家接续不断地端上来时,看得人眼花缭乱,人也吃得痛快。七八碗下肚之后,胃便渐渐撑起来了。主家看到你放下碗筷的时候,又笑盈盈地把一碗“宽干”端至眼前,名为敬饭。听过敬茶敬酒,敬饭倒是第一次听到,尽管已经饱得不能再吃了,但架不住主人的再三热情谦让,索性恭敬不如从命了。吃罢,我们几个便问起这“敬饭”的缘由,才知道本来没有这一说法,但灵台人实在,主人怕客人嫌碗小吃不畅快,也怕客人吃的碗数多了拘谨难堪,便用“敬饭”的举动让客人吃得饱一点。这一小小的举动倒也体现了灵台人真诚的待客之道。
灵台手工面的独特不仅仅在于吃法,叫法也是五花八门。和面、揉面和擀面与西北其他地区别无二致,但在灵台,除了正常的长面以外,还有“福禄寿喜”面。地处西北的小县城,由于缺少蔬菜、海鲜等食材,面条曾一度是人们最为依赖的吃食,人们把对生活的蕴意也寄托在面条上。“福禄寿喜”面分为白、绿、黄、红四色:白色面粉加入绿菜汁后做成绿色面,添加蛋黄后做成黄色面,掺入血块后则是红色面。同时,面的叫法也很讲究。过寿时吃的面叫“长寿面”;过年时吃的面叫“过年面”;原先的人用镰刀收割庄稼,收割完毕后便把镰刀挂在墙上,这时候会吃“挂镰面”;还有出嫁的姑娘在婆家第一次做的“试刀面”……都是同样的面条,但在不同的场合却有着不同的称谓,把生活中的仪式感体现在吃喝上,让传统的礼数渗透在饮食上,这让平朴的生活多了一分期待。
前段时间听朋友说灵台手工面正在“申遗”,这既是对饮食文化的传承,又是对特色面食的宣传。不管“申遗”是否成功,我想这也是让手工面进入更多人视野的一个大好机会,我们在享受食物带来的愉悦之时,也让文化走进了我们的心里。
直到今天,我还对蕴含文化的灵台面念念不忘。这种文化不经意间会烙在一个人的身上,并渗入骨子。灵台面的这种文化是乡土文明传承的产物,犹如我身上流着麦客的血液一样,和养育我的土地一起滋润着我的生命。
麦客是一种称谓,也是一种身份。在有些地方志中,明清时代,就已经有麦客出现了。
我生活的地域和宁夏的西海固地区接壤,过去有一段时间也隶属于宁夏。这里常年少雨,可以想象这里的人们曾经的生活是何其艰难。当时的农人在寻找生活的出路,不料想竟创造了一种具有地域代表性的“职业”——麦客。
我父亲曾是麦客大军中的一员。父亲八岁时失去了父母,一直寄居在别人家。成年后,为了改变生活,便和堂哥奔向陕西关中“赶麦场”。
四五月份,贫瘠的土地上难得有些生机,桃花、杏花、梨花相继开放,大豆、玉米这些农作物在土地的滋润下逐日饱满。柳絮在场院里、山洼上随意飘飞,布谷鸟旋在高空,一遍又一遍地叫着“喧黄喧收”。这时节,陕西关中一带的麦子就快收割了。
父親和堂哥背上干粮,拿着水壶,挂着镰刀,天刚蒙蒙亮的时候就出发。一路上他们尽量沿着河岸走,这样就不用翻山越岭,能省下更多气力,还可以随时喝上洁净的溪水,保持体力。河的两岸有由坍塌而形成的天然土洞,他们可以随时随地休息,特别是晚上。半个月的赶路时间,白天他们会找户人家帮忙做事,报酬可以是钱,也可以是干粮。他们前半夜赶路,后半夜休息。当麦客们陆续进入关中后,便成了一支浩荡的收割大军了。麦客们随意聚在路边、地埂边,主家需要人手且谈好价钱时,他们便走向麦地开镰,没有谈好价钱的麦客坐在原地抽着旱烟,聊着天,等着继续和主家谈价钱。
说是麦客,其实到了关中一带,什么活能挣钱就干什么活。父亲和堂哥一起喂过牲口,砌过墙,盖过房,割过草料,但主要还是收割小麦。
当时割一亩小麦能收入一到两元钱,和父亲一起的这些麦客们天刚蒙蒙亮便一头扎进地里,到了晚上才能回到主家提供的住处,中午的时候,主家把饭菜和水提到麦地边,麦客们随意找个地方就可吃饭,稍作休息后,又投入到收割之中。当关中的小麦收割结束以后,父亲一路北上,边走边割,再有半个月才能回到家里。而此时,老家的小麦也到开镰收割的时候了。
现在父亲老了,而且患肺心病多年,常年卧床,偶尔天气晴朗的时候在院子里活动一下筋骨,也只是轻微地活动,常常提不上一口气来,他再也拿不起镰刀了。
正因为父亲曾有过“麦客”的经历,他对粮食的珍惜程度高于常人。割完自家的小麦后,他和母亲会把掉落在地里的麦穗拾到篮子里,打碾完后,又将散落在院墙周围的麦粒用指头抠出来。这让我一直对小麦心怀敬畏,这种敬畏自然而然地转移到面食上。
我在城市的角落里寻找钟情的面食时,或许是在寻找曾经的生活,也或许是在寻找即将消失的麦客记忆。
对于我而言,面食承载着太多的故事,曾几次想把这个故事写下来,又感觉于心不忍。在灵台,遇到了这半生难得一见的手工面,这让我很欣喜,也让我自己多了一份对文化的敬仰。当然,麦客也是我难以绕过的门槛。在这个门槛上,我曾彷徨过,好在我和父母亲一样,一直向阳而生。
每个人都是生命中的过客,现在,我依然钟情于最简单的面食,依然不会忘记我是麦客的后代。
作者简介:尹巨龙,甘肃静宁人,系中国诗歌学会会员,有诗歌、散文在《诗刊》《诗歌月刊》《延河》《中国诗人》等刊发表。
(责任编辑 刘冬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