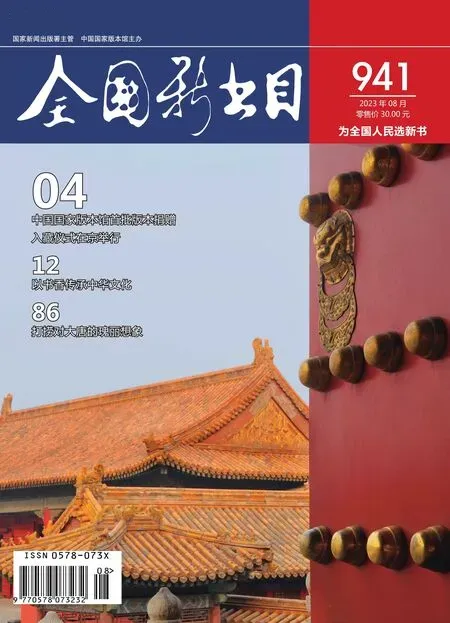诗文之辨
——酒饭妙喻
孙绍振
诗歌评论家。曾任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现为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著作有《文学创作论》《文学的坚守与理论的突围》等20 余部,散文集《愧对书斋》《灵魂的喜剧》等。2006年出版《孙绍振文集》8 卷。

《出口成诗的民族:中国古典诗歌微观艺术解密》孙绍振 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4/88.00元
诗与文的区别或者说分工,在中国文学理论史上相当受重视,在古典诗话词话中也长期众诉纷纭,但在西方文论史上却不像这样受到关注。在古希腊罗马的修辞学经典中,这个问题似乎很少论及,这跟他们没有我们这样的散文观念有关。他们的散文在古希腊罗马时期是演讲和对话,后来则是随笔,大体都是主智的,和我们今天心目中的审美抒情散文不尽相同。在英语国家的百科全书中,有诗的条目,却没有单独的散文(prose)条目,只有和prose 有关的文体,例如:alliterative prose(押头韵的散文)、prose poem(散文诗)、nonfictional prose(非小说类/非虚构写实散文)、heroic prose(史诗散文)、polyphonic prose(自由韵律散文)。在他们心目中,散文并不是一种特殊的文体,而是一种表达的手段,在许多文体中都可以使用。就像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关注的不是诗与散文的关系,而是诗与哲学、历史的关系:历史是个别的事,而诗是普遍的、概括的,从这一点来说,诗和哲学更接近。他们的思路和我们的不同之处还在于方法上,他们是三分法,而我们是诗与散文的二分法。
在我们早期的观念中诗言志、文载道,是把诗与散文对举的。我们的二分法一直延续到清代,甚至当代。虽然形式上二分,但是在内容上许多论者都强调其统一。司马光在《赵朝议文稿序》中,把《诗大序》的“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稍稍改动了一下,变成“在心为志,发口为言。言之美者为文,文之美者为诗”。元好问则说:“诗与文,特言语之别称耳。有所记述之谓文,吟咏情性之谓诗,其为言语则一也。”(《元好问诗话·辑录》)以上都是把诗与文对举,承认诗与文有区别,但强调诗与文的主要方面是统一的。司马光说的是二者均美,只是程度不同;元好问说的是表现方法有异,一为记事,一为吟咏而已。宋濂则更加直率:“诗文本出于一原,诗则领在乐官,故必定之以五声,若其辞则未始有异也。如《易》《书》之协韵者,非文之诗乎?《诗》之《周颂》,多无韵者,非诗之文乎?何尝歧而二之!”(《宋濂诗话》)这种掩盖矛盾的说法颇为牵强,挡不住诗与文的差异成为诗词理论家们长期争论不休的课题。不管怎么说,谁也不能否认二者的区别,至少在程度上有所不同。《徐一夔诗话》说:“夫语言精者为文,诗之于文,又其精者也。”把二者的区别定位在“精”的程度上,立论亦甚为软弱。
诗与散文的区别不是量的,而是质的,这是明摆着的事实,可许多诗话和词话家宁愿模棱两可。当然,这也许和诗话、词话的体制偏小,很难以理论形态正面展开有关,结合具体作家和作品进行评判要方便得多。黄庭坚说:“诗文各有体,韩以文为诗,杜以诗为文,故不工尔。”(转引自宋陈师道《后山诗话》)在理论上从正面把诗文根本的差异提出来是需要时间和勇气的。说得最为坚决的是明代的江盈科:“诗有诗体,文有文体,两不相入。”“宋人无诗,非无诗也,盖彼不以诗为诗,而以议论为诗,故为非诗。”“以文为诗,非诗也。”(《雪涛小书·诗评》)
承认区别是容易的,但阐明区别则是艰难的。对于诗与文的区别,人们一直争论不休,甚至到二十一世纪,这仍然是一个严峻的课题。古人在这方面不乏某些天才般的直觉,然而,即使对起码的直觉加以表达,也是要有一点才力的。明庄元臣值得称道之处就是他把自己的直觉表述得很清晰:“诗主自适,文主喻人。诗言忧愁媮侈,以舒己拂郁之怀;文言是非得失,以觉人迷惑之志。”(《庄元臣诗话》)这实际上就是在说诗是抒情的(不过偏重于忧郁),文是“言是非得失”的,也就是说理的。这种用说理和抒情对诗、文进行区分的方式,至少在明代以前,应该是有相当的根据,可惜把话说绝了,因而还不够深刻,不够严密。清邹只谟在《与陆荩思》中则有所补正:“作诗之法,情胜于理;作文之法,理胜于情。乃诗未尝不本理以纬夫情,文未尝不因情以宣乎理,情理并至,此盖诗与文所不能外也。”应该说,“情理并至”至少在方法论上带着哲学性的突破,不管是在诗中还是文中,情与理并不是绝对分裂的,而是互相依存,如经纬之交织,诗情中往往有理,文理中也不乏情致,情理互渗,互为底蕴。只是在文中,理为主导;在诗中,情为主导。这样的说法比较全面,比较深刻。在情理的对立中,因主导性的不同而产生了不同的性质,这样精致的哲学思辨方法竟然出自这个不太知名的邹只谟的笔下,是有点令人惊异的。当然,他也有局限,毕竟仅仅是推理,还缺乏文本的实感。真正取得理论意义上的突破的,则是吴乔。他在《围炉诗话》中这样写道:“问曰:‘诗文之界如何?’答曰:‘意岂有二?意同而所以用之者不同,是以诗文体制有异耳。文之词达,诗之词婉。书以道政事,故宜词达;诗以道性情,故宜词婉。意喻之米,饭与酒所同出。文喻之炊而为饭,诗喻之酿而为酒。文之措词必副乎意,犹饭之不变米形,啖之则饱也。诗之措词不必副乎意,犹酒之变尽米形,饮之则醉也。文为人事之实用,诏敕、书疏、案牍、记载、辨解,皆实用也。实用则安可措词不达,如饭之实用以养生尽年,不可矫揉而为糟也。诗为人事之虚用,永言、播乐,皆虚用也。……诗若直陈,《凯风》《小弁》大诟父母矣。’”
这可以说是真正深入到文体的核心了。邹只谟探索诗与文的区别仍拘于内涵(情与理),吴乔则把内涵与形式结合起来进行考虑。虽然一开头他认定诗文“意岂有二?”,但他并没有把二者的内涵完全混同,接下来马上声明文的内涵是“道政事”,而诗歌的内涵是“道性情”;形式上则是一个说理,一个抒情。他的可贵之处在于指出了由于内涵的不同,导致了形式上的巨大差异:“文喻之炊而为饭,诗喻之酿而为酒。文之措词必副乎意,犹饭之不变米形,啖之则饱也。诗之措词不必副乎意,犹酒之变尽米形,饮之则醉也。”把诗与文的关系比喻为米(原料)、饭和酒的关系。散文由于是说理的,如米煮成饭,不改变原生的材料(米)的形状;而诗是抒情的,感情使原生材料(米)“变尽米形”成了酒。在《答万季野诗问》中,他说得更为彻底,不但形态变了,性质也变了(“酒形质尽变”),这个说法对千年的诗文之辨是一大突破。
生活感受在感情的冲击下发生种种变幻是相当普遍的规律,所谓情人眼里出西施,抒情的诗歌形象正是从这变异的规律出发,进入了想象的假定的境界。例如“一日不见,如三秋兮”“谁谓荼苦,其甘如荠”“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都是以感知强化的结果提示着情感上的强烈的原因。创作实践是走在理论的前面的,而理论的落伍使得我国古典诗论往往拘泥于《诗大序》的“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陈说,仿佛情感直接等于语言,有感情的语言就一定是诗,情感和语言、语言和诗之间没有任何矛盾似的。其实,从情感到语言之间横着一条相当复杂的迷途。语言符号并不直接指称事物,而是唤醒有关事物的感知经验。而情感冲击感知发生变异,语言符号的有限性以及诗歌传统的遮蔽性都可能使得情志为现成的、权威的、流行的语言所遮蔽。心中所有往往笔下所无,言不称意,笔不称言,手中之竹背叛胸中之竹,是普遍规律。正是因为这样,诗歌创作才需要才华。司空图似乎意识到了“离形得似”的现象,但这只是天才的猜测,限于简单论断,未有必要的阐释。
吴乔明确地把诗歌形象的变异作为一种普遍规律提上了鉴赏论和创作论的理论前沿,在中国诗歌史上可谓空前。它突破了中国古典文论中形与神对立统一的思路,提出了形与形、形与质对立统一的范畴,触动了诗歌形象的假定性。很可惜的是,这个观点在他的《围炉诗话》中没有得到更系统的论证,但在当时已经受到了重视,比如《四库全书总目》,还有纪昀在《纪文达公评本苏文忠公诗集》中、延君寿在《老生常谈》中都曾加以发挥。当然,这些发挥今天看来还嫌不足,主要是大都抓住了变形变质之说,却忽略了在变形变质的基础上,还有诗文价值上的分化。吴乔强调读文如吃饭,可以果腹,因为“文为人事之实用”,也就是“实用”价值;而读诗如饮酒,可醉人而不能解决饥寒之困,旨在享受精神的解放,因为“诗为人事之虚用”。吴乔的理论意义不仅在变形变质,还在功利价值上的“实用”和“虚用”。这在中国文艺理论史上应该是超前的,他意识到诗的审美价值是不实用的,还为之命名曰“虚用”,这和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所言审美的“非实用”异曲同工。当然,吴乔没有康德那样的思辨能力,也没有建构宏大体系的演绎能力,他的见解只是吉光片羽。这不仅仅是吴乔的局限,也是诗话词话体裁的局限,但这并不妨碍他的理论具有超前的性质。
吴乔之所以能揭示出诗与文之间的重大矛盾,一方面在于他的才华,另一方面也不能不看到他心目中的散文,主要是他所说的“诏敕、书疏、案牍、记载、辨解”等,其实用性质是很明显的。按照姚鼐《古文辞类纂》中的界定,散文是相对于词赋类的,形式很丰富:论辩类、序跋类、奏议类、书说类、赠序类、诏令类、传状类、碑志类、杂记类、箴铭类,基本上是实用类的文体。在这样的背景下观察诗词并进行逻辑划分有显而易见的方便之处,审美与实用方面的差异也可以说是昭然若揭。这一点和西方有些相似,西方也没有我们今天这种抒情审美散文的独立文体,他们的散文大体是以议论为主、展示智慧的随笔(essay)。从这个意义上说,吴乔的发现仍属难能可贵,毕竟西方直到差不多一个世纪以后才有雪莱的总结:“诗使它触及的一切变形”。在这方面,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理论家赫士列特说得相当勇敢,他在《泛论诗歌》中说:“想象是这样一种机能,它不按事物的本相表现事物,而是按照其他的思想情绪把事物揉成无穷的不同形态和力量的综合来表现它们。这种语言不因为与事实有出入而不忠于自然;如果它能传达出事物在激情的影响下在心灵中产生的印象,则是更为忠实和自然的语言了。比如,在激动或恐怖的心境中,感官察觉到了事物——想象就会歪曲或夸大这些事物,使之成为最能助长恐怖的形状,‘我们的眼睛’被其他的官能‘所愚弄’。这是想象的普遍规律……”其实这个观念并非赫氏的原创,很明显,感官想象歪曲事物来自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第五幕第一场中希波吕忒与忒修斯的台词:“忒修斯,这些恋人们所说的事真是稀奇。”“情人们和疯子们都有发热的头脑和有声有色的幻想,疯子、情人和诗人,都是幻想的产儿……诗人的眼睛在神奇狂放的一转中,便能从天上看到地下,从地下看到天上。想象会把虚无的东西用一种形式呈现出来,诗人的妙笔再使它们具有如实的形象,虚无缥缈也会有了住处和名字。强烈的想象往往具有这种本领,只要一领略到一些快乐,就会相信那种快乐的背后有一个赐予的人;夜间一转到恐惧的念头,一株灌木一下子便会变成一头狗熊。”西欧浪漫主义诗歌衰亡之后,马拉美又提出了“诗是舞蹈,散文是散步”的说法,与吴乔的诗酒文饭之说有异曲同工之妙。
可惜的是,吴乔的天才的直觉在后来的诗词赏析中没能得到充分的运用。如果把他的理论贯彻到底,认真地以作品来检验的话,对权威的经典诗论可能会有所颠覆。诗人就算如《诗大序》所说的那样心里有了志,口中就有了相应的言,然而口中之言是不足的,因而还不是诗,即使长言之,也还不是转化的充分条件。至于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对于作诗来说,不管如何手舞足蹈都是白费劲,如果不加变形变质,写出的作品肯定不是诗。从语言到诗歌并不简单,也不像西方当代文论中所说的那样,仅仅是一种语言的“书写”。这种说法不如二十世纪早期俄国形式主义者说的“陌生化”到位,当然俄国形式主义者并未意识到诗的变形变质不但是感知的变异,而且也属于语义的变异(与日常、学理语言、散文语言拉开语义的“错位”距离)。语义不但受到语境的制约,还能从诗歌形式规范的预期中获得自由,因而它不但是诗歌风格的创造,也是人格从实用向审美高度的升华。正是在这升华过程中的突破,更主要的是突破原生状态的实用性的人,让人格和诗格同步向审美境界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