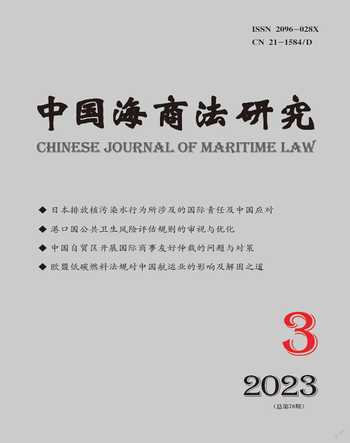中国自贸区开展国际商事友好仲裁的问题与对策
王淑敏 李银澄
摘要:对于传统的国际商事仲裁而言,友好仲裁是一项巨大的挑战。基于其偏离法律的风险,目前中国国际商事友好仲裁制度主要在自贸区进行探索和尝试。尽管如此,无论是《仲裁法》还是自贸区地方立法,均无对国际商事友好仲裁的明确规定。此外,在实践中,如何界定公平善意原则的定义与具体标准以及国际商事友好仲裁裁决公共政策的司法审查面临着难题。为此,提出相关建议如下:第一,修订《仲裁法》,增加国际商事友好仲裁专门条款,完善自贸区地方立法或规章,夯实立法的基础;第二,明晰公平善意原则的定义,以彰显保护弱势群体利益的公平善意原则;第三,借鉴《国际商会法国工作组的友好仲裁报告》的先進经验,确立公平善意原则的具体标准;第四,廓清公共政策的内涵与外延,合理运用公共政策对国际商事友好仲裁裁决进行司法审查。
关键词:自贸区;国际商事友好仲裁;公平善意原则
中图分类号:D997.4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028X(2023)03-0059-11
Study on the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Concerning the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miable Composition in Chinas Free Trade Zones
WANG Shumin,LI Yincheng
(Law School,Dalian Maritime University,Dalian 116026,China)
Abstract:For traditional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amiable composition is a great challenge. Due to its risk of deviating from the law, Chinas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miable composition system is currently mainly explored and tried in the free trade zones. Nevertheless, neither Arbitration Law nor the local legislation of the free trade zones has any explicit provisions of intermational commercial amiable composition. In addition, in practice, how to define the principle of ex aequoet bono and the judicial review of the public policy for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miable composition awards are facing difficulties. For this reason, some relevant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Firstly, to amend Arbitration Law, add special clauses o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miable composition, improve local legislation or rules in the free trade zones, and consolidate the legislative foundation; secondly, to clarify the definition of the principle of ex aequo et bono in order to highlight the principle of ex aequo et bono in protecting the interests of vulnerable groups; thirdly, to draw on the advanced experience of Amiable Composition: Report of the ICC France Working Group to establish specific standards for the principle of ex aequo et bono; finally, to clarify the connotation and extension of public policy, and reasonably apply public policy to judicial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miable composition awards.
Key words:free trade zone;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miable composition; the principle of ex aequo et bono
国际商事友好仲裁是当事人意思自治的产物,仲裁庭可以在符合公平善意原则的情况下适用法律,如果适用的法律违背公平善意原则,则可依照国际商事惯例与合同条款作出裁决。由此看出,国际商事友好仲裁的亮点在于:第一,公平善意原则贯穿于仲裁程序始末。如果适用国际商事惯例或合同条款更能体现公平善意原则,则可偏离法律,依照国际商事惯例或合同条款作出裁决。第二,友好协商,有利于维系国际商业合作。对于长期合作的国际商事主体,出于对法律严格性损伤未来合作关系的担忧,可适用国际商事友好仲裁解决争议。
目前,上海自贸区、辽宁自贸区与江苏自贸区已经开展国际商事友好仲裁;此外,北京、厦门、长沙、广州、南京等地亦全区域实行了国际商事友好仲裁制度,自然覆盖了所在的自贸区片区。但令人遗憾的是,中国自贸区在开展国际商事友好仲裁的过程中,在立法、公平善意原则以及仲裁裁决的司法审查方面存在较大障碍。基于此,笔者先行梳理国际商事友好仲裁的概念,并以国际商会为蓝本、厘清国际商事友好仲裁的裁决依据,在此基础上立足于中国现状对上述问题展开分析,并提出解决的对策。
一、国际商事友好仲裁的概念梳理
迄今为止,国际社会尚未形成统一、权威的国际商事友好仲裁的概念。
(一)域外诉讼法视野下的友好仲裁
追本溯源,友好仲裁起源于法国,1981年《法国民事诉讼法典》开创性地规定了友好仲裁制度,并得到了他国的效仿。英国学者克里斯蒂·R.H.教授指出,在13世纪中叶的法国,教会将和解、善意理念与法学理念融合,裁判者提出供各方批准的解决方案以解决国内争议,其后,裁判者的职能逐渐扩大,有权作出具备强制执行力的裁决,友好仲裁初具雏形。(R. H. Christie,Amiable Composition in French and English Law,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rbitration,Mediation and Dispute Management,Vol.58:259,p.264(1992).)1981年《法国民事诉讼法典》于第1474条与第1497条分别明确了国内友好仲裁与国际商事友好仲裁两种方式。(1981年《法国民事诉讼法典》第1474条规定:“仲裁员应按照法律规则裁断案件,除非当事人在仲裁协议中已授予仲裁员进行友好仲裁的权力。”第1497条规定:“如果当事人授予仲裁员此项权力,那么仲裁员可进行友好仲裁。”参见罗结珍译:《法国新民事诉讼法典》,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311、316页。)但无论使用哪种方式,都必须获得当事人的授权。更值得关注的是,该法典更加鼓励第二种方式——国际商事友好仲裁。也就是说,友好仲裁适用于国内争议时,仅作为“依法律规则仲裁”的例外存在,而友好仲裁适用于国际争议时,则作为与“依法律规则仲裁”并列的制度存在。紧随其后的是,《意大利民事诉讼法典》完全效仿了法国的立法,(《意大利民事诉讼法典》第822条规定:“除非各方当事人已明确要求仲裁员依据公平原则解决纠纷,否则仲裁庭应依照法律规定制作裁决书。”参见白纶、李一娴译:《意大利民事诉讼法典》,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24页。)其第822条沿袭了1981年《法国民事诉讼法典》第1474条的规定。
《德国民事诉讼法典》则对1981年《法国民事诉讼法典》的规定加以传承与变革。《德国民事诉讼法典》第十章并未对国际仲裁与国内仲裁作出区分,而是在第1051条第3款作出规定。(《德国民事诉讼法典》第1051条第3款规定:“仲裁庭只有在当事人明确授权的情况下才应按照公平善意原则或者作为友好仲裁员作出决定。当事人可以直到仲裁庭作出决定时方向仲裁庭作出这样的授权。”参见丁启明译:《德国民事诉讼法》,厦门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33-234页。)从其规定可知:第一,友好仲裁必须获得当事人明确授权,授权可以贯穿于仲裁始末,但必须限于作出裁决之前;第二,“按照公平善意原则仲裁”与“友好仲裁”作为可互换的术语使用;第三,友好仲裁既可适用于国内争议,亦可适用于国际争议。
(二)《联合国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对国际商事友好仲裁的界定
从上述域外立法来看,虽然友好仲裁可适用于国内民商事案件,但其更适用于国际商事领域,(参见刘晓红、向磊:《论友好仲裁的裁决权力来源及运用》,载《中国国际私法与比较法年刊》2020年第2期,第209页。)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于1985年主持制定的《联合国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简称《示范法》)为此作出了指引。根据《示范法》第28条第3款,经过当事人明确授权,仲裁员才能够根据公平善意原则,或者是以友好仲裁方式进行裁决。并且,依据第4款,无论在何种情形中,仲裁庭均应依照合同条款与贸易惯例进行裁决。由是观之,其一,公平善意原则系友好仲裁的根本特征。“按照公平善意原则仲裁”与“友好仲裁”成为可互相交换使用的术语。国际商事仲裁案例亦表明,针对上述术语并未进行区分,而是作为同义词使用。(Kiffer Laurence,Nature and Content of Amiable Composition,International Business Law Journal,Vol.2008:625,p.626(2008).)其二,友好仲裁须获得当事人明确授权,并依照合同条款与贸易惯例进行裁决。易言之,此为对“按照公平善意原则”或“作为友好仲裁员”作出裁决这一行为的法律限制。
(三)学界对于国际商事友好仲裁的界定
英国学者克里斯蒂·R.H.教授提出,国际商事友好仲裁指的是根据公平善意原则、合同条款以及国际商事惯例进行裁决,如果适用法律更符合公平善意原则,那么仲裁员可优先适用法律。
(R. H. Christie,Amiable Composition in French and English Law,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rbitration,Mediation and Dispute Management,Vol.58:259,p.259-264(1992).)美国学者劳伦斯·基弗和瑞士学者保罗·米歇尔·帕特基进一步指出,在国际商事友好仲裁中,仲裁员必须获得当事人的明确授权,如果适用法律有违公平善意原则,仲裁员可不严格依照法律仲裁,甚至可对法律解决方案进行修正。(Kiffer Laurence,Nature and Content of Amiable Composition,International Business Law Journal,Vol.2008:625,p.626(2008);Paolo Michele Patocchi,Arbitration Ex Aequo et Bono(“Amiable Composition”),Romanian Arbitration Journal/Revista Romana de Arbitraj,Vol.11:19,p.19(2017).)法国学者艾曼纽尔·维拉德从权利角度对国际商事友好仲裁进行界定:国际商事友好仲裁指的是当事人失去要求严格适用法律规则的特权,在公平善意原则的要求下,仲裁員反过来获得修改或缓和合同后果的权利。(Emmanuel Vuillard & Alexandre Vagenheim,Why Resort to Amiable Composition,International Business Law Journal,Vol.2008:643,p.643(2008).)
综上所述,国际商事友好仲裁系指在获得当事人的明确授权下,可以在符合公平善意原则的情况下适用法律,如果适用的法律违背公平善意原则,则依照国际商事惯例与合同条款作出裁决的一种争议解决方式。
二、国际商事友好仲裁裁决的依据——以国际商会为蓝本
《国际商会法国工作组的友好仲裁报告》(Amiable Composition: Report of the ICC France Working Group)发表于2005年国际商会第6号刊物,旨在指引、改进仲裁实践。2008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召开的国际商会委员会会议上,这份报告正式获得批准。(Edouard Bertrand,From A to B:A Step Forward to a Methodology of Amiable Composition,Romanian Arbitration Journal/Revista Romana de Arbitraj,Vol.8:69,p.70(2014).)据此报告,国际商事友好仲裁的裁决依据如下:第一,公平善意原则下适用法律;第二,公平善意原则下适用国际商事惯例;第三,公平善意原则下适用合同条款。(Edouard Bertrand,Amiable Composition: Report of the ICC France Working Group,International Business Law Journal,Vol.2005:753,p.757-759(2005).)
(一)公平善意原则下适用法律
负责起草《国际商会法国工作组的友好仲裁报告》的国际商会友好仲裁工作组主席爱德华·伯特兰指出,一方面,在国际商事友好仲裁中,仲裁员并無依照法律仲裁的义务;但另一方面,法律毕竟蕴含千锤百炼、反复验证的概念与结构,大部分情况下能够形成公平善意的裁决,因此工作组并不排斥法律的适用。(Edouard Bertrand,From A to B:A Step Forward to a Methodology of Amiable Composition,Romanian Arbitration Journal/Revista Romana de Arbitraj,Vol.8:69,p.71-72(2014).)换言之,在国际商事友好仲裁中,仲裁员可以依照法律仲裁,但是,如果法律不符合公平善意原则,仲裁员往往在个案中会根据公平善意原则对法律的适用进行部分、细微的修正,从而形成公平善意的解决方案。(Edouard Bertrand,From A to B:A Step Forward to a Methodology of Amiable Composition,Romanian Arbitration Journal/Revista Romana de Arbitraj,Vol.8:69,p.71-72(2014).)
在“加利福尼亚希姆普纳能源有限责任公司诉印度尼西亚国家电力公司案”中,合同选择适用的是印度尼西亚法律,仲裁员对此认可,多次援引印度尼西亚法律,最终形成的裁决是基于符合公平善意原则的印度尼西亚法律以及仲裁员的个人良知而作出的。三、中国自贸区开展国际商事友好仲裁的现状与问题中国自贸区已对国际商事友好仲裁进行了探索和尝试,但在现实中,尚存部分问题,亟待解决。
(一)中国自贸区开展国际商事友好仲裁的现状
考察自贸区的地方立法,无论是自贸区条例抑或是管理办法等,均未规定国际商事友好仲裁。只有上海自贸区、辽宁自贸区、江苏自贸区从仲裁规则层面将国际商事友好仲裁纳入其中。除此之外,中国部分地区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亦规定了国际商事友好仲裁,如北京、厦门、长沙、广州、南京,这些地区均设有自贸区,国际商事友好仲裁自然适用于这些自贸区。
1.自贸区仲裁规则以及部分地区仲裁机构仲裁规则已有国际商事友好仲裁表述
自贸区的仲裁规则及部分地区仲裁机构仲裁规则认可的国际商事友好仲裁,分为两种情形。
第一种情形是直接使用“友好仲裁”的表述,亦明确了“依公平善意原则仲裁”的原则。如《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仲裁规则》第56条、《中国(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仲裁规则》第54条、《长沙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第76条、《广州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第125条、《上海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第 51条。
第二种情形是虽未直接使用“友好仲裁”的表述,但明确了“依公平善意原则仲裁”的原则。如《中国(江苏)自贸区仲裁规则》第95条、《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第69条、《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第70条、《厦门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第34条。上述仲裁规则虽未直接规定“友好仲裁”的称谓,但实际上已经认可了友好仲裁。例如,北京仲裁委员会的官网明确在国际商事案件中可以进行友好仲裁。
2.自贸区仲裁规则以及部分地区仲裁机构仲裁规则的国际商事友好仲裁裁决依据
前文述及,《国际商会法国工作组的友好仲裁报告》的国际商事友好仲裁裁决依据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公平善意原则下适用法律;第二,公平善意原则下适用国际商事惯例;第三,公平善意原则下适用合同条款。受此影响,中国自贸区仲裁规则及部分地区仲裁机构仲裁规则亦有类似规定。
首先,适用国际商事惯例。一是无论何种情况均应考虑国际商事惯例。如《中国(江苏)自贸区仲裁规则》第95条、《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第70条、《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第69条以及《长沙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第100条。从条款表述上看,仲裁庭对于国际商事惯例与法律并无必然的适用上的先后顺序,而是任何情况下,均可考虑国际商事惯例的适用。此种规定与《示范法》类似,均明确可以不依照法律而依照国际商事惯例仲裁。二是并未提及如何适用国际商事惯例。例如《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仲裁规则》《中国(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仲裁规则》以及《厦门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等。
其次,适用合同条款。如《中国(江苏)自贸区仲裁规则》第95条、《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
第70条、《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第69条以及《长沙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第100条均沿用了《示范法》第28条第4款的体例,即无论何种情况均应考虑合同条款。但《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仲裁规则》《中国(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仲裁规则》《厦门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则并未对此进行规定。
最后,无论适用何种依据,均应符合公平善意原则。前文已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仲裁规则》第56条、《中国(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仲裁规则》第54条、《长沙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第76条、《广州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第125条以及《中国(江苏)自贸区仲裁规则》第95条、《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第69条、《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第70条、《厦门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第34条等均明确了“依公平善意原则仲裁”这一内容。由此可知,无论如何,友好仲裁均应符合公平善意原则这一规定已经得到普遍认可。
3.自贸区开展国际商事友好仲裁的现实需要
中国自贸区开展国际商事友好仲裁的现实需要在于一方面顺应了商事纠纷国际化发展趋势,另一方面顺应了商事纠纷多元化发展趋势。
首先,国际商事友好仲裁顺应了自贸区的商事纠纷国际化发展趋势。据统计,2021年,自贸区虽面积不到全国面积的千分之四,但作为经济发展的高地,在对外贸易规模层面却占全国比重的16.5%,而且,其实际使用外资占比达到18.1%。(参见《第二届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论坛举行 建言献策谋发展》,载中新网2021年10月27日,https://www.chinanews.com.cn/m/cj/2021/10-27/9596595.shtml?f=qbapp。)國际商事交易的繁荣,亦导致商事纠纷数量迅速增长。以上海市浦东新区法院为例,2014至2020年间,所受理的自贸区内涉外民商事纠纷案件数目持续增长。(参见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自贸区法庭课题组:《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涉外商事纠纷多元解决机制研究》,载上海市司法局网站2020年11月25日,https://sfj.sh.gov.cn/qmyfzs_fzyjcg/20201125/2dc6135ae147478cadf8df0d13e9815f.html。)《中国国际商事仲裁年度报告(2020—2021)》亦显示,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2020年度受理的案件数量同比增长8.5%,案件国际化因素明显增强。(参见中国国际商事仲裁委员会:《中国国际商事仲裁年度报告(2020—2021)》,载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网站,http://www.cietac.org.cn/index.php?m=Article& a=show&id=18091。)国际商事主体诉诸仲裁的原因是希冀通过公平、中立、高效的争议解决方式解决争议,国际商事友好仲裁具备此种优势。正因如此,国际商事友好仲裁作为与国际接轨的争议解决方式,得到了法国、意大利、瑞士、德国等国家的普遍认可,对该制度进一步完善与施行,有益于为自贸区的国际商事争议的解决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
其次,国际商事友好仲裁顺应了自贸区的国际商事纠纷多元化发展趋势。以上海市浦东新区法院2013至2017年间所受理的自贸区涉外民商事案件为例,整体呈现纠纷多元化趋势,结构类型存在显著变化。(参见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自贸区法庭课题组:《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涉外商事纠纷多元解决机制研究》,载上海市司法局网站2020年11月25日,https://sfj.sh.gov.cn/qmyfzs_fzyjcg/20201125/2dc6135ae147478cadf8df0d13e9815f.html。)值得一提的是,国际商事友好仲裁在处理多元、新型争议时具备独特优势。寺村信一指出,当法律难以追及实践发展脚步时,国际商事友好仲裁将成为保障当事人权益的有力工具。(Nobumichi Teramura,Ex Aequo et Bono as a Response to the ‘Over-Judicialisation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Kluwer Law International,2020,p.186.)例如,区块链技术(如智能合约)和人工智能等数字化手段的发展日新月异,但法律在规制此种高新技术时的滞后性已经在仲裁领域初露倪端。(Nobumichi Teramura,Ex Aequo et Bono as a Response to the ‘Over-Judicialisation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Kluwer Law International,2020,p.186.)有鉴于此,面对此类多元化、新型纠纷,国际商事友好仲裁无需严守法律,使得能够在处理纠纷时形成当事人认可的、巧妙的公平。
(二)中国自贸区开展国际商事友好仲裁存在的问题
国际商事友好仲裁属于舶来品,在中国自贸区的实践尚处初期,面临着以下难题:第一,缺乏立法支持。不仅《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简称《仲裁法》)第7条对国际商事友好仲裁进行了否定,且自贸区地方立法亦未对其进行规定。第二,公平善意原则的定义模糊。第三,公平善意原则的具体标准并不明确。第四,法院如何对国际商事友好仲裁裁决进行司法审查亦不明确。虽然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出台了相关意见对国际商事友好仲裁裁决的司法审查进行规定,但并未明确如何运用公共政策这一关键问题。至于其他自贸区,则根本缺乏此类规定。
1.缺乏立法的支持
虽然上海自贸区等的仲裁规则陆续规定了国际商事友好仲裁,但在立法层面,无论是上位法——《仲裁法》,还是自贸区的地方立法,均未明确这一特殊的仲裁形式。
首先,上位法《仲裁法》第7条排除了国际商事友好仲裁的合法性。根据《仲裁法》第7条,仲裁裁决的作出必须符合两个要件:一是根据事实,二是符合法律规定。如前所述,国际商事友好仲裁的要旨在于:可以脱离立法的束缚,依据国际商事惯例或者合同条款进行裁断,这显然与《仲裁法》第7条中的第二个要件有所冲突。
其次,作为上位法的《仲裁法》相关规定的缺失,(根据《立法法》第11条第10款,对于仲裁基本制度,必须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法律。)导致作为下位法的自贸区地方立法或规章等亦难以规制国际商事友好仲裁。究其原因,根据法的效力位阶理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简称《立法法》),上位法是下位法的依据和本源,其效力高于下位法。正如凯尔森所言,法律秩序是一个规范体系,下位法规范效力的理由始终是另一个规范,即上位法,而不是一个事实。并且,上位法作为规范体系中的效力源泉,构成了组成一个法律秩序的不同规范之间的纽带。(参见[奥]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173-175页。)由此可见,在缺失上位法的前提下,下位法想要逾越上位法,另行规定国际商事友好仲裁的做法是根本行不通的。退一步讲,即使根据《立法法》第16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可以授权下位法突破上位法的部分规定,且这一做法已不乏先例,但细予考察,目前中国的自贸区地方立法或规章并未获得此类授权,也就是说,《仲裁法》依然适用于所有自贸区。有的自贸区地方立法仅仅授权自贸区仲裁机构制定适应自贸区特点的仲裁规则,如《中国(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条例》第60条,或仅授权仲裁机构借鉴国际通行规则,如《中国(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条例》第67条、《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条例》第64条。还有的立法一方面强调以法律法规作为裁决依据,另一方面规定“并借鉴”国际商事惯例,这与国际商事友好仲裁可不适用法律、适用国际商事惯例的裁决依据相背离,例如《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条例》第56条与《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条例》第79条。
这直接导致了一个严重的问题:自贸区在缺失上位法或下位法的情形下,采取了“迂回策略”,不得不依赖仲裁规则以推行国际商事友好仲裁。但这一做法符合法理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一方面,《仲裁法》之所以不可缺失,是因为其对于境内发生的仲裁活动具备普遍的管辖效力,是仲裁规则的效力源泉。众所周知,《仲裁法》规定了受案范围、仲裁协议的效力、一裁终局、仲裁委员会和仲裁协会的组建、仲裁员的资质、仲裁协议的内容、仲裁程序和仲裁庭的组成、开庭和裁决、申请撤销裁决和执行等事项的基本原则和法律框架;而仲裁规则在受案范围、仲裁协议的效力、一裁终局、仲裁委员会和仲裁协会的组建、仲裁员的资质、仲裁协议的内容、仲裁程序和仲裁庭的组成、开庭和裁决等方面细化了《仲裁法》的规定,并结合了本机构的自身特点。对于裁决的撤销和执行问题,仲裁规则往往并不涉及。另一方面,仲裁规则均应服从《仲裁法》。对于《仲裁法》与仲裁规则而言,《仲裁法》一方面允许当事人通过意思自治对仲裁规则进行选择,并且对于适用的仲裁规则予以支持、补充,(参见赵秀文:《国际商事仲裁法原理与案例教程》,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179-181页。)但另一方面,《仲裁法》对仲裁规则亦起到规制与监督作用。(Alec Stone Sweet & Florian Grisel,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Judicialization,Governance,Legitimacy,Oxford University,2017,p.30.)仲裁规则本质上等同于获得《仲裁法》认可的契约,仅对局部的仲裁机构有效,当事人可根据意思自治原则自由地选择仲裁机构和仲裁规则。(Ian Pennicott,Why Are There So Many of Arbitration Rules,Asian Dispute Review,Vol.20:69,p.70(2018).)但无论如何,仲裁规则不得违反《仲裁法》的强制性规范。
基于此,仲裁规则只不过是对《仲裁法》的拾遗补缺,而不是对《仲裁法》的突破或超越。为此,一方面,中国应以《仲裁法》修订为契机,设置国际商事友好仲裁的专门条款。2021年7月30日,司法部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修订)(征求意见稿)》,借此契机,建议修订《仲裁法》中的涉外仲裁特别规定,借鉴《示范法》第28条第3款,设置国际商事友好仲裁的专门条款。另一方面,有必要完善自貿区地方立法或规章,为自贸区国际商事友好仲裁提供支持。
2.公平善意原则的定义较为模糊
国际社会尚未明确权威、统一的公平善意原则的定义。正如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前顾问凯瑟
琳·蒂提所言,“在如此长的时间里,很少有法律概念能够产生持续激烈的争论,但公平善意原则跨越了一个时代,其既是寻求正义的火炬,又滋生分歧”。(Catharine Titi,The Function of Equity in International Law,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21,p.1.)国际法院曾希冀公平善意原则成为解决国际争端的利器,但实际上,由于国际公法领域对于公平善意原则的运用往往掺杂颇多政治因素,致使此种愿望落空。(Catharine Titi,The Function of Equity in International Law,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21,p.vii.)即便是在国际商事仲裁领域,仍罕有学者对公平善意原则进行深度解读。例如,法国学者勒巴尔贝·诺伊特曾对公平善意原则进行解释,即适用理性、效用、和平、道德等标准。(Benoit le Bars,How to Improve the Reliability of the Process of Equitable Arbitration:The French Committee Proposals,International Business Law Journal,Vol.2008:635,p.639(2008).)不过,类似上述观点仍然缺乏深切的挖掘。相较于依法仲裁,国际商事友好仲裁的自由裁量权尤其引发担忧,法国学者艾曼纽尔·维拉德指出:“如果仲裁员对于什么是公平善意的看法压倒了仲裁所追求的正义价值时,友好仲裁将变得极其危险。”(Emmanuel Vuillard & Alexandre Vagenheim,Why Resort to Amiable Composition,International Business Law Journal,Vol.2008:643,p.650(2008).)因此,有必要厘清究竟何为公平善意原则,进而为中国国际商事友好仲裁的实践提供指引。
3.公平善意原则的具体标准尚未确立
中国国际商事友好仲裁的实践案例十分稀少,尤其是自贸区成立以来并无国际商事友好仲裁的案例产生。在中国国际商事友好仲裁的实践案例中最具代表性的为1988年3月9日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对外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的“旅行车合同交货争议案”。但该案年代久远且仅为昙花一现,仲裁员亦并未对公平善意原则进行充分解释与说理。这体现了仲裁实践中国际商事友好仲裁公平善意原则具体标准的缺失。
在“旅行车合同交货争议案”中,申诉人(买方)与被诉人(卖方)签订了一份买卖旅行车的合同,合同是由申诉人的委托人与被诉人谈妥后委托申诉人与被诉人签约成交的。委托人在合同订立之前曾承诺以50万港元作为合同的差价补给被诉人,以便通过降低旅行车的合同价格使合同能够获得当局的核准。合同签订之后,申诉人开出了信用证,但被诉人没有收到50万港元的差额,因此没有交货。申诉人要求被诉人支付合同总金额20%的罚款。仲裁庭认定这是一笔不正常的交易,根据实事求是和公平合理的原则,对申诉人提出的赔偿要求,不能予以支持。(参见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编:《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裁决书选编1963—1988》,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48-151页。)在该案中,仲裁员根据事实,认为因合同条款的规定导致不正常交易的发生,以致于出现了显著的不公,最终仅依靠事实与公平合理原则作出裁决。但十分遗憾的是,仲裁员并未进行十分细致的说理,亦未对公平合理原则的具体标准进行解释。
基于此,有必要明确何为公平善意原则的具体标准。法国学者爱德华·伯特兰指出,在国际商事友好仲裁中,虽然仲裁员享有自由裁量权,但亦应避免出现裁决所依据的标准差异过大的情况。(Edouard Bertrand,From A to B:A Step Forward to a Methodology of Amiable Composition,Romanian Arbitration Journal/Revista Romana de Arbitraj,Vol.8:69,p.70-72(2014).)凯瑟琳·蒂提亦指出,虽然公平善意原则提供了更可塑的框架,但有必要采取一种一致的方式,以同样的方式处理同样的案件,进而实现平等。(Catharine Titi,The Function of Equity in International Law,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21,p.26.)
4.如何进行司法审查
在司法审查过程中,审查国际商事友好仲裁裁决是否违反公共政策是关键要素,但如何界定公共政策、如何运用公共政策对国际商事友好仲裁裁决进行司法审查却并不清楚。
首先,是否违反公共政策是对国际商事友好仲裁裁决进行司法审查的关键要素。国际商事仲裁裁决司法审查指的是内国法院对国际商事仲裁裁决依法作出的法律影响和控制。(参见宋家法:《国际商事仲裁司法审查制度研究》,武汉大学2014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8页。)审查的原则在于维系仲裁意思自治与司法干预的平衡。(参见宋连斌:《仲裁司法监督制度的新进展及其意义》,载《人民法治》2018年第5期,第22页。)一方面,如果法院对仲裁裁决采取过激的审查方式,将变相鼓励败方到法院碰運气,导致仲裁仅仅成为司法审查的前奏,进而丧失其高效的优势。(F. D. J. Brand,Judicial Review of Arbitration Awards,Stellenbosch Law Review,Vol.41:247,p.249(2014).)另一方面,仲裁不可完全脱离法院的司法审查。原因在于,仲裁需要法院的力量与协助,且法院有义务确保仲裁不会被用于不公正的目的。(F. D. J. Brand,Judicial Review of Arbitration Awards,Stellenbosch Law Review,Vol.41:247,p.249(2014).)基于此逻辑,针对国际商事友好仲裁裁决的司法审查的审查事项被严格限定,包括仲裁协议的有效性、仲裁是否符合正当程序、仲裁庭的组成或仲裁程序是否符合仲裁规则、仲裁庭是否越权仲裁,以及裁决是否违反公共政策五方面因素。上海市二中院亦出台了相关意见对此进行规定,(上海市二中院认为:“若适用友好仲裁方式系经各方当事人书面同意,不违反我国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且仲裁裁决符合《自贸区仲裁规则》的规定,在司法审查时,可予以认可。”参见《上海市二中院关于适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仲裁规则〉仲裁案件司法审查和执行的若干意见》第13条。)但其内容较为笼统抽象,且仅强调了仲裁协议的有效性与仲裁裁决是否符合仲裁规则两方面因素。实际上,在前述审查事项中,最值得重视的是仲裁裁决是否违反公共政策这一要素。美国学者劳伦斯·基弗、日本学者寺村信一、英国学者
R.H.克里斯蒂、法国学者艾曼纽尔·维拉德等均重点强调国际商事友好仲裁裁决是否违反公共政策这一事项。(Kiffer Laurence,Nature and Content of Amiable Composition,International Business Law Journal,Vol.2008:625,p.632(2008);Nobumichi Teramura,Ex Aequo et Bono as a Response to the ‘Over-Judicialisation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Kluwer Law International,2020,p.123-150;R. H. Christie,Amiable Composition in French and English Law,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rbitration,Mediation and Dispute Management,Vol.58:259,p.259-264(1992);Emmanuel Vuillard & Alexandre Vagenheim,Why Resort to Amiable Composition,International Business Law Journal,Vol.2008:643,p.647(2008).)究其原因,对于国际商事友好仲裁而言,仲裁协议的有效性、仲裁庭的组成或仲裁程序是否符合仲裁规则、仲裁庭是否越权仲裁等均易于判断,唯有是否符合公共政策这一审查事项,因公共政策本身即缺乏统一的界定标准,并且公平善意原则亦缺乏明确指引,仲裁员的高度自由裁量权会引发对仲裁裁决违反公共政策的担忧。
其次,公共政策尚无准确、权威的定义。这关系到国际商事友好仲裁裁决违背公共政策的衡量尺度。国际商事仲裁的意思自治必须以公共政策为底线,公共政策犹如一面盾牌,捍卫国内良好、普遍的道德观念,根深蒂固的伦理传统和基本的正义原则等。(Catharine Titi,The Function of Equity in International Law,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21,p.29-31.)西班牙学者贾维尔·加西亚·德恩特里亚指出:“公共政策将保护某些价值的神圣性以及正义和道德的最低标准。”(Javier Garcia de Enterria,The Role of Public Policy i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Law and Policy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Vol.21:389,p.392(1990).)但如果对其概念进一步细化,则十分困难。个中缘由在于公共政策的概念不仅国与国之间的差别甚大,并且即便是同一国家,不同的历史时期对公共政策的看法亦并不一致,因此,无论是国际层面抑或是国内层面,均无法进行精准的定义,公共政策甚至被称为法学领域最难以捉摸和分歧最大的概念之一。(Javier Garcia de Enterria,The Role of Public Policy i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Law and Policy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Vol.21:389,p.401-402(1990).)
最后,对于国际商事友好仲裁裁决,应当如何衡量其是否违背了公共政策呢?相较于依法仲裁,国际商事友好仲裁裁决的作出必须符合公平善意原则,但目前缺乏对公平善意原则的明确指引,这似乎意味着裁决危及公共政策的风险更高。对于法院而言,如何对国际商事友好仲裁裁决进行司法审查,是十分关键的问题。
四、中国自贸区开展国际商事友好仲裁的对策
为解决前述存在的问题,建议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第一,修订《仲裁法》,增设国际商事友好仲裁专门条款,并对自贸区内的地方立法、规章予以修订。第二,仲裁实践中厘清公平善意原则的定义。第三,仲裁实践中明确公平善意原则的具体标准。第四,法院准确运用公共政策。
(一)完善国际商事友好仲裁立法或规章
建议从两个维度对国际商事友好仲裁进行完善,即修订《仲裁法》,并对自贸区的地方立法或规章进行完善。
1.修订《仲裁法》
建议于《仲裁法》涉外仲裁章节中专门增设国际商事友好仲裁条款,与总则第7条形成特别规定与一般规定的效力。
基于此,应借鉴《示范法》第28条第4款,增设如下条款:“只有获得当事人明确授权,仲裁庭才可按公平善意原则或友好仲裁方式作出裁决。”藉此为自贸区地方立法或规章以及仲裁规则提供法律依据。
2.修订自贸区地方立法或规章
建议修订自贸区地方立法或规章,细化、实施《仲裁法》对国际商事友好仲裁的规定。例如对于仲裁员的选定问题,鉴于国际商事友好仲裁裁決依据的特殊性,其对于仲裁员的要求无疑更高,应当鼓励仲裁机构选定资质优良、专业能力过硬的仲裁员队伍作为推荐名册,同时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的选择,允许其在推荐名册之外选任仲裁员。再如,对于国际商事惯例的适用问题,鼓励仲裁机构适用国际商事惯例裁判案件,在国际商事惯例更为符合公平善意原则时,甚至可优于法律适用。
(二)明确公平善意原则的定义
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一书中指出:“公平有时并非法律的公正,而是对于法律公正的修正。法律的普遍性有时无法顾全所有情况,存在错误的可能性……当普遍适用法律出现了个别的特殊情况时,适当的做法是纠正立法普遍性造成的疏漏。因此,非法律的公正,或许在某些情况下较法律的公正更有优势。”(参见[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王旭凤、陈晓旭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29页。)解读他的观点,笔者认为,所谓“普遍性”与“个别的特殊情况”对应的是全体民众与弱势群体,法律的公正在于兼顾各方利益的平衡,有时忽视弱势群体的特殊诉求,实现的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正,在此种情形下,道德公正等非法律的公正或许较之法律公正更有优势,更加利于实现资源分配的公平。
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得到了后世的传承。首先,从哲学层面来看,中世纪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在亚里士多德的论述基础上,将公平的价值进一步廓清,即将规范的公平与自然正义价值如“仁慈”“人道主义美德”“明爱”等连结。(Catharine Titi,The Function of Equity in International Law,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21,p.23.)此外,近代著名哲学家罗尔斯在其著作《正义论》中对于公正进行了论述,罗尔斯对于公平的本质的阐述与亚里士多德的论述同出一辙。罗尔斯运用著名的正义二原则阐释公平的本质,即“权利平等自由原则”与“社会与经济利益分配原则”。其中,“社会与经济利益分配原则”指出,社会与经济利益的分配,应当兼顾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参见[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页。)其次,从法学层面来看,凯瑟琳·蒂提指出:“公平于国际法中的作用一方面是纠正正义、补充正义,指的是在法律规则缺失、显著不公时,追逐个案正义价值的作用。另一方面则彰显了分配的正义,指的是社会资源的分配、利益与负担的分配,实现一种类似于代际公平的正义。”(Catharine Titi,The Function of Equity in International Law,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21,p.12.)日本学者寺村信一指出:“虽然国际商事友好仲裁不可避免地需在裁决中确定胜者,但公平善意的理念不是要确定某件事是绝对正确还是错误,而是要决定各方之间的优势与劣势分配,因此仲裁庭必须在一定程度上考量败者的利益。”(Nobumichi Teramura,Ex Aequo et Bono as a Response to the ‘Over-Judicialisation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Kluwer Law International,2020,p.178-179.)
综上所述,在国际商事友好仲裁中,公平善意原则侧重对弱势群体的保护,注重于社会资源分配的整体公正,即便是这种保护从表面上看似乎并不公正。
(三)明确公平善意原则的具体标准
有必要汲取《国际商会法国工作组的友好仲裁报告》的合理标准,为仲裁员的自由裁量提供边界与指引,借此防范仲裁员超越必要限度,甚至违背公共政策的行为发生。
根据《国际商会法国工作组的友好仲裁报告》,“为追求公平善意,经授权的仲裁庭可作出以下行动:一是保护那些当事人,他们的意思表示可能不算完善,但并非完全无效;二是处罚那些当事人,尽管他们并非疏忽大意,但显然构成粗心大意,或者他们尽管并未出于恶意,但显然过于循规蹈矩、墨守陈规;三是当情形完全由一方控制时,采取措施以达到公平;四是灵活、自由地调整时效,可以中止或中断时效,甚至拒绝法律规定的时效;五是将赔偿范围扩大到间接或不可预见的损失;六是如果法律并不完全认可某一方所施行的减损行为时,考虑其所做的努力;七是承认责任限制,即便所系法律行为是有缺陷的且不符合责任限制的有关法律规则;八是在合同履约困难的情况下,即便不符合不可抗力的法律规则,也可视为不可抗力的情形;九是修改合同中规定的违约利率。”(Edouard Bertrand,Amiable Composition:Report of the ICC France Working Group,International Business Law Journal,Vol.2005:753,p.762-763(2005).)不过,上述列举并非是穷尽的,仲裁庭完全可以根据自由裁量权加以判断并运用。
值得一提的是,在参考上述标准运用公平善意原则时,为避免自由裁量超过必要限度,仲裁员有必要进行充分论证与说理。加拿大学者约翰·E.C.布莱利指出:“公平善意原则的自由裁量将受到个人良知、正义理念的影响。”(John E. C. Brierley,‘Equity and Good Conscience and Amiable Composition in Canadian Arbitration Law,Canadian Business Law Journal,Vol.19:461,p.465(1991).)显然,此种过强的主观因素将造成一定的不可预测性与风险。(Ahmet Cemil Yildirim,Amiable Composition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Journal of Arbitration Studies,Vol.24:33,p.37(2014).)美国学者威廉·W.派克亦指出,对于仲裁员而言,争议的解决不应根据仲裁员对于结果的倾向性或者兴趣,而是应当根据争议的是非曲直。(William W.Park,Rectitude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Arbitration International,Vol.27:473,p.475-480(2011).)既然如此,仲裁员有必要在国际商事友好仲裁裁决中,明确运用公平善意原则的逻辑进路,阐释如何运用公平善意原则实现个案正义、保护弱势群体,藉此作出令当事人信服的仲裁裁决。
(四)法院准确运用公共政策
为准确衡量国际商事友好仲裁裁决是否违反公共政策,有必要廓清公共政策的内涵与外延,进而指出实践中司法机关应当如何运用公共政策对国际商事友好仲裁裁决进行司法审查。
1.廓清公共政策的内涵与外延
针对国际社会目前并无关于公共政策的统一、权威的界定的现实,笔者认为,违反公共政策的内涵可定义为,违反中国法律基本原则、侵犯中国国家主权、危害社会公共安全、违反善良风俗等足以危及中国根本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其中,必须涉及社会上不特定的多数人利益,至于仲裁结果不公、涉及国有资产、仲裁员并未正确理解法律等并不构成对中国公共政策的违反。
至于外延,可以梳理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对于下级法院拒绝承认与执行仲裁裁决请示的复函,通过肯定式列举与否定式列举方式廓清公共政策的外延。(参见何其生:《国际商事仲裁司法审查中的公共政策》,载《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7期,第147-148页。)
第一,肯定式列举方法。在2010年复函中,最高人民法院将违反中国的公共政策的情形限于违背中国基本法律制度,以及危及中国根本社会利益的情形。(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不予承认日本商事仲裁协会东京07-11号仲裁裁决一案的请示的复函》([2010]民四他字第32号)。)在2013年复函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违反公共政策的情形,应当理解为违背中国法律基本原则、侵害中国国家主权、危及社会公共安全、有违善良风俗等足以危害中国的根本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申请人Castel Electronics Pty Ltd.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一案请示的复函》([2013]民四他字第46号)。)
第二,否定性列举方法。对此,通过梳理最高人民法院对于下级法院拒绝承认与执行仲裁裁决请示的复函,可以归纳出以下情况下并不属于违反公共政策的情形:一是仲裁结果显失公平;二是争议事项的不可仲裁性;三是错误理解或适用法律;四是案件涉及国有资产;五是案件涉及强制性法律规则。(参见何其生:《国际商事仲裁司法审查中的公共政策》,载《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7期,第147-148页。)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公共政策的内涵与外延,应当作出限缩性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在两个复函中均明确了这一要旨,其目的在于避免对于公共政策的滥用。(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韦斯顿瓦克公司申请承认与执行英国仲裁裁决案的请示的复函》([2012]最高法民四他字第12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就申请人帕尔默海运公司与被申请人中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一案请示的复函》([2018]最高法民他140号)。)此种谨慎态度符合国际通行做法,即合理运用公共政策。国际法协会发布的《关于公共政策作为拒绝执行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工具的临时报告》指出,司法审查机构必须维系平衡,一方面,防止裁决违反公共政策;另一方面,也应尊重仲裁裁决的最终结果。(Audley Sheppard,Interim ILA Report on Public Policy as a Bar to Enforcement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l Awards,Arbitration International,Vol.19:217,p.217(2003).)总之,只有当仲裁裁决明显违反了一国神圣不可侵犯的、不惜一切代价维护的社会公共利益时,方能撤销、拒绝承认与执行仲裁裁决。
2.合理运用公共政策对国际商事友好仲裁裁决进行司法审查
追根溯源,国际商事友好仲裁司法审查中最为关键的要素即为裁决是否违反了公共政策。相较于其他仲裁形式,国际商事友好仲裁裁决的特殊性在于其裁决依据的特殊性,根据前文总结的裁决依据,仲裁员可在符合公平善意原则的前提下,在个案中对法律、国际商事惯例以及合同条款的运用进行修正,使裁决符合公平善意原则,甚至,仲裁员可仅依赖公平善意原则作出裁决。在此过程中,固然前述已经明确了公平善意原则的定义与具体标准,但仍需衡量是否违背了公共政策的底线,分为以下两种情况。
第一,如果运用法律、国际商事惯例或合同条款裁决符合公平善意原则,那么,可以按照惯常做法检视裁决是否违反了公共政策。此种情况下,法院对于国际商事友好仲裁裁决是否违反公共政策的审查与对其他形式的仲裁裁决的审查并无区别。
第二,如果在个案裁决中,按照公平善意原则对法律、国际商事惯例或合同条款的运用进行了修正,甚至仅运用公平善意原则作出裁决,此时仲裁裁决的可预测性稍低,法院应当重点审查据此作出的仲裁裁决是否违反了公共政策。一方面,如果仲裁裁决确系触碰了中国公共政策的底线,如侵犯中国国家主权、危害社会公共安全、违反善良风俗等,可撤销或不予承认与执行该国际商事友好仲裁裁决。另一方面,如果裁决仅涉及当事人之间的私益,而不涉及社会上不特定的多数人的利益,如仅对利率、损害赔偿范围修正,使诉讼时效中断、中止或延长,改变不可抗力与责任限制的适用条件,以及存在其他对合同关系进行平衡的举措,那么,不应当仅据此认定裁决违反了公共政策。即便上述修正违背了强制性法律规则,但未必与公共政策相悖。如最高人民法院复函所述,法律强制性规定与公共政策并不是同一概念。(参见何其生:《国际商事仲裁司法审查中的公共政策》,载《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7期,第154-155页。)正如国际法协会发布的《关于公共政策拒绝执行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工具的临时报告》所指出的那样,公共政策是一国最后的安全阀,仅在有可能违反一国最基本的道德和正义概念时,法院方可以违反公共政策为由拒绝执行外国仲裁裁决。(Audley Sheppard,Interim ILA Report on Public Policy as a Bar to Enforcement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l Awards,Arbitration International,Vol.19:217,p.219(2003).)
五、结语
通盘致思,中国自贸区开展国际商事友好仲裁的动因在于探索与国际接轨的争议解决途径,契合商事纠纷国际化与多元化发展趋势。笔者旨在探寻国际商事友好仲裁的完善路径,从立法层面,建议修订《仲裁法》,新增国际商事友好仲裁条款,化解国际商事友好仲裁上位法缺失的癥结,并修订自贸区地方立法或规章,为国际商事友好仲裁提供更加具体、可操作的下位法指引。从实践层面,聚焦解决仲裁实践中如何界定公平善意原则、厘清具体标准,以及法院如何对国际商事友好仲裁裁决进行司法审查三个问题。在公平善意原则的定义界定方面,公平善意原则侧重于保护弱势群体利益,注重于实现社会资源分配的整体公正,即便是这种保护从表面上看似乎并不公正。在公平善意原则的具体标准方面,可立足于中国实践,缕析域外先进经验,并借鉴《国际商会法国工作组的友好仲裁报告》。在对国际商事友好仲裁裁决进行司法审查方面,鉴于公平善意原则的运用可能会带来仲裁员的自由裁量边界的扩张与裁决可预测性的下降,因此审查仲裁裁决是否违背公共政策是关键问题。有鉴于此,廓清公共政策的内涵与外延,合理运用公共政策对国际商事友好仲裁进行司法审查,有利于维系仲裁意思自治与司法干预的有效平衡,防范司法审查工具的滥用。
收稿日期:2022-11-07
基金项目:2020年度辽宁省社科规划基金重点项目“辽宁自贸区多元化争议解决机制运用区块链的问题研究”(L20AFX005)
作者简介:王淑敏,女,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银澄,男,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国际法专业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