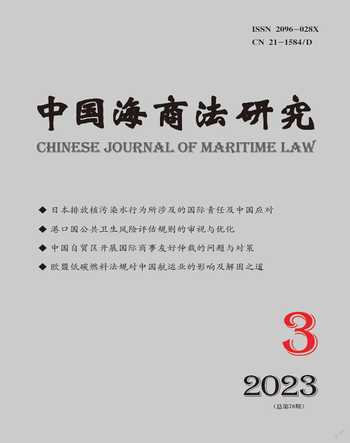海上公共卫生治理国际法困境及完善路径研究
摘要:海洋既是连接世界、承载全球供应链的桥梁,也是公共卫生风险的传播途径。海上公共卫生治理是涉及疾病预防控制、航运畅通、贸易自由与人权保障的全球治理问题,而非单纯的卫生技术问题,要求在全球治理层面塑造多重面向。海上公共卫生治理国际法困境的凸显,呼吁价值共识与理念革新以调和多领域交叉下的国际法价值冲突,完善国际法制度以摆脱主权国家主导下的国际法执行窘境,健全国际合作机制以打破多元主体参与合作的壁垒。中国在海上公共卫生治理中要体现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国际法意蕴,统筹推进海上公共卫生领域的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
关键词:海上公共卫生;多重面向;国际法困境;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D993.5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028X(2023)03-0049-10
Study on the Dilemma and Improvement of International Law on Maritime Public Health Governance
PENG Yu
(School of Law,Shanghai Maritime University,Shanghai 201306,China)
Abstract:The ocean serves as the entry point to the global supply chain. Public health risks can also be transferred via ocean. Maritime public health is a matter of global governance, not only health technology.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shipping unimpeded, trade freedom, and human rights protection are all aspects of maritime public health governance. The dilemma of international law on maritime public health governance, calls for value consensus and idea innovation so as to harmonize the value conflicts in international law in the context of multidisciplinary cross, improvement of the system of international law to get rid of a lack of collective action in the execu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as currently dominated by sovereign states, and perfection of the mechanism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o break the barrier to the multiple participation in cooperation. China needs to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the cooperation and governance of maritime public health, reflect the international law implication of a community of common health for mankind, and promote the domestic rule of law and foreign rule of law in the field of maritime public health.
Key words:maritime public health;multiple aspects;dilemma of international law;a community of common health for mankind
全球化進程不断深入增进了国际社会的相互依赖关系,也促使全球性问题凸显,其中就包括全球公共卫生问题。由于航运的国际性与病毒的无国界性高度重合,海上公共卫生天然属于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重要对象。新冠疫情不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也绝不是最后一次传染病大流行。新冠疫情不再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并不意味着海上公共卫生问题的结束。传染病给海上公共卫生带来的威胁不会就此停歇,无法预知传染病的再次全球大流行会在何时到来。新冠疫情暴发后,近100个国家和地区曾关闭了海上边境,以阻止新冠病毒通过海上渠道入侵。海上公共卫生涉及公共卫生、航运、贸易、人权等多个领域,存在大量冲突解决与协调治理的需求。疫情对于航运业和集装箱港口造成了冲击,挑战其适应能力;(Theo Notteboom,Thanos Pallis & Jean-Paul Rodrigue,Disruptions and Resilience in Global Container Shipping and Ports:the COVID-19 Pandemic Versus the 2008—2009 Financial Crisis,Maritime Economics & Logistics,Vol.23:179,p.179(2021). )国际法规则下“邮轮困境”的凸显,(参见吴蔚:《国际法规则的“邮轮困境”与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建设》,载《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04年第4期,第55页。)引发了对国际客轮运输安全立法的讨论,(参见陈琦、蔡楠:《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中的国际客轮运输安全立法:制度审视与规则重构》,载《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第1页。)而国际邮轮中疫情预防和控制的法律争议有待解决;(ZHANG Xiaohan & WANG Chao,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COVID-19 Pandemic on International Cruise Ships:The Legal Controversies,Healthcare,Vol.9:281,p.281(2021). )国际贸易与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参见时业伟:《新冠肺炎疫情下国际贸易规则与公共卫生治理的链接》,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21年第2期,第136页。)疫情对海员休假、遣返、医疗援助等权利造成了破坏,(Anish Arvind Hebbar & Nitin Mukesh,COVID-19 and Seafarers Rights to Shore Leave,Repatriation and Medical Assistance:A Pilot Study,International Maritime Health,Vol.71:217,p.217(2020). )大量船员换班、遣返等合法权益难以实现。(参见陈鹏:《新冠病毒肺炎疫情下的船员权益保障问题》,载《中国海事》2020年第4期,第20页。)
针对海上公共卫生治理面临的挑战,不同学者从多角度出发进行了分析。有学者从全球卫生治理角度讨论了分隔世界中国际法和公共卫生问题,重点提到海洋作为联通世界的媒介,需要进行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法律应对;(Yves Beigbeder,Global Health Governance: International Law and Public Health in a Divided World,tudes Internationales,Vol.37:306,p.306(2006).)有学者从国际法以及合作机制的维度,探讨推动并完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机制的建设,(参见刘晓红:《国际公共卫生安全全球治理的国际法之维》,载《法学》2020年第4期,第19页。)而邮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从全球卫生治理角度来说,需要全球合作治理;(Richard Pougnet,Laurence Pougnet,et al.,COVID-19 on Cruise Ships:Preventive Quarantine or Abandonment of Patients,International Maritime Health,Vol.71:147,p.147(2020). )有學者分析了涉疫邮轮停靠沿海国家港口时,沿海国家可以选择的治理公共卫生风险的法律框架;(Anne Choquet & Awa Sam-Lefebvre,Ports Closed to Cruise Ships in the Context of COVID-19:What Choices Are There for Coastal States,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Vol.86:1,p.1(2021). )有学者研究了邮轮拒载的非法性和原因,提出了国际法下的全球邮轮旅游治理机制;(HU Zhengliang & LI Wenwen,Global Health Governance on Cruise Tourism:A Lesson Learned from COVID-19,Frontiers in Marine Science,Vol.9:1,p.1(2022).)有学者对《国际卫生条例(2005)》[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s [QX(Y10]([QX)]2005[QX(Y10])[QX)],简称IHR 2005]中涉及人权保护的关键条款进行了梳理和分析;(Bruce Plotkin,Human Rights and Other Provisions in the Revised 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s [QX(Y10]([QX)]2005[QX(Y10])[QX)],Public Health,Vol.121:840,p.840(2007).)有学者认为后疫情时代,有关海上公共卫生安全的防控治理,需要应对人类活动与海洋环境保护的冲突、主权与人权的冲突、国际法规则碎片化、国家履约中的能力不足与意愿欠缺、国际组织权利受限及职能欠缺等挑战。(参见白佳玉、李玉达、王安娜:《后疫情时代海上公共卫生安全法治的挑战与中国方案》,载《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第54页。)
海上公共卫生具有全球性、公共性和综合性的特征,是典型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问题。全球化时代需要全球治理,而全球治理的最佳路径是法治化。(参见姚金菊:《全球行政法的兴起:背景、成因与现状》,载《环球法律评论》2015年第4期,第110页。)然而,以IHR 2005为核心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在海上公共卫生治理上仍有诸多需完善的空间,呼唤国际综合法治及多层次全球合作以协同解决问题。鉴于此,笔者从海上公共卫生在全球治理下的多重面向出发,分析海上公共卫生治理的国际法困境,探索海上公共卫生治理理念革新及完善路径,提出中国因应,以期提升海上公共卫生治理成效,为更好应对传染病再次流行造成的海上公共卫生问题提供智力支持。
一、海上公共卫生:全球治理下的多重面向
全球化趋势下,传染病的威胁不再局限于各国边界,公共卫生问题由单纯的国内事件演变成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参见陈颖健:《公共卫生问题的全球治理机制研究》,载《国际问题研究》2009年第5期,第54页。)国际公共卫生是涉及国际秩序、经贸合作与公共安全的全球治理问题,而非单纯卫生技术问题。国际卫生治理的根基并非人道主义,而是有关疾病的国际政治。(David P. Fidler,International Law and Infectious Diseases,Clarendon Press,1999,p.279.)海洋既是连接世界、承载全球供应链的主要桥梁,也是风险传播的渠道之一。任何传染病都可能随海上供应链的延伸而扩散到全球各地。在疾病预防控制、航运畅通、贸易自由与人权保障等多领域间寻求平衡和妥协,始终是海上公共卫生治理的核心关切。多领域交叉带来的多元价值冲突和矛盾的应对与解决,要求在全球治理层面塑造海上公共卫生的多重面向。
首先,疾病预防控制要求在全球治理层面塑造海上公共卫生的秩序性面向。面对传染病全球大流行,主权国家通过各种途径获取信息,对外来船舶和海上人员往往采取隔离和限制入境等措施以切断病毒跨洋传播途径,防止疫情向国内扩散。然而,传染病全球大流行造成的是系统性影响,海上公共卫生治理对象不局限于单一领域。为保障公共卫生秩序而采取的措施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国际交通,港口拥堵、船舶靠港困难及国际航班短缺等情况时有出现。一方面,船员超期服务、换班难的现象在传染病全球大流行期间持续存在。新冠疫情暴发后的一段时间内,根据国际航运公会估计,约25万名船员滞留,在船服务时间远远超期。(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Review of Maritime Transport 2021,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2021,p.14.)同时,邮轮上染疫乘客无法及时靠岸就医,包括健康权在内的人权无法得到保障。另一方面,国际航运受阻的同时,国际贸易也无法幸免。新冠疫情的冲击导致海上贸易在2020年收缩了3.8%。(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Review of Maritime Transport 2021,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2021,p.21.)
其次,海上人员人权保障要求在全球治理层面塑造海上公共卫生的保障性面向。人权是全球治理的基本价值理念,(参见蔡拓、杨雪冬、吴志成主编:《全球治理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82页。)健康权作为基本人权的一种,是人人所享有的普遍性权利,是受到国际法保护的重要价值之一。在卫生法领域中,生命健康权保障原则是卫生法的核心理念和最高价值。(参见解志勇:《卫生法基本原则论要》,载《比较法研究》2019年第3期,第8页。)由于海洋环境的特殊性以及国际社会对海上人员健康权的关注度和保护力度不足,海上人员健康权受到侵犯时得不到救济。一旦传染病全球大流行短时间内无法有效控制,长期处于工作状态的船员个体极易面临传染病威胁和心理打击的双重困扰。整体性身心健康是公众正常参与社会生产活动和实现个人价值的基础条件与普遍共识。采取海上公共卫生治理措施难免影响到个人权利的实现。但是,群体健康与个体健康并不对立,群体健康需要在个体健康得到普遍保障的基础上才能实现。
最后,国际航运畅通和国际贸易自由要求在全球治理层面塑造海上公共卫生的包容性面向。传染病全球大流行期间,国际航运畅通和国际贸易自由受到疫情防控措施收紧和贸易保护措施升级的双重压力。国际航运作为国际运输的重要交通方式,是全球供应链的基础,通过其运输的货物占全球商品贸易量的80%以上和货值的70%以上。(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COVID-19 and Maritime Transport:Impact and Responses,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2021,p.11.)根据基尔贸易指数,(基尔贸易指数:基于对船舶运动数据进行实时评估的指数,记录全球500个港口的抵港和离港船舶数据,从吃水信息中推导出集装箱船的有效利用情况。)2022年,全球约有11%的货物滞留在集装箱船上,(Kiel Trade Indicator 04/22:World Trade Stabilizes,Kiel Institute for the World Economy(5 May 2022),https://www.ifw-kiel.de/publications/media-information/2022/kiel-trade-indicator-0422-world-trade-stabilizes.)材料的短缺会阻碍生产和运输的进行。疫情对全球供应链的地理配置产生极大的影响,不仅割裂了全球供应链,也使得国际航运和国际贸易遭受重创。以往依赖于国际贸易、国际航运进行流转的全球公共卫生产品、原材料、生产要素等的进出口活动受到限制。传染病全球大流行将会增加国际航运和国际贸易的难度,也增加了全球货物生产分布的不确定性,压缩了全球供应链的参与空间。此时,区域性的贸易组织显得十分重要,为保持、维护供应链的完整性和自主可控性,各经济体将更加重视双边贸易组织或多边贸易组织的建设,世界的区域经济合作将增强。(参见陈永森、张埔华:《以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助推全球化进程》,载《国外社会科学》2021年第1期,第17页。)供应链的区域化成为当前降低风险较为普遍的举措,疫情导致全球供应链的缩短,而区域化交易的不断发展使美洲、欧洲和亚洲将把重点逐渐转向区域内部的自给自足上,而不是依赖此前作为全球化代表的遥远且错综复杂的全球供应链。(参见[德]克劳斯·施瓦布、[法]蒂埃里·马勒雷主编:《后疫情时代:大重构》,世界經济论坛北京代表处译,中信出版社2020年版,第59页。)
二、海上公共卫生治理的国际法困境及成因
国际公共卫生治理背后是政治经济学问题,其不仅仅是卫生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权力、资源和利益的再分配问题。(参见陈一峰:《健康主义抑或安全主义?反思全球卫生法的理论基础》,载《国外社会科学》2021年第4期,第82页。)为防止疾病国际传播所采取的隔离、限制等措施极有可能会干扰国际交通便利和海上人权保障。这需要国际社会公认的国际法予以保障与协调。海上公共卫生治理涵盖的不同领域均建立了较成熟的国际法体系。公共卫生领域中,海上公共卫生治理仍受到IHR 2005的调整。人权保障领域中,多个国际公约对公共卫生治理中的人权保障都予以规定,如《世界卫生组织组织法》《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等。国际航运领域中,海洋、海事有关国际法对海上公共卫生治理也有着良好的指引作用,如《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便利国际海上运输公约》等。国际贸易方面,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简称WTO)框架下的国际法体系也包含公共卫生与国际贸易问题的处理,如《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关于卫生与植物检疫措施的协议》等。其他领域的国际法通过多种方式和途径对公共卫生领域的国际法加以扩张和渗透。多领域国际法相互叠加,缔约国难以明确自身责任,无力或无法履行冗杂甚至矛盾的义务。强有力的国际机制的缺失致使IHR 2005在执行过程中面临极大的挑战,加之主权国家国际合作积极性不强,现行海上公共卫生治理面临诸多国际法困境。
(一)多领域交叉下的国际法价值冲突困境
海上公共卫生治理不同领域有着不同的价值期待。不同领域的国际法在发展过程中更多考虑的是自身领域国际法价值更好地实现,缺乏沟通和交流。随着全球化进程不断深入,彼此间的互动愈加频繁,其中难免会产生摩擦和矛盾。面对传染病的冲击,多领域交叉下的国际法价值冲突可能会更加尖锐。
IHR 2005允许各国基于科学原则和科学证据采取额外卫生措施,给予主权国家自主权的同时也加剧了不同国际法价值之间的冲突。IHR 2005将“充分尊重人的尊严、人权和基本自由”作为首要原则。IHR 2005第2条中指出其目的之一是避免对国际交通和贸易造成不必要的干扰。并且,第28条第1款规定,除第43条或适用的国际协议另有规定外,不应当因公共卫生原因而阻止船舶或飞机在任何入境口岸停靠。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简称WHO)也一再强调采取额外卫生措施的必要性与适度性,然而一旦发生公共卫生问题,一些国家倾向于采取过度限制措施。(参见周阳:《〈国际卫生条例(2005)〉的法理冲突与规则重构》,载《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报》2020年第6期,第73页。)一些国家在防控传染病跨国传播过程中,往往
优先考虑本国利益而无视相关国际法的规定。(参见徐军华:《国际航空旅行限制措施在“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情势下的适用》,载《政法论坛》2021年第2期,第101页。)面对传染病全球大流行,国际航运受阻、国际贸易受限、海上人员健康权难以保障的情况在海上公共卫生治理中屡见不鲜。缔约国对多领域交叉下的国际法价值冲突的解决不尽如人意,国际法履约程度仍有待提升。
首先,在人权保障方面,健康权作为基本人权的一种,在海上公共卫生治理中应当受到国际社会的重点关注和保护。《世界卫生组织组织法》序言中提到,享受可能获得的最高健康标准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之一,不因种族、宗教、政治信仰、经济及社会条件而有区别。《阿拉木图宣言》郑重宣告健康是基本人权。《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明确将健康权规定为公民应当享有的权利,健康权也已被写入大多数成员国的宪法或法律之中。(参见敖双红、孙婵:《“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参与全球卫生治理机制研究》,载《法学论坛》2019年第3期,第153页。)作为船员权利法案的《2006年海事劳工公约》(Maritime Labour Convention, 2006,简称MLC 2006)在总则第4条对船员劳动保障作了明确规定,规则2.4和规则2.5中明确了船员拥有休假与遣返的权利,体现了对船员健康的保护。为防止传染病跨洋传播,港口国、沿海国等国家采取额外卫生措施难免会对海上人员正常入境、治疗、遣返造成限制,船员基本的换班权利也无法得到保障。海上人员包括健康权在内的人权难以实现。
其次,在国际航运方面,海上运输的便携与效率受到海上公共卫生治理的影响。《便利国际海上运输公约》第1条规定,缔约国“保证采取一切适当措施,以便利和加快国际海上运输,防止对船舶及船上人员和财产造成不必要的延误”。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9条、第21条、第25条中的相关规定,沿海国可以采取必要措施禁止违反本国公共卫生国内法的船舶通过其领海。《国际海港制度公约与规约》第17条中提到港口国可基于国家公共卫生安全的考量,拒绝相关人员及货物过境。这些国际法为港口国、沿海国等国家拒绝涉疫船舶靠港提供了制度性支持。船舶流动受阻无疑会阻碍国际航运畅通,进而影响国际贸易自由进行。
最后,在国际贸易方面,WTO框架下的国际法体系中,《WTO协议》允许公共健康问题成为其自由贸易规则的例外。(参见黄骅:《“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视角下的若干国际贸易法律问题》,载《上海商学院学报》2021年第1期,第115页。)《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第20条提到,允许缔约国采取为保护人类、动物或植物的生命或健康所必需的措施。根据《实施动植物卫生检疫措施的协议》第2条第2款规定实施的贸易限制措施,不得超过为保护人类、动物或植物的生命或健康所必需的限度。但是,传染病全球大流行极易导致各国实施贸易限制举措和禁航禁运管制,这将直接破坏WTO框架下的国际自由贸易规则体系。(参见沈国兵:《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及纾解举措》,载《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0年第7期,第85页。)国际贸易受限会造成海上公共卫生治理医疗、食品等必需物资的短缺,影响整体治理进度。
海上人员健康权实现、国际航运畅通、国际贸易自由在今后仍然会受到传染病全球大流行的影响。缔约国海上公共卫生治理能力、价值追求和局势判断有所差别,所采取的防疫措施也存在差异。适用额外卫生措施仅是海上公共卫生治理的手段之一。不同领域国际法价值之间的协调本就充满挑战,在特定时期,更要注意动态平衡的实现,避免某一价值的过度牺牲。
(二)主权国家主导下的国際法执行困境
主权国家是全球治理的主要实施主体。(参见蔡拓、杨雪冬、吴志成主编:《全球治理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13页。)海上公共卫生治理需要主权国家主动参与。海上公共卫生治理中,国家主权
的让渡以及国家利益在一定程度上的损失,引起部分主权国家对国际合作的抵制,导致海上公共卫生治理的集体行动和缔约国的国际法履约程度明显不足。现有的国际体系中不存在一个超国家的组织对主权国家是否遵守国际法进行严格的监督。《联合国宪章》确立了国家主权平等原则,各国须互相尊重主权与领土完整。WHO缺乏有效途径对额外卫生措施的科学性及必要性进行评估,IHR 2005约束力不足和监管惩戒机制的缺失导致其对主权国家不履约的情况束手无策。
一方面,主权国家在额外卫生措施的实施、内容、程度等方面有极大的自主权,即便IHR 2005第43条规定额外卫生措施一旦对国际交通造成了明显干扰,需要在采取措施后的48小时内向WHO通报。新冠疫情暴发后,在WHO发布的第18号情况报告中,72个缔约国实施了额外卫生措施,只有23个(32%)向WHO进行了通报。(WHO,Novel Coronavirus(2019-nCoV) Situation Report-18,WHO(7 February 2020),https://www.who.int/docs/default-source/coronaviruse/situation-reports/20200207-sitrep-18-ncov.pdf?sfvrsn=fa644293_2.)在第50号情况报告中,仅有45个国家进行了通报并说明了理由,实施额外卫生措施的主要原因是国家能力有限,缺乏应对能力以及病毒相关情况的不确定。(WHO,Corona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 Situation Report-50,WHO(10 March 2020),https://www.who.int/docs/default-source/coronaviruse/situation-reports/20200310-sitrep-50-covid-19.pdf?sfvrsn=55e904fb_2.)这些理由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必要性难以验证。另一方面,IHR 2005约束力不强,难以对缔约国履约情况进行监督,削弱了WHO在公共卫生领域的领导力。此次新冠疫情期间,尽管WHO在临时性建议中多次强调不赞成采取旅行或贸易禁令,然而,部分缔约国选择性无视甚至拒绝采纳,究其原因,IHR 2005在第15条中虽然授权WHO总干事对缔约国拟采取的卫生措施发布临时性建议,但也赋予了缔约国采取额外卫生措施的权利。在充分尊重各成员国国家主权的同时,也增加了主权国家在处理公共卫生问题上的随意性,临时建议是否执行完全取决于缔约国意愿。仅寄希望于缔约国的自觉遵守而没有监督执行机制难以发挥WHO在公共卫生上的领导性作用。
(三)多元主体参与下的国际合作机制实施困境
国际合作是海上公共卫生治理的重要手段。船舶在海上遭遇传染病暴发时援救难度高,需要一定的综合实力。由于治理理念的分歧和治理水平的参差,相关国家相互推诿援救责任,难以形成全球范围的统一行动,不能集体应对并解决其带来的风险,增加了海上公共卫生的治理难度。
1.海上援救责任分配不明
船舶在海上遭遇传染病暴发时援救责任难以明确。“钻石公主”号邮轮遭遇新冠疫情后,港口国和船旗国对海上人员的处理和安置情况并不理想。海上人员的国籍所属各有不同,在海上这样的特殊环境中,国籍所属国开展援救有一定难度,在特定时期也会造成有限资源的过度消耗。《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91条第1款中提到国家与船舶之间必须有真正的联系。船旗国对于航行在公海上的登记在册的船舶有着天然的管辖权,对在海上遭遇公共卫生危机的船舶,需要肩负起其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但是,方便旗制度的兴起,部分开放方便旗船旗登记的国家综合国力有限,难以对登记船舶承担起船旗国应有的责任。
船舶在公海或者他国领海遭遇传染病暴发时,船旗国的援救受距离等现实因素的影响也难以展开。《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和《1989年国际救助公约》在船舶发生海难事故时,对船舶、人命、船上财产的救助有着清晰的界定,但对遭遇传染病暴发的船舶援救未有涉及。现行国际公约中对沿海国、港口国的义务仅有原则性规定,并没有条款明确规定必须对遭遇传染病暴发的船舶进行援救。IHR 2005在第13条和第14条中明确了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WHO与政府间组织和国际机构的合作,在第44条中也规定了各缔约国应负的合作与援助义务。这也仅是原则性的规定,并没有对具体细则作出任何指示。海上开展援救需要具备一定的经济实力和援救能力。WHO、国际海事组织(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简称IMO)等国际组织联合船旗国、港口国、沿海国等国家展开国际合作,对参与国的综合国力也是极大的考验。
2.治理水平参差,合作意愿欠缺
各国治理理念和水平参差不齐,制约着海上公共卫生治理国际合作的可能性。在处理全球卫生问题的过程中,多采取本国利益优先的原则,导致全球卫生治理在理念上难以形成共识。(参见高明、唐丽霞、于乐荣:《全球卫生治理的变化和挑战及对中国的启示》,载《国际展望》2017年第5期,第135页。)一方面,WHO和IMO分别作为国际权威公共卫生和海洋海事领域的多边机构,在海上公共卫生治理中开展合作,这离不开主权国家的支持和落实。各國在海上公共卫生治理中开展合作时,由于信息沟通和交流不够充分,应对策略和行为方式会有所不同。有的国家始终坚持本国利益优先,拒绝国际抗疫合作,甚至退出WHO,不利于国际组织工作的开展。另一方面,IHR 2005附件第1条中关于公共卫生能力的核心要求,对于主权国家港口口岸的公共卫生建设,也是一个巨大考验。部分发展中国家卫生基础设施的资金来源尚且存在较大缺口,技术发展也相对落后,应对港口口岸公共卫生核心能力建设更是捉襟见肘,海上公共卫生治理能力相对欠缺,即使有心也无力参加海上公共卫生援救工作。海上公共卫生治理成效的长期保持,需要世界各国海上公共卫生治理能力的普遍提升。在传染病暴发时,传播风险大、援救成本高、公共卫生建设能力欠缺、合作意愿不强等各种原因削弱了海上公共卫生治理国际合作的可能性。
三、海上公共卫生治理理念革新及路径完善
海上公共卫生国际法在价值冲突、规则执行以及合作机制实施中的困境呼唤新理念、新制度和新机制。其中,理念是制度设计与机制实施的指引,制度是理念的载体,机制是理念有效落实的保障。海上公共卫生治理理念的有效革新具有全局性、先导性的作用,需要首先得到回应。
(一)以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为价值引领
疫情造成的全球性冲击,制约着全球公共卫生事业的可持续发展。疫情的快速蔓延意味着全世界都处在一个休戚相关、唇亡齿寒的共同体中。(参见王瑞、王贤斌:《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视域下全球疫情治理机制创新》,载《理论建设》2021年第2期,第40页。 )海上公共卫生治理不当,海洋就会成为传染病快速扩散的渠道。而其他国际法价值在海上公共卫生治理中也不容忽视。不同国际法价值之间的均衡需要强有力的理论作支撑。理念共识是摆脱全球层面集体行动困境的第一步。立足于全人类公共卫生共同安全及人类健康价值旨趣的角度,以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为价值引领为推动海上公共卫生国际法价值选择提供了一个新思路、新视角。
传染病直接威胁到了人类的生命健康安全,各国人民的生命健康在公共卫生危机面前,都应当得到尊重,无关性别、种族、职业。无论各国的发展模式、发展道路如何,在公共卫生治理方面都应坚持“以人为本”。(参见张守文:《公共卫生治理现代化:发展法学的视角》,载《中外法学》2020年第3期,第592页。)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以维护全人类的生命健康为目标。在海上公共卫生治理中,应以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为价值引领,坚持生命至上、健康至上的价值取向,推动国际法价值选择。因此,主权国家需要将人的生命健康置于优先位置,塑造以人为本、促进健康权普遍实现的共同价值观,以指导海上公共卫生治理。在传染病全球大流行时期,主权国家可以成立国内外专班小组,回应海上人员对于生理、心理健康的合理诉求。在新冠疫情期间,为保障国际航行船员的合法权益,中国交通运输部决定成立国际航行船舶船员换班工作专班,(参见《交通运输部关于成立国际航行船舶船员换班工作专班的通知》,载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网站2022年1月4日,https://xxgk.mot.gov.cn/2020/jigou/haishi/202201/t20220104_3634757.html。)对国际船员换班问题的解决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海上公共卫生治理中,不同国际法价值之间并不是截然对立的。主权国家要看到不同国际法价值相互依存的可能性,抛弃对抗性思维,在求同存异、相互尊重、互学互鉴的基础上,就海上公共卫生治理的关键问题深入对话,共谋长远发展。在抗击新冠疫情的国际合作中,中国用实际行动践行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基本理念和主张,赢得了世界各国的普遍赞誉和认可。(参见齐峰:《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话语和行动》,载《社会主义研究》2020年第4期,第125页。)任何国家、国际组织、群体、个人,在海上公共卫生治理中都是平等的。海上公共卫生治理需要世界各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高度凝聚国际法价值共识。因此,以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为价值引领,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是主权国家形成统一战线合理的路径选择。
(二)强化国际法的制度性效力
在应对不断变化的人类公共卫生问题过程中,公共卫生治理逐步机制化、常态化和全球化,其背后就是以国际法治为基础的规范化、制度化过程。(参见毛俊响:《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需要国际法治》,载光明理论2020年12月30日,https://theory.gmw.cn/2020-12/30/content_34505016.htm。)国际法治是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载体。(参见周婧:《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导下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载《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第161页。)IHR 2005的完善将为构建海上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奠定坚实的国际法基础。主权国家要主动承担国际法下的责任和义务,所采取的措施要受到国际法的限制和约束,参与并推动IHR 2005等国际法的完善和发展。
一方面,建立评估、监督和执行机制。从国际社会整体利益出发,WHO发布临时性建议,协调各国行动。在传染病全球大流行时期,WHO可以联合IMO等其他国际组织相关领域专家建立评估小组,与主权国家保持实时联系与信息沟通,对采取额外卫生措施的科学性和必要性展开调研,协助主权国家改善海上公共卫生治理策略。强化WHO监督和监管能力,开通信息披露与反馈渠道,对于部分国家违背IHR 2005原则采取额外卫生措施或者拒绝履行相关国际法义务,通过一定途径加以提醒,同时搭建信息共享平台将有关信息加以公开,提高缔约国违约成本。WTO争端解决机制被视为有效发挥作用的全球治理机制,但是,它的实施也强烈地依赖于国家之间的相互制约。(参见蔡拓、杨雪冬、吴志成主编:《全球治理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25页。)国家在国际交流中都十分重视自身国际形象,评估、监督和执行机制的建立将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主权国家履约自觉性。
另一方面,采用软硬兼顾的立法结构以便IHR 2005缔约国在海上公共卫生治理中灵活应对,保障IHR 2005规定的原则和权利得以充分实施。海上公共卫生治理所追求的多元价值的实现,需要建立在IHR 2005原则性规定的基础上,充分考虑不同领域国际法价值的协调与平衡,衍生更加具体化的细则,减少适用上的不确定性。IHR 2005对国家主权的让渡,允许缔约国结合实际自主采取额外卫生措施,有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在国际法领域,软法和硬法广泛存在。单纯通过硬法的拘束力在海上公共卫生治理中不能兼顾多元主体的利益,而软法在国际条约中的适用能够顾及到各国国情,利于复杂多样化情况的灵活性处理。MLC 2006将强制性规范与任意性规范编排在统一的规范性文件中。(参见王秀芬主编:《国际劳工组织的船员立法趋势及我国的对策研究》,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47页。)IHR 2005可以参照适用MLC 2006的立法结构,就公共卫生治理中所涉及到的原则性、关键性要求在主要条款中明确提出,对于具体细节和要求则留有一定选择空间,允许主权国家自我管理。
(三)基于国际法的国际合作机制完善
面对全球性的问题,国家和国际组织间需要展开深入而广泛的合作,缓和彼此的对立与冲突,集体应对并解决其带来的风险。国际合作被确立为国际法基本原则之一,贯穿于包括卫生健康在内的国际法各领域。(参见王勇:《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国际法合法性问题》,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1年第5期,第11页。)应以国际法为基础,明确涉疫船舶援救责任分配,提高援救的及时性和有效性。还应践行多边主义,充分发挥国际合作在海上公共卫生治理中的效用。
1.明确海上公共卫生援救责任分配
海上人员的国籍所属国应肩负起应然的援救义务。基于现实考虑,国籍所属国的援救受到空间和时间的限制,就近采取措施才能最大程度保障海上人员的生命健康安全。在海上如不幸遭遇传染病暴发,海上人员援救需要港口国、沿海国开启绿色通道,在采取防疫措施的前提下,为海上人员的救治与遣返提供可行方案。港口国、沿海国因此可能会承受极大的压力和巨额的成本,有关国际组织可以联合世界各国、船公司等募集专项援救资金,对参与海上公共卫生援救且取得一定成效的国家予以特别的经济补偿,提高港口国、沿海国等参与海上公共卫生援救的积极性。
除此之外,船旗国对登记在册的船舶理应承担应然的援救义务,但是,船旗国难以克服距离上的不便及时有效开展援救。涉疫船舶上携带的有限资源也难以支撑到船旗国援救的到来。因此,设立允许涉疫船舶就近靠港的机制更为可行,利于船上人员的妥善安置。在有关国际法的修改和完善中,细化在传染病全球大流行下允许船舶临时停靠的细则,建立对船舶公共卫生风险的科学评估方案。船旗国对船舶应肩负起应然的监管和援救义务,对港口国、沿海国的防疫工作及船上人员遣返工作提供支持。港口國、沿海国应在确保国家公共卫生安全的前提下,科学评判船舶的公共卫生风险,将评估结果作为采取下一步行动的依据,在其能够接受的范围内提供援救。周边国家可联合成立区域性的海上公共卫生援救组织,对于发生在区域内而超出单一国家可控能力的情况及时开展合作援救。
2.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国际合作
海上公共卫生的安全关系到全球性的抗疫成果。世界各国已逐渐承认多边治理的重要性,要求在国际事务中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加强合作、反对一意孤行和霸凌主义,主张通过多边外交共同解决全球卫生问题。(参见沈文辉:《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困境与出路》,载《东方论坛》2021年第1期,第127页。)海上公共卫生治理需要多边主义,单一力量的应对往往是难以奏效的。
在国际机制交叠不断增多、各种全球问题愈加复杂的形势下,国际组织间合作正成为多边合作的新范式。(参见张贵洪:《多边主义、国际组织与可持续的和平发展》,载《人民论坛》2020年第32期,第27页。)海上公共卫生治理决策要兼顾公共卫生的专业性和海洋、海事的特殊性。因此,要加强和发挥不同国际组织的专业性优势,通过协商对话的方式缓解矛盾和冲突,坚定维护WHO在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中的权威和领导地位,吸收IMO对海洋、海事更权威的评估和意见,结合其他国际组织的多样化需要,协调主权国家间的合作,多维度完善海上公共卫生治理。同时,鼓励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等广泛、灵活地参与海上公共卫生治理国际合作,借助它们在各领域专业性、综合性的资源调配、协调能力,填补国际合作的空缺,为海上公共卫生治理提供新的选择。
海上公共卫生治理要充分调动主权国家的参与积极性。主权国家负责国际法贯彻执行和国内公共卫生环境的稳定,只有依靠主权国家才能真正承担起国际法责任并基于国际法落实具体行动。因此,在海上公共卫生治理中,主权国家首先要切实履行IHR 2005等国际法下的义务,结合实际作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提高履约程度。在此过程中,对于需要协调的问题,主权国家应以平等和包容的心态,通过谈判协商的方式,积极开展国际合作,共同寻找突破口。部分主权国家由于发展水平滞后导致能力有限,易成为全球海上公共卫生整体治理的薄弱点,WHO、IMO等国际组织可联合有关方募集专项资金,统筹资源予以必要的资金和技术援助。海上公共卫生治理成效的维持有赖于世界各国海上公共卫生治理能力的普遍提高。
四、海上公共卫生治理的中国因应
新冠疫情发生以来,中国不仅贡献了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创新及相关行动倡议,更是以实际行动分享抗疫经验、援助医疗物资、携手科研攻关,提升了中国在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中的影响力和参与度。同样,在海上公共卫生治理中体现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国际法意蕴,发出中国声音、作出中国贡献,既是中国深入参与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提升国家影响力的契机,也是在海上公共卫生领域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的重要途径。
(一)体现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国际法意蕴
中国在海上公共卫生治理中,要体现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国际法意蕴。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以人类的共同利益为出发点,以维护全人类的生命健康为目标。在应对新冠疫情上,中国始终坚持将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安全放在首位,将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作为参与公共卫生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必要时适度牺牲局部利益换取一个稳定而长效的良性公共卫生环境,(参见刘雁冰、马林:《〈国际卫生条例〉在新冠疫情应对中的困境与完善》,载《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第121页。)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佳的抗疫成效。实践证明,中国面对新冠疫情的防控政策和措施是科学有效且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中国在海上公共卫生治理中,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对人的生命健康的重视放在优先位置。世界各国人民的生命健康在海上公共卫生治理中都应当得到尊重。天津港快速且妥善处理了“歌诗达赛琳娜”号邮轮靠港,船上外籍人员的基本权利得到了有效保障。为应对船舶防疫,中国率先颁布了《船舶船员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操作指南》并经由IMO向国际社会推广,给各国船员在工作期间的疫情防护提供了行动指引,充分保护了各国船员在船工作的生命健康。同时,中国积极履行国际义务,尽己所能提供医疗援助。
中国以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为指引,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同国际社会进一步深化海上公共卫生治理国际合作。第一,深化海上公共卫生治理区域合作。通过与周边国家建立海上公共卫生风险区域预警机制,促进区域内的联防联控,共同探讨和协商解决区域内所面临的海上公共卫生治理问题。第二,搭建多层次、多方位的国际合作平台。充分利用“一带一路”、上海合作组织等国际平台的作用,引导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等共同参与。第三,积极开展公共卫生外交。公共卫生外交是实现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必经之路,(参见晋继勇:《浅析公共卫生外交》,载《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第82页。)提高国际社会对海上公共卫生治理的重视程度,通过公共卫生外交促进海上公共卫生治理国际多边合作与交流。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提出为海上公共卫生治理指明了方向。海洋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立场和方案。(参见姚莹:《“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国际法意涵:理念创新与制度构建》,载《当代法学》2019年第5期,第143页。)疫情的全球蔓延也使人们更加深刻地意识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价值,进而将推动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的大变革。(参见秦立建、王烊烊、陈波:《全球战疫背景下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构建:基于公共经济学视阈》,载《社会科学研究》2020年第6期,第29页。)而话语权是引领时代变革发展的重要力量。(参见闫安:《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载《内蒙古日报(汉)》2018年5月21日,第9版。)积极参与海上公共卫生治理将为中国更好参与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奠定坚实的话语权基础。
(二)统筹推进海上公共卫生领域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
疫情不仅是对一国公共卫生能力的考验,也是对一国国内法治建设的考验。全面加强和完善公共卫生法治建设,提高依法防控、依法治理能力,是中国参与海上公共卫生治理的基石。《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的出台就与2003年“非典”防治工作密不可分。同样,经历新冠疫情的考验,中国海上公共卫生法治建设也必将取得新的进展。《全国人大常委会2022年度立法工作计划》中指出,全国人大常委会计划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法”,(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2022年度立法工作计划》,载中国人大网2022年5月6日,http://www.npc.gov.cn/npc/c30834/202205/40310d18f30042d98e004c7a1916c16f.shtml。)在国内法治层面推进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有关法律修订与制定工作;交通运输部《交通运输“十四五”立法规划》中提到研究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条例》,并研究适时上升为船员法,(参见《交通运输“十四五”立法规划》,载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网站2021年11月11日,https://xxgk.mot.gov.cn/2020/jigou/fgs/202111/P020211111339228956598.doc。)这些举措将为船员权益提供更加充分的法律保障。
法治是一个国家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参见黄进:《习近平全球治理与国际法治思想研究》,载《中国法学》2017年第5期,第18页。)由于海洋天然的国际性,以及中国建设海洋强国、航运强国的进程不斷加快,中国海上公共卫生治理领域的涉外法治同样亟需完善。疫情以来,海上公共卫生的相关国际法得到深刻调整。2022年3月1日,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日内瓦海上人权宣言》发布,该宣言旨在保护所有生活、工作在海上和穿越海洋的人的人权,指出海上健康权是典型的海上人权。该宣言提出了海上人权保护四项基本原则,(《日内瓦海上人权宣言》海上人权保护四项基本原则是:1.人权具有普适性;人权适用于海上,且与陆上适用人权并无二致。2.所有海上人员都有权享有其人权,不加区别,一视同仁。3.无任何明确海事原因可否认海上人权。4.在海上,必须尊重依据条约法和国际惯例法确立的所有人权。参见《〈日内瓦海上人权宣言〉发布》,载搜狐网2022年3月4日,https://www.sohu.com/a/527290537_121123843。)为船旗国、港口国、沿海国的义务准则提供讨论基础,对违反海上人权的事项进行明确,有助于国际范围内对海上人权提高重视、形成共识。中国是海洋大国、航运大国,也是船员大国。截至2021年底,中国共有注册船员180余万人,位居世界第一。其中,具有海上服务资历的海船船员为41万余人。然而,中国在船员权益保护领域的立法,多为管理性规定,且立法层次较低,涉及船员人权保障的内容更多地体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等法律法规中,并没有针对以船员为代表的,在海上工作、生活人员的特殊性作出人权保护的专门规定。中国坚持把人权的普遍性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走出了一条符合时代潮流、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权发展道路。中国应加强对《日内瓦海上人权宣言》的研究,积极跟踪国际动态,了解主要海洋大国的态度,及时作出研判,为中国参与海上公共卫生治理作充足准备。2021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第16条第1款规定:“国务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有关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船员境外突发事件预警和应急处置机制,制定船员境外突发事件应急预案。”该规定为船员境外权益的保障提供制度性支持。
在海上公共卫生治理中,要强化法治思维,运用法治方式,充分借助立法、执法、司法等手段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第一,充分把握海上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变革的良好契机,总结中国在港口疫情防控、船员换班等海上公共卫生治理重难点问题上的丰富经验,推广实践中的有效措施,以人類卫生健康共同体为指引,积极参与海上公共卫生治理中的国际立法、执法等活动。第二,满足涉外法治人才的需要,培养一批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的海上公共卫生治理涉外法治人才队伍,强化涉外法律服务,加快涉外法律体系建设,同时不断完善国内相关立法,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的良性互动,提高法治化工作水平,为中国参与涉外司法活动提供法律依据。充分保障中国航运企业、贸易企业、海上人员等应当享有的合法权益,同时依法维护外国公民、企业在中国的正当利益。第三,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和学术交流,充分利用各类国际平台跟踪研究海上公共卫生治理有关国际法问题,提高相关议题设置能力,在海上公共卫生治理纠纷解决中,整合各类资源,积极发挥沟通协调作用,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坚决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促进海上公共卫生治理问题的妥善解决。
五、结语
各国对新冠疫情防控从应急模式过渡到将新冠疫情与其他传染病一同管理,并不意味着传染病全球大流行的结束。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绝不是海上公共卫生治理面临的最后一次危机。未来,传染病的再次暴发会对海上公共卫生治理造成怎样的冲击无法预知,届时应对海上公共卫生治理所面临的挑战可从这次危机应对中寻求借鉴。后新冠疫情时代,海上公共卫生治理凸显出的国际法困境依然需要继续完善解决路径。海上公共卫生治理中的多元价值要求在全球治理层面塑造海上公共卫生的秩序性、保障性和包容性面向。以IHR 2005为核心的现行海上公共卫生国际法仍面临价值冲突、规则执行以及机制实施等困境。应以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为价值引领,在多元国际法价值的冲突与矛盾中找到相适应的均衡点,促进海上人员健康权的普遍实现;提升主权国家履约意愿,把共同利益放在首位,以更加审慎的态度采取海上公共卫生治理措施;健全国际合作机制,联合多方力量成立专项小组,予以必要资金的援助,践行多边主义,打破国际合作壁垒。海上公共卫生治理是推进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革新的良好契机。中国应以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和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引,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在海上公共卫生治理有关国际法的制定、修改与互动中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展现中国的大国担当与大国形象,以增强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主导权,与世界各国携手共筑海上公共卫生治理的安全防线。
收稿日期:2022-09-02
基金项目:2018年度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课题“新时代海洋强国视域下中国海员发展主要矛盾转化与解决路径研究”(2018EGL015)
作者简介:彭宇,男,工学博士,上海海事大学法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上海高水平地方高校创新团队(海事安全与保障)成员,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