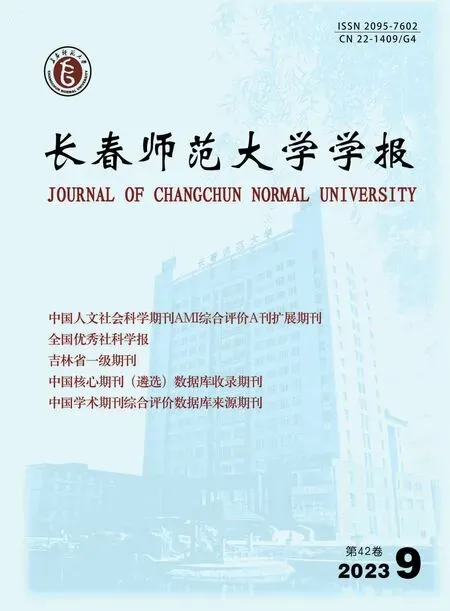耿文光目录学思想的承旧启新与晚清目录学转型
王 晓,雷 帆
(1.东北师范大学 学术期刊社,吉林 长春 130024; 2.东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4)
晚清目录学在旧学与新学、中学与西学的交织影响下发展。目前学界对晚清目录学的研究,更多关注晚清目录学家承乾嘉余绪而进行的各种考据活动,对社会动荡、西学冲击背景下目录学家在学术思想上的新变关注不够。事实上,这些处在新旧交替时期的目录学家,一面继承传统方法、遵循传统步伐、研究传统典籍,一面打破常规、呈现出反传统的面貌,他们比传统朴学家更开明,又比近代目录学家更保守。他们在传统目录学和近代目录学之间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对近代目录学的开启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山西学者耿文光(1833-1908)就是一位处于新旧交替时代的藏书家、目录学家。他撰写的解题式目录学著作《万卷精华楼藏书记》(以下简称《藏书记》)和传记体目录学著作《苏溪渔隐读书谱》(以下简称《读书谱》),总体上以传统目录学经典《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简称《总目》)为宗,但又并非完全拘泥于《总目》所构建的框架。耿文光对《总目》治学方式和学术取向的继承与改进,体现出其目录学思想的承旧启新,呈现出鲜明的后四库时代特征。
一、耿文光目录学思想的承旧
《藏书记》对《总目》的继承是耿文光学术承旧的表现,体现出耿文光目录学思想的保守性。耿文光认为目录之学是学中第一要事,“欲治群书,先编目录”[1]412。耿文光对《总目》推崇备至,认为《总目》“于学问之授受,诗文之支派,靡不穷究源流,指陈得失,实从来未有之目录,永宜奉为典要者也矣”[2]1952,故而在撰写《藏书记》时将《总目》作为重要参考。
《藏书记》对《总目》的继承,首先体现在《藏书记》的提要编写上。耿文光深受乾嘉考据浸染,编写提要时以《总目》为师,认为“凡读书宜字求其训,句求其解”[1]250。《藏书记》中各书的提要编写首先标出书名卷数,又将丰富的资料辑录在一起,包括书之作者、版本信息、内容、关于本书的各家序跋与要语,还会收集诸家论说以及耿氏考据性案注语。可见,《藏书记》的编写风格深受《总目》的影响。
《藏书记》对《总目》的继承,还体现在对书籍的分类与著录上。《藏书记》的分类体系与《总目》相比,除了在史部下增加谱牒、金石二类外,其余完全一致,各类目名称以及排列顺序也丝毫不差。可见,《藏书记》对《总目》的承袭度极高。在书籍著录方面,《藏书记》也多借鉴《总目》。这里说的不是书目的具体名称与数量,而是著录旨趣,如两目对小说的看法与著录如出一辙。《总目》对通俗小说不予收录,认为其是“诬谩失真,妖妄荧听者”[3]1182。近百年后,《藏书记》对《聊斋志异》等艺术价值颇高的通俗小说作品与《总目》一样不予著录。耿文光为小说家类所撰小序中提到“余于小说不甚留意”[2]2864,其精神旨趣可谓完全继承《总目》。
二、耿文光目录学思想的启新
《藏书记》对《总目》的突破是其学术启新的表现,体现出耿文光目录学思想的开明性。在西学输入、汉学危机、学术碎片化等背景下,耿文光的学术研究带有独特的时代印记,其目录学思想受晚清大变局的影响颇大。《藏书记》和《读书谱》对《总目》的突破,表现为灵活变通的类目设置、普惠初学的读书之法、实用为主的版本著录、调和汉宋的学术取向、针砭俗学的批判意识这五个方面。
(一)灵活变通的类目设置
《藏书记》四部下的各类目名称和排列次序承袭《总目》,不同的是史部下增加了谱牒、金石二类。这是耿文光从实际情况出发,对《总目》在类目设置上的灵活变通,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谱牒类著作起源很早,《汉书·艺文志》术数略的历谱类下就著录有早期的谱牒类书籍,此时尚属于我国谱牒类文献发展的萌芽期。随着谱牒著作的大大增加,《隋书·经籍志》《新旧唐志》《宋史·艺文志》《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文献通考·经籍考》等官私目录中的谱牒类书籍都位于史部下的二级类目之下,谱牒类书籍二级目录的地位不断得到稳固。到了明清时期,谱牒类书籍开始被剥离出史部,到《总目》时被放于子部类书类中,沦为“四部之内,乃无类可归”[3]1141的地位,此后的其他目录著作纷纷效仿。谱牒类书籍具有重大的价值,“中华谱牒在其发展过程中,始终承担着为社会、政治、家族服务之功能”[4],尤其在谱牒文献大增的晚清,其价值不容忽视。耿文光从实际出发,认为“氏姓之书由来远矣”[2]1428,应当给予重视。所以,他一反《总目》将谱牒类书籍放于子部类书类中的做法,把其置于史部谱牒类下,恢复其二级类目的位置。耿文光改变《总目》氏族之书入类书类的设置,认为“今以其书甚多,且关系甚重,谨巡皇朝《通志》立谱牒一门,次于地理之后。”[2]1428“其书甚多”与“关系甚重”就是耿文光关于类目设置的标准。
金石类书籍“不仅难为专类,即于四部之类属亦时有凌乱。”[5]《总目》在史部目录类下设置经籍、金石二属,至此金石类书籍才在四部分类体系中成为一个子目。但是,金石类书籍仍然遍布于四部之中,分类不甚条理。金石类书籍价值巨大,朱剑心先生指出:“金石文字,自成独立专门之学,可不待言。而其有裨于他学者,亦有三焉。”[6]耿文光在史部下设置二级类目金石类,专收金石类书籍,从当时“金石之学专门者五十余家。著述之富,行世者千有余卷”[2]1773的现实出发,将金石类书籍“别为一类”[2]1773,所收录金石著作达一百零六种。所以,将谱牒、金石二类设置为史部下的二级目录是耿文光敢于突破权威的编制实践,是在承继前人分类方法的基础上自觉创新的结果,体现出耿氏立足于现实情况、以书籍价值和流传情况为著录标准的务实倾向。
(二)普惠初学的读书之法
耿文光提到《藏书记》的撰写“与各家书目用意不同,其要在于分门别派,按部读书,据书编目,因目知书”[2]5。清代书目侧重于书籍字句或版本的著录,与指导读书的联系并不紧密。而耿文光编撰书目的目的在于读书、治学。他遍求古人读书之法,是为了给读书人指示门径。《藏书记》在耿氏读书理念的框架内把书籍的作者、版本、内容、序跋、要语、诸家评论与耿氏按注语巧妙集于一书,辑录了大量资料,兼具资料性与学术性。耿文光对每年所读之书,挖掘其源流,论证其得失,按年录书,撰成《读书谱》,示人以读书之法。笔者立足于《读书谱》,将耿文光有远见的读书之法分类列于表1中。

表1 耿文光的读书之法(部分)
耿文光在其著作《目录学》凡例中提到“是编为读书而作,非藏书之目”[1]423,在《紫玉函书目》叙中提到“盖彼意著藏书,而此则意在读书”[1]559,其提出的读书之法广泛分布于其著作中。耿文光将传统书目与读书之法结合起来,把目录学看成是读书的学问,秉持“藏书为治学”“编目为读书”的理念,纠正了历来收藏家夸多斗靡、不求实用的弊端。这是耿文光在学术理论方面的创新,体现出其目录学思想的开明。
(三)实用为主的版本著录
《总目》因著录版本不详而受人诟病,余嘉锡先生在《四库提要辩证》中说:“总目之例,仅记某书由某官采进,而不著明板刻。”[7]耿文光《藏书记》提要丰富,其宗旨之一就是“明书之纯杂,辨板之精粗”[2]5,以补《总目》之弊。
耿文光的版本观不同于许多佞宋的藏书家,他追求的是错讹较少、内容完整的实用性版本。耿文光对“专辨宋板明抄,而不解其中之义理旨趣者”“手披口诵,天天研摩,而不能识其面目者”[1]422提出批评,认为只关注版本的珍贵,而不理解书中旨趣、不注重实用与学术研究,是不可取的陋习。“必得宋本而后读书,则终身无读书之日”[1]557是他的真知灼见。《藏书记》卷一百二十五《亭林文集诗集》下的按语“凡钞古书,宜求实用”[2]3438,卷七十八《肘后备急方》下的按语“通行本不足录,然吾为读书计,取其实用”[2]2133,都表明耿文光追求的是版本的实用性。《藏书记》讲求版本的实用性,著录了很多明清刻本,对清代版刻研究有很大的参考价值,这是耿氏著作对当今学界的又一贡献。
(四)调和汉宋的学术取向
汉宋之争是清代学术的重要方面。《总目》标榜“汉宋兼具”的态度,本着“参稽众说,务取持平”[3]1的原则,对汉学与宋学似乎采取的是消融门户、不偏不倚的做法,但实际上仍是“重汉轻宋”。如《总目》诗类序:“今所采辑,则尊汉学者居多焉”[3]119,其“崇汉抑宋”之心可见一斑。张舜徽先生在《四库提要叙讲疏》中论及《总目》的汉宋观:“然通观全书,于评定学术高下、审断著述精粗之际,仍多扬汉抑宋之辞。”[8]19世纪,汉宋对立仍然存在。“乾嘉以降的十九世纪是汉、宋争论最激烈的时期,由于不同的争论者处于不同的‘学’与‘术’的交错关系之中,因而也使汉宋的争论呈现出不同的面向。”[9]
耿文光坚持反对门户之见,主张汉宋调和、相互促进。他认为,“由汉学而入者,书斯精;由理学而通者,书皆化,化汉学于理学之中,是真理学也。”[2]2耿文光对汉宋两家进行了切实的定位:“以记诵为无知,以闻见为务外,察事理之是非,核吾心之真妄,专用力于人道之所宜,而不屑屑于考辨名物者,此理学之宗旨也。字求其训,句求其解,因文识义,因义明理,融会而贯通,得心而应手,此汉学之家法也。”[2]2面对当时“门户之习深,而攻击之患起”[10]的情况,他提出:“余于汉宋两学只求其至精至当之处,于朱陆之学力求其深造自得之妙,而门户纷争之论概不欲观。”[1]355他在《藏书记》中收录方东树《汉学商兑》四卷,对《汉学商兑》作出“一人私说未必服众”“迂拙之苦心”“不免于门户之见”“实出于愤激,殊失和平”[2]2733的评价,可见他对门户之见的反对。他反对汉宋对立,主张汉宋调和,认为“无论汉学宋学,只学便好。以汉学读书,以宋学穷理,如是而已”[1]318,并且终生奉之。这种学术旨趣是对《总目》“重汉轻宋”态度以及19世纪汉宋之争的排斥,是耿文光目录学思想的重要部分,体现出耿氏对传统学术观念的突破。
(五)针砭俗学的批判意识
耿文光反对读书只为科场取名的行为,反对学以图利的俗学,认为很多人为获取功名而只读俗本,失去了治学的精神。《藏书记》序中论及著此书的目的之一在于“训俗”,即“读书略备于此,大抵针之,法砭俗学,使知门径。”[2]2耿文光在“未受明师之益,先染俗学之腥”[2]3的浑浊环境中,力求自己能宏通淹贯,不与世俗流为一体,只为寻找到真正的读书之法。
耿文光父亲的去世使他一生的学术活动发生转变,《读书谱》“道光二十五年”条载:“自是年以后,遂以购书为事,求古人读书之法,而诗文不甚致意。”[1]318-319耿文光为了找到真正有利于促进学术发展的读书门径,避免自己陷入“幸获一第,沾沾自喜,似乎圣人之学不过如是”[1]414-415的泥沼,一改少时读书只读经的情况。对俗学造成的危害,耿文光认为“实足以汩没性灵,涂泥耳目,毒之所中,百万莫治”[1]414。所以,他认为对俗学必须要“匡谬正俗、发蒙祛妄”[1]416,手段便是“发愤购书,遍求古人读书之法”[1]416,从而实现“使读者知书,编目者知目,学者由是而人,依目访书,以书印目,庶不为俗本所误,而可臻绝学”[2]1952的目标。这也正是他在《藏书记》序中提及的“训俗”。他将针砭俗学与探求读书之法联系起来,抨击俗刻陋本与鄙俗之说。“训俗”成为他终生追求的信条之一,他读书的目的已经由求道向求真转变,这是其开明学术思想的重要体现。
三、耿文光与晚清目录学转型
晚清时期在我国目录学发展史上是一个转折时期,耿文光的目录学实践在对传统目录学继承与批判的基础上,形成了目录学新思想的萌芽,是晚清目录学转型的先行军。任何目录学实践与思想都是时代的产物,都会具有时代的印记。耿文光的目录学思想较《总目》为代表的传统目录学开明,又较近代目录学保守。对耿文光目录学思想的地位与价值的分析,要结合其所处的晚清时代,结合他的学术实践,要看到他的变与不变。
(一)耿文光目录学思想在晚清目录学转型中的地位
耿文光目录学思想兼具“开明”与“保守”的特征。耿文光对《总目》所作的突破,尤其是他编目为读书、学术重实用的思想,体现出他的目录学思想是开明的;但囿于他的平民身份以及山西灵石的偏僻,他的书目编撰仍以传统书籍为主,“四部”之书足以满足其目录编制的绝大部分内容,所以他又是保守的。
当乾嘉考据学风深深植入学者治学风格之中时,晚清学术又多有对乾嘉考据学的反动。在时代变迁和个人理念的综合影响下,耿文光对《总目》作出的很多改进显示出目录学新思想的萌芽已经出现。耿文光虽不具备趋新学者的超前意识,但其目录学确有很强的前瞻性,其编目为读书、学术重实用、治学反对门户之见、针砭科举等思想体现出其对近代目录学的开启之功。乾嘉时期的书目编撰多重校勘训诂,主要侧重于对书籍的考据,而对普惠初学的读书之法涉之甚少,与指导读书的联系并不紧密。而耿文光的编目活动是为了治学,自始至终贯穿着指导读者读书的方法。耿文光曾说:“爱惜所学,深惧人知者,予甚病焉,因谱所学,以质同志。”[1]225这表明耿文光的学术理念已经开始由“求秘”向“求用”转变,耿文光已经开始由“读书人”向“知识人”过渡。耿文光也有以《目录学》直接命名的著作,体现出中国古代目录学学术话语的近代转型。1956年邓广铭先生在北京大学历史系的课堂上公开提出,“要以职官、地理、年代、目录作为研究中国史的四把钥匙”[11]。《读书谱》“道光三十年”条载:“凡读史年号、职官、地理最宜熟记。”[1]327“四把钥匙”在当今学界成为诠释历史的重要手段,而近百年前耿文光就已经有所酝酿,可见其学术目光之锐利。
在传统学术受到西学很大冲击的晚清,传统的四部之书仍是耿文光藏书与编目的大部分内容,这体现出其目录学思想在突破传统的同时又有一种回望,这是其保守的一面。与耿文光同时代的晚清重臣张之洞的《书目答问》旨在指示士人的读书入门途径,其“把目录学作为指导读书‘门径’的思想发展到了极致”[12]。《书目答问》与《藏书记》是同一时代完成的目录学著作,二者在内在思想上存在颇多相似之处,代表了当时的一种崇古风尚。但耿文光与张之洞的目录学思想不在一个层级上,张之洞目录学实践的目的在于维护传统学术的地位,是其“中体西用”思想在文化方面的实践;耿文光更注重对书目的考证和对传统目录学的总结,目录学思想更趋于保守。耿文光目录学重在“通经致用”,张之洞目录学重在“经世致用”,重治学、讲实用是两人目录学思想的相同点,但“严格说来,‘通经致用’与‘经世致用’尚有差别。后者主要强调致用,而前者则将‘通经’和‘致用’两者并举,甚至视‘通经’为‘致用’的前提条件。”[13]耿氏编目是通过“通经”,即对传统四部书的考据梳理,从而宣扬自己的读书之法,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则是将中国当时的中西新旧各类学术进行一番选择,其融合中西的学术倾向远高于耿文光。无疑,《藏书记》比《书目答问》等近代目录学著作更趋于保守。
(二)耿文光目录学思想在晚清目录学转型中的价值
王安功先生说:“我们发现对耿文光的学术研究,可以在内容和方法上分析其因循乾嘉考据的学术路数,在学术视野上宜以后四库时代的书目编撰特点和价值予以观察。”[14]值得注意的是,在那个特定的年代,有一批学者与耿文光的学术思想一脉相承,形成了一个群体。这一群体包括以浙江湖州皕宋楼的陆氏、杭州八千卷楼的丁氏、江苏常熟铁琴铜剑楼的瞿氏、山东聊城海源阁的杨氏为代表的清末四大藏书家。一方面,晚清四大藏书家的编目沿袭了《总目》之框架,在《总目》建设的类目框架下多重视考据,提要的撰写多反映出对珍本的重视和对书籍的考证。另一方面,其编目在发展乾嘉考据学的同时,也形成了新的特点,有不同于传统书目的地方。如《善本书室藏书志》有一条收书准则——“道光前的旧籍,即便是时代晚近的本子,仍可酌情收入;而咸丰已降的书籍,即便是未曾刊刻的稿本,也一律不收。”[15]110“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丁氏看重是文本的旧,而非版本的旧。这说明其藏书是为读书,而不是简单地为玩版本。”[15]110海源阁的主人杨以增与杨绍和“提供借抄、刊刻、助资等以共享和扩大私藏的传播”[16],与保守派藏书家是有区别的。总之,清末四大藏书家在继承传统的同时,也作出了诸多转变,其藏书编目理念相较于前人更加开明,与耿文光的为学旨趣可谓相似。
与耿文光同邑的部分藏书家、士绅在钻研传统学术、践行儒家纲常礼教的同时,也在逐渐调整知识结构,治学观念趋于开明,是这一群体的重要成员。《读书谱》“同治九年”条载:“又得杨氏书五百余种”[1]409。耿文光万卷精华楼的藏书很大一部分来自同乡杨尚文。耿、杨是同乡,并且有着相同的学术旨趣。儒家文化是三晋学人共同的精神追求,他们尊崇传统学术的同时又有创新,耿文光和杨尚文都是如此。杨尚文刊刻的《连筠簃丛书》收录了从唐至清的珍本书籍,该丛书对所收各书进行了校订。同时,该丛书的刊刻又与现实紧密联系,收录了许多有关西方与实学的著作,何绍基评价《连筠簃丛书》:“(杨墨林)刻《连筠簃丛书》十余种,皆发明经史,裨益实用之书。”[17]
耿文光等人对传统目录学进行的继承和批判,成为近代目录学新思想的萌芽,其“编目为读书”“学术重实用”等思想丰富了目录学的功用。不应忽视耿文光等人在目录学史上的地位,不应忽略他们对近代目录学的开启之功。加强对耿文光承旧启新的目录学思想的研究,有利于廓清目录学在清末的发展面貌,加深目录学史乃至晚清学术转型研究。
四、结语
耿文光《藏书记》将《总目》奉为圭臬,又在时代变迁和个人理念的综合影响下对《总目》作出突破,表现为灵活变通的类目设置、普惠初学的读书之法、实用为主的版本著录、调和汉宋的学术取向、针砭俗学的批判意识这五个方面。《藏书记》对《总目》的继承是耿氏学术承旧的表现,对《总目》的突破是耿氏学术启新的表现。耿文光在目录学实践方面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其“编目为读书治学”的目录学指导思想开拓了目录学的深度和广度,在目录学史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耿文光的目录学思想兼具“开明”与“保守”的特征,晚清目录学转型的萌芽就在这开明的目录学思想与实践中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