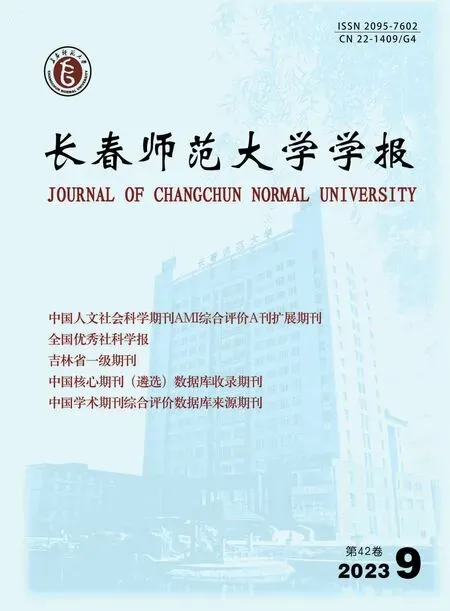敦煌本《文选音》残卷抄录者探析
董宏钰,邹德文
(长春师范大学 《昭明文选》研究所,吉林 长春 130032)
20世纪初,敦煌藏经洞首次被发现,出土了大量的敦煌遗书,其中包含一大批《文选》写卷。敦煌吐鲁番《文选》写卷对当代文选学研究具有重要的版本、文献及校勘价值。《文选》研究在隋唐时期多以音义为主,先后出现萧该《文选音义》、曹宪《文选音义》、公孙罗《文选音诀》等著作,惜诸书或已不传,或已亡佚。敦煌出土的写卷文献包括《文选音》残卷两件,编号为P.2833与S.8521,分别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和英国国家图书馆。周祖谟先生在《问学集》中对敦煌《文选音》残卷的评价很高:“然而兹卷之可贵,非止可以考校隋唐之旧音已也,盖篇中之字关乎《选》学者尤重。考唐代之精于《文选》学者,有李善、公孙罗、陆善经、五臣诸家。公孙、善经之注虽湮没已久,而《集注》存其遗绪。千载之下,微言旧义,已有可徵……综覈四家之书,文字己多歧异;推寻残卷,复与众本有别,是唐代《文选》传本,得此而为五矣。”[1]对敦煌写本《文选音》残卷的研究已取得不少成果。王重民先生在《巴黎敦煌残卷叙录》一文中假定《文选音》作者为萧该①。周祖谟先生在《论〈文选音〉残卷之作者及其方音》一文中否定了王重民的“萧该说”,提出作者可能是许淹的观点②。王重民先生对此回应称:“许淹说”尚欠实证③。张金泉、许建平两位先生在《敦煌音义汇考》一书中将P.2833与S.8521两个残卷作了缀合,对《文选音》进行了较为详细的题解和注音校记④,但疏于考证。饶宗颐先生在《敦煌吐鲁番本文选》一书的前言中对王重民、周祖谟的观点有所评论,认为二人理据不甚充分,尚待研究⑤。罗国威先生在《敦煌本〈昭明文选〉研究》一书的附录中抄写了法藏P.2833号残卷⑥,但并未对作者问题进行考证。范志新先生在《唐写本〈文选音〉作者问题之我见》⑦一文中对王重民的“萧该说”与周祖谟的“许淹说”同时进行否定,并对其进行细致的考辨,但对作者究竟是谁并未给出明确的答案。徐真真⑧、杨秋波⑨、席倩倩⑩和董宏钰等研究者都只是推断《文选音》抄写的时代,对抄写者问题涉及较少。
可见,对于P.2833和S.8521《文选音》残卷抄写者问题,学术界多有争论,无法形成共识,尚有继续研究的空间。本文通过对P.2833和S.8521《文选音》残卷的时代背景、抄写体例、抄写方式、抄写内容、书法水平和被注音字等情况的分析,推测《文选音》残卷的抄写者究竟是谁。
一、文教政策与科举制度在敦煌地区的施行促进了《文选》的传播
西晋末年“八王之乱”后,大批文人学士远离中原,避难于敦煌地区。许多人在此长期定居,不仅保存、传播了中原的先进文化,而且推动了河西之地文化的发展,为敦煌地区文教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而深厚的基础。敦煌地区处于沟通中西方的交通要道,是唐代边陲的重要战略要地,容易接受中央政权的政令与中原文化。所以,唐代前期制定的教育政策使敦煌地区的学校教育形成一派兴盛繁荣的景象。
唐王朝推行“尊儒崇圣”的文教政策,屡下诏令兴办学校,推广儒家教化于全国各地。敦煌地区的教育分成官学、私学、寺学三类型。官学由中央政府在敦煌州郡、县、乡设置,私学则由私人在乡里、巷坊兴办,官学、私学皆以修习儒家典籍为主。寺学是在社会剧烈变迁之下形成的宗教与教育结合的特殊型态,具有儒释相融的教育特色。魏晋以来,敦煌地方官府举荐的人才多为具有较高文化修养的世家大族子弟。敦煌文献记载的世家大族有索氏、张氏、阴氏、李氏、曹氏、宋氏、马氏、罗氏、翟氏、令狐氏等,他们撰写的志传、碑铭赞、莫高窟供养人题记等都反映出世家大族对儒家文化的崇尚。他们的子弟为官后,通过儒学思想教化民众,推动儒学在敦煌的传播。从其他的一些敦煌文献中也可以见到不少抄写儒家经典的文书题记,可见当时敦煌社会习儒的风气十分浓厚。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敦煌文献中的“儒家典籍”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基本可以代表唐代的主流精英传统文化,《文选》《开蒙要训》等也要归入其中。大批的《文选》白文本、注本等写卷在敦煌出土,正是这方面的反映,这与后来四部分类法中的子部儒家类有着较大的区别。
唐立国之初,将选拔人才列入重要政事。科举考试作为选拔人才的主要方式,对敦煌地区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登科及第亦成为敦煌地区士子追求人生理想的唯一途径,以读书换取名位的功利思想成为敦煌社会认定的主流价值。所以,就出现了《秋胡变文》中有关秋胡离家赶考的记载:“(秋胡)辞其了道,服得十袟文书,并是《孝经》、《论语》、《尚书》、《左传》、《公羊》、《谷梁》、《毛诗》、《礼记》、《庄子》、《文选》,便即登逞(程)。”[2]秋胡携带的书籍都是科举考试所用之书,其中包括《文选》。这说明《文选》确实是科举考试重要的参考书。
二、敦煌《文选》写卷抄写者的身份
在敦煌藏经洞发现的五万余件写卷,全部出自当时、当地人之手。敦煌出土的《文选》残卷俱为写卷,这些写卷的抄写者很复杂。从抄写的形制、特点和抄写人的身份来看,写卷的抄写者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官方书手、僧道书手、民间书手。他们处于社会不同阶层,具有不同的文化素质,其抄写的内容也就不尽相同。这些差异对《文选》文本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反映了《文选》在敦煌地区传播的情况,对我们推测《文选》原貌有很大帮助。因此,探究敦煌《文选》写卷抄写者的问题是研究敦煌《文选》写卷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写卷的抄写者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类是官方书手。就敦煌文献的抄写而言,官方书手抄写的文献可以代表敦煌地区的最高水平。唐朝实际控制敦煌地区以后,该地区的教育开始与中央政府接轨。地方政府通过“统一”形式抄写“儒家典籍”,将其作为各类学校之范本。如:中国历史博物馆藏吐鲁番抄本《文选序》,抄写极其认真,书法功底和学养也极其深厚,全篇几乎没有任何污迹和改动,堪称书法精品。我们从法国巴黎藏P.2005的敦煌写本《沙州都督府图经》残卷中可以知道沙州府官学设置情况:经学博士二人,从九品上,助教一人,学生五十人;医学博士一人,从九品下,助教一人,学生十二人。经学博士和助教的主要职责是掌管校理典籍、刊正错谬[3]。这些笔法精当、工整有度的《文选》写卷可能是由在当地官府任职的经学博士或助教抄写,并被下发给各类学校作为范本使用。
第二类是僧道书手。敦煌地区是佛教传入中原的必经之地,境内有大量的佛寺。唐朝统治者以道教始祖老子李耳的后代自居,对道教大加提倡。敦煌地区的佛寺、道观不仅从事普通的宗教活动,还组织翻译经文,甚至承担本地的教育活动。一些文化素养深厚的僧道之士抄写经书,不仅是重要的功德活动,也是其必修课。但是,他们抄写的内容并不限于佛道经典。敦煌写本中很多“儒家典籍”的写本也出于僧侣、道士之手,只不过这些僧道之士的书法水平高低不同,有的工整干净、行款整齐划一,有的则书写潦草、杂乱无章,与官方书手书写的经卷水平有较大差距。如:法藏P.2528《西京赋》,卷尾署题“永隆年二月十九日弘济寺写”一行。弘济寺在长安,此卷可能为长安弘济寺僧人抄写,后流入敦煌地区[4]。此卷字体为行楷,间杂草书,凝练遒劲,轻重对比明显;结体修长,中宫蹙收,斜划紧结,重心偏上。此卷的书写也有不足之处,即书写风格并不纯粹。“无论是从用笔还是从结体上而言,既有典型的行书与草书,又有典型的北碑楷书与初唐楷书;既有很多佳构,又有不少败笔。因为字小,这些问题显得不突出。”[5]僧道之士无入仕登第的功利观念,其抄写经文主要是为了宣传宗教。《四部律并论要用抄卷上》的题记说,“纵有笔墨不如法”。在僧道之士的眼中,法度高于一切。
第三类是民间书手。民间书手包括职业书手和百姓书手。职业书手是以代人抄经写书为职业的人,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和书法水平,其抄写的典籍较为精良。他们是敦煌文献抄写者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地位上远低于官方书手。百姓书手不能真正称作“书手”,最多只能称为“抄写者”。就敦煌文献内容抄写者而言,他们书写文书的目的并在于获取经济利益,而在于实用性。敦煌文献中数量较多的儒释道经典、社会文书、经济契约、启蒙读物等皆出自百姓书手。百姓书手可以分为普通百姓和士子学童。一般来讲,普通百姓文化水平相对较低,他们在书写文书时多注重内容的实用、书写的方便;士子学童接受过一定的教育,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他们抄写的内容多为传统的儒家典籍,也有一些文学作品。如:法藏P.3480《登楼赋》就为当地士子抄写,其字迹拙劣潦草,不讲行款,俗字与讹字颇多。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他们抄写的材料实用性强,往往在失去效用后被毁弃,但是这些材料对真实地还原敦煌地区的社会风貌、生活习俗起到重要作用。
三、《文选音》残卷的内容特征
士子要想在科举考试中脱颖而出,只熟悉九经是远远不够的。《文选》因其“略其芜秽,集其清英”的魅力和“文章奥府”的价值,在有唐一代作为教科书的作用得以突显。《文选音》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有如下特征。
其一,《文选音》残卷体例是随文注音不释义,以顺读选文;注音方式是反切、直音、标调并用,以反切为主,以直音为补充,另有少许直接标出平上去入四声。与李善音注、五臣音注、文选集注对比考证,发现《文选音》残卷与三者音注迥然不同,可以推断《文选音》为未经李善、五臣注释的古本《文选》三十卷本的部分。
其二,写卷有讹字、衍字、脱字、异体字和错字涂去的现象,定是几经传抄之本。通篇一百多行以楷书写成,书写娴熟娟秀,楷法遒美,章法整洁均匀。科举考试要求文字书写规范、美观,这是决定其能否入仕的重要条件。《旧唐书·职官志二》“吏部尚书”条载:“凡择人以四才,校功以三实。四才,谓身、言、书、判。其优长者,有可取焉。”[3]《新唐书·选举志下》载:“凡择人之法有四:一曰身,体貌丰伟;二曰言,言辞辩正;三曰书,楷法遒美;四曰判,文理优长。四事皆可取。”[6]第三条以“书”取士的标准就要求士子书法有力度和筋骨,字形遒美。
其三,P.2833号,稍残,存97行,残卷首尾不全,起于《文选》卷二十三任彦昇《王文宪集序》后半部分,迄于卷二十五干令升《晋纪总论》前半部分;S.8521号,仅存5残行,行中有“褚渊碑”三字,残卷起于蔡伯喈《陈太丘碑文》中的部分字,迄于王仲宝《褚渊碑文》中的字。由残卷中“第廿四”“第廿五”字可以推知,其所依据的底本当是《文选》三十卷古本。残卷中的篇章标题都采用省略的书写方式,如“贤臣(王褒《圣主得贤臣颂》)”“充国(扬雄《赵充国颂》)”“出师(史岑《出师颂》)”“酒德(刘伶《酒德颂》)”“功臣(陆机《汉高祖功臣颂》)”“东方(夏侯湛《东方朔画赞》)”“三国(袁宏《三国名臣序赞》)”“魏志”“蜀志”“吴志”“封禅(司马相如《封禅文》)”“美新(扬雄《剧秦美新》)”“典引(班固《典引》)”“公孙弘(班固《公孙弘传赞》)”“晋纪(干宝《晋纪论晋武帝革命》)”“总论(干宝《晋纪总论》)”“褚渊碑(王俭《褚渊碑文》)”,残卷所包含的文体有序、颂、赞、符命和史论等。两个残卷并不相连,但注音方式、书写形式相同,应属于萧统《文选》古本白文三十卷中的同一卷中的两部分,并为同一人所书写。
其四,从《文选音》残卷被注音字的情况看,抄写者选择被注音字时倾向于较为简单的字,注音的难度明显不大,并且和《文选集注》音注、李善音注、五臣音注有较大的差别,这可能与《文选音》残卷所残存的文章鲜有僻字、难字有关。反切、直音不仅标注出被注音字的读音,还可以通过其字形、字音透漏出来的信息对被注音字进行训释,显示出两者在字形、字音上的某种关联。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看出。
(1)定字音
《文选音》残卷对大量的多音字加以辨音,并且不厌其烦地多次注音,如:“行”字出现9次,“应”字出现8次,“乐”字出现8次,“量”字出现7次,“”字出现7次,“胜”字出现6次,“长”字出现5次等;还对一些较为简单的多音字,如“契”“令”“折”“乘”“舍”“守”“论”“处”等多次注音。
(2)析形讹
《文选音》为写卷,抄写过程中因字形相近而普遍出现讹误现象。
例1:曰越;日人一
“曰”与“日”字形相近极易产生讹误,且二字字形只有胖瘦之分,故手写极易混淆。《文选音》为区分“曰”与“日”二字,“曰”注音“越”17次,注“越”表明该字此处当为“曰”字而非“日”字,“日”注音“人一”共11次。由此可以很好地区分二字,不至于产生讹误。
例2:已、己以;已、己纪
《文选音》对“己”“已”二字分别注音5次、16次。“已、己”是两个构形相近、在书写过程中极容易产生讹误的字形。二字读音也相近,已以,以母止韵上声;己纪,见母止韵上声,只是声母不同。
(3)辨正误
《文选音》中有些字形体相似,偶有混用现象。作者在注音时以正字改误字,有些正字辨析的意味。
例1:昨/祚
《文选音·功臣》:“跨功踰德,祚尔辉章。”“昨”字被训为“祚”。查《文选》各版本,此句都为“祚”字。祚,《说文》:“福也。从示乍声,徂故切”,从母暮韵去声,在《文选音·功臣》中为“赐福”义,与文义符;昨,《说文》:“垒日也。从日乍声,在各切”,从母铎韵入声,与文中义不符。两字只是声母相同。故作者在注音时,以正字“祚”改误字“昨”,是谓“昨”当为“祚”。
例2:與/典
《文选音·功臣》:“穆穆帝典,焕其盈门。”《文选音·封禅》:“舜在假典,顾省阙遗。”“與”字被训为“典”。查《文选》各版本,此句都为“典”字。典,《说文》:“五帝之书也。从册在丌上,尊阁之也。”庄都说,典,大册也。,古文典从竹。多殄切,端母铣韵上声。與,《说文》:“黨與也。从舁从与。,古文與。余吕切,以母语韵上声”。《文选》中的“典”字,应训为“典章制度”之义,“與”字无此义项。是知“與”乃“典”之误。两者只是字形相近,声母、韵母都不同。故作者在注音时,以正字“典”改误字“與”,是谓“與”当为“典”。
(4)明假借
《文选音》中有些注音字被用来指明假借用字现象,即用本字解释借字,也就是传统训诂学中所谓“破读”。《文选音》的作者用注音字之音之形直接标出被借字,能破被借字之形,进而能知其音、明其义,显示了本字与借字的关系。
例:智/知;知/智
《文选音·贤臣》:“无有游观广览之知,顾有至愚极陋之累。”《文选音·美新》:“言神明所祚,兆民所托,罔不云道德仁义礼智。”“知”与“智”互训。《广韵·寘韵》:智,知也,知义切,知母寘韵去声;《广韵·支韵》:知,觉也,欲也,陟离切,知母支韵平声。在古音上,知、智二字读音相同,均为知母支部开口三等。《集韵·寘韵》:“知,或作智。”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知,假借为智,古籍中二字多通假。”《论语·里仁》:“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陆德明《经典释文》:“知,音智。”《劝学》:“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注:知,读为智。故“知”“智”二字为同源通假。
四、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知道敦煌《文选》写卷的抄写者大致可以分为官方书手、僧道书手、民间书手等三类。那么,《文选音》的抄写者究竟是谁呢?
从《文选音》残卷的书法水平来看,残卷以楷书写成,楷法遒美,用笔娴熟,自然质朴,功力寓于法度之内,书法达到较高造诣。
从《文选音》残卷的内容来看,残卷有讹字、衍字、脱字、异体字和错字涂去的现象。
从《文选音》残卷被注音字的情况来看,作者选择被注音字时倾向于简单的字,注音的难度明显不大,并且与《文选集注》音注、李善音注、五臣音注有较大的差别。
从《文选音》残卷的体例来看,残卷是随文注音不释义,以顺读选文。
从《文选音》残卷的抄写方式来看,其抄写具有很强的随意性,随意性的根源在于抄写者自用自抄的抄写意图,目的往往是自己能够看懂,并且能够应对实际的需要。
《文选音》残卷的这些方面似乎可以透漏给我们一些信息。唐代科举以“诗赋取士”。掌握《文选》,精通《文选》理,就可以“秀才半”。出于实用的目的,《文选》成为广大士子必备的学习参考用书。如韩愈在《故中大夫陕府左司马李公墓志铭》写道:“年十四五,能暗记《论语》、《尚书》、《毛诗》、《左氏》、《文选》,凡百余莫言,凛然殊异。”[7]可见,《文选》在当时的地位己经非常高,可与经书并列。学习《文选》,必先识字。一字之中以音为首要。不明音韵,《文选》若天书。故音韵明,《文选》通。在这种情况下,《文选音》的抄写者就有这么一种可能,即其可能是一名正在为科举考试而勤奋学习的士子。
[注 释]
①“(《文选音》)持与《集注》所引《音决》相校,多不相同,则此残卷非公孙罗音。王子渊《圣主得贤臣颂》:‘清水淬其锋,’《集注》引《音决》云:‘曹,七对反,萧,子妹反,’曹为曹宪,萧为萧该,此残卷作‘七对’‘子妹’二反,与曹宪音不同,又知非曹宪书。李善音间存《选》注,许淹音蓋已无存,而此残卷所载‘子妹’一音,适与《音决》所引萧该音合。余虽仅得孤证,在未见许淹音以前,无宁假定此残卷为萧该《文选音》也。”黄永武编:《敦煌丛刊初集》第9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194页。
②“案两《唐书》言曹宪、公孙罗均江都人也,许淹者句容人也,江都、句容相去未远,故语音亦自相近。吾所以谓此残本《文选音》蓋许淹之书者以此。”俞绍初、许逸民主编:《中外学者文选学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55-56页。
③“周祖谟撰‘论文选音残卷之作者及其音反’一文(载《辅仁学志》第八卷第一期),证明此残卷所作音,大致与江都选学诸大师所作音合,因欲定为许淹《文选音》。余曾谓‘在未见许淹音以前,无宁假定此残卷为萧该《文选音》’。今周先生所举例证,有助于否定此残卷非萧该音,但欲骤定为许淹音,则犹待有进一步之例证。” 王重民著:《敦煌古籍叙录》,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23页。
④“无书题。王重民定萧该撰,周祖谟定许淹撰。‘民’、‘治’不缺笔,‘国’作‘圀’,用武后新字,知其抄于武后年间。……书案《文选》,随文摘字注音兼录异文而成……又多俗体……亦多讹误……文题多省成二字……注音与《广韵》大体相同,形式除反切、直音外,尚有只注声调者……今以《六臣注文选》校记于后。”张金泉、许建平著:《敦煌音义汇考》,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10页。
⑤“法京敦煌卷P.2833《文选音》,研究者多家,王重民以书中王子渊《圣主得贤臣颂》‘淬其锋’之‘淬’字,《文选集注》引《音决》云:‘萧,子妹反。’与此卷合,遂定该卷为萧该之《文选音》。周祖谟从《广韵》音切,校其与此卷之违合,谓曹宪、公孙罗皆江都人,许淹则为句容人,江都、句容地相迩,故语音亦近,因定此卷为许淹音(说见《问学集》),理据未甚充分,尚待研究。” 饶宗颐编:《敦煌吐鲁番本文选·前言》,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4-5页。
⑥罗国威著:《敦煌本〈昭明文选〉研究》,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05-312页。
⑦范志新根据《唐钞文选集注汇存》第四十八卷陆士衡《赠尚书顾彦先一首》中保存的一条许淹佚文,并对“许淹”和“道淹”、“文选音”和“文选音义”两组专有名词分别作了区分,证实了许淹所撰的是音义兼释的《文选音义》,而不是只注音不释义的《文选音》。范志新:《唐写本〈文选音〉作者问题之我见》,《晋阳学刊》,2005年第5期。
⑧《敦煌本〈文选音〉残卷研究》(《敦煌学辑刊》,2008年第1期)一文对P.2833与S.8521两个残卷的抄写时代、注音特点、文献和版本价值进行探索。认为:“残卷的著作时代一定是在唐高宗之前,也就是公元649年之前的时代。”
⑨《敦煌〈文选〉写本音切研究》(南京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一文将敦煌《文选》写本残卷音切的声、韵、调系统与《广韵》相比较,认为敦煌《文选》残卷语音系统是一个反映唐代读书音的语音系统,既有对前音义反切的继承,又有作者的时音特点。
⑩《敦煌残卷〈楚辞音〉、〈文选音〉反切研究》(上海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8年)一文认为:P.2833与S.8521两个残卷抄写年代不大可能在武后时期,在唐代的可能性也很小,或许是五代及之后的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