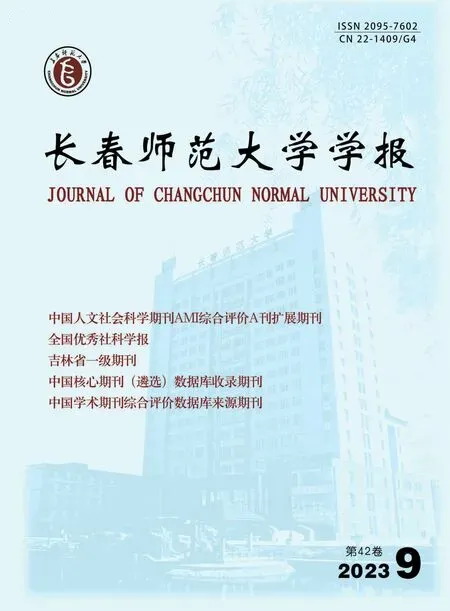晋代吴方言的唇音声母
——基于民族语言融合的视角
王素敏, 钟 健
(防灾科技学院 文化与传播学院,北京 101601)
永嘉之乱使中原西晋王朝土崩瓦解,居住在我国北方的鲜卑、匈奴、羯、氐、羌相继入侵中原。原来统治中原地区的司马氏政权被迫南迁,大批士族、汉族人民也相继南迁,导致南北两地居民的民族构成发生巨变。在北方地区,少数民族和汉族的接触使他们不可避免地存在语言文化方面的隔阂、冲突与融合;在南方地区,负载着中原文化的世家大族向江左地区迁徙,导致中原文化与江左文化发生激烈冲突、碰撞和趋同、整合。
民族的接触与融合会引起语言的变迁。《颜氏家训·音辞》记载南北朝时期的语言状况:“南染吴越,北杂夷虏,皆有深弊,不可具论。”[1]意思是说,中原语言杂有北方少数民族的语言,南渡的北语也带上了吴越方言的色彩。关于北语南渡的问题,陈寅恪《东晋南朝之吴语》[2]和郭黎安《关于六朝建康的语言》[3]从历史的角度,周一良《南朝境内之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4]和余嘉锡《世说新语笼疏》[5]及刘泰廷《东晋南朝士人所持北音、吴语之交融概说》[6]从政治的角度,鲁国尧《“颜之推谜题”与南北朝语言和方言》[7]和何九盈《论普通话的发展历史》[8]从语言学的角度分别提出北语在南渡之后沾染了当地吴越音的特征。但对于“南染吴越”这个“染”字的具体内涵,前修时贤尚未提供语言事实方面的证据。本文以《经典释文》所引徐邈音注和《字林》音注为对象展开研究。徐邈和《字林》的作者吕忱祖籍都是山东,吕忱一生未到过南方,徐邈于东晋康帝建元二年(公元344年)出生于京口,史书记载其为上层士大夫。根据儿童语言习得理论,可以推测徐邈不可能完全说京口地区的吴语,他的语言应该是以北语为主体且杂有吴方音色彩的新语言。有鉴于此,本文比较徐邈音与吕忱《字林》音,辨析吴方音的特征,进而将其与吴郡文人顾野王的《玉篇》比较,为“南染吴越”的“染”字提供语言事实上的证明。
一、材料与方法
结合文献语境,用意义审定音切的方法,排除了《经典释文》中解释意义的、辨析形体的、明假借和表示异文的假性音切,共得到反映徐邈方音信息的音切1192条,其中涉及唇音的有103条;共得到吕忱《字林》反映齐鲁方音信息的音切745条,其中涉及唇音的有60条。我们在这些真值唇音音切的基础上分析徐邈和《字林》的唇音特点。
由于唇音材料相对较少,无法用反切系联法系联徐邈和《字林》的唇音反切。我们主要采用反切比较法和结合意义审定音切的方法,分析二者的唇音特征。反切比较法以《切韵》(《广韵》)为标准,用徐邈、《字林》音切与其作比较,确定两类读成一类的比例为20%,因为《广韵》音系的唇音特征是轻唇与重唇不分,《广韵》轻重唇不分的比例为17.32%。为严谨起见,我们把这个交替的比例定得稍高一些。同时,徐邈、《字林》反切与《切韵》反切交替,情况复杂。交替是否反映语音关系,要看数量和比例。在交替比例不能起决定作用时,要辅助以文献语境反映的语音关系来证明,这就是意义审定音切的方法。如:徐邈幽三韵类字7例:璆(居虬)、觩(音虬)、纠(居虬)、遒(在幽)、滫(相幼)、糔(相幼)、絿(音虬);其中,“遒,《切韵》(自秋切)”“滫,《切韵》(息有切)”“糔,《切韵》(息有切)”“絿,《切韵》(巨鸠切)”这4例是徐邈幽三交替《切韵》尤三。徐音尤三韵类字共15例:陬(侧留)、妯(直留)、抽(直留)、傁(所流)、炰(甫九)、愀(在九)、庮(余柳)、茆(音柳)、扭(女酒)、忧(于救)、柚(以救)、臭(尺售)、雠(市又)、纽(女酒)、攸(以帚);其中,“傁,《切韵》(苏后切)”(候一)是徐音尤三交替《切韵》候一,其他14例全部是徐邈尤三对应《切韵》尤三。总体来看,徐邈幽三、尤三韵类字共22例,其中,二者发生交替的共4例。这样,幽三、尤三交替数占总数之比为18%。这个比例很难说明徐邈反切系统尤三开、幽三开是否区别。这就要结合文献语境来看。《周易·大有》:“君子以遏恶扬善,顺天休命。”《释文》:“休命,虚虬反,美也,徐又许求反。”《左传·昭三》:“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释文》:“休,虚喻反,徐许留反。贾云:燠,厚也;休,美也。”“徐又许求反”,此处的又音即《左传·昭三》音义中的“许留反”,表示“痛念之声”义。所以,徐邈对“虚虬反”和“许求反”的注音音值是不同的,徐邈反切系统幽(虬)、尤(求)是不能区别的两个韵类。
综合以上,本文以《经典释文》这部书为研究范围,以书中陆德明所引的南北朝时期徐邈、吕忱的唇音音切为研究对象,以《切韵》音系为参照,用反切比较法和意义审定音切的方法分析、归纳南北朝时期南北两地不同的语音系统。同时,对南北两地的语音系统进行比较,进而得出南北朝时期民族迁移所带来的语音变迁。
二、晋代吴方言的唇音声母特点
(一)徐邈唇音声类
1.用反切比较法看唇音声类的关系
用aA/bB/cC/dD4个字母代表4种发音方法,分别是清、次清、浊、次浊;大写代表博普蒲莫,小写代表方芳符武。下面以《切韵》五十一声类为标准,主要从发音部位、发音方法两个角度对徐邈的唇音声类特点进行分析。
(1)方类与博类
徐邈方类对应《切韵》方类(aa型26例):柎(音鈇)、邠(甫巾)、封(甫用)、披(甫髲)、陂(甫寄)、藩(甫言)、贲(甫寄)、谝(甫浅)、標(方遥)、炰(甫交)、嶓(甫河)、并(方聘)、掊(甫垢)、俾(甫婢)、秕(甫里)、跛(方寄)、邴(甫杏)、畀(甫至)、庇(方至)、閟(方冀)、鷩(方利)、蔽(方四)、芾(方蓋)、塴(甫邓)、辟(甫亦、补亦)、偪(甫目)。
徐邈方类交替《切韵》博类(aA型5例):嶓(甫河)、把(甫雅)、嬖(甫詣)、頒(甫云)、氛(扶云)。
徐邈方类交替《切韵》芳类(ab型3例):丕(甫眉)、姇(方附)、拊(音府)。
徐邈方类交替《切韵》符类(ac型2例):膑(扶忍)、辟(甫亦)。
徐邈方类交替《切韵》蒲类(aC型3例):逋(方吳)、炰(甫交)、掊(甫垢)。
徐邈博类交替《切韵》符类(Ac型1例):纰(補移)。
总体看来,徐邈方类与博类aa型26例,aA型5例,Aa型3例。细音对应《切韵》细音26例,洪细交替8例。加进不同发音方法的例子:ab型3例,ac型2例,aC型3例,Ac型1例,即不同发音方法之间,细音对应《切韵》细音5例,洪细交替4例。在对应徐邈方、博二类的《切韵》反切中,细音与细音对应31例,洪细交替12例,洪细交替占总数之比为38.7%。可以认为徐邈不区分方类与博类。
(2)芳类与普类
徐邈芳类对应《切韵》芳类(bb型2例):漂(敷妙)、皫(芳表)。
徐邈芳类交替《切韵》普类(bB型5例):纰(孚夷)、伻(敷耕)、淠(孚蓋)、扑(敷卜)、踣(敷豆)。
徐邈芳类交替《切韵》方类(ba型2例):葑(音豐)、猋(芳遥)。
徐邈芳类交替《切韵》符类(bc型5例):剽(敷遙)、沨(敷剑)、泙(敷耕)、蚹(音敷)、谝(敷連)。
徐邈芳类交替《切韵》蒲类(bC型1例):仆(敷木)。
徐邈普类交替《切韵》蒲类(BC型1例):沛(普蓋)。
总体看来,徐邈芳类与普类bb型2例,bB型5例,洪细交替数大于对应数。加进不同发音方法例子:ba型2例,bc型5例,即细音对应细音共7例;bC型1例,为洪细交替;BC型1例,为洪音对应洪音。细音对应细音9例,洪音对应洪音1例,洪细交替6例,交替与总数之比为37.5%。这说明徐邈不区别芳类与普类。
(3)符类与蒲类
徐邈符类对应《切韵》符类(cc型11例):缝(扶用)、陴(扶移)、貔(扶夷)、蚍(扶夷)、摽(符表)、牝(扶死)、矉(扶眞)、蕡(扶畏)、便(扶捐)、圯(扶鄙)、敝(扶灭、符灭、伏灭)。
徐邈符类交替《切韵》蒲类(cC型17例):蓬(扶公)、庞(扶公)、芃(符雄)、韸(音丰)、培(扶來)、陪(蒲来、扶杯)、疱(扶交)、炮(扶交)、旁(扶葬)、洴(扶经)、罢(扶彼)、扁(扶忍)、部(扶苟)、偝(扶代)、孛(扶愦)、暴(扶沃)、薄(扶各)。
徐邈蒲类交替《切韵》符类(Cc型2例):脾(蒲隹)、蠯(薄鸡、父幸)。
徐邈符类交替《切韵》普类(cB型1例):伾(扶眉)。
材料显示,徐邈符类与蒲类cc型11例,cC型17例,Cc型2例。细音对应细音11例,洪细交替19例。加进不同方法的例子:cB型1例,为细音对应《切韵》洪音。交替数与总数之比为64.5%。这说明徐邈不区别符类与蒲类。
(4)武类与莫类
徐邈莫类对应《切韵》莫类(DD型4例):梦(莫公)、霾(莫戒)、沔(莫显)、铭(音冥)。
徐邈武类对应《切韵》武类(dd型2例):盟(亡幸)、刎(亡粉)。
徐邈武类交替《切韵》莫类(dD型7例):蒙(武邦)、摩(亡髲)、冥(亡定)、弭(武婢)、袤(亡侯)、厖(武讲)、埋(武乖)。
徐邈莫类交替《切韵》武类(Dd型1例):侮(亡抚、音茂)。
总体来看,徐邈武类与莫类DD型4例,dd型2例,dD型7例,Dd型1例,交替数与总数之比为57%。这说明徐邈不区别武类与莫类。
2.结合文献注音看徐邈唇音声类
(1)方类与博类
《尚书·太甲上》:“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师。”《释文》:“辟,必亦反,徐甫亦反。”
《尚书·洪范》:“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释文》:“辟,徐补亦反。”
上面两例中“辟”字都是“君王”义。也就是说,对于同一个“君王”义,徐邈注了一个“甫亦反”、一个“补亦反”。只能认为这两个反切是异形同音音切,“甫”是方类,“补”字是博类。这说明徐邈不能区别方类和博类。
(2)芳类与普类(缺例)
(3)符类与蒲类
《周礼·膳夫》:“王日一举,鼎十有二,物皆有俎,以乐侑食。”注:“鼎十有二,牢鼎九,陪鼎三。”《释文》:“陪,徐蒲来反。”
《左传·昭五年》:“飧有陪鼎。”《释文》:“陪,薄回反,徐扶杯反。”
这两例的“陪”字都是“叠加、相重合”义。徐邈注的两个音“蒲来反”“扶杯反”只能是同音异切。因此,徐邈不能区别蒲类和符类。
(4)莫类与武类
《诗·柏舟》:“觏闵既多,受侮不少。”《释文》:“侮,音武,徐又音茂。”
《礼记·曲礼》:“礼不踰节,不侵侮,不好狎。”《释文》:“侵侮,徐(云)亡抚反”
《周易·盘庚上》:“汝无侮老成人。”《释文》:“侮,亡抚反。”
《左传·宣十二》:取乱侮亡兼弱也。”《释文》:“侮,亡吕反。”
《柏舟释文》中“侮”是名词“侮辱”义,《曲礼释文》中“侮”是动词“欺负,侮弄”义。《柏舟释文》的音茂是徐邈的又音。除非有证据证明这个又音也是为“侮辱”的意义作注,不能直接认为这里徐邈的“又音茂”也是和《释文》首音注同一意义。《释文》一共有4个侮字注音:《盘庚上释文》《宣十二释文》没有一例可证明徐邈的“音茂”是为“侮辱”的意义作注。只能认为这里的音茂是徐邈为动词“欺负、侮弄”义作的音。所以,徐邈的“音茂”和“亡抚反”是同音异切。因此,徐邈不能区别武类和莫类。
反切比较法和《释文》反切材料都证明了徐邈的方芳符武和博普蒲莫是不区别的,即只有洪音博普蒲莫一组。
(二)《字林》唇音声类
1.用反切比较法看唇音声类的关系
(1)方类与博类
《字林》方类对应《切韵》方类(aa型1例):鳺(甫于)。
《字林》博类对应《切韵》博类(AA型4例):蚆(音巴)、豝(百麻)、秕(音匕)、编(布干)。
《字林》方类交替《切韵》博类(aA型11例):昄(方但)、闭(方結)、襮(方沃)、犦(方沃)、驳(方卓)、髀(方爾)、贬(方犯)、穮(方犯)、嬖(方豉)、枫(方廉)、秠(夫九)。
总体来看,《字林》方、博类共16例,其中细音对应《切韵》细音1例,洪音对应《切韵》洪音4例,洪细交替11例。方类与博类洪细交替数占总数的11/16,交替比例为69%,远大于25%,反映《字林》音不分别方类与博类。
(2)芳类与普类
《字林》普类交替《切韵》芳类(Bb型4例):副(匹亦)、丰(匹忠)、孚(匹于)、仆(匹往)。
《字林》普类对应《切韵》普类(BB型4例):眅(匹姦)、媲(匹地)、盼(匹间)、剽(匹召)。
总体来看,《字林》普、芳类共8例,其中洪音对应《切韵》洪音4例,洪细交替4例,交替数占总数的50%。这个比例说明《字林》芳类与普类尚不能区分。
(3)符类与蒲类
《字林》蒲类对应《切韵》蒲类(CC型2例):藨(平兆)、欂(平各)。
《字林》符类交替《切韵》蒲类(cC型8例):駜(父必)、仳(扶罪)、鵧(父隹)、鲂(音房)、凭(父冰)、瓣(父见)、軷(父末)、批(父节)。
《字林》符、薄类共10例,其中《字林》细音交替《切韵》洪音8例,洪音对应《切韵》洪音2例,洪细交替数占总数的80%。该比例说明《字林》的符类与薄类不能区分。
(4)武类与莫类
《字林》武类对应《切韵》武类(dd型4例):蝒(亡千)、蟁(亡巾)、冕(亡辩)、鸍(亡支)。
《字林》莫类对应《切韵》莫类(DD型4例):皿(音猛)、坶(音母)、鹛(音眉)、獌(音幔)。
《字林》武类交替《切韵》莫类(dD型18例):霾(亡戒)、甍(亡成)、蟊(亡牛)、昧(亡太)、霡(亡革)、堥(亡牢)、楙(亡到)、梦(亡忠)、冥(亡定)、灭(武劣)、冕(亡辩)、貉(亡白)、霿(亡弄)、睦(亡六)、蛑(亡牢)、鸍(亡支)、姆(亡又)、堥(亡周)。
《字林》武、莫类共26例,其中《字林》细音对应《切韵》细音4例,《字林》洪音对应《切韵》洪音4例,洪细交替18例,交替数占总数的69%。这说明《字林》不区别武类与莫类。
2.结合文献注音看唇音声类
(1)方类与博类
《诗·扬之水》:“素衣朱襮,从子于沃。”《释文》:“襮,音博,《字林》:方沃反。”《切韵》:“襮,黼领,博沃切”;“衣领,补各切”。
《字林》:“方沃反”,反切上字“方”是方类,对应《切韵》“博沃切”的“博”(博类)、“补各切”的“补”(博类)。
《诗·载芟》:“厌厌其苗,绵绵其麃。”《释文》:“其麃,表娇反,芸也。《说文》作“穮”,音同,云:‘穮,耨鉏田也。’《字林》云:‘穮耕禾闲也。方遥反。’”
《字林》的“方遥反”是为“穮”字作音;《集韵》:“穮,悲娇切,耘田除草。”《字林》“方遥反”,切上字“方”(方类)对应《集韵》“悲娇切”的切上字“悲”(方类)。
上两例说明《字林》音切上字“方”可以对应《切韵》的博类,也可以对应《集韵》(《切韵》未收“穮”字)的方类。这说明《字林》音的方、博是不区别的两声类。
(2)普类与芳类(缺例)
(3)蒲类与符类
《诗·生民》:“取萧祭脂,取羝以軷。”《释文》:“軷,蒲未反。《说文》云:‘出必告道,神为坛而祭为軷’,《字林》父末反。”《切韵》:“軷,蒲盖切,祭道神,又蒲葛切”;“蒲拨切,将行祭名”。
《字林》“父末反”,切上字“父”(符类)对应《切韵》“蒲盖切、蒲拨切”的切上字“蒲”类。
《书·顾命》:“相被冕服,凭玉几。”《释文》:“凭,皮冰反,下同。《说文》作凭,云:‘依几也’。《字林》同,父冰反。”《切韵》:“凭,凭托,扶冰反。”
《字林》“父冰反”,切上字“父”(符类)对应《切韵》“扶冰反”的切上字符类。
上两例说明《字林》音切上字“父”可以对应《切韵》的蒲类,也可以对应《切韵》的符类。这说明《字林》音的符、蒲是不区别的两声类。
(4)莫类与武类
《诗·采苹》:“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听从。”《释文》:“姆,莫豆反。《字林》亡甫反,云:‘女师也’。郑云:‘姆者,妇人五十无子出,不复嫁,以妇道敎人,若今时乳母也。’”《切韵》:“姆,女师,《说文》作娒,莫侯切。”
《字林》“亡甫反”,切上字“亡”(武类)对应《切韵》“莫侯切”的切上字莫类。
《礼记·郊特牲》:“冕,玄冕斋戒。”《释文》:“亡展反,《字林》亡辩反。”
《切韵》:“冕,亡辩反,冠冕。”《字林》“亡辩反”,切上字“亡”(武类)对应《切韵》“亡辩反”的切上字“亡”(武类)。
上两例说明《字林》音切上字“亡”既可以对应《切韵》“莫侯切”的切上字“莫”(莫类),也可以对应《切韵》“亡辩反”的切上字“亡”(武类)。这说明《字林》音的武、莫是不区别的两声类。
据以上材料可知,《切韵》唇音所分细音方芳符武与洪音博普蒲莫8类,《字林》唇音不区别洪细,只有4类。这4类也可以叫作普蒲莫。它们与《切韵》博普蒲莫的区别是《切韵》这4类有与之对立的细音方芳符武,《字林》音则无。
(三)徐邈、《字林》与《玉篇》唇音声类比较
通过以上分析,得出徐邈的唇音博、方交替占总数的38.7%;普、芳交替占总数的37.5%;符、蒲交替占总数的64.5%;武、莫交替占总数的57%。《字林》唇音博、方交替占总数的69%;普、芳交替占总数的50%;符、蒲交替占总数的80%;武、莫交替占总数的69%。从交替比例来看,徐邈和《字林》的唇音都只有重唇音。但是,祖籍同为齐鲁方言区,《字林》的作者吕忱的博、方交替比例比徐邈的更大,这说明徐邈的博、方类开始分化得比《字林》要早。吕忱一生未到过南方,而徐邈是南渡之后的文人,他的语言应该更多地维持了北方语言的特点,南渡之后又受到吴方言的影响。徐邈的唇音分化是否受到了江东方言的影响呢?可以用反映江东方言的《玉篇》唇音来进一步证明:如果江东方言的博组、方组是分立的,就说明徐邈的唇音受到江东方言的影响。
对于《玉篇》的唇音声母,前人作过详细的研究。周祖谟[9]指出,《玉篇》是考察六朝吴音的重要材料,能够反映六朝江东方音的实际状况。他认为,江东方音的唇音博、方是分开的两类。欧阳国泰[10]认为,《玉篇》基本上分为博组和方组两类音。河野六郎[11]认为,《玉篇》基本上分为博组和方组两类音。综合各家研究,可以认为江东方言的唇音有博组和方组两组。徐邈的博组、方组开始分化,吕忱只有博组,两人唇音特征不同的原因应是徐邈南渡之后受到了当地方言的影响。这也是语言的接触与融合的结果。
三、从唇音声母看中原语言文化与江左语言文化的融合
南渡后的中原士族与江左士人的接触与融合,必然带来语言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上文通过对徐邈、《字林》唇音的研究,得出《字林》的唇音博组与方组是不分立的,徐邈的博组与方组已经开始分化。徐邈、《字林》的唇音不同,原因是徐邈南渡之后受当地吴音的影响,带上了吴音特色。但是,就整个语音系统而言,南渡北语更多地保留了北语的特征,因为北方迁居江左的世家大族在政权上、文化上占有绝对优势。这些中原移民基于其在政治、文化和人数方面的优势,对迁入地的江左文化有巨大影响力,使江左文化圈经受了强烈的冲击。南迁以后,世家大族仍然秉承中原语言文化,并以此严格教导子弟。颜之推《颜氏家训·音辞篇》:“吾家儿女,虽在孩稚,便渐督正之,一语讹替,以为己罪矣。”[1]233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士大夫子弟,数岁以上,莫不被教,多者或至《礼》《传》,少者不失《诗》《论》。”[1]65这都反映了东晋至南朝中原南渡士族对子弟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视。《文心雕龙·声律》:“张华论韵,谓士横多楚,《文赋》亦称知楚不易;可谓衔灵均之声余,失黄钟之正响。”[12]这是刘勰对陆机作文使用吴语的批判。可见,当时的雅音仍然是中原世家大族带过来的北语,当地吴语则受到轻蔑。
然而,江左语言文化亦对中原语言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当过江者老去,在江东出生的北人虽仍被视为中原士族,受到中原文化的熏陶,但自幼浸于吴音之中,其语言就不可避免地受到当地吴音的浸染,而带有吴方音色彩。上文得到徐邈的博组、方组开始分化,吕忱只有博组,江东方言的唇音有博组和方组两组。徐邈、吕忱语音特点不同,就是因为徐邈是南渡之后生于江东并在此成长,其语言在这过程当中必定会沾染吴方音特点。正如胡宝国所说:“东晋中期以后,侨人使用吴语应该是相当成熟了,他们已经可以模仿江南民间流行的吴歌进行创作。”[13]《世说新语笺疏》“刘真长始见王丞相”条下论曰:“东晋士大夫侨居久,又与吴中士庶应接,自不免杂以吴音,况其子孙生长江南,习其风土,则其所操北语必不能尽与洛下相同。盖不纯北,亦不纯南,自成为一种建康语。”[14]可见,南渡士人的语言也受到江左语言的影响。
中原语言文化与江左语言文化各自的特点导致两者之间的冲突与碰撞。但是,二者又在碰撞中不断地交流、融合与趋同。就语言而言,融合的过程大体是先出现双语现象,接着,如果两个民族关系越来越密切,其中某一个民族就会放弃自己的语言而接受另一个民族的语言。融合完成后,即便是被替代的语言,也会在胜利者的语言中留下自己的痕迹。徐邈祖籍为齐鲁地区,且是上层士大夫,他的语言一定保留了南渡前北语的底子。但是,由于他出生在江左且长期生活在吴音的环境下,他的语音出现了一种介于吴音和北音的中间状态。正如《颜氏家训·音辞》记载的南北朝时期的汉语已经“南染吴越,北杂夷虏”。也就是说,北语作为语言的胜利者,也带上了吴方音的色彩。文化方面,中原士族以其政治上的优势、文化上的感染力,引领了南方文化的潮流,使得江左士人竞相仿效。《抱朴子》的《疾谬》和《讥惑》篇就谈到当时江左吴人从礼俗观念到语言和书法艺术等方面效仿中原士人的情况。同时,迁居异域的中原士人要和江左士人和平相处,也必然受到江左地区语言、习俗、文化观念上的影响。如《乐府诗集》中属于南朝民歌的《子夜吴歌》《子夜四时歌》,反映出江左音乐深得中原南迁之士欣赏,且广为朝廷乐官演奏。
总之,江左语言文化、中原语言文化各自有选择地从对方的文化基因中选取有利因素,最终相互融合并趋于统一。 因此,东晋江左地区的语言并非是简单的北语与吴语并存,而是形成一种以北语为基础且杂有吴音特点的新语音。江左文化亦呈现出以传统中原文化为主题、以吴文化为特色的新面貌。
四、结语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民族大迁徙、大融合的时期,语言成为民族融合中的重要因素。语言接触会使语言之间相互影响,逐渐形成语言融合。永嘉之乱后,在汉族与少数民族聚集的北方地区,各少数民族与汉族融合,融合后的语言成为这些少数民族的共同语。值得肯定的是,语言融合在增进国家统一、提升文化认同、促进民族团结、加强民族互动等方面具有积极意义。西晋末年,大批北方士族豪门南迁,给南方注入了新鲜的文化因子,促进了不同民族间语言文化的融合,逐渐形成特色鲜明、风格迥异的“六朝文明”,为盛唐文化奠定了基础,对中华民族多元文化的丰富与发展起到重要作用。总的来说,永嘉之乱带来的社会变迁,在客观上促进了南北各民族在语言文化上的接触与融合。这场社会变革促进了民族的融合,推动了语言文字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