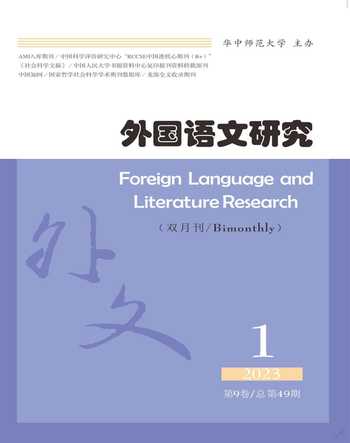非自然叙事与认知
张玉红 许庆红
关键词:非自然叙事学;反模仿;认知
作者简介:张玉红,安徽大学外语学院讲师,安徽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和美国、新西兰族裔女性文学。许庆红,安徽大学外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目前主要从事英语文学、西方文论和比较文学等领域的研究。
近些年,对非自然叙事的研究呈上升趋势,随着认知研究①的蓬勃发展,以及国内学者对“ 物叙事” ②的提出与研究进展,关于非自然叙事的研究空间也得以极大拓展。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领域越来越注重与认知科学的交叉,文学研究中出现了认知转向(cognitive turn),文学研究者借鉴认知科学提供的理论启示、研究方法乃至技术手段,拓展相关文学研究理论视域、更新研究方法、延伸研究路径(熊沐清296)。20 世纪60 年代以来,随着文学进入更加具有先锋性的后现代主义时期,文学叙事艺术继现代主义叙事研究之后成为一个更加重要的关注点。后现代叙事实践的创新速度惊人,而叙事理论却发展缓慢,未能将这些创新充分概念化,并整合到现有的叙事理论模型之中。在这一背景下,非自然叙事学(Unnatural Narratology)的概念应势而生。
非自然叙事学始于1987 年其首创者布莱恩· 理查森(Brian Richardson)对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中的反常或极端叙事的探讨, 旨在分析现当代欧美小说多种反模仿的叙事行为。在《非自然的声音:现当代小说的极端化叙述》(Unnatural Voices: ExtremeNarration i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Fiction)中论及“ 非自然” 的概念时,理查森把非自然界定为反模仿、陌生化的场景、实体和事件,如不可能的空间、颠倒的因果进程以及公然蔑视自然口头叙事范式的叙述行为(48- 52)。他认为,面对偏离现实主义认知框架的时间形式,经典叙事学的时序概念束手无策。在对模仿(mimetic)、非模仿(nonmimetic)和反模仿(anti-mimetic)的虚构作品进行区分之后,理查森继而指出,只有反模仿才是非自然的。受莫妮卡· 弗卢德尼克(Monika Fludernik)与理查森的启发,一批叙事学研究者,如扬· 阿尔贝(Jan Alber)、亨里克· 斯科夫· 尼尔森(HenrikSkov Nielsen)及斯特凡· 伊韦尔森(Stefan Iversen)也加入到自然叙事学与非自然叙事学的辩论中,与理查森一起撰文阐述非自然叙事理论。“ 非自然叙事” 与“ 非自然叙事学” 概念在阿尔贝、伊韦尔森、尼尔森以及理查森的合著论文《非自然叙事、非自然叙事学—— 超越模仿的范式》(“Unnatural Narratives, Unnatural Narratology: BeyondMimetic Models”)中得以正式形成:“ 非自然叙事学” 所研究的“ 非自然叙事” 指的是“ 违背传统现实主义参数的反模仿文本,或者是超越自然叙事规约的反模仿文本”(114)。
作为一种新的诗学,非自然叙事学研究一直在不断发展与完善之中。其研究者从未希望或试图将非自然叙事学视为严格统一的叙事研究范式,他们在基本概念、研究方法、研究目标等方面观点并不一致,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两大阵营,即本质派与非本质派。前者以理查森和尼尔森为代表,关注文本的“ 内部本质”;后者以阿尔贝为代表,重视对文本进行“ 外部阐释”(Richardson, Unnatural Narrative 19)。对于非自然叙事学研究的“ 内部本质” 与“ 外部阐释” 阵营的形成,认知进化与文化进化理论提供了崭新的阐释视角。认知与文化有着相互缠绕、相互促进的关系,因为人是进化的产物,基因、环境和文化促进了人的进化,也影响了人对文学的阐释。认知进化与叙事有着密切的关系,叙事是文化学习,也是社会学习,而文学研究者们“ 运用认知科学的理论、话语、方法和技术去讨论文学艺术问题或文艺作品,其中有些人有着自觉的理论建构意识,引发了许多传统的、经典的和流行的文学研究范式嬗变,甚或衍生出全新的研究范式”(熊沐清299)。随着认知与进化的发展,叙事研究的概念与实践也呈现出丰富多样性。
非自然叙事的基本概念方面,理查森意识到文学进化过程中“ 模仿论” 所受到的挑战,“在文学进化过程中,模仿的规约持续受到原创作品中不断涌现的新文学形式的挑战”(“Unnatural Narrative Theory” 388)。不同于传统叙事中的“模仿”,理查森提出了“反模仿”的叙事概念和实践,认为违反非虚构叙事前提、现实主义实践的非自然事件、人物、背景或框架表征,或其他建立在非虚构叙事基础之上的诗学,都是“反模仿”的(Unnatural Narrative 3-5)。以理查森为代表的本质派从叙事本质出发,关注文本对叙事规约的反叛,将文本中的非自然叙事等同于“反模仿”叙事,认为非自然叙事指的是那些“反模仿事件、人物、场景或叙述行为的叙事”(Richardson, Unnatural Narrative 5),而现有叙事理论“几乎是完全建立在模仿叙事作品和模仿概念的基础之上的,并未给当代文学作品中广泛存在的创造性的、不可能的、戏仿的,或矛盾的事件和人物留有任何理论空间”(Richardson, “Unnatural Narrative Theory” 387-388)。理查森以莎士比亚戏剧《仲夏夜之梦》和《麦克白》为例,撰文探讨剧中的“反模仿”叙事时间,解释其中的时间和因果关系的非自然构造,引起人们对广泛存在的各种非自然叙事文本的注意(Richardson, “Time is Out of Joint” 299, “Hours Dreadful and Things Strange” 284)。事实上,“反模仿”的叙事概念和实践与后现代小说的叙事实践相互缠绕,如弗卢德尼克在《走向“自然的”叙事学》(Towards a “Natural” Narratology)一文中所言,结构主义叙事理论中的自然叙事研究范式具有局限性,无法对违背现实主义传统的后现代小说中的反常叙事模式做出合理解释。基于这一问题,理查森撰文对弗卢德尼克的自然叙事理论做了补充,在自然叙事学的基础上提出“非自然叙事学”,专门研究虚构叙事文本中具有“反模仿”元素或呈现“反模仿”特征的事件、人物、环境和结构。通过借鉴后现代主义理论,理查森研究分析了果戈里、康拉德及贝克特等作家作品中呈现出的违反常规叙述的叙事时间、声音和情节进程,确定了在现实世界中不可能的六种类型时间結构,构建了一个非自然的模型③。
通过区分“反模仿”(即适当的非自然)、“非模仿”(或传统的非现实主义)和“模仿”(或现实主义),理查森认为违反模仿常规是非自然叙事的首要特征。一个与现实世界具有相似的概率标准的虚构世界是模仿的,一个基于熟悉的命运或天意概念的超自然世界是非模仿的,而一个过去的事件可以被改变或抹去的世界是反模仿的或非自然的(Richardson, “Unnatural Narrative Theory” 392-393)。因此,本质派通过解读虚构叙事文本中与故事、时间、叙述、人物和结构相关的“反模仿”元素,发掘在主流叙事建构过程中被忽略的叙事实践,为当代文学作品中广泛存在的反模仿叙事提供了一种阐释方法,丰富了叙事的概念与实践,实现了文学阐释与认知进化的同步发展。
从认知科学的角度而言,进化是认知的,文化也是认知的,认知是文化的一个重要维度,而文化本身的进化在人类进化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影响了文学研究,人的认知生态位说明,文化比基因更能促进人的进化。因此,多数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本都旨在打破现实主义,尝试模仿幻觉、嘲弄“自然”文本规约,但是,自然叙事理论似乎无法给读者提供阐释和认知这些具有“非自然叙事”元素文本的理论支撑。理查森等人基于认知理论,提出可以依照流动的、变化的规约,通过“丰富认知框架”(frame enrichment)来拓展叙事研究(“Unnatural Narratives, Unnatural Narratology” 118)。
综合来看,无论是本质派还是非本质派,二者对非自然这一概念的界定都是以反模仿为理论基础,强调偏离现实世界认知框架的各种叙事策略。然而,与“ 内部本质”阵营有所不同,在非自然叙事实践方面,非本质派倾向于从认知文化层面阐释和解读文本里的非自然元素。阿尔贝倡导使用认知叙事学的相关成果去解读一些叙事文本依赖并挑战人类基本的意义建构能力的行为,“ 非自然叙事文本中大量存在的棘手难题可以借用认知叙事学的一些观点进行阐明”,通过阐释和理解非自然叙事,发掘其认知功能及其意蕴,“ 让奇特的叙事更加具有可读性”(“Impossible Storyworlds” 81)。將现实的经验世界视为基本参照,同时关注读者的认知维度,非本质派更偏重于寻找非自然事件认知上的作用,并判断其意义。
从认知角度而言,非自然叙事学为叙事文本中非自然元素的系统研究提供了新的认知叙事类别和小说中叙事表现的扩展模型,包括类型多样的非自然叙述者、非自然人物、不可能的事件序列和非自然场景。从理论属性来看,非自然叙事学者认为他们并非意欲否定、推翻或替代现有的其他叙事理论,而是通过关注虚构文本中那些被忽略的“ 反模仿” 叙事元素,建立“ 一个模仿和反模仿双重互动的模式”(Richardson,Unnatural Narrative 5),对现有叙事理论进行认知方面的补充和拓展。戴维· 赫尔曼(David Herman)认为, 叙事就是一个认知资源库,通过阅读叙事,人类可以认识自己的经验,但“ 任何一个单一的研究视角:模仿、综合或意识形态的视角,都必然是不充分的。留下来更多的是对反模仿人物的分析和拓展”(234)。赫尔曼从认知科学的基本框架开始理论建构,在叙事学研究中引入心理学前沿理论,丰富了叙事学领域基本概念的内涵,在认知叙事学的道路上不断开拓。弗卢德尼克将“ 非自然叙事” 界定为“ 逻辑上或认知上的不可能,以及寓言、魔幻、超自然”,认为以自然叙事学为表征的普适认知叙事研究方法不仅可以“ 为叙事性的建构提供理论原型”,而且“ 可以成为认知起源的核心生产模式”(Towards a “Natural”Narratology 234)。弗卢德尼克曾多次撰文对自然叙事学和非自然叙事学之间的异同进行剖析,并与理查森和阿尔贝等人展开对话。就此意义而言,非自然叙事学的研究效果,更多产生于人们对非自然叙事文本的阐释过程之中,产生于文化在人类进化的过程之中所发挥的作用。读者通过对非自然叙事文本的关注,解读出作品中被经典叙事理论忽视的那部分内容,使用认知叙事学的相关理论对非自然叙事元素做出合理的解释,并重新建构意义。
除了前面述及的“ 反模仿” 概念,非自然叙事学中最贴近认知叙事学的另一个核心概念是“ 不可能的故事世界”(impossible storyworlds)。阿尔贝在论文《不可能的故事世界:以及怎么理解它们》(“Impossible Storyworlds-And What to Do with Them”)中首次对“ 非自然” 这一概念做了界定,并阐发其所包含的两种“ 不可能的故事世界”。其一,“ 非自然” 这个术语指的是物理上、逻辑上或人类世界不可能出现的行为,这些行为已经被“ 规约化”(conventionalization),成为熟悉的叙述表现的惯例。其二,“ 非自然” 还指尚未被“ 规约化” 或者仍然被陌生化或者仍处于被“ 规约化” 过程中的现象,就像后现代主义文本中的大多数非自然元素及其呈现的“ 不可能性”,比如死去的叙述者、化身成其他人物、倒退的时间线和能够改变形状的设置一样。阿尔贝认为,“ 非自然” 这一概念就变成了一个基本的认知类别,给人们留下奇怪、令人不安的印象,“ 认知叙事学的观点可以帮助阐明非自然元素所造成的大量的、有时难以解决的阐释困难”,并提倡使用“认知叙事学的研究来阐明有些叙事文本如何不仅仅会依赖而且也会猛烈地挑战基本的思维理解能力”(“Impossible Storyworlds” 80)。阿尔贝相信,由于我们受到自身认知结构的限制,所以只能通过使用框架和认知草案来研究非自然。阿尔贝认为“叙事中的这类非自然(或不可能)是基于‘自然(真实世界)中的认知框架和草案的,而这种认知框架和草案又是和自然规则、逻辑原则和标准化的人类知识和能力限度相关”(Unnatural Narrative 3)。以阿尔贝为代表的非本质派从认知出发,提出非自然叙事的阐释策略,帮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借助真实世界的认知将非自然叙事“规约化”(3)。换言之,要理解非虚构叙事文本中的非自然元素,读者需要调整、整合或拓展其认知框架,通过认知阅读,把非自然叙事元素“规约化”。
针对“不可能的世界”,非本质派的研究方法需要注意的是文化相对性的问题。如果将“非自然”定义为物理上或逻辑上的不可能性,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跨文化以及文化的进化或变化,人们将很难决定这些术语的可能性与不可能性。很多概念在某种文化中具备不可能性,但在其他文化中,其可能性却被广泛肯定。因此,需要从认知的角度假设科学标准是唯一可能的仲裁者。正如阿尔贝和理查森在他们最新合编的《非自然叙事学:延申、修订与挑战》(Unnatural Narratology: Extensions, Revisions and Challenges, 2020)一书中所指出,当把一个行为或事件定性为非自然时,其不可能性通常是根据科学公认的物理定律或逻辑公理来判定的,比如,强风不能像卢西恩(Lucian)的《真实故事》(A True Story)那样把船吹向月亮。无论人们是否利用爱因斯坦或亚里士多德的科学理论,这些事件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可能的。逻辑的公理同样是普遍的:被排除在外的中间法则同样不会,也不能随着时间或跨文化而改变。他们认为,非自然叙事学所提出的非自然概念与支配物质世界的已知定律、公认的逻辑原则(如非矛盾原则)或人类对知识和能力的标准限制相矛盾,比如,说话的乳房、尸体,或飞行的岛屿在世界各地和整个时间段都是不可能的。因此,识别非自然叙事的唯一前提是叙事接受者相信这些准则、原则和限制(Alber & Richardson, Unnatural Narratology 9-10)。虽然本质派与非本质派对非自然的表述不同,但他们都认为,非自然指的是由经验证据和基础科学探究建立的现实世界中不可能的事物或现象。
事实上,非自然叙事无处不在,甚至会自发地独立产生。坚持模仿立场的认知叙事学理论强调人类体验与文学交互作用的同源性,忽视甚至抛弃了许多未被理论化的经典和现代叙事的非自然特征,包括数以千计的反模仿人物(从阿里斯托芬的戏剧到贝克特笔下“无法称呼的人”,再到兔八哥),以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述的原住民小说,梵语戏剧和中国古典小说,反现实主义的日本能剧,具有很多反现实主义技巧的中世纪叙事。正如阿尔贝和理查森在《非自然叙事学》后记中所言,非自然研究涉及大量西方经典文学作品,从阿里斯托芬、拉伯雷到詹姆斯·乔伊斯,从文艺复兴到浪漫主义,从莎士比亚到斯威夫特和菲尔丁,可谓成果颇丰,针对与西方传统关联较弱的古典梵语故事、中国古典文学、现代漫画、漫画小说、电影、电视和数字媒体的非自然分析也日渐丰富(Unnatural Narratology 209-218)。因此,每一个时期,每一种类型的非自然叙事都在蓬勃发展,值得研究者从这个广阔的理论角度进行研究。
纵观近十年的非自然叙事研究,非自然叙事理论拓宽了研究的边界,突破了现有叙事理论的模仿偏见,为广泛存在但长期被忽略的边缘叙事实践提供了新的解释模式,成为叙事理论中一个重要而富有成效的新范式。受到维克多· 什克洛夫斯基(ViktorShklovsky)、米哈伊尔· 巴赫金(Mikhail Bakhtin)、克里斯汀· 布鲁克- 罗斯(ChristineBrooke-Rose)、莫妮卡· 弗卢德尼克、布莱恩· 麦克黑尔(Brian McHale)、詹姆斯·费伦(James Phelan)和沃纳· 沃尔夫(Werner Wolf)等人在叙事理论研究方面的启发,非自然叙事学家将认知叙事学、女性主义、酷儿理论、后殖民以及接受理论等其他研究理论融入非自然叙事研究,实现理论和方法的交叉与互补,致力于寻求不同领域之间的对话④。需要指出的是,尽管非自然叙事的文本案例属于激进政治运动所寻求的实验艺术形式,但非自然叙事理论在意识形态上仍是中立的。还有理论家指出,非自然叙事学研究者应该将非自然叙事学与情感研究、文化相对主义、流行文化等研究融合,拓展非自然叙事学的研究范畴,以求在发展过程中不斷修正、完善、拓展其自身的理论建构。然而,在非自然叙事学不断拓宽研究边界的过程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作为一个新兴的叙事研究范式,非自然叙事理论受到学者们来自各个方面的质疑、批评与挑战。自2010 年起,西方叙事学界对非自然叙事学的研究表现出极大的学术兴趣,对其探讨的热度不断增强。文学研究领域的著名期刊《文体》(Style) 在2016 年第4期以专题论坛的形式,隆重推出“ 非自然叙事学” 专题,学者们从多个角度对其发起批评和挑战。有些学者对非自然叙事学的创新性或对模仿的潜在理解持怀疑态度;有些学者则认为,由于非自然叙事学内部未能形成统一的定义,那么从其研究的出发点、内容和属性三个方面来看,其学理性都不强;还有学者认为非自然叙事学内部在非自然、规约与不可能等概念的界定方面仍存争议,缺乏作为一个叙事研究范式的合法性。针对以上的质疑与挑战,理查森与阿尔贝也围绕非自然叙事的基本特征、中心策略及其影响在最新出版的《非自然叙事学:延伸、修订与挑战》一书的前言部分进行了回应。
非自然叙事理论的内部差异对非自然叙事学作为一个叙事研究新范式的整体性建构带来了一定的挑战,不利于非自然叙事学作为一个一元叙事研究流派的进一步确立。非自然叙事在对现有的模仿叙事研究进行补充和拓展的同时,也因研究者所持立场不同,其内部存在诸多观点差异,面临一个如何统筹和整合内部的多维研究视角的问题,但其研究视角的多维性又将吸引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尤其是年轻的研究者,运用非自然叙事理论解读文本中的非自然元素,推动非自然叙事学迅速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