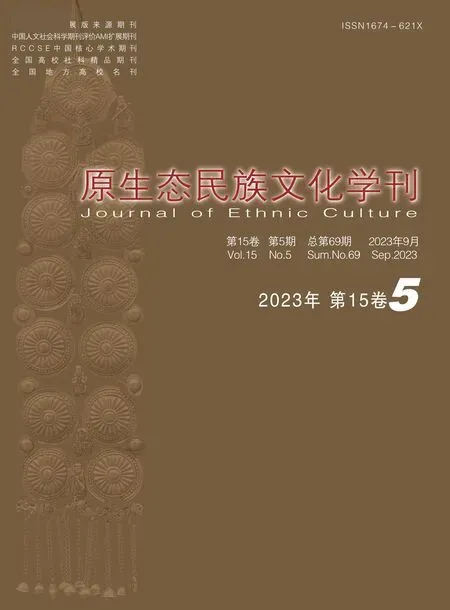略论黔北渝南的历史地理学意义
马 强,郝家彬
现代地理语汇中的“黔北渝南”大体是指渝西南綦江流域至贵州北部大娄山山地及其部分乌江、赤水流域地区,包括今日重庆之南川、綦江、万盛,贵州遵义及其东北的桐梓、绥阳、道真、务川、正安等地。从历史上看,这一地区虽然地处华夏文化的边缘地带,但汉夷混杂,民族分布众多,交通地位显要,军事战争频繁,经济交流密切,文脉血肉相连,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中不可忽略的西南一角。在中国石器时代考古谱系中,黔北地区是古人类进化史上重要一环,“桐梓人”早已闻名中外考古学界。商周战国秦汉时期这一地带酋邦①根据著名人类学家摩尔根的理论,“酋邦”是指原始社会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以氏族为基本单位,大致经历了氏族、胞族、部落、部落联盟等几种社会组织形式。战国秦汉时期中原地区早已进入王朝国家时代,而西南地区的夜郎、且兰、鰼国、滇等《史记》所载之“西南夷”,虽然文献冠之以“国”之谓,实则尚未进入国家社会阶段,多为以家族血缘为纽带的部落联盟,故以“酋邦”称之相对合适。林立,先后有鰼国(今赤水、仁怀一带)、古巴国、鳖国(今绥阳、桐梓、遵义一带)鰼国等出现,战国后期到至秦汉,又有夜郎国控制该地区。魏晋南北朝唐代,渝南黔北主要是僚蛮地盘,唐代盛极一时的“南平蛮”即以今日南川、綦江、桐梓为活动中心。而自唐朝末年形成的播州杨氏土司在遵义存在七百余年之久,系元明时期西南地区势力最大的土司王国。在现代中国革命史上,黔北渝南曾经是红军长征北上由危转安的转折之地,綦江、桐梓是遵义会议期间中央红军的前哨警卫阵地,保障了遵义会议的安全顺利召开。而赤水河流域尤其以1935 年中国工农红军占领遵义后召开的“遵义会议”及其毛泽东指挥的“四渡赤水”辉煌战役而载入史册。20 世纪60 至70 年代,又是国家三线建设重要布局的一部分,大量兵工、电子、机械工业迁徙这一地区,今天已经成为中国现代西南重要的工业文明遗产地。除此之外,赤水河流流域的名酒文化、綦江流域的悬棺文化、黔北地区的移民文化等也是颇有地方特色的文化遗产,因而渝南黔北地区历史文化资源十分富集,而且具有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典型意义①笔者近年关注渝南黔北历史地理,此前曾经发表《略论赤水河流域的历史地理地位及其意义》,对连接川黔赤水河沿线历史文化资源及其历史地理学研究价值一文作过初步阐述,参见刘一鸣主编《赤水河流域历史文化研究论文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18年。,这里试从四个方面略加探讨,以请教于诸方家。
一、黔北渝南的考古地理学意义
考古地理学(archaeological sequence)是指以考古发现及其遗址现象为研究对象,考察人类古代文物遗址的地理空间分布地理现象的科学。黔北渝南是西南考古地理的富集地区,在现代中国考古图谱上是一个从云贵高原文明向四川盆地古蜀文明的过渡地带。黔北的史前时代有重要的考古地理学意义,云贵高原文明曙光升起之前远古人类活动留下踪迹较多的古人类遗迹。从近几十年来黔北地区的考古发现来看,旧石器时代人类活动踪迹主要分布于黔北地区的桐梓县与赤水河一带。上世纪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考古工作者先后在遵义地区发现了桐梓县岩灰洞、马鞍山、马鞍山南洞,遵义市风帽山等多处史前洞穴遗址。进入21 世纪以来,考古、文物工作者又先后发现了绥阳县营盘洞、叉口洞,习水县渔溪洞、打游洞等史前遗址,随着新的考古发现的不断增加,使得考古学界对这一地区的旧石器时代遗存有了更加深入和全面的认识。在黔北旧石器时代考古文化中,最重要的就是距今20 万年的“桐梓人”发现。“桐梓人”之所以倍受考古学界的重视,是由于它填补了古人类发展进化过程中一个关键环节。在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古人类进化序列中,已经发现了距今170 万年的元谋人、70 万年的蓝田人、60 万年的北京人、50 万年的马坎人、40 万年的长阳人、30万年的丁村人、10万年的观音洞人、4万年的柳江人。在“桐梓人”发现以前,我国境内距今20万年左右的古人类化石一直是一个缺环。“桐梓人”的发现正好连接上这一人类发展进化的链条。从“桐梓人”岩灰洞出土的旧石器和烧骨的研究中,发现了古人类用火的痕迹,是迄今长江以南最早的发现,具有重大的学术研究价值。
地处川黔古道的重庆綦江、南川、万盛沿线虽然尚未发现桐梓区那样的远古古人类活动遗迹,但却拥有多处汉代崖墓、抗击蒙古城堡及其僚人遗迹。綦江区三角镇东汉崖墓群,目前已现发现43 座、分布面积达1 500 平方米的东汉崖墓。类似的崖墓还在三角镇的桐垭金银、黄泥湾、海会寺、洞子河、双龙湾等都有发现,总数达65个之多。崖墓,当地俗称“蛮子洞”,实际上是汉代较为流行的一种仿生人住宅、凿山为室的墓葬形式。即东汉人冯衍所说:“凿岩石而为室兮,托高阳以养仙”②范晔:《后汉书》卷28《冯衍传》,中华书局,1965年,第999页。。当然,这类人工开凿的洞穴也有可能是时人养生求仙的修炼作用,如明朝人沈季友所说崖墓为“古得道之人藏丹之所”①沈季友:《檇李诗系》卷21《青龙观古墓有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75 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年,第484页。。道光《綦江县志》记载:“渝州远近多七孔子,而綦江最多,横于山颠,或河岩石壁上……去地什高,需数十步长梯可上人,窥内洁净干燥,空无所有”②《綦江县志》卷9《古迹》,重庆市地方志办公室辑,《重庆历代方志集成》卷47,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0年,第84页。。可见綦江崖墓分布之广泛。重庆南川境内古代遗址同样数量多,2019年2月至3月,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及南川区文物管理所对来游关墓地两座宋代墓葬开展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工作,发现的宋代墓葬雕刻,图案精美、工艺精湛,可能与川渝地区佛教净土宗的影响有关,且级别高。此外,黔北渝南还是南宋抗击蒙古的重要防御前线,宋蒙古战争留下了南川龙崖城、遵义海龙屯这样重要的宋蒙战争古城堡,已经日益引起学界的重视③说参马强、张祥永:《关于深化四川宋蒙古战争古城堡研究的若干问题》,《西部史学》2022年第1期。。今日重庆南川一带自古以来就是黔北到渝西的必经之路,为兵家所必争。南川的南宋龙崖城是著名的抗蒙山城,修筑于宋理宗宝祐四年(1256 年),两年以后迫于云南蒙军对于四川的威胁,又对龙崖城进行了增筑。开庆元年(1259年)曾两次击退蒙军的进攻,是南宋抗蒙元山城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曾经牢牢阻击南下的蒙古军于山城之下五载而未失守,与合川钓鱼城齐名,被誉为“南方第一屏障”。龙崖城曾在民国二年(1913 年)进行过维修,继续发挥重要的军事防御作用。民国五年,川军一个连驻守在龙崖城上,与云南护国军历经了两次战斗,2000 年被重庆市列为第一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遵义汇川区的海龙屯虽以明末平定播州土司杨应龙而闻名,实则为最早修筑于南宋抗击蒙古侵略之时,与重庆著名的合川钓鱼城的修筑大约同一个时期,曾经有效地防御了蒙古军队从云、贵包抄南宋川南防线的企图。因此,海龙屯的考古从年代层面上说至少可以具有两个中国历史上重大事件的考古学价值。
二、黔北渝南:历史政区地理中的“犬牙交错”现象
在我国跨省际地带存在一些行政区域交错存在的地区,历史地理学把这一政区现象形象地比喻为“犬牙交错政区地带”。历史进入国家社会以后,在疆域管理与控制上施实施行政区划是一个国家基本的政治行为,战国中期出现的郡县制度就是延续时间最长的一种政区制度,但政区地理又往往受地理环境特别是山川地貌的制约。一般而言,秦汉至唐代,王朝国家体国经野、设置划分政区的原则是山川形便,即大体上以山脉、河流、湖泊的自然界线为政区分界,便于行政治理与权属管辖。秦汉时代的州郡县制度、唐代前期的道制(由监察区形成)基本上遵循了这一政区划分原则。大致从唐代中期安史之乱以后开始,这一政区划分原则被不断打破,政区开始出现因政治、军事行为而形成的相互穿插的复杂态势,历史地理学将这一现象形象比喻为“犬牙交错””。在蒙元征服全国的战争背景下,蒙古元朝出于战争的需要,有意打破此前政区地理山川轮廓的整体性,设置诸多行中书省,如把自秦汉以来一直属于巴蜀政区的兴元府(汉中)划给陕西行中书省就是典型事例。渝南黔北作为中国西南东北边缘历史上长期处于汉夷混杂地带,其政区地理中的“犬牙交错”形成时间更早,表现得得十分典型,特别是黔北地区历史上在川黔之间变迁频繁,归宿不定,反映了不同时期中央王朝在这一地区政区建置沿革的不确定性。
因地理环境的封闭与地理方位的偏僻,黔北渝南地区进入华夏主流史学记载体系时间相对较晚,主流史学大致从战国秦汉时期开始对这一地区有了零星的记述。与此同时,黔北渝南地区的政治地理即呈现复杂的态势。开始出现历史记载的战国时期,黔北地区即分别存在夜郎、牂柯、巴、蜀、鳖、鳛等邦国。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 年),唐蒙出使夜郎,中央置犍为郡,郡治鄨县(今遵义城区),初领夜郎等二县。元鼎六年(前111年)平南夷并设牂牁郡,领县十二,即僰道、江阳、武阳、南安、资中、符县、牛鞞、南广、朱提、蚲鄢、堂琅、汉阳,地跨今日川、黔、滇三省。
唐宋时期渝南地区行政区划屡屡变迁,省并更名频繁,蛮僚汉民混杂,区内经制州与羁縻州相互参杂并存。活跃在唐代的“南平獠”就分布在这一地区,史载“南平獠,古部落名,东与智州、南与渝州、西与南州、北与涪州接。部落四千余户……遣使内附,以其地隶于渝州”①《旧唐书》卷197《南平獠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5277页。。《旧唐书·地理志》:“夜郎,汉夜郎郡之地。贞观十七年,置于旧播州城,以县界有隆珍山,因名珍州。丽皋、乐源并贞观十六年开山洞置。”②《旧唐书》卷40《地理志》,第1629页。《宋史》:“渝州蛮者,古板凳七姓蛮,唐南平獠也,其地西南接乌蛮、昆明哥蛮,大小播州部族数十居之”。其中智州即为羁縻州,而《宋史》则明确认为“渝州蛮”源自秦汉时期的“板凳(楯)蛮”③脱脱等:《宋史》卷496《蛮夷四·威茂渝州蛮》,中华书局,1985年,第14240页。。
唐代史籍文献对黔北渝南地区政区建置、隶属、沿革等舆地文献记载稀疏简略,且不少州县的建置省并语焉不详,而有关碑刻则一定程度上弥补一些政区地理的缺陷,保存着一些有价值的政区信息。幸存的《大周珍州荣德县丞梁君墓志铭》④郑珍,莫有芝原纂,遵义市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整理:《遵义府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1431-1432 页,对此碑历史地理价值的详细考证参见马强《乌江流域土司碑刻的史地学考察》一文,《民族学刊》2018年第5期。大约作于武则天万岁通天二年(697 年),是乌江流域前土司时代最早的唐人石刻。墓志铭载志主梁师亮先医后宦,“起家任唐朝左春坊,别教医生”,武则天时,“授珍州荣德县丞”。武后万岁通天二年卒。其中提供了唐代珍州的政区信息。珍州为唐初所置县,与夜郎县⑤唐代有二夜郎县,一在今湖南新晃,一在今贵州桐梓。(唐朝夜郎县城遗址位于现贵州省桐梓县城北48 公里的夜郎镇,贞观十六年置)相邻,今属地贵州省正安县,荣德县两《唐书》失载,但梁师亮墓志题额却赫然有“珍州荣德县”。《旧唐书》卷四十《地理志》:“珍州,下,贞观十六年置。天宝元年改为夜郎郡,乾元元年复为珍州。领县三,户二百六十三,口一千三十四。至京师四千一百里,至东都三千七百里”,未载具体三县县名。《旧唐书·地理志》又谓“夜郎,汉夜郎郡之地。贞观十七年置于旧播州城,以县界有隆珍山,因名珍州。丽皋、乐源,并贞观十六年开山洞置”⑥《旧唐书》卷40《地理志》,第1629页。,仅仅提及珍州领有丽皋、乐源二县,遗漏荣德县。而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则明确载有丽皋、乐源、荣德诸县,并说“以上三县,皆唐贞观十六年开山洞,分夜郎之地以置,其县并在州侧,近或十里,或二十里,随所畬田处为寄理移转,不定其所”⑦乐史:《太平寰宇记》卷122《江南道·西高州》,中华书局,2007年,第2426页。。可见珍州有荣德县并非虚言。珍州也为唐朝流贬罪臣之地,武则天时内史邢文伟坐附宗秦客罪,“贬授珍州刺史”⑧《旧唐书》卷189《邢文伟传》,第4960页。;酷吏周利贞也曾流放珍州⑨《新唐书》卷209《周利贞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5913页。,安史之乱后宗室李元平因降附方镇李希烈,“流于珍州”①《旧唐书》卷130《李元平传》,第3630页。。后来卢征因坐刘晏事也曾流放珍州②《旧唐书》卷146《卢征传》,第3966页。。但这些记载均只言及珍州,而未及荣德县。《太平寰宇记·江南道·西高州夜郎郡》条载:“唐贞观十七年,廓僻边夷,置播州镇。后因川中有隆珍山,乃以镇为珍州,取山名郡也。长安四年,又改为舞州。开元十三年改为鹤州,十四年复为珍州”。并在“西高州”条下说领有四县:“夜郎、丽皋、荣徳、乐源”③乐史:《太平寰宇記》卷122《江南道·西高州》,中华书局,2007年,第2426页。。《太平寰宇记》虽成书于北宋初,但所载政区大多属于中晚唐政区地理建置实际状况,因此唐代珍州有“荣德县”的确实是确凿无疑的,并非无文献依据,而《大周珍州荣德县丞梁君墓志铭》则表明,至迟在武则天万岁通天年间,即有荣德县存在,为珍州辖县,这为研究唐代西南政区地理提供了一条珍贵的石刻资料。虽然《大周珍州荣德县丞梁君墓志铭》属于一件前土司时代的石刻,但因珍州地处后来的播州土司区,昭示了从唐宋羁縻府州向元明清土司州县制度过渡期间某些“边地”区域行政区隶属的复杂性。
唐初开始,对綦江流域的政区屡有调整变动,贞观十六年(642 年)置江南道溱州(治今万盛经开区),辖荣懿、扶欢、乐来三县。先天二年(713 年)改隆化县置宾化县,治今重庆南川。开元二十一年(733年)析山南道为山南西道与山南东道,原涪州隶属山南东道,又自江南道析出黔中道,治黔州(今重庆彭水),溱州并入黔中道,另置南州归属黔中道。元和三年(808年),废珍州,并入溱州;宾化县改隶黔州。綦江东段区境分属黔中道溱州荣懿县、扶欢县及山南东道涪州宾化县。五代十国时期,前蜀废道,以州统县,后蜀继之。区境分属溱州荣懿县、扶欢县及涪州宾化县。《元和郡县图书志》载:“(溱州)本巴郡之南境,贞观十六年有渝州万寿县人牟智才上封事,请于西南夷窦渝之界招慰(尉)不庭,建立州县。至十七年置,以南有溱溪水为名。”④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30《江南道》,中华书局,1983年,第744页。溱溪水即溱溪河,在今万盛关坝镇境内。可见唐代渝南地区的政区置废省并不断,其中一个重要背景原因就是夷僚不断内附,朝廷安置内附民族所致。即使进入21世纪以来,今綦江流域的政区仍然没有固定,处于在调整之中。2012年4月10日,重庆万盛区发生群众聚集的“群体性”事件,因重庆万盛区和綦江县合并为綦江区后,所引发当地群众利益诉求,并希望“复区”。后在重庆市政府大力调解下,事件始归平息。“万盛复区”事件虽然因群众的利益诉求引发,但也与地方政府归并万盛区未能深入考虑并尊重这一县级政区建置悠久的历史有一定关系。
三、黔北渝南:西南历史交通地理的复合走廊
黔北渝南是连接巴蜀与云贵高原的过渡地带,以綦江至遵义的渝黔古道及其黔北的赤水流域则是巴渝入黔的重要通道。经济地理方面,历史上川盐入黔、黔茶出黔、黔北煤铁及其其他矿产入川等都要通过黔北渝南的几条陆路或水路。自今日重庆南川、綦江区沿綦河西行至松坎、桐梓抵达遵义的渝黔古道是巴蜀入黔最古老的通道之一。綦江系长江重要支流之一,发源于乌蒙山西北麓贵州省桐梓县花坝火盆洞,流经重庆市綦江区,于重庆江津区仁沱镇顺江村汇入长江。 据明代曹学佺《蜀中名胜记》载:“江发源夜郎,作苍帛色,故名綦”。綦江因流经夜郎境曾称夜郎溪。南齐时称棘溪,元代又称南江。綦江流经贵州省北部和重庆市西南部,地跨贵州省桐梓县、习水县和重庆市綦江区、江津区、南川区、巴南区等六个区县。是历史上一条具有重要交通意义的水上航道。特别是在清代以来,渝黔通道的交通意义重大。綦江自发源地至赶水镇称松坎河,松坎河是贵州省至重庆市綦江的重要河段。松坎为千年古镇,也是清代后期綦江上源崛起的港口之一,素称“黔北门户”。咸丰七、八年(1857、1858年)贵州爆发回民起义,战乱频发,“各途皆阻,惟松坎尚通川路”①夏鹤鸣,廖国平《贵州航运史古、近代部分》,人民交通出版社,1993年,第132页。。綦江航道在战乱年代发挥了重要交通运输作用。松坎河流入綦江安稳镇境内叫响马河。响马河在两河口流入綦江赶水镇地界,在赶水与藻渡河、羊渡河一同汇入綦江。松坎河是旧时川黔物资交流,特别是綦岸川盐入黔的主要通道。川盐入黔在清代乾隆初年形成了仁岸、永岸、綦岸、涪岸4 条固定线路。綦岸是川盐入黔的四大运道之一,也是重庆境内清代川盐入黔最重要的运道之一。
清代为扩大川盐运黔,多次疏浚綦江航道。雍正七年(1729 年),凿疏江口石梁数滩。光绪四年(1878 年),自江口向上源整治,凿疏江口之头渠、二渠、三渠上下漕口,使船运通至綦江县城。抗日战争时期,綦江交通运输作用更显重要。为保证重庆到贵州经济、军事交通通畅,特别是贵州煤、铁的北运,政府组织第二期渠化工程,修建了“大胜”(乔溪口)“大利”(车滩)和“大民”(五岔)三座船闸。一、二期渠化工程的实施,但工程完成后,支撑了抗日战争期间在重庆的钢铁、军工企业的生存,也促进了沿江经济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对各闸坝进行闸门改造、坝体维修,对一些区间航道进行整治。在清溪河、笋溪河上又建成3 座船闸。为发挥綦江潜在的水能、电能,流域内兴建了大量的水利水电工程。但是,随着纵贯綦江流域的川黔铁路通车与公路网络的形成,原有船闸通航技术明显落后,綦江航运日渐衰萎,与历史时期已经不能同日而语。1985 年交通部曾经组织勘探测量,提出“渠化”方案。綦江赶水镇以下至河口130余公里,全面渠化改造,铁路、公路、水路合理分流,水道仍可进一步利用,按《重庆市内河航运规划》(2001 年~2020 年),綦江选定10 级渠化方案,2020 年赶水至江口河段通航100 吨级船舶②马小玲:《綦江地质探秘之六:这条河见证綦江人改造自然的智慧》,“重庆綦江网”2020年09月16日报道。。
綦江通黔古道沿线名胜古迹众多,风俗民情奇异,早在晚清即闻名遐迩。近代英国著名的汉学家庄延龄(Edward Harper Parker,1849~1926)曾任职于英国驻重庆领事馆,是第三任英国驻重庆领事。与前任贝德禄和继任谢立山相同,在重庆任职期间,庄延龄多次对四川及其周边进行考察,足涉川东、川北、川南、鄂西、黔北等地及长江、乌江、綦河、嘉陵江等航道,撰写了一系列游记和考察报告,其中《North Kwei Chou(黔北)》一文详细记录了作者从重庆海棠溪沿陆路至贵州松坎镇再沿水路返回的见闻,涉及沿途的交通、物产、商业、民俗、地理等信息,是清中叶川黔大道改走黄葛垭后重庆路段最早也是最详细的考察纪行,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③辛岚:《重现140 年前的渝黔古道——庄延龄《North Kwei Chou》部分中文翻译》,重庆文物考古研究院“重庆考古网”2021年12月21日。。遗憾的是目前公布的只有《North Kwei Chou(黔北)》的部分译文,全本翻译尚待有识之士全文译出刊布。
四、“南平僚”及其华夏化进程:历史民族文化地理研究的典型区域
黔北渝南地区历史邈远地处华夏文化与西南众多民族的交汇地带,曾经创造出丰富绚丽的古代民族文化。从历史文化的纵向发展看,这一地域先后出现过賨巴文化、夜郎文化、濮僚文化、僰人文化,相互叠加、继承、融合,构成了历史民族文化地理上斑驳交杂的“马赛克”现象,从专题文化而言还有悬棺文化、崖墓文化、盐道文化、丹砂文化、男根崇拜的生殖文化等。战国秦汉时期,黔北渝南地区处于云贵高原的夜郎国文化地带,酋邦林立,部族交错分布,夜郎、且兰、鄨国(中心在今遵义,地盘大致在今绥阳、桐梓一带)①王义全:《鄨国略论》,《黔南民族师范专学报》1994年第1期。、鰼国(今赤水、仁怀一带)等犬牙交错。夜郎进入中原主体记载是在战国,但其历史肯定早于此。夜郎与滇国是当时两个最大的西南邦酋。《史记·西南夷列传》说:“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唐守节《史记正义》注曰:“今泸州南大江南岸,协州、曲州,本夜郎国”;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引用韦昭之说:“(夜郎)其君长本出于竹,以竹而为姓也。”②司马迁:《史记》卷116《西南夷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第2991页。明确指出泸州长江南岸即今日之黔北赤水河流域为汉代夜郎国之地。有学者认为,夜郎的创世纪传说与竹崇拜密切相关,竹类生命繁殖力与生长强,竹崇拜实质上就是生殖崇拜,有一定道理,可备一说。

庄延龄渝黔纪行原文地图,边注中文地名为译者辛岚女士作者经实地考察所加。
秦汉以后,黔北与巴蜀及中原地区交往渐多,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华夏化过程,战国时期黔北处于属于“西南夷”地理圈范围,处于夜郎国的边缘。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分裂战乱,边地治理废弛,西南地区也动荡不安,出现规模持久的“僚人入蜀”。有学者认为黔北渝南的“僚人”实则为从嘉陵江、渠江流域迁徙至渝南黔北的巴人部落,与当地夜郎人、濮人融合,逐渐形成被史学家称为“僚(獠)人”的部落,构成了这一时期黔北渝南主体人口为“僚人”。唐代,渝州南川、綦江一带为“南平僚”活动的核心地带,《旧唐书·南平獠》云:“南平獠者,东与智州,南与渝州,西与涪州,接部落四千余户,土气多瘴疠,山有毒草,及沙虱蝮蛇。人并楼居,登梯而上,号为干栏。男子左衽,露发徒跣。妇人横布两幅穿中而贯其首,名为通裙。其人羙髪为髻鬟垂于后。以竹筒如笔长三四寸,斜贯其耳,贵者亦有珠珰。土多女少男,为婚之法,女氏必先货求男族,贫人无以嫁女,多卖与妇人为婢。俗皆妇人执役,其王姓朱氏号为剑荔王。遣使内附,以其地隶于渝州”①《旧唐书》卷197《南平獠传》,第5277页。。僚人是西南地区一个古老的部族,早在东晋南北朝时期即不断进入巴蜀地区,广泛分布于今陕南及川北、川南地区。《旧唐书·南平獠》的记载虽有数处地理错误,但记述“南平獠”人口、居住、服饰、婚姻颇详,有重要史料价值。《通典》、《旧唐书》、《新唐书》均为“南平僚”专门立传,可见其在唐代影响之大。关于南平地域范围,《旧唐书·地理志》说:“南平,贞观四年分巴县置。于县南界置南平州,领南平、清谷、周泉、昆川、和山、白(僰)溪、瀛山七县。八年改南平州为霸州,十三年州废,省清谷等县,以南平县属渝州”②《旧唐书》卷39《地理志》,第1542页。。郭声波先生认为“南平”语汇意指当地地势较平,地多平坝,取坪去土为名③郭声波:《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唐代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828页。。南平僚在唐宋间演化是一个十分有意义的文化现象,南宋祝穆《方舆胜览·南平军》引《南平图经》载:“自唐宾服,开拓为郡,今衣冠宫室,一皆中国”。又引真景元《送南平江知军序》谓:“南平故汉巴渝地,至唐犹以獠名。我朝元丰中,声教远浃,始即其地置军焉。百三四十年间浸以道徳,熏以诗书,斌斌焉,与东西州等矣。”④祝穆:《方舆胜览》卷60《南平军》,中华书局,2003 年,第1061 页。按《方舆胜览》所引《送南平江知军序》,原作者将南平置军时间搞错,根据《宋史》卷496《渝州蛮》记载:“熙宁三年,转运使孙固、判官张诜使兵马使冯仪弁简杜安行图之,以祸福开谕,因进兵复宾化砦平,荡三族,以其地赋民凡得租三万五千石,丝绵一万六千两。以宾化砦为隆化县,隶涪州,建荣懿、扶欢两砦。其外铜佛坝者,隶渝州。南川县,地皆膏腴,自光吉等平,他部族据有之。朝廷因补其土人王才进充廵检,委之控扼。才进死,部族无所统,数出盗边。朝廷命熊本讨平之,建为南平军,以渝州南川,涪州隆化隶焉”。这表明从唐至南宋,经过近一个半世纪的进化,綦江流域的“南平僚”的汉化程度已经很深,习经诵诗,彬彬有礼,与汉人已经无甚差别。“南平僚”作为綦江流域民族华夏化进程的一个事例,在中国民族文化地理学史上是一个代表性个案,具有典型意义。
五、结语
要而言之,黔北渝南地区历史政区地理错综复杂、綦江流域水上交通在清代以降的迅速崛起,历史民族文化地理的“马赛克”现象及其“南平僚”的华夏化都颇具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意义。本文只是一个概论式的初步报告,尚有很大的探索空间,诸如这一地带的土司与经制州的地理空间分异、历史移民地理及其地名学、姓氏学、綦江流域、大娄山区及赤水河流域的历史军事地理等,值得学界重视并深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