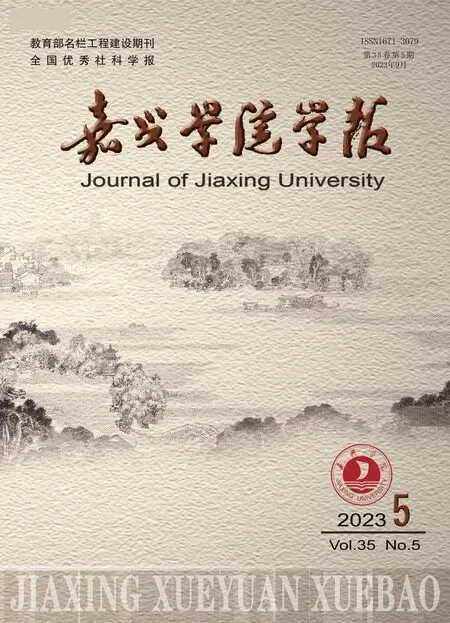“暗香浮动月黄昏”
——从《影梅庵忆语》董氏形象透视清初士人的遗民心态
王文芳
(深圳市螺岭外国语实验学校,广东深圳 518000)
《影梅庵忆语》为明末清初文人冒襄所撰,成书于清顺治八年(1651)。书名“影梅庵”取自冒辟疆的书斋之名,“忆语”二字则意指对亡妾董小宛的悼亡。此文不仅在当时影响颇深,甚至对“忆语体”这一文体的开创有着重要作用。全篇共二千四百言,按所述内容大致可分为四卷,记叙了冒董二人的爱情经历、日常片段以及甲申之变后的坎坷经历以及谶言与梦幻,并从宿命观的角度解读两人的姻缘。
正如文章开篇所述:“爱生于昵,昵则无所不饰。”[1]1爱乐之情出于狎昵之乐,人们没有不对其进行粉饰与美化的。作为回忆性散文,《影梅庵忆语》虽以真实为底色,但逝世的董小宛作为被描述者,已然处于失语的状态,在文本中成了缺席的被表述者。其呈现带有冒襄较为明显的个人取舍,并非完全还原。因此,文中的“董小宛”亦可被视为文学形象进行深入解读。
一、董小宛的“错位”形象
(一)出身与才情的错位
《影梅庵忆语》中董小宛形象的“错位性”构建,始于其出身与才情的差异。在散文开篇,介绍完董小宛的姓氏字号后,紧跟着便是一句“籍秦淮,徙吴门。在风尘虽有艳名,非其本色。倾盖矢从余,入吾门,智慧才识,种种始露”[1]1。可见,在承认董小宛出身乐籍的同时,冒襄也迅速对其出身所带有的风尘性质做了切割,似要切断旁人的种种臆想。《说文解字》对“妓”有如下解释:“妓,妇人小物也。从女,支声……‘妓’的原义为妇人小有才艺,表示古代从事歌舞表演的女子。例如‘歌妓’、‘舞妓’”[2]。后由歌、舞妓发展至参与宴席宾客的应酬接待,进而侍奉主人或与客同床共眠。西溪山人的《吴门画舫续录》在论及程月蛾时便曾说 “惜狭斜中重歌舞而轻文墨者十八九也”[3],意指青楼文化中大部分人重视歌舞而轻视文墨。
按其所述,董小宛虽出身低微,但翰墨技艺及文思才情出众,已逾越一般的妓女或是乐妓,在侍奉之余,更讲求文人风范。因此得以与顾横波、卞玉京、柳如是、李香君等名妓一起被后人并称为“秦淮八艳”。《影梅庵忆语》亦不惜笔力对董小宛的才学进行了摹写,她“剪彩织字、缕金回文,各厌其技,针神针绝”[1]10;“能做小丛寒树,笔墨楚楚”[1]13;“四时草花竹叶,无不经营绝慧”[1]15。更为可贵的是,还能凭借学识与才情对冒襄的文人事业进行辅佐。冒襄编纂“全唐诗”时,董小宛终日“佐余稽查抄写,细心商订”[1]12;冒襄令其手抄奇僻之书时,董小宛“遍搜诸书,续成之,名曰《奁艳》”[1]12;冒襄在读书时所做摘录,都由她“立抄成帙,或史或诗,或遗事妙句”[1]13。由此,不同于一般女子,董小宛凭借后天习得的丰厚知识和文学功底,对以出身高低为重要考量因素的传统价值评判标准达成了第一层反叛。在冒襄与董小宛的相处中,不会出现李渔所谓“我欲言而彼默,我思静而彼喧,所答非所问,所应非所求”[4]的蠢然场面。相反,董小宛得以与冒襄共同经营生活琐碎,甚至进入了冒襄作为文人的精神世界。
冒襄对茶文化颇有研究,董小宛便“嗜茶与余同性。又同嗜界片”[1]13;冒襄精通书画,董小宛便也手抄贴录临摹名画;冒襄在饮食上“嗜香甜及海错风薰之味”[1]17,董小宛便尽其慧心做佳肴美味。借助书法、绘画、饮酒、煮茶、插花、茗香等日常事项的施行,冒襄与董小宛在精神生活中的私人属地得以成形,与同时期外界的风起云涌形成鲜明对比。可以说,在这些精巧细致的生活细节背后,彰显着江南名士所特有的儒雅风范,是二人精神乌托邦的具象化载体,是他们得以对现实暂时逃避的甬道,甚至附着有二人因能脱离现实而产生的自然得意。
然而,在两人琴瑟和鸣的表象之下,更值得注意的是董小宛“错位形象”的建构。董小宛异于常人的才情,始终服务于冒襄“文人式”儒雅生活的需求,凸显着冒襄对江南精致士人文化的恪守。而借由对董小宛出身与才情的“错位性”形象建构,冒襄觅得了一个理想的文人伴侣,能更好地达成对儒雅生活的要求。冒襄享受于传统江南文化所带来的优越感,沉溺于以文人雅士为代表的精英文化对庸俗文化在精神上的超越,从而使自己在现实中难以寻得定位的困境得到了开脱,并聊以自慰。
(二)身份与气节的错位
“出身与才情”的错位,主要是受到外部影响的呈现,真正使董小宛形象建构成型并流传于世的,是其“身份与气节”的错位。与其他纵情声色的秦淮女子不同,董小宛身为名妓,却在处世之举中有着自己的风格与态度。余怀的《板桥杂记》中描述其“性爱闲静,遇幽林远涧、片石孤云,则恋恋不忍舍去;至男女杂坐,歌吹喧阗,心厌色沮,意弗屑也”[5]。冒襄描述其因“厌薄纷华”,便“挈家去金阊矣”[1]2。不仅如此,董小宛的坚毅与勇敢之气魄也非寻常女子所能及。一句“我装已戒,随路祖送”[1]5,便跟随冒襄辗转浒关、梁溪、昆陵、澄江等地,坚以身从,无见怨言。
在文人世家的秩序规训下,董小宛也习得了更多的道义纲领,识时务和大体。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攻占北京,崇祯帝自缢而亡,地方豺狼虎豹势力渐起。为避祸乱,冒襄举家夜渡,向北遁往浙江盐官。仓皇之中,冒襄不忘尊卑有序,一手扶母一手拉妻,对董小宛的关心则是一句“汝速蹴步,则尾余后,迟不及矣”[1]20。识大体的董小宛在脱险后作如此回应:“当大难时,首急老母,次急荆人、儿子、幼弟为是。彼即颠连不及,死深菁中无憾也。”[1]21
无独有偶,在清兵入关剃发令下,人心惶惶之时,冒襄欲将董小宛托付友人,就此别过。其直言:“我有年友,信义多才,以子托之,此后如复相见,当结平生欢,否则听子自裁,毋以我为念”[1]21。决绝之意昭然若出。对冒襄“有义无情”的决定,董小宛不但不怨恨,反而表示赞同,甚至愿意以死明志 “我随君友去,苟可自全,誓当匍匐以俟君回;脱有不测,前与君纵观大海,狂澜万顷,是吾葬身处也”[1]21-22,表露自己愿舍生以取义的忠心。如此勇猛坚贞的胆魄与气节,已远远超乎寻常女子。为此,冒襄甚至发出了“姬明大义、达权变如此,读破万卷者有是哉?”[1]21的赞叹。
在冒襄的笔下,董小宛总是那样深明大义、顾全大局,但不能否认的是,在赞誉的背后,是冒襄弃董小宛于不顾的现实行为,使她独自一人在兵荒马乱之际“颠连趋蹶,仆行里许”[1]20。在这一点上,冒襄对董小宛的“怜惜与珍重”可见一斑,更有甚的是在冒襄父母的挽留下,董小宛才不至于流离失所。
与冒襄相反,董小宛不仅在危难之时愿意为他舍身求全,在冒襄深受病痛折磨之时,亦不离不弃。冒襄在五年内三遇危疾,均由董小宛一人尽力服侍。董小宛直言“竭我心力,以殉夫子”[1]23,且言出必行。冒襄生疾一百五十日,董小宛便陪护一百五十日,自己“仅卷一破席,横陈榻边,寒则拥抱,热则披拂,痛则抚摩”[1]22。长期的辛劳与照料,令董小宛“星靥如蜡,弱骨如柴”[1]23,容颜不复往昔。虽然侍疾是姬妾的分内之事,但像董小宛这般呕心沥血,连冒襄的母亲与妻子都深感怜惜,实乃世间少有。在冒襄笔下,出身低微的董小宛不仅知书达理,更心有大义,且能将这般气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达到知行合一的境界。
二、“错位”背后:遗民心态的时代折光
冒襄与董小宛的爱情故事,浅看荡气回肠、缠绵悱恻,实则存在值得推敲的失实之处。在董小宛形象错位的背后、在表象与真实的歧出之处,是冒襄作为时代遗民士人的心态折光。

而冒襄在儿女私情与家国大义中毅然选择后者的决绝,也与其身份地位息息相关。《清诗别裁集》有载:“冒襄,字辟疆,江南如皋人。南渡时,用为推官,不就,以贡士终。有朴巢诗集。辟疆与宜兴陈定生、商丘侯朝宗矜名节,持正论,品核执政,不少宽也。”[6]冒襄出生正统,其父冒起宗是崇祯元年(1628)进士,其母马氏与其妻苏氏皆为深受儒家传统伦理观念浸染的女性,冒襄亦将孝义忠悌刻印于心。此外,冒襄还积极参政,曾与张明弼结盟,参加复社。因与侯朝宗、陈贞慧、方以智交往密切,而被列为“四公子”之一。四人或诗酒唱和、或议论朝纲、或抨击阉党,寄望挽救国家危亡。冒襄才华横溢,胸有格局,心怀朝政,可谓为一代知识分子之典范,绝非仅关心风花雪月的迁客骚人。因此,在拒绝董小宛后,冒襄虽心有怜惜,但“得轻身归,如释重负”[1]5。对儿女私情的果断撇舍,无疑是冒襄践行传统价值规训的体现。
由此可见,冒、董二人的传世佳话固然有情感作为重要的动力,但更不可避免地带有现实底色,含有二人出于经济、政治等方面的思量。然而,在冒襄的笔下,并未见到关于这方面的过多叙述。文中较少提起董小宛从良前的生活,也较少进行物质方面的比较。即使有所提及,也只是以“倾改始从余,入吾门,智慧才识,种种始露”[1]1;“耽寂享恬,谓骤出万顷火云,得憩清凉界,回视如梦如狱”[1]10等春秋笔法一带而过。
诚然,作为一篇追忆性散文,《影梅庵忆语》的抒情笔法包含对亡妾董小宛的尊重,但冒襄的选择性取舍依旧不容忽视。正是此种技法的运用,使忆文在悼念亡妾董小宛的同时,也为作传人冒襄的种种选择进行了合理化辩护,最终呈现冒、董二人一个心怀大局、一个忠贞不渝的理想画像。二人的爱情故事在渐趋理想化与模范化的过程中,也得以被提炼出更为丰富的能指意义,在服务于士人形象的自我建设,呈现心怀家国、舍小我为大我的美好品性的同时,也影射出时代底色下士人的窘迫与无奈。
冒襄将原本人们对董小宛的关注点,借由错位的形象叙述而得以转移。董小宛虽出身低微,但有着很强的人格魅力和性格张力,因此不仅能作为冒襄的理想学伴、红颜知己,还被冒襄及其身边的友人赏识。然而,董小宛再深明大义,终究是一名女子,在性别结构与社会结构中都处于弱势地位,始终要依附他人,危急动乱时也会害怕胆怯,甚至“惊悸瘁瘏”[1]22,惊惧成疾。但在《影梅庵忆语》有详有略的文脉布局下,在冒襄“避轻就重”式的处理下,董小宛弱势的社会地位与真实本性中的人性弱点均被隐匿,不再是完整的她自己。为人所熟记的是董小宛的深明大义与体恤知义,是理想化的气节与品格。
在《影梅庵忆语》中,冒襄更是将董小宛与士人、与平凡女子,甚至与世间人等进行比对,直言“传其慧心隐行,闻者叹者,莫不谓文人义士难与争俦也”[1]1;“余何以报姬于此生哉!姬断断非人世凡女子也”[1]23。在层层比照之下,董小宛的形象魅力已然跨越了性别和阶层,得到了拔高与升华。如文章开篇所言:“矧内屋深屏,贮光阒彩,止凭雕心镂质之文人描摹想像。”[1]1女性因居于深闺,能为人所知的心性品质多源于文人的描摹与想象。通读此篇悼文,不难发现,冒襄对董小宛的态度发生了迥乎不同的转变:从起初婉拒董小宛后的“得轻身归,如释重负”[1]6,到对董小宛过门后各项技艺的交口称赞,到对变乱时期董小宛勇于舍生取义行为的大方称许,最后因其逝去发出“今忽死,余不知姬死而余死也”[1]1般万分追悔的慨叹。诚然,冒襄与董小宛之间切实存在令人动容的爱情,但这样的慨叹却并不尽是为董小宛的逝去而扼腕叹息。
文中曾述:“忆年来共恋此味此境,恒打晓钟尚未著枕,与姬细想闺怨……”[1]15正如冒襄闻到香味会想起曾伴身旁的董小宛一样,其撰文悼念亡妾时,也透过追思在凭吊文盛的往昔。董小宛们所经历的磨难,不过是时代的缩影。当朝代式微,繁盛成为过去,新的身份认知问题便自然浮出水面。在朝际更替的统一命题下,人人都面临变或不变的抉择困境。
从社会身份层面而言,冒、董二人均有“失节”之症,同病相怜。董小宛出身乐籍,是伦理道德中的失节之人;而冒襄经历了明朝的覆灭,却未以身殉国,亦是一种文人失节。而精神层面的失节更为人所不耻,亦是冒襄内心之刺。枕边人董小宛的出现,其忠诚坚贞,重情重义,甚至不惜以死明志的种种举动,对冒襄无疑是一种无形的冲击。因此,取舍之下,冒襄在对董小宛这些品质放大化的描写中,已然暗含着肯定。在被表述的理想化人格与残酷现实的落差下,折射出的是冒襄作为遗民时代的士人,对担当家国责任的既想又忧,既愿又惧。
冒襄虽然也曾多次拒绝清廷的征召,为前朝守节,但作为以儒家传统观念安身立命的士人,注定无法与国家社稷全然分离,其所想所愿也难以得到实现。而如果要服膺于清廷,因为遗民的身份属性也不会被朝廷全然信服,甚至落得两头受抨击的下场。
在《影梅庵忆语》的种种叙述中,亦能看出冒襄对时代背景之驳杂的种种隐喻与暗示。譬如冒襄曾如此品茗:“宫香诸品淫,沉水香俗。俗人以沉香著火上,烟扑油腻,顷刻而灭。无论香之性情未出。”[1]14在提及“宫里人”与“俗人”两类人后,冒襄便接着论述自己对沉香的种种见解,以自己的“懂得欣赏”反衬“俗人”不懂欣赏。言语之中,未尝没有含沙射影之意,未尝不是在借助精巧雅致的江南生活格调为士人的自我优越感赋能,从而纾解自己受困于现实郁闷难耐的情绪。
董小宛和柳如是的出身相似,但没有柳如是的后世名声,亦没有留下足够多的诗文供像陈寅恪这样的学者研学,以尽可能还原其心路历程,完成对自身形象的真实体认。董小宛形象中“身份与气节”的错位建构,其对气节近乎没有犹豫的全然坚守,究其根源,是带有遗民身份的冒襄对渴望践行儒家传统伦理、逾尽忠贞的士人情结在作祟。错位的背后是失实,失实的背后是冒襄一类时代遗民的心态折光。
三、“错位”的内核:忠明士人的自我想象
在冒襄带有倾向性与遮蔽性的忆语之下,董小宛是一个理想伴侣,却不是完整的她自己。其“避轻就重”使董小宛所达到的境界,正是以冒襄为代表的遗民群体内心理想的一种投射与放大。
经历了明清易代,以冒襄为代表的文士已然背负了“前朝遗民”的身份 “夫子生而余死犹生也;脱夫子不测,余留此身与兵燹间,将安寄托?”[1]23若将董小宛所指称的“夫子”替换为“明朝”,则其所言便可谓一语成谶。黄宗羲在《两异人传》中记录了晚明遗民的生活群像:“自髡发令下,士之不忍受辱者,之死而不悔。乃有谢绝世事,托迹深山穷谷者,又有活埋土室,不使闻于比屋者。然往往为人告变,终不得免……”[7]明朝政权灭亡后,这些文人的生存也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一方面,他们不愿委身于满清王朝;另一方面,他们也不敢公然与朝廷对抗,或是勇敢赴死以证清白。
在复国无望与赴死无胆的两难困境中,这些深受折磨的士人,其无奈与惆怅之心绪,需要得到抒发与宣泄。曾经“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8]的烟花之地,见证文化艺术交流的秦淮河畔,便是他们的不二之选。当时场景的富丽几何与短暂易逝,于张岱的《陶庵梦忆》中可见一斑。曾经“海内所夸者无他”[9]152的绍兴灯景,成了轻薄子随口吟出的“蕺山灯景实堪夸,胡筿芋头挂夜叉。若问搭彩是何物,手巾脚布神袍纱”[9]153。起于花朝,尽于端午,游人赏乐的西湖香市,后成了人们口中如“山不青山楼不楼,西湖歌舞一时休。暖风吹得死人臭,还把杭州送汴州”[9]173的诮语。末了,张岱还附上一句,此“可作西湖实录”[9]173。一片繁华,转眼成空。钱谦益《西湖杂感二十首》(其八)中,亦有感于名妓柳如是从“杨柳长条人绰约,桃花得气句玲珑”[10]139的才神兼具,到“今日一灯方丈室,散花长侍净名翁”[10]139以禅度日的孤寂生活,道一句“不是承平好时节,湖山容易著神仙”[10]140。可见,寄怀感伤,以古鉴今,借以缅怀尚未易主的大好江山,历来是文人对名妓群体进行书写的重要原因。
一边是家国大义,一边是纵情声欲,如此矛盾复杂的心理,若以冒襄为切入点辐射开来,推演至当时的江南文化,亦不乏成立的可能。齐聚秦淮的遗民文士,表面上沉浸于风月绵绵,快意如白居易《卯饮》中“卯饮一杯眠一觉,世间何事不悠悠”[11],实际更多的是“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12]的无奈与失意。他们并非隔江唱曲不知亡国恨的商女,而只是欲借酒浇愁的失意之人。对政局上的失意和对朝廷的无望,使他们试图在别的领域找回失落的主动权和话语权,审美领域便成了他们的意中之选。
据汤漱玉的《玉台画史》所引《画征续录》:“蔡含,字女萝,吴县人。如皋冒辟疆姬也。生而胎素,性慧顺。好画……辟疆姬人,又有金晓珠,名玥,昆山人。居染香阁,亦善画。”[13]在董小宛之后,冒襄又纳入蔡女萝、金晓珠为妾,陪伴左右,共事山水书画之乐。冒襄在《影梅庵忆语》中流露的情深意切、愧怍难耐,虽未见得在现实中得以知行合一,但他对雅致生活的追求却仍然保留了士人风格。
从“夜夜笙歌”满足肉身需要,到“鼓瑟吹笙”弥补精神空缺,青妓趋向雅致化的表现,一定程度上美化了青妓行当的通俗秉性,但并未改变其本质。在某种程度上,琴棋书画、吟诗作赋亦是青妓为迎合文人所需,对已有文化现象进行模仿的行为,其目的更多在于引发消费,并非指涉“文化”本身。然而,纵使士人深知的所谓秦淮风月,本质不过是一场交易,但因时代的驳杂与士人精神世界的空缺,于他们而言,青楼这般太虚幻境,仍是他们愿意豪掷千金买上一剂的“解药”。
士人的想法投射在诗文中,便具象化为对秦淮名妓姿态容颜的描摹、气度品性的品评。让“隔江犹唱后庭花”[14]的名妓,富有“闺阁心悬海宇棋,每于方罫系欢悲”[15]的民族大义。在本色描写之外,未尝不含有当事人的辛酸与无奈,导向的是一场文化与审美的塑形。以吴伟业所作《圆圆曲》为例,在他人看来“无边春色来天地”[16]556的繁花似锦,本质上是以陈圆圆为代表的一众女性“错怨狂风扬落花”[16]556的颠沛流离,是她们在面对男性选择与民生评议时无力与被动的处境。
另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相比于对经济、政治等现实因素影响的淡化式处理,《影梅庵忆语》对董小宛的种种追随行为,却是不遗笔力,且往往将其追随归因于痴情和衷心。而董小宛一番忠情所付诸的对象,即是慷慨风义的冒襄本人。不仅如此,文中还多借旁人之口,就董小宛对冒襄的倾心追随加以称赞,诸如“余母恒背称君奇秀,为余惜不共君盘桓”[1]5“吴门知姬者咸称其俊识,得所归云”[1]9等。
在旁人看来,董小宛的形象有多么贤良淑德、顾全大局,那么作为董小宛所钟情之人便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由此,在将董小宛形象诉诸笔端之时,冒襄也透过董小宛在这段情感关系中的种种行为,对自身加以理想化注解,以肯定与赞许的眼光,完成了自我形象的再塑造。
如《影梅庵忆语》中冒襄对董小宛形象的错位式建构,折射的是冒襄本人对“知行合一”这一理想境界的渴盼,虽然遗民士人在文学中对名妓的种种“错位式”书写不能变更时代洪流面前人人皆危的事实,但其作品所附着的审美价值与意义无疑仍能为其自身的无奈带来慰藉,对其所承受的时代伤痛有所消解。
明清易代之际,在诗词文章中构建各式各类名妓形象,对名妓施予认同感的同时,诗人文士们也在其中寻找着自己的定位,期待着一种“镜像式”反馈,以达成对自我价值的观照与认同。一如高彦颐学者所言:“在忠明男性眼中,名妓与效忠间的关系非常强。在明廷陷落后,名妓成了忠明诗人自我想象的化身。”[17]被描写与建构的“董小宛们”,便是在时代昏黄之际能寄托士人精神期望的那抹浮动的暗香。在跨性别跨语境对“江南名妓”进行理想化塑形后,惹来的那一众赏花赞花惜花之人,其实仍是那群自怜自悔又自惜之人,他们渴望在“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18]的相对观照中达成美好愿景,在“不因重做兴亡梦,儿女浓情何处消”[19]中消解时代变迁带来的失意与无力之感,聊以自况。
——冒辟疆的角色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