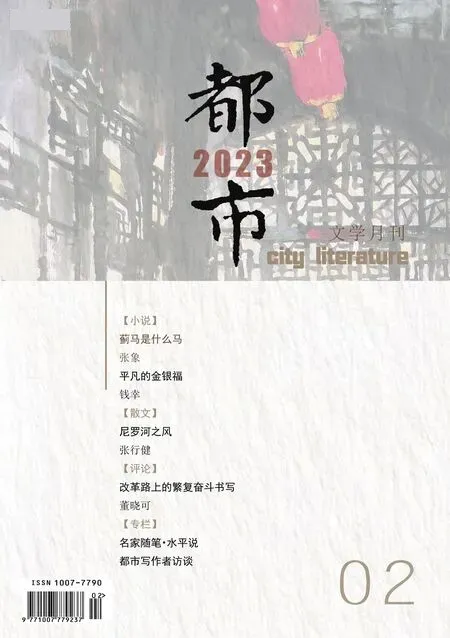梦想之所
文 陈煜
晨雾一点点融化,洒向花园的碎石小径。散步归来,露水沾湿了孟晓鸥的裙摆,她在农舍木门廊上的藤编休闲椅上坐下来,整个身体完全放松下来,把自己摊成一只达利的时钟。此时太阳的热度刚刚好,空气中飘浮着淡淡的花香。阳光洒在洋绣球粉红淡紫浅蓝的花瓣上,还有那些三色堇和桔梗花的花瓣,在明亮的阳光下呈半透明的琉璃色,杂树或栅栏阴影下的色彩却凝重而深沉。阳光随着微风在花瓣上跳跃,如同山间小溪在碎石上跳跃。一切是那么迷人。晓鸥思寻着,该用怎样的色彩和笔触描绘眼前这晨光,这花瓣上的晨光的明亮,这凝重的、琉璃色的花朵。毕竟多少年没碰过画笔了,她已找不到画笔与画布触碰的感觉。晓鸥总想画一幅属于自己的花园,就像莫奈的花园一样,叫晓鸥的花园。
恍惚之间,她感到脚面湿漉漉的,才回过神来。她正在厨房里放水洗菜准备做晚饭。刚才经过餐厅时,她看到餐厅墙上挂的那幅她自己临摹的梵·高的《盛开的杏花》,一下子又勾起她心中的梦想——在“晓欧的花园”里读书画画。一阵子思绪乱飞,竟忘了关水龙头。客厅电视里的声音盖过了水流声,再加上刚才稍一走神,水池里的水就漫了出来。她赶紧关了水龙头,一溜小跑到阳台找拖把和抹布。赵雷的谍战片正看到关键之处,被她搅了,嘴里咕哝道:“又发什么神经?跑来跑去的,能不能慢一点?”
孟晓鸥没工夫理他。当初装修的时候地漏没处理好,有一回水管三通在半夜里坏了,等到早上起来发现,家里已是水漫金山。水漏到楼下,害得楼下一家断电一周,人家只好去外婆家避难。幸亏楼下这对小夫妻心善,不仅没怪罪他们,还抱来自家不用的毛巾被给他们吸水。这次无论如何再不能把水漏下去了。孟晓鸥赶紧又拖又抹。没留神扭了腰,又酸又痛。有一刻腰就卡在那儿了,不能动,也直不起来。过了好一会儿才能直起来,但是还不能大动,依然疼。晓鸥心中便生出一股怨气,却又不知道怨谁。那个把脚跷在茶几上,躺在沙发上看电视的人——不用看,孟晓鸥就知道是那个姿势——他平时难得在家,偶尔待在家里,再计较他做一星半点的家务既没啥意思,也解决不了多大问题。只能怪自己胡思乱想。而这突然的腰痛带来的幽怨又是模糊的,无处安放的,无的放矢的,有点使不上劲的感觉。
孟晓鸥做家务的时候喜欢思绪乱飞,不知不觉中,活儿干完了,也不觉得时间长。以前她会咿咿呀呀地唱歌,那是她从小养成的习惯。但婚后渐渐就不唱了。这样的话,只剩下“胡思乱想”,这个词是赵雷给她的中肯评价。
在餐桌上摆好饭菜和碗筷后,她通常会在椅子上坐下来,望着对面墙上那幅梵·高的《盛开的杏花》发会儿呆。每次凝望这幅画,孟晓鸥的心总会被什么东西轻轻挠一下,像被微风吹拂的水面一样荡起细微的波纹。她有时候会想,当年自己从师范学院美术系毕业后,如果安心做一名美术老师,而不是选择去当时工资待遇比较高的银行工作,会是怎样的情景呢?人有选择的自由,却也要承担选择的后果。然而,这也只是她心里稍纵即逝的波动,很快就恢复了平静。
当初刚拿到属于自己的这套房子时,晓鸥一心想在餐厅里挂一幅自己临摹的画。她翻开画册,一打开就看到梵·高的《盛开的杏花》。她非常喜欢那低饱和度的蓝和纯洁的白,喜欢那画面的洁净。那是狂放粗糙的梵·高难得泄露的一丝柔情。晓鸥利用几个休息日,在这间刚装修好的空荡荡的客厅里临摹。一拿起画笔她便全身心投入,把自己融了进去,忘了眼前这幅画之外的一切。她的内心充满激情又如此宁静。她想,什么时候自己也能像梵·高一样创作一幅让自己充满激情而又极其宁静的作品,也就此生无憾了。《盛开的杏花》终于临摹好了,晓鸥对此还算满意。她喊赵雷帮忙挂到餐厅墙上。赵雷过来看了一眼,淡淡地说:“你忙活了这么多天,就弄了个这东西?冷冰冰的。餐厅挂画应该有些烟火气。”
晓鸥说:“你根本就不懂。”
赵雷说:“你懂,别人不懂啊?别挂了,明天我去重买。”
晓鸥没理她,自己一个人爬上爬下,拿电钻钉了膨胀螺丝,亲手把画挂上。为此赵雷生了好长时间的气,说自己说话一点用也没有了。晓鸥说你说这话真不凭良心,家里大事小事不都听你的,装修也听你的,就这一点听我的又怎么了?
他们婚后很长一段时间是和公婆一起生活的。结婚的时候,晓鸥想过二人世界,赵雷说他妈妈让他们住家里,将来有了孩子好一起帮着带。他家宽敞,三室两厅的大居室。晓鸥想想也是,就没再坚持。
婚后,她确实也享受到了跟公婆一起生活的好处。从怀孕到坐月子,她被照顾得无微不至,以致产假结束时她比怀孕前胖了二十斤。越是临近上班,她越焦虑。自己这副完全走形的模样,不仅无法面对班上的小姐妹,也无法面对自己。婆婆一个劲儿地让她喝鸡汤喝鱼汤喝蹄髈汤。还说,营养充足了,奶水才充足,孩子才养得好。晓鸥心想,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但作为一个母亲,她无法反对。她的身形就这样像棉花糖一样膨胀了起来,减肥的话题当然开不了口。婆婆对她总是嘘寒问暖、关怀备至。还体贴地说,产妇月子坐不好要落下病根的。这话在理,但晓鸥心想,睡不好觉才是要命的,夜里一会儿喂奶,一会儿换尿布,哪里有觉睡?
她的心事无处可说。婆婆是一个难得的好婆婆,圆脸,慈眉善目,双眼笑起来就成了俯卧的括号,略厚的嘴唇给人很实诚的感觉,加上胖墩墩的身材,看上去就像弥勒佛。婆婆从没拿她当外人看。要说婆婆有什么缺点的话,就是话多,“厚嘴唇拙于辞令”的说法,在她身上却得到了相反的验证。
公公可能是几十年来受够了,所以他不是躲书房看书,就是一个人出门散步。反正家里有的是听众。反倒是小夫妻间没多少时间交流了。夜晚他们有了独处的空间,两人都想着抓紧时间休息,都挺累的。晓鸥有时候想说点什么,又懒得开口。看赵雷嘴张那么大,哈欠连天的,更没了交谈的兴致。
吃完晚饭,婆婆习惯坐在一桌鸡骨头、鱼卡子、青菜梗、韭菜叶边继续她在吃饭时没说完的话题。她的话题可以像一眼泉水汩汩一样而出,永不停歇。在晓鸥看来,那些吃的时候很香的食物,一旦经过咀嚼后被吐出来就变得恶心了。婆婆怎么能如此神态自若,泰然处之。晓鸥不知道是婆婆不对头还是自己不对头。不管怎么,她是待不下去的。所以饭后她总是起身收拾碗筷。这个时候,婆婆会主动打断自己,对她说,你放那儿吧,等会儿我来。晓鸥晓得婆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起来。婆婆做事总是不紧不慢,从未看她着急过。这满桌狼藉她实在看不下去。再说去厨房洗碗也可落个耳根清净。
有个晚上,晓鸥洗完碗出来,他们正在客厅里吃西瓜,照惯例,瓜心会被挖给赵雷。婆婆就差把瓜子儿也替他剔掉了。晓鸥看不惯,只能背后说赵雷。赵雷却说,享受妈妈的服务,她开心啊,只要她开心就好。
婆婆喊晓鸥过来吃西瓜。晓鸥不喜欢一家人围一起拿勺子挖西瓜,在她娘家,吃西瓜都是切片的。晓鸥推说不想吃,要进屋去看看宝宝。婆婆说宝宝睡着呢,你坐下来歇一会儿吧。晓鸥坐下来,耳朵却竖起来听着卧室里的动静,但凡卧室里传出什么响动,晓鸥就像遇到救星一样冲进去。这个时候,婆婆总会夸赞她:“我们家晓鸥真是好姑娘,我就喜欢。”
孟晓鸥一直想搬出来单过,有一个自己独立的生活空间。赵雷却很享受在他妈妈面前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生活。婆婆也不同意他们搬出去。她说一大家子人在一起多热闹啊。她就怕冷清。直到孩子快要上小学了,晓鸥才找到要买学区房的理由,搬了出来。
孟晓鸥情绪低落地坐在餐桌边出神,竟然忘了叫那父子两个吃晚饭。直到儿子从房间里跑出来喊饿,她才没好气地说:“你们是客吗?吃饭还要请?”
儿子看她的表情,愣住了,忙问:“妈,你没事吧?”
孟晓鸥没有回答,用手托着下巴,一滴眼泪莫名其妙地落了下来。儿子吓了一跳,问她:“妈,你怎么了?难道是谁欺负你了?还是哪里不舒服?”孟晓鸥只得说是腰扭了,疼。儿子贴心地替她揉腰,她不知道怎么回事,心一酸,竟然哭出声来。赵雷听到了这边的动静,关了电视过来问是怎么回事。儿子告诉他说妈妈腰扭了。赵雷说:“你啊,怎么这么不小心,刚才就看你十慌八慌的。有什么事喊我啊,我来帮你按摩按摩。”
孟晓鸥推开他说:“别在这里假惺惺的,要做事,家里多的是,还要人叫?”
“我弄得不好又要被你说帮倒忙。”赵雷尬笑着到冰箱里拿出冰块帮晓鸥敷上。
冰块敷上了,是感觉好了些。但她心里的委屈似乎跟疼痛没有多大关系。她想的是明天以及无数个明天的事。明天是星期天,照例他们一家三口要去婆婆家。一个星期看不见,奶奶想孙子了,儿子也想去奶奶家。关键是晓鸥一个星期没去那里,家里又乱得插不进脚了。婆婆平常大大咧咧,做家务也是马马虎虎,现在年纪大了就更马虎。橱柜上、地板上满是油水汤汁菜叶什么的,菜刀菜板洗菜盆到处乱放,看上去像刚经过一场激烈战斗的战场,惨不忍睹。晓鸥每个星期天都要去替他们打扫整理,到下周去了又是一塌糊涂。不知道是不是现在自己年岁渐长,体力渐渐也跟不上的缘故。晓鸥总是害怕星期天的到来,害怕那一堆家务在等着她。她有时候觉得是不是自己上辈子欠赵家的,这辈子成了他家的免费钟点工。
当她头脑中有这样的想法时,她又陷入了深深的自责。她为有这样没良心的想法而羞愧。儿子在奶奶家长到上小学,身体养得棒棒的,结实得像头牛。晓鸥有时候想想就对自己说,比起那些不愿带孩子的婆婆,你知足吧。晓鸥就觉得自己像一只陀螺,被一根看不见的鞭子抽着,无法停歇。
因为腰疼,孟晓鸥先在床上躺下了。赵雷还没进来,这两米宽的大床显得很空。孟晓鸥突然感到自己跟大床一样空。虽然她的时间被各种事务挤得满满的,却莫名其妙地感到自己是空的,空得只剩下躯体。甚至连躯体也不是自己的。甚至,她记忆里的那个孟晓鸥也不存在了。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被一点一点掏空。然而生活却是实实在在的,从她放弃画画起,就变得实实在在。难道当初自己不就是为了日子过得踏实一点,好一点的吗?这十几年不就是这样过下来的吗?可现在为什么觉得自己空了呢?她感觉不对劲,这十几年来,她完全失去了自我。她问自己,孟晓鸥,这是你想要的人生吗?不,她不知道她的人生怎么会是这样。她想,她不应该再这样下去了。她觉得自己必须做点什么。
过了很久,赵雷终于关了电视进来了。他问:“晓鸥,你睡了吗?”
晓鸥没搭腔。
赵雷躺了下来,伸过手来轻轻地试探着扳过晓鸥的肩膀。这是他们之间心照不宣的秘密讯息。此刻晓鸥心里却感到难过。她一巴掌打开他,身子往边上挪了挪。腰还疼着呢,难道自己只是台按程序运行的机器吗?
机器?晓鸥心中一惊,自己怎么会想到了这个词?不,这个词不够准确。但一时间晓鸥也找不出更好的词来替换。赵雷问:“还疼吗?”
晓鸥还是没搭腔。
赵雷说:“要不要我给你揉揉?”
晓鸥说:“你明天跟你妈妈说,找个钟点工。我现在也不年轻了,两边实在顾不过来。”
赵雷说:“妈妈早说了,让我们过去住,你偏要搬出来,弄得两头忙,两头不定当。”
“我就想要有一点自己的空间、自己的生活,不行吗?”孟晓鸥说,“他们又不是雇不起钟点工,要是他们舍不得,工资我们付。”
赵雷说:“不是钱的事。”
孟晓鸥说:“那为什么不能找个人帮帮忙?”
赵雷说:“妈妈不喜欢家里有外人。再说了,雇来的人大多只想要钱,不想做事,钱都花冤了。”
孟晓鸥道:“那我就活该做保姆?”
“瞧你这话说的,”赵雷说,“作为晚辈,一个星期为老人做一次饭也不算过分,再说哪个女人在家不做家务,怎么就是保姆了?”
“女人还不是跟你们男人一样要工作,哪个单位领导会因为你是女人让你少干点儿?在单位有些事情女人甚至比男人干得还多。女人回家还得干家务管孩子。合着女人不是人,是神啊。”
赵雷嬉笑着说:“你怎么突然这样想?不都是女主内男主外嘛。”
“你主外,你天天往你妈家里跑,你这叫主外?真没见过像你爸妈那么黏子女的父母。还有你,自己儿子的学习从来不问,天天陪父母。”
“儿子学习不是有你吗,还要搭上几个人?”赵雷说,“爸爸现在脑子有点糊涂了,药吃没吃过,我得盯着点儿。”
“以前你爸脑子好的时候,你不也天天往那边跑?你就从没把这小家当家。”
“你又乱想了,儿子晚上写作业,要安静。我待在家里干吗?干瞪眼?刚好去那边陪陪老人,有什么不好的?”
赵雷如果不加班,下班后一般都会去他妈家。他若是有两三天没回去,那边电话就会打过来。晓鸥心中虽有不满,但总归比在外面吃喝嫖赌好百倍千倍吧。现在这社会,那种男人不要太多吧,在这些方面,她从未为丈夫操过心,赵雷也算是难得的好男人。她知道他在那边,陪他爸妈聊天、看电视,或者弹弹脚踏风琴,为婆婆伴奏。婆婆退休后,参加了老年合唱团,要练歌的。家里有台老掉牙的脚踏风琴,是赵雷小时候弹过的。现在刚好给他妈妈伴奏。这么老实的丈夫上哪儿去找?况且人家又不是老实无用。凭技术,该有的职称、职位一个不少,收入也不低,手上几个证书放人家小公司还有一笔可观的外快。赵雷所有的收入又一分不少地全部交给了晓鸥。晓鸥除了内心深处偶尔生出的孤独感,一切真的无可挑剔。晓鸥时常对自己讲,不可太贪心,应当知足。却又不由自主地无端地生出一些莫名的委屈来。
晓鸥说:“我腰疼,明天那边就不去了。”
赵雷说:“你早说呀,绕这一大圈子。好吧,你明天一个人在家好好歇歇。”
晓鸥说:“谁绕圈子了?我就是这么想的。”
赵雷又伸过来手来轻轻地拍拍她的肩膀说:“好吧,休息吧,明天再说。”
第二天,晓鸥醒来的时候,她发现真的是她自己一个人躺在床上。她在床上打了个滚儿,又把自己躺成了一个“大”字。四周安静极了,安静极了,安静极了,就像一片寂静的山谷。她没有起来,继续赖在床上。今天他们把时间留给自己,晓鸥要随心所欲,想不干吗就不干吗。她不打算做任何家务,他们早上喝完牛奶的杯子、洗澡换下来的衣服、平时她容不得有一点灰尘的地板等等等等,她通通不想管了,也不打算给自己弄吃的。一般在某个工作日的晚上,儿子上晚自修时,晓鸥会去看看自己的父母,在那里一直待到儿子下自修前再离开。她爸妈一般不愿麻烦子女。晓鸥觉得一个星期至少要去看他们一次,这是晓鸥给自己定下的规矩。不然的话,在家洗洗刷刷,准备准备第二天的饭菜,也就没时间了。现在她就一个人待在家里,谁也不想。她不再是谁的妻子,谁的母亲,谁的儿媳妇。她就想做一回自己,做真正的孟晓鸥。她就想完完全全放空自己,她就是要无所事事,百无聊赖。她就想体验一下自己完全属于自己是啥感觉。
她躺在床上,窗帘也没拉开。家里寂静得像夜晚。不知道现在是几点,她也不想知道现在是几点。时间好像混沌了,自己仿佛婴儿般,从一片混沌中获得了初生。她发现自己正一点一点地活回来,她听到了血液在血管里流淌的汩汩声,听到了清脆的心跳声。当她听到胃在咕噜咕噜叫时,便轻快地跳下床去,穿着睡衣,来到厨房,打开冰箱,从里面拿出一盒牛奶、一个手撕面包和一个苹果。她把牛奶倒进杯子里,放进微波炉加热,不一会儿,一股奶香飘了出来。晓鸥深深地嗅着奶香,就像婴儿寻觅着母乳。
享用完溢着乳香的早午餐,晓鸥习惯性地凝望着墙上那盛开的杏花。但今天的心情完全不一样,她不必再在凝望中匆匆离开,她今天可以完全沉浸其中,就像潜入奇异的海底世界,如果有可能,她愿意永远也不浮出水面。她仔细地动情地凝望着画幅中间花丛中那三个尖尖的红色小花苞。那是即将绽放的生命,它们蕴含着勃勃生机和无限可能。《盛开的杏花》是梵·高为弟弟提奥即将出世的孩子所作,是一幅迎接新生命的画作。是的,新的生命有无限的可能,而自己的生命呢?它正在失去生机,像一台安装了既定程序的机器,机械地运转着。机器,她怎么又想到了这个词?
这么多年,她就没问问自己想干什么。
她不明白自己这样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年迈的父亲曾说过,人活着的意义就是活着。这是一句极具玄妙与哲思意味的话语。但那是个年已八旬,因严重的眼疾而不得不舍弃他每日相伴、视若珍宝的藏书的老人的感悟。那是“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之后,“看山还是山”的洞彻。尽管他爸讲这话的时候很平静,她听了却有几分伤感。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必须做点什么。晓鸥对自己说。
经过这个平静的周日之后,晓鸥的心却再也不能平静了。她再也不能把以前所做的一切视为理所当然。她要对自己重新做出安排。
这天夜晚,赵雷带着儿子回家后,晓鸥跟他说想找个钟点工。
赵雷说:“妈妈不要钟点工。”
晓鸥说:“我是说我们自己找个钟点工。”
“我们自己找个钟点工?”赵雷感到十分惊讶,“我们年纪轻轻的,家里又没有小孩子要照顾,找个钟点工,这不奇怪吗?你看哪家像我们这个年纪找钟点工的,以后你忙不过来吩咐我做就是了。”
晓鸥知道,这又是句不靠谱的承诺。以前又不是没有过。本来晓鸥搬出婆家也是想锻炼赵雷做家务的,怎奈当初买房时综合考虑了学区和靠近一个人的单位,结果就选了他们现在居住的这个小区。小学、中学都离家近,也靠近晓鸥的单位。距离赵雷上班的地方就比较远了,他早上出门,晚上又不在家,能指望他什么?
既然无法从这个家里得到解放,她就有必要为自己找个避难之所。在经济方面她有这个能力。小家庭的财政大权一直由她掌握,若想划出一小部分作为私人开支,完全可以不用知会赵雷。
带花园小径的农舍虽然是晓鸥的梦想之所,仔细考虑之后,还是觉得不现实。这是基于时间成本的考虑,而不是如赵雷所说——她曾经跟他说过,想将来找一处农舍养老,屋前种花,屋后种菜。赵雷说她又在胡思乱想,让她真去农村住住看,保证一天也待不下来。真正的农舍,仅仅是蚊虫这一点就让人受不了。
晓鸥想在家的附近找一处安静的小房子,在工作和家务之余,每周抽点时间给自己,躲在那里,一个人静静地待着,或者读书,或者画画。
她对房子的要求是要安静,要干净,要有给她画画的空间。她在网上寻找一些比较适合的小房子。还没等她选中满意的,一个个中介就将电话打了过来,搞得她不胜其烦。
房产中介接待她的是一位年轻帅哥,看到他的客户竟然是一位中年妇女,不禁露出狐疑的目光。他在跟她交流的时候,不停地用目光打量她。晓鸥仿佛听到了年轻人脑海里的声音:这位衣着讲究、颇有品位的中年女人为什么会要一所很小很小的小房子?难道她是一位离了婚的单身女人?对。晓鸥心想,他一定是认为她是个弃妇。因为她有信心认为,以她的气质仪态,她看上去绝对不像个有不正当需求才要租房子的女人。他可能已经在同情她了。他一定认为她的淡定是装出来的,事实上,她的淡定确实是装出来的。她的手心甚至连手指头都沁出了细微的汗珠。她没想到她真的会出来寻找房子,如果不是中介们一个劲儿骚扰的推动,也许这样的念头跟她以前的那些念头一样,在她脑海里转悠转悠便无疾而终。
如今她真的要去看房子了,她有些害怕,也有些兴奋。她的人生终于要有改变了。不知道这样的改变会给自己带来什么,但肯定不是无数个重复的死气沉沉的昨天。她握紧的拳头微微战栗,她要勇敢地面对明天。
看房子没费多少周折,是她网上看好的,再实地挑选一下,只要房东愿意搬走多余的家什就可以了。至于房租年付,押金为一个月还是两个月房租这些对晓鸥来讲都不是问题。她只需要一个比较空阔的空间,她需要的是画室兼书房。房东说那些东西都曾是他自己用的好东西,不是专门用来出租的劣质产品。房东对她要求搬走他原有的东西产生了怀疑,询问她租房的用途,晓鸥不想告诉他,晓鸥不想告诉任何人。这将是她一个人的隐秘世界,告诉别人就失去了意义。房东转弯抹角地说,有人租用住宅楼搞传销啊或者其他一些商业用途,万一被投诉,给自己找麻烦。晓鸥告诉他,让他放心,绝对是正当用途,绝不会给他惹麻烦。房东看了看晓鸥,想了想,把中介小哥拉一边去嘀咕了几句。这位小帅哥便过来,带着颇为尴尬的表情对晓鸥说:“不好意思了,姐,我不是想打听您的私人问题。但房东要求,若是……额,您和您先生一起带着证件来签约……”
“在这方面有什么规定吗?我是租房,又不是买房。”晓鸥问。
“啊,不是,没有规定。不过现在房东租房都这样要求。这不是,现在外面骗子多嘛。走个程序,走个程序而已,放心。”
“知道了,”晓鸥说,“那就再联系吧。”
晓鸥逃也似的从那个小区出来,额头上也沁满汗珠,心跳得也厉害,自己刚刚好像做了贼。不过那也差不多,人家就是像防贼似的防着她。晓鸥不仅没有租到房子,还受了一番侮辱。心里难受得要死。
好长时间,她的心情才慢慢平复,可她心里的那个魔咒却无法平复。她曾用心临摹的梵·高的《盛开的杏花》就挂在餐厅的墙上,好像在时时刻刻提醒她,她再也无法将以前的生活视为理所当然。她要将那个丢失的孟晓鸥找回来。这个念头日日缠绕着她,压迫得她无法呼吸,使她心绪不宁。虽然她每天还在做那一切,但心已不在上面,她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将自己真正投入这样的生活里。她神思恍惚,也常常出错。当她一而再再而三地把鱼煮糊了,肉烧咸了的时候,儿子终于忍不住了,笑着问她:“妈妈,你是不是把爱心弄丢啦?”
“什么?”
“你不是说,要带着爱心烧菜,菜才能烧得好,好吃吗?”
晓鸥没想到儿子会这么问她。这话她以前是说过而且也是这么认为的。而今情况不同了,她心里有些难过。她只能对儿子说:“对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