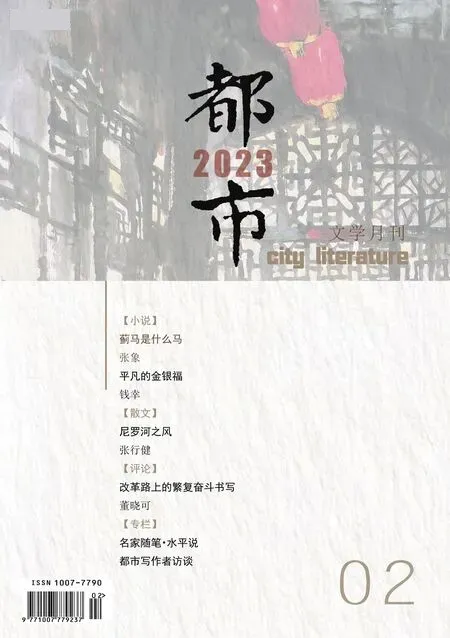河畔的父亲
文 宋耀珍
我发现父亲经常深夜悄悄起床后不知去向,是在上小学一年级后的第一天。那个夜晚,我的脑子里像放幻灯片一样,一直闪放着一张张新同学的面孔,有的熟悉有的陌生,尤其有一张对我不怀好意。半睡半醒之际,我听到了父亲和母亲的窃窃私语声,接着就是父亲窸窸窣窣穿衣服的声音,接着下地、趿拉上鞋、推门、关门,然后狗儿在院里“哼哼”两声,就跟着父亲离开院子了。很长时间过去,母亲已打起了呼噜,父亲还没有回来。我的好奇心陡起,钻出被窝,搂起衣服蹑手蹑脚出了屋子。我边走边穿衣服,很快就来到街道上。天空明亮,空气如清水,隔几家院门,门前就卧着一条看门的狗,我路过时,狗儿听到脚步声,有的抬起来眼皮看一下立刻闭上,有的眼睛刚睁开个缝就马上闭上,继续沉浸在它的美梦中。啊,洁净、安谧和充满信任的小城之夜!
但我走遍了小城的角角落落都没有找到父亲和我们家大黑狗的踪影。
不过我有的是办法。第二天临睡前,我在大黑的尾巴上拴了个小布袋,里面装上细石灰粉,在小布袋的一角再剪一个小洞。大黑不知道我在鼓捣什么,“嗯嗯呀呀”的极不情愿。我一觉醒来,先跑到院子里,把大黑尾巴上已经扁塌塌的小布袋解下来扔了,然后挨到了上学时间,一溜烟跑出了院子。我逃了一次学,顺着依稀可辨的石灰白线,来到了城西的河畔。这条河,是我们的乐园,我们的游泳场,我太熟悉了!这里一切如故,但父亲来这里做什么呢?
接连几个夜晚,父亲睡得很深,好像从来就没有深夜起床出行过。
谜底是母亲亲口告诉给我的。一个雨天,母亲没有下地干活,坐在房檐下望着雨水发呆。因为没有雨具,我拖延着不愿意去上学。“坐过来吧。”母亲说。我家的房子地基高出地面有一米,屋檐探出去又有两米,两边的墙壁砌起来,让门厅前变得像一座小戏台。我就搬个小凳坐了过去。雨点敲打着院子里砖块铺就的地面,水花前赴后继地盛开、消失,现在依然历历在目。“你想知道你的父亲深夜出去干什么吧,”母亲笑盈盈地看着我,薄薄的嘴唇轻轻扇动,像两片花瓣在风中开合,“你的父亲是一只水獭。”母亲说完,表情非常平静,好像她说出的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水獭”,我记住了这个词的读音。“你不要惊扰他,他很辛苦。”母亲继续用平静的口气说。“长大后你就会懂得你父亲了。”母亲补充道,接着用一声叹息结束了我们在这个雨天的对话。
父亲的职业是医生,在那个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他凭借自己的医术养活了我们一大家子。多年之后,我知道父亲在乐观的脸庞后面隐藏着的忧虑,这忧虑时时刻刻萦绕在他的心里,侵蚀着、蚕食着他的肉体与精神。父亲喜欢喝酒,而且经常大醉而归,他试图用酒精抗拒忧虑、消灭忧虑。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酒精帮助他赢得了短暂的胜利,因此酒精成为他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可以依赖的战友。但父亲清醒的时候更多,他要给慕名而来的病人把脉和开药。
几天后的一个深夜,我被母亲允许跟踪父亲。夜色下,父亲像是被一种激情催动,一改日常里慢吞吞的步伐,肥胖的身体敏捷地穿过街巷,潜入杂草丛生树木茂密的树林,我气喘吁吁地紧随其后。父亲钻出树林时,身体已经匍匐在地,变得圆鼓鼓的,一头栽进树林边哗哗作响的流水中。父亲真的是一只水獭!他在水里愉快地翻滚着,搅得水花飞溅。我遵从母亲的吩咐,很快爬到一棵树上,把身体严严实实地藏在浓密的树冠中。
父亲很快停止了嬉戏,他从水中爬到岸上来,甩动身体,水点被抛向四周,亮闪闪的。他快速走近河畔上最近的一棵树,那是一棵杨树,有碗口粗,他露出了锋利的牙齿,朝着树干贴近地面处啃去。我听到类似锯子在树木上拉动的声音,还有“吭哧、吭哧”有节奏的喘息声。大约十几分钟后,树干开始晃动,枝干上的树叶彼此撞击,像一群酣睡中被弄醒的婴儿。树干朝着河水倒了下去,父亲兴奋地冲向树冠部分,继续用他锋利的牙齿把枝枝丫丫咬断,留下光溜溜的树干。然后,他又把树干分成若干段,开始在河水流动湍急的地方建筑巢穴。他显得非常专心,也非常专业。父亲在故乡河畔忙碌的身影,永远篆刻在我的心上,让我现在写下这些文字的同时,心还在微微颤抖和隐隐作痛。
第二天早饭时,我发现父亲的嘴唇上有带血的伤痕。我张开嘴试图问候,但母亲递过来一个眼神,我只好把要说的话咽进了肚子。
我们家住在一个狭长的院子里,大门向东,靠近西边是一个单位二层办公楼的后墙,后墙上没有窗户,所以父亲就顺着这堵整齐的砖墙,朝东搭了一个十来米长的棚子。棚子里放着五六根水桶粗的剥了皮的树干,“这是盖房用的主要材料,房梁。”有一次,母亲一边搭晒衣服,一边对躺在这几根树干间的缝隙间乘凉的我说。我看着母亲两条白皙、圆润的手臂在湿漉漉的衣衫间挥舞,强烈的阳光把残留在手臂上的水珠照得闪闪发亮,像一颗颗晶莹剔透的永不掉落的珠宝。上初中时,我读到杜甫《月夜》中的诗句“清辉玉臂寒”时,心里蓦然出现的竟然是母亲在阳光下晾晒衣服的情景。
其时,正值暑假。我发现父亲深夜去往河畔的频率越来越高,早晨时,我在父亲的肩膀和背部看见了带血的划痕。“我要去看看父亲的建筑物建造到了什么程度”,怀着这样的渴望,我在一个下午独自来到父亲深夜忙碌的河畔。穿过密林时,遇到几对谈恋爱的男女躺在草丛中拥抱着,他们的喘息声粗重而急促,几只野兔从灌木丛中惊起,奔向另一片灌木丛,蝴蝶在树干间翻飞,树叶间漏下来的阳光斑点和草地上细碎的小花,混杂在一起分不出彼此,四面八方持久的鸟鸣,让人仿佛置身于一个巨大的音箱中。我淌水走进河水里,沿着河畔寻找了一圈,什么也没有,甚至没有任何痕迹。我回到岸上,靠近河畔没有一棵树桩能证明父亲曾经用锋利的牙齿啃断过它们。我失望地回到家中,等母亲从地里干活回来,迎上去就问“河畔为什么什么也没有”,母亲稍微愣怔了一下,弄清楚了我的问题后轻描淡写地回答道,“那是被洪水冲垮了。”“可是,连树桩也没有。”我继续追问。“是吗?”看母亲的表情她的心思根本就不在我的问题上,“我得赶紧给你们做饭了。”母亲说完,把我一个人丢在院子里,径自走进了屋子。
夏夜太热,我迷迷糊糊中听到有人穿衣服的声音,接着是穿鞋、推门、关门,肯定又是父亲。我等了一会儿,屋子里只留下母亲和兄弟们此起彼伏的呼吸声时,我赶紧蹑手蹑脚地溜出了屋子。屋外非常凉快,大黑卧在门口,差点把我绊倒。它哼哼唧唧了几声,像是埋怨我惊扰了它的美梦。我快步跑向河畔,穿过密林时听到河畔有喊叫声。我站在河畔,看见变成了水獭的父亲被四五个大人围在中间,这些人赤身裸体,但手里都握着或粗或细、或长或短的树枝。他们是些酒鬼,在城里醉酒后喜欢跑到河边来泡进河水里冲凉、醒酒。他们大笑着,或者用树枝抽打父亲,或者用力戳到身体上去,或者索性走近踢上两脚,父亲负痛躲避,这些人就兴奋得哈哈大笑,因大笑而扭曲的身体形态各异,显得无比丑陋。“把他翻过来,看看是公是母!”一个公鸡嗓子尖声喊道,其他几个人就“好”“好”地喊着应和。“让他自己翻!”公鸡嗓子又喊,一个人就走上前用树枝抽打父亲,“快翻,快翻,让老子看看你究竟是公是母。”我再也忍无可忍,扑了上去,抱住用树枝抽打父亲的人的胳膊,张嘴狠狠地咬住不放。这人开始喊叫,扔掉树枝,用两只大手扭住我的头,试图让我松口。我绝对不会松口,除非把咬在嘴里的这块肉撕下来。我最后还是被摔在了河畔的沙石上,然后看着这伙人抱着衣服扬长而去。父亲已经回到河水里,继续用树干加固他的建筑。他仿佛无视我的存在,一个人默默地用嘴、用身体、用短短的爪子当作工具,每个动作都显得非常专心。他仿佛已经忘记了刚才受到的羞辱,仿佛对自己所做的工作怀着神圣的使命感,并且在其间能够感到无穷的乐趣。
随后的几天,我发现父亲的腿有些瘸,走路非常吃力。而且,在一起吃饭时,我和他偶尔对视,我感觉他总是把眼神故意避开。既然父亲不想提及,我就把这件事当作一桩秘密吧。
在北方农村,盖房子是一个家庭最重要的事情,尤其对于像我们这样兄弟众多的家庭,没有房子是娶不到媳妇成不了家的。盖房子是一个家庭开支最大的项目,木料、砖瓦是基本材料,其中最重要、最费钱的就是木料。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一间房子的柱子、大梁、椽和门窗以及随后配置的简单家具都要用木料。“你父亲盘算着要尽快盖起来十二间房子,得赶得上你们的年龄。”多年后的一个下午,母亲坐在宽敞明亮的房子里,回忆起已经去世的父亲,这时候阳光照着的已经不再是原来那张饱满、俊俏的脸庞,岁月已经腐蚀了原来的那张脸。也就是那天下午,我知道了父亲为了盖起来房子而做的旷日持久的种种艰辛努力。父亲为了能够用最便宜的价格买回各种木料,总是在深夜和山里的农民交易,因为只有在深夜可以躲过检查,购买到农民偷偷砍伐的木材。比较细的椽头用平车拉或者用肩膀都可以扛回来,像柱子和大梁就必须用拖拉机,响声大、费用高,还得打点好夜里巡查的有关人等,父亲为此低声下气、煞费苦心。十二间房子用料量大,父亲几乎用了近二十年的时间来做这件浩大的工程。也就在这天下午,我彻底解开了父亲为何变成水獭的谜底。父亲常常深夜出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让我产生强烈的好奇。其时,我得了一种病,偶尔会产生幻听与幻觉,因此常常把现实和幻觉搅和在一起,分不清哪部分是现实哪部分是幻觉。我当时肯定看到过关于水獭的图片,听到过对水獭的介绍,而且水獭在河畔不知疲倦建造房子的形象让我印象深刻,于是在故乡漫长的夏夜里,我在半睡不醒的状态下,脑子里就幻化出一系列关于父亲变成水獭的故事。多年后,我成为一名诗人,同行们盛赞我诗歌想象力的丰富与诡异,其实只有我自己心里明白,这是一种疾病,至少是那种疾病的后遗症使然。现在想来,水獭建筑房屋的锲而不舍与父亲要盖房子的渴望与行动高度契合,水獭的形象就是父亲的形象,水獭的行为就是父亲的寓言。
据母亲说,父亲为了筹措盖房子所需要的工钱,求遍了全部亲戚和友人。当我大学毕业回到故乡参加工作,父亲浩大的工程已经完毕。昨天,几个朋友在一起喝茶,不约而同提到各自的父亲,其中一个小说家朋友说,他的父亲也是因为盖房子积劳成疾而病逝的。他说他的父亲是一个贫穷而尊严感极强的乡村教师,心里一直盘算着要为两个儿子盖起来一座院子。为此省吃俭用、兢兢业业,直到退休之前,终于拆除了原来既窄小又破损严重的旧房子,重新盖起来一排屋脊高耸的大瓦房,“那是他为后代建造的宫殿,”朋友说,“在房子建好全家住进去以后的几年里,他原来柔和的神情变得威严,累弯的腰开始重新挺得笔直,骄傲感和成就感流露在他日常说话的语气和动作中。”但是,隐藏着的疾病开始在他放松的神经下蠢蠢欲动,“如果那一排房子建不起来,他是不会得病早早离开我们的。”朋友声音低沉、语调悲哀,我看见一滴眼泪掉进了他端起来的茶杯中。突然,旁边一个女士哭出了声,是那种压抑了很久终于控制不住而发出的哭声。她是大学经济学教授,温文尔雅,眉清目秀,但一瞬间眼泪在她脸上肆虐,五官因痛苦而扭曲,她变得像孩子一样哭得无所顾忌。等她的情绪渐渐平息下来,她用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给我们完整讲述了她的父亲为了盖房子而经历的千辛万苦和百般羞辱。教授出生在遥远南方的一个偏僻乡村,她的故事中充斥着南方的气候、色彩、呢喃、鸟鸣、湿滑的石板路和雾蒙蒙的早晨。她的讲述不断被她自己的抽泣打断。这是一个关于父亲与房子的荡气回肠的故事,我打算把它写成另外一篇小说献给读者。我们离开茶馆时已是黄昏,分别前,大家不约而同地站起来,肃穆地垂下头。大家心照不宣,这是为天下所有辛劳的父亲默哀与致敬。
我的父亲在他的宫殿建成几年后,因病去世,当时他只有六十岁。父亲得的是肺癌,我试图曾用诗句描述他的痛苦:“咳嗽让他失眠。他变成梦呓的倾听者/睡眠的仇敌”“我看见父亲双手捧着他的病肺/在低头落泪”,我甚至猜测“他想往人类的梦呓中投放毒药/他黑暗中的眼神令人胆寒”。哦,父亲,请原谅我的猜测!
父亲出殡的那天,天阴沉沉的,世界变得像一个哀悼者,整个天空仿佛蓄满了泪水,准备大哭一场。我们在雨中向墓地走去,我扶着父亲的灵柩,心里浮现出早年读过的诗句:“父亲和我都怀着难言的恩情/安详地走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