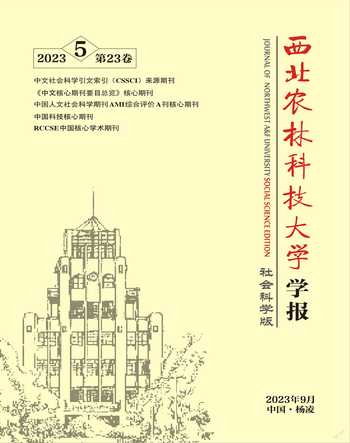内外耦合式发展:数字乡村建设的策略选择
郑永兰 周其鑫
摘 要: 數字乡村建设是建设数字中国、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必然选择和重要抓手,厘清数字乡村建设的动力来源是有效开展数字乡村建设的关键要义。从当前实践来看,我国正处于外源型模式的数字乡村建设初级阶段,具有短期内提升乡村数字化水平的优势,但也不可避免地面临可持续困境。随着乡村振兴制度设计的不断优化和村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以及数字技术普惠效应的充分释放,内生式发展逐渐成为数字乡村建设的创新方案。有别于“外源型输送”的发展模式,“内生式发展”模式更注重内生力量的激发,但同时“内生式发展”模式存在着“动力黑箱”的梗阻。未来要可持续地建设数字乡村,应该发挥外源和内生模式的联动作用,从筑牢乡村的硬件基础、培育数字乡村共同体、优化制度设计理念以及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等方面打造外源与内生耦合的建设图景,为实现数字乡村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方案。
关键词: 数字乡村;内生式发展;外源型输送;数字素养;乡村数字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23)05-0043-10
收稿日期:2023-02-11 DOI:10.13968/j.cnki.1009-9107.2023.05.05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1BZZ078)
作者简介: 郑永兰,女,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乡村治理。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回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当前城市的快速扩张与部分乡村的不充分发展使两者差距日益增大。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治理命题,并强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可见,实现农村现代化不仅是缩小城乡发展差距的重要选择,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中之重。步入21世纪以来,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的催化下,引发了一场数字化革命。数字技术的广泛嵌入与深度融合,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动能,乡村发展也迎来新的历史机遇。2018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要“实施数字乡村战略”,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历史性地将数字乡村建设上升到战略层面,清楚界定了数字乡村的内涵,明确了数字乡村建设的重点领域、指出了数字乡村建设的阶段目标。随后从中央到地方一系列的政策文件相继出台,加之地方乡村数字化实践的不断尝试,使得数字乡村建设开始从理论迈向实践。
在国家顶层设计与基层自主实践的双轮驱动下,数字乡村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发轫于数字信息技术革新的数字乡村建设不仅是实务界高度关注的行动方向,同时也引起理论工作者的广泛讨论。系统梳理起来主要集中于两大类。
第一,关于数字乡村基础领域的研究。主要包括价值内涵、主要内容、困境与路径、发展评估等内容。关于价值内涵的研究大致从“治理视角”“发展视角”和“技术视角”展开。“治理视角”认为数字乡村建设推动了乡村治理模式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单一主体走向协同治理,提升了乡村治理的精准性与科学性[1];“发展视角”认为数字乡村建设对于实现乡村振兴[2]、促进城乡融合发展[3]、实施数字中国战略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4],“技术视角”则强调技术与乡村的互嵌互生,主张充分释放信息化在农业农村升级转型中的巨大潜力[5]。关于主要内容的研究则涵盖传统乡村建设的诸多领域,认为数字乡村建设包括数字生产、数字生活、数字生态以及数字治理等重要领域。关于数字乡村建设的困境与路径的研究,主要从制度供给、乡村基础设施[6]、乡村数字人才[7]、村民数字参与以及农民信息素养[8]等维度对数字乡村建设的现实困境以及优化路径展开讨论。关于数字乡村建设评估的研究,张鸿等学者通过数字乡村宏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信息环境、政务环境以及应用环境5个维度构建了数字乡村发展就绪度评价指标体系,并进行了实证评价[9]。
第二,关于数字乡村建设发展模式的研究。数字乡村建设发展模式的研究解决的是如何更好地进行数字化乡村建设。系统梳理既有文献的研究,学术界主要聚焦于“外源型输送”的视角。 具体而言,主要存在三种逻辑。其一是国家逻辑,认为国家是数字乡村建设的制度引导者、体系创新者、要素调配者以及安全维护者[10],主张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从加强政策引领[11]、财政支持以及制度保障[12]等角度发展数字乡村建设;其二是市场逻辑,强调市场是开展数字乡村建设不可或缺的主体[13],认为数字乡村建设要充分发挥市场优势,鼓励电信运营商、大数据企业、现代金融物流企业等走进乡村,在基础设施建设、乡村公共服务供给、乡村电子商务发展等维度注入市场活力;其三是社会逻辑,认为乡村建设的根本意义在于处理好技术与社会的关系,强调技术只有与作为生产主体的人充分结合,才能真正释放数字技术的价值[14],认为应该注重加强村民的数字素养教育,提升村民的数字参与能力[15],发挥高校等科研院所的协同作用,为数字乡村建设注入社会力量。
整体来看,经过学术界的孜孜探索,勾勒出较为清晰的数字乡村建设理论轮廓,对于阐释数字乡村是什么、有哪些、怎样做作出了一系列的理论回应。然而,中国现代国家建构强调将分散的乡村社会整合成组织化的治理体系,确保国家权力在乡土社会中自由流动,最终将乡土社会吸纳进国家行政权力中[16]。在这样的治理结构中,乡村社会呈现出双重治理逻辑,即由国家权力形塑的外源治理逻辑和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内生治理逻辑。数字乡村建设同样展现出双重治理逻辑:依托政府制度性安排,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等方式向乡村地区“输血”的“外源型输送”与尊重乡村内生地位、激发乡村内生动力的“内生式发展”。从实践来看,“外源型输送”模式是当前各地开展数字乡村建设的主要方式,这种模式可以在短期内提升乡村数字化水平,但其发展是否具有可持续性仍有待观察与思考。“内生式发展”虽具备可持续发展的优势,但同时也面临动力“黑箱”的梗阻。因此,实现两种模式的有机耦合,优化数字乡村建设的发展模式,是有效开展数字乡村建设的关键所在,也是本文要回应的核心命题。
二、外源型输送:基本面向及其限度
伴随着数字技术在乡村公共空间的渗透,中国的乡村社会俨然进入了数字乡土时代。数字技术在乡村场域中的应用,变革了乡村社会结构,优化了乡村社会治理模式,壮大了乡村经济产业发展,繁荣了乡村公共文化建设。作为一种全新的乡村建设范式,数字乡村建设遵循“试点先行、总结经验、全面推广”的发展原则,在具体实践中,主要通过政府财政转移支付的形式完善乡村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出台一般性的政策文件去指引特殊性的数字乡村建设方向,逐渐形塑出“外源型输送”的发展模式。
(一)外源型输送模式下数字乡村建设的基本面向
1.技术下乡铺陈。《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指出:“数字乡村是指伴随网络化、信息化和数字化在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应用,以及农民现代信息技能的提高而内生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和转型进程”。从顶层设计的话语表述来看,数字乡村建设旨在通过数字信息技术推动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数字乡村建设的实践涉及乡村经济、农业基础设施、乡村公共服务、乡村治理以及乡村文化等各个领域[17]。循此逻辑,数字乡村建设的本质就是“数字技术下乡”的过程。“数字技术下乡”具有两层含义:一 是技术的“硬件”维度,强调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兴信息技术赋能乡村社会的过程,形塑出一批诸如“智慧农业”“电商经济”“数字产业”等新业态,造就了类似“大数据中心”“数字农业平台”“环境遥感监控”“城乡社会数字化治理平台”等新平台;二是从技术的“软件”出发,借助数字技术在乡村的嵌入与驱动提升村民的数字素养,缩小城乡数字鸿沟。
2.行政力量嵌入。数字乡村建设的实质是国家通过数字技术与科层体制的双重嵌入,实现乡村的数字化改造[13],为国家深度整合乡村社会提供契机。在实践过程中,政府将乡村纳入数字平台,借助于数字技术缩短国家与乡村的时间与空间,通过可视化的监管和精细化的服务方式实现乡村社会的透明化。数字乡村建设的实践逐渐成为国家政权整合乡土社会的重要维度[18],国家为有效形塑“其眼中的社会[19]”,采取了行政嵌入的方式,助推乡村的数字化转型。地方数字乡村建设的实践中,政府的身影无处不在。从学术界对实践的研究来看,行政嵌入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出台地方乡村数字化转型的政策规划;二是成立专门的指导部门;三是协调企业与社会力量参与共建数字乡村。
3.指标考核导向。数字乡村建设作为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同时也是地方各級党委政府要完成的政治任务,但在现实发展中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出现脱节。由于缺乏标准化指导体系,叠加“政治锦标赛”[20]的激励与压力,地方政府普遍追求短期成效,在数字乡村建设的战略规划下争先恐后开始乡村数字化转型,采用干部驻村和引进技术人才组成“技术官僚”下沉乡村方法,以期尽快推进数字乡村建设。更有甚者,为完成上级的绩效考核任务,不惜斥巨资打造数字平台,不考虑“云端”上的新事物与“乡土”社会的适配度,不仅加重地方财政负担,同时加深了地方政府的形式主义。
(二)可持续困境:外源型输送模式下数字乡村建设的主要限度
“外源型输送”的发展模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乡村的数字化水平,然而从长期和稳定的角度看,这种“输血式”发展无法解决数字乡村建设中普遍存在的“贫血”和“失血”问题,治标不治本。从资源、发展、主体的角度来看均存在一定局限性。
1.资源维度:难打通的“最后一公里”。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是近年来国家为破除城乡二元体制壁垒的重大举措,随着税费制改革以及农业税的全面废除,国家与乡村的关系从“汲取”转向“给予”[16]。国家通过提供公共服务的形式,推动城市资源向乡村流动,试图“以城带乡”“以城促乡”,最终实现“城市反哺乡村”“城乡融合发展”的愿景。既有研究表明,外源型发展模式推动了资源、资本、技术等要素的下乡,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乡村经济社会发展,但也具有很强的局限性。一方面,国家向乡村输入资源越来越多,并且越是国家输入资源农民就越是“等靠要”[21];另一方面,当前乡村人口外溢以及村庄空心化愈发严重,大多数村民通过进城务工实现脱域流动,在村村民缺乏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与积极性,难以对资源的利用形成有效监督。此外,国家对乡村的资源供给主要通过县乡两级政权组织实现,对上负责和对下脱离的弊病造成资源利用效果差和浪费严重,形成了难以打通的“最后一公里困境”[22],逐渐成为制约数字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
2.发展维度:亟需纾解的“马太效应 ”。发轫于信息技术变革的数字乡村建设,是数字技术与乡土社会的有机耦合,数字土壤的肥沃与否决定了数字乡村建设水平的高低。《县域数字乡村指数(2020)》指出,我国数字乡村建设取得初步成效,但仍面临区域发展不平衡、试点项目难推广等方面的问题,“东部发展水平较高、中部次之、东北和西部发展滞后”的格局未发生改变,截至2020年,东部、中部、东北和西部县域数字乡村指数分别为(68∶61∶46∶48)[23]。忽视乡村内生发展动力的“外源型输送”模式往往受制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东部地区具有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较为发达的技术基础以及较为完备的信息产业,这些先天优势使其有更为殷实的资源供给乡村,从而导致“强者恒强”。反观西部地区,由于特殊的地理区划以及历史发展背景,使得这些地区在基础设施建设、资源开发利用以及技术人才引进等方面处于相对劣势,这些地区在开展乡村数字化实践中往往沦为同级其他地区的“陪跑者”,从而陷入“弱者愈弱”的泥潭[12]。可见,外源型输送的发展模式已经造成了亟需纾解的“马太效应”,同时也是实现数字乡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症结。
3.主体维度:日趋紧张的“挤出效应 “挤出效应”原意指政府扩张性财政政策导致的利率上升所引起的私人投资减少。本文意指政府等行政主体的参与,挤压了乡村内部精英的参与空间,从而产生了挤出效应。 ”。信息技术具有门槛效应,受教育水平、科技能力等因素的限制,一部分人会在数字技术时代被隔离在技术壁垒的高墙外。数字乡村建设被认为是化解城乡数字鸿沟的有效载体,然而,由于乡村社会的数字发展环境薄弱,大量的数字弱势群体存在,而外源型输送的发展模式强调对乡村的“输血”,从而造成了数字乡村建设悬浮于乡村社会之上。科层体制压力传导下基层政府通过行政手段不断干预乡村治理,抑制了乡村的自主性和积极性。地方政府通过组建“技术官僚”团队的形式进入乡村,这些“技术官僚”往往是为了完成上级下放的绩效考核目标,从而追求短期发展效应,忽略长期发展动能。同时,“技术官僚”的下乡,使得原有熟知乡村情况的内生性精英退出乡村建设舞台。此外,当前地方在实践中,不惜巨资打造的数字平台,名义上提升了乡村的数字化水平,但实际上挤压了更多的乡村群体,一些不具备数字设备使用能力的数字弱势群体只能游离观望。外源型输送模式下的数字乡村建设模式,对乡村内生性主体无疑产生了“挤出效应”,日趋紧张的“挤出效应”俨然成为掣肘数字乡村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瓶颈。
三、内生式发展:价值意蕴及其梗阻
“内生”(endogenous)一词源于植物学研究中,意味某种植物不受外在条件的左右,从内部生长出与母体相同的新个体[24]。内生式发展(endogenous development)作为发展理论源流中的一种新兴理论思考,是与外源型发展(exogenous development)相对立的概念,发轫于瑞典Dag Hammarskjld财团1975年在联合国经济总会报告。该报告中指出“如果发展作为个人解放和人类的全面发展来理解,那么事实上这个发展只能是从一个社会的内部推动[25]”,以此为开端,内生式发展的概念相继引入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不同学科,在欧美和亚洲国家引起了广泛讨论,经过西川润、宫本宪一、鹤见和子、Ray等学者的接力阐发,逐渐形成了内生式发展理论以及新内生式发展理论。内生式发展理论的实质强调,发展要满足人类的真正需要,确保自身的全面发展,目的是为人类服务;主张以人为中心主体,发展的模式要适应本身的特色;强调要协调好各方关系,确保经济、社会、自然、文化的可持续性[26]。与外源型发展不同,内生式发展具有自下而上的性质,更注重社会发展的综合提升而非单一领域的增长,主张社会发展要根据自身的文化特征和思想、结构,寻找适合自身的发展类型和方式。
内生式发展理论传入中国以后,引起学者广泛关注。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国内部分学者从内生式发展的视角对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展开论述。张行发等基于新内生式发展的理论视角,结合研究案例,讨论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衔接过程中乡村内生动力的激发路径、价值意蕴及其运作逻辑[24]。卢飞以民族地区为个案研究,发现在完成脱贫攻坚迈向乡村振兴的阶段中,乡村发展的内生性动力并未被激活,由此构建了乡村振兴内生式发展的分析框架,探索民族地区实现乡村振兴的路径[27]。沈费伟则是从数字乡村建设的视角出发,对数字乡村内生式发展模式的主要类型、实践逻辑以及优化策略等问题进行讨论[28]。可以看出,内生式发展理论在中国乡村建设中已经得到了广泛应用。然而既有研究更多是将内生式发展的视角聚焦于乡村振兴,虽有研究将视角关注于数字乡村,但是针对数字乡村内生式发展的内在机制缺乏深入讨论。
(一)数字乡村内生式发展的价值意蕴
1.全面推进乡村振興的制度安排。数字乡村建设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是推动农业农村农民现代化转型的必由之路。充分尊重乡村内生地位、发挥村民主体作用,不仅是全面铺陈数字乡村建设的题中之义,同时也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制度安排。《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指出要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切实发挥农民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作用,增强农业农村自我发展动力;《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提出“要激活主体、激活要素、激活市场,不断催生出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数字乡村发展行动计划(2022-2025年)》则强调“坚持以人为本、内生驱动,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从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可以看出,内生式发展模式是数字乡村建设的必然选择。
2.村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中共十九大报告中作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的论断,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成为当前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矛盾。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成就使人民在物质生活、精神领域等得到了巨大的提升,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进的核心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方略[29],“人民至上”理念进一步强化了人民在国家建设目标定位中的地位[30]。数字乡村建设能否有效推进,核心也在于能否发掘乡村社会发展和社会建设的内生动力[31]。当前,数字乡村建设中存在两股重要的内生力量:一类是在域村民,诸如留守在村的中青年群体、部分乡村精英;另一类是脱域村民,例如外出务工的青壮年劳动力以及部分新乡贤。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逐渐激发了这两类群体参与村庄经营管理的热情,由于具有乡土情怀,这两类群体在开展数字乡村建设中往往能够发挥更大的效能,对于有效打破“最后一公里困境”、消弭区域发展的“马太效应”、推动乡村数字化转型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
3.数字技术的普惠效应充分释放。农业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农业物联网、人工智能等农业信息技术的进步与渗透推动了数字经济在农业领域的发展,利用数字技术赋能农业有助于提升农业生产效率与发展质量[32]。随着乡村网络基础设施的不断普及和信息产业的快速发展,基于数字技术的信息红利不断向乡村地区和农业领域快速扩散,乡村逐渐摆脱了传统意义上的落后、贫穷,迎来了发展与富裕的机遇。数字技术为城乡融合发展创造了可能,以“互联网+医疗”“互联网+教育”“互联网+养老”等为代表的新型公共服务供给样态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姿态渗透乡村,以“淘宝村”“直播带货”“电子商务”等为样板的新型经济发展模式使村民的“钱袋子”逐渐鼓了起来。数字技术的普惠效应精准有效地穿透进乡土社会,提升了村民的经济水平,更新了村民的精神观念,激发了村民内生性主体意识,为数字乡村内生式发展积蓄了动能。
(二)动力“黑箱”:数字乡村内生式发展的现实梗阻
既往的乡村社会治理实践中,国家重视资金、技术、人才的外部输入,忽略了乡村本身的内源性因素才是推动其发展的动力,在实践中也曾遭遇“有增长无发展”的挫败[33]。与外源型输送模式强调外部力量输入不同,内生式发展主张地方发展的内生动力。然而,在认识到其蕴含的巨大价值的同时,也需要厘清这种内生动力是基于何种土壤产生,又如何能得到维持与复制,显然这些还处于“黑箱”之中[34]。
1.观念迟滞:乡村公共精神式微。公共精神在民主治理的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35]。乡村公共精神是指村民在处理个人利益与村庄公共利益的关系中所具有的关心与积极参与公共事务、政治利他、爱心和奉献等公共价值与信念[36],是有效开展乡村建设的文化灵魂和精神动力。它能够将原子化的村民整合在集体的目标和利益之下,从而凝聚人心,是促进乡村社会发展的动能[37]。受多重因素的影响,当前乡村公共精神逐渐式微,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数字乡村建设的内生发展。一方面,村民集体主义观念淡薄,热衷于追求个人利益,对乡村公共事务参与不足[38];另一方面,乡村公共空间萎缩,随着经济体制改革以及乡村集体生产方式的解体,加上数字信息技术的应用普及,村民的闲暇时间被手机、电视、电脑等媒体设备所充斥,集体性的公共行动越来越少,个体化的行动越来越多,培育乡村公共精神的传统载体不断萎缩[39],从而挤压了村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热情。
2.信息贫困:村民数字素养匮乏。数字乡村建设是数字化、网络化以及信息化技术在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应用,强调的是农民现代信息技能的提高和内生的农业农村现代化转型。作为建设数字乡村的“关键内核”,村民数字素养的高低直接影响数字乡村建设的水平。《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中国乡村数字素养调查分析报告》数据表明,当前乡村居民的数字素养得分为35.1分,城市居民数字素养得分为56.3分。根据第5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2年6月我国乡村网民规模为2.93亿[40]。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58.8%,尚有2亿多乡村人口没有接触互联网。在城镇化浪潮的推进下,城乡二元结构被打破,越来越多的乡村劳动力流向城市,农村人口大量流失使乡村人口老龄化现象日益加剧。老年人受限于意识固化、文化有限以及适应性差等制约,使得他们缺乏掌握数字设备的能力,缺乏数字意识。此外,中国地方经济发展呈现典型的“东强西弱、南高北低”的特征。以笔者调研过的中部H省和西南G省M县为例,两省之间城镇化率基本持平,然而县域经济水平差异显著。通过走访调研发现,多数农户家庭里数字设施匮乏。与基层工作者进行溝通访谈得知,乡村工作重心在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有效防止脱贫人员再返贫,加之上级财政支持有限,部分地区缺少完善数字基础设施的资金来源,农民数字素养教育工作只能缓慢推进。
3.行动困境:乡村内生主体缺位。数字乡村建设的出发点是回应“是什么”的问题,落脚点是考虑“谁来建”的问题。乡村本土组织作为乡村内部自发成长起来的关键群体,是有效推进数字乡村建设的关键动力,然而一段时期以来数字乡村建设一直是在政府的主导下进行。由于缺乏相应的政策机制,乡村内生性主体始终处于“缺位”状态,多元主体参与数字乡村治理呈现“有心无力”的瓶颈。一方面是绝大多数“不想动”。传统的乡土社会格局被打破,后乡土社会叠加上城镇化进程的催化,越来越多的乡村居民离开乡村流向城市。据《2020年中国农村发展报告》预测,2025年我国农业就业人员所占比率进一步下降至20%。大量的人口外迁,导致乡村空心化程度严重。流动人口的外迁实现了脱域流动,留守村民绝大多数为“386199” 386199指的是留守在农村的妇女、儿童以及老年群体。 部队,这部分群体对于乡村建设事务多漠不关心或者有心无力。另一方面是关键少数“不愿动”。作为一项集系统性、长期性与复杂性为一体的战略工程,数字乡村建设需要持续性的资源输入,一些民间资本作为本土成长起来的内生力量对于参与数字乡村建设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由于数字乡村建设周期长、见效慢且缺乏明确的政策引领,多数社会企业、民间资本都处于观望状态。虽有少数具有“企业家精神”的社会力量参与数字乡村建设,但始终难成规模。
4.资源脱嵌:数字产业发展脱位。空间社会学认为,空间概念的社会建构根植于生产社会关系之中,随着生产方式的变革及社会形态的转型,空间的存在形式及其属性也随之发生变迁。数字技术的横空出世,催生出了数字空间概念,促使了人类生产生活场域的变革。数字乡村建设作为数字技术在传统乡村空间的嵌入,为乡村社会发展提供了新的资源,例如数字资源要素等。然而,传统的乡土性以及新兴的数字化在乡村社会之间的并存,促成了乡村新型二元社会格局的产生。数字生产要素与传统农业生产要素在数字空间的“狭路相逢”,毋庸置疑地形成了巨大的张力。数字生产要素是发展数字经济的关键内核,数字产业是推动数字乡村建设的动力引擎,以数字生产要素为驱动的乡村数字产业能够极大程度激活乡村集体经济的动能,发挥数字经济的乘数效应,是激活数字乡村内生发展动力的重要“原料”。然而,当前数字乡村建设过程中数字生产要素呈现明显的“脱位”状态。一方面,乡村特色产业资源没有充分开发,使得产业数字化转型“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另一方面,当前乡村数字产业的发展模式更多地受传统农业生产的路径依赖,生产要素的流动、产品的加工与销售等依旧以传统农业为主;当前村民的数字意识有限,大多数村民对于产业数字化的概念主要集中于使用微信、支付宝等线上支付平台,虽有部分村民通过开展“网店”的形式进行线上销售,但这部分群体终归是少数,尚未形成规模且仅仅实现了销售的数字化,对于生产、加工等环节的数字化依旧处于空白状态。数字产业发展的脱位,使得数字经济的规模效应未能充分释放。
四、内外耦合式发展:数字乡村建设的前景展望
“耦合”作为一种物理学名词,原意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电路构成一个电路网络时,如果其中一个电路电流或电压发生变化,则会影响到其他电路发生类似的变化,这种网络便称为耦合电路。该概念经过社会学学者的阐释与延伸,逐渐被应用于研究社会发展之中。数字乡村建设在实践中出现的“外源型输送”和“内生式发展”两种模式,表面上看是相互对立,实则互相补充。从“耦合”的概念出发,本文建构出“内外耦合式”的发展模式,借以展望数字乡村建设的前景。内外耦合式发展承认数字乡村建设需要借助外部资源的输送,同时也不忽视内生动力的激发。在数字乡村建设实践中,不能将两种模式进行割裂,而是需要充分发挥两种模式的功效,在此基础上形塑出“外源促内生、内生强外源”的内外联动型发展理念,为数字乡村建设提供双重动力,从而实现数字乡村建设的可持续发展。
(一)筑牢乡村的内生基础
1.提升村民数字素养。数字素养是村民在数字时代参与数字乡村建设的必备素质,同时也是释放数字乡村内生活力的关键要素。政府作为关键行动者,首先要制定提升村民数字素养的行动计划,各级文化宣传部门需加强数字技术的宣传与教育,广泛开展“数字下乡”活动。其次,加强财政转移支付,不断完善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政务服务平台在乡村的延伸,加快宽带、5G光纤网络的全覆盖。最后,持续选派具备良好信息素养的干部下沉乡村,组织培训村干部掌握数字化办公能力。此外,要充分利用好高校等科研院所等平台,开展大学生下乡行动,以培训和指导的方式组织村民拓展数字媒介的接触渠道、提高其数字媒介的认知水平,提升农民的数字素养。
2.营造乡村公共空间。乡村公共空间是村民围绕公共话题(活动、事件)展开交往、沟通的公共场所,对维系乡村社会秩序、形塑乡村公共精神、营造乡村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41]。激活数字乡村建设的内生动力需要重新营造乡村公共空间,通过乡村公共空间营造,可以实现村民的“再组织化”,使村民拥有参与数字乡村建设的平台与媒介。首先,要用好传统的乡村公共空间如新时代农民讲习所、村民活动中心、公共文化广场等。这些公共空间有助于维系“看得见的乡愁”,通过组织大家以集会的方式开展数字乡村建设事项的讨论,既有助于达成共识,也有助于形塑乡村公共精神。其次,要用好虚拟型乡村公共空间,如乡村微信群、网络互动平台。虚拟型乡村公共空间有助于形成“看不见的乡愁”,作为数字技术在乡村公共空间的嵌入,可以有效跨越物理场域的限制,实现不同群体的互动沟通。例如,通过微信群开展乡村公共事务讨论,一定程度上可以提升决策的效率,同时也可以使一些身处他乡的村民增强对乡土的情感认同。
(二)培育数字乡村共同体
实现内外耦合式发展的数字乡村建设,主张系统内外部的协同与联动。作为一项系统性的战略工程,数字乡村建设从来都不是由政府部门独自参与的“独角戏”,而是由多元行动主体共同参与的“大合唱”。数字技术的兴起打破了传统的物理桎梏,实现了多元行动主体的跨时空交流。此外,随着内生组织和社会力量逐步成长,这些行动主体也可以为数字乡村建设注入生机活力。培育以数字技术为纽带的数字乡村共同体,是有效开展数字乡村建设的必然选择。
培育数字乡村共同体需要充分明确各行动主体定位。(1)发挥政府“引路人”的作用。首先,加强政府部门工作人员的数字化教育,提升数字化办公水平,定期开展业务培训;其次,做好政策设计工作,制定数字信息技术创新、财政税收支持、金融保险服务、培训研修、人才引育、小农户与现代农业衔接等配套制度,优化营商环境[42];最后,推动政府职能部门之间信息共享、资源互通,打破部门壁垒,完善政务服务平台建设。(2)发挥市场“驱动者”的作用。一方面,引进平台企业参与数字平台的开发、运营与维护;另一方面,引进电商企业开辟乡村市场,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借助“平台经济”的规模效应,激活乡村经济发展活力。(3)强化村民“弄潮儿”的意识。首先,在村民中间广泛开展数字乡村教育宣传,强化数字乡村建设的战略意义,引导村民树立“主人翁”意识;其次,充分发挥乡村党组织的堡垒作用,村干部、在村党员、乡村精英要起模范带头作用,为数字乡村建设建言献策;最后,积极引导外出务工人员参与建设,通过互联网络平台打破时空束缚、物理桎梏,使他们能够再次融入乡土社会之中,成为数字乡村建设的“主力军”和“弄潮儿”。(4)发挥社会“协同者”的作用。首先,加大高校、科研院所等研究机构的下乡活动,开展校地帮扶行动,以大学生下乡、专家下乡等方式为依托,为数字乡村建设提供人才支撑、技术支撑;其次,发挥行业自律性组织协同作用,通过招商引资、技术培训等方式为数字乡村建设注入经济动力。(5)发挥技术“支撑者”的作用。首先是平台支撑,加强平台研发资金投入,实现政府、市场与社会的互联互通,加大农业科技技术研发力度,推动农业产业数字化转型;其次是服务支撑,加强政务服务一体化建设,优化村民办事流程,提升村民办事效率,加大政务数据开放力度,满足村民日益增长的对公共数据的需求;最后是决策支撑,完善村民参与乡村事务治理的渠道,绘制乡村事务的精准画像,提升乡村事务决策的科学性[42]。
(三)优化制度设计的理念
数字乡村建设不能采取“抄作业”的模式,这与数字乡村建设的价值理念背道而驰,要从乡村的历史性、内生性地位出发,转变当前政策制定的理念,由普遍性转向引领性,以特殊性强化精准性。近年来,国家数字乡村建设的指导性文件相继下发,地方政府先后出台适配性的政策文件。仔细解读相应的文件,多是对国家战略安排的回应,少部分结合地方发展实际做出调整,而到了基层政府,政策的制定往往存在较大偏差。要克服这种现象,就必须综合考慮,从乡村的内生性地位出发,推进数字乡村分级分类建设。
首先,增强政策的引领性。地方政府要扮演好引路人的角色,明确数字乡村建设并非一蹴而就,要逐步推动数字乡村战略的实施。(1)要明晰数字乡村建设的内涵,明确数字乡村建设的重点任务,深刻领悟《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和《数字乡村发展行动计划》等一系列政策文件的精神。(2)要厘定数字乡村建设的基础领域和重点领域,有针对性地结合区域社会发展现状出台政策文件。此外,政策制定的过程中不仅要避免“文字形式主义”的问题,同时要防止“一刀切”的现象发生。
其次,尊重乡村的特殊性。从地理区划来看,中国的东西南北地区具有高度的差异性、复杂性,是以乡村面貌也呈现特殊性,地方政府在制定数字乡村发展的政策文件时要充分尊重乡村的特殊性,明确乡村的不同类型[44],以《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中重点提出的四类村庄为例,分类施策、精准指导。例如:集聚提升类村庄要充分发掘产业资源,政策制定过程中侧重扶持地方产业发展;城郊融合类村庄要以城乡融合为基础,政策制定中侧重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等领域;特色保护类村庄要以保护地方特色文化、开展文化资源产业化建设等为政策制定的侧重点;搬迁撤并类村庄要以营造乡村公共空间、提升村民价值认同为侧重。坚持“特色村庄特色建、一般村庄一般建”的建设原则,以乡村主体地位为出发点,在尊重乡村特殊性的基础上,充分释放乡村发展的内生活力。
(四)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
从可持续发展理论视角来看,推动数字乡村内生式发展并不意味着完全排斥外部力量,而是要处理好内生与外源的关系,推动空间的整合,进而实现数字乡村的高质量发展。针对当前数字乡村建设的现状来看,须对城市与乡村两个空间进行整合,秉持“以城带乡、以城促乡、城乡融合”的发展理念,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1)推动要素互通。首先是科技创新要素从城市辐射乡村,推动城市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科技要素向乡村的流入。例如通过开展远程医疗解决乡村看病难的问题,通过开展线上教育的方式缩小城乡教育鸿沟,通过遥感系统开展农业农情监测,推动农业的精准化发展等。其次是乡村特色文化资源从乡村渗透城市,将具有乡土气息的文化资源流向城市,对于缓解城市压力、增强城乡之间文化认同大有裨益。(2)促进产业互融。数字技术为产业的规模化发展提供契机,充分释放了数字经济的乘数效应,数字产业正加速重塑经济生活和生产形态,促进城乡产业的互融。一方面要利用城市数字产业的集群优势,推动乡村第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另一方面依托城市健全的数字体系,带动乡村特色产业全流程发展,形成集生产、加工、储存、销售等环节为一体的全科产业链。此外,要加快乡村现代农业向城市产业结构渗透的步调,打通乡村传统产业与城市新兴产业联动的渠道[45],将乡村的农产品、土特产与城市的电商平台、数字经济相结合,实现产业互融。(3)实现价值共生。首先,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大对乡村公共服务的投入力度,通过设立专向财政资金,切实增强乡镇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能力,积极引进市场力量和社会力量;其次,保障城乡居民基本权益均等化,以乡村工作为重点,坚持社会公平正义原则,加强民生保障政策向乡村的倾斜。
诚然,数字乡村建设作为一项国家战略工程,势必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未来,应该加强对数字乡村建设的案例考察,持续深入地追踪典型案例。通过对地方行动方案的总结,进一步丰富“外源型输送”与“内生式发展”两种模式的框架体系与实践路径,从中绘制出更加清晰的耦合图景,并不断凝练出数字乡村建设的经验,为助推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更加丰富的理论参考。
参考文献:
[1] 郑永兰,周其鑫.数字乡村治理探赜:理论图式、主要限度与实践路径[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25(01):1-11.
[2] 赵星宇,王贵斌,杨鹏.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数字乡村建设[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2(06):52-58.
[3] 赵成伟,许竹青.高质量发展视阈下数字乡村建设的机理、问题与策略[J].求是学刊,2021,48(05):44-52.
[4] 曾亿武,宋逸香,林夏珍,等.中国数字乡村建设若干问题刍议[J].中国农村经济,2021(04):21-35.
[5] 谢文帅,宋冬林,毕怡菲.中国数字乡村建设:内在机理、衔接机制与实践路径[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43(02):93-103.
[6] 冯朝睿,徐宏宇.当前数字乡村建设的实践困境与突破路径[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53(05):93-102.
[7] 陆九天,陈灿平.民族地区数字乡村建设:逻辑起点、潜在路径和政策建议[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42(05):154-159.
[8] 苏岚岚,彭艳玲.数字乡村建设视域下农民实践参与度评估及驱动因素研究[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05):168-179.
[9] 张鸿,杜凯文,靳兵艳.乡村振兴战略下数字乡村发展就绪度评价研究[J].西安财经大学学报,2020,33(01):51-60.
[10] 邢振江.数字乡村建设的国家逻辑[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42(06):58-68.
[11] 刘少杰,周骥腾.数字乡村建设中“乡村不动”问题的成因与化解[J].学习与探索,2022(01):35-45.
[12] 刘天元,田北海.治理现代化视角下数字乡村建设的现实困境及优化路径[J].江汉论坛,2022(03):116-123.
[13] 韩瑞波.技术治理驱动的数字乡村建设及其有效性分析[J].内蒙古社会科学,2021,42(03):16-23.
[14] 吴宗友,朱镕君.数字乡村建设行动中的空间张力与空间整合[J].社会发展研究,2021,8(04):14-26.
[15] 郑素侠,刘露.数字乡村背景下农村居民信息能力及提升策略——以行动者网络的视角[J].新闻爱好者,2021(02):40-44.
[16] 王雨磊.数字下乡:农村精准扶贫中的技术治理[J].社会学研究,2016,31(06):119-142.
[17] 劉少杰,罗胤斌.推动数字乡村建设行动的有效路径[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02):182-189.
[18] 郭明.互联网下乡:国家政权对乡土社会的“数字整合”[J].电子政务,2020(12):24-30.
[19] 周梦冉.乡村数字治理中农民主体性问题研究[J].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22,136(04):97-104.
[20] 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J].经济研究,2007(07):36-50.
[21] 贺雪峰,田舒彦.资源下乡背景下城乡基层治理的四个命题[J].社会科学研究,2020(06):111-117.
[22] 刘建平,陈文琼.“最后一公里”困境与农民动员——对资源下乡背景下基层治理困境的分析[J].中国行政管理,2016(02):57-63.
[23] 北京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数字乡村项目组.县域数字乡村指数(2020)[R/OL].(2022-05-30)[2023-03-07].http://www.ccap.pku.edu.cn/nrdi/xmycg/yjxm/363361.htm.
[24] 张行发,徐虹,张妍.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新内生发展理论视角——以贵州省Y县为案例[J].当代经济管理,2021,43(10):31-39.
[25] LINSTONE H A.Another Development: Approaches and Strategies[J].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1979(01):95-96.
[26] 张慧,舒平,徐良.基于内生式发展的乡村社区营建模式研究[J].现代城市研究,2017(09):72-77.
[27] 卢飞.内源式发展: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路径探索——基于四川T县的实地调研[J].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40(01):118-128.
[28] 沈费伟.数字乡村的内生发展模式:实践逻辑、运作机理与优化策略[J].电子政务,2021(10):57-67.
[29] 申来津,邹译萱.以人民为中心:构建服务型政府的核心价值取向[J].社会主义研究,2018(06):97-101.
[30] 何阳,汤志伟.互联网驱动的“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网络化建设[J].中国行政管理,2019(11):69-74.
[31] 杨嵘均,操远芃.论乡村数字赋能与数字鸿沟间的张力及其消解[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1(05):31-40.
[32] 沈琼.用发展新理念引领农业现代化:挑战、引领、重点与对策[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6(03):81-90.
[33] 肖平,周明星.新时代乡村社会治理创新:基础、困境与路向[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38(04):110-117.
[34] 方劲.内源性农村发展模式:实践探索、核心特征与反思拓展[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5(01):24-34.
[35] 珍妮特·登哈特,罗伯特·登哈特.新公共服务:服务,而不是掌舵 [M].丁煌,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27.
[36] 吴春梅,石绍成.乡村公共精神:内涵、资源基础与培育[J].前沿,2010(07):131-135.
[37] 张润君,任怀玉.乡村振兴精神及其培育[J].甘肃社会科学,2020(03):92-99.
[38] 陈洪连,孙百才.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公共精神的缺失与重塑[J].长白学刊,2022(03):148-156.
[39] 祝丽生.新时代背景下乡村公共精神培育研究[J].广西社会科学,2018(09):133-137.
[40]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5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2022-08-31)[2023-03-09].https://www.cnnic.cn/NMediaFile/2022/0926/MAIN1664183425619U2MS433V3V.pdf.
[41] 郭明.虚拟型公共空间与乡村共同体再造[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8(06):130-138.
[42] 赵德起,丁义文.数字化推动乡村振兴的机制、路径与对策[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4(06):112-120.
[43] 郑永兰,周其鑫.乡村数字治理的三重面向:理论之维、现实之困与未来之路[J].农林经济管理学报,2022,21(06):635-643.
[44] 武小龙.乡村建设的政策嵌入、空间重构与技术赋能[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1(01):9-22.
[45] 陈潭.数字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着力点与新路径[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1(02):19-27.
The Picture of Exogenous and Endogenous Coupling:The Prospect and Future of Digital Rural Construction
ZHENG Yonglan,ZHOU Qixin
(1.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Nanjing 210095;2.School of Government,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875,China)
Abstract: Digital rural construction is an inevitable choice and important starting point for building digital China and realizing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Clarifying the power source of digital village construction is the key to effectively carrying out digital village construction.From the current practice,China is in the initial stage of exogenous digital rural construction,which has the advantage of improving the level of rural digitalization in the short term,but it also inevitably faces a sustainable dilemma.With the continuous optimization of the desig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ystem,the growing needs of villagers for a better life, and the full release of the inclusive effect of digital technology,endogenous development has gradually become an innovative solution for digital rural construction.Different from the development model of “exogenous delivery”,the “endogenous development” model pays more attention to the stimulation of endogenous forces.But at the same time,the “endogenous development” model has the obstruction of “power black box”.In the future,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rural areas,we should give full play to the linkage of exogenous and endogenous models.From the aspects of building a solid rural hardware foundation,cultivating a digital rural community,optimizing the system design concept and promoting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the construction picture of exogenous and endogenous coupling is created,and a theoretical solution is provided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rural areas.
Key words: digital rural areas;endogenous development;exogenous delivery;digital literacy;digital rural community
(責任编辑:张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