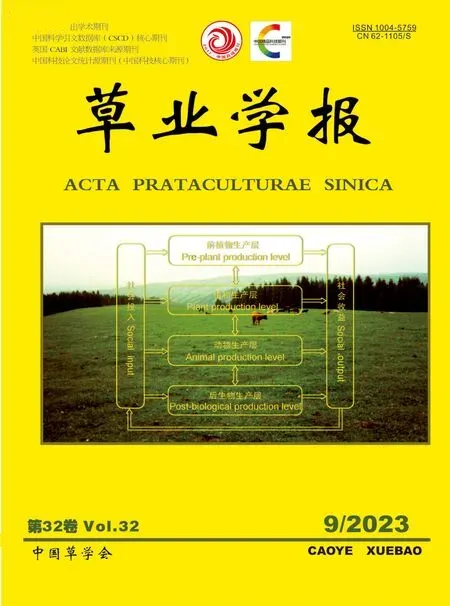高寒草地不同灌丛化梯度下土壤酶活性研究
张东,侯晨,马文明,王长庭,邓增卓玛,张婷
(西南民族大学青藏高原研究院,四川 成都 610041)
青藏高寒草地是我国重要的碳汇区,0~1 m 土层中土壤有机碳(soil organic carbon, SOC)含量达33.5 Pg,占全国SOC 的23.44%,是全球SOC 库的2.4%,因此,该区域SOC 储量的轻微变化,将会对区域乃至全球碳循环和气候变化产生重要影响[1]。近年来,由于气候变暖和过度放牧,该地区灌丛化现象日渐严重。1999-2009 年,青藏高原地区39%的高寒草原已发生灌丛化[2]。最新研究表明,青藏高原东缘地区灌丛在1987-2018 年整体呈增长趋势,截至2000 年,灌丛增长26.9%,2000-2013 年增长约32.7%。灌木侵入将改变草地地上生物量及各功能群生物量,导致土壤养分空间分布异质化[3]。同时,灌木可通过改变凋落物基质质量并减少表面有机物的光氧化,增加凋落物累积,进而影响土壤碳库[4]。刘超文等[5]的研究表明,灌木扩张将影响土壤呼吸强度,改变土壤养分动态。Li 等[6]利用Meta-analysis 方法研究表明,草地灌丛化对0~50 cm 土层SOC 含量有较大影响,在-50%~300%内变化,同时SOC 含量在半干旱和潮湿地区呈增加态势,豆科灌木侵入的草地增加幅度更大。目前,灌丛化对土壤碳库的影响仍存在争议。如熊小刚等[7]研究发现,小叶锦鸡儿(Caragana microphylla)侵入提高了原样地SOC 含量;何俊龄[8]发现,金露梅(Potentilla fruticosa)侵入青藏高原高寒草甸,同样提高了原样地SOC含量;Turnbull 等[9]研究表明,在不同梯度灌木侵入下,灌丛样地土壤有机质含量均显著高于未灌丛化草地。而刘小龙等[10]对若尔盖高寒草地灌丛化研究发现,高山绣线菊(Spiraea alpina)灌丛斑块土壤有机质含量降低了3.7%;杜慧平等[11]发现金露梅侵入高寒珠芽蓼(Polygonum viviparum)草地后SOC 含量减少了29%;Hughes等[12]研究表明牧豆树属(Prosopis)灌木侵入后温带稀树草原表层SOC 含量无明显变化;丁威等[13]以小叶锦鸡儿为研究对象,发现轻度、中度和重度灌丛化草地的植被叶片和土壤C、N 库差异均不显著。灌木侵入对土壤碳库的影响至今尚无一致结论,且不同梯度灌木侵入相关研究较少,而土壤酶作为有机质的重要分解者,土壤养分活化、周转及迁移的驱动者,是影响土壤碳库的关键因子,在土壤物质转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14]。史惠兰等[15]研究发现,金露梅侵入显著增加了样地土壤过氧化氢酶、蔗糖酶及脲酶活性。研究表明土壤酶活性在不同土层深度具有较大差异[16],且较多研究[17-19]均表明土壤酶活性随土层加深而逐渐降低。虽然灌丛化现象在我国较为普遍,但目前关于青藏高原地区灌丛化影响下土壤酶活性变化研究相对较少,且研究多集中在土壤表层,对次表层及更深土层研究较少,因此进一步揭示高寒地区灌丛化对土壤酶活性的影响尤为必要。
灌丛化梯度按照盖度可分为重度灌丛化(盖度>60%)、中度灌丛化(盖度为40%~60%)和轻度灌丛化(盖度为20%~40%)[20]。草地灌丛化后,土壤中地上和地下输入的有机碳的质与量都将发生变化,而土壤中物质循环的驱动者酶的活性是否受不同灌丛化梯度的影响,这种影响在不同的土层深度将怎样变化?基于此,本研究拟利用3 种高寒草地典型灌丛和3 个灌丛化梯度,探讨不同灌丛化梯度对高寒草地土壤理化性质以及土壤酶活性变化的影响,以期为高寒草地土壤碳库管理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位于四川省红原县境内(32°49′38″ N,102°34′21″ E,平均海拔3485 m)。该区域处于四川盆地向青藏高原过渡的高原区,属于大陆性高原季风气候,年均温1.4 ℃,日温差大,且干湿季节分明,年均降水量791 mm,年蒸发量为648 mm。土壤以高山灌丛草甸土为主,坡积物为成土母质。草地植被类型为高寒草甸,由草本和灌木植物构成,复合群落的总盖度约达70%,其中灌木的分盖度约50%,草本层植物种类和生物量较少,分盖度约30%。典型灌木为金露梅、高山绣线菊和小叶锦鸡儿。未灌丛化草地植被类型主要有禾本科、莎草科、菊科、豆科和毛茛科,其中伴生种中的禾本科与莎草科主要种类有发草(Deschampsia cespitosa)、垂穗披碱草(Elymus nutans)、垂穗鹅观草(Roegneria nutans)、剪股颖(Agrostis clavata)、溚草(Koeleria cristata)、草地早熟禾(Poa pratensis)。本试验样地基本概况如表1 所示。

表1 研究区基本概况Table 1 General information on the study area
1.2 研究方法
1.2.1 样品采集 于2021 年7 月,根据研究区草地灌丛化发展程度,参考Liao 等[20]划分的3 个灌丛等级,每个灌丛化样地设置为50 m×50 m,在样地内选择轻度(3 个重复样方,1 m×1 m)和重度灌丛化(3 个重复样方,1 m×1 m)采样区(海拔及朝向相同)。3 个典型灌丛类型(小叶锦鸡儿、高山绣线菊和金露梅)×2 个灌丛化梯度×3 个重复+3 个未灌丛化草地共21 个样方。每个样地内沿对角线选取6 个点,用土钻采集0~10 cm、10~20 cm、20~40 cm、40~60 cm 和60~80 cm 5 个不同深度的土壤样品(3 个重复),注意每一层样品取完后及时清理土钻再进行下一次采样。
1.2.2 样品处理及分析 按照《土壤农业化学分析方法》[21]中标准方法测定土壤理化性质,采用105 ℃烘干法测定土壤含水率(soil water content,SWC),采用雷磁pH 计(Remagnet pH meter,pHSJ-6L,中国)测定pH(水土比1∶5);采用重铬酸钾-硫酸溶液滴定法测定土壤有机碳(soil organic carbon)含量;采用凯氏定氮仪(Kjeltec Nitrogen Analyzer,NKY6120,德国)测定全氮(total nitrogen,TN)含量。按照《土壤酶及其研究法》[22]中标准方法测定土壤酶活性,采用磷酸铜比色法测定蔗糖酶活性,采用靛酚蓝比色法测定脲酶活性,采用碘量滴定法测定多酚氧化酶活性,采用硝基酚比色法测定葡萄糖苷酶活性,采用茚三酮比色法测定蛋白酶活性,采用蒽酮比色法测定纤维素酶活性。
1.3 数据处理
采用SPSS 22.0 软件统计分析数据。使用单因素方差分析(one-way analysis of variance)检验不同灌丛类型、不同灌丛化梯度以及不同土层的土壤理化性质差异性(统计检验的概率显著性水平为P=0.05)。在使用方差分析之前,对所有数据进行正态分布与方差齐性检验。采用CANOCO 5 软件冗余分析(redundancy analysis,RDA)功能分别对5 个土层深度的土壤酶与环境因子的关系进行分析,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SEM)来模拟不同灌丛化梯度、土壤理化性质和酶活性之间的关系,模型中的路径系数和决定系数(R2)由AMOS 23 软件来计算,采用Origin 2018 绘图。
2 结果与分析
2.1 高寒灌丛化草地土壤理化性质
试验结果表明(表2),除小叶锦鸡儿(重度)外,在0~10 cm、40~60 cm 土层,不同灌丛化梯度草地的土壤pH均显著高于未灌丛化草地(P<0.05);在10~20 cm 土层,高山绣线菊(轻、重度)和金露梅(重度)显著高于未灌丛化草地(P<0.05);在20~40 cm、60~80 cm 土层,未灌丛化草地显著低于各灌丛化草地(P<0.05)。

表2 不同灌丛化梯度对土壤理化性质的影响Table 2 Effect of different shrub encroachment gradients gradients on soil physicochemical properties
在0~40 cm 土层,不同灌丛化梯度草地土壤含水率均显著低于未灌丛化草地(P<0.05);在40~60 cm 土层,未灌丛化草地土壤含水率显著高于小叶锦鸡儿(轻、重度)及金露梅(轻)灌丛化样地(P<0.05);在60~80 cm 土层,小叶锦鸡儿(轻、重度)及金露梅(轻、重度)灌丛化样地土壤含水率显著低于未灌丛化草地(P<0.05)。
不同程度灌丛化草地对土壤表层SOC 含量影响较大。在0~10 cm 土层,未灌丛化草地土壤SOC 含量显著低于金露梅(轻、重度)、高山绣线菊(轻度)及小叶锦鸡儿(轻度)草地;在10~20 cm 土层,未灌丛化草地显著低于各灌丛化草地(P<0.05);在20~60 cm 土层中SOC 含量无显著差异;在60~80 cm 土层中,各灌丛化处理与未灌丛化草地间差异不显著。
灌丛化显著降低了表层土壤TN 含量。在0~20 cm 土层中,未灌丛化草地TN 含量显著高于各灌丛化草地(P<0.05);在40~60 cm 土层中,高山绣线菊(重度)和金露梅(重度)TN 含量显著高于未灌丛化草地(P<0.05);在60~80 cm 土层中,高山绣线菊重度、金露梅重度灌丛化草地TN 含量显著高于未灌丛化草地(P<0.05)。
2.2 不同灌丛化草地土壤酶活性特征
3 种灌丛(轻、重度)总体上降低了土壤酶活性,且轻度灌丛化影响较大。不同土壤酶活性对轻度灌丛化的响应存在差异(图1)。3 种轻度灌丛化样地和未灌丛化样地蔗糖酶活性:0~10 cm 土层金露梅显著低于未灌丛化草地(P<0.05),10~20 cm 土层金露梅、小叶锦鸡儿显著低于未灌丛化草地(P<0.05),20~40 cm 土层3 种灌丛化草地均显著低于未灌丛化草地(P<0.05),40~80 cm 土层3 种灌丛化草地与未灌丛化草地无显著差异(P>0.05);脲酶活性:0~20 cm 各土层金露梅、小叶锦鸡儿显著低于未灌丛化草地(P<0.05),20~60 cm 各土层3 种灌丛化草地与未灌丛化草地无显著差异(P>0.05);多酚氧化酶活性:各土层3 种灌丛化草地与未灌丛化草地均无显著性差异(P>0.05);葡萄糖苷酶活性:0~20 cm 各土层中3 种灌丛化草地显著低于未灌丛化草地(P<0.05),20~40 cm 土层中金露梅、小叶锦鸡儿显著低于未灌丛化草地(P<0.05),60~80 cm 土层中金露梅、小叶锦鸡儿显著高于未灌丛化草地(P<0.05);蛋白酶活性:各土层3 种灌丛化草地与未灌丛化草地均无显著差异(P>0.05);纤维素酶活性:0~10 cm、40~80 cm 各土层3 种灌丛化草地与未灌丛化草地均无显著差异(P>0.05),10~20 cm 土层金露梅、高山绣线菊显著低于未灌丛化草地(P<0.05),20~40 cm 土层3 种灌丛化草地均显著低于未灌丛化草地(P<0.05)。

图1 轻度灌丛化各样地的土壤酶活性Fig.1 Soil enzyme activity of sample plots under lightly shrub covered
不同土壤酶活性对重度灌丛化的响应存在差异(图2)。3 种重度灌丛化样地和未灌丛化样地蔗糖酶活性:0~20 cm 土层3 种灌丛化草地与未灌丛化草地无显著差异(P>0.05),20~40 cm 土层未灌丛化草地与小叶锦鸡儿灌丛化草地有显著差异(P<0.05),40~80 cm 土层未灌丛化草地与高山绣线菊灌丛化草地有显著差异(P<0.05);脲酶活性:0~10 cm 土层金露梅、小叶锦鸡儿与未灌丛化草地有显著差异(P<0.05),10~20 cm 土层小叶锦鸡儿和金露梅显著低于未灌丛化草地(P<0.05);多酚氧化酶活性:10~20 cm 土层金露梅与未灌丛化草地有显著差异(P<0.05),20~40 cm 土层金露梅与高山绣线菊有显著差异(P<0.05),且20~80 cm 各土层3 种灌丛化草地与未灌丛化草地无显著差异(P>0.05);葡萄糖苷酶活性:0~10 cm 土层未灌丛化草地显著高于灌丛化草地(P<0.05),10~40 cm 土层未灌丛化草地显著高于金露梅、小叶锦鸡儿灌丛化草地(P<0.05),60~80 cm 土层高山绣线菊显著高于未灌丛化草地(P<0.05);蛋白酶活性:0~20 cm 各土层3 种灌丛化草地显著低于未灌丛化草地(P<0.05),20~40 cm 土层小叶锦鸡儿显著低于未灌丛化草地(P<0.05),40~60 cm 土层3 种灌丛化草地与未灌丛化草地无显著差异(P>0.05),60~80 cm 土层金露梅显著低于未灌丛化草地(P<0.05);纤维素酶活性:20~40 cm 土层金露梅、小叶锦鸡儿显著低于未灌丛化草地(P<0.05),其余各土层3 种灌丛化草地与未灌丛化草地无显著差异(P>0.05)。

图2 重度灌丛化各样地的土壤酶活性Fig.2 Soil enzyme activity of sample plots under heavily shrub covered
2.3 不同灌丛化梯度及不同土层土壤酶活性特征
不同灌丛化梯度下土壤酶活性总体随土层加深而递减(图3)。轻度灌丛化影响下,与未灌丛化草地相比,高山绣线菊(图3a)、小叶锦鸡儿(图3b)与金露梅(图3c)灌丛样地在0~40 cm 各土层中,蔗糖酶、脲酶和葡萄糖苷酶活性均呈降低趋势,且3 种酶活性均在金露梅灌丛样地中降幅较明显,蔗糖酶活性在20~40 cm 土层降低35.3%,脲酶和葡萄糖苷酶活性在10~20 cm 土层分别降低25.7%、44.9%。蛋白酶和纤维素酶活性在0~80 cm 各土层中均呈降低趋势,2 种酶活性均在金露梅灌丛样地20~40 cm 土层降幅较明显,分别降低54.5%(蛋白酶)和52.8%(纤维素酶)。多酚氧化酶活性在金露梅灌丛样地各土层中呈降低趋势,在10~20 cm 土层最明显(37.3%)。
重度灌丛化影响下,与未灌丛化草地相比,高山绣线菊(图3a)、小叶锦鸡儿(图3b)与金露梅(图3c)灌丛化样地在0~20 cm 土层中,蔗糖酶、脲酶和葡萄糖苷酶活性均呈降低趋势,且3 种酶活性均在金露梅灌丛样地10~20 cm 土层中降幅较明显,分别降低25.7%、24.8%和37.9%。蛋白酶和纤维素酶活性在0~40 cm 各土层中呈降低趋势,其中蛋白酶活性在金露梅灌丛样地10~20 cm 土层降低38.2%、纤维素酶活性在小叶锦鸡儿灌丛样地20~40 cm 土层中降低52.8%。多酚氧化酶活性在金露梅灌丛样地各土层中呈降低趋势,在60~80 cm 土层最明显(90.0%)。
2.4 土壤酶活性调控因子
采用RDA 排序模型,利用方差膨胀因子分析,对5 个环境因子进行共线性分析,所有环境因子变量都小于10,各土层土壤理化性质对土壤酶相关性RDA 分析结果如图4 所示。所有环境因子解释率分别为:0~10 cm(图4a)60.4%、10~20 cm(图4b)65.1%、20~40 cm(图4c)62.9%、40~60 cm(图4d)54.2% 和60~80 cm(图4e)46.5%。各土层土壤酶活性的主要解释因子均为SWC,分别可解释土壤酶活性变异的41.2%、50.5%、37.1%、41.5%和26.0%。
SEM 分析进一步探究了不同灌丛化梯度下土壤理化性质和土壤酶活性之间的作用关系(图5)。结果显示,不同灌丛化梯度可直接显著正向影响蔗糖酶(0.14)、脲酶(0.15)和纤维素酶(0.15)(P<0.01),葡萄糖苷酶(0.11)、蛋白酶(0.08)(P<0.05);对多酚氧化酶活性无显著影响(P>0.05)。不同灌丛化梯度也可显著正向影响pH(0.27)(P<0.001),进而负向影响葡萄糖苷酶(-0.13)(P<0.05),蛋白酶(-0.21)和纤维素酶(-0.23)活性(P<0.001);或通过正向影响pH,进一步负向影响TN(-0.43)(P<0.001),进而对蔗糖酶(0.43)、脲酶(0.46)、多酚氧化酶(0.33)、葡萄糖苷酶(0.52)、蛋白酶(0.61)和纤维素酶(0.57)活性产生正向影响(P<0.001)。不同灌丛化梯度也可通过显著正向影响SOC(0.25)(P<0.01),进而影响多酚氧化酶活性(0.18)(P<0.01);或通过直接影响SOC,进一步正向影响TN(0.21)(P<0.05),进而对蔗糖酶、脲酶、葡萄糖苷酶、蛋白酶和纤维素酶活性产生影响。虽然灌丛化梯度不直接显著影响SWC(-0.09)(P>0.05),但SWC 仍是影响酶活性的主要因子,其可通过负向影响土壤pH(-0.52)(P<0.001)、正向影响SOC(0.29)(P<0.01)再影响TN,进而影响酶活性。不同灌丛化梯度主要影响SOC、pH 和SOC∶TN,对SWC 和TN 无显著影响。

图5 不同灌丛化梯度下各土壤性质与土壤酶结构方程模型分析Fig. 5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of soil physical and chemical properties and enzyme activities of grassland with shrub encroachment gradients
3 讨论
3.1 不同灌丛化梯度对土壤性质的影响
草地灌丛化(shrub encroachment)作为一种全球性现象,改变了原有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18],且不同灌丛化梯度对土壤的影响不同,本研究结果表明:相比于未灌丛化草地,轻度和重度灌丛化影响下土壤理化性质及土壤酶(蔗糖酶、脲酶、葡萄糖苷酶、蛋白酶、纤维素酶和多酚氧化酶)活性差异较大(图1 和图2),且轻度灌丛化对土壤酶活性影响较大(图1)。总体上高山绣线菊、小叶锦鸡儿和金露梅3 种灌丛在轻度和重度梯度下SWC、pH、有机质及土壤酶活性变化特征基本一致,灌丛化(轻、重度)降低了土壤酶活性及SWC、TN 含量,增加了土壤SOC 含量,土壤pH 略微上升,但土壤仍呈微酸性(pH 5.5~6.5),且各指标均随土壤深度增加呈下降趋势(图3)。
土壤作为土壤酶发生作用的载体,其性质的变化对土壤酶活性影响明显。土壤酶是土壤中具有催化作用的一类蛋白类化合物,其来源主要为动植物残体、微生物代谢以及植物根系分泌物[23]。土壤酶活性高低调控着土壤碳氮循环,影响土壤养分周转和积累,催化土壤中各种有机、无机物质的转化,对土壤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起重要作用,同时其也是评价土壤质量的关键指标。本研究中3 种灌木灌丛化(轻、重度)草地浅层土壤蔗糖酶、脲酶、葡萄糖苷酶、蛋白酶和纤维素酶5 种水解酶活性均低于未灌丛化草地(图3),且随着土层加深各土壤酶活性差异不显著,这可能是灌木侵入改变了原有草原生态系统的平衡,草灌资源竞争差异导致[24],Liao 等[25]研究发现,草本凋落物比木本凋落物更适合作为微生物基质和土壤酶催化底物,且随着灌丛化梯度的加剧,使植被地下根系数量减少,土壤中凋落物及腐殖质减少,进而影响土壤微生物数量,降低土壤酶活性,导致土壤质量下降,影响土壤矿化速率[26],因此未灌丛化草地各土壤酶的活性高于灌丛化草地。
在本研究中,未灌丛化草地0~40 cm 土层土壤SWC 含量均高于轻度、重度灌丛化草地,可能是灌木侵入破坏了高寒草甸草地原有的复杂根系结构,且试验样地中,灌木侵入导致原草地形成空斑,使蒸发量上升、土壤保水性降低,从而降低了土壤SWC,同时水分作为影响酶反应的溶剂,3 种灌木在轻度、重度灌丛化条件下均不同程度降低了土壤酶(蔗糖酶、脲酶、葡萄糖苷酶、蛋白酶、纤维素酶和多酚氧化酶)活性;未灌丛化草地0~20 cm 土层土壤TN 含量均高于轻度、重度灌丛化草地,可能是因为试验样地垂穗披碱草等优势草本本身具有较高的氮含量,灌木侵入导致优势种被取代,地上生物量降低和凋落物成分改变[27],进而使TN 含量降低。同时脲酶作为土壤N素状况的表征因子,3 种灌丛在轻度和重度灌丛化影响下均不同程度降低了土壤脲酶活性,研究表明[28],土壤脲酶活性和土壤供氮能力呈正比,其活性降低将影响凋落物分解进程,减弱氮元素释放,不利于该地区氮素的积累。灌木侵入在改变植被类型的同时,地上、地下凋落物基质质量、种类及微环境也发生相应改变,而pH 作为影响酶活性的重要因素,pH 的轻微变化将对不同土壤酶活性产生影响,试验结果显示,对比未灌丛化草地,3 种灌丛化草地(轻、重度)土壤pH 均有所上升,但轻度、重度灌丛化样地之间差异不显著,且pH 变化和土壤SWC 变化密切相关,灌木侵入改变了原样地植被类型及土壤微环境,降低了土壤导水率、透水及透气性[29],使土壤pH 值略微上升,进而影响了土壤酶活性。
蔗糖酶作为评价土壤肥力水平的重要指标,轻度和重度灌丛化影响下土壤蔗糖酶活性降低,可表征灌丛侵入降低了该地区浅层土壤肥力,减弱了土壤碳循环效率,且轻度灌丛化对蔗糖酶活性影响更大。葡萄糖苷酶和纤维素酶可将大分子物质水解成植物易吸收的小分子物质,对土壤碳、氮循环具有重要作用,其活性降低也说明灌木侵入降低了原生态系统碳氮循环效能。蛋白酶与土壤有机碳、有机氮含量显著正相关,其活性降低说明灌木侵入不利于该地区土壤蛋白质水解和转化,将减缓土壤有机碳、有机氮含量的积累,但本试验结果显示,轻度和重度灌丛化均显著增加了土壤SOC 含量,而土壤蛋白酶活性仍呈减弱趋势,可能是其他环境因子占主导,如TN 及SWC等。多酚氧化酶活性和灌丛化梯度无显著相关性,可能是影响多酚氧化酶活性的其他环境因子占主导地位,如温度和氧气[30],郝建朝等[31]研究发现,氧气充足的条件下多酚氧化酶活性是缺氧条件下的1.6 倍,其在45 ℃时活性最高,且多酚氧化酶在pH 为4~7 时活性变化不明显。由于本试验样地的特殊性,样地的高含水率可能导致土壤氧气含量达不到多酚氧化酶的最适需氧条件,且试验地年均温1.4 ℃,昼夜温差较大,土壤温度达不到其最适酶活温度,且本试验结果显示,各样地各土层pH 值5~6,pH 值对多酚氧化酶活性影响不显著(P>0.05),印证了郝建朝等[31]的研究结论。多酚氧化酶活性的结果表明,在宏观尺度上,灌丛化对该研究区土层温度、氧气含量影响较弱。蔗糖酶、脲酶、葡萄糖苷酶、蛋白酶和纤维素酶活性随土层深度增加而递减,可能是因为表层土壤具有较高的外源性碳输入,如植物凋落物、根系分泌物等[32],试验结果也显示,不同梯度灌木侵入显著增加了土壤表层SOC 含量,这可能与本试验中的灌丛均为落叶灌木有关,其叶片凋落物向灌丛斑块下输入大量的有机质,使得灌丛下方土壤SOC 含量升高[33]。且表层较高的氧气及水热条件更适宜微生物繁殖,微生物活性显著高于深层[8],其与土壤酶活性具有极强的耦合,存在正向反馈,微生物进行代谢分泌胞外酶分解低质量凋落物(高木质素含量),通过外修饰作用,将较大体积的凋落物或动物残体分解,释放更多的土壤酶,因此灌丛和草地表层以及浅层土壤酶活性高于深层。蔗糖酶、脲酶、多酚氧化酶、葡萄糖苷酶、蛋白酶和纤维素酶活性在重度灌丛化梯度下各土层内高于轻度灌丛化,随着pH 升高土壤酶活性受到显著影响,但多酚氧化酶活性在轻度灌丛化和重度灌丛化各个土层变化不显著,整体来看土壤酶在轻度和重度灌丛化都呈随着土层深度加深活性降低的趋势,该结果与哈文秀等[34]的研究结果相似。蔗糖酶、葡萄糖苷酶和纤维素酶都参与土壤有机质的转化过程,在碳循环中起着重要作用,其活性受到土壤微生物、有机质的影响,酶活性的变化可预示着土壤中有机质的变化。
3.2 不同灌丛化梯度土壤酶活性影响因子分析
草地向不同灌丛转化的过程中,土壤理化性质和土壤酶活性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本研究RDA 分析结果表明(图4),各环境因子对土壤酶活性在不同土层中解释度不一致,但主要解释因子均为SWC,SEM 分析(图5)进一步探究不同灌丛化梯度下土壤理化性质和土壤酶活性之间的作用关系,结果和RDA 分析一致,SWC 是影响酶活性的重要因子,这和前人的研究结果一致[35-36],其可通过直接影响土壤酶活性,或间接影响pH、SOC 和TN,进而影响土壤酶活性。这可能和采样地的特殊性相关,青藏高原高寒草甸区根系分布主要集中在0~30 cm 土层,根系分布层强烈影响着SWC 含量[37],灌丛入侵改变了原有草原生态系统根系的空间分布,进而改变SWC 分布格局,影响了土壤酶活性。灌木侵入显著影响土壤pH(图5),pH 显著影响土壤碳循环,本研究表明(图5),葡萄糖苷酶、蛋白酶和纤维素酶活性和pH 值显著负相关,可能是植物凋落物分解产生大量CO2引起的土壤酸化增加了土壤中C、N 等营养元素的含量,提高了土壤微生物活性,进而促进了土壤酶活性的升高[38]。但对蔗糖酶、脲酶和多酚氧化酶活性影响不显著,可能是不同灌丛化梯度下各参与土壤碳氮循环的土壤酶之间协同关系存在差异[39],故部分土壤酶活性差异不显著。同时,SOC[40]和TN[41]也是影响土壤酶活性的重要因子,可能是灌木侵入引起的土壤外源有机质的改变,会显著影响土壤微生物效应[42],外源有机质的分解和转化需要土壤微生物和土壤酶的协同作用,而土壤微生物是影响土壤SOC 和TN 含量的重要因子,故SOC、TN 和土壤酶活性显著相关。
4 结论
高寒草地灌丛化改变了土壤性质及土壤酶活性,灌丛化显著提高土壤表层pH 和SOC 含量,显著降低SWC和TN 含量(P<0.05),不同灌丛化梯度下土壤酶活性总体随土层加深而递减。蔗糖酶、脲酶、葡萄糖苷酶、蛋白酶和纤维素酶在表层土壤活性低于未灌丛化草地,活性降低表明灌丛侵入对该地区碳循环产生消极影响。蛋白酶与脲酶活性的降低会对氮循环产生消极影响。同时,SWC 是影响该地区土壤酶活性的主要因子,其可通过直接影响土壤酶活性,或间接影响pH、SOC 和TN,进而影响土壤酶活性。综上,酶活性可作为该区域土壤碳氮循环指示指标,与土层深度、SWC 和SOC 等环境因素有关。故本研究表明,灌丛化梯度不断加大,会显著降低该地区土壤酶活性,可能对土壤物质循环产生一定的负向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