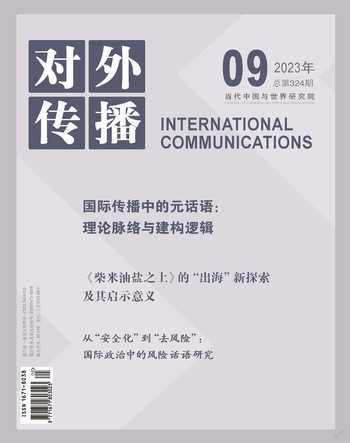“和合”文化观与中国国际传播元话语的构建
常江 狄丰琳
【内容提要】国际传播在本质上是不同传播主体所奉行的话语体系的建设与竞争。“元话语”作为一切话语生产与传播实践的基础观念,可以成为我们理解全球信息与文化传播格局、探索本国国际传播实践突围路径的认知出发点。元话语不仅是语言、表达和叙事,更是为各种类型的交流实践提供规则的结构性思维和文化泛型。中国的国际传播实践所奉行的“和合”元话语反对“中心-边缘”话语秩序,强调不同传播主体的道义责任,并主张维系一个动态均衡的世界体系。充分发扬“和合”元话语在国际传播中的潜能,须遵循两个基本策略:不断将抽象的文化理念转化为可为全球受众理解和共情的流行叙事项目;充分利用全球传播技术革新的前沿成果以建立数字信息生态下的先发话语优势。
【关键词】元话语 国际传播 和合 西方中心主义
一、引言
过去70余年间,中国的国际传播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走出了一条独立发展的道路。因应国际政治与文化环境的变化,国家于不同时期提出“一国一策”“因国施策”“全媒体格局”等全球传播战略,体现了务实的态度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然而,由于历史积因和政治偏见等结构性因素的长期存在,中国的国际传播事业在可预见的相当长的时间里仍将面临来自欧美国家的挑战。
从传播渠道来看,在国际舆论场上,无论是具有悠久历史和良好品牌认知度的传统媒体,还是广泛采纳前沿技术的新型数字媒体,欧美国家均占据竞争优势。在知名品牌价值评估机构GYbrand编制的2023年度“世界品牌500强”中,英国天空广播公司(Sky)、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和美国广播公司(ABC)等英美老牌媒体机构仍名列前茅。互联网调查公司DataReportal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全世界活跃用户数量排名前五的社交媒体平台分别是脸书、优兔、WhatsApp、照片墙和微信,其中有四个为美国高科技公司所有,而在这之中数字科技巨头Meta就拥有三个。①统计数据固然不能说明全部问题,却可以提示我们问题所在:国际舆论环境格局“西强东弱”态势依旧;自西向东的国际信息流动方向,以及西方新老媒体把持着国际舆论话语权的情况仍未改变。②经济实力的强大会重塑文化和传播领域的权力格局,但这一过程的实现或许会比我们想象得更为缓慢,且需要实践者不断进行科学的策略规划和行动设计。
渠道的固化令国际传播内容生态的革新变得更加困难。在诸多涉华关键议题和关键事件中,欧美媒体仍据有显著的话语优势。除去个人能力和文化鸿沟等客观因素,一些有影响力的欧美媒体机构及其从业者在政治上的偏见和傲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更有甚者,长期存在于国际舆论场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刻板观念在由欧美平台所主导的全球数字沟通网络中得到强化。这些平台出于驱动流量、追求利润的目标而大多采取同质化信息过载策略“包裹”其用户,固化而非弥合原有的观念分歧,制造信息茧房和舆论极化,并从仇恨言论中获益。③在国际传播的内容生态中实现中国概念和中国故事的顺畅流通,与全球媒体受众(用户)建立理性和建设性的对话机制,在世界范围内为中国文明与文化赢得真正意义上的尊重,仍有大量工作有待完成。
传播在实践层面体现为渠道和内容的问题,而在观念层面则是一个话语、话语权和话语体系建设的问题。话语不是在真空形成的,而是在日常传播实践中被塑造和凝炼而成的,它同时受到社会规范、价值观和权力的引导。不同的行动和理念要素在实践中不断互动并建立结晶化的关系,就会不断培育具有合法性和流通性的传播策略和表述方法。④在国际传播场域,无论渠道竞争还是内容竞争,起决定性作用的始终是隐于历史和权力关系中的话语结构。换言之,我们可以认为欧美媒体对中国形象的“操演”在实践中体现为渠道和内容范畴的一系列行动,但这些行动的“成功”与否,或是否能够获得“认可”,则由国际舆论场的话语结构所决定。因此,在国际传播中,话语和话语权问题有着最高的优先级,从根本上解决国际传播“西强东弱”的问题也应从话语体系的构建入手。
本文尝试以“元话语”(metadiscourse)为基本概念框架和理论工具,对当下国际传播场域“西方中心主义”(Eurocentrism)意识形态的生成逻辑和传播方式进行分析,并基于反思和批判的思维,深入本土丰厚的历史和文化资源,探讨中国现行国际传播元话语建设应当采纳的策略。本文期望通过这样的观念探讨,为更具文化影响力、更符合文明互鉴原则、更符合人类命运共同体设想的国际信息传播新秩序的建设提供支持。
二、什么是元话语
元话语的概念最初由语言学家泽里格·哈里斯(Zellig Harris)提出,作为对既往话语理论的一种反思和修正。在哈里斯看来,话语不仅体现为命题性和说明性的文本,更具有组织文本并促使特定受众准确理解文本的功能。因此,元话语不仅是语言、表达和叙事,更是为各种类型的交流实践提供规则的结构性思维和文化泛型,天然具有跨文化(cross-cultural)、跨传播语境(cross communicative contexts)的属性。⑤质言之,一般意义上的话语主要用于生成文本和传递意义,但元话语则关注文本之外的历史和社会世界,在文本和人之间建立关联,并为既有的具体话语提供表述结构和合法性依据,是“关于话语的话语”。⑥在日常传播实践中,元话语具象化为通过结构化思维建立起来的有理有据的话语表达体系,以及逻辑严谨、条理清晰、符合交流对象诉求并準确传达传播者态度的话语结构。但在观念层面,我们要看到元话语这一概念所承载的更为复杂的内涵:它既关乎我们在传播中具体应当说什么,也关乎我们如何说以及以怎样的方式令我们所言说之物具有公认的合法性。
在国际传播领域,对元话语的构建意味着三方面的努力:第一,为所有具体的话语表达提供一种文化上的“模板”或“母题”,即我们所生产的内容和生发的观点应当具有某种深层的历史逻辑一致性。例如,欧美主流媒体就将西方启蒙主义意义上的“平等”和“人权”等概念作为自己一切话语表达的“模板”或“母题”,并通过对其反复的阐释和递归不断申明自身传播活动的合法性;第二,话语表达活动要致力于构建良性的传受关系,这意味着传播者必须要考虑到接受者多样而细腻的文化意图,并致力于在双方交流关系和更宏观的历史、社会语境之间建立联系。在数字时代,这种良性传受关系的形成显然应当体现为一种协同性意义生产体系,意即传播者须在通过话语生成意义的过程中与目标受众进行充分的协商;第三,基于上述“模板”或“母题”,以及持续构建中的良性传受关系,动态性地建设具体的话语表述规则,包括关涉当下国际传播场域重大和关键议程的媒介叙事、语篇规则和表达技巧。在具体操作中,这项工作可体现为被绝大多数国际新闻传播从业者所共同遵守的专业守则或语言规范。
元话语的概念和理论对于我们从语言和文化的视角理解国际传播的本质有显著的启发意义——它不仅可以为日常性的具体传播活动提供指引,而且可以揭示隐匿于话语背后的认知图示、政治意图和主体间性。只有从元话语的概念出发,我们才能跳出将传播视为“信息、商品或服务的交换”的功能主义观点,从而深入到传播主体的文化背景、态度与个性、意识形态认同等范畴,挖掘当下国际传播不平等格局的深层症结。⑦在某种意义上,中国与欧美国家在国际传播场域的复杂关系的本质,就是两种传播体系所依托的元话语之间的本质矛盾;而我们对于有效而和谐的中国国际传播实践方案的设想,也要建立在对上述元话语矛盾的剖析和阐释的基础上。
接下来,我们就基于上述思考,探讨“西方中心主义”作为支配欧美主流国际传播实践的元话语,与中国国际传播“和合”元话语之间的关系、冲突与调和之道。
三、元话语的矛盾:“西方中心主义”与“和合”
中国和欧美世界在国际传播中的冲突的根源,存在于两种文化的基因之中。在西方,这种基因是衍生自二元论古典哲学的“西方中心主义”;在中国,这种基因则是长期存在于儒家伦理价值体系中的“和合观”。前者强调主体与客体之间不可调和的关系,以及主体对客体进行界定、操演和征服的行动意图;后者则主张在日常生活中动态调试不同行动者之间的关系,维系一种建立在协商和秩序基础上的稳定结构,追求社会的平缓演进。⑧
衍生自二元论哲学的“西方中心主义”元话语,是欧美国家国际传播实践中遵循的文明冲突论话语框架的文化内核,这一框架强调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和矛盾的不可调和性。基于这一框架,欧美文化建制和主流媒体对非西方文化的理解和再现体现出了鲜明的操演性特征:异于西方的事物、制度和思维方式往往被简单贴上“落后”或“反动”的标签,而非西方社会在欧美国际传播话语体系中所承载的感情色彩往往由其现状在多大程度上与西方接近所决定。一项关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对中国和印度两国形象呈现的差异化策略的研究印证了这一点。⑩
而从“和合”文化观出发,中国的国际传播实践则更多强调合作与共赢,且体现出因时而异的辩证性。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国际传播和对外宣传方针因国际关系格局、中国自身的发展需要和中国文化观念的影响而进行了多次调整。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寻求建立一种既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又开放务实的动态国际传播策略,即“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⑨从“和合”的元话语出发,中国的国际传播实践衍生出一系列具体的话语结构和文化泛型,包括:“立己达人”“求同存异”“合作共赢”“多边主义”“睦邻、安邻、富邻”“人类命运共同体”“丝绸之路经济带”“人类安全共同体”“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等等。这些差异化表达尽管皆是因应不同时期的外交方针提出,但其始终紧扣“和合”的观念内核。
从中国本土文化主体性立场出发,我们可以认为基于“和合”文化观的中国国际传播元话语体系更多是历史的、辩证的和战略性的,它所致力于建设的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人类文明交流机制。而“西方中心主义”的欧美国家国际传播元话语则体现为更直接的行动方案和操作指南,往往针对的是具体的议题和诉求,却时常忽视文化差异的历史性。两种截然不同的世界观衍生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方法论,并在实践层面体现为国际传播场域的纷争和国际信息秩序的不平等。对此,我们应当有深刻的认识,并不断从问题的根源入手探索解决路径。
四、基于元话语的国际传播叙事逻辑
“西方中心主义”与“和合”两种元话语在文化政治意义上的差异在叙事领域得到最集中的体现。由于“讲故事”是话语生产知识和权力关系最重要的方式,因此不同元话语体系在效能上的差别就体现在它们以什么逻辑叙事,以及它们所主张的叙事策略与方法在多大程度上为受众所接受。⑩故而,对于中国和欧美国家国际传播叙事逻辑的比较,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两种元话语之间的矛盾是如何在日常实践中被持续再生产和维系的。
(一)国与国的关系
在对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构想上,“西方中心主义”元话语倾向于将国際社会存在的诸种分歧和冲突的根源解释为文化上的冲突,且这种冲突几乎是不可调和的。整个世界是一个遵循零和博弈法则的话语战场,一种文化的兴盛必然意味着其他文化的衰落。因此,在有学者看来,不同文明间的“断层线”(fault lines),亦即包括西方文明、中华儒家文明和拉丁美洲文明在内的不同文明在观念和话语上的交汇点,就是全球话语纷争的主战场。11在这个意义上,对于“西方中心主义”的信奉者来说,国际传播活动本身就是西方和非西方世界争夺权力、影响力以及文化和宗教霸权战争的一部分,它几乎没有自己独立的形式和规律。12在这一元话语体系的支配下,欧美国家的国际传播活动时常体现出对某些既有的固化叙事要素的重复,比如强调新兴国家与传统国际霸主之间矛盾不可调和的“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叙事框架,以及各种类型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表述方式。
而对于奉行“和合”文化观的传播主体来说,长期主导国际传播格局的“中心-边缘”话语秩序不仅是错误的,而且也不具备道德上的合法性。从儒家伦理的原型出发,一种理想的国际传播生态与一个和谐的大家族的内部生态具有某种同构性:一方面,据有不同历史和道德角色的国家应当履行自己的天然责任,从而实现这一生态下所有行动者各司其职、各安其事,同时保持距离并相互尊重的动态平衡关系;另一方面,在国际传播的场域中,尽管不可避免存在力量差异和微观权力关系,但所有行动者也都奉行着一套朴素的道德原则。这种道德原则在中国的国际传播话语体系中体现为“风雨同舟”“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等观念和口号,其目标即在于建立一种适用于所有行动者的自我约束机制,时刻保持对可能出现的弱肉强食局面的警惕。从理性角度看,“和合”的国际传播叙事显然更具观念和道德上的优势,但这种叙事也面临着一个巨大的接受障碍:抽象性。无论出于历史还是跨文化的原因,目前对于中国的媒体和国际传播实践者来说,如何将“和合”的中国观念转化为全球受众听得懂、理解得了的故事——无论新闻故事还是影视故事,仍处在艰难的探索之中。近年来,随着电影《流浪地球》这样基于“和合”元话语完成的叙事作品在国际传播中取得的成绩,代表着中国实践者在这一问题上的可贵探索,其中第一部甚至在相当程度上得到了欧美主流评论界的认可。13
(二)本国与世界的关系
在关于本国与世界关系的阐释上,“西方中心主义”元话语所派生出来的是一种去语境化和非历史化的“普世价值”话语体系,这套话语体系宣扬一系列在形式上具有人类社会普遍适用性的概念和理想,但却回避这些概念和理想在不同文化土壤中可能拥有不同内涵的现实。因此,日裔哲学家有坂阳子主张,只有将欧美价值观中的“普世主义”(universalism)置于后殖民批评的框架中加以理解,我们才能更为客观地看待“东方与西方的关系”。14在国际传播实践中,时常能够看到欧美传播主体对诸如自由、人权等概念的使用,与其特定时期的国家利益和外交方针之间存在着互为犄角的关系:在当下适用于某一国的描述和叙事,在未来的某个时间也许会变得不再适用。而这种转化不但缺少充分的现实依据,而且在标准上存在多重性和模糊性。例如,一项对于1975-2010年间美国媒体的国际新闻报道取向和美国对外援助状况的关联性分析就发现,那些接受美国援助并被其纳入自身文化想象范畴的国家往往具有更多和更正面的媒体曝光度,而这些国家的制度在“西方标准”体系下看往往存在巨大的差异。15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基于“西方中心主义”元话语形成的本国与世界关系的叙事体现出高度的挥发性和易变性,其标准会因外交政策的局面而陡然转变,而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传播与信息秩序则迫使绝大多数国家服膺这一关系格局。
而从“和合”文化观出发,任何国家都是一个动态均衡的世界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不同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不但可以、而且也应该努力做到和而不同。由于“和合”的元话语是以“关系”为中心描述和界定外部世界的,因此它会倾向于以更具包容度和共情力的视角来看待共同构成这一世界的不同传播主体之间的互动。受中华传统文化普遍性道德标准的影响,符合“和合”文化理想的国际传播活动应当充分尊重不同国家和社会基于其历史形成的独特性,并在日常实践中竭力避免将动态过程静态化、对复杂问题简单化,其本质仍是中国传统哲学朴素的身心合一论:既然“身”和“心”不是彼此分离的两个实体,那么由“心”(观念)所支配的“身”(行动)就必然要时刻受到道德、修养乃至艺术的约束。16由于一切观念和行动之间的组合关系都是客观存在并有其历史和文化合理性的,因此也就不存在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统一标准。据此,不同文明之间彼此交流、相互再现的活动均须遵循“最大公约数”和“最小伤害”两项原则展开。不过,“和合”的文化理想也有可能产生一个潜在的问题,那就是在对均衡与和谐关系的追求中失去对自身主体性的确认。因此,在认同“和合”作为国际传播元话语的合理性的前提下,一切实践活动都应建立在费孝通所强调的文化自觉(cultural consciousness)的基础上:“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要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17
五、结论:构建中国国际传播元话语体系的策略
话语不仅是表达、叙事和价值观的播撒,更是社会实践的再语境化(recontextualization)。18构建中国国际传播的元话语体系是一项关联中国文化传统、道德原则、现实情境和愿景规划的复杂系统工程,而中国的国际传播实践长期以来奉行的“和合”文化观为我们在当下反思既有传播理念、优化未来传播实践提供了有价值的启发。基于此,本文认为在如今这个技术环境持续动荡、全球舆论结构日趋极化、东西方价值观冲突日益凸显的时代,构建中国国际传播的元话语体系应遵循两个基本策略。
第一,通过系统的理念整合与细密的操作设计,将抽象的“和合”元话语转化为一系列可为全球受众理解和共情的流行叙事项目,进而实现对抽象观念的具象化,将中国和欧美文化间宏觀的“世界观之争”转化成微观、可控的“讲故事之争”。事实上,一切元话语体系只有被转化成具体可感的“讲故事”的实践,方能产生实际意义上的传播效果。因为人只能与具体的故事互动,而无法与抽象的观念互动。“西方中心主义”元话语在国际传播场域形成的历史优势,首要是其衍生故事并借助故事向受众灌输价值观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是在好莱坞、英国广播公司(BBC)、美剧和流行纪录片成熟的大众叙事体系中获得的。所以,讲好中国故事并不只是一句动员口号,更应当成为一套可“落地”的行动指南。
第二,充分利用全球传播技术革新的前沿成果,在传统媒介渠道和内容样态数字化,以及整个传播系统的智能化方面加大投入,努力以更新锐的技术创新挑战或绕开欧美主流媒体在现代新闻与大众传媒领域形成的话语优势,19建立数字媒体生态下的自主话语体系。对于一切有着明确利益诉求的传播实践来说,元话语应当是稳健、甚至是稳定的,但它在生产和流通中的形式却应当保持与时俱进。须知,数字媒体和人工智能在国际传播中的应用,不仅体现了一种技术进步,更是在构建新型的社会关系,20在这一新的关系网络中,所有国家都是“新选手”。而摆脱了历史和结构负担的“和合”元话语,完全可以利用中国相对的先发技术优势,实现与网络化的新型国际关系的有机融合。
人类社会的信息环境和国际社会的关系格局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变化,唯有于其中锚定那些不会改变、也不应改变的价值基石,中国的国际传播事业才能真正为全球文化与传播新秩序的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
常江系深圳大学传播学院教授、深圳大学媒体融合与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狄丰琳系深圳大学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注释」
①Dave, C., Global social media statistics research summary 2023, https://www. smartinsights.com/social-media-marketing/social-media-strategy/new-globalsocial-media-research/.
②姬德強:《“双重西方化”:中国外宣的困境与出路》,《青年记者》2021年第6期,第18-20页。
③Zhang, X., Ding, X., & Ma, L., The influences of information overload and social overload on intention to switch in social media, Behaviour & Information Technology, vol.41, no.2, 2022, pp.228-241.
④Carbaugh, D., Cultural discourse analysis: Communication practices and intercultural encounters,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vol.36, no.3, 2007, pp.167-182.
⑤Qin, W., & Uccilli, P., Metadiscourse: Variation across communicative contexts, Journal of Pragmatics, vol.139, no.1, 2019, pp.22-39.
⑥Crismore, A., Metadiscourse: What is it and how is it used in school and nonschool social science texts, Urbana-Champaig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1983.
⑦Hyland, K., Metadiscourse: Exploring interaction in writing, London: Continuum, 2005.
⑧Littlejohn, R., & Li, Q., Chinese and Western philosophy in dialogue, Educational Philosophy and Theory, vol.53, no.1, 2021, pp.10-20.
⑨黄斐:《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话语建构视阈下中国共产党的话语逻辑》,《理论月刊》2017年第11期,第116-121页。
⑩Hagstr?m, L., & Gustafsson, K., Narrative power: how storytelling shapes East Asia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Review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32, no.4, 2019, pp.387-406.
11Haynes, J., Donald Trump,“judeo-Christian values,” and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The Review of Faith &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15, no.3, 2017, pp.66-75.
12Huntington, S. P.,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fairs, vol.72, no.3, 1993, pp.22-49.
13Kenigsberg, B.,“The Wandering Earth” Review: Planetary disaster goes global, https://www.nytimes.com/2019/02/17/movies/the-wandering-earthreview.html.
14Arisaka, Y., Beyond “East and West”: Nishida’s Universalism and Postcolonial critique, The Review of Politics, vol.59, no.3, 1997, pp.541-560. Scott, J. M., Rowling, C. M., & Jones, T. M., Democratic Openings and
15Country Visibility: Media Attention and the Allocation of US Democracy Aid, 1975–2010,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vol.16, no.3, 2020, pp.373-396.
16张学智:《中国哲学中身心关系的几种形态》,《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第5-14页。
17费孝通:《文化自觉的思想来源与现实意义》,《文史哲》2003年第3期,第15-16、23页。
18Van Leeuwen, T., Discourse and practice: New tools for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19常江、罗雅琴:《人工智能时代的国际传播: 应用、趋势与反思》,《对外传播》2023年第4期,第27-31、53页。
20程曼丽:《多维建构“数字中国”国际传播话语体系》,《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年1月5日,第3版。
责编:谭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