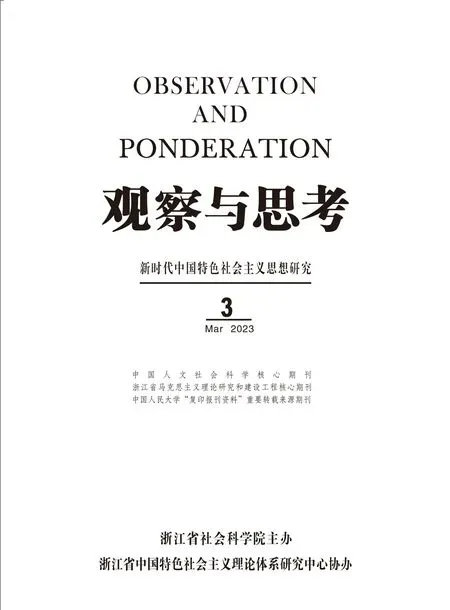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三重思想渊源
唐 晓 燕
提 要: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拥有三重思想渊源:一是法国唯物主义,二是德国古典哲学,三是英法德空想社会主义者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马克思沿用了特拉西的意识形态概念形式,但超越认识论维度,在存在论维度揭示意识形态从观念出发改变世界的空想性;德国古典哲学砥砺马克思实现对意识形态理解的存在论革命,并激发马克思在政治社会学视域、功能学维度赋予意识形态概念以现代涵义;19世纪上半叶英法德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展开的全方位的尖锐批判,为马克思展开自身意识形态批判的具体内容提供了历史材料和思想启迪。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史观中,“意识形态”是一个尤为重要的概念;在意识形态概念200 余年演进史中,马克思被公认为是提供了最丰富理论成果的思想家。①参见[英]米勒、[英]波格丹诺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69 页。通常认为法国唯物主义和德国古典哲学是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直接思想先驱,但如下两个方面思想资源的影响常被忽略:一是青年黑格尔派尤其是鲍威尔、施蒂纳的思想;二是19世纪上半叶英法德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展开的全方位批判。若充实这两方面思想资源,则法国唯物主义、德国古典哲学、英法德空想社会主义者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呈现为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三重思想渊源。
一、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法国唯物主义渊源:概念形式的沿用与内容的扬弃
意识形态概念具有复杂的演进历史。正如麦克里兰所言,尽管意识形态这个词本身是法国启蒙运动的直接产物,但就思想渊源而言,“这个概念却显然植根于有关意义和方向的一般的哲学问题之中”①[英]麦克里兰:《意识形态》,孔兆政、蒋龙翔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 页。。正是以培根为代表的近代英国经验论者勇敢地起来批判中世纪神学和经院哲学,积极探讨谬误之源,启发了法国启蒙学者对偏见的无情批判,最终由特拉西创制法语意识形态概念。
被马克思称为“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31、333 页。的培根在建立唯物主义经验论的过程中,悉心探究阻碍人类追求真理的重重困难和障碍,在《新工具》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四假象说”,将迄今为止蒙蔽人类智慧的假象区分为四种,即族类假象、洞穴假象、市场假象和剧场假象,初步揭示了谬误产生的思想根源和社会根源,开启了英国经验主义传统对谬误之源的探讨。霍布斯在《利维坦》一书中发挥了培根的“市场假象说”,列举了四种,滥用语言的形式,指出语言的滥用将导致错误的观念,倡导正确使用语词以求减少滥用情况的发生。③参见[英]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20 页。洛克的《人类理解论》是英国唯物主义经验论在观念来源和本质问题上的经典解答,其中的观点对于意识形态概念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针对当时流行的天赋观念论,洛克提出著名的白板说,指出人类理性和知识方面所有的一切材料“都是建立在经验上的,而且最后是导源于经验的”④[英]洛克:《人类理解论》,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74 页。唯物主义观点。洛克将观念产生偏差的根源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对观念尺度的误识,二是语言运用上的混乱。对于前者,洛克列举出观念运用存在“四种错误尺度”,与培根的“四假象说”有异曲同工之妙。对于后者,洛克延续了霍布斯对语言与观念关系问题的探讨,揭示观念紊乱背后语言文字本身的缺陷以及人们对语言文字的误用。《人类理解论》中对人类认识问题的探讨对于特拉西创制意识形态概念产生了直接影响。黑格尔注意到二者的内在关联,指出:“洛克这种对于复杂的观念的所谓分析以及对于这些观念的所谓解释,由于非常清楚明晰,曾受到普遍的欢迎……所以法国人特别采纳了这种说法,并加以进一步的发挥;他们所谓Idéologie(观念学)所包含的不外是这种东西。”⑤[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四卷),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151 页。
18世纪法国启蒙学者继承了英国唯物主义经验论者的传统,高扬理性的旗帜,对封建专制、宗教迷信、愚昧落后开启了无情批判。在这股批判的浪潮中,孔狄亚克、爱尔维修、霍尔巴赫三位学者共同持有的感觉主义立场、对传统偏见的批判与揭露是特拉西意识形态概念的直接思想来源。孔狄亚克将洛克的经验论引入法国,坚持以彻底的感觉主义立场来批判当时盛行于欧洲大陆的形而上学独断论体系,指出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马勒伯朗士等哲学家所进行的脱离了感觉的抽象思辨都只是偏见。孔狄亚克的思想对他的学生特拉西创制“意识形态”概念产生了重要影响,特拉西甚至将他奉为观念学的真正作者。在马克思看来,“爱尔维修同样也是以洛克的学说为出发点的,在他那里唯物主义获得了真正法国的性质”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31、333 页。。爱尔维修把唯物主义运用到社会生活方面,深入利益层面探讨偏见的来源,提出了“精神界就是不折不扣地服从利益的规律的”⑦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460 页。等著名论断。他认为,在不同的利益诉求的驱动下,人们对相同事物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思想观念,个人利益的狭隘性以及由此带来的立场的局限性使得偏见成为可能。霍尔巴赫在他被称为18世纪“唯物主义的圣经”的哲学著作《自然的体系》中,对封建宗教思想进行了无情的批判。霍尔巴赫将宗教产生的根源归结于无知,这种无知与极端落后的生产力、人在面对强大自然力量时的孤立无助密切相关,对宗教根源的披露深入到社会经济层面。
1796年,特拉西创制了意识形态法语词“Idéologie”,用来指称“观念的科学”,以研究认识的起源、界限、可靠性程度为对象。特拉西秉承了彻底感觉论的立场,认为我们无法认识事物本身,只能认识对事物的感知所形成的观念,任何无法还原为感觉的知识存在必定是谬误或偏见。“观念的科学”的建立旨在通过包罗万象的还原,为一切科学知识提供坚实基础。然而,承载着启蒙运动理性旗帜的意识形态概念在拿破仑政权失败后被用作替罪羊,意识形态转而从揭露认识中的谬误和偏见的科学,转变为抽象和幻想观念的代名词。特拉西期望以“观念的科学”为依据,实现对从学校教育到社会制度的整体变革的设想,显然具有一定空想性。因此,马克思沿用了这一意识形态概念形式(德语词“Ideologie”),但承袭了对该词的贬义用法。在1837年3月2日写给马克思的信中,父亲亨利希·马克思使用了法语的意识形态概念。他写道:“谁研究过拿破仑的历史和他对意识形态这一荒谬之辞的理解,谁就可以心安理得地为拿破仑的垮台和普鲁士的胜利而欢呼。”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45 页。正是在这封信中,马克思第一次接触到法语的意识形态概念,信中对“意识形态”一词荒谬性的认识,影响了马克思对该词理解的最初定向——认识论视域内的批判定向。《博士论文》中,马克思首次在认识论层面使用贬义的意识形态概念,“我们的生活需要的不是意识形态和空洞的假设,而是我们要能够过恬静的生活”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36 页。,将“意识形态”与“空洞的假设”并列使用。必须指出的是,这一时期的马克思尚未把握揭示意识形态“借以和具体现实的本质发生有机联系的那种东西”③[法]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第一卷),刘丕坤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89 页。,而揭示意识形态与现实存在的内在联系正是马克思思想早期对于意识形态概念的核心贡献所在。易言之,承继意识形态概念认识论层面的贬义理解,其思维层次仍束缚于近代认识论哲学框架;踏上自身思想道路后,马克思不再满足在表层上、从认识论维度揭示意识形态的荒谬、空洞,而是追求从本质上、从存在论维度揭示意识形态从观念出发改变世界的空想性。这集中表现为,马克思批判德国小资产阶级哲学为“德意志意识形态”(Die Deutsche Ideologie)。这里的“意识形态”(Ideologie)的本质内涵是唯心主义的。
综上,虽然特拉西创制了法语的意识形态概念,但马克思仅仅沿用了这一概念形式,这一概念的“观念的科学”的内容因名实不符而被抛弃。马克思致力于完成对意识形态理解的存在论革命,在这一视域内,意识形态概念的重心不在于意识本身的真假,而在于它是社会存在的观念反应;不是“意识”,而是“存在”,才是意识形态研究应予以关注的重心。正如户坂润所指出的,“意识形态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是观念乃至意识的问题”④[日]户坂润:《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郭莉译,长春:长春出版社,2021年版,第4、11 页。,而“意识问题……从观念论乃至个人主义的角度出发,是无解的。只有把意识问题当作非意识的问题,将其作为从属于历史性社会的问题,才能得到正确合理的解决”⑤[日]户坂润:《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郭莉译,长春:长春出版社,2021年版,第4、11 页。。由此可见,若诉诸历史来解释,后人之所以对意识形态概念如雾里看花、尤其容易陷入意识形态真假之辩,部分地归咎于意识形态概念形成之初形式与内容相分离这颇具戏剧性的一幕。
二、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德国古典哲学渊源:存在论革命的砥砺与现代涵义的启发
法国唯物主义和德国古典哲学对于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生成有着截然不同的影响。特拉西创制了法语的意识形态概念,但马克思仅仅沿用了其概念形式,扬弃了其概念内涵“观念的科学”,指认“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的本质内涵为“唯心主义”。之所以能实现这样的扬弃,是因为青年黑格尔派哲学及宗教批判思想的砥砺。在完成意识形态理解的存在论革命后,马克思开始在新的理论地平即唯物史观基础上审视意识形态,赋予意识形态概念以现代涵义——“统治阶级的思想”。这种对意识形态理解从哲学视域向政治社会学视域的转换,思想因子可以追溯到黑格尔的教化与异化思想。
(一)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砥砺马克思实现意识形态理解的存在论革命
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理解的存在论革命的实现经历了艰难、复杂的思想转变过程,核心线索正是对青年黑格尔派哲学及宗教批判思想的吸收—批判—扬弃。
1837—1841年间,青年黑格尔派领军人物、马克思的老师——鲍威尔的思想给予马克思以深刻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体现为理论范畴的沿用,也体现为思维模式、语言习惯方面潜移默化的影响。鲍威尔认为,宗教源于自我意识的自我异化,是人类加诸自身的精神枷锁。为了消除这种自我意识的自我异化,鲍威尔诉之于“批判”,掀起对人的自我意识的革命以扬弃异化,实现“自由”(自我意识复归自身)。“自我意识—异化—批判—自由”,是鲍威尔自我意识哲学的逻辑结构和基本内容。①参见孙伯鍨:《探索者道路的探索——青年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43 页。就文本而言,不仅马克思在自身思想起点——《博士论文》中持有的自我意识立场承袭自鲍威尔,在该文中马克思宣称自我意识具有最高的神性,“不应该有任何神同人的自我意识相并列”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 页。,而且此后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论犹太人问题》中的思维习惯、表述方式甚至所用范畴都有鲍威尔的影子。但长期以来,人们对鲍威尔的理解是通过《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镜像来进行的,这两部著作中马克思对鲍威尔不遗余力、完全彻底地批判,客观上遮蔽了马克思与鲍威尔的思想的传承关系。罗森意识到这一点,竭力扭转人们对二者思想关系的误解,大声疾呼“鲍威尔对马克思思想的形成所起的作用被人们不适当地低估了”③[波]罗森:《布鲁诺·鲍威尔和卡尔·马克思——鲍威尔对马克思思想的影响》,王谨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8 页。。
然而,当《莱茵报》时期马克思日益接触社会现实,以鲍威尔为核心人物的柏林“自由人”却沉湎于思辨哲学争论,思想分歧日益演化为思想冲突。针对柏林“自由人”空洞无物的宗教批判,马克思提出了“更多地在批判政治状况当中来批判宗教,而不是在宗教当中来批判政治状况”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十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4 页。的要求。与鲍威尔分道扬镳的马克思,开始借助于黑格尔理性主义国家观理解现实生活,却惊异地意识到黑格尔理性主义国家观与现实国家生活状况存在“应当”与“事实”的遥远对立与矛盾。此时,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进入马克思的视野。费尔巴哈认为,“只要经常将宾词当作主词,将主体当作客体和原则,就是说,只要将思辨哲学颠倒过来,就能得到毫无掩饰的、纯粹的、显明的真理”⑤《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荣震华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02 页。。费尔巴哈批判黑格尔思辨哲学的“颠倒”方法,被马克思所吸收并运用于批判黑格尔国家哲学。《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指出,在黑格尔国家哲学中,“观念变成了主体,而家庭和市民社会对国家的现实的关系被理解为观念的内在想像活动”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0、199、199 页。。虽然沿袭了费尔巴哈的方法,但马克思通过将这种颠倒追溯到颠倒的现实存在从而超越了费尔巴哈。从人本学唯物主义出发,费尔巴哈对于宗教进行了批判,认为宗教的起源与唯心主义的起源具有一致性,二者都源于对思维与存在内在关系的人为割裂。唯心主义将概念与其得以生成的物质基础割裂开来,概念被视为独立的实体;宗教的产生具有相似性,“人在宗教中将他自己的隐秘的本质对象化……上帝跟人的这种对立、分裂——这是宗教的起点——,乃是人跟他自己的本质的分裂”②[德]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荣震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67、349 页。。“神学之秘密是人本学,属神的本质之秘密,就是属人的本质。”③[德]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荣震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67、349 页。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批判继承费尔巴哈宗教批判思想,阐释了自己的宗教批判思想。在马克思看来,宗教“是还没有获得自身或已经再度丧失自身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0、199、199 页。,人依赖于宗教这种“颠倒的世界意识”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0、199、199 页。获得虚幻的安慰。一方面,作为颠倒的意识的宗教有其存续的现实社会土壤;另一方面,宗教是对颠倒的社会现实的精神补偿。对于宗教这种意识形态的社会存在根基及其社会功能的深刻认识,表明马克思已经把握到了意识形态概念内含的基本要素。
在考察马克思的思想发展时,过去惯常的做法是将费尔巴哈哲学视为历史唯物主义形成之前的最后一个环节,施蒂纳的“唯一者哲学”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麦克莱伦在《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一书中提及产生这种误解的根由。他指出:由于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将费尔巴哈放在施特劳斯、鲍威尔、施蒂纳之后叙述,给人一种错觉即按照时间顺序费尔巴哈是这些人中最后一个影响马克思的人。但费尔巴哈对青年黑格尔派的争论所写的最后一部重要著作,即《未来哲学原理》发表于1843年7月,而施蒂纳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出版于1844年末。⑥参见[英]麦克莱伦:《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夏威仪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41 页。更重要的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费尔巴哈”章之后的“圣麦克斯”章对施蒂纳展开了详尽的批判,这部分内容占到全书近十分之七的篇幅。究其实质,“施蒂纳才是青年黑格尔派中最后影响马克思的人”⑦刘森林:《为什么我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中不重视施蒂纳?》,《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 期。。正是对施蒂纳“唯一者哲学”这种极端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哲学理论的批判,标志着马克思对青年黑格尔运动理论发展批判的最后完成。“唯一者哲学”的诞生表明,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运动找不到从抽象思辨的理性王国走向感性存在的现实世界的正确道路,到了施蒂纳这里,黑格尔哲学体系极端发展的结果必然以“唯一者哲学”如此这般极端的方式呈现出来。然而,施蒂纳将“我”之外的所有思想体系视为意识形态加以批判和否定的方法,为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提供了启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将以青年黑格尔派为代表的思想体系统称为“意识形态”,并对自身以往的意识形态观进行清算,认为以往将意识形态批判局限于宗教批判的做法,缩小了意识形态批判的对象范围。同时,“施蒂纳对费尔巴哈的尖刻批判促进了马克思同费尔巴哈的彻底决裂”⑧侯才:《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发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5 页。。马克思扬弃了作为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核心及其宗教批判手段的“类”概念,指出青年黑格尔派无论从“自我意识”还是从“类”“唯一者”出发终将无法触摸到观念背后的社会现实,更无法本质上地改变现实,最终落入唯心主义窠臼。正是通过批判以青年黑格尔派哲学为代表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实现了意识形态理解的存在论革命,代表性论断为:“意识[das Bewuβtsein]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das bewuβteSein],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5 页。。理解“意识形态”的重心,根本不是“意识”,而是“存在”;意识形态批判的表层,是对诸种形态的意识的批判,深层是对诸种形态的意识以之作为现实前提的社会存在的批判。基于该种认识,马克思重新确立了意识形态批判的逻辑起点——现实的个人及其活动,将意识形态批判确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并由此打开了意识形态批判的广阔空间,意识形态批判不仅包含对宗教的批判,也包含对哲学、政治学、政治经济学等其他观念上层建筑的批判。
(二)黑格尔的教化和异化思想激发马克思赋予意识形态概念以现代涵义
当完成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批判,转而在唯物史观视域内理解、在整个社会结构中定位意识形态时,马克思开始使用另一个概念即Bewuβtseinsformen。必须指出的是,作为代表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核心观点的著述,《德意志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使用的意识形态概念不是同一个德文词,前者使用的是Ideologie,后者使用的是Bewuβtseinsformen;就词源而言,前者源自特拉西的“Idéologie”(直译为“意识形态”),后者源自黑格尔的“die Gestalten des Bewusstseins”(直译为“意识诸形态”)。②参见周民锋:《当代中国意识形态观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2-23、26 页。国内最早系统研究意识概念史的学者俞吾金清楚地指明了马克思离开哲学视域、转而在政治社会学视域内理解意识形态概念时,黑格尔对马克思的深刻影响表现在:“黑格尔几乎很少提到‘意识形态’这一概念,但《精神现象学》却对与社会历史发展相对应的各种意识形态作出了卓越的阐述,尤其是对异化了的现实世界的说明和对教化的虚假性的揭露,为‘意识形态’概念涵义的根本转折奠定了基础。”③俞吾金:《意识形态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 页。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的“意识诸形态”是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另一个词源。指出这一点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既然译成中文的“意识形态”概念有两个不同的词源,那么我们就“不能误以为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只是Ideologie,更不能只是从Ideologie 出发,而应从Bewuβtseinsformen 出发理解马克思的作为科学用语的‘意识形态’概念”④参见周民锋:《当代中国意识形态观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2-23、26 页。。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研究对象是意识诸种形态,精神现象学就是意识形态学。黑格尔在这里在广义上使用的意识形态概念——“意识诸形态”是马克思在一般意义上使用的总体意识形态概念、现代政治社会学概念——“统治阶级的思想”的来源。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将人的意识从最初的、最直接的感性阶段到最后的绝对知识阶段的发展道路划分为三个部分六个阶段。在第四阶段即精神阶段,黑格尔提出了著名的“教化(Bildung)”和“异化(Entfremdung)”思想。“精神”的发展又可被区分为“真实的精神,伦理”,“自我异化了的精神,教化”,“自我确定的精神,道德”三个阶段。“真实的精神,伦理”是个体意识与集体意识混为一体、尚未发生自我异化的第一阶段。“自我异化了的精神,教化”是精神彻底自我异化的阶段。所谓教化,就是个体从自然状态向自在存在状态过渡的手段,国家通过教化激发个体的“高贵的意识”,使个体致力于服从国家权力。个体在意识到教化的虚假性和欺骗性后,自我意识力图超越这种状态。启蒙是克服主客体对立、扬弃异化的开端,但启蒙并不能真正克服异化。在“自我确定的精神,道德”阶段,主客体统一依然无法真正实现,只有到了绝对知识阶段,精神才在概念中达到主客体的真正和解从而扬弃异化。
黑格尔的教化和异化思想立足政治社会学视域理解意识形态,赋予意识形态概念以现代功能学内涵,深刻揭露了意识形态得以运转的社会历史根源,给予马克思以深刻的思想启发。黑格尔的教化思想表明国家通过推动个体服从国家的思想统治体现自身思想型权力的必然性,异化思想表明个体在接受国家思想统治后意识从自然状态向自在状态转变的必然性。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肯定了这双重的必然性,尤其是国家彰显自身思想型权力的必然性,代表性论断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0-551 页。虽然《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并未明确以“统治阶级的思想”来指称意识形态,因为《德意志意识形态》的首要思想任务是批判“意识形态之个别”——“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唯心主义”本质进而确立唯物史观,但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意识形态的“观念上层建筑”的定位,可以推论出“统治阶级的思想”正是唯物史观视域内马克思对于“意识形态之总体”的内涵的理解。上述代表性论断清楚表明,进入政治社会学视域后,马克思将对“意识形态之总体”即一般意义上意识形态概念的理解与一定阶级的统治及其权力紧密联系在一起。从此,意识形态是否虚假降格为次要问题,因为意识形态是否虚假取决于统治阶级所处的发展阶段,在于统治阶级是否代表先进生产力要求与发展方向,由此决定掩盖自身特殊利益和赋予自身思想以普遍性形式的必要程度;升格为首要问题是:意识形态作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型权力,其思想引领、观念重塑、社会重构功能如何实现。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意识形态其实是什么这个问题,只能从意识形态的社会效力和社会职能中去理解”②[匈]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下卷),白锡堃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506 页。。
三、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空想社会主义批判思想渊源:意识形态全方位批判的思想材料
思想孕育于时代之中,体现时代的要求,也受制于时代的局限。马克思赋予意识形态概念以现代内涵 ——“统治阶级的思想”,这是他对一般、总体意识形态概念的理解。马克思提供了这一思想火花,但并未具体展开,他不可能超越他所属时代的要求提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概念,而这恰恰是列宁的思想使命。马克思立足他所处的时代,完成时代赋予他的使命——展开对资产阶级哲学、政治学、政治经济学意识形态的彻底批判。然而,马克思并非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第一人,而是他此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批判资源的继承者和扬弃者。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从资本主义国家诞生之时就已经开始,在19世纪初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充分展开后,集中体现为发展到高级阶段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所展开的,对资产阶级宗教、政治学、政治经济学意识形态全方位的批判。19世纪初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和傅立叶、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19世纪三四十年代德国空想社会主义者魏特林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对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但这一点以往“几乎被所有的意识形态论著忽略了”。①周宏:《理解与批判——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文本学研究》,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11 页。指出这一点非常重要,政治社会学视域内马克思使用意识形态概念的批判定向,正是指向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
19世纪初空想社会主义代表人物圣西门、傅立叶、欧文是以控诉资本主义制度、探求变革现存社会制度路径、设想未来理想社会蓝图为己任的先进思想家。马克思、恩格斯高度重视他们的著作的启发意义。恩格斯在1845年3月17日致马克思的信中,将这三位思想家的著作称为“能给德国人提供最多的材料和最接近我们原则的著作”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49 页。。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专门提到这三位思想家的体系,一方面指出其历史局限性——“是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还不发展的最初时期出现的”,“看到了阶级的对立”却“看不到无产阶级方面的任何历史主动性”,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31、432 页。对于未来社会的描绘还停留于幻想;另一方面肯定他们的著作“含有批判的成分”,“这些著作抨击现存社会的全部基础。因此,它们提供了启发工人觉悟的极为宝贵的材料”。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31、432 页。他们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宗教、政治学、政治经济学意识形态的批判,为马克思此后基于唯物史观展开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全面、彻底的批判提供了历史资源参照和思想启迪。
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被马克思、恩格斯誉为“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第一人。圣西门批判了传统宗教神学,对宗教根源的阐释和对宗教暂时性的理解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性,对宗教在阶级社会中功能的揭示更是触及了宗教的本质。圣西门认为,宗教根本不是如神学家所言是神的创造,而是由人发明的,是人掌握的科学知识不够充足、愚昧无知的必然结果。“当人们的知识已经大大超过代神立言的人的知识,并且能够揭露被尊为天书的书籍中的错误的时候,人们自然不会再信神启。”⑤《圣西门选集》(第一卷),王燕生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77 页。圣西门还指出,在封建社会宗教沦为僧侣阶级为有权势的阶层谋利而统治穷苦阶级的工具,揭示宗教在阶级社会异化为统治工具的本质。圣西门对宗教神学的批判为马克思此后开展的宗教批判提供了思想资源。
另一位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进行了精彩批判。通过将资产阶级的美好誓言与资本主义社会物质和精神的贫困现实相对照,傅立叶批判资产阶级“哲学家”(包括政治学家、道德学家、经济学家等)的一系列以“社会契约”“天赋人权”“博爱”“自由”为关键词的思想体系“与经验不相符合”,只是将幻想“当作规律”。他们所谓的“自由”是“为某个人的自私自利目的而牺牲群众利益的虚伪的自由”⑥⑦⑧ 《傅立叶选集》(第三卷),汪耀三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78、226、147 页。,所谓的“博爱”是“夺取两百万条人命的博爱”⑦,所谓的“社会契约”并不能给穷人以起码的生活资料与劳动机会,所谓的“天赋人权”不过是“在一般公认的自由、平等名称掩盖下的空话”⑧。他讽刺说,这些哲学家们脑中的思想“在他们的第一次实验——法国革命——中证明了自己的破产”⑨《傅立叶选集》(第一卷),汪耀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49 页。,从此以后大家就一致认为他们的学说是精神上的迷误。恩格斯认为,傅立叶对资本主义“现存的社会关系作了非常尖锐、非常机智和非常幽默的批判”①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20、358 页。,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之前能够进行这种批判的只有傅立叶一人。②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20、358 页。傅立叶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对于马克思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起到了良好的启发作用。尤其是傅立叶将文明制度称为“一切罪恶的渊薮”③《傅立叶选集》(第三卷),汪耀三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70 页。“颠倒世界”④《傅立叶选集》(第二卷),赵俊欣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10 页。的思想,已经触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颠倒特性。
这一时期,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运用自身的经济学理论,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说的种种谬论。欧文一针见血地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永远是相对抗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鼓吹的“个人利益”“个人自由”“自由竞争”等冠冕堂皇的原则,只不过是维护资产阶级在法律保护下自由追逐高额利润、剥削和压迫广大劳动人民的口号。实际情况是,一面是资本家获取越来越丰厚的利润、不劳而获、贪婪无度,一面是工人生产出愈来愈多的财富,得到的工资却日渐减少。针对这一现实状况,欧文质问道,工人们“除了外表以外,他们有没有任何方面可算是真正自由的工人呢?……他们除了挨饿的自由以外还有什么旁的路可走,或者说还有什么自由呢?”⑤《欧文选集》(第一卷),柯象峰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64 页。从而撕开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说的重重面纱,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相较于之前制度更为浓重的虚假性和欺骗性。欧文将私有制视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不平等、劳动群众忍饥挨饿的罪魁祸首,“私有财产是贫困以及由此而在全世界造成的无数罪行和灾难的唯一原因”⑥《欧文选集》(下卷),柯象峰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4 页。。马克思非常重视欧文的批判,认为欧文已经“推测出…文明世界的基本缺陷”,“对现代社会的现实基础进行了深刻的批判”。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0 页。
由于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直到19世纪三四十年代德国才产生了自己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魏特林的共产主义体系。魏特林的代表作《和谐与自由的保证》被马克思誉为德国工人“史无前例的光辉灿烂的处女作”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90 页。。马克思认为,作为工人阶级的代表,当魏特林用这部著作批判现存社会状况、指示出达到共产主义的必要路径的时候,正是表达了真实的、合规律性的“时代的需要”。在《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中,魏特林对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商业、金钱制度、拜物教进行了无情批判,其中对泛滥于资本主义社会的金钱拜物教的批判,尤其是正确地指称这一现象是对“虚假的偶像”的“崇拜”⑨[德]魏特林:《和谐与自由的保证》,孙则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120、107-108 页。,这种意识形态批判的深刻性远远超过了以往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并对马克思此后批判货币拜物教产生了重要的启发作用。魏特林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富者愈富,穷者愈穷,金钱成为富人维持这种不平等的工具,成为支配人们命运的力量。对金钱的崇拜与追求成为普遍现象,“统治人物、传教士、立法者、教师、法官、强盗、凶手、窃贼,一切的一切都向黄金伸出那贪得无厌的手,人人都相信他那现世的幸福必须在这里面找寻”⑩[德]魏特林:《和谐与自由的保证》,孙则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120、107-108 页。。魏特林历数了金钱拜物教影响下的种种社会罪恶:金钱使富裕手工业者的儿子变成商人,商人堕落为骗子,骗子变成游手好闲的懒汉,懒汉成为自私而狠心的吝啬鬼;金钱无止境地榨取劳动者的脂膏,吮吸劳动者的骨髓,使他们在贫困潦倒中死亡……魏特林对于金钱拜物教现象的批判相当尖锐,但仍属于“温情道德的和心理上的批判”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72 页。,并未能揭示金钱拜物教的本质,算不上“纯唯物主义”的批判。但这一批判思想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展开对商品、货币、资本拜物教的唯物主义批判提供了重要参照。
必须指出的是,上述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批判虽然机智而全面,但由于没能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找不到创造理想社会的阶级力量,最终他们改造旧制度的设想与呼吁沦为空想与口号。但不可否认他们提供的批判资源,特别是圣西门、傅立叶、欧文在资本主义制度胜利不久就洞察出了这个制度的几乎一切的弊病,为马克思提供了科学地研究与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的宝贵材料。
结语
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具有多重思想渊源,这不仅是因为意识形态概念具有复杂的演进历程,也因为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自身的变动性。法国唯物主义为马克思提供了意识形态概念形式,德国古典哲学砥砺马克思实现意识形态理解的存在论革命,并为意识形态概念从哲学视域跨入政治社会学视域提供了思想因子,英法德空想社会主义批判思想为马克思展开对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的彻底批判,提供了历史资源参照与思想启迪。
理解激发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生成的三重思想渊源,不仅有助于具体地、历史地理解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也有助于在当代中国语境下实现对于意识形态概念的科学理解和准确运用。
基于当代中国语境、站在马克思所奠定的思想地平上理解与运用意识形态概念,需要特别注意如下几点:其一,深刻理解马克思所实现的对于意识形态理解的存在论革命,由此紧紧结合意识形态赖以存续的“社会存在”来讨论意识形态,才能触及意识形态的本质。反之,若在认识论维度抽象地谈论“意识形态”的真假,则仍处于前马克思的、近代认识论的思维框架中。这种抽象的谈论,不仅意义非常有限,也容易使对具体意识形态的探讨误入歧途。其二,联系马克思所处的社会历史背景来理解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思想,不能将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尤其是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批判使用到其他社会意识形态之上,否则将犯以偏概全的错误。其三,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形而上学批判、意识形态批判、资本批判“三位一体”的全面批判。在“三位一体”的批判格局中理解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必须看到马克思不仅揭露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虚伪性,更揭示了其哲学根基——唯心主义和其社会根基——以资本运动为起点的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其四,虽然马克思并未提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概念,但他将一般意识形态视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定位为“观念上层建筑”的观点,为列宁基于新的时代要求创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概念提供了思想因子。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对于一般意识形态概念的界定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构理论的思想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