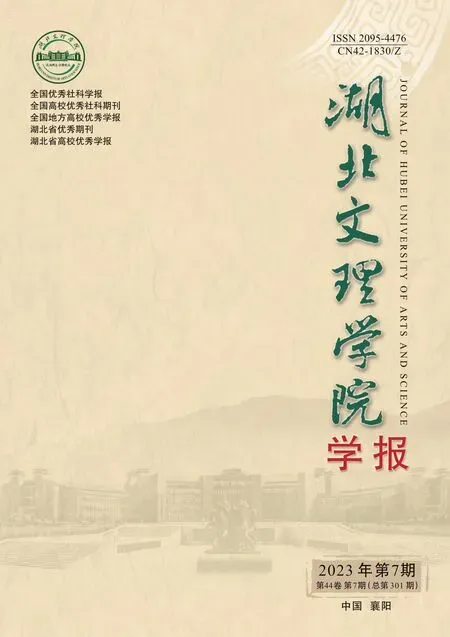比较诗学视域下《狼图腾》翻译中的诗学转换
车明明,刘云云
(西安理工大学 人文与外国语学院,陕西 西安 710054)
诗学(poetics)古老而常新,闪耀着千年光辉,被称为“世界上不多的几座理论金山之一”[1]32。诗学的范畴广泛,狭义上可指诗歌研究,广义上可指一切文学理论或文学批评。[2]比较诗学(comparative poetics)基于诗学发展而成,和诗学一脉相承。比较诗学是“从跨文化的角度对文学理论进行的比较研究”[3],旨在通过对比的研究方法,以平行互释的研究手段,建立中西文学与文化的“共同诗学”[4],形成通古达今、融通中西的思维框架,因而具有跨学科、跨文化的属性。翻译是跨文化的交际活动,故比较诗学所采取的跨文化研究思路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视野。
当代作家姜戎的长篇小说《狼图腾》[5]讲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内蒙古草原上牧民与草原狼之间的故事。小说场面宏大壮观,故事玄妙离奇,是一部关于我国少数民族生活的史诗般的“旷世奇书”[5]1。美国著名汉学翻译家葛浩文(Goldblatt, H.)的翻译成就斐然,在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方面功勋卓著,被喻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接生婆”[6],他的《狼图腾》译本[7]较为贴切地反映了原作的诗学特性,体现了其诗学价值。本文基于比较诗学理论对葛浩文的英译本进行研究。
一、比较诗学与翻译研究
(一)比较诗学的学理阐释
比较诗学是对“不同文化中的文学理论或批评的比较”[8],它与比较文学相伴相生。正如比较文学,比较诗学采取跨文化的互相比较和互相阐发的研究手段,在跨越的界域中阐述不同研究对象所具有的诗学特征,其着眼点在于求同存异之上的比较、参照和反思。比较的过程本着“和而不同”和“互识、互证、互补”的原则,化“对立”为“对谈”,化“交锋”为“交流”,尽可能地在参照性对话过程中开掘每一方的价值资源和言说问题的独特之处。[1]39中西语言与文化在思想体系上差异迥殊,而且,处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在对待事物的思维和认知上会存在鸿沟和藩篱,因而,比较诗学“必然会成为通向当代多元文学世界的入思和读解诠释的必然途径,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需求”[1]13。从本体构成来说,比较诗学包括“比较”和“诗学”两种要素,相应地,比较诗学便具有“可比性”和“诗学性”两大主要理论特性。
首先,在比较诗学框架内,不同文化之间思维不同,认知殊异,但亦不乏相通之处,正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这便构成了研究对象间的可比性。同时,比较诗学作为一种双向阐发的跨文化行为,其跨文化性也为文学研究的可比性奠定了基础,使得两种文化在跨域性对比和对话中使彼此得以互阐互释,实现了诗学上的融通互鉴。“比较”就意味着“两种声音一直在进行相互对话,它们彼此互识,同时在这种彼此互识中塑造着自己”[9],故比较的维度宽广,诸如比照、对照、互释、反思等,均可视为一种比较的方式。
其次,在比较诗学框架内,尊重不同文化,承认其诗学性和诗学价值,这是诗学研究的本体性认知。植根于尊重他者基础之上的诗学对比,是一个循序渐进、迁思回虑、鞭辟入里的认识和评鉴过程,这使得跨文化的诗学比鉴具有深刻的认知属性,这便是诗学认知(poetic cognition)的过程。诗学视野下的文学研究用诗学的思维方式思考和解决文学问题,聚焦文学的诗学性,是对文学的本质现象和社会历史等方面的系统研究,此为诗学思维和认知的本体论,亦为方法论。
概言之,比较诗学是基于文学可比性和诗学性两个层面对文学作品进行评鉴和批评,通过对异质文化、文论和文本的研究,达到认识和发现文学的一般诗学特性、规律和原则的最终目的。
(二)比较诗学视域下的翻译研究
文学作品所特有的文化特征和社会属性形成其诗学特性。在翻译过程中,这种诗学性要求译者站在诗学的高度,将研究对象纳入“诗学的轨道”,以便在译文中重构原文中不能言表的蕴意[10],这就是翻译的诗学认知和诗学转换(poetic transference)过程。换言之,鉴于文学作品独特的诗学特性,要完美再现原文的诗学特性和诗学价值,在翻译过程中首先需要进行诗学认知,然后需要进行合理有效的诗学转换。因此,在比较诗学框架下,翻译研究不仅着意于原文的语言特性和审美特性,更力求在翻译过程中充分再现文学作品的诗学功能,追求译文与原文的诗学对等,实现文本的诗学价值。
由是观之,比较诗学视域下的翻译研究“兼具诗学思辨的向度及认知的特性”[11],既具诗学性,又具认知性,故翻译的过程一方面需调用译者的诗学思维,同时有赖于其诗学认知。翻译的诗学性和认知性明晰了翻译的任务,那就是,译者需首先找寻和挖掘原作中的诗学特征和诗学价值,在尊重原文的条件下通过诗学转换,最终完成原作在翻译过程中的诗学再现。
综上,比较诗学框架下的翻译研究依赖于比较诗学的可比性,仰仗于诗学认知,从跨文化视域对文学作品的翻译进行研究,一方面探究文学作品的文学特性、文化内涵及诗学特性,一方面研探原文的诗学价值在译文中的再现,因而,比较诗学视域下的翻译研究包括诗学认知、诗学转换和诗学价值实现等不同环节。
二、《狼图腾》翻译中的诗学转换
《狼图腾》描述了内蒙古草原游牧民族的生活画面,呈现出我国少数民族文化的壮美、神奇和悠远,体现了中华文化大观园的神秘性、史学性和诗学性。本文就小说《狼图腾》翻译过程中的社会观念、价值取向、伦理道德等维度的诗学转换进行研究。
(一)社会观念层面的诗学转换
“社会观念”是指社会不同群体对整个社会的普遍认识,是社会群体的精神总和,它既包括具有独特逻辑和独特结构的表象,如形象、神话、观念等的体系,也包括没有经过理论的定性而形成的一定社会心理或者观念体系。作为意识形态的一种,社会观念是人的意识的一种观念化、模式化、程式化的呈现。葛浩文对《狼图腾》的翻译从意识形态方面产生了有意无意的操控,在社会观念层面形成了有效的诗学转换,呈现了原作的诗学精髓,展现了原作的历史性、现实性和诗学性品格。
例(1)一岁的狗会抓兔,一岁的狼会掏羊,一岁的小孩还在穿开裆裤。[5]64
A dog at one year can hunt rabbits, a wolf at that age can hunt sheep, and a one-year-old childis still in diapers.[7]107
“开裆裤”是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一种东西,小孩穿开裆裤,这是中国人长久以来的风俗习惯。在译文中,译者没有直译,而是根据自己的文化经验将其译为“尿片”(diapers),这是因为美国没有“开裆裤”这种东西,小孩都是用的尿片。葛浩文根据中西方不同的生活习惯对原文做了文化阐释,进行了对等的诗学转换,传播了中国的社会风俗和文化特色,使得译文更加符合目标语读者的认知,有利于读者理解语言背后真实的诗学含义。的确,译者作为翻译主体,享有翻译的自主行为和操作权力,因而“源语与译语之间不是一对一机械对应的关系”[12]36。
然而,比较诗学以开放、平等、互珍的视角对待不同文化,兼顾不同文化的诗学性,比较诗学视域下的翻译也因之是在尊重文化异质性前提下,以译介原语文化之异质性为目的的翻译。基于此思路,该例也可翻译为“in open crotch”,如此便可向域外读者译介“开裆裤”这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意象。根据上下文语境,目标语读者应该也不难理解这种翻译。
基于该例的分析,翻译的比较诗学视域认为,翻译应持有辩证的诗学对等观,它不过多垂青或贬损某种特定的翻译方法或翻译结果,而是采用辩证的视角,经过整体性的斟酌与选择,最终采取合宜的解决方法。该例的翻译若采取辩证的、开放的诗学转换思路和策略,则有利于很好地将中国文化的社会风俗和观念展现在目标语读者面前。
例(2)汉人不光是向游牧民族学了短衣马裤,骑马射箭,就是你们读书人说的胡服骑射。[5]61
You Chineselearned more from nomadic peoples than how to dress in short clothing, or how to use a bow and arrow on horseback, what you call “barbarianattire and horse archery”.[7]102
历史典故“胡服骑射”最早出现在《战国策·赵策二》,意指战国时期赵国武灵王为了国家强大推行胡服和骑马射箭的故事,表现出武灵王注重实用、勇于改革的形象。在中华文化历史中,“胡人”是中国古代对北方边地及西域各民族人民的称呼,后也泛指华夏民族以外的人。该译例有两处翻译欠妥,一是将“汉人”译为“You Chinese”,另一处是将“胡人”翻译为“barbarian”。
首先需指出,“汉族”(the Han Nationality)和“中国人”(the Chinese)并非一回事,该处应翻译为“You Han Nationality”。“汉族”是中华多民族群体中最大的一个民族,若按该例中翻译为“You Chinese”的话,俨然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不属于同一个国家,这便犯了原则性的概念错误。“中国人”(the Chinese)是一个政治概念,指的是中国作为世界诸多国家政体中的一员,而中国不同民族的人们之间所谓的“汉人”便是“汉族”(the Han Nationality)的意思。
该例的另一问题是将“胡人”翻译为“barbarian”,这既不符合历史语境,也不符合该语言语境。的确,历史上确有一些人认为“胡人”是尚未开化的民族,这是基于儒家文化背景下的大一统观点。但是,在该例的语境中,“胡服骑射”是中性词语,特指说话者所在的特定人群,不含任何贬义。译者将“胡人”翻译为“barbarian”,意为“野蛮人”“未开化的人”“无教养的人”等,曲解了千百年来我国汉民族和少数民族之间融合的历史背景。从翻译角度来说,由于对历史典故“胡服骑射”的认识不足,葛浩文未能合理地再现原文所蕴含的诗学观。在翻译过程中,对社会观念的传递和再现是译者之意识形态的体现,该译例便反映了葛浩文作为译者在中国文化及社会观念方面的偏差和欠缺。
例(3)可是农耕人口恶性膨胀的势头谁能挡得住?连蒙古的腾格里和中国的老天爷也干没辙。[5]189
But I’m afraid the population explosion among peasants can’t be brought under control, not by the Mongols’ Tengger and not by ourOld Man in Heaven.[7]291
在翻译活动中,意识形态与翻译存在互动关系,一方面操纵翻译活动,另一方面翻译活动又生产意识形态。[13]翻译过程是不同意识形态的交流和交锋,每一次成功的翻译都包含着外来意识形态与本土意识形态的对抗、妥协、征服,翻译便是意识形态作用于译者社会观念的结果。从社会观念来说,“老天爷”在中国人心目中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Heaven”是基督教中的概念,译者考虑到目标语读者的文化背景和社会认知,将“老天爷”变通地译为“Old Man in Heaven”,就属于基于不同社会观念的一种诗学变通,该翻译再现了原文的文化意象和社会观念,实现了诗学对等。翻译中存在“借体寄生”[12]58的现象,这实际是一种有机的诗学转换,也是原语文字和思想在目标语文化中安身立命之所在,有利于目标语读者的文化认知。
有道是“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由于社会观念方面的认知差异,对于同一文本的翻译,不同的读者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翻译过程中的诗学转换不是任意为之,译者必须在尊重原文的基础上,秉持辩证的诗学观来进行有效的诗学转换,以求在译文中实现与原文诗学特性的对等。
(二)价值取向层面的诗学转换
“价值取向”指的是一定社会主体基于自身的价值观在面对或处理各种矛盾、冲突、关系时所持的基本价值立场、价值态度以及所表现出来的基本价值判断。价值取向因人而异,它是人的价值观的一部分,处于不同文化中的人群也会有不同的价值观。翻译是译者意识形态的体现,不同的翻译也会打上译者价值取向的烙印。
例(4)把最恶最毒的人叫做狼,说他们是狼心狗肺,把欺负女人的人叫做色狼,说最贪心的人是狼子野心,把美帝国主义又叫做野心狼,大人吓唬孩子,就说是狼来了……[5]174
… we say the greediest people have the appetite of a wolf; the American imperialists are referred to asambitious wolves; and anytime an adult wants to frighten a child, he cries out Wolf![7]270
中西文化对狼的认知存在差异。狼在西方文明起源中充当了特殊角色,传达着特殊的文化信息,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和作用。[14]在西方文化中,狼是韧性和耐力的象征,具有王者或游侠的气宇轩昂,但对于中国人来说,狼是一种凶恶残忍的动物,具有狡诈凶狠、残暴贪婪、不讲道义的文化意象。
译者的意识形态会对翻译过程和翻译结果形成操纵,意识形态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15]牵制着译者的价值取向,影响和操纵着译者的翻译方法。该例的原文中把“美帝国主义”称为“野心狼”,这一贬义词讽喻了美国一直想要称霸世界的“狼子野心”,但在译文中却被译为“ambitious”,该词褒贬含义兼而有之,意为“有雄心的”和“有野心的”,故使用该词未能体现出原文中当时历史条件下对“美帝国主义”的鞭笞力度。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往往会故意对原文进行改变、改动,乃至篡改,即进行了有意的诗学转换。译者葛浩文在自身价值观的支配之下,不动声色地将该意象改变为让美国读者乐于接受的正面意象。该例的翻译发挥了译者的主体性,对原文的意象进行了美化,削弱了原语中讽刺和批判的效果。实际上,将“野心狼”译为“avid wolves”或“aggressive wolves”,更能与原词中所包含的“好斗的”“挑衅的”“贪婪的”等意义对等,才能真正体现该原文中的内涵。该译例说明,葛浩文作为异族译者的价值取向在翻译过程中构成了意识形态方面的诗学操控。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应采用合理恰当的翻译方法呈现原文意义,彰显异域文化,惟其如此,方能在译文中恰当再现原文文本所表达的诗学观。
例(5)读书人每人都有一本“语录”,就像现在的红本本语录一样。[5]123
Every literate person had his own “quotations”, like today’slittle red book of quotations by Chairman Mao.[7]198
“红本本语录”指的是20世纪60年代初在我国编辑出版的《毛泽东语录》,亦称《毛主席语录》。时过境迁,中国读者尚且有可能不知道其为何物,大多数目标语读者更是知之甚少,而对于“红本本语录”更是不知所云。葛浩文在翻译时发挥了自身的诗学认知能力,通过增译的方法将其解释性地译为“little red book quotationsby Chairman Mao”,使得目标语读者对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化背景有了很好的了解。价值取向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一个国家之社会历史和客观现实的影响,葛浩文基于对原文及中国历史深刻的诗学认知和领悟,对“红本本语录”进行了有效的诗学转换,再现了特定历史时期的价值取向,实现了原文的诗学价值。
例(6)包顺贵像发现了大金矿,大声高叫:真是块风水宝地,翡翠聚宝盆啊……[5]178
Bao Shungui looked like a man who had found a gold mine. “This isa perfect site!” he shouted. “Ajadecornucopia”.[7]276
中国文化讲究“风水”,大多数中国人相信,居于风水宝地能助人升官发财或富贵显达。译者只简单地将“风水宝地”译为“一个完美的地方”(a perfect site),没有体现原文的文化理念和诗学观念。文化的传播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诸如“道”“豆腐”“叩头”等音译词已被异域文化所接受,实际上,“风水”一词已被音译为“fengshui”。价值取向决定着人的行为准则、指导思想和社会原则,原文中的“风水宝地”是中国文化代表性的价值取向,如果将其直译为“fengshui treasure place”,不仅再现了原文的价值取向,也可使目标语读者涉猎中国文化,也有助于中国文化的传播。翻译的比较诗学视域主张,译者应着力研探原文独特的诗学特性,翻译的操作行为则应以认同原作的诗学观为前提,且应以赞赏、共享和再现不同文化的诗学价值为译者的指导原则和努力方向。
“聚宝盆”有聚拢财源、招财进宝的寓意,可以解释性地译为“treasure house”或“treasure bowl”等。该例的翻译中使用了来源于希腊神话的“cornucopia”一词,意为“哺乳宙斯的羊角”或“丰饶之角”。从本体意义上来说,“聚宝盆”(treasure bowl)和“丰饶之角”(cornucopia)都是具有美好寓意的东西,但因为“丰饶之角”的文化意象在西方文化中具有根深蒂固的印象,所以在译文中使用之则更能引起目标语读者的共鸣。从语义内涵和诗学价值来说,“聚宝盆”和“丰饶之角”满足了诗学对等转换的条件,故葛浩文采用借用法将“聚宝盆”变通地译为“丰饶之角”,实现了不同价值取向的诗学对等。有鉴于此,翻译的比较诗学视域主张,诗学价值的对等不是表面文字的一一对应,文学翻译不能停留于语言表面的对等,只有根据自身的诗学认知对文本进行深入探究,找到最适合目标读者的话语,才会再现原文的诗学特征。
(三)伦理道德层面的诗学转换
“伦理道德”指的是“文学作品中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社会之间形成的伦理关系及道德秩序”[16]。一个作者的思想意识和文学表达受制于社会规范,文学作品无不蕴含着伦理道德,文学与伦理道德关系密切。在伦理道德范畴之内创作的文学作品,才具有高台教化的艺术感染力。同理,翻译活动也是一种社会行为,必须受到一定的道德制约,因此翻译离不开伦理道德。译者的责任在于将原文中关于伦理道德的信息再现出来,以便充分再现文学作品的诗学特性。
例(7)儒家的纲领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强调的是上尊下卑……[5]195
Our Confucian guiding principle is emperor to minister, father to son,a top-down philosophy...[7]300
中国传统文化遵从伦理道德,注重尊卑关系,儒家思想中的纲常伦理对人们的生活有重要的制约作用。在该例中,“上尊下卑”指的是中国文化中“主上尊贵、臣下低贱”的伦理观念,而“论资排辈”指的是按照资历的深浅和辈分的大小决定级别和待遇的高低。诚然,在比较诗学视域下,翻译重在体现语言的诗学含义,强调翻译过程中的诗学转换,旨在生成和建构具有相同功能的诗学意义。因而,葛浩文将“上尊下卑”笼统地译为“top-down philosophy”(自上而下的关系),可谓对原文所做的整体性的诠释和转换。但到底谁为尊(top),谁为卑(down),译文未能体现中国文化中“主上、臣下”的尊卑关系和伦理道德,因此,就原文诗学内涵的再现来说则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此外,该例中将“论资排辈”被译为“stressing seniority”,也属于翻译较为笼统的情形,使得译文缺失了原文的文化意象。如果将其译为“stressing qualifications and seniority”,便是通过有效的诗学转换凸显了原文所蕴含的伦理道德,从而达成语言对等并实现原文的诗学价值,亦可使译语读者更为全面地了解中国语言和文化。
例(8)陈阵说:“轻柔漂亮,高贵稀罕的狼崽皮,是做女士小皮妖的上等原料。此时己成为北方几省官太太的宠爱之物,也是下级官员走后门的硬通货”。[5]40
Chen said:“Those pelts, soft and shiny, rare and expensive, were used for women’s leather jackets, and were cherished items of the wives of northern officials; they also provided hard currency for lower-ranking officials willing todo business out the back door”.[7]72
“走后门”是一个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短语,指的是用托人情、行贿等不正当的手段来获取一些好处的做法。在英语中有类似的习语“pull the strings”,它和中文的“走后门”意思相似,但葛译本舍弃了英语中的对应表达,而采用一一对应的直译方法,将其忠实地译为“do business out the back door”。这种翻译让目标语读者了解了中国特殊的文化现象,彰显了译者实事求是的诗学态度,很好地保留了原文的诗学价值。
比较诗学视域下的翻译以尊重不同文化为前提,翻译的目的就是为了传递异质文化,从这点来说,这种直译的翻译方法可谓翻译的最高境界。
例(9)天色已暗。陈阵把小狼崽放回狼窝,并抓了母狗崽一同放进去,好让小狼在退膜睁眼之前,与母狗崽混熟,培养它俩的青梅竹马之情。[5]110
Night had fallen, so Chen returned the cub to his den and put one of the female pups in with him so he’d feel comfortable around her even before the membranes fell from his eyes. He wanted them tobecome friends.[7]178
“青梅竹马”这一文学典故来自于唐代诗人李白的《长干行》,描写了一位多情女子的思夫之情。在该例中,译者将其简单地译为“成为好朋友”(to become friends),不仅使得译文了无生趣,也使得该典故所蕴含的文化内涵丧失殆尽。如果将其译为“to become childhood sweethearts”或者“to cultivate puppy love between them”等,便可以充分体现其文学含义,并传递原文的诗学内涵。在比较诗学框架内,翻译应着意于挖掘原文文本独特的语言特性、审美特性及诗学特性,通过译者对原文的诗学认知和有机的诗学转换,才能实现译文与原文的诗学对等。
《狼图腾》蕴含着丰富的社会观念、价值取向、伦理道德方面的信息,具有浓厚的中国文化底蕴和诗学价值。葛浩文较为准确地再现了《狼图腾》的诗学价值,彰显了比较诗学下的诗学转换,体现了比较诗学对于再现文学作品诗学价值的指导作用。
比较诗学采取相互比照、相互阐释的研究方式,旨在寻求不同文化之研究对象间的普遍规律和原则,其认知机制对于跨文化的翻译研究具有强有力的学理支撑。对葛浩文在《狼图腾》翻译中的诗学转换进行剖析,发现中西文化在诗学认知方面差异甚殊,惟有秉持比较诗学视域下的翻译理念,方能充分挖掘原作独特的诗学特性,并在译作中合理再现其诗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