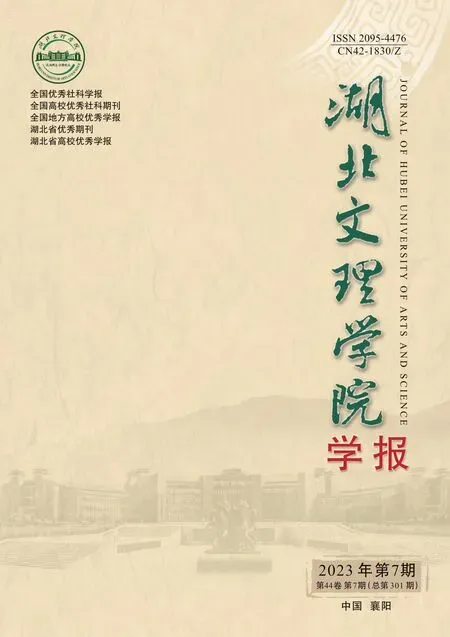变异与救赎:索洛古勃短篇小说《白毛狗》探析
章天煜
(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费奥多尔·库兹米奇·索洛古勃(Фёдор Кузьмич Сологуб, 1863—1927)可谓是俄罗斯文学白银时代的象征派代表人物之一,其在象征主义文学的创作中有着鲜明的个人特色与复杂意味。索洛古勃在俄国文坛上拥有多重身份,他既是热爱艺术的诗人,也是讲述故事的能手。纵观索洛古勃的文学创作,其中篇幅介于诗歌与长篇小说之间的短篇小说创作就好比其思想观念与风格特色的融合与浓缩,在索洛古勃的文学创作中占据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这些小说向人们呈现了一个极为宏伟庞杂、光怪陆离的象征世界,其神秘文字背后交织着多层次的意味与复杂情感。俄罗斯著名的思想家列夫·舍斯托夫曾评价索洛古勃的诗歌创作:“他的整个诗歌都是从一个特定的点出发,凝然不动而又十分紧张的凝视。”[1]事实上,这位作家的小说创作也如其诗歌一般有着贯彻始终的根源,从怪诞离奇的设定与层叠交错的意蕴之中可对索洛古勃的思想意识窥探一二。
《白毛狗》[2](Белая собака, 1903)是索洛古勃的短篇小说之一,主要围绕俄国偏僻服装厂的一位剪裁师——亚历山德娜·伊凡诺夫娜展开。在与工厂另一位女工的一场争执之中,这位看似平凡普通的主人公显露出一个不可思议的秘密:这是一位可以变形为狗的女人,每天夜间独自对着月亮嗥叫。在争吵过后的那个夜晚,郁结于心的伊凡诺夫娜再次变形为狗对着月亮嗥叫,最终被他人发现并枪击。在社会生活的压迫之下,主人公无奈变形为动物,企图通过嗥叫来宣泄与抒发情感,但仍然难逃现实的阻挠,最终陷入厄运的深渊。在索洛古勃笔下这个人类可以变形为动物的荒诞世界中,我们仿佛看到了现实社会中那些精神处于孤独、痛苦、变异中的人们。他们犹如一只只被囚禁的野兽在苦苦哀嚎着,却永远难以摆脱现实世界的束缚。“象征是通往无限的窗口。”[3]通过分析《白毛狗》这一象征小说中各种意蕴丰富的象征,我们可以体会到身为创作者的索洛古勃独特而深刻的个人体验。
一、变形现实:嗥叫的人类
短篇小说《白毛狗》与索洛古勃大多数作品的时空背景类同,都是发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偏僻落后的外省。故事在省城的一家服装工厂中展开,一开场映入眼帘的便是人们日常生产生活中最为现实的琐碎场景:“在偏僻的省城的这家服装厂里,一切是这样凝滞毫无生气:这一大堆裁好的纸片衣,缝纫机整日发出‘笃笃笃’声响,来厂里订做衣服的那些女人的挑剔劲儿,这一切真是太腻味了。”[2]290
这样与现实无二的文学世界,恰如其所描述的那般——“这一切真是太腻味了”。然而,在这世俗之中一切都在潜移默化中展开,走向难以预知的未来。主人公亚历山德娜·伊凡诺夫娜与女工丹妮奇卡的争执正是在这样凝滞无趣的背景下发生的,而丹妮奇卡在极为平静的情绪下冒出的一句话却暗示着一丝不寻常。这话语看似反抗实则隐含窥探与揭露意味,她直指伊凡诺夫娜的痛处:“您,亚历山德娜·伊凡诺夫娜,可是一条道道地地的狗。”[2]290是的,正如丹妮奇卡所说的一般,主人公亚历山德娜·伊凡诺夫娜与“狗”这一种动物有着密切的关联。小说中种种细节都显示这位人物身上所拥有的各种犬类特征:日夜不停的嚎叫声、狼狈不堪的衣着、聪明机智的双眼……更甚之处在于,伊凡诺夫娜在深夜时会赤裸着身子躺在地上对着月亮嗥叫。
然而随着故事的发展,我们发现伊凡诺夫娜也许并不是这个世界唯一的异类。她被丹妮奇卡戳到痛处后就曾在胡思乱想时不停揣测这位女工的真正身份,她怀疑这个女人也许是“一条蛇”或许是“一只狐狸”,或是“其他的什么东西”。[2]292可见,这种怪异的变形事件在伊凡诺夫娜看来并不是一件罕见之事,这个秘密在现实世界的掩盖之下如暗潮一般汹涌流动。此外,外婆斯捷潘尼达的存在同样可以印证这个世界中人类发生变形的普遍化事实。这是一位有着如老鸟儿般又高又弯的鼻子的老太太,从伊凡诺夫娜与她的交谈中可知这位老人是一只老朽的乌鸦。这无疑是一个异化变形的世界,生活着会从人类变形成各种动物的群体。这样怪谬的世界图景让人感到似曾相识,其在索洛古勃的小说作品中屡见不鲜。如《小矮人儿》中的主人公萨拉宁,他喝了缩小药水后身体不断缩小直至如尘埃消失于风中。
然而,索洛古勃在《白毛狗》中所描绘的并不是一个完全脱离现实的魔幻世界。变形、怪诞、幻想的元素充斥着文本的各个层面,人物、情节、情感都让人感到荒诞至极,但却紧紧嵌入现实之中。[4]事实上,故事中人类会变形为动物这一设定并不是如魔幻小说一般成为文学世界中纯然的既定事实,而更像是一种似真似假、亦真亦幻的描写。如伊凡诺夫娜被他人指出是狗的心理活动:“得了,狗,就算是狗呗。”[2]292而外婆斯捷潘尼达也表示:“说我是乌鸦,我也正是。”[2]294文中对于人变形为动物往往是用“就算”“像”“正是”这样模棱两可的字眼来进行描述。小说中最为大胆点破这个世界中的变形秘密的是一个小伙子,他指出嗥叫的白毛狗也许是“会变形的人”[2]295,而这在他的口中却也只是一种传说罢了。作者运用似是而非的言语描述着荒诞的变形故事,这加深了读者对于人类会变形为动物一事的可信度,但实际上这一怪诞的设定却从未在小说中清晰描述与揭示。尽管索洛古勃并没有全盘打破现实,但一切都在现实中悄然变化。这是索洛古勃小说创作的惯常手法,他擅长用文字将幻想的虚构与自然的现实巧妙融合。在他的笔下,文学诞生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虚构痕迹被深深地掩埋,不为人所察觉。在《白毛狗》的叙述中,人们也在不知不觉中走入了这个人好似会变形为动物的世界了。
需要注意的是,这一世界中人变形为动物是被排斥的,而他们的“嗥叫”也是不被允许的存在。文中曾多次出现“嗥叫”这一字眼,嗥叫是属于兽类的吼叫,其对于变形人来说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主人公每夜在怅惘中对着月亮狂野哀嚎,但是十年之前那个“年轻、快乐、轻松”的她并没有夜晚去黑暗的窗口嚎叫的举动。可见,对她而言对着月亮的嗥叫行为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长期在生活的苦闷与怅惘之下的产物,是对现实不满、精神苦闷的悲鸣与反抗。除此之外,另一位人物斯捷潘尼达也如一只乌鸦般会发出鸣叫,对于厄运有着预见能力的她一看见有悲剧宿命的人就十分想要鸣叫。不论是“嗥叫”还是“鸣叫”都喻示着难以抑制的思维言语与心理表达。可以理解为一种自然与真实情绪的流露,是一种发泄、一种表达、一种原始的居于人类心底的语言。
可惜的是,这种微弱、遥远而无攻击性的声音在人类社会依然是不被允许的。外婆斯捷潘尼达的言语给了我们极强的暗示,她预见厄运的鸣叫对于那些浑浑噩噩的人而言是避之不及的。除此之外,文中的人类对于白毛狗的嗥叫也表示这并不是好兆头。可见,无论是伊凡诺夫娜宣泄怅惘的嗥叫还是斯捷潘尼达带有厄运预见的鸣叫,这种由内心发出的难以抑制的声音在人类世界却是被摒弃的存在。
二、彼在世界:野性的大地
“艺术是从现实世界向理想世界的无比向往,是永久的渴望欣喜,是从日常生活的桎梏中解放出来。”[5]索洛古勃的文学创作往往描写深渊中的邪恶和人世间的不公,现实世界的非正义与不平等在他的作品中暴露无遗。在他的《白毛狗》中同样出现了那么一个隐匿于人物追忆与文字细节中的理想世界,这是一个古老、自然、自由的野性大地。那彼在世界正是主人公伊凡诺夫娜的心灵深处无比向往与不断追逐的,它永远漂浮在人们的回忆、精神与幻想之中:“在那里,那些生灵四处漂泊,在露天里自由自在地寻食,出于对古老大地的怅惘而尽情地嗥叫。这高悬着的月亮的形态与神情,就像在彼时,就像在彼地。”[2]292
对于象征主义流派而言,双重世界的思想往往蕴含着“结构性的意义”。[6]218在索洛古勃的笔下,残酷的现实世界与神秘的理想世界是对立存在的矛盾体,但二者时而又可以通过一定的方式与物象交织在一起,形成了意识层面的联结通道。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有两种细腻的联结方式使得伊凡诺夫娜能够无限靠近甚至暂时感知那理想中的世界。
其一是文中屡屡出现的月亮。月亮在遥远的天边,它的光芒对太阳而言是清冷的,和星辰相较却又充满力量。与现实不可分割下的疏离使得月亮在这个世界中似乎有着无与伦比的力量与意义。一方面,它是现实世界的人类眼中“能占卜问凶能施发魔法魅惑人心”[2]296的不祥之物。而另一方面,它与这个千疮百孔的世界离得那么遥远,仿佛是另一个世界的倒影。在此,月亮甚至可以看作是“此在世界”与“彼在世界”的连接物:“月儿悬在天空,又圆又亮,其形态其神情就像在彼时,就像在彼地,完全一模一样,它悬挂在像沙漠一样广袤的草原上,悬挂在野生动物栖居于其间的故乡。”[2]292
可以发现,月亮对伊凡诺夫娜具有难以抗拒的召唤力量:“月儿直勾勾地瞅着她的脸,执拗地召唤着,直让人感受着煎熬。晦暗的怅惘弄得心儿抽紧了,实在是坐不住了。”[2]295-296此时的月亮挂在阴冷的天空之中,弥散着花白中夹杂着绿色的清冷光辉。与白日中炽热的太阳不同,月亮在此处像是这个世界的残酷现实与激烈情绪之中的特殊存在,冰冷而透亮的月光之下是难得的平和安宁。处在黑夜的月光之下,就犹如是疲惫不堪、忧愁怅惘之人的避风港。月亮这一物象也由此成为了理想世界与现实世界的联结,在索洛古勃笔下有着特殊的意味。除此之外,老太太那“古老的、自古就有的话语,能产生奇迹的话语”[2]294亦让人联想到彼在世界,与理想世界有着紧密联系。正因如此,主人公伊凡诺夫娜每夜都对着月亮嗥叫,这是她对于现实世界的逃避与理想世界的向往。
另一条通往“彼时彼地”的相关路径是——赤裸,这需要抛开外物以光赤的肌肤与大地接触。伊凡诺夫娜就十分喜爱赤脚踩在大地之上的感觉,这种与自然的亲密接触能够给怅惘的她带来快乐:“在穿堂里,她听到那堆满垃圾的地板的木条在她那光赤赤的但却暖洋洋的脚板下,吱吱地发响,她感觉到一些细木屑与小沙子在快乐地、开心地抚弄着她腿上的肌肤。”[2]293可以发现,“赤脚”的象征对于索洛古勃的文学创作有着别样的意味,这是他诗歌与小说中反复出现的重要意象。正如索洛古勃的诗歌:“吻吧,大路上的尘土,吻我那光裸的双脚,我的心忐忑不安,听一听小鸟的鸣叫。”[6]359其中“赤脚”这一情节与具体社会有着紧密的联系,带有一定的社会意图。赤裸的双脚在大地上与尘土接触,是与大地的赤诚交流,更是借此对世俗的洗净。而在小说《白毛狗》中索洛古勃进一步以愈发完全的方式展现其中的意味。可以发现,文中主人公喜爱光脚甚至赤裸,在这个世界上以赤条条的姿态与大地接触。短短一天之中,伊凡诺夫娜经历了“衣裳整齐——赤脚——裸体”的全过程。这一行为的背后是主人公与惨淡迷惘的现实世界逐渐剥离的过程,试图让一切回到最初的纯净与快乐。这种无比原始的状态,可以让人抛开一切尘世的杂念,犹如与理想世界亲密相接。讽刺的是,伊凡诺夫娜最终是在赤条条的状态下对着月亮嗥叫的时候被其他人类用枪击中的,最后也回归为赤身裸体的状态:“闷雷似地滚过一声枪声。狗尖叫起来,蹦起两条后腿站立起来,变成一个裸体女人,全身通体淌着血,她挣扎着要跑开,尖叫着,哀号着,嗥啕着。”[2]297
伊凡诺夫娜的厄运是注定的,从外婆斯捷潘尼达对其带有预见的两声鸣叫就可知道最终不可逃脱的结局。索洛古勃是热衷于死亡的,鲁迅也将其称之为“死的赞美者”[7]。《白毛狗》中主人公伊凡诺夫娜最终是否死亡,我们无法从正文中得到准确的判断。但可以确定的是,她与理想世界的联结被彻底阻断了,试图逃避现实并奔向理想世界的幻想无疑也在一声枪击中破灭了,在以最为虔诚的姿态企图与心中的理想世界建立联结时,她迎来了血淋淋的破灭。
可以猜测,《白毛狗》中这种美好而虚幻的彼岸世界在试图建构的时候就已经破碎崩塌了。从中亦可以看出对现实世界无比失望的索洛古勃在文学创作中寻找“现实之代用品”的阶段性尝试,而“幻想之建构”仍在进行当中。[8]
三、生命体验:笼中的野兽
“他(索洛古勃)从天堂被放逐出来,然而却时刻怀念着天堂,他以全部身心揭露并否定地狱,他猛烈地抨击因循守旧畸形丑陋的尘世现实。”[9]无论是人会变形成动物的现实世界,还是古老自然的理想世界,《白毛狗》中所隐含的层叠意蕴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对当时社会现状的折射与反映,是对尘世中不堪与黑暗现实的揭露与批驳。
小说最后的结尾无疑是令人玩味的,其将叙事焦点从主人公伊凡诺夫娜身上转移到了另外两个人身上,并着重描绘了二人在射击白毛狗后的具体反应:“蓄着黑胡子的与头发微微鬈曲着的那两个人顿时都跌落到草地上。在野性的恐惧中,他俩也嗥叫起来。”[2]297当他们看见伊凡诺夫娜被射击之后站立起来变成了一个裸体的女人,二人惊慌失措并同样发出了属于野兽的“嗥叫”。从前文可知,“嗥叫”属于兽类的叫声,是人变形成动物后的呼喊。然而,在此处那些排斥并伤害变形人的人类同样也在“野性的恐惧”中发出内心的嗥叫。毋庸置疑,这两人同样与变形动物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文中还有一个细节值得推敲,当头发微鬈的小伙子向黑胡子男人提及“会变形的人”时,黑胡子男人的回答却是叮嘱小伙子不要去变成动物。可见,在这个世界中正常的人类都有变形成动物的可能性。这种变形并不是与生俱来的种族基因,而是在后天环境影响下的一种变异。此外,伊凡诺夫娜是一只白毛狗,外婆斯捷潘尼达是一只乌鸦,还有真实面目难以确定的丹妮奇卡等。这些例子无疑向我们暗示着在这个世界中人都是会产生变形的,也许他们的心中都藏着一只野兽。这只暗藏心中的蠢蠢欲动的野兽会是人在现实社会环境下的各种变异,可能是狗、乌鸦、狐狸、蛇……
但是人真的会变形成动物吗?文中的细节暗示了“变形”这一设定既可以理解成生理层面的变形,亦可以是精神层面的。事实上,正如前文所提及的那样,小说中的人变形成动物并不是既定事实,而是一种似是而非的描写。其中变形之人的“变形”并不是外在的变异,而是趋向精神的异化。文中曾对变形后的伊凡诺夫娜进行了外貌描述,可以发现它依然保持着女人的特征:大于正常狗的体型,身上如发辫的斑点,赤条条的肌肤,看不到尾巴……“这一切给人的感觉又很像是,在这草地上躺着的、像狗一样嗥叫着的本是一个裸体的女人。”[2]297由此可知,变形的伊凡诺夫娜并没有变成狗的形态而依然是人类的外形。此外老太太斯捷潘尼达虽然承认自己是一只乌鸦,但她同样是没有翅膀的。
可以猜测,索洛古勃笔下的这个变形世界中,人类所发生的变化并不是真正从一个人变成一只动物。而是人们的心灵在现实世界的挤压之下最终发生了精神蜕变与人格丧失。这背后的原因诸多,如现实社会的压迫、平凡人的失语等。而与此同时,他们在现实压迫之下会发出各种各样的声音:内心怅惘的嗥叫、预见厄运的鸣叫、恐惧之中的嗥叫。社会中每一个人都有如被囚禁于笼中的野兽,只是自知或者不自知罢了。他们通常只能以薄弱的声音表达内心的哀鸣,发出自己的声音。《白毛狗》中这种人会变形成动物的象征不由让人想起了作者索洛古勃在1905年创作的诗歌:“我们是被囚禁的野兽,只会用各种声音叫唤,所有的门都已被关死,我们又岂敢把门打开。”[10]相较于这一首诗歌,《白毛狗》中的现实意味更进一步。在这个世界中,“嗥叫”就如现实社会中人们对于生活所发出的抱怨与愤怒的声音,而“鸣叫”犹如智者对于社会不公与罪恶的劝告话语。可惜这些声音同样是不被社会允许的,需要小心翼翼地掩藏,其中无疑有着无尽的暗示意味。在强制束缚之中,现实社会的人们被剥夺了话语权最终陷入一种近乎失语的状态。除了人心灵变异的话题,这种话语权被剥夺的失语的社会背景与现实都有所揭露。
从《白毛狗》中“人的异化”这一主题可以看出,索洛古勃所关注的是人类在扭曲的现实世界下灵魂深处的矛盾与病态。此处的“人之异化”已不仅是精神在压抑之中寻求以哀鸣的方式来宣泄、释放,而同样展现出人们在不自知的情况下不断地被社会的“恶”同化。他们的心理趋向病态,却只知如野兽般以叫声宣泄而不知自救。这些变异之人都陷入一种无限循环之中,他们厌恶现实世界的恶却在精神上趋于不自知的变态与变恶。如主人公伊凡诺夫娜由于秘密被丹妮奇卡所窥探而感到压抑与愤怒,需要变成动物对着月亮嗥叫来抒发自己的愤懑。对此,她表示自己对他人秘密的尊重:“我可没有去窥探,去追踪,去查证,她究竟是谁。”[2]292但在后文中她却完全违背了自己的诺言,转而对老太太斯捷潘尼达的秘密进行窥探,并直截了当向其求证变形的真相。不仅如此,窥探他人还让她感到异常兴奋与快乐,这无疑是一种满足窥私欲而获得快感的内心变态。索洛古勃在文中同样暗示窥视他人是要受到惩罚的,丹妮奇卡与伊凡诺夫娜的不幸遭遇正是如此。
《白毛狗》呈现了索洛古勃惯常的写作手法,他擅于从现实和虚幻两个层面着手,展现存在的双重层面。在这部短篇小说现实与虚幻的象征主义双重结构中,它不仅仅揭露了社会现实的压迫与不公,更是通过存在主义神秘色彩的刻画与渲染,强调了人在现实社会环境中精神内心深处的异化。这种平凡人被压迫、被桎梏的失语生活不仅仅是当时俄国的现实面目之一,更是其“存在的属性”[6]211。
四、创作追寻:“一线之光”
索洛古勃的创作是丰富而神秘的,从短篇小说《白毛狗》中即可感受到其创作思想与立场的复杂性。我们从中能体会到他惯有的颓废姿态,能看到其对社会的不公与“恶”的揭露,但也能感受到他文字中不羁的反抗与坚定的向往:“我酷爱那一线之光,不管它来自何方,因为黑暗总使人恐慌。”[6]355
索洛古勃及其他象征派代表人物常常被认为是“颓废主义者”,但在其诗歌及小说作品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其本人世界观的复杂性与多重性。他也许并不是颓废主义者,甚至很多时候都站在颓废的对立面。索洛古勃的文字崇尚魔鬼、地狱、死亡等主题,但这些主题的选择并不是其创作的根本。“这种个人主义,主要还是主体对存在状态的悲剧性的体验,是被异化的、孤独的个体对生命、对自然、对宇宙的存在状态的体验方式。”[11]那些颓废、黑色、荒诞的元素下暗藏着索洛古勃作为一位艺术创作者的希望、幻想与尝试,他通过文学创作这种自我沉溺的方式体验了孤独与异化个体的存在,在此基础上揭露了社会的黑暗与不堪。
在《白毛狗》看似悲观的世界观中,索洛古勃的“文化哲学”蕴含其中。在小说中我们看到了一只对着月亮嗥叫的白毛狗,而在索洛古勃的一首无题诗中他同样将自己也描述成一条对着月亮嚎叫的狗:“你的计划我并不想毁掉,心想:‘我不妨就当狗一条。’马马虎虎我学会了嚎叫,甚至习惯于对着月亮吼叫。”[12]从中可以看出索洛古勃认为自己也是现实社会中异化的一员,他的变形是对生活的无奈与妥协,并且习惯了对着月亮吼叫。然而在诗歌最后,他却表示自己不再继续做狗,因为他是一位“热爱艺术的诗人”。在《白毛狗》中亦是如此,他竭力揭示在残酷无情的现实社会中人类的精神变异,但我们同样可以感受到黑暗缝隙中透出来的一丝亮光。《白毛狗》中人变形为哀鸣难抑的野兽,其追寻理想世界以失败告终。而人在现实世界中注定是孤独与痛苦的,他们对于理想世界的期盼与追寻亦是难以实现的妄想。但诗人索洛古勃的理想世界构建仍在继续,他试图通过艺术去寻找与建构一个更为美好的世界。《白毛狗》中的那个古老、自然、自由的新世界的出现正是索洛古勃对于构建理想世界的一次试探性实验。于索洛古勃而言,唯一且真正值得去做的,是创作中的自由幻想,是独属于人类个体的精神活动。[3]11
作为一位创作者,索洛古勃从未停止构建一个集爱、美与理想为一体的新世界的步伐。三部曲小说《创造的传奇》就是索洛古勃对自己心中理想世界的构造与阐释,他在作品一开始就表明自己的用意:“对你——灰暗而平庸的生活,我——一个诗人——在黑暗里坐得不是腿脚僵硬发麻就是浑身遭人难耐,在绞尽脑汁杜撰着美丽迷人的传说。”[13]而这种创造传奇的向往贯穿他的文学创作生涯,在诗歌、小说、戏剧中皆有所显现。
鲁迅曾对俄国文学有所定义:“俄国的文学,从尼古拉斯二世时候以来,就是‘为人生’的,无论它的主意是在探究,或在解决,或者堕入神秘,沦于颓唐,而其主流还是一个:为人生。”[14]索洛古勃的短篇小说《白毛狗》正是其中之一,篇幅不长却意味深长。在此,我们不仅看到了现实社会中普通人的异化与大环境下平凡人的失语,还感受到掩埋于黑暗之中的挣脱力量。索洛古勃在内的许多作家的文字多是如此,满目疮痍之下仍在艺术之中寻找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