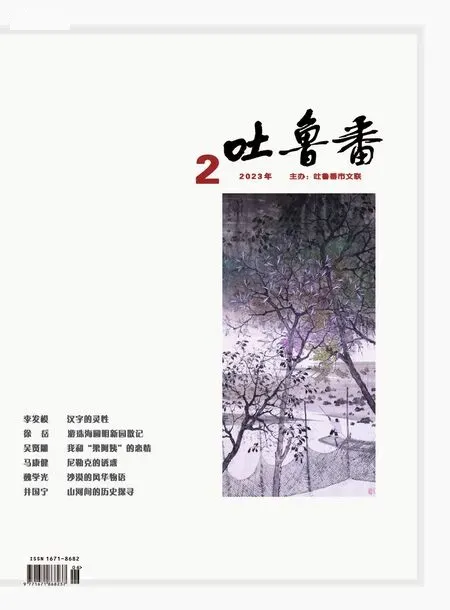驴兄
王彩利

驴兄是十三年前父亲用20块钱买回来的。
驴兄刚出生,驴兄娘因小姨喂的黄豆大多,致使肚子膨胀而死。驴兄断开母乳,加上小姨喂养粗心,日渐枯瘦。出生两个月了,肚子干瘪,毛发枯黄干涩,耳朵耷拉,粘稠的眼角屎在眼眶处干涸。小姨想到驴兄一直这样下去一定会死,所以牵到集市上去卖,正巧被赶集的父亲遇着了。父亲问小姨要卖多少钱,他买。小姨说:“如果你买一分钱也不要。”父亲说:“哪成呢!长毛牲畜不能白送人,你开个价。”“放下二十块钱你就牵回去,但你要想好,我是喂不活才卖的。”
就这样,驴兄跟着父亲来到我家。
刚到我家的那天傍晚,驴兄躺在圈棚里,父亲端来水,把铡碎的谷秸杆放在驴兄眼前,它闭着眼看也不看,奄奄一息。
母亲埋怨:“就这样子它能活?不吃不喝,今晚它就要咽气了。
父亲说:“它走了几十里路,累了。你如果累了,还想活蹦乱跳吗?”
母亲火气更大了:“它是驴啊,生来就是吃苦受累。你牵回来是靠它滚碾转磨,耕地拉车,不是供奉老人啊。你一个半老汉走几十里路还没觉得累,它就累成那样,要它干啥?你啊,常就做这些亏本生意……”
父亲也不依不饶:“它才出生三个月,而且一直缺乏营养,你出生三个月还在被窝里睡觉了,更别说走路了!”
“啊?你拿我和驴比较啊?你说这是什么话啊?……”
驴兄的到来,使我们原本平静的家庭变得“硝烟弥漫”。
看着驴兄病病恹恹的样子,父亲犯愁了。他咨询了乡上兽医站的兽医师。当时驴价大跌,即使一头健康的驴也卖不了多少钱。兽医师看到驴兄身体瘦骨嶙峋以及软泥般的瘫痪卧姿,对父亲说,别费心了,没有治愈的希望,也没有治疗的价值了。
如果没人打搅,驴兄嘴不张,眼不睁,静静躺在驴圈里,奄奄一息之状让父亲愁苦无奈,但他没有放弃救活驴兄的希望。有空就蹲在驴兄跟前,抚摸驴兄的耳朵、眼睛、鼻子,或用笤帚一遍遍涮扫驴兄身上干涩的鬃毛。像哄小孩子一样,轻轻拍打驴兄的脊背,让驴兄站起来,把铡碎的上等谷秸杆放在石槽里,让驴兄吃。把黄豆炒熟碾成碎沫,和在泔水里,吹口哨哄逗驴兄喝。尽管驴兄一次吃喝得很少,哪怕一口,父亲都很欣慰。他说,身体是铁,饭是钢,只要嘴里能吃进食物,就有活下去的希望了。
邻居们笑话父亲,你亲生的三个孩子你都没给喂过一口饭,却把一头将死的黑驴当宝贝一样服侍。
父亲说,黑驴也是一条命啊,只要有一线存活的希望,我就把它当作自己孩子一样关照。
尽管父亲对驴兄精心喂养,但驴兄的身体没有太大的好转,不过就是出一口气而已。因为驴兄每日吸收的营养仅能维持体力的消耗。
一日,父亲去小镇赶集,碰到一位退休的老兽医师,他告诉了父亲一个能让驴兄康复的偏方。他说,每天给驴兄灌二两食用油,诸如麻油或菜籽油等。这样坚持一星期,驴兄的食欲就会大增,身体会一天比一天强壮。
父亲遵照医嘱,每天在邻居的帮忙下给驴兄灌食用油。一星期后,驴兄果然食欲增加,咀嚼谷秸杆时的清脆声、喝水时“咕噜咕噜”的下咽声、躺在院子里打滚儿的欢畅,把父亲醉倒在幸福中。“活了,终于活过来了!”父亲幸福地自言自语着。驴兄从九死一生的病难中活过来,似乎也迈过了生命中重要的一个坎儿。
驴兄成长至一周岁了。身体健壮,黑眼珠滴溜溜乱转,野性十足。像母亲说的,它该吃苦受累了。春天,父亲与母亲牵驴兄上山学犁地。母亲在前面牵缰绳,父亲一只手扬着鞭子,一只手攥着犁铧,初出茅庐的驴兄被犁铧与缰绳牵着行走,从地头这边还没到那头,就挣脱母亲手中的缰绳,拖着犁铧遍山疯跑,没有被驯服之前的野性毕露无遗。它不能容忍被束缚。母亲坐在地畔欲哭无泪,责备父亲把一头驴养成老虎。父亲没有去追,他蹒跚的步履哪能追赶上一头健康驴子?
“随它去疯吧。身上还套着犁铧呢。跑上一阵它会累的,累了自己会回来的。”父亲说着坐下来,装了一锅旱烟,吧嗒吧嗒,悠然吸着,胸有成竹。果然,父亲在镢头上磕烟灰的时候,驴兄在山顶上扯开嗓子“呐喊”。
“我就知道你会停下来的,让你再跑!”父亲自语,有些得意。
驴兄被父亲牵回来,继续先前的犁地,乖顺,步子沉稳,规规矩矩走在犁道里,蹄子也不乱蹦了。
母亲说,这坏家伙累了就规矩了,不捣蛋了。父亲说,累了就适应了,适应了就规矩了。就像小孩子刚开始走路,没走就开始跑了。当跌撞过几次,就不跑了,慢慢学着走路了。
短暂的一个春天里,驴兄学会了拉车、犁地、滚碾推磨,对父亲温顺而恭从,替父亲分担艰辛,偶尔也会因耐不住束缚挣脱缰绳而狂奔撒欢,待父亲一阵教训之后,它用头在父亲的身上磨蹭来磨蹭去,请求父亲原谅。父亲说:“这次饶了你,你给我长点儿记性,没有下一次了!”驴兄两只竖着的尖耳朵抖几下,伸出舌头,对父亲龇牙傻笑。
这是1996 年春天的事情。驴兄以一个家庭劳动力角色,与父亲早出晚归,共同劳作田间之事。
1999 年,我结婚。驴兄头上佩戴着一朵红花,在清亮的唢呐锣鼓声中,风光无限地拉着平车,载着我简单的嫁妆,翻山越岭,来到另一个枣花飘飞的院落停脚。卸下嫁妆,二叔将它拴在院内的枣树上。但它朝着院门口长鸣,久而不止。宴席间的亲戚以为它渴了,赶紧舀来一盆水让他喝,它似乎没看见一样,继续嘶鸣。二叔以为它累了,解开僵绳,牵着走出院落,让它躺在硷畔上的槐树下歇息。驴兄狂奔至硷畔的槐树下,顷刻间撒尿拉屎,再没有仰天长鸣。二叔这才明白,原来驴兄不想在广众之下“出丑”,不愿影响宴席间朋友亲戚吃饭的兴致,所以声嘶力竭找个僻静的地方“解手”。
妹妹远嫁内蒙,弟弟出外求学,每次回家来,都是父亲牵着驴兄到十里外的小镇,接他们回村。父亲说,驴兄是他的好帮手,顶他半个儿子,家里苦重的活计,驮水、拉车、滚碾拉磨,凡驴兄能干的,它都一声不吭地承担了。对我和弟妹来说,它是至亲的兄长,它替我们替父亲分担解忧。如果没驴兄,无法想像父亲操持田间的艰辛。
一晃十年。2009 年初秋,父亲病倒了,前往陕西省人民医院治疗,一住四十天。这是驴兄入住我们家与父亲分别最长的时间。父亲踏进院门第一件事就到驴圈看驴兄,驴兄竖起耳朵,头亲昵地蹭父亲的手臂,欢喜、撒娇。父亲吆喝母亲拿来笤帚,在驴兄身上反反复复涮扫,埋怨母亲没精心喂养驴兄。他说牲畜活着就凭人照看了,人不好好照顾哪能活成了?驴兄确实瘦了。四十天里,驴兄不适应母亲的喂养方式,饮水不喝,喂草不吃,母亲牵驴兄上山,防止驴兄“叛逆”,还给驴兄上口缰,驴兄稍不听话,她就勒一下,驴兄被勒疼了就高声长鸣,抗议母亲的“虐待”。再加上母亲为父亲担心焦虑,根本没心思悉心喂养驴兄。她说,人都命悬一线了,有啥心思喂养牲畜?
父亲从坐上去省城的火车那刻起,注定今生不能再与驴兄相守了,要弃驴兄先奔往另一个世界。之后的一年半时间内,父亲病病恹恹,一直在家与医院周旋着。只在身体稍微舒适的时候,摸摸驴兄的耳朵,捡一把木萱放到驴兄嘴边,看着它慢慢咀嚼,慈爱之情溢满脸膛,偶尔间又闪过一缕凄凉与无望。而悉心喂养、与驴兄朝夕相处的只有母亲了。驴兄帮着母亲春种秋收,驮水拉车,割草砍柴。母亲腿病严重,但凡走远路,就牵出驴兄,驾上车,在车辕前放个棉毯子,一屁股坐上去,驴兄就出发了。
2011 年春天,父亲终于没能逃脱病魔的折磨,带着对人生的眷恋去往另一个世界。下葬那天,凄凄哀哀的哭声、唢呐音弥漫着院子,父亲的灵柩将要被抬出院门时,驴兄扯着脖子悲恸长嚎,一种穿越时空的凄凉刹住了所有的哀哭声,齐刷刷的目光聚集在驴兄身上,但没有人敢上前阻止驴兄,包括母亲。所有人认为,驴兄的疯狂恸哭,是父亲的魂灵附在驴兄身上。抬灵柩的人走也不是,停也不是,僵直地站着,惊得满头大汗。唯恐向前迈一步,父亲就会跳出棺材一样。向来迷信鬼神的本家二叔,命令人将汽油洒在驴兄身上,放火“烧鬼”。大爹立即拿来一瓶汽油,伤痛中的母亲突然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跑上前夺过大爹手中的汽油狠狠扔出院墙,说:“你们这是烧驴娃,不是烧鬼,我明白驴娃要干什么了。”之后镇定地走到驴兄跟前,说:“别发疯了,让你送主人上山。”驴兄停止嚎叫了,凸圆的眼睛滚出两行泪水来。母亲解开缰绳,牵驴兄到圈棚里,驾上平车,让驴兄“送”父亲。所有人都不解了。自古以来,人死后,是孝子们抬着灵柩上山,哪有让牲畜载着灵柩送行?这不明摆着对仙世者不敬吗?本家二叔劝母亲,伯父也劝母亲,母亲想了想,觉得在理,驴娃与父亲感情再深,毕竟是牲畜,这一点永远不能改变。回头将驴兄牵回圈棚时,驴兄又伸直脖子,望着灵柩狂嚎,如波涛翻滚,气势咄咄逼人。在场的人无不躲避。本家二叔叫响父亲的名字,说:“兄弟,我知道是你是想让驴娃送你。今儿顺你的心,让驴娃送你一程,就安心走吧!”
这样,父亲就由驴兄一路驮送至墓地,表现出从末见过的乖巧和老实,它站在墓地的一旁,静静目睹父亲的灵柩入穴,直到坟头白色引魂幡在旷野中随风飘荡时,它突然一声长嚎,挣脱缰绳,狂奔到前面的山崖前,一头冲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