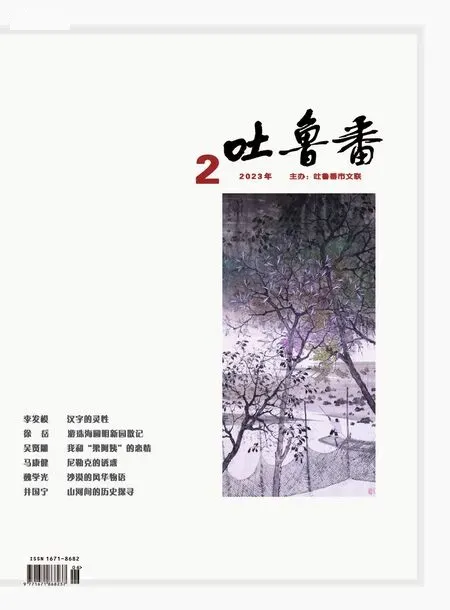被风吹走的父亲
于 晓

一开始,风是贴着地面轻轻跑的,像是一把刚长出的绒草,细细碎碎,生怕折断了夜的衣裳。然后它们跑到墙上、树上、瓦上、烟囱上,又从窗户、门缝钻进屋子,在干草上、灶灰上、衣服上跑着。跑着跑着,它们就跑醒了天光,跑醒了虫鸣,跑醒了整个村庄。
父亲拿了木锨去稻场扬谷。他弯着背,风吹着他,一些树枝在暗影里浮浮荡荡。这是一个晴朗的早晨,草叶上的露水还在大颗大颗往下掉。父亲扒开稻堆上的干草,扎好步子开始一锨一锨往风中扬谷。利用风力分离谷壳是一项古老的技术活,它需要在力度和距离上掌握得分毫不差。父亲对此项技术十分娴熟,他能一边扬谷一边用目光打探别的消息,比如那些谷壳的去处。风一把一把吹过来,父亲托着木锨,在青灰的晨光中一会儿上、一会儿下、一会儿左,一会儿右,有时候又突然不见了,像是被风吹走了一样。
父亲经常被风吹走。被风吹走的父亲有时候在树上,有时候在草丛里,有时候在云朵上——风将父亲吹得到处都是。
春天,风吹进村子,村民们开始垦荒、种豆、插柳、嫁枝、修补家园……父亲抹去农具上的灰,架好牛套去犁田。他走上河堤,走向风中。风吹着他,他越来越小,越来越不可见。但他很快又出现在稻田里,像是那里突然长出的一棵庄稼。那是块椭圆形稻田。而实际上,在我眼里,所有的稻田都是椭圆形的,因为没有什么东西比它们更像一粒稻子。父亲将犁深深挖进去,风鼓动他的衣物,使他看起来像是一个矿工,他将在里面取出他的金银铜铁,取出他的一生。但五十多岁的父亲已经有了衰老的痕迹,他握着犁把的手布满了时间的根须,一用力那些根须就会从他手上飞出去,他的腰和腿越来越像一块风干的泥巴,一用力它们就会分崩离析……他休息的时间越来越长越来越密集。休息时他会不停地捶打自己,像捶打一块淬火的铁,但风不是吹掉他的头发,就是吹落他的牙齿。有时候,他干脆靠在树上睡觉,头耷拉着,四肢摊开,任鸟在头上飞来飞去。村里多野树,它们长相深邃,骨节粗粝,身上满是时光的皱褶和创口,父亲靠着它们,恰如它们身上长出的一个硕大结节。
或许,父亲正在朝某个结节里慢慢长去。
夏天多南风。干燥的南风将所有的水分一点一点吹干,热烘烘的空气闷火一样填满村子,填满人的口舌。村民们开始抢着给稻田灌溉。他们昼伏夜出,幽灵般蛰伏于田间地头,在各自的领地里严防死守,奔突的抽水声在漫长的黑夜里长成一棵棵大树。堰塘、沟渠很快只剩一张骨架,被黑色的植物根系和死去的水草包裹着,散发着腥臭和滚烫的气息。这些骨架要经过一场大雨后才能再次复活成新的堰塘和沟渠。但一场大雨要等到什么时候?也许三两天,也许一个月,也许更久。谁知道呢?父亲也不知道。在他五十多年的经验中,他唯一缺少对雨的认知。雨像古老山林笼罩的雾障般神秘莫测,他是山林中走失的小孩。他开始期盼一场北风,因为北风会带来雨,会带来整个气候的转变。但北风迟迟不来,它似乎被南风吹死了,整个世界烟尘弥漫。
父亲和村民背着铁锹在路上走来走去,在稻田周围走来走去,他们走来走去的样子像是一群觅食的蚂蚁。北风终于来了,它扛着一杆大旗,呼啦啦在村子里奔跑着。实际上,在预测风向这件事上,村民们并不比一台精密的感应器差。他们可以通过天色、空气、草木的细微变化判断风的走向。当空气开始潮湿、草叶开始滞重的时候,他们知道风很快从遥远的森林掉过头来。但他们秘而不宣,似乎一说出来,所有的感知就不灵验了。第一缕风吹到时,他们才开始抢暴(即抢收外面铺晒的干草和稻子)。他们像蚂蚁一点一点往屋里搬,往安全的地方搬,风贴着地面跑着,他们的脚牢牢抓住地面,像是树根抓住生命。抢暴是一个很重的词,它是千百年来被风雨浸泡出来的,凝结着祖祖辈辈不屈的意志和力量。它亦贯穿我的整个童年。小时候,半夜经常被父母喊起来去抢暴。此时,梦还在周围浮荡,夜却黑得像一个巨洞。我们大气也不敢出,像蝙蝠紧贴着墙,然后踩着父亲的影子深一脚浅一脚地往稻场挪去。父亲早已开始忙碌,他挑着箩筐不停地走来走去,长长的灯影在我们的脚上、手上不停晃动,一晃动,我们感觉自己也被装进了父亲的箩筐里。雨是无影脚,往往随风而至。抢收不及,只好就近拖了稻草或塑料布将谷堆紧紧盖住,上面压上锨板和农具。即便这样,父亲仍不放心,点了烟坐在堂屋里守着。烟火明明灭灭,雨声远远近近。有时候突然醒来,看见有光闪动,以为天亮了,爬起来,却看到与黑暗融为一体的父亲。他似乎睡着了,脑袋搁在椅子上,身上轮廓起伏,像是横亘在黑暗里的一座山脉。
风来得多了,就成了村庄的一部分。若长久不来,村民们便开始砍掉一切阻碍风的东西,有的还会推倒一堵墙,或拆掉一块门板。父亲则跑到河堤上喊风。他喊风跟喊人无甚区别,只不过喊风的声音更高一些更长一些,类似于狼嚎。实际上,父亲只是想将胸腔里那股子闷气喊出来。每到干旱的日子,父亲就会沉默不语,似乎一说话就会砸出一个洞来,他甚至感觉自己的嘴巴正在长出一把锤子,喉咙火辣辣的,像是灌进了一条滚烫的河流。他开始不停地走来走去,走到稻场里,走到河堤上,然后对着天空喊了出来,嗷呜嗷呜,奔腾的声音将天空砸得一闪一闪。喊完一嗓子,他感觉脖子上有了毛绒绒的凉气,接着他看见草叶动了,河水也起了微澜……风竟然被他给喊来了。
很长一段时间,父亲都沉浸在这种奇妙的巧合中。他甚至坚信自己具备某种神秘的力量,并不断佐证其真实性,譬如某天晚上梦见一白胡子老人送给他一本无字书,某天晚上又梦见自己在山上飞。除此之外,他总是神秘消失,像是被风吹走了一样,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直到有一天他进了一间屋子。
那是一间杂屋,也是我们家最恐怖最肮脏的地方,里面不仅放着坏了的农具、木盆、断了腿的椅子和烂衣服,还有老鼠、蟑螂、蛇以及我们所有想象中的怪物也都盘踞在此。那会儿,父亲正在里面找一把很久不见的镰刀。他将农具一件一件挪开,将木盆里的衣物一件件拿掉,最后,他看见了那条蛇。它像人一样悠闲地蜷在木盆里,嘴里正慢慢吞着一只尺来长的老鼠。蛇吃老鼠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父亲则认为那是神的启示。那天傍晚,他敛手走进了那间屋子,他走得有些缓慢,不像是被风吹进去的。屋子里有灯,他的影子模模糊糊映在窗户上。透过窗缝,我们看见父亲正对着墙上的一个神像念念有词,神像前摆着米饭和瓜果,瓜果上漫漶着一层莹光。我们忽然被一种情绪击中,好像父亲突然变成了另一个人,一个与我们毫不相干的人。我们被这样的想法弄得十分忧伤。后来父亲告诉我们那是土地菩萨,是守护一方的地神,他是神的子民,那场风是他作为神的子民喊来的。父亲的话我们从来深信不疑,因为在某种意义上,他就是我们心中的神。只是当再遇到干旱时,他再也没有喊来风。
风去了哪里?或者风从哪里来?谁也不知道。很长一段时间,我以为风是从地里长出来的。因为它们来的时候常常会带来一些松针、腐草或干土的气味,根据这些气味,大抵猜测它们来自一座山、一条河,或者来自一片广袤的平原。每当我站在那条唯一通往村外的公路上时,脑海里就会出现一把风青烟一样从草丛、岩石、腐草中不断生长的画面。如果凝神静听,还能听到它们呼呼卷来的细密声音。那声音如此辽阔,像是一个庞大的梦境。我一直认为风声是自然向人类发出的友好警示,是人类探索自然隐秘的途径之一。但有些声音是听不见的,譬如树叶凋零的那一瞬。村里的老人临终时,大多都是无声无息的。他们躺在肮脏的床上,黑暗大口大口地吞咽着他们。风从瓦上吹下来,吹动堆积着陈年积灰和蚊虫尸体的帐顶,将帐顶吹出一个倒扣的坟包。老人就在缓缓下坠的坟包中咽下最后一口气。死亡的声音如此轻微,如同一块泥土融入另一块泥土,一片落叶融入另一片落叶。多年以后,当我站在父亲的床边,看着他卷曲的身体和微张的嘴巴,我就会想起那些风,想起那些被风吹落的树叶,感觉自己也被一阵风吹起,双脚悬空,正飘向一个未知的地方。
2017 年春,父亲的身体像被虫蛀空的大树,突然坍塌在生命的十字路口。我们将他送到镇医院,又送到县医院……我们想尽办法为他嫁枝补叶,为他填补身体的空,却无济于事。他蜷缩在病床上,整天吵着要风,要呼吸。我们将所有的门窗打开,给他戴上呼吸机。但还不够。他像一尾搁浅的鱼,在风中大口大口呼吸,他想要将所有的风都吸进去,吹动那个已经停止运转的肺叶。但他一生信任的风不仅没有吹动他的肺叶,反而将他从人生的树枝上吹落了。
被风吹落的父亲成了时间的一个结节。
次年清明回家祭祖,村庄人影寥落,万物岑寂,被雨淋湿的村路变得格外漫长,似乎永远也走不到尽头。隔着雨雾看过去,祖坟静静卧在一片高岗上,高低错落,密密匝匝,满地花草覆盖着它们,春的气息无限生发,仿佛死亡从未发生,它们像是一个楔子,将村庄的生与死契合得如此天衣无缝,诠释了什么叫向死而生。父亲与祖辈们在和土地、自然相处的一生里,何尝不是一次次向死而生,一次次前进与妥协。他们与风斗、与雨斗、与生斗、与死斗,最后还是被风吹到了这里,吹到了草木中。
父亲走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感觉不到风的存在,它们似乎随着父亲一起吹走了。直到那天再次走向村庄,走向父亲长眠之地,才发现它们一直都在。它们在草丛里,在路边,在树杆上。我停下来看它们,却看到无数个父亲,耕田的、挑担的、守夜的、喊风的……村庄真小啊,小到盛不下太多的父亲。
忽而想起多年前,我在河堤上追蝴蝶,父亲则沿着河堤去砍柴。他拿着扁担、绳索和砍刀,低着头,一步步往河堤深处走去,往植物深处走去,往时光深处走去,风吹着他,像是吹着一片走向荒芜的落叶。我一边追着蝴蝶一边喊他,他好像什么也听没见,只管往前走着,他走过一片树,又走过一片树,直到走到一片暗影里,我再也看不见他。
后来我一直在想,父亲那天到底听见我的喊声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