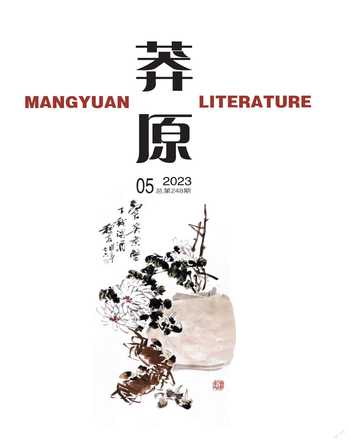从“尖尖角”到“半遮面”的人性形而上与艺术性
蒙克
摘要:就徐清松由专业性的文学评论为导引建构该文本的创意,追求异质性写作与对人性从形而上的解构进行探赜,一定程度上构成了阅读与理解的难度。故事套故事、碎片化、互文性是该文本的主要特征,笔者借以故事中三篇评论和评者,从他们各自生活着眼进行梳理,呈现三位论者不同的心理与思维路径,深入小说文本架构与艺术园圃,以此展示徐清松对人性隐性与裂变进行透视与缝合,实现异质性写作的拓展与突围,给人启示与思考。
关键词:元小说 出轨 人性 异质性 艺术性
在当前小说创作越来越同质化倾向下,如何突破与创新,具有创新性思维与野心的小说家无不进行着尝试和突围。徐清松的短篇小说《一篇由三则评论拼贴而成的小说》[1] ,文本具有很强的突破性。
小说以评论的方式解读了一个碎片化、男女主人公称谓模糊的出轨故事。严格地说,这属于后现代元小说。其特征为:故事套着故事,碎片化,互文性,出轨双方人物性格无指向的陌生化表达……等等。文本最大的实验性在于,故事以写评论展开,使核心故事“我想出轨了”成为故事内部道具而被碎片化地分布在三篇评论之中。仿佛一件精美的收藏品,无意中被失手打碎,已无形状,交由三位技艺高超的工匠修复。
小说中的三位评论者,前两位是受邀进行专业性评述,而后一位仅仅是从阅读感想而论,他们从各自生活为着眼点出发,评述故事中男女主人公是否有出轨的可能,带出三位论者不同的情感心理与评判,以及隐秘的人性裂变和反叛精神的不确定性,文本的实验性和作家对异质性写作的尝试与创新,使得读者在阅读与接受上有一定的难度与困惑。笔者将从三个方面,对文本做全面分析、阐述,抵近作家创作意图与用心。
一、小荷才露尖尖角:文本耀眼的人性锋芒与异质性
对于以评论为主体评其碎片化的小说给读者复述出一个圆润和完整的故事,其难度可想而知。其一,作家要具备小说评论的专业水准,通常的小说家只是单一地创作小说故事,不具备文学评论的能力;其二,故事在评论中得以展开情节和体现完整性,这个难度又要求高超的驾驭评论和故事的双重表现力,而不是单一地为写评而写评,更不是要插入故事为展示人物、情节、事件等的全面书写,是适当地进行引入和克制地进行评述;其三,写婚外情的出轨,表现故事中人物从精神到肉体出轨的可能性事实,是高难度的,囿于故事的碎片化,既要精准对位,又要考虑故事的圆润与引力,否则就会有理论的僵硬与枯燥,而缺乏故事的质地与意蕴。作家处理得非常好,一是他既写小说又写评论,有着两栖性;二是他有强大的对元小说创作的创意与构想,抱有强烈的追求异质化写作的愿望。在后现代元小说这块沃土上,徐清松不断地耕耘,之前发表于 《西湖》 的小说 《一个句子对作者和读者的抵抗》[2],写的也是“出轨”故事,但其中的主人公在出轨边缘及时止步;而 《一篇由三则评论拼贴而成的小说》同样写出轨,却没有悬崖勒马,反而有大肆喧嚣、大刀阔斧地进行到底的坚决。当然,前者主人公已接近中年,是异地出轨,而后者男女主人公较为年轻,又在同城,有一定的反差。并且,从写作手法上看,后者文本的难度要高于前者。
我们先了解一下文本中碎片化故事的大意,引用文本中的概括:
短篇小说《我想出轨了》故事并不复杂,讲述了一对夫妻“我们”中的一方已经不在婚姻状态了,与另外一位“异性同事”(构成了“他们”)的三次“单独在一起的幸福时光”。
小说中既没有鲜明的人物形象,也没有鲜明的人物性格,更没有连贯的故事情节。[3]
显然,小说故事的内核是“我想出轨了”,但小说家未就此大尺度地展示其肉体与精神上的描摹,而是极克制、极简约地在三篇评论中碎片化地抽丝剥茧,根据每个论者不同的精神向度给予重塑。小说以“我想出轨了”为诱饵,做道具,不咸不淡却抓挠读者的心,在故事开篇有“小荷才露尖尖角”的稚嫩和娇艳,极具诱惑力。由此笔者觉得,徐清松仿佛一个偷工减料的建筑商,为节省成本,他不按套路出牌,弄出了在这之前他的那篇《一个句子对作者和读者的抵抗》中所称之为“四不像”的文本。
这篇小说是由三篇评论拼贴而成,文本中的三位评者:评论家、作家、研究生,好比三位厨师,用同一品种食材,各炒各的菜,色香味完全不同。但是就文本的意蕴与人性的内涵,既带有雷蒙德·卡佛笔下人物的焦虑症和紧迫感,又内含着菲利普·罗斯 《乳房》里对欲望的无限膨大而对身份认同感缺失所彰显的模糊与迷离,更有贝克特对 《等待戈多》 的既有则有既无全无的渺茫与无指向的演绎,三方论者各自的俗世生活与小说评论交织成一张紧密、张弛有度的情爱隐秘之网,将人性内核捕捞上岸。卡耐基在其 《人性的弱点》 一书中用弗洛伊德的话举例,一个人做事的动机不外乎两点:性冲动和渴望伟大[4]。在笔者看来,前者是本我的实现,后者是超我的升华。“我想出轨了”是故事的内驱力,也就是弗洛伊德界定的第一人格——本我。三位评论者借助“我想出轨了”演绎各自本我的感受和“渴望伟大”的人格魅力。这似乎正是作家借助三位主人公在文本中建立人性峰值,给予透视和解构,彰显文本的异质性与创新性。
从人性视角解析,可以概括:一是“评论家”对现实生活中助手小薇暗怀的占有是初露,是人性內在的涌动,是一种潜伏状态;二是“作家”借助酒力对美女学员的欲念做了初试,并就找到最终谁是《我想出轨了》 的作者做了探寻构想,是将欲望付诸行动的一派;三是“研究生”最大的兴趣是探寻故事出轨双方肉体白热化看点,对其同居男友已然产生更换的潜在涌动与表述,是随时随地做出反叛的实践型女性。三位论者,恰恰构成了小说故事情节的律动,演绎“我想出轨了”这个故事内核的实质,缝合了故事情节的空档,让人性形而上的辨识度具有了戏剧性的微妙与意韵,文本的实验性旨趣突破了传统边界。
作家徐清松试图对人性做出渐变透视与观照。一方面借助修复故事的本我肌理,另一方面在以打碎故事与人格的方式内审人性的多面性,以模糊学原理实现“渴望伟大”的再度重塑的可能,呈现给文本以耀眼的人性锋芒,建构一种异质性,抵达创意写作实验的突破和建构自我异质化的创作路径。无疑,该文本已呈现了这一主旨,给人以异质化审美效应。
二、早有蜻蜓立上头:人性欲念的站位与文本的构建
小说中的那一对男女的出轨,第一次是在单位加班,第二次是在“轨道咖啡馆”,第三次是在出租屋。故事的内核(也视为道具)隐含在三篇评论之中,分别以开端、发展、高潮为结构,正如引文所讲“并不复杂”,而复杂的是这三篇评论,小说中的“评论家”“作家”“研究生”三者的评论是导引,但是,三人各自写评的前前后后的生活经历为“我想出轨了”的故事做了不同程度的弥补和双关,与其说是在做评述,毋宁说是在揭示三位论者各自怀有出轨的隐秘心思。
第一位“评论家”。他是一位在文学研究所供职的专业文学评论家,受邀对 《XX》文学期刊“某某省小说专号”写点评,这里的时间为“2026年”,是一种超前时间的定位,这是后现代元小说写作的一个特征。或者说,这是元小说作家们写给未来的小说,是对未来某个时间节点的一个期冀,期待在那个时候能完全被认知和欣赏。正如卡尔维诺那篇《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是写给千年之后(姑且这样认为)的读者的。这个时间的定位,在“作家”和“研究生”的章节里都有表述,并且是临近2027年的春节,这就给已出的“第13期”写评从时间上带来紧迫感和焦虑。
“评论家”早已不再写期刊综评,这次是碍于 《XX》文学期刊主编的面子。而其中那篇《我想出轨了》的小说引起了“评论家”的注意,并决定写这篇小说的评论。如果仅就以评刊作为小说故事的发端,无疑会过于理论和生硬,不论是对故事还是对“评论家”本人都没有生活氛围和情调,人物也更会显得平板和单一。好在小说为“评论家”设置了一个助手,那个身材苗条的小薇。在这里并不是“评论家”看到 《我想出轨了》 才对小薇产生暧昧或者说暗恋,而是早就有所心动。“评论家”由2027年羊年春节的到来,看到大街小巷挂着“羊年的图像”,内心产生这样的感念:
我喜欢温顺的小绵羊,觉得它们湿漉漉的目光特别像柔媚的女子,默默地望向你的样子,让你心生怜惜。准确地说,小薇就有一双那样清亮的眸子,并不善睐,也并不狐媚,但是她定定地看着你的时候,你心里的不安就浮现了。其实我们并没有什么,虽然我偶尔会想有点什么,但是又不知道她是否也想有点什么。[5]
“偶尔会想有点什么”是“评论家”孤寂的内心萌动,是雄性荷尔蒙驱使本我散发的燥热,真实呈现了对影星一样的小薇产生了暗恋或者说性爱的内心隐秘世界。小薇是有老公的,只是老公在国外,春节时回来过年,小薇在给“评论家”取完快递包裹后就去机场接老公了。“评论家”自己也认为和小薇没有什么,只是他自己心动——“偶尔会想有点什么”,不知道对方“是否也想有点什么”。这样的心理,对于一个已经心动的男人来说,是一种焦灼和煎熬,以至于看到小薇去机场接老公,一种焦躁涌上心头。小说的开端,就产生了这种要出轨的萌动。这是对“我想出轨了”的映射和双关。同时,文本中春节临近的生活场景,“评论家”赶写评论,因暗恋的人老公回来团聚感受到冲击,“评论家”的那种与卡佛笔下人物一样的焦虑症和紧迫感在此得以呈現。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评论家”的欲念在潜伏期,人性中有了站位,至于何时付诸行动,对他来说只是时间和机缘问题。这恰是小说开端设置的隐秘所在。
第二位“作家”。“作家”也同样是受邀写评论的,与“评论家”不同,他是被一向敬仰和尊重的女编辑指定来写《我想出轨了》的评论,理由是他“个人生活方面比较放得开”,并且向他透露:“作者虽然是化名,但是你见过其人,上次在省城文学培训班上,我们一个桌吃的晚饭。”“作家”生活在县级市小城,距离省城的 《XX》 文学期刊80公里,每次有活动或饭局,带上小城三两个文学爱好者开车不到两个小时就能来赴会。他的“放得开”是每次所带的女文学青年,饭局上或者饭后酒醉受到女文学青年的特别“关照”都被女编辑尽收眼底,才被标以“个人生活方面比较放得开”。确实,“作家”也是趁醉酒:“右手死死地揽住她的腰部,然后摸摸索索地把左手搭在她的右肩头,这才站稳。迷离的路灯下看不清对方的表情,但是馨香的喘息声在我脖颈处起伏不定,搅扰得我心神不宁。在微风的吹送下,柔软的长发不时拂过脸颊,拂得我脸痒、脖痒、心痒,便情不自禁地扭头将脸深埋下去。”“作家”在这里比“评论家”更前卫一些,他心有所动就付诸行动,不论对方是否接受,就像那首歌所唱的“爱了就爱了”,是亲力亲为的一派。
尤其得知 《我想出轨了》 的作者是“上次在省城文学培训班上,我们一个桌吃的晚饭”里的某一位,“作家”用排除法,排除了写诗歌和写散文的两位作者,判断出“从小说内容上看,深受杜拉斯和张爱玲影响的豪放女可能性大一些,但是从现代派手法来看,似乎卡夫卡的徒子徒孙络腮男更大一些。”并决定下次去老丈人家的B城,约上这两个人,三人聊文学探听哪位是 《我想出轨了》 的作者。由此可以看出,“作家”的“放得开”,是内心有所想的执行者,是菲利普·罗斯 《乳房》 式的欲望无限膨大的制造者,是对身份认同感的缺失,要找寻到准确称谓的不达目的不罢休的追踪者。尼采说:“人要么永不做梦,要么梦得有趣;人也必须学会清醒:要么永不清醒,要么清醒得有趣。”[6]“作家”要找出 《我想出轨了》 的作者,就像贝克特的 《等待戈多》那样有一种坚定的执着,是揭示谜底,要“清醒得有趣”的一种筹划,但无论找到与否,都不能解决《我想出轨了》 的主人公称谓的指向性,也不能寻得到生活原型的“他们”和“异性同事”,或者仅仅是出于“梦得有趣”吧。从“作家”这一章节的书写,为揭示 《我想出轨了》的故事的模糊性,增添了戏剧性,故事情节脉络逐步明晰。
第三位是“研究生”。她阅读 《我想出轨了》 前后的情绪变化,她的评论,准确地说,是读后感,既符合她作为女性审视这篇小说所给出的猜测,也符合读后感对出轨所做的分析和探究。作为一个追韩剧的粉丝,对出轨戏的理解已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认知,“研究生”从精神和肉体双向来分析文本,而文本在这方面又是那种白描式的叙事,带给这位看惯了性爱大尺度表现的“韩粉”内心既痒痒又燥热的拷问:“如果我们必须选择,是愿意选择肉身出轨,还是精神出轨?是‘出城还是‘入城?而这之间的意义边界又在何处?”而文本没给出任何一种答案,全凭借读者自己用想象来填补空白。
“研究生”读完这篇小说已经是深夜11点,其男友去给比导师小二十岁的第三任小师娘庆生日还未归,引起她的强烈不满,决意要更换男友:“再不回来,老娘就要换人
了。老娘人选多得是!”潜意识中表达着直接更换“人选”,而不是要去“出轨”的偷偷摸摸行为。何况“出轨”与她搭不上边。她是同居而非婚居的性质,随时都可能分手另寻他处他人。“研究生”的心态是明朗的,表达的意愿非常直接,合则聚,不合则散。同时她的情绪化与她的年龄和未婚有一定的关联性。她既不像“评论家”那样暗恋,也非“作家”那样有着“花花肠子”一样的油滑,她是青春的,血气方刚,更是直接而干脆,属于“甩你没商量”的一代,人性里饱含一种攻击能量。
对于出轨,或者说对婚姻家庭的背叛,如果说 《我想出轨了》 的碎片化故事是用以发酵的酵母,是“小荷才露尖尖角”的人性隐秘的初露,那么“评论家”的暗恋和“作家”的“想了”就付诸行动的那种谋划,已经不止于“才露尖尖角”,而是“早有蜻蜓立上头”的欲念站位,尤以“研究生”最为明显——她有“飞走”和甩掉男友的想法和决心,她的观念中具备着像弗洛伊德所说的“渴望伟大”的魄力,有着实现自我独立与尊严的价值目标。性爱仅仅是冲动的前提,而实现人格“渴望伟大”需要魄力——内驱的执行力。文本中“我想出轨了”的“想”是欲望的流露和性冲动,是预谋,是行动的进程,而“出轨了”是终结,是对本我的突破,走向“渴望伟大”。“研究生”的这种“渴望伟大”,符合未来——00后青年人的特质,叛逆得直接,且毫不含糊,是梦幻与现实都“清醒得有趣”的人。人性隐秘的裂变在三者身上流溢出不同的纹理和色彩,为故事的连贯性做了一定的缝合,具备了浓厚的现实生活趣味和形而上的叩问与追索。文本在此达到高潮,完成小说故事完整性,同时也拓展和突破了当下小说的艺术园囿。
三、千呼万唤始出来:人性形而上与“半遮面”的艺术性
互文性在这篇小说里无处不在,体现出文本的思想架构与艺术能指。
首先看“评论家”的菜肴。他是从人性的精神与肉体的二律背反来阐述出轨的可能性。“评论家”引入马洛伊·山多尔的《烛烬》做了互文,以增强两篇文本写作上的相似处,表明出轨的不确定性。我们知道“评论家”有暗恋助手小薇的隐秘心理,他能否与小薇这个有夫之妇做出“出轨”之事,我们从他的评论中就能嗅到:
事实上,这篇小说就出轨这个事实而言,如标题所示,“想”也就是起于想,而止于想。在后面第二、第三次“单独在一起的幸福时光”的叙述中,作者在将主人公内心焦虑更加深化的同时,依然让人物在肉身和精神的二律背反中游来荡去,从而增强了小说主题意蕴的模糊性,将小说意义指向推往更为宽广的多维性空间。[7]
“评论家”对小薇能否迈出出轨的步伐,他似乎也在“肉身和精神的二律背反中游来荡去”,“‘想也就是起于想,而止于想。”他的评论自然带出他对出轨判断的模糊性和人性内在裹挟着既有悲观性又珍重当下生活的满足感。何也?因为当他经历过了“2020年的春节,新冠让多少无辜的百姓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那场劫难,在2027年的春节即将到来之時,他要在大年初一凌晨四点就起床,看羊年的第一缕曙光,认为“活着真好”。他的情感世界储满了对生活、对世事的满足感,不想再经历任何的不论是自然灾害还是人为的劫难,能很好地活着,感受生活幸福就是人生的最大快乐。因此,他以形而上对小说人物的精神内涵进行分析,认为“女人往往是从故事变成事故或事实,而男人往往从事实变成事故或故事”,得出“‘想也就是起于想,而止于想”这样的论断。他呈现给我们的这道菜的口味是不咸不淡的适中。出轨故事也正是从“评论家”这里,作为发端向前推进,为阅读做了提速。
第二道菜是“作家”的。他与“评论家”一样是受邀请写评,但他是被指定写“出轨”这篇,理由是他“放得开”,虽然带有些许的戏谑,但他确实是有故事的人。他的评论是“不确定的确定性”,他比评论家更进一步给出这样的判断。他引用了贝克特的荒诞戏剧 《等待戈多》 作为互文,陪衬 《我想出轨了》 也是“什么也没有发生的戏”,“却又让人期待会发生点什么的戏”,符合他的“不确定的确定性”。接着他又进一步以残雪的 《五香街》 互文,从形式上 《五香街》与 《我想出轨了》 有相似之处,那就是评论大于故事,碎片模块化,评论是一个放大了的光环,而实际问题只是这光环中万分之一点。互文性在小说中很占比重,起到了很好的陪衬、补缀和双关,加深对故事内核的破解和诠释。
在“放得开”的“作家”分析中,出轨双方的暧昧味道变得浓郁,这就是“有故事”的“作家”的故事性心理:
在接下来的讲述中,他们又转换了话题,直到蜡烛被夜风拂熄,“他们”中的一方说我冷。另外一方就绕过面前的桌子,将对方这边的那扇窗户关严实,然后将身上的羽绒服脱下来,摸索着披在对方身上。而对方却把靠近这方的羽绒服敞开一个空位,这方就把上半身拱进来,将脑袋挤进一个“暖烘烘的温热之所”,度过了第二次“单独在一起的幸福时光”。[8]
如果没有这样的分析,碎片化的故事就显得模块、生硬,失去故事的趣味和质地。从评论中我们可以看到“出轨”故事没有那些大尺度的描写或对人物精神和心理的关照,从而为评论者对“精神和肉体”出轨的可能性猜测构成很大篇幅的讨论,模糊性、不确定性、无指向性构成一张大网笼罩在故事中。但在“作家”这道菜里,已见出轨端倪。就像“作家”已经知道这篇小说的作者出自和他们一起吃饭的某一位,只待他进一步找机会去识别,定能水落石出。对“出轨”最终的走向,也像《等待戈多》那样遵循一种坚持,结果可能有所预料也可能无所预料,但都不重要,重要的都在过程中拥有了故事性的意义和人性中的那份显现。“不确定的确定性”也正是基于此,让小说高潮的到来像鼓满了风的船帆。
喜欢追韩剧的“研究生”,“出轨”这篇小说对她的吸引力,就像她读后感所评述的“似是而非或似非而是”,孱弱而模棱两可。小说在这一章节,就进入了尾声,是谜底揭示的时候,是“出轨”能否成行和呈现的精彩部分,是故事的高潮。这道菜火候和时间要求厨师拿出看家本事,不可以有“关键时刻掉链子”或“书到用时方恨少”的尴尬。不论文本内的评者还是文本外的读者,都在为这个收尾工程望眼欲穿极具期待,要印证“狮头,猪腰,豹尾”这样一个成功的文本,而不是像“扶不起的阿斗”那样成了“烂尾工程”。但文本绝不会在此处偷工减料,即便是“减料”,那也一定是别具一格的创意。
“研究生”从出轨男女是否抵达具有“性爱”这个标志性的出轨实质展开探寻和分析。由女性视角审视,“研究生”分析得细致入微。如对第一次:“他们又待了20分钟,方才离开办公室”,“这段时间究竟有没有肉身出轨”?第二次因停电室内冷,一方将羽绒服披给另一方,一方就敞开一个空位让另一方拱进来,“研究生”的好奇就要探寻:“究竟拱进来多久?拱进来之后呢?一直躺着?还是干了其他什么事情?”这里体现了“研究生”女性细腻的心理和对细节的分析。对第三次二人“单独在一起的幸福时光”的分析,依然是最关键部分,这跟前两位男性的评论完全不在一个维度上。“评论家”是以大概念“精神与肉体”做探究,“作家”是从怀疑论上放大出轨的可能,而“研究生”则是细致入地观察其色彩,聆听其声音,拷问是躺着还是干了其他事情,并分析“既然已经有了精神的碰撞,那么其他碰撞不是自然而然的吗?女人不都从心到身吗?如果隐含的叙述者‘TA是个心猿意马的臭男人,那么是否意味着是从身到心,再回归身?”尤其对第三次出租房里“这‘吱嘎是坐在床上的声音,还是人们想象中的声音,依然无法“确认‘他们该发生的都发生了,不该发生的是否也已经发生了?”对这种拷问,体现了“研究生”的细致和细腻,不放过任何一处蛛丝马迹的可能进行追踪。无疑,性爱是00后“研究生”的看点,也是判断出轨的决定性证据。
而上升到理性评判的是,“研究生”通过以卡尔维诺的 《不存在的骑士》 进行互文,融入哲学形而上讨论。就肉体与灵魂的互相依存,“是选择肉身出轨,还是精神出轨”这个问题虽然概念化,却反映出“出轨”是否有真爱的可能,也就是说,选择肉体的话,是本我的表现,也就是弗洛伊德关于力比多的阐述,是出于动物性的本能需要而发泄;如果是精神出轨,则是上升到超我,从而达到完美主义,实现理想化的自我价值,意即“渴望伟大”。“渴望伟大”有着征服含义,也就是一方征服另一方,以精神的力量,而不是本我力量。“研究生”从出轨者的“第三次待在一起的幸福时光”中嗅到了大尺度气味,单从字面上并不确定真正意义的出轨,正如“捉贼捉赃”“捉奸捉双”,要有足够的证据,她只是综合了多种因素感觉到了“出轨”的意蕴,只能用“似是而非,或似非而是”这样模棱两可、含糊其辞的不确定性来评定。
纵观三位评者在各自的评论中,对出轨的分析、互文、解构,尽其所能,使出浑身解数,有着“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羞赧和遮掩,停止在隐秘而模糊上,未见“庐山真面目”。该文本的“半遮面”藝术效应,似乎应和了《等待戈多》的结局,自始至终都是落空的等待。唯有在这个过程中,三方论者的“故事”才构成了故事性,窥探到人性隐秘的内核,人性的隐秘性在此昭然若揭。三方的评论事实上为“出轨”故事做了一定的补缀和双关,将碎片化的故事艺术性地黏连、整合,有声、有色、有情调,有了质感和纹理。
小说家徐清松的这篇实验性文本,不论是对传统小说,还是对后现代元小说,都是一个具有突破性的创意,彰显作家独特的创造个性和异质性写作追求,给人启示与思考。该创意写作奇特而不怪异,先锋而不诡谲,收敛而不龟缩,理性而不概念,具象而不泛滥,尖锐而不俗世。作家立于异质性写作起点,向广远延伸。
注释:
[1][3][5][7][8]徐清松:短篇小说 《一篇由三则评论拼贴而成的小说》,《青年作家》2021年第2期.
[2]徐清松:短篇小说 《一个句子对作者和读者的抵抗》,《西湖》2017年第4期.
[4][美]戴尔·卡耐基,袁玲译:《人性的弱点》,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8年1月.
[6][德]尼采:尼采名言第1条,51贴图网,https://so.51tietu.net/ct/ltx823767.
责任编辑 丁 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