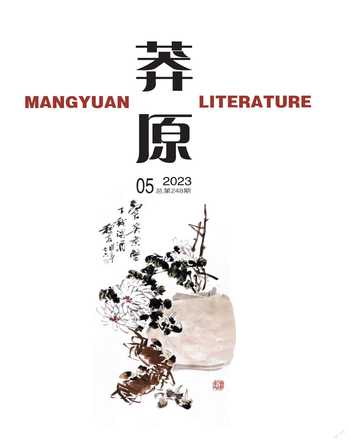隔墙有耳
孙晓燕
推荐语:
隔墙有耳,乃因隔墙有人。
只要有人,便难免是非:被他人冒犯,或冒犯他人。
比如金媛:她的婆婆常偷聽她和丈夫的声音,她成了被冒犯者;而当她搬到新家,她和丈夫的声音又影响到了患病的邻居,她又成了冒犯者。
人与人之间应该有边界,也必须有边界。一旦边界被人为破坏,和谐也将不复存在。
金媛看见许多只耳朵突然从地底下长出来,像雨后的蘑菇。它们爬上墙壁,攀上窗台,有几只耳朵贴在窗上,一只特别长的耳朵从窗缝里钻进来,伸到了床边。它的耳垂儿上有个小洞,她认出那是婆婆的耳朵。婆婆常拿着一根用钝了的牙签,探测耳前小洞的深度,眯着眼睛,表情满足地说,这是个富贵洞啊!
在婆婆的耳朵大张着,似要急切地打听什么。
金媛尖叫起来:“出去!都搬出来了,你还来偷听啊……”
方德运睡在客厅沙发上,听到动静,鞋都没顾上穿,光着脚跑过来,摇醒金媛:“你说梦话的毛病越来越严重了。做梦都跟我妈吵架,声音这么大,楼下在群里投诉呢!”
金媛睁开眼睛,意识到自己又做梦了,她抹了一把眼睛,拿起手机,看到单元楼微信群里102业主在抱怨:“202业主你有没有点素养啊?讲不讲道德啊?大半夜两口子吵架就不能小点儿声,你以为这是在你们村呢?”
看着一串问号,金媛脸上的肌肉拉紧了。
金媛为了逃开婆婆的耳朵,从原来的大房子里搬出来,搬进了这套小房子,可没想到房子小了,窗外的耳朵却没少,大小有些动静,就会招致楼下邻居的呵斥甚至谩骂。
她跟方德运刚结婚时,婆婆总爱窥探他们小两口的私生活。有一天晚上,小两口亲热完了,金媛觉得有些饿,想出去找点吃的,一开门发现婆婆弯着腰,正把耳朵贴在门上偷听。被发现后,婆婆大大方方地直起身来,说了句:“日子长着呢,节制点啊。”从那以后,金媛就开始变得畏首畏尾了,甚至对夫妻间的事也没了起初的兴致,以至于结婚两年多了一直没要上孩子。
金媛是个丰乳肥臀的女人,走起路来屁股一扭一扭的,让男人们想入非非;方德运个子偏瘦,嘴巴偏大,嘴唇厚实,是个男人不会羡慕、女人也不会讨厌的男人。两个人从外形上看,像同一棵树上的两根枝条,一根粗壮,一根细弱。婆婆常说屁股大的女人欲望强,怕瘦弱的儿子吃不消。
那时候,他们还住在一起。婆婆经常出去打牌,总是用牙签顶着耳垂儿上的小洞,跟牌友们说金媛天没黑就拉着男人,不让他出来;说两个人整天粘在一起,也没能怀上孩子……人们听了她这话,心领神会地捂着嘴笑。
金媛有些懊恼,就撺掇着方德运搬了出来。这是一个回迁小区,虽然是城中村,但离市中心也只有两站地,许多人都来这里找房子,小区楼房的外墙上贴满了出售和招租的小广告,原来的广告被物业铲除了,新的广告又贴上去。墙上白一块红一块,像一些刺眼的补丁。金媛从一个拆迁户手里买这套二手房,原本为了逃开婆婆的耳朵,却又遇见了102的耳朵,难道自己真的无路可逃了吗?
好好一个回笼觉被搅醒了,金媛看着102业主的头像,歪着脖子说:“我在自己家里说话还要受你限制?想清静怎么不住别墅?”她是过敏性体质,每到春天,花粉都会引发鼻炎,说话时带着浓重的鼻音。
金媛点开女人的头像,看到了她的个性签名:我坚强不催,我无所不能——好像对全世界的宣言。金媛撇了下嘴,冲着地板神经质地说:“一看就是个刁钻不吃亏的人。说别人没素质,自己的猫却不管好,把公共区域当成自己家了。”女人养着一只猫,经常在地下室窜来窜去。
“要不我们也养只猫吧,这样你就不用眼红别人了。”方德运说。
“我是眼红她吗?”金媛一下子坐了起来,懊恼地说。
“不是吗?那你因为什么?”方德运说。
方德运说话的声音跟他这个人一样单薄。一边说着,一边在床边坐下来。
金媛揪住了他的耳朵,压低声音却是恨恨地说:“耳朵,耳朵,怎么到哪儿都躲不开这些耳朵?我咋这么倒霉啊……”
方德运“嘿嘿”笑了,笑得有些无赖,也有些暧昧,一边脑袋就在金媛的低胸睡衣上蹭来蹭去。显然,他又想了。
但金媛这会儿不想。她把方德运的脑袋推开,又把睡衣往上提了提,裹得更紧了些:“别,别你妈又说我欺侮你。”
“可我就想让你欺负,我愿意。”方德运扑了一下,把金媛扑倒,顺势压在了她身上。
金媛这会儿真的不想,她看着他那黏黏糊糊的眼神,说:“今天你要去你妈那儿,别你妈见你没精打采的,又说我欺侮你。”
“我精神着呢,我妈看不出来……”方德运又用了一些力,他闻到了她身上温热的肉味,身体往边上挪了挪,想亲吻她的嘴。
金媛蜷了蜷腿,用膝盖抵住方德运的胸口:“别,你妈那眼睛,鸡蛋里都能挑出骨头,毒着呢。上次还说找我找错了,不如你的前女友,说我强势……”
方德运知道做不成了,也不再用强,但仍然没从金媛身上下来,说:“谁让你个子比我高,我妈是怕你欺负我。”
“我欺负你?”金媛用膝盖把他推了下去,跟着也坐了起来。
“不是吗?”方德运一向憷金媛,不知道她为什么总爱发脾气。“你说要就要,说不要我连边都沾不到;好好的大房子不住,偏要搬到这螺蛳壳里……”
“你倒怨我了,要不是你妈天天偷听,我能搬走吗?现在这房子虽然小,也是我花钱买的,住我自己的房子轻松,自由!”金媛真有点生气了。
但方德运没有生气,仍然笑嘻嘻的,说:“轻松吗?自由吗?你忘了楼下还有双耳朵呢。”
好像在为方德运证明,单元楼微信群里102业主又开始抱怨了:“楼上的缺不缺德啊,天不亮就折腾,周末也不让人好好休息啊!”同时,楼板就响起“咚咚”的声音,好像有什么在撞击。
金媛颓然倒下。
方德运看了看手机,3点20,说:“欧冠半决赛开始了,你再睡会儿吧,我看球去。”说着便急匆匆出了主卧室。
天亮前那么一折腾,金媛和方德运都起得晚了。因为方德运要去看他妈,来不及做早饭,金媛决定去门口早点摊儿买豆浆油条对付一下。
买了豆浆油条回来,金媛刚走进门洞,就看见一个女人长发一扬,闪进了102的门,只留下一个虚胖的背影,穿一件印花上衣,像一个棉花包袱。搬过来快两个月了,金媛还从未跟102的女人打过照面,今天看到的也只是一个背影和一袭浓密的长发,烫着大波浪,汹涌澎湃的样子,还有满楼道香水的味道。她耸了耸鼻子,又皱了下眉头,觉得女人那虚胖的身材实在配不上这一袭浓密的长发,也辜负了这么好的香水。
金媛一边沿着步梯上楼,一边在心里想,这是个什么样的女人呢?怎么这么多事啊?她家里还有什么人,能受得了她这臭脾气?这么想着,上了一半楼梯,金媛竟停下脚步,回头看着102的门,静静地听了一会儿,却什么也没听见。
回到家里,金媛跟方德运说她刚才看见102的女人了,说那女人的头发很好,用的香水也很好。方德运说他早就见过了,还说那女人不但头发好,眼睛也很大,很漂亮。金媛刚想骂方德运贱,方德运又说,可惜了,那么好的头发和眼睛配那么虚胖的一堆肉……金媛把骂人的话咽回肚里,回了他一个英雄所见略同的微笑。
“她家里还有谁,能受得了她这臭脾气?”金媛又提出疑问。
“不知道,只知道她养着一只猫,好像她从不对那猫发脾气。”方德运咬了一口油条,“你留心一下,说不定会有新发现。”
“我不像你妈,对别人的事不感兴趣。”金媛揶揄道。
“怎么又扯上我妈了?”方德运有些不高兴。
“不是吗?要是你妈在,趴在她门上听听,一切就都清楚了。”金媛坏笑了一下。
“我妈也是为咱们好嘛……”方德运为他妈辩解。
“是为咱们好吗?你的心被狗屎糊住了,你要真能说一句公道话,也算是个男人。”金媛抢白道。
方德运不再接话,几口喝完了豆浆,推开碗,用桌子上的一块抹布擦了擦嘴,站起来离开饭桌。金媛呸呸地冲着地上啐了两口,“真是你妈的儿子,用抹布擦嘴啊……”
金媛还想说什么,方德运已经走到了门口,说中午不回了,在他妈那边吃饭,就走了。
金媛懒得收拾餐桌,但不能不梳洗。这是她多年来养成的习惯,也是方德运给她惯下的坏毛病,早上起床后,一般都是先刷牙,再吃饭,然后才梳洗。她走进卫生间,对着镜子把头发拢到脑后,盘成了一个大发髻,看见肤色有些发暗,脸上竟有了沟沟壑壑,眼角也有了伞状的皱纹,觉得自己最近老了一大截。都是楼下那个女人,搅得自己连着几晚都没有睡好。这么一想,就再没有心思打扮了,草草洗过脸,抹了几下防晒霜,就开门下楼了。
他们这栋楼在小区的最后一排,楼后面就是围墙,地面倒是铺了花砖,可是很少有人经过,花砖的镂空处已经长出了野草,差不多到脚踝那么深了。金媛一边抱怨物业也不清理,一边蹚着草,一步步小心地往里走,野草扎进了她的裤子,弄得她小腿上有些刺痒。但好奇心驱使着,她还是继续往里面走去。
许是觉得靠着围墙,102的后窗竟然没有关,甚至没有拉上窗帘。金媛放慢脚步,假装找什么东西,低着头走了过去。走到102的后窗下,她佯作不经意地抬起头,看见那女人背靠窗子,坐在沙发上,怀抱着那只猫。那只猫趴在女人肩上,耳朵很长,两只蓝汪汪的眼睛看着金媛,女人倒一无所知。金媛放心了许多,高一眼低一眼把那女人看了个清楚。其实也还只是个背影——还是那件印花上衣,还是像棉花包一样虚胖的身材,她身上最吸引人的,仍然是披在肩上的大波浪卷发。因为背对着窗子,看不出她的年龄,不过从身形上看,应该不年轻了,三十多岁?四十岁?总归是不到五十岁吧。女人怀里抱着那只猫看电视,或许并没有看,她用手摸着猫的脊背,像是跟它亲昵地说话。客厅里几乎没有什么装饰,没有绿植,也没有字画,只有沙发、茶几跟墙上的电视。
金媛来来回回走了几趟,每一次都在102的后窗外停一会儿。她觉得还应该有更多的发现,女人正是承上启下的年龄,老人呢?丈夫呢?儿女呢?应该也有孙辈了吧,总不会就她一个人吧?然而,客厅里静悄悄的,除了女人,连个人影都没有。金媛有些明白了,一个独居的女人,肯定是渴望听到些什么声音的,不然,生活在棺材一样的屋子里,那该是多么寂寞无聊啊。所以她才总是处于聆听的状态,总能听到楼上金媛家的动静。这么一想,金媛忽然对女人的耳朵有了兴趣——这么一个女人,她长着怎样的耳朵呢?小巧的花朵耳?硕大的张风耳?她的耳朵上是不是也有像金媛婆婆那样一个富贵洞呢?可是看不见,女人的头发太茂密了,乌黑,油亮,蓬松,遮住了大半个脑袋,看不见她的脖颈,也看不见她的耳朵。那么,是怎样的一双耳朵,才能对邻居家的声音明察秋毫呢?
正这么胡思乱想,金媛忽然看到楼的拐弯处,走过来一个男人。男人也看见了金媛,抬起手,似乎想跟她打招呼。金媛心里慌了一下,转过身子,匆匆地逃开了。
回到家里,金媛还在想着102的女人。这个女人是干什么的?上班族?还是退休了?应该还不到退休年龄吧,可是怎么不见她上班呢?她怎么有那么多时间关注别人家里的事呢?
窗外楼下传来一阵刺耳的噪声,把金媛吓了一跳。她走到窗前,撩开窗帘看了一眼,见那个男人正推着剪草機在修剪楼下花砖里冒出的杂草。剪草机发出巨大的噪声,所过之处,半尺深的杂草纷纷倒地,好像被那狂躁的声音给吓趴下了。哈哈,这声音可比金媛两口子弄出的声音刺耳多了,而且就在102的窗外,等着吧,有好戏看了。金媛一边幸灾乐祸地想,一边站在窗口等待着。可等了好大一会儿,也没见102那女人有什么反应。难不成那女人是选择性耳聋?抑或是专门找她茬儿的?金媛愤愤不平地想。又等了一会儿,还是没有动静,金媛才失望地离开了。
从客厅到卧室,从厨房到卫生间,金媛转了一圈,终是无所事事,就在沙发上半躺下来,打开了电视。江苏卫视正重播“非诚勿扰”,金媛摁了一下遥控器,就翻了过去。一页一页翻下去,没有一个感兴趣的节目,又倒过来一页一页地翻,还是没有喜欢的节目。忽然想到婆婆最喜欢“非诚勿扰”,就重又找到江苏卫视,想知道这个节目有什么吸引婆婆的地方。男嘉宾刚刚出场,正在表达他的第一个愿望:“我希望女朋友不在意与我妈一起生活……”话音未落,嘣嘣嘣嘣,二十四盏灯就灭了大半。男嘉宾不知所措地看向主持人,主持人问男嘉宾为什么强调要与母亲一起生活,男嘉宾说他幼年丧父,是母亲一个人把他抚养大的,他应该给母亲一个幸福的晚年。嘣嘣嘣,剩下的灯又灭了大半。主持人点了一个女嘉宾的名字,女嘉宾说,她理解男嘉宾的孝心,也愿意同男嘉宾一起尽孝,但不能接受共同生活,因为代沟的差异,生活习惯、三观问题、个人隐私,共同生活会产生很多麻烦和矛盾。嘭嘭嘭,剩下的灯全灭了。男嘉宾的第二个愿望也不用讲了。按说男嘉宾可以直接退场了,但主持人让后台播放了男嘉宾的个人资料——果然是一个感人的故事,男嘉宾的母亲靠捡垃圾抚养儿子,供他上学,受尽了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好几个女嘉宾都感动得哭了;男嘉宾从小学读到大学,从国内读到国外,学成回国后,自主创业,不到四十岁就成了一家上市公司的老板……很励志,很感人。主持人先赞扬了男嘉宾的母亲,毫不吝啬溢美之词,转而又说:“母爱是伟大而无私的,但母爱是对自己的儿女而言的。婆婆永远是婆婆,不可能变成妈妈。婆媳关系最好的状态应该是相互尊重,保持距离……”
金媛早就看不进去了。男嘉宾的家庭与方德运有相似之处。方德运的父亲是个厅级干部,四十多岁死于出差途中的一场车祸,属于因公死亡,有一大笔抚恤金,加上生前的高工资,虽然方德运才上初中,他母亲只是个中学老师,但优渥的生活一点没受影响。而且,方德运的父亲去世后,他母亲对他更是呵护备至,关爱有加。金媛与方德运是大学同学,他看上的是她的美貌,她看上他什么呢?金媛至今都说不清楚,只记得三年多时间里方德运对她穷追不舍,一个官二代加富家子弟,能放下身段天天给她打饭,为一根哈根达斯能三更半夜跑遍全城买来送到她手里,大小节日都给她买礼物,没有节日编造节日也给她买礼物……金媛被方德运这份诚心打动了,忽略了他平平的相貌,也忽略了他的原生家庭。但结婚后才发现,因为少年失怙,方德运的母亲就特别害怕他受欺侮,甚至怕金媛对他关爱不够、照顾不周,更怕高出一头的金媛欺侮她这个宝贝儿子。方德运的衣服都是他妈买的,一日三餐也都是他妈做的,有个头疼脑热,更是乖啊宝啊端茶送水,恨不得亲自把药片喂到她儿子嘴里。金媛倒是乐得少操闲心,也乐得远离厨房的油烟味儿,关键是婆婆做这些时,总是抱怨金媛不知道心疼男人。更让金媛不能忍受的是,婆婆有双兔子一样的长耳朵,但凡这边卧室有点动静,婆婆在那边卧室不是咳嗽,就是打喷嚏;就算没有动静,婆婆也会悄悄来到他们小两口的卧室听房。终于忍无可忍了,金媛才不管不顾地从那套大复式里搬了出来。一开始方德运还在犹豫,婆婆更不同意,但金媛以离婚相要挟,才总算如愿以偿。
这么想着,金媛竟有些恍惚,她看见窗外刚刚被修剪过的草地上,花砖缝隙间长出了许多蘑菇。那些蘑菇爬上墙壁,攀上窗台,变成了许多耳朵贴在窗上。一只特别大的耳朵从窗缝里钻进来,向她伸来,这只耳朵上有个小洞,她认出那是婆婆的耳朵;还有一只耳朵,咝咝地往外喷着香水,浓烈的香水味一直飘到她枕边,弄得她昏头涨脑浑身冒汗,她知道是102长发女人的耳朵。那些耳朵越来越大,越来越近,好像要把金媛吸进去……
金媛大叫一声,醒了。窗外已是暮色苍苍。
方德运是和他妈一起回来的。金媛没想到婆婆会来,一时有些不知所措。方德运解释说,妈这两天头疼,明天带她去省医看看。他们住的这个小区离省人民医院很近,方德运这么说,金媛自然不便多言。
婆婆一眼就看见了没有收拾的餐桌,说,还是早上的剩饭吧?午饭没吃?接着就抱怨开了,说自家男人不照顾也就算了,自己的生活总该安排好,这哪像过日子的样子……一边说着,就要过去收拾。
金媛赶紧上前拦住,说:“妈,还是我来
吧。昨晚没睡好,不知不觉睡到了现在。”
婆婆看了看方德运,又看了看金媛,眼睛里充满了狐疑,似乎想说什么,咂了咂嘴,终是没有说,转身朝厨房走去。
“妈,您身体不舒服,晚饭我来做。”金媛又抢了一步,上前拦住了,“您去看电视吧,非诚勿扰,可以看回播呢。德运,帮妈把电视打开。”
她这话有些言不由衷。本来就没打算做晚饭,想等方德运回来一起去外面吃的,可婆婆来了,多了一张嘴不说,做饭也马虎不得。她之所以不让婆婆动手,更像一种主权宣示——这是她的家,她是主人,餐桌厨房都是女主人的领地,容不得婆婆这个客人插手。
金媛开始在厨房忙活。她真像一个家庭主妇了,腰里扎上围裙,油盐酱醋,煎炸烹煮,弄出一阵热烈的声音。客厅里,方德运在陪着他妈看非诚勿扰,她真希望这母子俩能看到那个男嘉宾的结局,让他们听听主持人关于婆媳关系的高见。可那个男嘉宾迟迟没有出场,二十四个女嘉宾倒是吸引着母子。婆婆说,德运,你要是去非诚勿扰,这些灯都得给你亮着。方德运说,那是自然,就你儿子这样貌、这风度,还不迷倒一大片?金媛撇了下嘴,心里说,就你这样儿,连报名都未必通过。说实话,金媛一开始真没看上方德运,她就是觉得他脾气好,待人真诚,还有他穷追不舍的精神。婆婆说,我喜欢三号这姑娘,你看那俩耳朵,肯定有福气。方德运说,不行不行,那招风耳太大了。婆婆说,大才有福呢,刘备就是这样,两手过膝,两耳垂肩。
金媛把做好的两个菜端出去,接着婆婆的话:“妈,两手过膝那是长臂猿,两耳垂肩那不成猪八戒了?”
“你懂什么,这才是富贵相呢。”婆婆用牙签捅着她耳垂儿上那个洞,很惬意的样子,“你们,也去参加非诚勿扰吧。”
金媛把盘子放到餐桌上,笑着说:“媽,我们都结过婚了。”
“有奖励的,免费旅游。”婆婆说。
“那我们离婚再去非诚一回?”金媛一本正经地说。
婆婆这才意识到自己说漏嘴了,扯了扯嘴角,讪笑了一下。
金媛进了厨房,继续热火朝天地操作。说实话,结婚这两年,生活有很多不满意,但她从没想过离婚,她拎得清,婆婆是婆婆,方德运是方德运,也说不上有多爱,可用眼下的标准看,方德运确实是个好丈夫,不吸烟,不喝酒,更不拈花惹草,对他妈百依百顺,却不是妈宝男;对金媛言听计从,却也有自己的原则和底线。就说从他妈那搬出来这事,能满足金媛的意愿,又安抚了他妈,就说明他是个小事糊涂大事清楚的人……
很快,剩下的菜也做好了,一一端出去,番茄炒蛋,清炒芦笋,红烧大黄鱼,辣子鸡丁,外加一个醪糟小汤圆,正好四菜一汤,连主食都有了。金媛对自己的作品很满意,对婆婆说:“妈,吃饭啦,尝尝我的手艺。”
婆婆却毫不领情,头都没扭一下,说:“你们吃吧,我身子不畅爽,没胃口。”
方德运站起身来,说:“妈,吃两口吧,也给你媳妇指导指导。”
婆婆仍然没动屁股,说:“家常便饭,不就是那两下子,有什么可指导的。”
金媛的热情顷刻间冷却了,便不再多说,先自坐了下去。方德运走过来,夸张地吸了吸鼻子,赞道:“嗬,有菜有汤,荤素搭配,色香味俱佳,老婆厨艺大长啊!”
金媛看了婆婆一眼,压低声音说:“热脸贴个冷屁股,不吃咱吃。”
小两口这边吃着,电视里,那个要跟母亲一起生活的男嘉宾终于上场了,嘣嘣嘣,一片灭灯的声音。婆婆就大声叫起来:“怎么啦?怎么啦?这是怎么啦?”
方德运吓了一跳,忙问:“妈,怎么啦?”
“儿子想跟娘一起生活怎么啦?”婆婆义愤填膺的样子,“家有一老,便得一宝,饭菜给你们做,衣服给你们洗,生了娃还给你们带,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金媛缩着脖子笑了一下,悄悄说:“指桑骂槐呢,咱俩也成狗了。”
方德运这才知道他妈在跟电视机生气,说:“妈,别人的事你生哪门子气,犯得着吗?”
“就是,别人的事我犯得着吗,自己还一屁股屎擦不干净呢……”婆婆站起来,拿遥控啪一下关了电视,扭身朝小卧室走去。
“我们躺枪了……”金媛终于憋不住,笑出了声,却被嘴里的菜呛了一下,咳嗽起来。
方德运忙给她又是捶背又是揉胸。
这是一套小三居,主卧大点,金媛两口子住,两个小间,一间做了书房,另一间做了客房。婆婆主动睡了客房,让金媛有些得意,看来婆婆还能摆正自己的位置,没有强做这家的主人。
小两口进了卧室,和衣躺在床上,金媛告诉方德运:“我今天偷偷去侦察了,见着102那女人了,没想到一个暴烈的女人,日子却过得那么寡淡。”
方德运说:“你懂什么,人家那是极简生活。”
“你才不懂呢,极简生活是简而不陋,是低调的奢华,她那个家,除了沙发、茶几,连个花草字画都没有,说徒有四壁都不为过。”金媛说。
“还有别的人吗?”方德运问。
“除了她跟那只猫,连个出气儿的都没有。”金媛说,“你说,她那个年龄,也没个男人,就不寂寞啊?”
“男人嘛,”方德运忽然叹了口气,“这儿倒有一个,有你也不用,你就不怕锈住啊?”
方德运这么一说,金媛忽然有些想了。实际上,金媛昨晚就想了。青春年少,干柴烈火的,能不想吗?要是不想,他们也不会搬出来住了。为买这套房子,金媛不但花光了结婚时的彩礼,婚前婚后的积蓄也都贴进去了。但她跟方德运不一样,方德运是一想就猴急,一急就直奔主题;她是越想越不着急,越想越从容。她觉得夫妻之事就像做一桌好菜,火候不到,再好的菜也吃不出好滋味。
“我才不怕锈住呢,我有防锈神器。”金媛从床上起来,走到衣柜跟前,从里面取出一个盒子,说,“给你看个好东西。”
“什么宝物?”方德运也坐了起来。
金媛诡谲地笑了笑,开始脱衣服。她像剥笋一样一层一层把自己剥开,露出全裸的胴体;又打开盒子,拿出一件黑色的、渔网一样的东西;双手一抖,那像渔网一样的东西就纲举目张了。
“情趣内衣啊!”方德运的眼睛瞪大了,“快,快穿上让我看看。”
“懂的不少,还知道这是情趣内衣。”金媛笑着,开始穿那件内衣。也没见她怎么费事,几下就穿好了。
这是一件性感吊带情趣内衣连身袜,紧紧地贴在她身上,像画上去的一样,她的胸更凸了,腰更细了,屁股更圆、更翘了;那疏密有致的网眼,组成各色图案,有花朵,有动物,透着神秘的诱惑。金媛款款走了几步,来到床边,一条腿踏在床上,一只手叉在腰间,歪着头,眼睛迷离地看着方德运。
方德运觉得金媛不是人了,是一个充满魅惑的黑色妖姬!
他嗷地叫了一声,把金媛扑倒在身下。金媛就势抱住了方德运,两个人像两条蛇,紧紧地纠缠在了一起。
忽然,金媛僵硬了身子,低声说:“听……”
方德运也停了手,听了一会儿,说:“没什么啊……”
金媛把方德运推开,悄悄地说:“躺好,你陪我说会儿话。”
方德运极不情愿:“说什么啊,这会儿我不想说,只想做……”
金媛把食指竖在唇边,轻轻嘘了一下,然后恢复自然状态,开始说话。
金媛说,从前啊,天上有一个神仙——方德运说,咱不说从前,说现在好不好?我不想听神仙,我自己想做神仙——金媛说,别打岔,你听我说。那神仙本来是带兵的元帅,可他不务正业,整天往仙女堆里扎,偷听人家的私房话——方德运说,你就是仙女,我不想听你的私房话,就想跟你做私房事。一边说着,一边就把手放到了金媛的胸上。镂空的胸衣很丝滑,比胸衣更丝滑的是下面的乳房,他感到那乳房软软的、热热的——金媛的身子颤了一下,她想把他的手拿走,可那手不肯走,她只好让它留在那里,继续说,仙女们发现了元帅这个毛病,就告诉了王母娘娘,王母娘娘施了法术,元帅每偷听一次,就让他耳朵长一寸;每偷听一次,就让他耳朵长一寸——方德运的手更不老实了,胸衣镂空处长出了一粒葡萄,硬硬的,凸凸的,他就用掌心轻轻地揉那粒葡萄,指尖顺势在金媛的乳房上画着圈圈——金媛感到很好受,又很难受,但她强忍着,她知道有人比她更难受,她就是想要那个人难受。于是,她继续说,元帅的耳朵越来越长了,像两个蒲扇。有一天,元帅刚把耳朵贴上去,门突然开了,又突然关了,元帅的耳朵被夹在门缝里,疼痛难忍,惨叫一声,打了个滚,就投胎到了人间的猪圈里——方德运说,你说的是猪八戒啊还是匹诺曹?
金媛嘘了一声,一下子翻身下床,蹑手蹑脚地朝卧室门口走去。她轻轻打开房门——婆婆靠在门框上,打着长一声、短一声的呼噜,竟然睡着了!金媛冷冷一笑,大喊了一声“妈”,婆婆惊了一下,睁开眼睛:“啊?我这是怎么啦……”随即看见金媛那一身吊带内衣连身袜,看着她性感而魅惑的身子,好像突然明白過来,觉得失了面子,几乎连牙上的劲都用上了,叫道:“金媛,你是间谍啊?”说完,也不待金媛回答,转身就回到了小卧室。
方德运从床上坐起来,问:“咋回事?咋回事?”
金媛终于憋不住了,放肆地大笑起来。其实,她早就察觉到婆婆在门外偷听了,所以才中止了跟方德运缠绵,把话题引到一个瞎编乱造的故事上,她忍受着方德运的挑逗,方德运猴急,她也很急,她知道门外的婆婆更急,可她引而不发,就是想看看婆婆会坚持多久。没想到婆婆坚持不住了还在坚持,终于把她自己坚持到了梦里。
“太可笑了,你妈太可笑了……”金媛笑着,把自己扔到床上,就势翻了个身,压到了方德运身上。
两个人早就急不可待了,方德运开始手忙脚乱地脱衣服,金媛也帮他脱,说不清是他自己脱光了,还是金媛把他活剥了,他们很快就连到了一起,齐心协力共赴最温柔最激烈的战场。方德运的身子起伏如海浪,拍打着金媛,也冲撞着金媛,一波连着一波……金媛便在这海浪里恣意沉浮,撩拨他,也鼓励他,期待着更大的滔天巨浪……浪涛便真的猛烈起来,在鼓噪中,在呐喊中,如同万马奔腾,层层叠叠,前推后拥……在每个巨浪跃到最高峰的瞬间,金媛也仿若一朵欢快的浪花,凌空开放,又缤纷落地……
方德运拿起手机,笑着说:“嘿嘿,楼下的快发疯了,骂我们呢,又撞楼板了。”
“别理她,有本事她把这楼给拆了。”金媛起身,从衣柜里取出一件干爽睡衣,换下那件吊带内衣连身袜,又抓起方德运的外衣内裤,扭着腰肢,去了洗手间。
一大早,方德运就领着他妈去了医院。因为可能要抽血化验,他们没吃早饭。
金媛一直睡到九点多才起床,简单洗漱了,热了昨晚剩下的饭菜,随便对付了一顿,就打开洗衣机,想把她和方德运换下的衣服洗了。方德运的衣裤在,可她那件吊带内衣连身袜却不见了。奇怪,昨晚明明是一起放进洗衣篮的啊,怎么单单那件内衣不见了呢?她看了看洗脸台上,没有;看了看浴盆里,也没有;打开储物柜,还是没有……真是奇怪,这巴掌大一个洗手间,愣是找不见她那件内衣。
金媛走到窗前,把头伸向了窗外,她看见102那个女人抱着猫,走进了门洞。心里一动,金媛想,该不会是那只猫昨晚进来了吧?这么一想,竟记不得刚才是自己开了窗子,还是窗子本来就没关。她有些恍惚了。想到猫,想到楼下的女人,又想到婆婆,金媛觉得这满世界都是耳朵,都在监视着她,都在跟她作对。她有些生气了,妈的,我在自己家里,凭什么不得自由?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穿什么就穿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买,这件丢了,我再去买一件。
金媛拎起包,走出屋门,去地下室取她的电动车。
地下室的通道很长,两侧是一间间储藏室,楼里的住户,每家都有一间,外面有门牌号。金媛推着电动车走出储藏室时,看见那只猫躲在一张旧桌子底下窥视着她。金媛单身时也养过猫,她认识那只猫是缅因猫,长长的大耳朵支棱着,好像在听有趣的故事,绿宝石一样的眼睛看着金媛,温柔而和善。她忽然有些喜欢这只猫了,好像忘了刚才还怀疑它偷了她的内衣。她下意识地摸了下手包,想起包里除了手机、面巾和化妆盒,什么也没有。她想,待会儿逛街时要记得买些猫食,再见时好犒赏一下这小家伙。
这时,楼梯间传来拖鞋下楼的声音,吧啪,吧啪,鞋跟疲惫无力地拍打着地面。到了地下室入口上面,停下了,似乎喘息了一会儿,女人沙哑着声音喊:“爱儿——”猫听到主人的呼唤,嗖地从桌子底下窜出来,回头看了金媛一眼,慢腾腾地朝通道尽头走去,又粗又圆的四肢,走得稳健而自信。金媛想,“爱儿”应该是猫的名字。她一时竟有些慌乱,她想那个女人如果走下来,会不会当面教训她?忽然有些心虚,就转身躲进自家的储藏室里。
“爱儿”,她想,为什么给猫起这么个名字呢?是亲爱的儿子?或者是亲爱的女儿?
外面静了下来后,金媛才走出储藏室,骑上电动车。门洞里弥漫着浓浓的香水味道,已经不见了那个女人,却听见“喵”地叫了一声。金媛看了看102的门,有一种上前把耳朵贴上去的冲动。
金媛在街上一直逛到下午,才回到小区。走进门洞,经过102的门口时,她下了电动车,想听听屋里那个搅事精在说什么,做什么。可102却没有一点动静,安静得有些可怕。但那熟悉的香水味还在,只是很淡很淡了。
站了一会儿,金媛才推车走进了地下室。刚拐过入口,就听见一阵猫叫,不是“喵喵”的声音,“啊——啊——”一声长着一声,像急切地呼唤着什么。金媛抬起头,看见102储藏室门口躺着一个人,“爱儿”绕着那人的身体不停地转圈,不时地伸出爪子抓那人的衣服,似乎想把那人从地上拉起来。近了一些,金媛看清地上是一个光头的人。她想,这里怎么会躺个秃顶男人呢?再近一些,终于看清了,地上的人是102那个女人——她的脑壳光秃秃的,一头浓密的大波浪掉在一旁,原来是假发,显然是被猫抓下来的。女人佝偻着身子,肩膀一耸一耸的,不知道是在哭还是在呕吐。
“你……怎么了?”金媛俯下身问。
女人睁开眼睛,想说什么却说不出来。
这是金媛第一次与女人照面,她发现这女人眼睛很大,眼梢往上挑,一看就是个不好惹的主儿。但她已经顾不上这些了,她早已心惊肉跳,手心冒汗,慌忙掏出手机,先拨打120,叫了救护车,又给物业打了电话,然后再次弯下腰,问:“你病了吗?坚持着啊,马上就来人了……”
但女人已经不能说话了,眼睛也重又闭上了。
那只猫安静下来,可怜巴巴地望着金媛。“没事的爱儿,别怕,马上就来人了。”她伸手去抚摸猫的脊背,那猫竟没有逃开,好像找到了依靠。
很快,物业就来人了;不大一会儿,救护车也到了,众人帮忙把女人抬出地下室,弄到救护车上,开走了。
金媛打开房门,方德运已经回家了。
“可吓死我了,刚才……”金媛心有余悸地说。
方德运瞪了她一眼,好像有点不高兴。
“怎么啦你?”金媛問。
“也不问问我妈什么情况,好歹也是上岁数的人了。”方德运说。
“哦,哦,什么情况?”金媛放下大大小小的购物袋。
“没大事。中耳炎引起的神经性头疼。”方德运说。
的确不是什么大毛病,婆婆耳朵上的小洞,不是福洞,不是金窝银窝,而是“耳仓”,是一种病。在医院做了个小手术,就直接回家了。金媛想,耳朵病了,这之后婆婆还会像以前那样总打听他们小两口的事吗?
“刚才你说什么把你吓死了?”方德运问。
“102那个女人,变成妖怪了,脑袋光秃秃的,跟皮球一样。”金媛说,接着又说了刚才地下室发生的事。
“就说她总是怪怪的,还真是个病人啊。”方德运说,“人在病中,难免就会敏感,看什么人、什么事都不顺眼。”
“你这是为你妈开脱吗?”金媛忽然说。
“哦,那倒不是,”方德运说,“就算是吧,我们也不该跟个病人一般见识,是吧?”
金媛点点头。她想起大学时有一次她生病了,就见不得室友化妆,看不惯室友在她面前晃来晃去,甚至听不得室友吃饭发出的声音。人病了,难道她眼里的世界都病了吗?金媛看着方德运,他们很少这么平心静气地讨论问题,她觉得她跟方德运的关系贴近了,似乎她跟这个世界的关系也贴近了。
“真可怜,那么孤苦伶仃的一个女人,要不是我发现打了120,不定出什么事呢。”金媛说。
“你确定她是一个人生活?”
“你见过她家里还有别的人?”
这么一问,他们都肯定102就只有那个女人,不由都生出了恻隐之心。
“我得下去看看……”金媛说着,先自跑了出去。
金媛去了地下室,却找不到那只猫了。她学着那女人喊,“爱儿,爱儿”,并不见那猫出来。她看了看桌子底下,没有;进了102储藏室,也没有;沿着地下室通道把犄角旮旯都找遍了,还是没有找到。大概女人突然病倒,没来得及给它喂食物,它又找不到主人,就跑了吧。
入口处传来一轻一重的脚步声,一个中年男人走了进来。他的脚似乎有毛病,走路一颠一颠的。男人中等个头,很敦实,鼻子头圆圆的,红红的,像刚喝完酒,又像一颗熟透的李子。他穿着灰色体恤,胸前油光光的,休闲鞋上也沾着油污。他双手交叉,怀里抱着那只猫。
“你是找这只猫吗?”男人问,脸上带着微笑,在金媛身上上下打量。
“是的,我找爱儿。”金媛被他看得很不舒服。
“不是爱儿,是Ear。”男人说。
“哎儿?”金媛变了一个声调。
“Ear。你没学过英语吗?”男人掏出一支烟,慢条斯理地吐着烟雾,“我姐姐原来是英语老师。”
爱儿——金媛忽然明白了,应该是“Ear”,英语耳朵的意思——天,又是一只耳朵,满世界怎么到处都是耳朵呢?为什么逃到哪里都躲不开一只只耳朵呢?
“你姐姐她咋样了?”金媛问。
“脑癌,一直在化疗,头发都掉光了……”男人俯下身去,捡起脚边那个发套,长长的,浓密的,仍然泛着大波浪,“可是效果不好,疼起来就用头撞墙。”
金媛想起业主群里女人的叫骂,又想起“咚咚”的撞击声,不由心中充满了羞愧——这个女人最痛苦的时候,正是她跟方德运最快乐的时候,还真是把自己的欢乐建立在了別人的痛苦之上。
“你愿意收养Ear吗?很乖的,也很懂事。不然它就成流浪猫了……”男人小心翼翼地问。
金媛把Ear抱回家时,方德运叫了起来:“你怎么把它给抱回来了?”
“它叫Ear,很乖的,也很懂事,我不想让它变成流浪猫。”金媛说。
“Ear,耳朵啊,”方德运倒是一下就听明白了,“你不是一直讨厌耳朵吗?”
“我讨厌过,可我现在不讨厌了。”金媛说着,把Ear放到地板上。
她想,她从大房子搬到这套小房子,逃开了婆婆的耳朵,却没逃过102女人的耳朵,也许这个世界需要诉说,就需要倾听,因而,每个人都有嘴巴,也都有耳朵。
Ear好像知道它以后就要在这个家里生活了,便开始讨好它的新主人。它先在金媛的小腿上蹭来蹭去,然后,眯起蓝宝石一样的眼睛,怯怯地看着方德运,试探性地伸出一只前爪,好像要跟方德运握手。方德运犹豫了一下,也把手伸了出去。Ear就势一纵,踩着方德运的手,跳进了他的怀里。
金媛拿起沙发上的购物袋,开始往外掏东西。上午逛街时,她已经给Ear买了猫粮。现在想来,真像是宿命,好像冥冥之中安排了Ear将要跟她一起生活。除了猫布丁、猫寿司,还有妙鲜包、肉干、肉条。Ear认识这些食物,它的嘴不停地吧嗒着,还伸出舌头舔了舔鼻子。金媛掀开一个罐头盖子,Ear“喵”的一声,从方德运怀里跳下来,跳到罐头盒子跟前,看了看金媛,又看了看方德运,仿佛在征求主人允许。
金媛笑了笑,说:“还真是个小馋猫,快吃吧。”
Ear这才欢快地吃起来。
金媛趁Ear吃食的工夫,开始归整买回的东西。她从购物袋里拿出新买的一件吊带内衣连身袜,方德运说:“呀,你怎么又买了一件?”
“昨晚那件不见了,我又买了一件。”金媛说。
“在这儿呢。”方德运说着,扭身从沙发背上拿过一件东西,正是她那件情趣内衣。
“怎么在这儿啊?”金媛感到奇怪。
“是我妈,”方德运顿了一下,“可能她收拾东西时,不经意装进了自己包里,到医院才发现,又给我了。”
金媛耸了耸鼻子,想,什么叫不经意啊,分明是嫉妒我年轻性感的身子,怕我勾引她儿子,故意偷走了呢。但她没说,只是很有意思地笑了笑。
Ear吃得正开心。
责任编辑 申广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