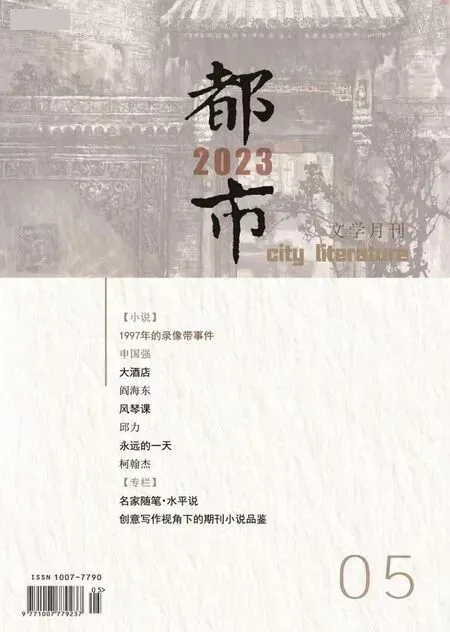纯粹的童年叙事
——读赵志明小说《怪客》
○李苇子
提到童年叙事,最先想到的两位作家便是鲁迅和萧红。前者的《社戏》和《孔乙己》,后者的《呼兰河传》。然而,细细研究,还是发现了一些问题,这些童年叙事的作品并非严格意义的童年视角,而是成年后对于童年生活的一种回望,属于典型的回溯性叙事。《社戏》有两个版本,流传最广的是删减版,原版小说中开头写的是“我”在北京看戏的两段经历,这两段经历都很糟糕,由此引出“我”对童年那次看戏经历的怀念。文本中潜藏着一个若隐若现的成年者的叙事声音,纵然是童年视角,也是经由成年叙事者过滤后的,有了成年人的情感认同与价值判断。纵观鲁迅这些关于童年的作品,不难看出无论他如何批判中国人的劣根性,孩子总是美好的,他们与成人世界形成一种泾渭分明的对立关系。这一点从少年闰土和中年闰土的对比可窥一斑。《故乡》里成年后的迅哥儿和闰土有了巨大隔膜,但是,小侄子宏儿却在想念仅有一面之缘的水生,作者经意或不经意间将我们引入更遥远的思考,宏儿和水生这段短暂的情谊不过是迅哥儿和闰土少年时情谊的翻版。在《孔乙己》中,儿童世界的澄澈与成人世界的浑浊更是形成了鲜明对比,作为浮游于儿童与成人世界夹缝间的一个怪物,孔乙己只能在孩子群体中寻找认同与共情。《呼兰河传》当然也是成年后的“我”对于在呼兰区那段生活的回忆式叙事,尽管也有大量关于孩童的感受性描写,但,那份浓郁的怀旧情绪,显然是属于那个成年叙事者的。
严格意义的童年视角必须要用儿童的心理、眼光、认知等,去打量、观察和体验这个世界,无论是情感评价还是认知深度,儿童都迥异于成人。作为思想的外衣,孩子的语言充满了想象力,不受现实逻辑的羁绊,表现出那种信马由缰、天马行空的任性和自由。偶尔他们能说出一两句类成人的语言,也不过是对成人的模拟与效仿,但,倘若一个孩子始终在用成人的语言表达,则是一件叫人毛骨悚然的事。另外,儿童世界感性大于理性,那是一种无序的、众生平等的慈悲,超越了成人秩序井然的现实经验。儿童的这些特点,让小说家获得了部分挣脱现实逻辑引力的特权,极大地实现了叙事自由。
赵志明的短篇小说《怪客》(《小说界》2022 年第3 期)也是一篇童年视角的小说,作者完全以童年的感觉和经验去叙说并非全是孩童的人和事。他虚构了一条忧郁且神秘的街道,以及一个孩子被昏黄的路灯拉长,拍扁,再拉长,再拍扁的投影。“我”的母亲不顾众人反对,在一条尚未成型的街上,倾尽所有,造了一栋很气派的三层楼房。在孩童天真的意识里,世界以自己家的房子为圆心朝四方扩散,所谓全世界不过是我们生活的那个镇子以及周边几个镇子的组合。因此,在《怪客》中,“我”家房子矗立的那条、未来会变得繁华的小街,似乎被高度提纯,浓缩了全世界的风景与可能性,由此也开启了“我”在这条街上的“历险”。
童年视角在这篇小说中意义非凡,在附于文后的“自问自答”里,作者坦言“小说里若有若无的诗意,得益于儿童视角……特别是在语言上,经常会旁逸斜出”。作为成年人眼中稚嫩的孩童,他们的边界意识最是淡薄。在孩子们看来,万物有灵,他可以与世界上的一切有生命体或无生命体对话。《怪客》中的“我”便是如此。“我”和邻居家的花猫是好朋友,经常与它交流,“花猫告诉过我,它从不吃素菜”。花猫在文中频繁出现,这不能不让我想起苏童小说里的那些猫,作为暗夜精灵,猫给人的感觉总是神秘莫测,它们像游魂一般在江南水乡低矮的屋檐上闲庭信步(作为江南人的赵志明应该拥有相类的童年经验吧)。由于家庭贫困,母亲在房子后面开辟了一片菜园,种了很多蔬菜,“我”认为那些菜蔬全是用母亲的泪水浇灌长大的,因此,“吃起来有一股苦涩味”。和李白的“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一样,“我”也将月亮视为一只白瓷盘,黛青色的天空则恍如湖泊,好友花猫邀请“我”去天空猎鱼,当鱼这个意象出现后,前边的白瓷盘瞬间便贴切起来。这简直就是一幅稚拙朴素的儿童画——暗沉沉的夜空,寥落疏星,雪白的瓷盘似的月亮上横着一条鱼,憨态可掬的花猫端坐于夜空下的泥鳅脊上,手里抓着一副雪亮的刀叉。
除了修辞的陌生化,视角的选择同样能实现陌生化效果。《红楼梦》第六回,刘姥姥一进荣国府,周瑞家的带她去找王熙凤,关于凤姐家厅堂里的陈设便是通过刘姥姥的视角展现出来的。在现代人看来不足道的钟表,却唬得她一展眼。读者跟着视角人物,重温了这一司空见惯的物件,同时,也会感叹于贫富悬殊对于视域绝对化的局限,当然,这种视角也会让人物更加立体饱满,显得真实。莫言的《生死疲劳》用几种动物的视角来描写1949 年后风云变幻的社会家国,借由动物的眼睛去凝视那些超越人类理解能力极值的种种疯狂和狂热。阿来的《尘埃落定》则经由一个傻子来讲述。此傻子非彼傻子,他的内心世界相当丰富,那些所谓正常人无法理解、无法看见的,他都能理解、能看见,简直就是一位智者。
《怪客》中最富有意味的角色便是一个被称为怪客的家伙。这一角色几乎没有正面出场,却像一种暗黑的力量,从故事躯体的每一只汗毛孔渗透出来,弥漫出一片淡紫色雾霭和笼罩全文的神秘感。一直将自己当作这片区域主宰的花猫,对怪客卑躬屈膝。“只要怪客出现,它就很安静,也很听话,简直就像最出色的仆人。”看上去,怪客具有未卜先知的能力,母亲恰恰是听信了他关于这条街未来会出现市集的预言,才毅然决然地建造了那栋楼宇,目的是开家庭旅馆养活自己和孩子。怪客住在“我”的隔壁,“我”另一边住着母亲。怪客、“我”、母亲,三个人住了三楼的三个房间。这情形多么像一张全家福,爸爸在左,妈妈在右,孩子居中。
“我”家旅馆的生意越来越好,形形色色的客人住了进来。住在“我”家202房间的一位女客,常常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有时候,母亲会去陪她,两个女人的哭声能穿越最厚的墙壁。后来,母亲带她去了怪客的房间。“我”却认为,这位女客人肯定是遇到困难了,去找怪客求助。
怪客唯一一次正面出场,是在小说中间偏后的位置。某个晚上,二舅让“我”去街上买酒和下酒菜,“我”怕黑,便让怪客陪着。怪客笑了,眼神炯炯发光,并且是一言不发地陪“我”出门。“我”像一位向导,引领着怪客,以及怪客身后的一众读者,从那条有路灯的老街走过,依次路过了粮管所、水电站、镇政府、医院、药店和派出所。于是,我们遇见了老鼠、花猫、黄猫、一条无精打采的狗、蝙蝠,以及那些“我压根看不清楚的生物”。归途,“我”建议走另一条小路,于是我们又一起领略了那条正在建设中的,未来商业街的雏形。整个过程,无论“我”说什么,怪客都不开口,只是微笑,“眼睛像星星一样明亮,只要他眨一下眼睛,夜空中就会划过一颗流星。”而一颗流星的划过,在童话故事里,代表着一个人的死亡。
就这样,我们从弥天大雾中窥见了残酷真相,所谓怪客,压根就不存在,那不过是“我”用孩童一厢情愿的天真虚构出来的角色。根据全文中父亲的缺席,我们不难猜到,怪客便是父亲。怪客虽有形(作者数次眼睛的刻画)却无实(从不开口讲话),因此,我们不妨做个大胆的猜测,怪客,其实是“我”隔壁房间墙上那幅父亲的遗照。在文末的“自问自答”里,作者也证实了这一点。若不是借由特殊视角,这种虚构便很难成立。
张悦然在《较远的观察者》一文中说,视角像阿莉阿德尼的线团,带领读者穿行于叙事迷宫,并最终走出来。我们仰赖于它才没有迷失,并且,收获了一些意义。然而,我们也受制于它,无法看到故事的另一面。世界是无序的,视角为我们建立了一种秩序。视角的选择对于一部小说的成功与否起着决定性作用。余华曾在《活着》的序言中说,最初他采用旁观者视角,故事很难推进,后来改成第一人称自述,于是奇迹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