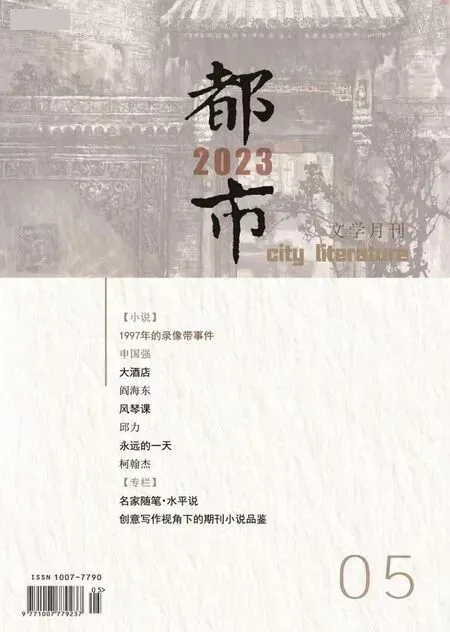灯下随笔三题
文 孙青瑜
文化与诠释
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史,其实都是一部诠释史。
传统意义上的中国文化也是如此,她很像西方数学的几何史,由一个又一个点域游戏构成,只是中国圆点关系不叫单纯的数理化,而叫八卦,也就是包罗万象的易学。
可能正是这个原因,中国的文化发展史和别的国家不太一样,她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分科,更没有什么所谓的专家一说。因为中国文化的各个分支,一直在易学里发展,所以中国文化都是围绕着易学而展开的百科诠释学,进而构成了中国文化发展史。
当然,诠释不是文化,但文化离不开诠释。
正是因为文化史就是诠释史,所以从古至今真正的大学问家,一般皆出于两支,一是文字学脉,二是律数象数派。两支人才大军就如象数和义理,从“易经时代”便开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前赴后继地推动着中国文化的发展。
记得陈寅恪曾说过:“中国真正的原籍经典(原典)不过一百多部,其余的书都是在这些书的基础上互为引述参照而已。”
其实陈所说的一百多部,纯属高估。
因为中国真正的原典不过三本——天、地、人。若再追根溯源,天、地、人三本大书又是另一本大书,一本围绕着天道律历——也就是时间问题而展开的点域认知学和诠释学。这正是刘歆为什么说“汉兴,天下唯有《易》卜,未有它书”的原因之一。
像先秦时期以《阴符经》和老庄为主的道学,汉以后,又以《黄庭经》《太平经》《周易参同》为主的道家,从黄帝时代开始以《奇门遁甲》为主的兵家,以“历法推算”为中心的中国数理几何音乐学的发展史,以五行说和卦变说为中心的中医药学史,以“为学”问题为主的儒家存在论……可以说都是诠释易学诠释出的“另立门派”。
当然,易学不但决定着这些文化门派的诞生,同时也支配并诠释着它们从头到尾的发展。而易学的发展,同样也离不开这些分支文化对她的反向诠释。比如汉音律、数学、几何学,以及老庄存在认知学、宋明理学……对后世易学的发展,都有反向的诠释性推动。
这种母与子相互诠释的文化现象,就像一张网,无论剪断哪一根线,网就不成网……这就注定中国文化里没有专家,只有文化学家。所以自古以来,中国文化都不提倡术业专攻,而是讲究博观约取和触类旁通。
而现代人读古,总是从百家开始,拿起《道德经》就一副很专家的样子解读“反其道而行之”,解读“上善若水”……好像每个字都识得准确无误,其实每个字又不认得,句义解得更是错得离谱。
比如“反其道而动之”这句话,出自《史记》,其理论来源,则是《道德经》里的“反者,道之动也”。反,在现代汉语里确实是相反、反对、反面之意,但是在老子时代的天道观里,“反”却不是现代汉语里的“相反”之意,而是“返”,即回复往返、往来返复之意,是顺化,而不对化,它是指按着规矩来,而不是反规矩和什么逆向思维。
从此我们看出,阅古不识字的现象,不仅是不识古字,更重要的还有知识结构的狭窄问题。
再比如“上善若水”,因为老子以坤为首,坤为母也、北水也。老子的本来意思是:能母仪天下者为上善,也就是要像母亲一样善良和无私,从而引发了它的空气和水滋养万物而不争的“上善”之母性理论,而不是在现代汉语下臆断的什么“你高我退去”之无知之谈。
从而我们可以看出,百家绝非纯粹的义理,整个中国文化都是一个围绕着天道时间展开的知识网,若不懂《易》,只在巴掌大的知识空间里,你所能“悟”到的只能是一隅之见,甚至错见。正如《周礼订义》里所说:“周礼之难行于后世也,久矣,不惟难行而又难言然……诸家解文或牵引枝蔓……”
诠释推动了文化学的发展,但是诠释本身也为后人学古识古造成了障碍,因为很多“很有道理”的道理和“注解”,可能只是个人认知局限下的一隅之真义,甚至错释。按说,诠释本身是为方便后人能够更明晰地学习和悟道,可由于学者水平良莠不齐,认知的境界千差万别,悟道的深度高低不同,知识结构的各异,把文化越注越复杂,越注越难学,越注越“《诗》不能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
虽然读不完的不是学问本身,而是海量的二手经验认知、诠释与解读。但是我们学文化,尤其是学中国文化,却又万不可只读一家之言、一派之说,一定要博采众长、纵横比较,才能取来那一道真经。
闲话中医药
中医和中药的叫法起源非常晚,但是用“中医”和“中药”概括中医药学,却再熨帖不过。
何为中医?就是求人体中和的医学!
何为中药?就是求人体中和的药物!
记得《松峰说疫》里载过这样一个医案:“余曾见一小儿患瘟热,热邪深重,寻得凉水一瓮,且浴且饮,一日后而愈。”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类似的医案,话说一监狱里发生了冬瘟,某犯人因染疫已死,狱卒把他扔到冰天雪地里冻了一夜,不想第二天,那人竟然苏醒过来,不但起了死,回了生,还免去了牢狱之刑。正如《类证治载》里所说:“人壮气实,火盛癫狂者,或硝水冰饮之,凉膈、解毒之类。”
可同样的凉水,如果破坏了人体内部平衡,破坏了人体八纲的平和,就会变成毒药杀人于无形。20 世纪70 年代,老家有一乡邻在大田里汗流浃背干了一天活儿,傍晚收了工,跳到河里洗了一个澡,不想这一洗却要了他的命……
由此可见,凡药皆毒,凡毒皆药。是药,是毒,就看怎么用。所以学习中医者只有掌握了“症变”,才能会“变症”,才能用好、用活中药这个武器,达到以一药治百病的威力,否则再美味的水果、调料和上品之药,也会吃来一身病,甚至要命。
记得《冷庐医话》里讲了一位不知“八纲”为何物的庸医,读了许叔微的《伤寒九十论》,非常喜欢,也开始效仿用麻黄汤给人治病。但是他不懂“病随人异,药随证转”之“八纲”大论,碰到一个热病无汗并脾虚至极的病人,一味“麻黄”给人家投下去,就投出了一场命案官司。
除此之外,《老残游记》里也记载过这样一个温派的经典医案——话说一女子害了喉蛾,已过五天,喉蛾就是今天所说的扁桃体发炎,请庸医来诊,不想越治越严重,已经滴水不能进了。于是又请来一位先生,看看病人还有没有救。不想那老中医一搭脉,面色沉了一下,再一看喉咙,两边已肿到合缝……
按说扁桃体发炎本来不重,可过喉之经密密麻麻,庸医不辨病灶,本来是内寒作热,需要引火归元。可医家不懂,用苦寒药一逼,火气更旺……
关于寒热问题,还有一个医案:某小儿呕吐多天,数家医生投以理中汤,皆无济于事,又请来儿科大医万全,用的也是理中汤,却一济见效!其父非常惊诧,问万全,用的都是理中汤,为什么别人用了治不好病,你用就治好了呢?万全说,因为你儿子胃寒太甚,投以温药博不过胃寒,我就用猪胆汁的苦寒和童便的咸寒辅佐理中汤……
什么意思呢?就是万全用猪胆“人为”地制造了一场“物极必反”“寒极生热”的病症,让“理中汤”有能力发挥它的中和作用。
这就是中医!
中药学不需要精密细微的化学分析,不需要实验室,其药理医理的科学性和精密性却能让人叹为观止。正如《医醇剩义》中所说,“秦有良医,曰和曰缓,彼其望色辩候,洞见膏肓,非所谓神灵诡导者欤……惟能知常,方能知变。”
还有一个张仲景用巴豆止泻的传奇故事。众所周知,巴豆是一味泻药,可张仲景却敢用巴豆给病人止泻。原因就是巴豆“遇热而泻,遇冷而止”的化学性质,体寒冷积、凝滞久泻之人,用巴豆不但不泻,反而能止泻。所以很多医生给病人用巴豆,用得多了,拉得收不住了,便让患者喝上一杯凉水,泻可立止。
中国文化有一个最精华的认知方式——以宏观论证微观,以微观论证宏观,尤其是中医药学,把中国文化以宏论微、以微证宏的认知理论应用得炉火纯青。只有把人体内部的物理化学环境和药物化学都双双研究透了,才能用好中药、用活中药!
像张仲景的麻黄汤、大小青龙汤,这些方子之所以有“还魂”之效,除了麻黄能扩充气管,还可以配合桂枝之力,急救水道、中和营卫。说白了,就是以表求里、以强表启动弱里的中和思想。
所以一般善学中医者,皆是“刁钻”的读方专家,因为历代经方和时方里都是大的医理,而大医理里头呢,也尽是大的药理。
明代大医张景岳就发挥了“桂附地黄丸”这个方子的精髓医理,他善用熟地救逆,通过补阴启阳,再用回逆的阳气反过来抑制和清除水阴……正如《医宗金鉴》里所说的:“意不在补火,而在微微生火,益火之源,以逍荫翳”,其实就是以“阴极生阳,阳盛阴弱”的太极思想,用张景岳自己的话说就是“善补阳者,必于阴中求阳,则阳得阴助而化生无穷”。
而另一位大医——火神派鼻祖郑钦安,好像并没有读懂“熟地”这味药,也没有读懂张景岳和“桂附地黄丸”的易医思想,可他也是一位不可否认的天才,因为他读懂了张仲景的另一个方子——“附子理中汤”,以君相二火启动中土之气,从而开辟了自己的医易体系。
每个好的中医,不管偏执于何种本体论,也不管用什么方法,其目的都是为了让人体的内循环达到中和,以此实现救死扶伤。所以医学史上“传方不传量”的深层原因,并不是保密,因为“量”没法传,同一个方子,药量不同,治的病都不同,在运用的时候,需要结合人体“八纲”随机应变,才能灵活定夺。像千古第一方“桂枝汤”,加重桂枝的量和加重白芍的量,治的病都不一样。
有些药材之所以被视作“毒”药,只是因为不好掌握“五味四气”“君臣佐使”与“八纲”之间的“中和”问题。而万毒之所以能变成良药,皆是因掌握了“中和”二字。
闲话艺术与学问
有某个自媒体宣称:一天背一首古诗,一百天后,就能让你达到“腹有诗书气自华”的境界。真不知道这个专家所说的“诗书”是什么样的学问,背一百首古诗就能背来“腹有诗书气自华”的神效。
艺术不是知识,艺术只是审美的对象。
知识和智慧的增长,靠的不是什么古诗、什么名句,艺术的本质是审美,不是背诵。你就是把唐诗宋词背得滚瓜烂熟,也不一定能够感受得到那些古诗词的美,也不一定变得有学问,更不一定能增长智慧。因为在古诗词里,涉及的知识非常非常庞杂,比如大家都读屈原,你真的能够读懂屈原的诗吗?没有深厚的中国古典哲学基础的人,是读不懂屈原的。再比如,杜甫也是妇孺皆知的大诗人,你真的能够读懂杜甫吗?杜甫的律诗,代表着中国应用音韵学的巅峰,如果没有深厚的应用语言学基础,也是一样读不懂杜甫的。
另外,世界上也没有一个文学家的创作是为了让读者背诵他的作品。他们创作的目的是让读者审美,通过审美,和他们的创作意向达到共鸣,懂他们,知道他们想表达的是什么,写的是什么,而不是让你去干背。
中国有句古话叫“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如果没有庞大的知识结构支撑你的阅读,你就是读一万遍,也理解不了书中之义。
艺术不是知识,但并不代表艺术里没有知识,也不代表艺术里没有知识的应用,像绘画艺术里的光学、几何学的应用;音乐学里声学、律学、文学、语言学的应用;文学里音乐学、语言学、心理学、图像学的应用……都是艺术家进行美学营造时,必备的基础知识。
当然艺术营造本身也是一门大学问。关于艺术营造这门大学问,在现代派艺术当中,更加凸显它的存在。
也就是说,艺术虽然不是知识,但知识却决定着艺术审美。艺术里不管有多少知识和知识应用,都是为了更有力更明晰的审美,而不是为了把审美变得更复杂、更无力、更模糊。艺术利用知识是为了更好的艺术,艺术的本质不是贩卖和灌输知识,而欣赏艺术却需要大量的知识储备。比如《芬尼根守灵夜》,如果没有物理学、音乐学、语言学的各类知识储备,肯定是读不懂的。再比如《追忆似水年华》,如果对神经认知学一窍不通,就可能看不懂那本书。再比如《红楼梦》里的各种知识,让无数的学者研究一生,“红学”直到今天也没能被研究穷尽。
同样,中国的很多古诗,也不只是表达“喜怒哀乐”那么简单的传情诗,还有很多哲理诗。就是算是传情诗,也不只是利用文字传情,还有很多利用了音乐学、韵律学,还有很多典故的应用……
记得某个社会名气非常大的小说家曾说,他读《庄子》一类书,越读越厚。
为什么很多人会觉得书越读越厚,越读越难呢?因为缺知识,不知道的太多,典籍里涉及的每一句话的背后,甚至每个字的背后,都是你还不知道的知识体系,肯定越读越厚。当你的知识结构支持了你的阅读,书是越读越简单的,越读越薄的。学问就像杜牧说的“丸之走盘,横斜圆直,不可尽知,其必可知者,知是丸不能出于盘也”。学问再驳杂,其实万变不离其宗,把“宗”研究透了,才能真的明白“为学日益,为道日损”的深意。世界上没有复杂和高深,之所以有些人觉得高深复杂,是因为还在“为学日益”的路上。用通俗的话说,就是还处在“少年不懂诗”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