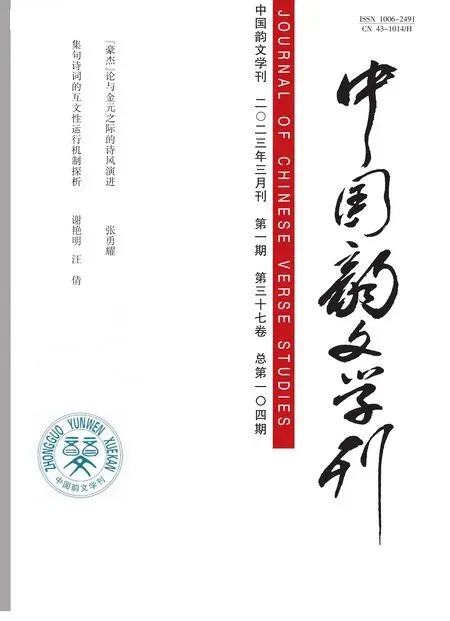论朝鲜时代女性次韵诗的技法:以丰山洪氏家族为中心
伏 煦
(山东大学 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山东 济南 250100)
一 丰山洪氏家族女性次韵诗创作概况
在朝鲜时代(1)即李氏王朝(1392—1910)统治朝鲜半岛的时代。的女性诗人中,丰山洪氏文学家族的女性诗人无疑值得瞩目,洪仁谟妻徐氏(1753—1823)有《令寿阁稿》一卷,存诗一百九十一首,其女洪原周(1791—?)有《幽闲集》,存诗一卷共一百九十三首;其季子洪显周之妻淑善翁主(1793—1836)为朝鲜正祖之女、纯祖同母妹,有《宜言室卷》一卷,存诗共三百四十二首。母、女、媳三人均有诗集存世,集中保存数量较多的次韵诗,亦是值得注意的现象之一,如张伯伟先生指出的那样:“徐氏诗稿以次韵、唱和之作居多,其对象一为古人,二为家人。”(《令寿阁稿》解题)[1](P616)而次韵古人之诗在数量上远多于次韵家人之作,其中,徐氏集中有次韵古人之作七十九首,洪原周集中亦多达八十八首,均超过存诗的三分之一,就这一比例而言,几与苏轼、黄庭坚同。而其中以次韵杜诗之作最多,徐氏有二十七题共四十三首,洪氏则多达四十一题四十七首,母女多有同题之作。(2)《幽闲集》中的《泛江送客》《江楼夜宴》《次花溪晓望》《题桃》等作虽未标明“次杜”,然皆为次韵杜甫之作。洪原周与其父母次韵杜诗作品的比较,可以参见左江《朝鲜时代的知识女性与杜诗》(《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第八辑,中华书局2012年版)一文的列表比较,第31—33页。淑善翁主的次韵诗亦多达六十首,皆为五言绝句,(3)《宜言室卷》所录三百四十二首诗中,七言绝句、五言律诗(含两首联句)和五言古诗(以六句为主)分别为二十、九、十首,三五七言体一首,其余皆为五绝,接近总数的九成。相对独立于洪氏母女之作,或不与之同时。(4)根据左江《朝鲜时代的知识女性与杜诗》一文的考证,徐令寿阁的创作时间集中在1808—1812年,而洪原周的创作时间从1808—1810年(大约为出嫁之前)。淑善翁主三十六岁之年(1828年)的手抄自作为《宜言室卷》,集中有两首与纯祖之子孝明世子(1809—1830)(《敬次春邸寄示韵》),与侄女明温公主的酬赠之作,并无与洪氏家族成员的唱和之作,故而推测淑善翁主的创作当晚于洪氏母女。
除杜诗之外,《古诗十九首》、陶渊明、王维、李白等名家名作亦受到洪氏母女的关注,(5)曹虹《论朝鲜女子徐氏〈次归去来辞〉——兼谈中朝女性与隐逸》(《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从隐逸思想的角度,讨论了徐氏《次归去来辞》的独特意义。结合洪氏长子奭周所编、指导其仲弟洪吉周《洪氏读书录》收录《文选》《唐音》《唐诗品汇》等选本,而别集中收录陶渊明、李白和杜甫等家,可知洪氏家族的阅读趣味以及对古诗与唐诗的接受情况。淑善翁主则次韵王勃、卢照邻、骆宾王、宋之问、杜审言、李白、王维、孟浩然、储光羲、岑参、刘长卿、韦应物等初盛唐与大历诗人的作品,其中李白有十二首之多,其次则是王维九首,再次刘长卿六首,表现出与洪氏母女截然不同的文学趣味。就整体情况而言,洪氏母女次韵的作者较少,然而所涉及的诗体较多;淑善翁主的次韵诗皆为五绝,然而涉及的诗人范围较广。三位女性诗人的次韵诗作品均形成一定的规模,不妨视作研究次韵诗技法的一个样本,来观照她们如何在前代诗人设置好了的框架内施展各自的才华,以一定的技巧和方法创作次韵诗,尤其是在押韵方面,如何因袭前作,而又怎样写出新意;同时,次韵诗作为一种在形式上有着严格要求的诗体,作者有无表达个人情感与生活经历的空间,亦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丰山洪氏家族三位女性诗人的次韵诗,在韵脚的意涵和诗作的意旨,与旧韵或合或离,其中透露出的更多是向经典诗作学习与致敬,而非刻意与古人争胜以逞才的心态。
二 因袭与转换:韵脚的文字游戏
次韵诗的核心无疑在“韵”,对原诗韵脚的因袭或转换,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次韵诗的意旨或诗境囿于原作的格局,或得以别开生面。总体而言,丰山洪氏女性的次韵诗在用韵方面,以沿袭原作的用法为主,或在此基础上稍加转换,几乎不刻意追求生新与出奇。尽管如此,我们不妨尝试以洪氏家族女性的次韵诗为样本,总结一般的次韵诗的写作技法及其效果,毕竟次韵诗的写作可能以模拟前作为手段,并达到学习名家经典作品的目的,未必刻意求新,或与古人争胜,以此炫技或逞才。如次韵李商隐《隋宫》[2](P1551)(见于《唐音》卷五与《唐诗品汇》卷八十八)的洪原周《隋宫怀古》[1](P884)(括号内为原作,下同):
玉楼琼宫带晚霞(紫泉宫殿锁烟霞),
繁华胜地属谁家(欲取芜城作帝家)。
清歌妙舞散如烟(玉玺不缘归日角),
惟有寒月照碧涯(锦帆应是到天涯)。
女墙寂寞虚无人(于今腐草无萤火),
旧台荒凉乱飞鸦(终古垂杨有暮鸦)。
万乘富贵今何在(地下若逢陈后主),
数株衰柳伴野花(岂宜重问《后庭花》)。
《隋宫》一诗所押霞、家、涯、鸦、花等韵全为名词,且无生僻字,洪氏次韵紧跟原作,以改换定语为基础构成新作,如变“烟霞”为“晚霞”,“帝家”为“谁家”,所用语词皆属平实,并未有较为生新峻峭之语。虽然李商隐原作也未能在前四个韵脚用典,但最后一韵“《后庭花》”,被洪氏以“野花”取代以后,原本就缺乏指代隋朝或炀帝典故的次韵之作,已经成为一首一般的怀古之作,“野花”与前一联的“飞鸦”一样,作为一种物象,诉说着无尽的荒凉与颓废之感。
类似的,如果韵脚为动词或形容词,亦可通过主体的转换进行创作,如洪氏《和杜吹笛》[1](P886-887)、[3](P1470):
林间栖鹤舞松清(吹笛秋山风月清),
云外惊鸿和笛声(谁家巧作断肠声)。
中曲萧萧梧叶落(风飘律吕相和切),
余音袅袅月轮明(月傍关山几处明)。
江边杨柳迷归梦(胡骑中宵堪北走),
塞上梅花送远征(武陵一曲想南征)。
万里乡思此夜起(故园杨柳今摇落),
故园露滴秋风生(何得愁中却尽生)。
在杜甫《吹笛》所押清、声、明、征、生等韵脚中,清、明为形容词,“清”的主体由“风月”变为松林,而“明”的主体由依傍关山的明月所映照思乡之人,转为月轮自身;“征”可作动词亦可作名词,原作“想南征”应为“想征南”,而次韵之作以之为名词,又代指远征之人;“生”为动词,原作乃指在愁中所生故园之情,而次韵之作已在出句点出“乡思”因笛声袅袅所起,故以秋风之“生”渲染此种悲凉气氛。
由此可见,以实词为主的韵脚相对容易通过主语或定语的转换,在一定程度上承接原作的意义,但与旧韵的关系未必能通过这一方式拉开距离,给熟悉原作的读者带来新鲜与陌生之感,有些次韵之作或有“偷语”之嫌,(6)这里借用皎然《诗式》所谓“三同”中的“偷语”的概念,皎然所举例子为陈后主诗“日月光天德”取傅长虞“日月光太清”,“上三语同,下二字义同”。见李壮鹰校注《诗式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9页。如徐氏与原周母女所拟李商隐《访隐者不遇成二绝》其二[1](P633)[1](P892):
竹巷松蹊客到稀,猿啼日暮掩荆扉。
浮云踪迹无寻处,独过青山风满衣。
山深水迭人烟稀,但见闲云拥竹扉。
声名不入五侯宅,何处高冈远振衣。
世事相违识者稀,白云青竹绕柴扉。
空庭惟有双飞鹤,不见幽人花满衣。
前两首为徐氏作,后一首为原周作,原周的次韵几乎全袭李商隐原作:“城郭休过识者稀,哀猿啼处有柴扉。沧江白石樵渔路,日暮归来雨满衣。”[2](P2090)所谓“识者稀”是隐居的原由,洪氏将其归为“世事相违”,亦可视作点明这一缘由;而“柴扉”一词沿用,并以“白云青竹”环绕而形容之,则是突出了环境的清幽,徐氏虽然以“荆扉”和“竹扉”进行了替换,实际上没有必要也难以改写隐居的环境,和这一环境所营造出的清幽氛围,何况徐氏的第一首作品也承袭了原作“猿啼”和“日暮”的意象;“雨满衣”在次韵之作中被转换为“风满衣”和“花满衣”,无非是以自然中的风霜花月来映衬隐士(幽人)这一主题,亦无新意。
值得注意的是徐氏第二首次韵之作,化用左思《咏史八首》其五“被褐出阊阖,高步追许由。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4](P990)之意,摆脱了原作自然物象的限定,实现了在韵中运用典故,(7)孙立尧《山谷次韵诗艺术论》(《清华大学学报》,2020年第4期)讨论了黄庭坚次韵诗在韵中用典,以此争“一韵之奇”的情况,可参。以此对原作旧韵更为彻底的转换,这种转换方式无疑是次韵诗因难见巧之处。(8)徐氏《次归去来辞》“临沧浪兮濯缨,陟高冈兮振衣”(《朝鲜时代女性诗文集全编》,第663页),亦用左思《咏史》“振衣”的典故。而从原周以“野花”次韵“《后庭花》”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将典故或专有名词一般化,显然是更简单更容易符合新作意境的做法。(9)类似的例子亦有洪氏《次杜晴》尾联“丛菊西窗下,芳香已醉心”(《朝鲜时代女性诗文集全编》,第904页),杜甫《晴二首》其二为“回首周南客,驱驰魏阙心”,典出《庄子》“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而洪氏“醉心”用以形容丛菊芬芳,并无用典。徐氏以“岁阑频作江湖梦,莼菜鲈鱼也已肥”(《右忆鸥湖》)[1](P640)次韵杜甫《秋兴八首》(其三)“同学少年多不贱,五陵衣马自轻肥”[3](P1487),张翰“莼鲈之思”的典故,亦见于《次归去来辞》“子陵一竿,季鹰扁舟”。[1](P664)洪氏继承母氏所用之典,作“寂寞渔舟空自系,旅窗谩忆鲈鱼肥”[1](P908)。杜诗典出南朝诗人范云“裘马悉轻肥”,而洪氏母女用晋人张翰“莼鲈之思”之典替换,更加符合次韵之作所抒发的羁旅思乡之情(徐氏诗颈联“三载光阴旅馆暮,一生心事故山违”),可谓是极为成功转换,用杜诗旧韵,而以他事抒发胸臆,造语自然,用典切当。
不过,在洪氏母女的诗歌中,刻意追求在次韵的韵脚中用事,以此实现转换原作之韵的内涵,并不是一种常见的手法。与原作题材相关的其他唐诗名作名句,亦是次韵之作灵感的重要来源,如原周《苑中遇雪》实为次韵宋之问《苑中遇雪应制》(《唐诗品汇》卷四十六),原作押来、台、开韵,末句作“疑是林花昨夜开”,而原周次韵借鉴了岑参名句“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唐音》卷三)[5](P253),以“千林万树琼花开”[1](P892)次韵。琼花与梨花皆为白色,以其比喻白雪亦无不可,宋之问原作即有以花树喻白雪之意,而岑参之作以色白之花进一步坐实此意,洪氏则以稍加改动岑诗的方式次韵宋作,实际上已经不为“开”字押韵所局限,而是句意层面的移植与借鉴了。
同样的情况亦见于次韵杜甫《峡口二首》其二,原作“疲苶烦亲故,诸侯数赐金”[3](P1555),原周《次杜峡口》尾联曰“蓬转京华远,家书胜万金”[1](P905),乃以杜甫《春望》“家书抵万金”为语典,易“抵”为“胜”,则更显出家书之贵、羁旅之愁(“猿声伤客心”)。《次唐闻歌韵》“仙娥香梦秦楼断,游女佳气汉水多”[1](P912),李商隐原作《闻歌》“铜台罢望归何处,玉辇忘还事几多”[2](P2072),洪氏用《周南·汉广》之典,并以秦穆公女弄玉的传说为出句,不仅对仗精工,所构成的华美而凄迷的氛围,亦与李商隐的风格相近;同时亦突破了自己借用古人陈辞过甚的做法,为以次韵诗的形式模拟经典诗作别开生面。
淑善翁主次韵李白诗的作品中,亦有化用前人之句的情况,如《次前人绿水曲》“莲花复莲叶,一色不见人”[1](P969),李白原作为“荷花娇欲语,愁杀荡舟人”[6](P346),“荡舟人”指齐桓公夫人蔡姬,事见《左传·僖公三年》;淑善翁主的次韵诗则取王昌龄《采莲曲》(《唐音》卷七、《唐诗品汇》卷四十七)“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乱入池中看不见,闻歌始觉有人来”[5](P345)之意,正是黄庭坚所谓“不易其意而造其语,谓之换骨法”[7](P265)在次韵之作中的体现,一方面避免了全袭古人陈言,而另一方面则体现了作者善于模拟,追求“貌异而心同”的效果。(10)这里借用了刘知几《史通·摸拟》篇的概念,浦起龙指出“六朝著述,率趋摸拟。子玄就彼风尚,析出形神两途,顿使仙凡立判”。[唐]刘知几著,[清]浦起龙通释《史通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209页。
不过,在韵脚是特殊名词的情况下,次韵诗转换出新的意蕴,恐怕并非易事。如淑善翁主《次前人(王维)崔九弟欲往南山与别》“莫度春色暮,柳絮飞如霰”[1](P971),霰是一种天气现象,即白色不透明的小冰粒,此字并无其他义项,王维原作“山中有桂花,莫待花如霰”(《唐音》卷六)[5](P332),以霰比喻桂花飘落,翁主所作,亦以霰为喻体,延续了王维原作。而次韵储光羲《洛阳道作献吕四郎中三首》其二(《唐音》卷六,《唐诗品汇》卷四十)之作所谓“白马黄金鞭,五陵年少多。乱入酒肆中,珊珊响玉珂”[1](P974),珂是白色似玉的美石,常用作马勒的饰物,储光羲原作为“大道正如发,春日佳气多。五陵贵公子,双双鸣玉珂。”[5](P334)诸如“霰”“珂”等较为生僻的韵字,几乎未能给次韵诗作者留有更多的转换空间,延续原作的用意恐怕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
同时,生僻韵脚而致“强押”的情况,在洪氏的次韵诗中亦曾出现,如次韵《古诗十九首》之《明月皎夜光》“南箕北有斗,牵牛不负轭”,李善注曰:“言有名而无实也。《毛诗》曰:维南有箕,不可以簸杨;维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睆彼牵牛,不以服箱。”[4](P1346)轭即牛马拉车时颈上所附器具,引申为束缚之意,原周次韵诗则云:“已忘童稚友,谁复念旧轭。”[1](P901)洪氏所述乃原作“昔我同门友,高举振六翮。不念携手好,弃我如遗迹”之意,然而所谓“旧轭”,不可能以牛马所用压迫颈部之器具,象征过往友情,故而此处只能视作“强押”。而《次唐闻歌韵》“丹唇开处翠眉峨”[1](P912),“翠眉峨”应为“翠蛾眉”,代指歌女;李商隐原作为“高云不动碧嵯峨”,嵯峨指山势高耸,若押韵为“峨”,势必难以摆脱原作,原周以“蛾”代“峨”,又颠倒语序,乃格律诗规范之下的权宜之计。
此外,若韵脚恰好是联绵词,次韵亦难以突破,如洪原周次韵《古诗十九首》之《西北有高楼》之作,原句“清商随风发,中曲正徘徊”押“徊”韵,亦不得不以“栏前双燕舞,感此起徘徊”[1](P901)和之了。有趣的是,宋仁宗朝臣亦遭遇过类似的困境:“仁宗赏花钓鱼宴赐诗,执政诸公洎禁从馆阁,皆属和,而诗中‘徘徊’二字,别无他义,诸公进和篇,皆押‘徘徊’字。”[8](P207)由此可见,尽管可以通过使用僻典等手段因难见巧,但次韵依然可能被旧韵的特殊性“围困”,除了无奈遵从别无他法,这或许是次韵诗这一形式感极强的文体为它的作者所下的一道魔咒吧。
三 旧韵与新作的离合
次韵诗在形式上追步原作的韵脚的同时,原作的主题与风格亦影响着唱和者,理论上以古人旧韵“用申今情”并无不可,(11)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评价傅咸、应璩一体为“全借古语,用申今情”(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1001页),作为集句诗渊薮的《七经诗》符合此语,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可以称次韵诗为“全借古韵,用申今情”。但次韵诗多大程度上可以表现作者自己的情怀和风格,实际上是值得怀疑的,由此可见“韵”的限制不仅在于形式,作者在次韵的过程中也自觉不自觉模拟原作的风格与主旨,在某种意义上追求与原作的“神似”;同时,在和作中融入自己的情感体验与价值观念亦并非不可能,在洪氏家族女性的次韵诗中,我们可以看到旧韵与新作之间的“合”与“离”,从中体会到作者以何种态度接受原作的影响。
洪原周《幽闲集》中的次韵诗通常与原作在主题上相合,如《隋宫怀古》次韵李商隐《隋宫》,亦是怀古之作,《蜀相》亦次韵杜甫《蜀相》,“草庐三顾起卧龙,祁山六出有余音。若添先主十年寿,能成丞相一片心”[1](P885)敷陈老杜“三顾频繁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3](P736),虽不免直白浅露,但也写出刘备、诸葛亮君臣机遇之幸,与武侯壮志未酬之憾;《长安秋夜》“霜落梧叶觉新秋,雁归远浦声入楼。风清雨霁白云歇,天高月出绛河流”[1](P885),次韵卢纶《长安秋夜即事》(《唐音》卷五),从“霜落梧叶”“雁归远浦”“风清雨霁”和“天高月出”亦可知其写秋夜;《和杜初月韵》“新月虽云微,光已满长安”,“纤纤不满弓,留约三五团”亦写新月。[1](P890)由此可见,无论是咏史怀古,抑或写景咏物等作,洪氏并未有意在体裁上特地与所次韵的原作产生差异,以此给熟悉原作的读者一种新鲜感与陌生感。尤其是写景与咏物之作,更容易流于俗套和重复。
《幽闲集》和杜诗之作多达三十八首,此外王维和李白等盛唐大家亦备受瞩目,如果说作为闺阁少女的原周学习老杜“沉郁顿挫”的风格有一定难度的话,那么王维诗歌描写田园风光,似乎离洪氏的生活与情感距离更近,如集中《辋川闲居》[1](P884)、[9](P1999):
朝日映闲窗(一从归白社),
青山绕柴门(不复到青门)。
濯缨坐前溪(时倚檐前树),
骋目对远村(远看原上村)。
瘦竹自生影(青菰临水映),
细柳因风翻(白鸟向山翻)。
林下无所事(寂寞於陵子),
种树成一园(桔槔方灌园)。
其中颔联“濯缨坐前溪,骋目对远村”之语,正是王维原作笔下的隐士最自然的生活状态,王维所谓“倚树”和“远看”显得过于平实,洪氏次韵则以“濯缨”和“骋目”重述类似的场景。其中,“濯缨”典出《楚辞·渔夫》“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4](P1533),比喻世道清明,可以出仕做官,此处用来形容隐居,似不如“濯足”更为合适,大约洪氏不愿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给人以当世昏暗的误解。颈联对原作的模仿痕迹也较重,“瘦竹自生影”无疑与“临水映”同义,只不过隐去“临水”;而韵字为“翻”,则改变了王维原作所写白鸟,依然以植物为主体,只不过细柳无从自翻,便以“因风”为凭借,亦在意义上与瘦竹“自生”而对。由此可见,无论是次韵还是模拟王维田园诗,其中的隐居场景,都可以通过转换语词和物象,构成新的文本,而在风格和情感上并未超越原作的藩篱,从这一点看,洪氏的次韵诗是与原作相合的,次韵诗亦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拟作。
拟作与次韵可以在文字上亦步亦趋地追随前人,但并非意味着全无倾注个人情感与价值观的可能性,严羽所谓:“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沧浪诗话·诗评》)[10](P667)这些与人生变故相关的题材,最能引起时人与后人的共鸣,也因注入了诗人的人生经历与情感体验而成为佳作。徐氏与原周母女次韵王维《送元二使安西》之作,实为送别洪氏长子洪奭周之作:
《送长儿用阳关韵》:苍苍晓色暗行尘,怅望楼头别恨新。多情最是陇山月,今夜分明远趁人。[1](P635)
《次右丞渭城韵送兄》:官楼云暗雨声新,征马嘶风驿路尘。今夜离情陇外客,明朝应作洛阳人。
《又》:遥看官路暗行尘,雨洒风翻草色新。此地年年几度别,秋来莫作未归人。[1](P896-897)
王维原作中的“渭城朝雨浥轻尘”,被洪氏母女代之以“行尘”或“路尘”,以此诉说着亲人行旅艰辛;“客舍青青柳色新”描摹雨后柳叶的青翠,而徐氏所谓“别恨新”看似语不惊人,然而不管是送别,还是“离别之作”,何尝不是永远新的旧事呢?无疑,每个人的一生都难免经历,而平凡人生中的波折,正是让诗人内心泛起微澜的风。与之相比,女儿原周的“雨声新”,无疑更贴合原作“渭城朝雨”,“草色新”则是转换了“柳色新”的主体,未免失之滑熟。在王维原作中,前两句写景作为起兴,而后两句写离别的场景,徐氏之作则在此句就点出主体的“别恨”,此后将个人的情感寄托于明月,明月多情故而追逐离人远去。“远趁人”应语出杜甫《题郑县亭子》“巢边野雀群欺燕,花底山蜂远趁人”,仇注指出“雀欺蜂趁,喻众谤交侵,而一身孤立,故自伤幽独耳”。[3](P484)为山蜂追逐自然不是乐事,但“明月逐远人”则有了几分温情,在意蕴上颇为接近李白“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
同样是用古人旧韵以抒今情,原周的“今夜离情陇外客,明朝应作洛阳人”则是借用了王之涣《九日送别》的句式:“今日暂同芳菊酒,明朝应作断蓬飞。”(《唐诗品汇》卷四十八)[9](P1597)王之涣的作品,在意蕴上与王维“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类似,皆以酒送别友人,表达了离别之后的漂泊无依。洪氏第二首“秋来莫作未归人”,当檃栝唐人崔鲁五言绝句《晦日送别》“明年春色至,莫作未归人”(《唐音》卷十四)[5](P420)之意。由此可见,次韵之作固然不限于模拟古人的游戏之作,亦可以抒发作者真实的情感体验,然而洪氏母女在选择次韵的对象之时,依然倾向体裁相近的作品,如王维之作乃送别友人之诗,原周所用的唐人语典,亦不出于送别之作的范围,次韵之作与古人之诗相合,而非有意与古人争胜,由此或可窥见洪氏母女效仿和学习经典的心态。
不过,次韵之作既然可以用来表达非常个人化的情感,也就意味着次韵者不可能完全在作品中隐匿自己,完全甘心成为经典的影子。洪氏母女次韵《古诗十九首》的作品,就有意与原作产生距离。徐氏《拟古诗仍次其韵》二首分别次韵《古诗十九首》之《行行重行行》与《青青陵上柏》,《行行重行行》写思妇之情,而徐氏次韵之作,则抒发了对亲子远行未归的思念[1](P637)、[4](P1343):
烟光何漠漠(行行重行行),
草色何离离(与君生别离)。
踯躅陇头立(相去万余里),
翘首望天涯(各在天一涯)。
众鸟趋林喧(道路阻且长),
喃喃何所知(会面安可知)。
乔木郁苍苍(胡马依北风),
岂无安巢枝(越鸟巢南枝)。
日暮耘歌催(相去日已远),
风暄村笛缓(衣带日已缓)。
长路隔云山(浮云蔽白日),
行子几时返(游子不顾反)。
主恩频许暇(思君令人老),
归来不愁晚(岁月忽已晚)。
篱花日向好(弃捐勿复道),
待儿持作饭(努力加餐饭)。
从“行子几时返”句,结合徐氏《令寿阁稿》中《长儿失期不来,次杜韵寄示怅望之怀》一诗可知,次韵之作并非“为赋新词强说愁”,而是自己的真情实感。徐诗以烟光漠漠、草色离离起兴,并未如原作一般直抒胸臆,次句则描写自己翘首期盼、望眼欲穿,继而以众鸟归林,反衬出长儿失期为归,因国事身不由己。但君主恩重,总有归家之日,这似乎有意与原作“浮云蔽日”之喻相悖,以此表示自己虽然伤于思子之情,但无怨无怒,较原作以“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结尾,无可奈何的同时,又只能无穷无尽地继续思念游子,徐氏次韵的结尾显然渐渐从“行子几时返”的“低谷”,走向一种乐观的情绪。“篱花日向好”当出于陶诗之典,代指菊花,(12)《长儿失期不来,次韵寄示怅望之怀》有“归来何太晚,空负菊花期”句(《朝鲜时代女性诗文集全编》,第654页),似乎作于此时之后,洪奭周在菊花花期过后依然未归。徐氏希望长子能尽快归家与之共赏;而“待儿持作饭”则是所有母亲对子女爱意的直接体现。无数子女在归家之后能吃到母亲亲手所做的饭菜,亦是人生最大的幸福,其中包含的情感,虽然是无数人表达过的、人类的共同情感,但徐氏将其写入次韵之作中,自然流露出与原作完全不同的情绪,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摆脱了原作形式与主题的影响,得以“全借古韵,用申今情”。
女儿原周集中亦有六题次韵《古诗十九首》,分别为《西北有高楼》《明月皎夜光》《庭前有奇树》《驱车上东门》《去者日以疏》《人生不满百》,其中次韵《西北有高楼》表达了“达且不足喜,穷亦何为悲。寄言闺中妇,不愧梁鸿妻”[1](P901),与原作“上有弦歌声,音响一何悲!谁能为此曲?无乃杞梁妻”[4](P1345)的情感基调与价值观念截然不同,洪氏推崇梁鸿妻孟光与丈夫归隐山林,甘于贫贱的人生选择和道德操守,在次韵“悲”与“妻”之时,一改原作所描写的悲音悲情,即便“鼓瑟和且乐”,又“何须奏清哀”,更是一反原作“一弹再三叹,慷慨有余哀”;末尾四句更是亦“神龙隐碧海,莫恨知者稀。甘雨沛然下,乃知云中飞”,似在表达“君子藏器,待时而动”(《周易·系辞下》)的观点,一方面有意以此突破原作“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的情绪,但另一方面又与前文所褒扬的隐居之士稍嫌违和,“见龙在田”应当有“飞龙在天”的一日,或许更符合洪氏自身的价值观念吧。
整体而言,《古诗十九首》普遍表达的失路之悲,和由此而生发的人生虚无感,恰是原周所不喜欢的情感倾向与人生观念,这对于一个生活在一千六百年之后的异国闺阁少女来讲,并非不正常。次韵《驱车上东门》中,她与原作者一样质疑“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4](P1348),“可笑汉武帝,能得千秋度。惜哉英武质,偏被方士误”[1](P902)。但原作最终走向“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的颓废与无奈,而原周则反思“自古皆如此,不如守清素”,则是安于清苦平淡人生的志向及追求。
由此可见,次韵诗尽管在形式和体裁方面限制著作者,但作者个人的创作才能和人生体验依然得以在次韵之作中反映,毕竟次韵古人之作与现场的、友朋之间的酬唱有所不同,(13)巩本栋《唱和诗词研究——以唐宋为中心》(中华书局2013年版)一书第三章《唱和诗词的类型与评价》将唱和诗词分为“同好之唱和”“同处之唱和”“同境遇之唱和”“同体验、同感慨之唱和”“同声气之唱和”,除了“同处之唱和”外,其余四种原作与和作均可能有一定的时间与空间的距离。作者选择次韵对象的余地更大,他们可以附和古人,也不妨翻案,亦可与古人争胜,或借用前人的旧韵完完全全表达属于自己的情感,这是一种主动的选择而非被动的接受,次韵诗的“魔咒”在这种情况下,又极有可能被诗人的才华与个性解除。
——兼议《中国书法全集73》徐氏楷书编排之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