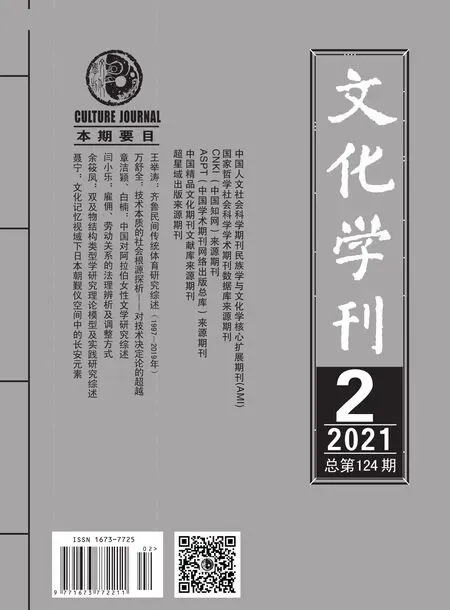浅谈苏轼出岭北归之次韵诗
朱 慧
次韵诗是唱和诗的一种,发源于唐代,在北宋时期得以繁荣。北宋很多为官出仕的士大夫都加入了次韵唱和的行列,代表诗人有王安石、苏轼、苏辙、黄庭坚等人。“宋初的《西昆酬唱集》,仍遵循着和意不和韵的老传统。和韵诗和险韵诗的大规模出现,是与宋人‘以才学为诗’的创作倾向同步的……随着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相继主持诗坛,次韵、险韵之风愈演愈烈。”[1]535-536宋代的次韵诗在数量与质量上都有极大提高,次韵诗的理论也得到了发展。宋人刘攽在《中山诗话》中对唱和诗的三种形式归纳了明确的定义[2],从其对次韵诗的界定来看,次韵诗要求诗作的韵字和次序都必须和原作一样,因此是唱和诗中最严格的一种。次韵诗在苏轼笔下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在苏轼诗歌创作生涯中,次韵诗的创作丰收期是苏轼贬谪时期,贬谪岭南时期是主要丰收期之一。在北归大庾道的路上,苏轼总共留下次韵诗20余首,约占北归大庾道时诗歌创作总量的一半。这一阶段,苏轼次韵诗的次韵对象主要是自己的诗歌以及次韵他人的诗歌。其中,次韵自己过去创作的诗歌居多,可分为次韵入岭时的诗歌、次韵出岭时先作的诗歌。
一、次韵南贬时期自己创作的诗歌
关于次韵南贬时期自己创作的诗歌,其中既有次韵自己南贬路途中的诗歌,也有次韵在岭南谪地生活的诗歌,如《次旧韵赠清凉长老》,即是次韵在南贬路过金陵时作的《赠清凉寺和长老》;又如绍圣元年(1094),苏轼在入岭过大庾岭时创作的诗歌《过大庾岭》:
一念失垢污,身心洞清净。浩然天地间,惟我独也正。今日岭上行,身世永相忘。仙人拊我顶,结发受长生。[3]2057
建中靖国元年(1101),诗人出岭时,再过大庾岭,想着入岭时的情景与心境,不免有感而发,于是创作次韵诗《余昔过岭而南,题诗龙泉钟上,今复过而北,次前韵》:
秋风卷黄落,朝雨洗绿净。人贪归路好,节近中原正。下岭独徐行,艰险未敢忘。遥知叔孙子,已致鲁诸生。[3]2425
韵脚字是“净”“正”“忘”“生”。从这两首诗来看,相同之处都是诗人登上大庾岭时创作的诗歌,皆是诗人真实心境之反映。不同之处在于:一是诗人过大庾岭的情况不同,前一首是南贬时路过大庾岭所作,后一首为诗人北归时路过大庾岭而作;二是诗人创作的心境不同,前一首诗歌的创作心境是痛苦的,后一首诗歌的创作心境是较为释然的;三是风格不同,前一首超脱中多沉郁,后一首是超脱中多明朗;四是主题不同,前一首表达了诗人遭贬后绝尘凡念的想法,后一首表达了诗人想被朝廷重用的愿望。
此外,苏轼入岭至虔州时写下了《郁孤台》一诗,在出岭路过虔州时,用《郁孤台》的韵字“游”“流”“秋”“洲”“楼”“州”“留”“舟”,写下了次韵诗《郁孤台》,但入岭与出岭写下的同题《郁孤台》,风格是不同的,创作的心境也是不同的。另外,苏轼还有用《郁孤台》的韵字以酬和他人的次韵诗,其唱和的对象都是与虔州有关的人,有虔州官员,如郡守霍汉英、监郡许朝奉(已失考),二人都对苏轼的诗进行了唱和,但今不传。苏轼又用上述韵字写了《次韵阳行先》一诗,引用禅宗之思想,使诗歌具有禅意。这首诗歌将阐发禅思、叙述阳行先本人、表达心境的内容融合一体,用次韵的方式写出,未体现出次韵的痕迹,反而显得更加自然、浑然天成。
还有就是次韵诗人在贬地惠州的诗作。在惠州时,苏轼有写给王子直的《赠王子直秀才》。后来,苏轼北归至虔州时,与王子直相逢,在分别之际,他用原诗韵字“游”“谋”“头”“侯”,次韵前诗写下别诗《王子直去岁送子由北归,往返百舍,今又相逢赣上,戏用旧韵,作诗留别》,表达了对友人王子直的美好祝愿。
二、次韵出岭时先作的诗歌
苏轼创作的次韵诗中也有次韵出岭时先作的诗歌,且数量较多,其次韵唱和有与兄弟苏辙、与方丈的唱和。与他人的唱和,分别次的韵是一样的,遗憾的是未见他人对苏轼之唱和诗作。
与苏辙的次韵唱和是苏轼在出大庾岭时写下的《过岭二首·其二》,按照这首诗歌的韵字“甘”“南”“岚”“毵”,并按次序写了一首诗寄予弟弟苏辙,题为《过岭寄子由》,其诗歌抒发的是得到朝廷诏令能够成功北返的激动与庆幸,但从“能雪冤忠死亦甘”“一片丹心”“数行清泪”等可以看出,这首诗歌更多表达的是诗人的自证清白与忠于朝廷之心。此首诗歌写出之后,苏辙回应了其兄苏轼,次兄诗韵写下《和子瞻过岭》。
次韵诗还有与和尚的唱和,如苏轼出岭至虔州时,因为受到禅宗的影响,所以,在北归路上览寺庙、访游方丈。在游览虔州的一座寺庙时,苏轼创作了一首《乞数珠赠南禅湜老》赠予寺庙的南禅长老。后来,苏轼又用韵字“遣”“转”“衍”“卷”“喘”“反”“茧”“浅”,与南禅长老次韵唱和四首诗歌,其中《南禅长老和诗不已,故作〈六虫篇〉答之》最大的特色在于戏谑的意味较为明显,此诗旁征博引,例如首两句征引贾谊、马融对凤凰、鸿鹄的书写,第三至六句征引庄子文章中的燕子、井底之蛙,韩愈诗歌中的蠹鱼,与首两句的大动物进行对比,突出了小动物的微小与见识短浅,最后两句引用了《风俗通》《世说新语》中关于老牛“见月则喘”的典故。这些引用也是诗人自比,戏谑自身的拙知以及年老之辛苦。诗歌的后半部分体现了诗人与南禅长老唱和的紧密。《明日,南禅和诗不到,故重赋数珠篇以督之二首》也是与南禅长老唱和的诗作,体现了禅宗思想。以上与南禅长老的唱和诗作,既体现了苏轼与南禅长老探讨思想之深入,也体现了诗人博学的思想,尤其是高深的禅宗学问。
三、次韵他人他作
除了次韵自己创作的诗歌,苏轼也次韵他人的诗,包括次韵友人、次韵北归路上遇到的当地官员、次韵家人侄儿等。遗憾的是,被苏轼次韵的原诗歌未找到,因此,本节主要探究苏轼创作的次韵诗的特色。
在北归韶州时,苏轼与郡守狄咸有交游唱和。狄咸的诗歌不存,苏轼有《次韵韶守狄大夫见赠二首》。其一,主要写诗人遭受贬谪后,无所寄身、生活窘迫、恃才放旷;回归之时,宋哲宗已驾崩,回想以前由于得到宋哲宗的赏识而从政七年之久,心中十分沉痛。这首诗歌既表达了苏轼遭受的苦难,也表现了对君王的忠诚。其二,是赞美狄咸。诗歌前四句引用白居易警策之言、杜甫之论,以及颈联中用西汉东海兰陵人疏受来比狄咸,还有尾联的溢美之词,皆是对狄咸的赞美。
另外,诗人在韶州时,曾与舒州“龙眠三李”之一的李公寅共游,写下了《次韵韶倅李通直二首》。虽是次韵李公寅的诗歌,但这两首诗歌的主题内容皆与诗人自身有关。这两首诗歌有所差异,其一,的前两联主要论述遭贬谪后又回归的感受;颈联叙述了诗人与李氏的交情;尾联“回首天涯一惆怅,却登梅岭望枫宸”[3]2411,“枫宸”指天子殿庭,表达了诗人依旧心系君王之情。其二,主要是在探讨北返之后的定居问题,展现了诗人想定居在舒州的想法。
苏轼在北归至虔州路上,还有与其他文人的次韵唱和,如与孙志举的唱和,孙氏一家与苏氏一家皆有交游唱和。孙氏为虔州虔化人,苏轼到虔州时,孙志举从乡里来访,苏轼有唱和诗作留下。这类唱和诗歌是为了次韵其侄子苏迟之诗而创作的,如《和犹子迟赠孙志举》,诗歌推奖了志举之博学工诗。全诗并非单单只是赠诗,从诗人所采用的侄子诗作之韵以及全诗的主题内容,可以看出,此首诗歌主要在于激励后辈,立意较远。此外,还有《用前韵再和孙志举》,全诗除了最后写了对志举的劝勉,主要还是在叙写想象中回成都的生活,以及关于室、堂取名,还有涉及朋友、后辈、乡里乡亲、学问的理想描述,表达了对晚年回家生活的向往。《崔文学甲携文见过,萧然有出尘之姿,问之,则孙介夫之甥也。故复用前韵,赋一篇,示志举》一诗则主要是对孙立节的侄儿崔甲的书写,以及对其诗文创作的赞赏与鼓励。
在虔州时,江公著(字晦叔)也有与苏轼的交游唱和。其实,在这之前,苏轼和江公著已有过交游,苏轼曾有诗作《送江公著知吉州》,因此,在虔州再次见面,两人自然有所唱和,但江公著予苏轼的诗作已不存,苏轼次韵江公著创作了诗歌《次韵江晦叔二首》和《次韵江晦叔兼呈器之》。
四、苏轼出岭北归次韵诗之特色
对苏轼次韵诗歌的概述与分析发现,苏轼晚年北返创作的次韵诗,形式上基本是同一韵中表达一个主题或一个题材,如次韵《过大庾岭》之诗,皆是过大庾岭时创作的;次韵《乞数珠赠南禅湜老》的诗作都是对南禅长老的酬和;次韵苏迟赠孙志举诗的系列诗作,都是酬和孙志举的。从内容上看,虽然苏轼的次韵诗大多是酬和之作,但读其具体诗作会发现,诗歌中多言之有意、有感、有味,而非单纯的唱和,如《和犹子迟赠孙志举》表达了对孙氏后辈、苏氏后辈的鼓励;与南禅长老的唱和诗,深入探讨了禅论;其他的唱和诗也有对自身问题的思索。从题材上看,苏轼之前的次韵诗大多单纯作为酬和,适用范围较为狭窄,在苏轼笔下,次韵诗得到了发展,题材扩大了,内涵加深了。从技巧上看,苏轼的次韵诗的创作更加得心应手。一方面,一韵多诗的情况在苏轼的诗歌创作中比较常见,如苏轼用《郁孤台》的韵写了五首诗,用《乞数珠赠南禅湜老》次韵写下了四首。另一方面,苏轼在诗歌创作中使用了次韵险韵,如《过岭二首·其二》《过岭寄子由》这两首诗中,韵字“甘”“南”“岚”都较为常用、常见,唯最后一“毵”字是较为少见、奇险的,在《过岭二首·其二》中押险韵已是不易之事,而在《过岭寄子由》还成功地次韵了险韵,这足以体现出苏轼次韵诗创作技巧的高超。“成功的次韵之作是韵与意的统一,是奇特精工与自然浑成的统一,它出自作者胸藏万卷的学术涵养和艺术修养。”[1]538-539因此,即使是一韵多诗、险韵多诗,苏轼创作的次韵诗并没有因韵害意,反而读之十分自然,甚至有些作品看不出是次韵诗,这足以体现苏轼有较强的文字驾驭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