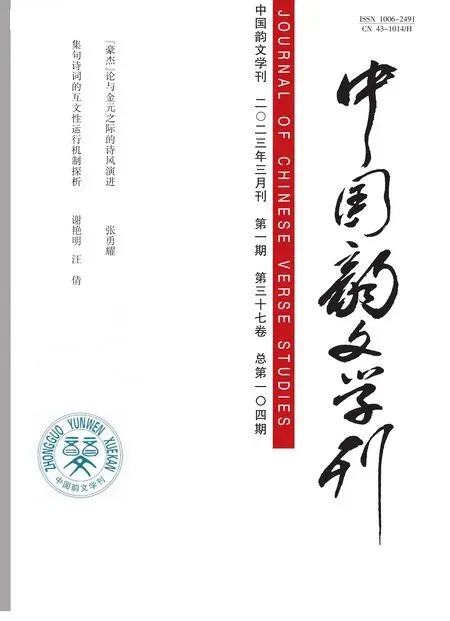“致广大而尽精微”:肖瑞峰《诗国游弋》略评
李锦旺
(宁波财经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宁波 315175)
《诗国游弋》是肖瑞峰教授新近出版的一部学术论文自选集,其遴选标准没有采纳学术界通行的“学术独创性”与“学术影响力”这两条常规尺度,而是别出心裁,“以反映本人学术全貌及进阶”为价值取向,因此颇以原生态的形式呈现出作者学术探索与开垦跋涉的足迹,凝聚着鲜明的学术个性与智慧。对个人而言,这或许不失为一次十分有益的学术总结;而对学术界而言,也足有启迪后学与金针度人之潜效。如果尝试用一句简洁的话语对作者的治学门径与学术特色加以概括的话,窃以为“致广大而尽精微”庶可当之。
一 “致广大”的恢宏格局
1.入门正大
肖瑞峰先生系十年“文革”终结之后中国高等教育尤其是研究生教育重回正轨以来培养出的首批古典文学研究生之一。当时的中华大地唱响了“科学的春天”的这一主旋律,但是“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二十年”[1](P37)。只有奋起直追,才能迎头赶上,居于我国教育体系金字塔尖之顶端的研究生教育,必然要义不容辞地承担起向国家输送高端科研人才的特殊使命。先生的学术起点显然也深刻地打上了改革开放之初特有的学术印记。他在负笈吉林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受到了张松如(公木)、郭石山、赵西陆、喻朝纲、王士博等杰出名师组成的导师团队的悉心面命与卓越指导,经历了严谨、规范而又系统的学术训练,为他日后在学术之路上行稳致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宋代诗论家严羽指出,“夫学诗者以识为主:入门须正,立志须高”[2](P1),并强调“论诗以李杜为准,挟天子以令诸侯也”[2](P168)。此论虽系针对学诗者而言,但又何尝不适用于古典诗学的研究者呢!据肖瑞峰先生回顾,郭石山先生曾有意识地指导弟子们“依次精研细读李白、杜甫、白居易集,并硬性规定每读罢一集都要提交一篇作业”[3](P468)。中国古典诗歌发展至唐代,高峰迭起,名家辈出,而李、杜、白等伟大诗人又堪称高峰中之高峰,由此入手研治古典诗歌,可谓深悉“入门须正,立志须高”之要诀。除此之外,先生还在诸师指导下研读了中唐杰出诗人刘禹锡与北宋西昆体巨擘杨亿的诗和婉约派大家秦观的词。在对上述六家诗词作品充分研读的基础上,先生撰写并陆续发表了十来篇论文,《诗国游弋》前两辑中的文章差不多过半属于本阶段的研究成果。其中《论刘禹锡的个性特征》与《重评〈西昆酬唱集〉中的杨亿诗》刊载于权威期刊《文学评论》与《文学遗产》;《春来花鸟莫深愁——杜甫花鸟诗探微》与《论淮海词》发表于颇具影响力的学术专刊《草堂》(后更名为《杜甫研究学刊》)与《词学》;《白居易三题》中的《“樊蛮”考》刊发于多收纳大家之随笔及札记的《学林漫录》;其他三四篇关于李、杜、白的论文亦分别见载于《北方论丛》《齐鲁学刊》等素有良好声誉的学术期刊。先生在短短两三年间不仅高水准完成了以刘禹锡诗歌为选题的硕士学位论文——研究刘禹锡的奠基者、南京大学卞孝萱教授“曾主持其论文答辩,以最优评语通过”[4](P1),同时还博涉诸家文集,精心结撰如此多高质量的学术论文,不仅足见其精专与勤勉,亦足彰其深得治学三昧!
吉大张松如、喻朝刚等教授颇以理论见长,受其濡染,先生对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的中外美学名著进行了广泛探索与熔裁取鉴,奠定了宽广而扎实的理论功底。针对古今学者断章取义指责李白在安史之乱期间醉酒使气,“窜身南国”,置身事外,远不如杜甫那样忧国忧民的苛论与谬见,先生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准绳,征引史料并结合李白大量作品辨真析伪,驳斥谬说,捍卫了太白作为伟大爱国主义诗人的崇高地位。《春来花鸟莫深愁——杜甫花鸟诗探微》不仅萃取郭知达、浦起龙、萧涤非、王嗣奭、仇兆鳌等古今杜诗学名家之成果,亦博采法国哲学家库申、苏联文学家高尔基以及我国古代诗论家王夫之、施补华、葛立方、叶梦得、刘熙载、刘勰等中外美学名家之观点,同时还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阐明杜诗虚实、动静、浓淡以及诗画相结合的艺术特质。先生在学习和运用中西理论与方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思维个性,既反对“食古不化”与“食洋不化”的学究气,又力倡以拿来主义心态借鉴其观察问题、分析问题的独特视角和手段,主张“脱略其形而求其神合”,做到“盐溶于水”,不着痕迹。
2.格局阔大
先生攻硕期间已经在学术上初辟开阔之局,在后续研究中又进行了纵横交错的多向开拓,形成了更为宏阔宽广的整体格局:一是在刘禹锡既有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深耕精研,往高、精、尖处作全方位的拓展;二是把目光由域内投向海外,开展并引领日本汉诗研究;三是由北宋杨亿、秦观进一步延伸至两宋时期最伟大的诗人苏轼与陆游,进行专题探讨;四是聚焦中国古典文学的别离主题,借以探讨中国文学的历史流程和古代作家的创作心理。
上述四大领域中,刘禹锡研究最为引人瞩目,计发表论文四十余篇,出版专著三部,但采撷入《诗国游弋》的仅有《论刘禹锡的个性特征》与《刘禹锡与洛阳“文酒之会”》两篇文章。不过二文恰好分属于作者早期与晚近之力作,而且均立足于“诗豪”这一研究制高点展开论述。前文透入刘诗之骨髓,就其特具的“骨力豪劲”的个性特征作了多层面的细致分梳与深入浅出的论述。后文则截取刘氏晚年创作的一个特殊时段,全面审视与辩证分析了他晚居洛阳时与诗友往还唱和所呈现出的既“欢快其外而悲苦其内”,又“锋芒虽匿,而气骨犹在”的独特创作景观,深入阐发了刘诗在保持稳定个性特质前提下的流变性与丰富性。两文对读,恰有互补与参证之效。
日本汉诗是先生的另一研究重镇,计发表近二十篇系列论文,出版专著两部。基于形式格律与历史、文化内涵和中国古典诗歌的相似性,先生认为日本汉诗既可视为“日本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可以视为中国文学衍生于海外的一个分支”[3](P229),因为“它总是分娩于中国文学的母体”[5](P212)。因此中国学者从事日本汉诗研究可以“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对中国古典诗歌进行总体观照和全面把握,使中国古典诗歌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得以拓展”[3](P229)。收入《诗国游弋》第三辑的五六篇文章,即是践行上述学术理念的一批力作。
3.视野宏通
《诗国游弋》展现的宏阔治学格局,映现出先生极其宏通的学术视野,二者实有相因相依、相生相成之妙。前者已如上论,后者亦体现出先生在理论方法上兼容并包的开放心态与科研上摆脱苟安一隅,大力拓展新领域的强烈使命。
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思想界迅猛迎来了又一次西学东渐的学术思潮,然而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大多数业内学者依然恪守传统的考订笺释等治学法门,“新方法论在古典文学研究界受到的抵制远比其他学科为甚”[3](P358)。在中西学术深度交融的特殊学术背景下,先生不仅积极投身于当时思想论争的急流与漩涡之中,而且试图因势利导,以推动古典文学研究跟上时代的浪潮。《关于古典文学研究方法的思考》《宏观研究与观念更新》等理论文章即系此时的探索成果。前文呼吁古典文学研究必须进行研究方法的变革,并对传统研究方法、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文艺观以及新方法论在运用实践过程中的利弊得失进行了全方位的省思,提出移植新方法的可行方案在于“内化”,并就“内化”的多元途径提出了颇具建设性的思考。后文则力主在古典文学领域开展宏观研究,认为宏观研究在学术思想日益系统化与整体化的时代背景下不仅势在必行,而且坚信“只要不再以抱残守缺的态度自我禁锢,那就一定会萌生出摆脱旧模式旧窠臼、变苟安一隅为周流寰球的强烈愿望,登上时代的制高点,在更宏阔的背景下,对扩大了的研究对象作时空合一的立体观照”[3](P353)。总体上看,先生每以上述理念自期自许,亦不吝以此称许学界同仁,如《评〈唐宋词通论〉》《评〈唐宋词史〉》两篇书评均对著者的哲学意识、历史意识与宏通视野赞赏有加。
4.目标高远
先生参与学术界的理论论争,并非着眼于各家理论本身的是非短长,而是确立了一个更具价值引领性的高远目标,即“勾通古今中外,促使‘中学’和‘西学’相互融合。在融合和改造的基础上,建立起新的思维定式和方法体系。不管其中有多少外来的成分,既然经过我们的融合、改造,必定具有中国的‘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3](P348)。当今学术界已在主流话语的强大引领下把“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视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主导方向,而先生却在改革开放之初西学盛行的时代倡发此论,体现出难能可贵的前瞻性与战略性。更重要的是,先生不仅这样说,而且这样做了。检视《诗国游弋》全书,随处散发着浓郁的“民族风格”和特色鲜明的“民族气派”。其中研治唐宋诗词的一系列文章仅透过诸如“花鸟诗”“文酒之会”“酬唱集”“时空艺术”“西湖镜像”“意象”“别离主题”等琳琅满目的主题词即可略窥我国唐宋时代韵文学特有的中华风韵与文化意涵,核之各文之论述,无不擘肌分理,尽洞其要。其研治日本汉诗的系列论文也一样打上了中华文化与诗学的烙印。《中国文化的东渐与日本汉诗的发轫》从中日跨文化交流与比较的视角审视中华文化长期流泽日本汉诗的曲折历程与丰富表现。基于“诗穷而后工”的中华诗学立场,先生不赞成某些日本汉学家所欣赏的菅原道真作为“诗臣”时的风范,而认为恰是迁谪生活“将他造就为‘诗人’后的作品才是弥足珍视的”[3](P317),从而得出了更加科学的结论,也合乎逻辑地将菅原的汉诗创作纳入中国诗学框架之内。
如果说入门正大得益于师门的科学培养与积极引导,那么先生超群拔俗的治学格局、博大深邃的学术视野、高瞻远瞩的学术目标则彰显出个人卓异的先天禀赋、勇于担当的学术精神、锐意攻坚的坚韧意志以及大力开疆拓土的浑厚学力。
二 “尽精微”的学术品质
先生不仅在治学理念上融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于一炉,亦在治学方法上兼采中西学术之长,从而使得《诗国游弋》在“致广大”的恢宏格局中蕴含着“尽精微”的独特学术品质。
1.思理精密
先生在理论上早入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美学之堂奥,崇尚实事求是、唯真是求的学术理念,长于运用缜密的辩证思维以破解各种学术难题。针对古今学者对西昆派尤其是杨亿诗从内容到形式全面予以否定的学术偏见,先生严谨详实地考察了杨亿诗歌创作的整体状况与有关背景资料,条分缕析地论证了其诗在内容上不仅心系宋室国运,而且融入了忧谗畏讥的身世之感,不乏一定的现实意义;在艺术上则使典无痕,寓实于虚,表现出一定的创造性;在诗史维度上亦对日趋平庸的白体唱和诗具有纠偏之效。在审慎甄辨杨亿诗艺术成就之后,先生呼吁“不应以偏概全,一笔抹杀,而应以马克思主义艺术论为指导,从作品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分析其艺术上的成败得失”[3](P130)。《苏诗时空艺术论》亦辟专节从艺术辩证法的角度探讨苏诗在时空艺术处理上的创获,提炼出微观时空与宏观时空的比照、静态时空与动态时空的转换、物理时空与心理时空的交融等多种创作模式,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先生尤擅于对经典作家及其作品进行“时空合一的立体观照”,以探赜其细腻曲折的情感流程与隐微难察的变化。如论述苏轼倅杭与守杭期间所作西湖诗的变化,从其身世投影入手由浅入深地钩稽出苏轼西湖诗的双重变化:一是政治诗的锐减,二是心境的变化。前者直接导因于倅杭时期所作政治诗诱发了“乌台诗案”等惨痛教训。就后者而言,守杭期间的西湖诗虽然风格如昨,但其情感基调、色调与咏物对象均发生了同步的变化:一方面,人生易老的寻常感叹嬗变为人生如梦的深刻感喟,同时摄入诗中的西湖景象也常常染上一层清冷甚至清寒的霜色;此外,倅杭时期在诗中所乐咏的莲花、桂花与牡丹也为守杭时期的梅花所取代,而且掺和着“前度刘郎”式的自怜自伤之感与“怕见梅黄雨细时”之类的政治隐喻。通过层层深入的对比与分析,作者把苏轼两度仕杭期间的创作变化作了细致入微的发掘。基于同一研究视角,先生对菅原道真汉诗创作之嬗变作了同样精妙的阐述,一方面理清了菅原由达入贬时创作上的显著变化,同时也对他两为“诗臣”即显达之际与两为“谪臣”即困顿之时诗歌情感与基调的细微变化均作了透辟的论析,大大深化了对菅原创作的整体认知。
2.论证精详
先生治学,坚持科学性与系统性的统一,当代科学常用的归纳法、列举法、统计法、对比法与作为传统学术之基石的考据法,先生常常交织运用,各极其妙。《中国文化的东渐与日本汉诗的发轫》即是一篇考论结合的典范之作。作者一方面考订汉字、汉籍输入日本之初况与日本汉诗创生之过程,钩稽日本遣唐使与留学生、僧侣传播中华文化与诗艺之历程,同时表彰日本历代天皇奖掖汉诗之盛况。在诸位天皇中,作者对村上天皇所论尤详,除举应和中召词臣赋“花光水上浮”诗和天德二年(958)举办“殿上诗合”之例外,作者还一气列举了诸如“内宴”“子日御游”等近二十种诗宴形式,就中对“曲水诗宴”与“重阳诗宴”作了尤为精细的考述,尽显“中国文化东渐”之魅势。《〈怀风藻〉:日本汉诗发轫的标志》则兼用数据统计与诗例分析的方法对《怀风藻》的体式(以五言八句居多)、句式(多用对句)、格律(平仄多有未协)与韵式(用韵雷同)作了极其详尽而精确的分析,无可辩驳地揭示出日本早期汉诗不可避免的“稚拙”特质。
先生还每以平怀审视唐宋诸大家,对其创作之得失作客观而完整的评述。《论陆游诗的意象》从巨量陆诗中提炼出雄阔、衰飒、清丽等丰富的取象类型与叠加法、比照法、拟喻法、逆反法等多元意象组合模式,对陆诗意与象的水乳交融以及独创性与丰富性的统一给予了高度的赞赏。但作者不仅无意于拔高陆氏,反而别开生面,系统梳理并且深入探讨了陆诗在意象熔铸与运用方面的两大突出缺陷:一是意象的因袭与重复,二是意象后缀以蛇足式的议论。最后水到渠成地得出了陆诗熔铸意象之实践成败兼具,值得今人总结与借鉴的结论。
先生亦长于对研究对象作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全面探究。《浙东唐诗之路与日本平安朝汉诗》前三节逐一论述了日本平安朝诗人向往天台,吟咏刘阮遇仙与严光垂钓以及抒发对剡溪的怀想之情,应该说已经完成了主要使命。但作者却在四五两节中以问题为导向继续把论域往深广处拓展:其一,日本诗坛何以迟至平安朝而不是在遣唐使频繁赴唐的奈良朝流行上述题材?其二,平安朝诗人何以唯独钟情于“浙东唐诗之路”而对唐代其他地区的风景名胜没有兴趣?作者采用传播学的视角就此作了深入透辟的论证。前一问题的解答是:日本汉诗的风会变迁晚于中国诗坛,奈良朝诗坛流行的仍是六朝诗,至平安朝以后摹拟对象才转变为唐诗。后一问题聚焦于“天台”,一方面认为“浙东唐诗之路”发端于天台,而天台恰是平安朝诗人渴望朝拜的佛教圣地;同时又指出无缘亲履天台的平安朝诗人是以留学僧为媒介来认识天台的,因而有关诗作没有采用奉佛者的观察角度与鉴赏眼光。通过引伸研讨,不仅得出了更加精审的结论,而且以“天台”为纽带与篇首遥相呼应,一气连贯,别具一种自然浑成之美。
3.解析精妙
先生虽然年近耳顺之年方始进行小说创作,但一发不可收,迄今已发表及出版中长篇小说数十篇,自觉地传承起“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中华文脉,彰显出诗心史笔的本真面貌。但事实上,先生在漫长的诗学研究生涯中早已洋溢着诗性的气质,所撰论著无论是商榷古今驳正旧说,还是博综群籍创立新论,都能直探诗家之心,直接从一手文献中获得内证与要证。
先生解诗,多要言不繁,往往通过透视一二人格化的意象即可披露诗人之心曲。如论刘禹锡诗“骨力豪劲”之特征,首先体现为“不畏‘衰节’,唱出意气豪迈的秋歌”,作者连举《学阮公体三首》之二与《始闻秋风》《秋声赋》等诗赋作品,拈出其中兼具个性化与类型化的三组意象——“老骥”与“鸷禽”、“马”与“雕”、“骥”与“鹰”,要言不繁地阐释出诗人寄寓其中的昂扬奋发的精神品质与雄风未减的报国壮志,给人豁然开朗之感。在论述杨亿诗充满忧谗畏讥、彷徨失路的危机感时,亦举《鹤》《禁中庭树》二诗并分析说:“作者借‘鹤’和‘禁中庭树’以自况,曲折婉转地传达了内心的款曲。孤鹤在漫天大雪中迷离失所、恓惶无依的痛苦情状岂不正是作者的孤危处境的形象写照?而‘岁寒徒自许,蜀柳笑孤贞’,一方面不乏傲视衰节的正气,另一方面又包含着忠而见谤、不为时知的无限惆怅和辛酸。它是自诩、自赏,也是自嘲、自伤。”[3](P126)寥寥百余字,即把诗中寓托的极其复杂的心志与情蕴披示无余。
即使那些纯用白描而无所寄兴的作品,先生亦每以简笔揭橥其妙谛。如论秦观词的羁旅之愁,曾品鉴其小令《阮郎归》说:“叙述旅况,无一字道及愁,无一字不含愁:‘风雨’敲窗,一重愁;‘庭院’空虚,二重愁;闻曲感兴,三重愁;乡愁梦断,四重愁;客中除岁,五重愁;无雁传书,六重愁。包裹在这么多愁里,不求解脱,也无法解脱,作者真可以算得上是‘天涯断肠人’了。”[3](P182)同样寥寥百余字,把词中潜蕴的“六重愁”层层析出,倘非兼具诗家之才情与学者之笔力,焉能如此举重若轻!
先生亦精于采用比较视角探析诗人之个性与作品之主题。为了深化阐释刘禹锡诗中不服老迈之“暮歌”,引入其文友诗敌白居易作为绝佳参照,认为刘诗更辩证地看到了老年人的有利因素与得天独厚之处,而白诗则大多咀嚼晚境之凄凉。为了突显刘禹锡的“诗豪”品性,又将李白、杜牧、苏轼、辛弃疾等同样以“豪”见称的文人纳入比较视野,认为他们的“豪”分别是“豪迈”“豪爽”“豪旷”“豪雄”,唯独刘禹锡体现为“骨力豪劲”。当论析陆游诗取象雄阔时,则引入同时代及稍晚的一系列诗人作为反衬:“豪情与壮景契合为既雄且阔、底蕴丰厚的意象,使读者感受到其内在的力度与热度。唯其如此,陆游才有别于石湖的‘边幅太窘’、四灵的‘景象太狭’、后村的‘思致太纤’而独享‘出奇无穷’之誉。”[3](P194)要之,比较视角既可用于辨同,亦兼用于析异,均有助于阐明作家之个性与作品之风格。
小结 “广大”与“精微”的有机统一
先生虽然力倡宏观研究,但对其缺点亦有清晰的认知:“宏观研究既然是站在某一制高点上对纷纭复杂的研究对象的鸟瞰,那么,它所致力勾勒的必然是整体的轮廓,于局部的显微则未必在在逼真。”[3](P352)因此主张在具体科研过程中实现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协调统一:“一方面宏观研究无法代替微观研究,另一方面宏观研究又有赖于微观研究所提供的坚实基础。只要我们坚持在宏观中统率微观、在微观中展现宏观,二者完全可以并行不悖。”[3](P352)对于这一治学理念,先生大约在染翰学术之初即已奉为圭臬,并在数十年学术生涯中始终身体力行之。一方面,论题宏大但绝不流于空疏,必出之以精微的辨析与精详的论证。如《日本汉诗三论》涉及三个论域宽广的不同分题,但作者将它们聚焦于探讨诗歌本质的复归,并且建立了以五山诗坛为中心的时空坐标作为日本汉诗衰而复兴的共同纽带,经过有条不紊的论证,不仅揭示出日本汉诗在三个不同维度的同步演变,而且在形散神聚的逻辑框架中的展现出散文式的文风及魅力。另一方面,论题虽然貌似“细小”却绝不流于琐碎,往往于小题中寓宏旨,在论证上亦呈尺幅千里之势。如《论陆游诗的意象》兼论陆诗熔铸意象之成败,隐含着以古鉴今的现实考量,折射出作者胸纳古今,关怀当下的人文精神。《宋词中的别离主题》虽然主体部分侧重于对宋代别离词进行艺术与类型分析,但结尾处却提升到生命意识与文化范型(宋型文化)的高度审视其人文价值。由于作者科学地处理了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之间的辩证关系,使得《诗国游弋》在整体上呈现出广大格局与精微品质的有机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