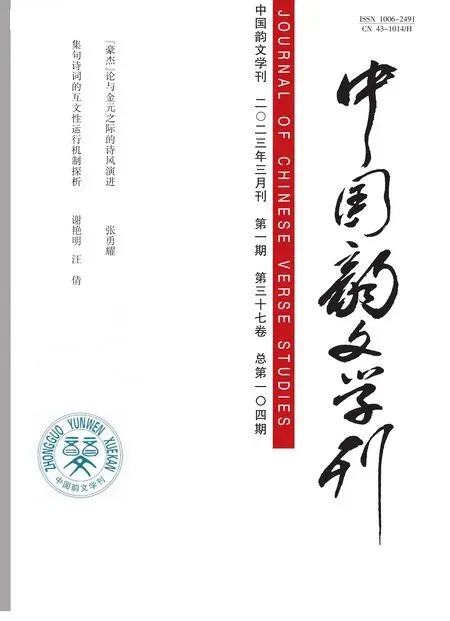晚清淮安“山阳诗群”的生成与质实诗风的建构
丛海霞,杜运威
(1.淮阴工学院 人文学院,江苏 淮安 223003;2.淮阴师范学院,江苏 淮安 223300)
宏观盘点清代文学史,明显呈现出地域、家族、流派等综合特质。作为重要组成部分的清代淮安诗歌自然也带着这类标签。从地域视角观之,淮安乃漕运和盐运的交通枢纽,商业繁荣,经济发达,私家园林星罗棋布。又因盐商巨贾、士绅豪门的组织和文人的积极参与,围绕淮安园林而兴起的文学活动成为地域文化的靓丽名片。自家族窗口切入,淮安有不少影响深远的名门望族,如丁氏、王氏、潘氏等,家学底蕴深厚,在品行塑造、文脉传承方面承担重要责任。然若单从诗歌史层面审视,清初之望社与清末之“山阳诗群”,无论是在淮安文学史,还是清诗史上,都是十分耀眼的存在。前者是带有鲜明政治目的的同声相应,以一腔悲愤抒发抑郁情怀,谱奏出一曲复杂辛酸的遗民血泪史;后者以变革诗歌历史地位为使命,对彼时过于独抒性灵而导致的纤细淫鄙和过于强调学问而造成的生气桎梏等弊端提出了新的补救措施,即“质实观”。本文重点讨论被人们忽视的晚清淮安山阳诗群的生成及其质实诗风建构等问题,试图以此重新认知淮安诗坛的历史地位。
一 晚清淮安“山阳诗群”的生成
如果说清初因为望社的出现,使得淮安成为《清诗史》中着重叙述的存在,那么,为何在更加昌盛的嘉、道、咸、同时期,淮安诗坛却在各大文学史中销声匿迹,陡然消失?盘点严迪昌《清诗史》、朱则杰《清诗史》、王小舒《中国诗歌通史·清代卷》等代表性文学史论著,仅仅止步于提点潘德舆、鲁一同等名家,都未关注到晚清淮安诗坛整体兴盛的现象,更没有看到“山阳诗群”的存在。
关于该群体,不少学者已经约略谈及。如朱德慈《潘德舆年谱考略》载:“四农(潘德舆)别树一帜,赢得了鲁一同、孔继鑅、叶名沣、吴昆田、黄秩林等众多追随者。探花诗人冯煦称其已独开一派……”[1](P3)笔者认为潘德舆等人“独开一派”之说或与事实尚有差距,但命名为“山阳诗群”是绰绰有余的。著名学者孙静也明确表示,潘德舆“在当时的诗坛上,树起一面旗帜,力图推挽一代诗风,使之沿着风雅方向发展”[2](P218)。笔者将顺着朱德慈、孙静等学者提出的设想,进一步揭示“山阳诗群”的内涵及基本特征。
山阳诗群是活跃于清代嘉庆、道光、咸丰时期的淮安地域性诗歌群体。以潘德舆为中心,以《养一斋诗话》提出的“质实”思想为创作纲领,通过地缘、学缘、血缘等关系,逐步发展起来的,有着共同审美倾向的诗人群。其中,以潘氏朋辈之丁晏、高士魁、丁寿祺、丁寿昌、徐登鳌、杨庆之,及弟子之鲁一同、吴昆田、孔继镕、刘湘云、潘亮熙、潘亮彝、潘亮弼、郭斗、鲍抢弼、梁法等为主力,其他山阳地域诗人为积极参与者,后辈之鲁蕡、尹耕云、高延第、徐嘉、段朝端、王锡祺等接踵其业,使得山阳一带火热的吟咏风尚持续了近半个世纪。
潘德舆倡导的“质实”理念既充分传承了古典诗歌的优秀传统,又符合彼时社会动乱、人心思变的社会趋势,当然在地域上也是勾连起淮安文化融通南北的节点。他说:
吾学诗数十年,近始悟诗境全贵“质实”二字。盖诗本是文采上事,若不以质实为贵,则文济以文,文胜则靡矣。吾取虞道园之诗者,以其质也; 取顾亭林之诗者,以其实也。亭林作诗不如道园之富,然字字皆实,此“修辞立诚”之旨也。竹垞、归愚选明诗,皆及亭林,皆未尝尊为诗家高境,盖二公学诗见地犹为文采所囿耳。[3](P45-46)
质实观内涵有二,一曰质,窃以为主要就艺术审美而言。钟嵘曾论“班固《咏史》,质木无文”[4](P12),质与文相对,上文亦以“文济以文,文胜则靡”为反例,都佐证质是一种朴实洁净的美学风格。然并非排斥文采技法,而是强调潜气内转,沉郁顿挫。如其言:“‘质’字之妙,胚胎于汉人,涵泳于老杜,师法最的。”又言:“今人诗无一句不求伟丽峭隽,而怒张之气,侧媚之态,令人不可向迩,此中不足而饰其外之过也。道园诗未尝废气势词采,而了无致饰悦人之意,最为今人上药,惜肯学其诗者希耳。”[3](P41-42)既师法老杜,又特以虞集为典范,都在说明质是一种外表朴实,却内功深厚的审美特征。二曰实,主要指内容意蕴,即所言之句有真思想、真情怀,特别是对当下正在发生的时事风云的关注,积极表达文人干预社会的责任意识。《养一斋诗话》载:“南宋以语录议论为诗,故质实而多俚词;汉、魏以性情时事为诗,故质实而有余味。分辨不精,概以质实为病,则浅者尚词采,高者讲风神,皆诗道之外心,有识者之所笑也。”[3](P46)“以性情时事为诗”清晰表明立场,而反对“以语录议论为诗”则将矛头直指乾嘉时期蔓延的“以学为诗”现象。
质实观的根本目的是试图恢复诗歌教化人心的作用。潘德舆说:“若事事以质实为的,则人事治矣;若人人之诗以质实为的,则人心治而人事亦渐可治矣。诗所以厚风俗者此也。”[3](P46)丁晏《潘君传》(潘德舆)更着重点出“君留心当世之务,感时抚事一寄之于诗,悱恻缠绵,出风入雅,蔼然忠孝人也”[5](P20)。有忠孝之心,方行忠孝之事,继言忠孝之诗也。
基于此内核,质实观在山阳一带产生了巨大影响。如鲁一同曾言:“凡文章之道,贵于外闳而中实。中实出于积理,理充而纬以实事,则光采日新;文无实事,斯为徒作,穷工极丽,犹虚车也。”[6](P422)至于“师事潘养一先生,能传其业”[7](卷首)(冯煦《吴稼轩先生传》)的吴昆田更在友朋书信数次谈及,如《与申秩亭书》云:“为文则不必求古,但须平实,以切情尽意而止。”[7](卷六)再如丁晏,评论家言其“穷居而能兼善一乡,有济于时,有补于物,不以空言为诗,读者当知有真经术在”[8](P373)。丁氏与王锡祺作淮安诗歌选集时特别关注民瘼时事与气势雄浑的诗风取向都与质实观有内在联系。因为理真,所以认同。潘氏凭借质实观及忠孝人品,逐渐成为淮安诗坛执牛耳人物。
一个诗群的成立不仅需要宗主、旗帜及成员,还离不开成规模的文学活动。首先,常规性的雅集唱和是诗群名副其实的前提。我们从各家别集中很容易拈出潘德舆、丁晏、鲁一同、吴昆田等淮上文人雅集的记录,如丁晏別集中就有《季冬二日,盛子履大士广文招集黄少霞师以炳、潘四农德舆、李少白续香、芷茳、友香兄弟饮澹然居。是日晚,复邀曹介樵若端、周木斋寅至城南僧寮痛饮,醉归有作》《黄少霞师以炳、潘四农、周木斋、曹介樵若端、倪渥生家骏祇洹精舍小集》《庆成门城楼落成,张介纯邑侯重九日招毛秋伯大令、周止安、庆石城大镛、杨荆门名超、吕星斋伟庚、广文周木斋登高宴集,即席和止安韵》等多首作品。至潘德舆下世,淮上吟咏非但未减,反而更盛,这在《山阳诗征续编》中有显著体现。单以编者王锡祺为中心的唱和诗,在《小方壶斋诗存》中就有数十首。需要指出的是,淮上文人唱和并非止步于娱乐消遣,更是创作思想相互交流碰撞的过程。其中不少诗人就受到潘德舆的影响或点拨,如徐嘉《遁庵丛笔》载:“云壑(方其洪)先生早岁登贤书,与四农先生为齐年交。逆旅公车,赓唱叠和,诗境日进。”[8](P444)“辅士(鲍抡弻)先生为四农先生快婿,且入室弟子也。诗笃守师法。”[8](P848)“朱磵南先生纻,字亦侨,与潘四农、黄蔚霞、赵吉人、阮定甫、宋绀佩诸先生皆至契,时相倡和。”[8](P175)丁晏《柘塘脞录》又载:“芋田(郭瑗)居车桥镇,贫而工诗,与潘四农明经衡宇相望,亦最契密,刻烛拈题,唱酬无虚日。”[9](P960)以上史料清晰记载了山阳朋辈与潘德舆之间的交游过程,至于潘氏家族、潘门弟子等受到潘德舆的影响就更加直接,也不必再详细举例。众人与潘氏交游学习的过程其实也是“质实观”逐步扩大影响以及诗群悄然建立的过程。
其次,选集的刊刻是诗群贯彻质实审美标准的重要路径。与山阳诗群有关的诗歌选集有四,分别是丁晏《山阳诗征》、吴山夫《山阳耆旧诗》、段朝端《山阳诗录》、王锡祺《山阳诗征续录》,吴、段二本流传未广,影响不大。丁、王二本与山阳诗群有紧密关系,甚至可以说,是该诗群创作的集体亮相。潘德舆《山阳诗征序》云:“若子之所征者,文也,而献实之,故足贵。然用诗存人,一二篇足矣;三篇外必至精者乃录之,弗以多贵也。俭卿然余言,余亦与删择役。要之,俭卿搜罗出处、行谊、轶事之功为大,后之览者,必由诗以知人,得其行己之大方,更由此以窥盛衰得失之故,则受范于乡先辈者远矣。且以罔罗掌故,庶几盛衰得失之明鉴法程。鄙拙如予,不克续采文献竟先世未竟志者,而亦深幸是编之成,借以偿吾愿也。”[10](P413)“然予言,予亦与删择役”及“偿吾愿”等字句已清晰说明潘德舆一定程度参与了《山阳诗征》的编纂。那么该选集势必带有潘德舆的编选痕迹,何况丁晏十分钦佩潘氏的诗歌成就及美学风格。因此,《山阳诗征》不仅具有常规选集的基本功能,还具有反映嘉、道时期淮安质实诗风的独特价值。
再看王锡祺所编的《山阳诗征续编》。王锡祺曾说:“段先生有志续编,辑有《山阳诗录》,斯役举以见饷。”[8](P1)换言之,续编充分吸收了段朝端《山阳诗录》的前期成果,甚至在选录的审美标准上也与之十分相近,从选录鲁一同、吴昆田诗歌即可管窥。[11](P32-35)王锡祺《山阳诗征续编序》进一步揭示:“士大夫幽忧愤郁,一倡百和,激为变征之声。迄今十余年间,岛寇鸱张,兴议变法,间有感时纪事形诸歌咏者,群非笑之,则纟由绎推寻,不亦可识。时局之纯漓,趋向之同异耶?”[8](P57)不难看出,续编所执标准与潘德舆推崇社会时事如出一辙。这也是《山阳诗征》及续编大量选刊民生疾苦、针砭时弊作品的根本原因。
综上所述,潘德舆提出的“质实”思想,在淮安一带产生了重要影响。以潘德舆朋辈弟子为纽带,在山阳一带逐步聚集起一批认同“质实”思想的诗人群体,他们通过常规性的雅集唱和与刊刻选集形式进一步强化了群体属性。
二 晚清淮安“质实”诗风的建构
若自诗歌史流变看,质实观的提出实质是对乾嘉学派和性灵诗派后期都出现严重弊端的一种反思和再平衡。乾嘉学派在学术研究和作文论理方面也强调朴实简洁,但由于过度重视考据义理,难免将这种学问化的思维和素材写入诗中,久之,直接导致以学为诗现象的极度膨胀。翁方纲肌理说纵有合理之处,但难逃此宏观局限。袁枚率先对此流弊发起诘难,其有讽刺诗曰:“天涯有客号詅痴,误把抄书当作诗。抄到钟嵘《诗品》日,该他知道性灵时。”[12](P111)倡导性灵与其说是针对以学为诗,倒不如说是诗歌审美发展过程中的自我转移。一代文风的转变有着多种因缘际会,随着乾隆后期爱新觉罗氏朝政生命力的逐渐流逝,雍容华贵、典雅丰腴的创作风格已经与世人心中诉求形成疏离态势,整个诗坛正在悄然酝酿新的变革。袁枚领导的性灵诗派的陡然兴起正是这种诉求和变革的佐证。然而,性灵诗派未能顺着吟咏真性情、真感慨的正道继续前进,反而陷入纤细狭隘、柔弱鄙俗的另一陋巷中,尤其自袁枚、张问陶、赵翼等核心人员仙逝后,明显后劲乏力,更无整改雄心。
随着潘德舆、龚自珍等一批新锐诗人的出现,嘉道诗坛大有洗心革面的势头。龚氏以一种更开放激进的姿态,划破原本压抑沉闷的天空;潘氏则以理性保守的面目,沉稳坚定地崛起于江淮大地。潘德舆不止一次批判性灵痼疾,如评吴以讠咸《古藤书屋诗存》云:“此集一扫袁、赵之习,诚近今作者。”[7](卷八)《养一斋诗话》又云:“诗积故实,固是一病,矫之者则又曰诗本性情。予究其所谓性情者,最高不过嘲风雪、弄花草耳,其下则叹老嗟穷,志向龌龊。其尤悖理,则荒淫狎媟之语,皆以入诗,非独不引为耻,且曰此吾言情之什,古之所不禁也。呜呼!此岂性情也哉?”[3](P160)基于此,潘氏提出以《诗三百》“柔惠且直”而定义性情,也就是学者总结的温柔敦厚。从思想史言之,这是一种典型的复古潮流,因而难免遭人谴责,并冠以“倒行逆施”云云。然需要提醒的是,此处所云是针对性灵派毫无节制的性情而发,更强调情之“厚”。所谓“真则厚,率则不厚”,又“诗有一字诀,曰‘厚’。偶咏唐人‘梦里分明见关塞,不知何路向金微’,‘欲寄征鸿问消息,居延城外又移军’,便觉其深曲有味。今人只说到梦见关塞,托征鸿问消息便了,所以为公共之言,而寡薄不成文也”[3](P16)。他有诗曰:“蒋袁王赵一成家,六义颓然付狭邪。稍喜清容有诗骨,飘然不尽作风花。”因此,性灵派之狭邪需用温柔敦厚的六义之旨和盛唐诸贤的诗骨来纠正。
潘德舆推进质实的重要举措有二:
其一,将社会时事纳入叙述视野,极大地抬高诗歌反映社会、记录历史的价值。这在诗群大将鲁一同身上表现得最为强烈,他对鸦片战争有着更为深刻的记录,钱仲联《梦苕庵诗话》称赞其“鸦片战争时,所为哀时感事之作,尤苍凉悲壮,足当诗史”[13](P252)。先读《观彭城兵赴吴淞防海》:
楼船下洪河,六月大兴师。
往问主将谁,南征行备夷。
舟山不复守,乍浦势尤危。
吴淞控大江,东南缠地维。
守险可百胜 ,严师固藩篱。
中枢下火符,副相总戎麾。
海疆八千里,腹背联络之。
侧闻蛟门军,半是吴中儿。
此辈市菜佣,临难心然疑。
楚兵气精锐,彪彪千熊罴。
百年养汝曹,危急安足辞。
猎猎大斾风,洸洸淮流驰。
弯弓指东溟,不得中顾私。
莫畏统御严,中丞有母慈。
行矣谢送徒,报国方在兹。[6](P213-214)
在外敌入侵、国将不国时,整个诗坛涌现出大量引吭高歌的爱国主义诗篇,他们积极抒发一腔怒火的初心是值得称赞的,然不少作品徒然为了表达的畅快而忽视了技法上的潜气内转,难免有直率庸俗,乃至沦为叫嚣谩骂的粗制滥造的语句。鲁诗澎湃气势的形成则很有章法,一方面是情绪张弛控送得很到位,另一方面是视角切入得很巧妙。上文先自主将入,宏论吴淞,次及中枢、副相、士兵,逻辑清晰;继以“危急、猎猎、洸洸、不得”等急促词语盘旋气势,最终立足点在报效祖国。这样写不仅反映出彭城守兵的坚定信心,更因记录下这段御敌抗辱的光荣历史,使诗歌成为鼓舞人心的重要载体,承担起时代赋予的使命。类似作品还有不少,如《读史杂感五首》《辛丑重有感》《烽戍四十韵》《崖州司户行》等论及林则徐虎门销烟及英勇抗敌的壮举;再如记浙江战事的《三公篇》,方家评其“最为巨制,笔力坚苍,叙事简净。……三诗不愧为大手笔,并时惟朱伯韩可为抗手”[13](P255-256)。
不唯鲁一同,其他诗人对战事也特别关注。如高延第《石桥庄筑围记》记载捻军乱淮甚详细:“咸丰庚申春,皖寇东扰,乡民望风遁散,贼踞清江浦十余日,马队四出,百里内焚掠殆尽。时天大风雪,流民遭屠掠饥冻死者甚众。贼退人归,室庐仅有存者,号哭震原野。既而念无险不可以守,不耕又无可得食也,乃始发愤,集乡里,筑围寨,为死守计……”[14](卷四)然更深刻的还是不同诗人笔下立体多维的诗歌,杨庆之有组诗十一首(《堵城》《止帅出》《民呐喊》《防夜火》《粜官米》《阖门节》《转沟壑》《杀不辜》《兵肆掠》《歼途枭》《杯影蛇》),第一首“我闻淮阴背水阵,死地后生人知奋。大吏此令第一功,二千余户咸安顺。……白发老儒坚不可,牴牾军令大声我。行橐返途簜节还,郡城大势重安妥”,叙述淮安军民共同御敌场面。至第三首“行者击柝坐者钲,五垛一鼓灵鼍铿。狗嘷鸡唱马长啸,喧豗口霅霵雷车轰”,聚焦战斗场面的混乱激烈。中间数首透过粮草、征人思妇、士兵、老翁等不同视角,反复渲染战争背景下的残酷景象。杨庆之的组诗完成了对捻军乱淮的多方位立体化描摹。其他同类作品还有如陈嘉干《庚申二月朔,袁江纪事二十韵》:“淮水赤复赤,流血饱蛟螭。(妇女投运河死者甚众)鳞鳞万瓦屋,一炬靡孑遗。贪狼恣属餍,邗上来援师。群丑鸟兽散,大府归迟迟。”丁寿祺《庚申八月纪事》:“风声鹤唳又经旬,感激居然社稷臣。排难无端招市侩,纵擒能否服南人。将军跋扈威难犯,宰相模棱意善嗔。日向城头望烽火,有谁赴阙靖黄巾。”丁晏《庚申守城》、程步荣《庚申春正月逆捻攻淮,孤城困守十日解围,感而有作》、潘亮熙《丙辰秋夜,述感短歌八章》等,皆是关于捻军诗歌,堪称实录。这类作品的集中出现,固然有生逢乱世的契机,但若无洞察社会之动机和积极表达的创作理念,即便战争摆在眼前,依然有大量文人选择漠视。
其二,拓宽诗言志及针砭时弊的现实作用。将文人目光由知识学问、吟风弄月、个人情怀转向民生疾苦。如吴昆田《纪旱》诗堪称诗史:“不雨四十日,中田成焦枯。飞蝗起东海,西与浮云倶。蝝生遂徧野,何计能驱除。大府急民瘼,祷祀丹诚输。……昔为麦祈实,立见甘霖敷。今已二旬历,灵应岂忽无。”连续四十日不雨,直接导致禾苗焦枯,蝗虫四起,民不聊生。面对“蝝生遂遍野”的现状,诗人心有余而力不足,那种忧国忧民的心绪跃然纸上。天灾已经使得民不聊生,然更加令人走投无路的恐怕还是人祸。吴昆田《纪蝗》前数句罗列蝗灾惨象后,将矛头直指当权者的漠视和贪婪:“贪苛谁乐召,饥馑只愁当。冠盗将乘起,干戈未许藏。萑苻虽异类,蟊贼实同方。天意何由测,人谋要贵臧。”不必再赘言解释诗中所指,犀利的语句已经将残酷的现实摆在面前。徐嘉《遯庵丛笔》曾指出:“(吴昆田)识议坚卓,能断大事。闻四方灾荒,盗贼窃发,辄忧愤形于言色,所为诗文多关当世之故。”[8](P524)山阳诗群中类似作品还有不少,丁寿征《蓟门吟》十首就是典型例证:第一首《盗铸钱》,悯愚民;第二首《不终制》,诮薄俗;第三首《钞币滞》,伤贪吏;第四首《银价贵》,忧钱法;第五首《赀郎宴》,讥纨绔儿;第六首《丽人游》,讽贵家眷;其他几首不一一罗列,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第七首《河堤决》,悲民流也,诗歌如下:
咸丰六年季夏月,永定河头水漰渤。惊涛骇浪风雨飞,疑是千弩万弩发。石工堤埽渺难寻,就中似有蛟龙窟。前日喧传南岸冲,多少田庐付沉没。监河见险仍疏防,北岸又复惊披猖。怒流决开二十丈,蝄像腾跃天吴狂。亡者谁为主,生者乃更苦。老羸转徙伤流离,计乏一椽与二鬴。国家岁帑百万金,未雨绸缪责谁任。斩茭伐竹宜早计,何为坐待长堤沉。帑金既浪掷,民命亦可惜。设官本以卫民生,谁知官多民转迫。会稽宗子谓御史宗君稷辰古遗爱,执法乌台冠流辈。上书天子救灾黎,请筹抚恤恐不逮。丁壮堵筑借免饥,笃老垂髫资斗概。官私并力全灾区,勿使穷民色如菜。[8](P682-683)
诗歌聚焦永定河水灾导致良田损毁、生民涂炭的现实悲剧,更悲剧的现象是“设官本以卫民生,谁知官多民转迫”,类似情形并不稀见,薛炳如《谭雨香邑侯德政颂》:“忆昨湖水涨漫弥,河东河西灾祲随。田禾失收费撑持,目极艰难岂忍窥。”又程步荣《大雪篇壬子腊月十八日纪事之作》:“湖湘一战万骨枯,彻骨荒寒更天数。行路难,灾民哭,逃亡满路皆枵腹。携男挈女走他乡,一日一夜一餐粥。是刀是雪飞岩谷,茫茫冻路寻骨肉。伤心篷栖与路宿,饥寒逼迫遭残戮。”鲁一同《荒年谣》组诗小序中说:“事皆征实,言通里俗,敢云言之无罪?然所陈者,十之二三而已。”换言之,以上诗人笔下的民生疾苦只是冰山一角,还有大量被遮蔽的社会乱象。此类作品的集体出现绝不是偶然,既是宏观经世致用思潮对诗歌的重大冲击,也是微观山阳诗群在质实观影响下的集体亮相。
另外,质实诗风的形成还与“诗品之人品”的观念有密切关系。淮安文人特别注重人品之高尚纯洁,哪怕诗歌有瑕疵,或成就不高,若有令人敬佩之人品,则其人其诗皆可传;反之,即便有八斗之才,亦半字不录。潘德舆曾云:“人与诗有宜分别观者,人品小小缪戾,诗固不妨节取耳。若其人犯天下之大恶,则并其诗不得而恕之。”[3](P7)他不止一次地在各种场合申辩人品与诗品之间的主次关系:
杜荀鹤诗品庸下,谄事朱温,人品更属可鄙。[3](P68)
(《养一斋诗话》卷四)
典而确,辨而洁,练而质,健而逸,传世诗文非此不立。……雄、深、雅、健四字,人品、诗文、书法,要皆如此。[10](P973)
(《自题诗稿后》)
静能隐居乐道,人品甚高,故其诗质而无饰如此,虽未逮道园之浑健,亦元人之特立者。[3](P43)
(《养一斋诗话》卷三)
邱文庄虽称淹博,而忮刻乖僻,与王端毅公相恶,其人品舛矣,安得与文靖肩随乎?况文靖尝教人读经穷理,殆有绳以贯钱,不得谓之无钱者也。文庄所讥,徒好胜而已矣,何足录乎?[10](P2133)
(《养一斋札记卷九》)
这种品鉴等第,首重人品,次谈诗品,二者相统一的风尚已经不是停留在个人观点层面,而是贯彻落实为山阳诗群内部的高压线。丁晏《山阳诗征序》大赞:“其间忠孝节烈、道德文采,彪炳天壤,足为斯集之光。”[5](P170)段朝端《晓渔诗草跋》云:“余幼时闻长老言,先生少失怙,事母极孝,属岁旱,大病,先生中夜露祷,愿延寿养亲,其疾良已。则是集又不以文重,而况芉绵清丽,有如此哉!”[8](P157)不以文重,重在孝道。再如夏涂山《瑚散言序》云:“存赤与予为忘年交,其为人也,静慤而坦直,卓有道气。茗底觞次,发一语,辄能以冷隽解人颐。”[8](P3)以上所论都在强调人品的重要性。这种诗论标准一方面彰显淮上文人淳朴忠孝的高尚品格,另一方面表现在诗歌中则是对节义忠诚题材的重视。如王锡祺盛赞霍克诚《题马贞女》诗;阎若琛《贞女歌》亦钦佩其中“妾心不可磨”的坚决。至于王德隆之女,嫁后遇贼,宁愿介沟崖投水而死,也不屈从之壮举,更博得诗人周龙藻的称赞(《题张桥王贞女墓》)。其他如刘湘云《祭露筋烈女祠乐章》:“白云初起,下映淮水。既洁且清,妾心如此。嫂止田夫,女守其愚。愚能全节,何惜微躯。”曹若曾《吊丁烈女》《哀郝烈女》,丁毓璨《何烈女祠》,刘广《何烈女》等,都是异口同声的表达。罗列这些作品,并非宣扬什么观念,只是为了佐证淮安文人对人品的重视不是停留在口头层面,而是落实到具体诗歌创作中,且形成了一种倡导忠孝节义的地域特色,这恰恰是质实观不可轻视的重要一端。
总而言之,山阳诗群的文学价值是被远远低估了的。晚清淮安出现的质实诗风既是地域性诗歌的独特风貌,也是对近世整个诗坛急需变革的现实回应。
结 语
综上所述,潘德舆倡导的“质实”理念既充分传承了古典诗歌的优秀传统,又符合彼时社会动乱、人心思变的社会趋势,更勾连起了淮安文化融通南北的节点。该理念得到了鲁一同、吴昆田、丁晏、王锡祺、高士魁、丁寿祺、徐登鳌、杨庆之、孔继镕、刘湘云等人的大力支持。由此,以潘德舆为中心,以“质实观”为创作纲领,以地缘、学缘、血缘等为纽带,形成了共同追求“质实”诗风的诗人群体——山阳诗群。山阳诗群主要通过两大途径建构起质实诗风:一是将社会时事纳入叙述视野,极大地抬高诗歌反映社会、记录历史的价值;二是将目光聚焦于民生疾苦,拓宽诗言志及针砭时弊的现实作用。此类作品的集体出现既是宏观经世致用思潮对诗歌的重大冲击,也是微观山阳诗群在质实观影响下的集体亮相。综合而言,山阳诗群的发现有利于准确定位清代后期淮安文学在整个清代文学史上的坐标,其质实诗风的建构是对乾嘉学派和性灵诗派后期出现严重弊端的一种反思和纠正。总之,凭借反映时事、针砭时弊、评鉴人品等特质,山阳诗群已然走出一条打着淮安地域特色旗号的诗歌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