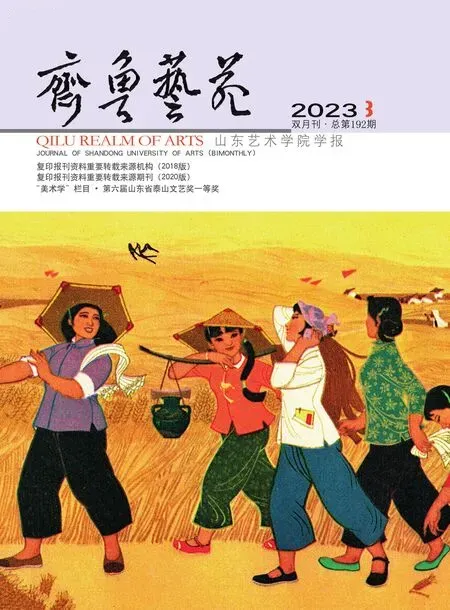全球化背景下设计更新背后的资本与伦理
唐世坪
(南京艺术学院设计学院,江苏 南京 210013)
动画片《玩具总动员》中,孩子长大后便着手将一些旧玩具卖出或转送,尽管这些物品曾陪伴他度过了美好童年——这样令人唏嘘的场景也常常出现在当代人的日常生活中。一方面,产品质量和使用年限下降,从而不得不更换;另一方面,由于大量物品频繁更新换代,在流行与时尚的操纵下,人对物品的感情显示出前所未有的阶段性特点。
丰富普遍化的后匮乏趋势悄然出现之时,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1938—)在《失控的世界》中提出,经济全球化导致的“人为风险”已经超出自然造成的“外部风险”,成为人类未来命运不确定性的新来源。虽然全球化使整个世界看似联结一体、形成纽带,但其影响下产品快速更新带来的包括过度设计、过度消费、环境问题和精神虚妄等在内的设计伦理问题,也构成了人类未来命运新的脆弱和不确定因素。全球化带来的科技成就共享使生产力提升、生活更加便捷的同时,设计产品在资本驱使下,利用全球化的科技成果和广阔市场掀起前所未有的物质浪潮,不加选择地“推陈出新”,也带来了难以忽视的负面影响。物品在个人生命中的存在时限愈发短暂,人们沉浸于产品代际更迭的现象,究竟是科技成果播撒的现世福音,还是全球化新风险、新脆弱奏响的未来序曲?
一、资本:幕后推动力
在产品生产领域,科技成果更新往往是各大全球化公司的竞争重点,其深层原因依然是企业对产品代际更迭的巨大需求。根据华为公司消费者业务CEO余承东透露,华为手机一年的研发投入高达60亿美元,超过中国所有手机厂商研发投入的总和。[1]华为P40系列在2020年3月27日正式预售,而此时距上一款方兴未艾的P30系列在法国巴黎会议中心最初发布(2019年3月26日)也只过去了一年时间。科技创新成为智能手机迅速更新的最主要推动力,但由此必然引发消费主体频繁地以旧换新。根据我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报告,手机用户的手机更换周期越来越短,有超过一半的消费者会每隔一年或者半年更换一次手机。[2]这显然超过了手机一般预设的使用年限,手机更新速度甚至远远快于消费者习惯新手机的速度。同样,无论是苹果手机、大疆无人机这样的数码产品还是日常生活用品,企业往往不遗余力地通过科技手段推出新版本或新型产品。而且随着新产品诞生速度日益加快,旧型号产品价格迅速逐级下降,甚至相隔时间并不久远的先前几代产品出现大幅缩减生产和售卖的情况,很快成为并不古老的“古董”。
如此看重科技成果及其带来的产品更新,企业又能从中获得什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发展过程中提出的有关资本剩余价值理论,即在科技迅猛发展的当今社会,资本要素在生产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已经超过劳动要素。资本可以用来剥削劳动力、创造新资本,甚至可以左右科学技术、劳动方式和思想观念。在全球化的商品生产、贸易和流通中,产品作为艺术设计与生产劳动的结合,其更新状况看似是科技全球化的直接影响,实际上背后大都由资本操控。简言之,就是如何创造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增加利润,积累更多财富。一方面,如果不及时推出新产品,企业当下占有的市场和知名度就会迅速缩减,资本难以获得更多利润乃至赔本亏钱,最终被席卷而来的产品浪潮淘汰。另一方面,可以推测,想要化解过剩产能,必须通过产品的推陈出新带来更多样化的选择,进一步拉动消费需求。以手机为例,据我国不同省份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辽宁省智能手机产量为279.4万台,上海市、南京市、南昌市分别为4711.44、597.89、4035.9万台,四省市总额近亿台。(1)数据来自《2018年辽宁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8年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8年南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8年南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利润驱使和市场导向导致的企业间竞争实属必然,而经济全球化则相当于将全世界渴望在国际市场有所作为的企业设置了更高标准的“合格线”,并将市场范围扩展至全球,这在某种层面上进一步加剧了竞争意识和竞争关系。科技进步与艺术审美作为产品设计更新的重要手段,对生产方吸引消费、扩大需求有着直接影响。但在供求均与资本挂钩的环境下,产品设计的话语权不会被牢牢握在设计师或消费者手中,产品设计的导向脱离了其本质目的与社会伦理,必然产生异样的转变,反而成为资本驱动下的收割机。
二、新的供需失衡
不可否认,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受市场经济影响的良性竞争能够促使产品通过设计更新提升品质,惠及大众生活。在产品设计和生产领域,科技影响下的不断更新使生活变得更加多样和便捷,企业生存发展也必须依靠科技进步。资本的推动在某种层面的确能够促进社会发展,成为人类进步的必经之路,但如果资本的力量过于庞大,也会带来很多社会问题,埋下一系列不可控因素。
所谓功能,本质上源于消费者在实践中生发的需求,具有一定的自觉性。如果是相对稳定、无大量外物刺激的生活,需求一般呈缓慢式而非井喷式增长。无止境的个人需求则大多来源于丰厚的物质条件、活跃的市场氛围和社会消费潮流的刺激。在20世纪中期新中国成立之初,科技和生产力都在稳步恢复,人们渴望拥有“四大件”,但脑海中大概不会产生像电视机、芭比娃娃一类的消费欲望,因为大部分消费者没有见过、也无法通过媒体获知类似产品的存在。广大消费者的需求也常常需要生产来反向刺激,适当扩大消费需求有利于提升生活质量,但在资本控制下,产品设计利用大众盲目跟风的非理性特点进行无限制的欲望扩张和需求刺激,制造了大量消费者实际生活中的“鸡肋”产品。就像现实生活中打开购物软件,各种强调多功能的家用电器令人眼花缭乱,消费者在广告的暗示下想当然地认为所有功能都会用到,但实际上往往忽视了家庭安装情况和使用习惯,最终常用的功能依然只有一两个。并且,虽然看上去功能数量增多,粗糙的做工、频频出现的质量问题却让使用效果不甚令人满意,不但用户的实际需求得不到真正解决,甚至还造成了新的使用问题,既占据了用户的使用空间,又带来了无意义的资源浪费。买家秀和卖家秀剥离,无数吐槽视频和发帖引发大量消费者共鸣,正说明铺天盖地的新功能的有效利用率和使用体验究竟如何仍要经由实践验证。对于购买过程而言,消费者往往由相对简单的需求引发挑选产品的行为,却在不知不觉中被附加了一系列条件,在无穷尽的比较中迷失方向、消耗时间,从而愈发疲劳。而这样的情况不得不说与资本引导下的精心设计有关——消费者在购物选择过程中的犹豫和徘徊,究竟是自主意志的驱使还是心甘情愿的“被迫”,已然很难划分。
即使如此,企业依然将很多新“创造”出的可有可无的功能作为产品卖点,造成商品买回后成为摆设,并未真正发挥应有功效,反而在某种程度上造成功能泛滥。最直接的原因,在于设计师和生产者企图为消费者的使用方式制造幻想、规划蓝图,高高在上地指导消费者如何消费、如何使用产品,而非站在用户的立场挖掘其痛点。而设计周期缩短则恰恰是导致设计者疏于调研、未能深入理解使用者生活需求的重要根结所在,由此引发了诸多关于设计伦理的问题。在很多产品生产者眼中,科技在产品设计中的宣传和增值要素的地位远远高于其能否精准地为大众解决日常生活问题。科技在设计中的应用原则“逐渐演变成以形式追求为中心,伦理性和目的性被取消了”[3]。尤其是当准确详细的消费调研跟不上资本要求的产品更新速度时,设计者似乎只能亮出所谓的“科技元素”,用模棱两可的新功能来吸引消费者的目光、为产品增加附加值。类似的生产经营模式直接影响了“功能”一词的新定义,使其从解决真实生活中的问题,变成了设计者、销售方共同利用所谓“新”性能的吸引力人为制造与暗示的新需求。
由此,整个社会也走向了日渐失控的消费狂热。其中的重要原因是投资商、生产方借助媒体的标榜宣传,塑造了与新产品对应的科技符号崇拜与身份象征,紧紧抓住消费者心理,共同编织了一张消费主义罗网。短平快的思维模式下,“几乎我们所有人都是利润体制宣传的牺牲品,我们已经不能够坦率地思考了”[4](P341)。当消费行为成为证明自我存在和寻找自我价值的手段时,失去理性的消费者唯恐落伍成为异类而陷入恶性循环,匆匆卷入如精神鸦片般一经产生就难以自制的狂欢。
三、问题和危害
为新而新的产品功能虽然填补了某些产品生产领域的空白,但也由于定位不精确、细节不到位等造成了新的供需失衡和用户体验感下降,甚至因质量问题为使用者带来新的麻烦与危险。比如,智能手机的芯片、处理系统、网络、摄像头等功能的频繁优化的确能给用户带来不同的体验感,但大部分年龄层的使用者几乎对此不太敏感,他们更看重联络通讯、休闲娱乐、软件安装等基础功能是否满足基本的使用需要,而无意间却因此投入了大量的时间、金钱和精力。再如,燃气灶的钢化玻璃面板,作为不锈钢面板的升级品,商家宣称具有易于清洁、造型美观的优势,但实际上这种面板时常发生爆炸事故,具有危害消费者的安全隐患。
设计一旦沦落为资本控制下的工具,在利益最大化目的的驱使下反而脱离了设计的本质要求和目的,忽略了大多数群体的基本诉求,从而成为将某些人边缘化的推手。虽然各类型产品的更新从未停步,但有助于少数、特殊群体生活的产品却始终处于尴尬境地,在市场主流中缺少话语权。不少老年人产品的开发以智能为营销旗号,但可有可无的功能实则以改变老年人生存习惯为代价。像与医疗服务相关的一键救护与报警、智能盒子等,由于存在位置固定、容易误触、安装繁琐等问题,老年人在紧急情况下依然不会想到使用它们,反而为原本的生活带来了困扰。类似的情况同样发生在残障人士身上,无障碍设计的深化在当下迟迟难以展开,盲道规划、如厕设施等都具有诸多不合理、不方便之处,有的甚至流于形式,这使得我国数以千万计的残障人士变成了社会中的“隐形人”。而拒绝这些设计就意味着本来处境糟糕的他们会被时代彻底抛弃,于是被迫使用着很多不能为自己解决实际问题的新产品——然而真正的好产品不是消费者通过强迫改变自我来适应产品的存在,层出不穷的科技新产品换来的不应是特殊人群的担忧和妥协。
对物品的使用如果超出个人可承受的限度,必然会加以丢弃和更换以腾出空间填补新的消费品,由此也产生了常见的囤物、购物狂等现象。而更深层次的是,连同物品一起被扔掉的,还有节俭、惜物的优良传统。维克多·帕帕奈克(Victor J.Papanek,1923—1998)在其著作《为真实的世界设计》中,透彻地将消费过度、用后即弃的现象比喻为“面巾纸文化”:久而久之,任何东西都会被我们看作陈旧过时的,扔掉了家具、交通工具、衣服和其他日常生活用品之后,我们会觉得婚姻(以及其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可以扔掉的,而且在全球范围内,国家——甚至整个次大陆都可以像面巾纸一样被扔掉。[5](P92)生活中习惯于遗忘和抛弃的人,能够适应大量物品带来的虚幻满足,更容易对亲密友好的关系失去兴趣。因为不懂得修复和保留的重要性,人际关系中遇到困难时是否也会选择逃避,而非及时寻找改变和处理问题的可能。由此,社会生活的基础关系陷入不确定与自我封闭的心理状态共同作用,就可能产生覆盖全社会的信任危机。信用体系困境、社会安全威胁、医患矛盾加深、价值观念崩塌等问题带来的困扰,使人人自危的社会更具不可控性,这将是可怕的。
无限制的产品设计生产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席卷世界的各个角落,甚至边远村庄和无人区。欠发达地区迎来了更富裕的生活和更开阔的眼界,但容易忽视的悲哀之处在于资本主导下的不平等关系依然牢不可破,具体表现之一即为淘汰品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从城市向农村转移,从人群密集区向无人区转移,大到数以吨计的垃圾倾倒,小到因不喜欢而转送农村的食物和书包。而资本的意志不会推崇克制,与此同时,过剩的产品成为价值观的重要参考框架,文化传统和习俗瓦解,人与环境的亲密联结逐渐解构,赖以生存的自然会承受包括资源浪费、污染在内的更大压力。法国纪录片《海洋》中,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漂浮在水上、沉入海底,严重威胁海洋生物生存。但环境危机带来的震撼不足以让人们停止对资本的追逐,就像《切尔诺贝利的悲鸣》和《黑天鹅》中反映的“脆弱”——人类不仅不会预防风险,而且即使再次遇到重大灾难,也依然不懂得如何规避和防御,并形成新一轮的绝望和恐慌。
结语
面对全球化科技浪潮裹挟的资本风暴及其带来的威胁,无数有识之士都进行了批判和反思。其中,以维克多·帕帕奈克为代表的设计学者从设计伦理角度探讨了设计的发展方向。设计伦理是对设计师一心盈利行为的道德约束,强调其作为“公民”承担社会责任的自我意识。在帕帕奈克看来,设计可以参与解决有些事关人的生存与福祉的问题(如他所提出的为第三世界设计、为老年人和残障人士设计等),并且必须超越私有的、个人的经济利益。[6]当今中国的很多学者、设计师面对复杂的经济社会状况,也在不遗余力地呼吁设计伦理。在设计教育方面,提倡“在传授设计专业技能的同时,应注重设计价值观和设计社会责任的教育,提升设计的职业规范教育和学生的综合素养”[7];商品生产方面,强调设计服务于广大普通民众,注重实用、审美和伦理价值,确立为人的生存生活服务的最终目的[8];同时也不能孤立地将“以人为本”作为口号,要从根源上正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互利共生的关系,并应用于实际生活中。
但资本仍是设计伦理的巨大阻力——资本运转的消费主义浪潮形成的现实,无疑与具有先见之明的有识之士的呼吁相背离,也使得设计始终处于资本扩张与伦理约束的矛盾中,设计伦理与资本操控时刻处于博弈的状态。在人类短期经济利益的驱使下,设计利用科技进步造成的产品过快更新成为资本迅速且持久地占领市场的工具,它带来的世界性危害与设计伦理所提倡的责任是相违背的。追求长远的设计观念和目标在消费社会的打击下变得脆弱不堪,大众在物品频繁更换的刺激下逐渐习惯简单平面化的直线型思维,逐渐偏激与漠然,生产者也沦为资本的奴隶。“设计师之所以长期的为‘欲求’设计,为扩大消费设计,甚至是为一种炫耀性的消费设计,一个很明显的原因是因为设计师从这样的一种设计中得到了产业界的认可,同时也满足了个体的私利。”[9]颇具讽刺性的还有美国建筑师R·巴克敏斯特·富勒(R. Buckminster Fuller,1895—1983)所言:“如果你想成为一个设计师,你必须下定决心,要么做有意义的事,要么就去挣钱。”[10](P91)对于设计师乃至各行业的从业者而言,赚取金钱与谋求福祉的愿望在资本控制下成了相背离的事情。这种现象是一个健康的、现代化的社会不应当出现的,大多数人在全球化带来的社会变革中渴望着自己的最优结果和最大利益,却忽略了过程的对错和背后的风险。
归根结底,“目标为手段所遮蔽,是所有较高文明的一个主要特征和主要问题”[11](P10),科技原本只是设计造福未来的手段,是设计需要选择权衡的事物,却成为了设计为产品增值的目标。这也是人类未来风险和脆弱性的来源之一。设计没有必要对科学技术亦步亦趋地追随,最重要的是找到自身存在的必要性和独立性,并“具有真正意义上的革命性和激进性”,就像帕帕奈克所言,“用最少的发明换取最大的多样性”[12](P355),用最少的资源消耗和准确的自身定位换取最大的收效,改变物品的过度消费、频繁更迭、供求失衡及精神脆弱等畸形现状。但也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设计想要对人类未来命运形成普遍的积极意义,必须在伦理与资本间寻求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