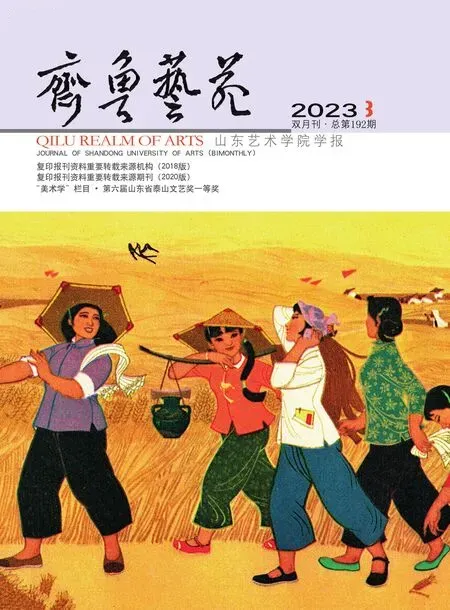症候迭合:“现象级”古装剧的四层叙事面纱
郭 敏
(山东艺术学院传媒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众人皆语自《琅琊榜》以后,古装剧便出现爆款缺位、同质化严重、量高质低的局面之时,《延禧攻略》横空出世。这部剧以“于正改邪归正”为口号,自上线便引来话题无数。随着情节的递进以及人物的铺展,该剧播放量、好评度、话题量日增,实可谓一部“现象级”作品。无独有偶,同样讲述乾隆朝后宫斗争故事的《如懿传》,尽管与《延禧攻略》打擂,但凭借《甄嬛传》的余温仍存,以及自身文本的可圈可点,同样争得了一席之地。《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以下简称《知否》)虽与落脚于后宫的前两者不同,但抛开“宫斗”与“宅斗”的外壳,《知否》《延禧攻略》《如懿传》,实质上都难以割断成长与爱情的母题。这些作品在中国古装剧的炫丽图谱中,可谓是抹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尽管它们出自品味各异、履历有别的三位金牌制片人之手,但三部“现象级”古装剧,尽皆描摹女性的成长与爱情,且都不谋而合地关涉了当今社会现实。
一、借“古”作表:视听形式的仿古与求真
近年来,随着网络小说的风靡,古装剧的IP改编火热,包括《宫锁心玉》《宫锁珠帘》《步步惊心》《甄嬛传》《琅琊榜》等在内的数十部古装剧,接连引发收视狂潮。尽管这些古装剧颇受好评,但其中大多数作品的视听表达都不能尽如人意。作为用视听语言呈现故事内容的艺术形式,古装剧在视听形式的运用层面可谓难上加难:既要符合西方沿袭而来的视听形式要求,又要契合中国传统的美学韵味。2015年上线的《琅琊榜》,可谓此前古装剧中视听形式的巅峰,该剧极具中国传统对称美学意味的构图、异常考究的服化道以及极富符号意味的物像,皆值得称道。
在同一制片人侯鸿亮的监控下,《知否》中构图方式与布景设置,较之于《琅琊榜》,显现得有过之而无不及。剧中中心式的单人构图、渐次式的群像位置以及规整、对称的布景设置,都让观众仿佛置身于恢弘、严谨的大宋王朝。值得言说的是,摄像师出身的导演张开宙在影片中贡献了无数值得称快的镜头:当顾廷烨与赵宗全被围攻之时,导演采用颇具纵深感的辐射式构图进行拍摄,将敌众我寡的局面以及顾廷烨临危不乱的状态悉数展现出来;在表现盛宅之时,导演采用俯瞰的视角将盛宅慢慢拉远,镜头中的盛宅四四方方,犹如困兽之境;为表现人物的情感状态,导演几次使用一镜到底的方式进行跟拍,呈现了话剧式的演绎风格。不仅如此,为了尽量做到仿古与求真,《知否》剧组放弃了传统的布光方式,选择用蜡烛装点环境、展示人物,因此,剧中的夜晚总是透着一丝古意与幽深。
在视听形式上,《如懿传》同样不输于流潋紫的前作《甄嬛传》,该剧不仅以航拍、俯角度推进式的镜头,展现乾隆王朝的恢弘与大气,还使用了大量细节性镜头,描摹宫墙之内的矜持与华贵。譬如透过玉柱散下的光,表现时光的易逝;王钦独饮的剪影,隐晦地处理了莲心的苦难;时隐时现的兽首,暗合了阴晴不定的圣心。不仅如此,该剧巧借帘幕、窗棂、重门构图,展现出一种帘幕重重、庭院深深的忧愁与深邃。实际上,《如懿传》剧组考证了大量的史实,全方位地还原了剧情所涉时空的礼节、礼制、礼器,将等级森严的封建王朝气象,展现得淋漓极致。其中,焚烧的香炉、摆动的闹钟以及琳琅满目的印章,既显示出乾隆皇帝的个人偏好,也展现出了创作者对旧时宫廷文化气息细腻捕捉、二度想象以及艺术再生产的历史积淀与丰盈的把握掌控。除此之外,《如懿传》的台词也尽可能的“仿古”,譬如如懿与乾隆“墙头马上遥相见,一见知君即断肠”(剧中台词)的相知相遇,后宫中“得不高不低之位,争不荣不辱之地,才得长久平安”(剧中台词)的生存之道,如懿“青春韶华锁深宫,低眉敛目,心绪深藏,或命殒旦夕,或寂寥一生,半点不由人”(剧中台词)的人生感悟等。
《延禧攻略》同样在构图上下足了功夫,除了常用中心式构图法展现皇宫的中正以外,导演多用框架构图法实现观众的视觉延伸,剧中人物游走在宫院、楼台之间,多有一番“满城春色宫墙柳”(陆游词)的余味。更值得赞叹的是,该剧的调色师以中国传统的绢本设色为蓝本,借鉴了冷枚的《春归倦读图》以及郎世宁的《午端图》,选用的色调区间集中于浅灰色调、灰色调、轻柔色调、浊色调之间。因此,《延禧攻略》在色调的处理上极具中国画古朴典雅、肃穆深沉的质感。除此之外,《延禧攻略》的场景以及服化道更是堪称精良:于正为了揭开历史的迷雾,花重金还原了一座别具一格的延禧宫;美术组在细节上的处理同样值得称赞,无论是雕栏玉彻,还是宫墙旧柳,都让观众如真似幻地置于历史的空间之内。不仅如此,《延禧攻略》人物的服饰、装扮皆可考证,“平居以通草绒花为饰,不御珠翠”(出自《清史稿·孝贤皇后氏》)的富察皇后,在剧中基本以恬淡、雍容的扮相示人,而皇帝“钟爱异常”(出自《清列朝后妃传稿》)的高贵妃,则色彩浓艳、盛气凌人,甚至于魏璎珞的宫女装扮,也与《道光帝喜溢秋庭图轴》中的端茶宫女如出一辙。
三者同样败也萧何,《如懿传》《延禧攻略》《知否》尽管画面美不胜收,但对于音乐元素的处理,实际上远逊于《甄嬛传》,且《知否》中乱用典故、语病连篇,《如懿传》中大拉翅发型实乃晚清之物,《延禧攻略》中高贵妃弥留之际献唱的《贵妃醉酒》实为京剧,而非应有的昆曲。尽管如此,三部作品仍不失为一次古装剧集体式的视听升级。
二、以“梦”为马:女性成长的书写与突围
在《内训》中,“贞静幽闲,端庄诚一”可谓古代女德的标准。在传统的古装剧中,女性往往温婉如《汉武大帝》中的卫子夫,顺从如《康熙大帝》中的苏麻喇姑,端庄如《康熙微服私访记》中的宜妃。她们往往作为皇帝/皇权的陪衬品出现,也是男性受众的情感寄托和欲望对象。随着时代的发展,女性在社会中的角色不再单一如初,而是变得愈加独立、开放。因此,古装剧中的女性形象也在不断变化、更新,实现了从依附型人格到独立型人格的转变。但矫枉过正的情况下,大量“穿越情节”应运而生,譬如《步步惊心》中的若曦、《宫锁心玉》中的晴川,都知古通今、无所不能。她们尽管不会被宏大叙事的主体建构所询唤,但也渴望回归现代这座自由的桃花源。《甄嬛传》实际上是一部试图展现两性对话锋芒的古装剧,甄嬛从无意入选、安于现状到走向巅峰,实现了人生中的三级跳。她不再是皇宫的囚徒,而成为内院之中的狩猎者,与代表封建权力巅峰的帝王正面对决。尽管如此,甄嬛在结尾中还是将权力移交,让子女回归无忧无虑的自在之境。而今的三部“现象级”古装剧所编织的“成长梦”则另辟蹊径,书写了迥异的成长旅途。
《延禧攻略》一反古装剧常规化的主角设置,塑造了一个恩怨分明、睚眦必报、心思深沉的“黑莲花”形象。《延禧攻略》中的表层成长线,正是这朵“黑莲花”的晋升线,从宫女、女官,最终成为襄助乾隆盛世的令贵妃,剧中的魏璎珞一反常态,她不再是甄嬛式的被迫入宫,而是主动入宫、直击敌人。她屡次挑战权贵,虽置身险境,却又凭借着聪明与智慧化险为夷。因此,魏璎珞在消解困境的同时,也消解了权力体系,宫墙之于《延禧攻略》,不再是牢笼与桃花源的分割线。实际上,观众随着魏璎珞的升迁之旅,完成了一次从劣势扭转乾坤的养成游戏,体验了一把逆袭的快感。《延禧攻略》更深层的成长线是魏璎珞性格与能力的成长及变化:魏璎珞在富察皇后的帮助下不仅数次脱险,还由鲁莽变得隐忍,从大字不识变得通晓笔墨。这不仅颠覆了以往古装剧“男性人生导师”的设置,还弥补了以往古装剧中主要人物在性格、能力等成长面向上的缺失与断层。《延禧攻略》最深层的成长线则是魏璎珞意识上的成长。魏璎珞三次入宫,实现了为姐姐复仇、为皇后复仇、完成皇后嘱托三个任务。在实现任务的过程中,魏璎珞的动力,也从最初的复仇,落脚于至善的初心。这样的成长变化,实际上逆反了《甄嬛传》由至善到复仇的人物动因,规避了“辣手摧花式”的宫廷生存法则。
《如懿传》与《延禧攻略》比较而言,受众少了几分逆袭的快感,多了几番成长的凝重。《如懿传》中的如懿,走上了一条逐渐看破真相、看透婚姻、看淡起伏的成长之路。在《如懿传》的开局,编剧设置的姑母形象,尽管戏份不多,但实际上分量足够。作为先帝废后的姑母,同如懿的最终结局相仿,但两者实际上有所差异。在姑母三言两语的关照里,透出的是她作为长辈对如懿的宠溺,以及作为家族前辈对如懿实现权力追逐的厚望。作为权力斗争的失败者,姑母将希望寄托于如懿,然而,如懿却以妻子的身份面对皇帝,以至于真情实感夹杂在权力欲望的斗争中,变得无所适从。实际上,《如懿传》的成长体现在两个面向:一是如懿从权力斗争过程中的置身事外,到面对问题行事果敢、爱恨分明,这一成长面向同《甄嬛传》相似,不同的是,甄嬛借助皇权统治下的所谓“智谋”登上了似乎可能存在的权力巅峰,而如懿则试图通过日常夫妻关系的身份视角与帝王平等对话解决问题。换言之,如懿渴望的是一种夫妻间的平等交流,渴望的是从男权社会中获得话语权;另一个面向则是如懿感情观的成长,即从“一生只一次心意动”的理想爱情观念,转变为身陷婚姻围城的淡然,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婚姻生活的自我反思,亦包含个体婚姻观与时代相悖后独有的质询。
《知否》不同于宫斗戏的垂直型权力结构(即女主所面临的问题仅与皇权休戚与共),盛明兰所面临的问题,分成了泾渭分明的两个部分:自身家庭(盛家)的生存困境以及婚后家庭(顾家)的生存难题。具体而言,作为庶女的盛明兰,如何在家中立足、为母报仇,以及婚后怎样面对时时掣肘的后婆母、在顾家自处,这成为明兰不断成长的动因以及观众持续关注的动力。具体而言,明兰受母亲临终所赠的《李娘子镇守娘子关》启示,发愤图强;又受祖母教诲,懂得隐忍、终报血仇;后与夫君同心,共抗家、国难关。如此的成长线路,实际上与人生不同阶段的历练与打磨相照应,且如兰实际上走的是一条从个体到家国的自我实现之路。着眼于细微,明兰的婚恋观同样经历了成长,她从最初执着于小公爷的海誓山盟,到认清小公爷的家庭局面以及其个人的无能为力,再到与心软、懦弱的贺弘文分道扬镳,最后与彼此心意相通的顾廷烨相守终生。当然,特殊的家庭局面也让她明白了在两性爱恨情仇之外的格局立场与自我精神的广阔天地。因此,《知否》使观众不仅仅陷于宅斗的情节之中,更落入明兰的细微成长之内。
正如波伏娃所说:“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1](P61)在女性日渐自主、自立、自强,且地位日益提高的当下,如何言说其成长命题显得十分重要。尽管《延禧攻略》中的魏璎珞善于钻营,《如懿传》中的如懿少了行动,《知否》中的如兰自带光环,但三部作品皆以女性的成长为基石,斩断了以往古装剧女性主体意识欠缺甚至缺失的锁链。
三、用“情”动人:“爱情异托邦”的补偿与满足
某学者在论述“异托邦”时,将其称作“某种对我们所生活的神秘而真实的空间进行的争议”[2],另一学者进一步解释“异托邦”的真实,认为“这种真实是具体的,这种真实在于异托邦存在于感知世界。”[3]也就是说,异托邦与其说是一种现实生活中的独特空间,毋宁说是一个可供反思的感知世界。实际上,当下的“现象级”古装剧都试图将文本打造为一座“爱情的异托邦”,供观众暂时从疲乏的爱情生活、枯燥的婚姻关系、疏远的都市空间之中抽离,以此得到某种情感补偿。
“暖男”作为韩剧中的常备人物形象,依靠细心体贴、温柔善良、擅长沟通等特质赢得了无数观众的芳心。中国影视剧中的“暖男”亦层出不无穷,从《我可能不会爱你》中的李大仁,到《何以笙箫默》中的何以琛,再到《那年花开月正圆》中的吴聘,“暖男”的建构不断地满足了女性观众的情感想象。然而,“暖男”形象实际上同中国传统文化、历史维度所标榜的男性形象相悖,作为现代都市社会的异质化产物,“暖男”是基于消费主义、个人主义风潮下,个体孤独症候的情感补偿。尽管如此,当下古装剧为了赢得市场,不得不为女性受众制造了一场“爱情的异托邦”,将“暖男”移至“古代”,使本就带有明显权力色彩的古代权贵们愈加温润如玉,《知否》中的小公爷齐衡便是其中典型。齐衡作为公爵独生的嫡子,本就身处高位,又痴情、英俊、好学,成为皇都之中无数闺阁少女的理想对象,同样,他也成为荧屏前无数女性受众的梦中情人。无独有偶,《延禧攻略》中的御前侍卫傅恒同样如此,傅恒作为皇帝亲信、皇后亲弟本就光环无限,又俊美、痴情、能文能武,因此,守望傅恒的爱情,成为大量女性受众追剧的不懈动力。然而,傅恒在人物设置上,不仅具有“暖”的特质,更具有鲜明的“骑士精神”。
“骑士”指影视剧中兼具“忠诚”与“勇敢”特质的男性形象,这类形象往往依靠着健美的身躯、勇敢果毅的性格以及英雄救美的情节赢得观众青睐。不同于“暖男”的移植于他处,“骑士”一直以来都作为古装剧不可或缺的形象出现,如《射雕英雄传》中的郭靖、《武林外史》中的沈浪、《小李飞刀》中的李寻欢等。不同的是,过去古装剧往往是以男性视角进行叙事,“骑士”们的“忠诚”与“勇敢”,并非只是服务于女主角,而当下古装剧中的“骑士”,实则成为女主角的附庸,他们甘于为女主角赴汤蹈火、万死不惜。《知否》中的顾廷烨,数次救明兰于危难,承诺她“我在男人堆中排第几,我就让你在女人堆中排第几”。《如懿传》中的凌云彻,为保如懿平安,忍辱负重,从容赴死。《延禧攻略》中的傅恒,矢志不移地守护魏璎珞,为了救她受瘴气所伤,伤后依旧大破缅军,马革裹尸。因此,“骑士”对于女性观众而言,同样是一剂有效的麻醉针,他们既满足了女性受众对于雄性荷尔蒙的想象,又迎合了女性受众渴望依靠、享受保护的心理。
“霸道总裁”作为影视作品的常备选项,经常性地走入大众的视野之中,这类形象兼备英俊潇洒、风流倜傥、家财万贯的特质,是创作者为受众勾画的“上层阶层”形象,如《杉杉来了》中的封腾、《泡沫之夏》中的欧辰、《一起来看流星雨》中的慕容云海等。落脚于古装剧,“霸道总裁”便随着情节的变化而不断翻新,成为皇帝、贵族、权威人物等角色的惯常人设。《延禧攻略》中的乾隆皇帝最为典型,他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他嫉妒魏璎珞与傅恒相恋,便利用权力将两人拆散;他发现魏璎珞偷喝避子汤,便与顺嫔上演移情别恋的戏码。《如懿传》中的乾隆,在前期为如懿不顾一切,欲忤逆母命封如懿为福晋,又在新婚第一夜逾矩与如懿同住。《知否》中的顾廷烨作为新皇重臣,钱权具备,在新婚之夜,他把全部身家托付给妻子明兰。“霸道总裁”的设置,同样是为了建构“爱情的异托邦”,女性受众沉浸于高度神化般的情感叙事中,想象权力逻辑所赋予她们的快感。因此,“霸道总裁”的人设,看似满足了女性渴望被权力阶层保护的私心,实则是女性依附于男性的另类体现。如此,《如懿传》中乾隆的设置,无疑给观众泼去了一盆冷水,这位有着极强的控制欲以及对皇权存有病态式眷恋感的皇帝,受政治身份的捆绑,愈加冷酷、残暴、敏感,因而逐渐在感情上被“束之高阁”。
事实上,三部“现象级”古装剧,虽然在本质上难以脱离“暖男”“骑士”“霸道总裁”的人物基底,但绝非照搬,而是将原有的形式加以糅杂、相互融合,给观众带来了崭新的体验。尽管如此,三种形象虽然激发了观众浪漫情怀的想象,但“却又让大部分人生活在困顿与衰败的挣扎中而不自知,反而更心甘情愿地像机器一样在现实生活中日复一日的劳作。”[4]
四、与“今”共鸣:现实世界的影射与反馈
正如康定斯基所说:“任何艺术作品都是其特定时代的产儿,同时也是孕育我们感情的母亲。”[5](P11)那些脱离了时代的作品,无疑会被时代所无情抛弃。因此,无数古装剧之所以能够热播,只因它们与当下的日常生活紧密相关,即古装剧创作者将现代视角、文化融入到历史演绎之中,赋予古装剧以现代感。这也提醒创作者,古装剧唯有寻觅自身与当下生活、文化的契合之处,体现现实社会的普遍诉求,才能迎合大众口味。正如前文提到的三部“现象级”古装剧,不仅追求现代感,更是现实生活的古装化演绎。
《延禧攻略》与其说是一部后宫生存录,不如说成是“后宫”的一场升职记,它直接影射了现代社会的职场风云。“宫斗剧”往往构架了一个封闭的集权中心——后宫,这座后宫更是暗合了竞争激烈的现代社会。后妃在对权力、身份的趋附与追逐中逐渐丧失自我。《延禧攻略》中的高贵妃、纯贵妃、辉发那拉皇后等人物,都是在危机的逼迫与权力的侵蚀下被欲望驱使,变得疯魔。而这为了后位/权力苦心钻营、尔虞我诈的众妃相,实际上同当今社会中的某些对于“职场生存”的当下想象相吻合。《延禧攻略》中的魏璎珞与富察皇后,则是面对身份焦虑、生存危机之下,做出了两种迥异选择,即“直击”与“逃避”。魏璎珞从初入宫的小宫女,到成为皇后心腹,再到权倾六宫,面对打击和压迫,其遇敌杀敌、有勇有谋,最终走向后宫/职场的巅峰。富察皇后则与之相反,作为封建礼教/职场规则的传播者和巅峰人物,她在遭遇继承人被害、副手背叛之后,选择死亡。富察皇后的死亡,既是她对丧失理性、利益为王的现实境况的逃避,又是她实现自由、回归初心的一次反叛。
《如懿传》看似讲述了波谲云诡的后宫,实则描绘了帝后婚姻中的信任困境,它与普通观众所面临的婚姻围城相似。“情感实际上就是一种集中、强化了的生命,是生命湍流中最突出的浪峰”[6](P43),《如懿传》的生命,就落脚于如懿与乾隆的感情之上。《如懿传》中的如懿,与乾隆从青梅竹马、两情相悦,到恩爱相知、患难与共,直至信任丢失、婚姻破裂。这缘于乾隆从起初承诺如懿“对着朕,还是可以保留青樱(如懿闺名)的性子”,但在婚姻之中,却又奉劝如懿“你得守着三纲五常,还有君臣夫妻”;他从来对如懿说着“你放心”,转头又成为太后口中那个“硬是一声不吭,也不来替她求情”的人;他一味地说着“相信”,却在天象之说/皇权、出轨传闻/男权面前彻底倒戈。同样,这也缘于如懿抱定“一生只一次心意动”的爱情观,却忽略了婚姻本身的不自由。甚至可以说,如懿沉溺在爱情的幻想里,无法忍受婚姻中的绝望和痛苦。除此之外,两人婚姻的破裂,也源于两者迥异的世界观,当得知一夫一妻制时,如懿兴奋异常,却换回乾隆的“痴心妄想”。作为觉醒的女性,如懿不甘成为“缺席和缄默”[7]的人,想要获得平等的人格尊严和独立地位,却面对的是一个皇权体制的代表者。因此,如懿与乾隆的婚姻,也败于“皇宫”这座封建的牢笼。
《知否》表面上关涉大宅院内的风起云涌,实乃串联了闺阁少女的婚配选择,其实是所谓当下时代择偶与婚配观念的某种焦虑性表达与话语策略。《知否》中的几个闺阁女的择偶观念各不相同:作为嫡女的华兰和如兰,一个受父母之命嫁于伯爵嫡子,一个则自主婚配嫁于寒门进士;作为庶女的墨兰和明兰,一个奉子成婚嫁入高门,一个则选择担当有余的朝廷“黑马”为夫;作为嫡支的淑兰和品兰,一个冲破世俗与“软饭硬吃”的穷秀才和离,一个则与青梅竹马的胡泰生相守。六姐妹面临的婚配对象,实际上同“妈宝男”“直男”“凤凰男”“渣男”“中央空调男”等当下常见“问题”男性别无二致。不仅如此,她们所面临婚配问题,亦与当今社会难以分离,如婆媳、门第、生子、出轨、财产、杂务等。作为主线的明兰,更是在面临担子太重的齐衡、心太软的贺弘文以及“托付中馈”的顾廷烨时,果断地选择了后者。在选择的过程中,明兰更是说出了择偶要看“品性的最低处”这种堪称当代择偶名言的金句。实际上,观众更是从明兰与顾廷烨婚后的生活中感知到夫妻间应该建立信任、互相帮扶、学会包容,这些也是《如懿传》中的两人走向决绝的关键之所在。因此,《知否》实际上描绘了一幅当代人的择偶大观,观众也借此品评了一番“男女梯度论” “资源交换论”“同类匹配论”“需求互补论”等,此三部“现象级”古装剧,不仅获益于其金玉般的外在,更因其存有对应现实、照见现实之内心。
这些不谋而合的与“今”共鸣,实际上戳破了目前影视剧叙事的又一层面纱:一切的想象性设置,只是影视剧的强心剂,只有让剧情落地于现实,才能真正意义上地引起观众共振。但是,我们不能忘记:“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8](P201)这种所谓的“现实”,终究被“宫斗”“宅斗”的情节所裹挟,成为空中之楼阁。
结语
所谓“现象级”古装剧,能够成为“爆款”,离不开它们的四层叙事面纱。这些创作者在重视经济效益和流行热度的同时,树立创新意识、确立现实基底,以至于获得了较好的口碑。但是,古装剧同样需要居安思危,毕竟一味地制造狂欢式的视觉效果、呈现不痛不痒的现实问题,却又让观众甘心沉浸在一场浮华假象之中,迟早会被厌弃。因此,如何在建立古装剧文化品质的同时,真正切合实际、关涉现实,仍是需要思考的问题。当下,仅是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