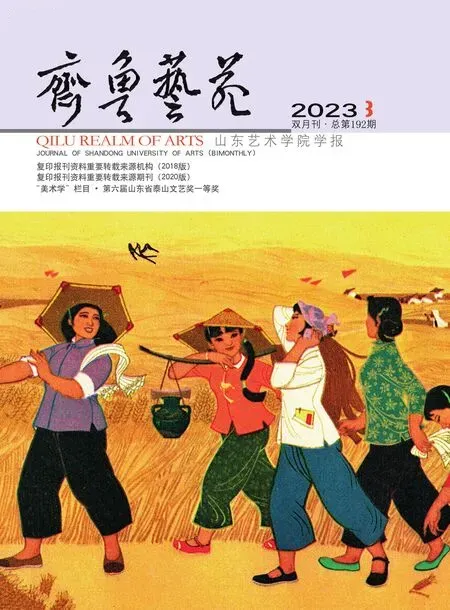小景画的“景”与“境”
刘娅萍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300)
“小景画”通常被称为“小景”,作为一个概念,出现在北宋中后期至南宋初期的相关文献中。主要有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宋神宗熙宁七年,即1074年)、米芾《画史》(约成书于1101年前后,1101年为宋徽宗建中靖国一年)、敕集《宣和画谱》(宋徽宗宣和二年,即1120年),以及南宋葛立方《韵语阳秋》(南宋孝宗隆兴元年,即1163年)、邓椿的《画继》(南宋孝宗乾道三年,即1167年)。郭若虚《图画见闻志》、米芾《画史》都未曾对“小景”做出概念的说明,但记载了数量不小的题为“小景”的画作。郭若虚《图画见闻志》中记僧惠崇与高克明都有小景画,米芾《画史》中更是罗列王维、易元吉、赵令穰等人的小景作品。《宣和画谱》中对小景画的概念陈述,反映了小景画在北宋的发展情况:“布景运思,不盈咫尺而万里可论。画墨竹与夫小景,自五代至本朝,才得十二人。”话语中表达了两个意思:一是“小景”这一概念在北宋时期形成;二是发端于五代的小景画,北宋时已成规模并受到官方肯定与认可。
一、小景画
小景画包括以花鸟表现为主的小景花鸟画和以山水表现为主的小景山水画,《宣和画谱》之后,南宋邓椿《画继》中有“小景杂画”一条,对小景画记载比较详尽,列段吉先、李达、刘浩等人,善画小景,好作沙汀远岸含蓄不尽之意,笔法轻清,景致幽远。总结《宣和画谱》《画史》《画继》等文献中的记载,可作出如下判断:
首先,小景画尺寸小。它们常被作于小轴、团扇、手卷上,尺寸较小,不盈咫尺。《画继》记赵伯驹多作“小图”,记赵令穰所作多“小轴”,记李昭“善墨花小笔”,《宣和画谱》记内臣罗存“性喜画,作小笔”……皆以“小”字定义。关于尺寸小的原因,米芾《画史》中自言当他碰到知音求画时:“只作三尺横挂三尺轴,惟宝晋斋中挂双幅成对,长不过三尺,褾出,不及椅;所映人行过肩汗不着,更不作大图,无一笔李成、关仝俗气。”按照米芾的说法,文人画家们以画“大图”为“俗笔”,但我们也可理解为文人们以草草逸笔表达情感足矣,他们很难像职业画家一样在较大的尺幅上深入表现多个物象和大场景。
其次,小景画景小。《宣和画谱》记赵令穰所画都是京城周围“坡坂汀渚之景耳,使周览江浙、荆湘,重山峻岭,江湖溪涧之胜丽,以为笔端之助,则亦不减晋宋流辈”,写驸马都尉王诜“写烟江远壑,柳溪渔浦,晴岚绝涧,寒林幽谷,桃溪苇村”,又记宗室赵孝颖的“小景图”取象于“池沼林亭所见”。 邓椿《画继》中亦曾提到赵令穰学苏轼画“小山丛竹”。米芾《画史》记王维画“小辋川”。根据王维的《辋川集·序》得知,辋川是由孟城坳、华子冈、竹里馆、鹿柴寨等20处景观构成,是王维享受“晚年唯好静,万事不关心”的隐逸闲适生活的地方。在王维所命名的20处景观中,并无“小辋川”一景。可以推测,“小辋川”大概是指多个“辋川小景”。可见,小景画之“小”在于所取之景非荆浩、关仝、范宽等所画的大山大水,而更多是江岸汀渚、村居野渡、灞桥风雪、人造园林中的小景致,以及花竹蔬果、虾鱼蒲藻等身边之物。
第三,虽然是小画幅、小景致,所画却都是可游、可隐、可居之地,因此,独有情致和别样气息。这些小景致,记录了文人日常生活的周边,表达了文人对田园生活的向往,比起北宋流行的高山大川,小景更接地气,更接近文人的生活。按照《宣和画谱》中小景画“布景运思,不盈咫尺,而万里可论”的说法,小景画尺幅虽小,却能以所描绘的有限物像体万里之察,容万里之思,可谓纸短情长,有苏轼所说的“观士人画如阅天下马,取其意气所到”的理想境界。
所以,小景画在两宋时期,广泛流行于两个群体。一个是文人、隐士群体,王维、巨然、徐熙、易元吉、惠崇、米芾等皆在此列。另一个是《画继》所说“侯王贵戚”以及与皇室关系亲密的内臣等,我们所熟知的赵令穰、赵令庇、赵孝颖、王诜、赵頵、赵士雷、赵士尊等人都属于这一群体。他们不是职业画家,但有条件与皇室、文人、职业画家亲密接触,并受到一定影响。他们以随手小幅、寥寥几笔,来表达特殊情绪,呈现寂静悠远的意境。比如端献王赵頵,“戏作小笔花竹蔬果,……复善虾鱼蒲藻,古木江芦,有沧洲水云之趣,非画工所得以窥其藩篱也”[1](P128)。宗室赵士雷“作花竹,多在于风雪荒寒之中,盖胸次洗尽绮纨之习,故幽寻雅趣,落笔便与画工背驰”。宗室赵士尊,“所作多以小景山水,实唱于士遵。然其笔超俗,特一时仿效宫中之化,非专为此等作也” 。前述驸马都尉王诜,“写烟江远壑,柳溪渔浦,晴岚绝涧,寒林幽谷,桃溪苇村,皆词人墨卿难状之景”[2](P705)。嗣濮王宗汉,太宗之曾孙、濮安懿王之幼子,亦曾画“荣荷小景图”。单从画题看,文献记载的职业画家的“小景”作品较少,这应该与他们的职业性质有关系。因为比起文人隐士与侯王贵戚,他们在创作内容与方向上较少自由度。他们的作品,更多要满足和服务于以皇室为代表的画作受众。《宣和画谱》记职业画家黄居寀有“小景竹石水禽图”,郭若虚《图画见闻志》中记有职业画家高克明、梁忠信等人亦曾画小景,其中,“高克明,京师人,仁宗朝为翰林待诏。工画山水,采撷诸家之美,参成一艺之精。团扇卧屏,尤长小景。但矜其巧密,殊乏飘逸之妙”,梁忠信则“体近高克明”[3](P482)。
最后,从文字记述中可知,小景画至少有两个可以追溯的源头:王维与李成。米芾《画史》、邓椿《画继》都提到赵令穰作小轴清丽雪景,类似王维汀渚水鸟。根据文字描述,王维的“汀渚水鸟”呈现出典型的小景之“景”:汀渚水鸟,或柳溪渔浦、桃溪苇村构成画面近中景,烟江远壑、寒林幽壑将观者视线引向远方,成平远之景——这就构成了小景画的基本样式。所以,本质上说,小景画虽名为“小景”,实为“大景”“全景”,其形式上更加复杂、全面,层次上更加丰富。“小景”之关键在“景”,近景、中景、远景具足,高、深、远完备。比起北宋流行的大山大水画,它尤善平远之景;比起折枝花鸟的局部放大,它是一个可以走进去的广阔空间。
米芾在论及自己画作的尺幅时表明,自己不作大图,因此,无一笔李成、关仝俗气。《画继》中,邓椿提到一位叫刘明复的画家,“为直龙图阁,师李成,特细秀”。大幅、细秀,可能是米芾认为李成画俗气的重要因素。《画史》《画继》中都记王诜的小景画与李成有不解之缘,《画史》说:“王诜学李成皴法,以金碌为之。似古今观音宝陁山状。作小景,亦墨作平远,皆李成法也。”[4](P984)熟悉李成作品特点的观者可知,善用笔墨、表现平远之景是李成山水画的独特之处。《宣和画谱》卷十记李成所画山林、薮泽、平远、萦带、曲折、飞流、危栈、断桥、绝涧、水石等,皆吐其胸中而写之笔下,并记李成作品如《秋岭遥山图》《冬景遥山图》《古木遥岑图》《远浦遥岑图》《平远窠石图》《小寒林图》……一个“遥”字,道出李成画面中“平远”所致的视觉效果。王诜等人将李成的平远在小景画中作了发挥,使其成为小景画的关键因素,它将观者视线引向远方,拓展了小景画的景深,比起北宋流行表现的高山大川、折枝花鸟,多出一个表现的空间与维度。可以说,平远,是成就小景画的关键因素之一,它使小景画成为“景”。
二、江湖景与江湖意
与小景画经常一同出现的几个词是:江湖景与江湖意。小景就是“江湖”的指代,是缩小的江湖。因此,在两宋的画史中,常有“江湖景”“取景江湖”“状江湖所有”等字样。人又会从“江湖景”中,获得“江湖意”,产生“江湖之思”。
郭若虚《图画见闻志》“论制作楷模”中,论及画水,要形态必备,“使观者浩然有江湖之思为妙也” 。通过画面物象的描绘,使人产生“江湖之思”“江湖向往”。
“江湖”就是与京国、朝市相去甚远的地方,江湖就是自然山水。郭若虚论“徐黄异体”时说徐熙状“江湖所有,汀花野竹,水鸟渊鱼”。“汀花野竹,水鸟渊鱼”,就是“江湖所有”。所以,现实中的“江湖”,可以为画中“小景”,“小景画”又能使观者浩然有江湖之思。
米芾《画史》记赵令穰作小轴清丽雪景,“有江湖意”,又记“杭士林生作江湖景,芦雁水禽,气格清绝,南唐无此画,可并徐熙,在艾宣张泾宝觉之右,人罕得之”[5](P983)。
《宣和画谱》记嗣濮王赵宗汉,“尝为《八雁图》,气韵萧散,有江湖荒远之趣。识者谓不减于古人”[6](P112);记内臣罗存“性喜画,作小笔,虽身在京国而浩然有江湖之思致,不为朝市风埃之所汩没。落笔则有烟涛雪浪,扁舟翻舞,咫尺天际,坡岸高下,人骑出没,披图便如登高望远,悠然与鱼鸟相往还”[7](P98);又记泼墨者王洽“性嗜酒疏逸,多放傲于江湖间”。放傲江湖是成就“真画者”、成就“真作品”的先决条件。
“江湖意”“江湖思致”是两宋“小景画”创作的本质目的。“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江湖”,比起京国朝市,是无限广阔的江河天地,是更适于安放灵魂、实现精神自由的地方。也是使物成为物本身、人成为人本身,使万物不失其性的地方。《宣和画谱》卷九“龙鱼叙论”中论《诗经》之《鱼藻》,言《鱼藻》中“有所谓颁其首,莘其尾,依其蒲,以言其游深泳广,相忘江湖,以比夫难致之贤者”,其对创作花鸟游鱼的要求已远远超出写貌状形的需要,以物寓意,表现鱼在藻间逍遥游,自在,安适。“鱼何在?在乎藻”(吴闿生《诗义会通》)只有在藻间游动,才能使鱼成为鱼。花、鸟、人等世间万物亦是如此。
《宣和画谱》所记文臣刘寀最为典型。刘寀少时狂逸不事事,放意诗酒间,与贵游少年相从无虚日,吟诗作画。他最善画鱼,但绝不是为了表现鱼的“富贵有余”“连年有余”的民俗含义,而是“深得戏广浮沈,相忘于江湖之意”。所以,将鱼置于水中,以水草、落花渲染落花流水、自由逍遥的环境。美国圣路易斯艺术博物馆藏有一幅刘寀的《落花游鱼图》,画群鱼嬉戏游耍于落花流水间,营造出一份自然自在的景致。这与仅仅表现鱼的“鬐鬛鳞刺”的画家出于不同的目的:仅画出鱼的鬐鬛鳞刺者,所画非水中鱼,故无涵泳自然之态。而“涵泳自然之态”才是表达鱼的生命本质的东西,刘寀画游鱼,可得此态,所以,颇为士人所推誉。刘寀是北宋时期一文官,曾“历任州县”,后为“朝奉郎”,“漂泊不得志,曳裾侯门”,却将生活过出了诗意,其自由心境,与游鱼无异。
景,由人而造,古代众多画家远离闹市,择一处幽景,画地为苑,构筑一个私人的自然园林,在此韬光养晦,并因此成为王诜、米芾、赵令穰等一干文人遥拜的偶像。王维有辋川,滕昌祐有蜀地“小筑”,荆浩有洪谷。这是一个浓缩版的自然,经常会被称为是“小筑”,日久,将这个“小筑”搬至画面,便有了“小景画”。《宣和画谱》记王维“卜筑辋川,亦在图画中,是其胸次所存,无适而不潇洒,移志之于画”。可以这么说,小景画表现出文人画家所生活的环境,代表的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状态,这不是所有人能够享受的,所以,人人向往,尤其是身处庙堂又难忘江湖的人。他们努力为自己造一份“景”。宗室赵孝颖,取象于“池沼林亭所见”,曾画“小景图”,模写陂湖间物趣,“得之遐想,有若目击而亲遇之者”。宋代宗室对江湖的向往之心可见一斑,小景画在北宋皇室的流行,绝非人云亦云的跟风,而是代表了宋代皇室、文人普遍存在的归隐心理,或者更具体地说,是在嘈杂的朝市生活中,追求诗意化的生存方式。
北宋在治国韬略上远不及唐代,但在文化上却足以与之鼎足。从文化的特点说,北宋趋于内省,追求精神上的超脱和解放,从中寻找个人诗意化的生存。即使是以追求客观、理性为主旨的理学也在教人寻孔颜之所乐。北宋理学代表人物邵雍就曾论及:对“理”的终极追求,是要达到润身、润心、生命亦润的目的,其它,都是“余事”。在这里,一个“润”字,就已经化理学的刚硬为诗意,“诗意化的生存,也就是文学化的生存,不仅理学如此,绘画也是如此”[8]。
“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唐白居易《中隐》)大隐喧嚣,需要极强的意志力才能在朝市与自由的心灵之间进行屏蔽。比如苏轼,在乌台诗案之前,也未能做到全然的超脱,并因此而深感痛苦;却又感觉丘樊清冷,因此也做不到像滕昌祐、刁光胤、林逋一样,真正远离朝市。文人总能为自己贪恋尘世又向往江湖的无奈之举找到解决的办法——于城市之中构筑园林,建筑一个只属于自己的自然景观,构筑精神家园。到了两宋,在城市之中建园造景的潮流更盛。从皇室到普通显贵,纷纷构筑自己的“小景”——私家园林。皇家有《艮岳记》,达官显贵、文人名士的园林著录于《洛阳名园记》。这其实是每个人内心深处的一亩田,是对白居易中隐思想的最佳阐释,充分表现出古代文人能够于儒道之间切换自如,在俗世与精神家园之间出入、行走自由,虽身在京国而浩然有江湖之思致,并不为朝市风埃之所汩没。这样,仍然能实现他们亲近自然、融于自然、天人合一的修身目的。《宣和画谱》记唐代画过《芙蓉杂禽图》的周滉,作远江近渚、竹溪蓼岸、四时风物之变,“揽图便如与水云鸥鹭相追逐”。虽身不在江湖,披图幽对,也能如望秋云,神飞扬,临春风,思浩荡!小景画具有“卧游”功能,当老之将至或拘于朝市时,小景画同样能满足人们对“江湖”和田园生活的渴望。
三、“无我”与“有我”之境
“小景”概念源出《宣和画谱》卷二十,该卷以“墨竹叙论”“墨竹(小景附)”为内容。多数人困惑于缘何“小景”附于“墨竹”卷中?
首先,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如“墨竹叙论”所言,墨竹多出于词人墨卿,他们“胸中所得固已吞云梦之八九,而文章翰墨形容所不逮,故一寄于毫楮”;而小景,虽不盈咫尺,但布景致思,万里可论,亦非俗工所能到。相比于传统文化中的其它花木,仅以墨色表现的竹,较早与文人品性内涵产生紧密联系。相较之下,小景画也是以身边寻常之物、寻常之景来表达文人士卿胸次。墨竹与小景,二者的共同功效在于:“拂云而高寒,傲雪而玉立,与夫招月吟风之状,虽执热使人亟挟纩也。”(《宣和画谱》卷二十)这个说法反映出文人画家对墨竹与小景的追求都在一个“境”字,境中有我,亦无我。
《宣和画谱》中单列“墨竹”一卷,说明墨竹画在北宋时期已然独立成科。但对墨竹画的发展及理论形成产生重要影响的,还是苏轼与文同的竹画理论及实践。在苏轼的绘画理论体系中,高人逸才的绘画比“世之工人”的作品有更高境界,能浑然天成,又能得诗人之清丽,“离画工之度数”甚远。因为文人画家更能把握无常形却含常理的山石竹木、水波烟云,能以数尺之竹,现万尺之势。所以,“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这里的“成竹”,是文人画家对竹子的本质、对竹子所表达的“常理”的宏观把握,最终做到“人与竹化”,人与竹子合二为一,画家不过是“托与斯竹”而表现出“常理”与“道”。但是,又“岂独竹乎”!在文人笔下,山水树石,水波烟云,都可以成为这个载体。文同之墨竹,是其表现“常理”与“道”的载体;同时,竹如我,我如竹,其竹画看似为无我之境,实为有我之境:正如他传世作品中唯一被公认为真品的《墨竹图》(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以竹干曲折,末端翻仰而上,屈伏之中枝掀叶举,似有隐隐幽意,让人想见其屈而不挠的风节”[9](P323)。
小景画亦然。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说,其与唐代人物画中的衬景有密切联系。现在我们能看到的大部分唐墓壁画中的花鸟形象,都未从人物画、装饰纹样中独立出来。比如,章怀太子墓前甬道西壁画的“侍女鸡冠花”,画中女子婷婷侧立,望向画面右下角的一株鸡冠花。这株鸡冠花,笔直挺立,根部被石块遮挡。古代人物画中的人物形象常被拉远了表现,所以人像多全身。满足于画中人物全身像的图式需要,花木鸟禽形象也多全株或全身。画面虽简单而稚拙,却已经呈现出一个全景的视角。当它完全脱离人物画而独立的时候,花木鸟禽完全成为画面的主角,成全了小景画的构图形式。
人能与花木共忧乐,亦能与花鸟互为替身。画中人的退出,营造出一个“无我之境”。《画继》卷四“缙绅韦布”中著录画家陈直躬时,引用苏轼为陈直躬题写的《雁》(诗全称《高邮陈直躬处士画雁二首》)诗中“野雁见人时,未起意先改。君从何处看,得此无人态”两句。据传高邮(今江苏高邮)人陈直躬为北宋文人陈偕之子,本出身富贵之家、书香门第,“家故饶财”。但陈偕独喜学画,以至于“家日以微,遂以为业”。陈偕兼具人品与画品,深受士大夫喜爱。陈直躬学艺于父,受到苏轼等文人追捧。苏轼向其求画,得此《雁》,遂有此题画诗二首[10](P614)。这两句诗的后一句是:“无乃槁木形,人禽两自在”(《高邮陈直躬处士画雁二首》其一)。人与雁正确的相处之道,也是能获得雁的真正形貌、窥探其形神的关键,在于人隐藏自我、忘掉自我,形同槁木,这样才能看到最真实的雁的形态,才能做到“人禽两自在”。同时,苏轼又赞雁的众人皆醉我独醒:“众禽事纷争,野雁独闲洁。徐行意自得,俯仰苦有节”。苏轼随即将愁绪烦恼寄情于江湖,“我衰寄江湖,老伴杂鹅鸭”。
人在景后,但情在景中。“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于无我之境,以物观物,定“是一番有我之境,水是我,烟是我,有水便有我,有烟便有我,水能入画,烟能入画,我岂不已隐隐然在其中了吗”[11]。画家们通过塑一株花、一丛竹、一只禽,来代替“我”,以相忘于江湖。
“我”的退出,成全了山、水、花、鸟、竹木的画面呈现。同时,那个可以代表“我”的花木或鸟禽,既来自自然、现实,又超越自然与现实,代表了人的理想与境界。王国维认为,有造境,有写境,这是“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分也。然而二者实难分别,在小景画中,不管是造境还是写境,终归是在表达“心境”:因为,心偏地自远。
竹子算作是小景画中最常见的花木之一,其可为山石旁寥寥数笔,也可为小山丛竹一片。元代才女管道升有一《烟雨丛竹图》(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安岐《墨缘汇观》对此画的描述可见小景画一斑:“淡墨细竹,沙渚遥浦,其间烟雾横迷,万玉幽深,茫茫有渭川千亩之势;坡陀皴法,大类松雪,布景一派,平远天真。”
——丰子恺漫画作品欣赏
——趵突小景
——以《诗馀画谱》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