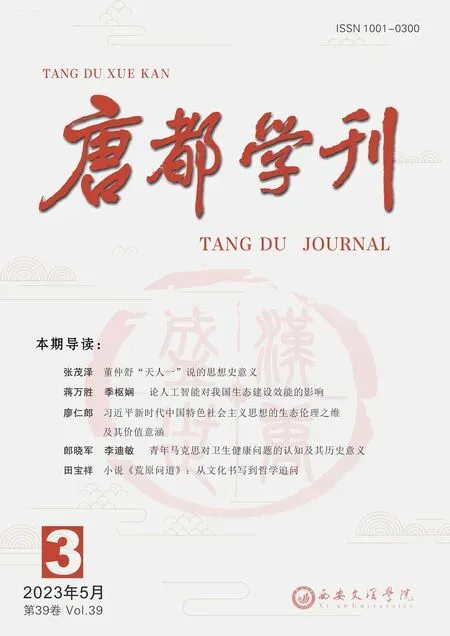论西汉时期“大共同体本位”之构建
——以董仲舒“大一统”思想为视角
焦春鑫,杨玉仁,2
(1.中国政法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北京 100088;2.甘肃政法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兰州 730070)
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认为,人类群体生活包含两种形式即共同体和社会,共同体是在大自然的选择下形成的,人类社会的形成是以个人意志的集合为基础的,个人意志是自由的、本我的,属于个人主体本位,共同体的存在是亘古不变的,而人类社会的存在发展则是生生不息的。中国人类学家将滕尼斯所称的共同体称为“社区”或“小共同体”,小共同体包含村落、宗族、家族等多种集合形式。秦晖教授认为中国还存在超越小共同体的大共同体的存在,即将各个小共同体以国家集权的形式组织起来形成的大共同体,这种共同体内部包含了思想、组织、文化等各方面的控制,而儒家作为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正统思想则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笔者认为,董仲舒所主张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正是此角色发展的开端,是对“大共同体本位”构建的极其重要的思想和制度设计。
一、大共同体本位的特点
有史以来,大共同体本位便已存在,自虞夏时便以分域而治,各司官职,中华民族的整体国家观肇始于此,至清而终。秦晖先生认为,中国古代封建王权是以秦始皇统一六国为开端的,秦朝开创的大共同体格局,将民众的私人欲望和利益统一到国家意志上来,此种“大共同体本位”的构建是以“王权专制主义”为基础的,对国家的强盛和统一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大共同体是以维护封建王朝统治为基点
自先秦时代,周天子从诸侯的分封,便处于天下共主的地位,即使后来礼崩乐坏,“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等阶段,各诸侯国名义上仍接受周天子的认可和册封。从文化角度来看,《诗经·小雅·北山》云:“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1]意为至少在礼节性的宏观概念层面,王权可以控制天下所有的资源。在华夷之辨层面,中国古代倡导以中华文明体制为核心,并接受中原王朝的册封。据《礼记·王制》载:“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2]由此可见,西汉时期各方须尊中华文明这个大共同体。
(二)大共同体是以“畿服”体制为具体形式
畿服体制是以距离和亲缘关系的疏远为参照对象形成的一种对国家的管控体制,距离首都近的地区享受的待遇与中央的亲近程度成正比。《国语·周语》载:“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3]五服体制将权利义务等级分为三个层次,首先是以王权为中心的甸服,是对皇权统治中心区域的管辖;其次是对诸侯管辖区域的侯服和宾服;最后是对蛮夷之地的要服和荒服。王权对五服范围内根据距离亲疏远近规定的权力和义务有不同的等级。西汉时期的京畿制度主要体现为二元制特点,不仅包括对内史和三辅地区的重点地区,还包括对弘农郡和三河地区的准京畿地区,在上述两个地区内不分封诸侯和王国,在税赋上也对重点地区予以优待,非重点区及边远地区则不享受此优惠。
(三)大共同体以宗法制、分封制、世袭制为纽带
自虞夏时,王朝便开始实行世袭制度,使国家由之前的“公天下”变为“家天下”,国家权力日益集中;到了周代在地方上实行分封制,国王将自己的亲属、近侍、功臣分封到各地去做诸侯,世代延续,定期朝见周天子,接受周天子的敕诏和册封,并负有提供赋税、力役、军事等义务。诸侯以下也层层分封,形成了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的结构模式,到了秦朝实行郡县制,废除了分封制,遏制了小共同体成长的土壤,反而促进了大共同体的成长,促进了大共同体在国家结构、权力等方面的急剧膨胀,一系列重大工程均是在此基础上建构起来的,如修建长城、阿房宫和骊山秦始皇陵墓等;到了汉代国家实行了郡国并行制,在郡国内部仍实行类似于周代分封制的宗法结构模式,另外在一些官职的设置上也实行世袭制,如史官。宗法制最大的特点是加强了家族的权力,使家族的力量和国家政权紧紧联系在一起,形成了“家国同构”的局面,在家族内部以父权、夫权为尊,在国家内部以君权为尊[4]。
二、“大一统”思想建构的背景
“大一统”思想构建古已有之,可追溯到尧舜时期,《尚书》中记载了大量关于大一统思想的内容,《尚书·禹贡》是中国古代第一部关于地理学方面的书籍,书中把古代中国划分为九个州,分别是雍、扬、兖、豫、冀、荆、青、徐、梁州,目的是为了“任土做贡”,将各州所须缴纳的贡赋做出了条理清晰,分门别类的划分。体现了天下一统的良好愿景;《禹贡》中还明确了“五服”的概念,规定了“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銍,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诸侯。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5]167-169此意为从畿服之地到下属各藩属国管理层级逐次下放,并兼顾文化教育和战争防卫,使华夏文明的教化思想远播到蛮夷地区,体现了华夏王朝的大一统治理思想。《尚书·尧典》中载:“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峻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5]245-289意为尧发挥自己的德行,使上下和睦,九族相亲,百姓安居乐业,达到了万邦和谐的效果。该文意为以“尧”为核心形成了一个由内而外的同心圆结构的国家治理模型,体现了家国团结、和谐共生的大一统思想。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大一统”思想日趋成熟,由于周王室的权威日益衰落,诸侯争霸的时代揭开了历史序幕,礼崩乐坏随即成为了时代主题。此时孔子创立的儒家学派成为凝聚人心的救世良方。孔子主张恢复以“周礼”为核心的统治秩序,主张恢复先周时期的礼乐制度,建立一套乐从属于礼的思想体系,礼是维护宗法制亲疏远近和等级秩序的基石,乐是用来缓和社会矛盾和规范等级秩序的利器。不同等级的人必须遵守各自阶层的礼乐规范,不得做出僭越之举,否则便是对等级制度的破坏,便是整个社会的公敌[6]。故孔子对季氏“八佾舞于庭”的行为做出了“是可忍孰不可忍”的评价,在孔子看来,季氏这是在践踏以“礼”为核心的王道秩序,是对等级秩序的僭越,是一种违反人伦纲常的极其严重的犯罪行为。故而,孔子提出了“克己复礼”的政治思想,主张恢复先周时期的等级秩序,以克制自身的私欲为出发点,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宗法秩序,以规范社会秩序,恢复先周时期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政治生态。孟子时期,中国历史步入了战国时期,社会更加动荡,诸侯征伐更加频繁,周天子已不再具有号令天下的实际权力,孟子的主张更倾向于取周代之的思想模式。《孟子·梁惠王上》将该思想归纳为“定于一”,要求统治者减少杀戮,实行仁政。《说文解字》中对“一”的解释为:“一,惟初太始,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此中的“一”意为“本质”“本源”,是万物产生的源头,在此基础上建立理想的统治秩序。孟子认为实行仁政的首要目标就是要“制民恒产”即“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 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 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 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 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7]86-88孟子还提出:“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拱秦楚之坚甲利兵矣。”[7]100-102即要保证百姓的基础物质生活条件,并辅之以孝悌忠信作为伦理约束,使国家安全得到保证。孟子基于“性善论”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学说,并将“定于一”思想发扬光大,为“大一统”论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秦朝基本上是以法家学说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大一统王朝,法家努力构建一种以皇权专制为核心的统治架构,主张君主皇权统驭一切,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事皆决于法,“明主使其群臣, 不游意于法之外, 不为惠于法之内。”即君主在行使自身权力的过程中要严格依照法律办事。在政治上建立三公九卿制的官僚制度体系,同时“废分封,行郡县”“车同轨,书同文”统一货币和度量衡,建立覆盖全国的驰道系统,使中国第一次在法令制度层面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统一。在思想文化方面实行“焚书坑儒”,将社会思想统一到法家思想上来,巩固了秦朝的大一统国家的思想基础,秦朝实行的一系列基于法家思想建立的统治秩序无疑为中国古代的“大一统”皇权专制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和制度基础,为后世的“大一统”王朝的建立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
三、董仲舒“大一统”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一)董仲舒大一统思想形成的基础——“独尊儒术”
汉初儒家的复兴不仅是其自身思想观念的重新整合,同时也是社会大环境选择的结果。西汉翦除王国割据,实现了国家统一,经过七十余年的休养生息,社会环境繁荣向好;汉武帝在北击匈奴,西凿西域等一系列维护国家统一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西汉皇室急需要一种统治思想来巩固现有成果,以尊崇皇权、维护统一为主要思想内容的“公羊学”正好满足了这一时代需要,登上了历史舞台。
“公羊学”是一门基于研究《春秋》和《公羊学》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学说,也称“春秋公羊学”,诞生于春秋战国时期,黄开国认为“《春秋公羊传》是战国时期沈子、公羊子解释《春秋》而不断发展演进而来”[8];任蜜林先生认为《公羊传》成书于战国末期;《公羊传》借助于对《春秋》解释,考据和义理再造及发明,明确提出了以“文王为正”的大一统政治观,面对汉初大一统局面的形成,董仲舒不失时机地放弃了传统公羊学所倡导的“实与,而文不与”,并在政事中努力践行之[9]。从而打破了战国以来所坚守的“文王之正”,以“道统”精神代之,并与君主专制所代表的“政统”紧密结合。董仲舒坚持以“孔子之学”为核心,通过对孔子思想和《春秋》精义的深入阐释,将“公羊学”与其他诸子的学说思想相融合,建立了符合时代需要的新儒学体系。在秦汉政权交替之际,其主张“《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目的是为大一统王朝的建立提供公羊学基础上的理论依据。董仲舒杂糅了各家关于“尊君”的各种主张,提出“君人者,国之本也。夫为国,其化莫大于崇本,崇本则君化若神,不崇本则君无以兼人”;在“君”与“民”的关系上提出“君者,民之心也;民者,君之体也;心之所好,体必安之,君之所好,民必从之”[10]的观点,即君主是百姓的主心骨,君主的喜好必定会得到百姓的拥护。董仲舒引用了法家的观点“有功则君任其贤,有过则臣任其罪”,主张“君不名恶,臣不名善,善皆归于君,恶皆归于臣”的观点。对道家“无为”思想的考量,董仲舒提出了“君无为而臣有为”的主张,并援引阴阳学说对君臣分工进行源头性探讨。对于名家,董仲舒对其“控名责实,参伍不失”的观点加以改造,提出“治天下之端,在审辨大。辨大之端,在深察名号”的主张,认为“事各顺于名,名各顺于天,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对于阴阳家思想,董仲舒更是不遗余力地加以研究,在其代表作《春秋繁露》中存在大量关于“阴阳”“五行”的篇目,如“阴阳终始”“阴阳位”“五行倒施”等内容[11]。《汉书·五行志》亦载“董仲舒治《春秋公羊》,始推阴阳,为儒者宗”。可见,“推阴阳”是董仲舒“为儒者宗”的重要内容。
董仲舒大一统思想的另一重要贡献即是对“天道”的阐释。董仲舒对天道的阐释的最终目的是要将“天”与“人”统一起来,建立天人相统、天人感应的有机统一整体,即要建立一种基于“天道”的人间秩序,使人世间的一切准则以之为依托,并和谐共生,人与天可以双相沟通、相互依存。董仲舒进一步指出:“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天道以“仁、义、礼、乐”为基本内容,皇权可以改变人间的制度模型却无法撼动天道。“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将以救溢扶衰,所遭之变然也”,因为“道之大原出于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即道是天的衍生品,承载着天的治乱兴衰表征,具有永恒的时空性[12]。在《天人三策》中,汉武帝试图对永恒的天道进行探究,以此获取对天下大治的思想依据,但他不明白天道是抽象笼统的,天道一旦落实到治国理政层面上便会成为“实践之道”。董仲舒进一步将“实践之道”与上古三王(尧、舜、禹)的治乱之道进行对比,指出上古三王之道是符合天道的,但实行了各自不同的“实践之道”,但这个“实践之道”是由天道导出的。董仲舒认为“忠”“敬”“文”三者融合构成天道,后世君主要严格遵循此天道而不可逾越,而三王在其各自的历史阶段无法对上述三者形成全面系统的践行,只能践行其中的某一部分,这就无法与天道相契合,是其无法循环往复的运行。因此,三王之道即是对“忠”“敬”“文”三者的分别对照,共同构成了一个圆满无缺的循环天道系统[13]。由此可见,实践之道是天道的表现形式,天道是实践之道的根本遵循。
(二)“大一统”思想的合法性来源——“天人之际”
董仲舒思想体系的突出表征是其贵“元”思想,在其代表作《春秋繁露》中指出:“谓之一元者,大始也。知元年治者,大人之所重,小人之所轻也。”“元者为万物之本,而人之元在焉。安在乎?乃在乎天地之前。”[14]167-168董仲舒认为“元”是万物的肇始,是万物衍生的本源之初。董仲舒也强调“人之元”与“乃在乎天地之前”,提出人之元是产生于人心理层面上的,而不是客观上的时间先后次序。“元”如地基一样建立以后,其他上层建筑如政治、经济、文化也随之建立起来,形成以“元”为核心的同心圆结构的精神伦理世界。董仲舒亦把“元”比作政治生活中的国君,认为“君人者,国之元,发言动作,万物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端也。失之豪厘,驷不及追。故为人君者,谨本详始,敬小慎微。”国君如果在自己的施政过程中产生很小的失误,则会投射到日常的政治和伦理世界中,引发巨大的灾难,因此国君在日常的施政过程中应该谨小慎微、兢兢业业,杜绝任何微小的失误现象发生。
在“元”与“天”的辩证关系上,董仲舒认为“元”是万事万物产生的本源,同时也是“天”产生的根本,但人无法直接与“元”发生关系,也不能与“天”一同违背“元”。故君主在实现其为政抱负的过程中,只能以“天”作为其参照,承继天道来达到顺天化人的政治目的,而不可能与“元”直接发生关系。这也是贯彻“天意”的具体表现,故而“元”完成其使命后就处于“虚位”,而“天”对人及万事万物才具有主宰作用[15]。
“天”作为人及万物的主宰,在人世间的各个方面皆发挥着重要作用,如人的躯体及性情便可以天作为参照,董仲舒认为“人有三百六十节,偶天之数也;形体骨肉,偶地之厚也。上有耳目聪明,日月之象也;体有空窍理脉,川谷之象也;心有哀乐喜怒,神气之类也。观人之体,一何高物之甚,而类于天也。物旁折取天之阴阳以生活耳,而人乃烂然有其文理。是故凡物之形,莫不伏从旁折天地而行,人独题直立端尚,正正当之。是故所取天地少者,旁折之;所取地天多者,正当之。此见人之绝于物而参天地。是故人之身,首而圆,象天容也;发,象星辰也;耳目戾戾,象日月也;鼻口呼吸,象风气也;胸中达知,象神明也,腹胞实虚,象百物也。百物者最近地,故要以下,地也。天地之象,以要为带。颈以上者,精神尊严,明天类之状也;颈而下者,丰厚卑辱,土壤之比也。……天地之符,阴阳之副,常设于身,身犹天也,数与之相参,故命与之相连也。天以终岁之数,成人之身,故小节三百六十六,副日数也;大节十二分,副月数也;内有五藏,副五行数也;外有四肢,副四时数也;乍视乍暝,副昼夜也;乍刚乍柔,副冬夏也;乍哀乍乐,副阴阳也;心有计虑,副度数也;行有伦理,副天地也。此皆暗肤著身,与人俱生,比而偶之弇合。于其可数也,副数;不可数者,副类。皆当同而副天,一也。”[14]171-173即人的躯体和精神可与“天”一一对应,“天”和“人”在结构上是一体的。在“天人感应”方面,董仲舒提出“美事召美类,恶事召恶类”“帝王之将兴也,其美翔亦先见;其将亡也,妖孽亦先见”,即帝王将要兴起的时候,美好的事物就会出现;将要败亡的时候,诡异的事将会出现作为预告,借此提醒统治者为政要谨遵上天的旨意,不可做出有违天意的事,否则将会受到上天的惩罚。相较于当世,董仲舒更加对五帝三王时代的统治推崇备至,“帝三王之治天下,不敢有君民之心,什一而税,教以爱,使以忠,敬长老,亲亲而尊尊,不夺民时,使民不过岁三日,民家给人足,无怨望忿怒之患、强弱之难,无谗贼妒疾之人,民修德而美好,被发衔哺而游,不慕富贵,耻恶不犯,父不哭子,兄不哭弟,毒虫不螫,猛兽不搏,抵虫不触,故天为之下甘露,朱草生,醴泉出,风雨时,嘉禾兴,凤凰麒麟游于郊,囹圄空虚,画衣裳而民不犯,四夷传译而朝,民情至朴而不文,郊天祀地,秩山川,以时至封于泰山,禅于梁父,立明堂,宗祀先帝,以祖配天,天下诸侯各以其职来祭,贡土地所有,先以入宗庙,端冕盛服,而后见先,德恩之报,奉先之应也。”[14]179-181即三皇五帝统治时期,“下甘露,朱草生,醴泉出,风雨时,嘉禾兴,凤凰麒麟游于郊”,出现了一系列美好的事物,主张汉武帝应对此加以效法。此外,相较于祥瑞,董仲舒更加强调对灾异的表述,以此来鞭策统治者实行善政。
(三)“大一统”思想的政治合法性依据——“王者配天”
董仲舒对“王者”的阐释是以“天”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的,通过对“天”的无尚尊崇来打造一个上天的“代言人”——“王”的角色,董仲舒从哲学层面论证了“德侔天地者称皇帝,天佑而子之,号称天子”,即皇帝必须是具有无上道德的人担任,这样上天才会加以保佑。可见,皇帝和上天以“德”为纽带,形成了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董仲舒更加重视“正名”的作用,主张从双向层面来为封建皇权正名,首先是自上而下的“天”授皇权,其次则强调自下而上的德行的积累而获得皇权。即“德侔天地者称皇帝,天佑而子之,号称天子”,两方面同时运行方可称得上“天子”。而“王者,天之所予也,其所罚皆天之所夺也”,为避免上天的惩罚,君主在施政过程中要做到“王者配天”。董仲舒强调君主必须要“知天”,并要熟练运用“天道”规律来治理国家,即“为人主者,予夺生杀,各当其义,若四时;列官志吏,必以其能,若五行;好仁恶戾,任德远刑,若阴阳。此之谓能配天。”董仲舒也将天之四时来对君主的“四政”一一对应,即“天之道,春暖以生,夏暑以养,秋清以杀,冬寒以藏,暖暑清寒,异气而同功,皆天之所以成岁也。圣人副天之所行以为政,故以庆副暖而当春,以赏副暑而当夏,以罚副清而当秋,以刑副寒而当冬,庆赏罚刑,异事而同功,皆王者之所以成德也。庆赏罚刑与春夏秋冬,以类相应也,如合符,故曰王者配天,谓其道。天有四时,王有四政,若四时,通类也,天人所同有也。庆为春,赏为夏,罚为秋,刑为冬。庆赏罚刑之不可不具也,如春夏秋冬不可不备也;庆赏罚刑,当其处不可不发,若暖暑清寒,当其时不可不出也;庆赏罚刑各有正处,如春夏秋冬各有时也;四政者不可以相干也,犹四时不可相干也;四政者,不可以易处也,犹四时不可易处也。故庆赏罚刑有不行于其正处者,《春秋》讥也。”董仲舒对君主的日常行为规范也做出了要符合“天道”的规范,认为君主的喜怒哀乐都要取乎天道,以“天”为自己的行动规范,即“圣人视天而行。是故其禁而审好恶喜怒之处也,欲合诸天之非其时,不出暖清寒暑也;其告之以政令而化风之清微也,欲合诸天之颠倒其一而以成岁也;其羞浅末华虚而贵敦厚忠信也,欲合诸天之默然不言而功德积成也;其不阿党偏私而美泛爱兼利也,欲合诸天之所似成物者少而霜多露也。其内自省以是而外显,不可以不时,人主有喜怒,不可以不时。”[16]因此,君主在施政过程中要谨小慎微,杜绝因为一己之私造成国家和百姓的困顿,国君要时刻反省自己的为政得失,接受臣民的批评监督。
在官僚体系的运作方面,董仲舒提出“官制象天”主张,认为“三起而成,四转而终”是天道。在官制设置上要严格遵守“天之大经”,并在《春秋繁露》中对官职的设置进行了详细的记述:“天子分左右五等,三百六十三人,法天一岁之数。五时色之象也。通佐十上卿与下卿而二百二十人,天庭之象也,倍诸侯之数也。诸侯之外佐四等,百二十人,法四时六甲之数也。通佐五,与下而六十人, 法日辰之数也。佐之必三三而相复,何?曰:时三月而成大,辰三而成象。诸侯之爵或五何?法天地之数也。五官亦然。”将官职的设置与一年的三百六十日相对应,还取象于五色,即春之青,夏之赤,秋之白,冬之黑,中之黄。将官职的设置与四时一一对应,以期为汉朝统治从“天道”层面提供法理依据[14]185-187。
在“天”“君”“民”的关系上,董仲舒依据春秋公羊学,提出要“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的主张,“天”是董仲舒政治思想的背景依据和出发点,“君”和“民”则是现实政治的关注点和落脚点。董仲舒借助三代对“天”人格化的思想,杂糅道家、阴阳、五行思想将封建皇权视为上天的授予,即“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还强调君主的重要性,“君人者,国之元,发言动作,万物之枢机……君人者,国之本也者,夫为国,其化莫大于崇本。”在董仲舒看来,君主是国家的“元”“本”,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是上天的化身,君主既是世间权力的拥有者,亦是道德教化的楷模。董仲舒从对《春秋》的研究提出了加强中央集权的必要性,提出“《春秋》之大一统,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认为“大一统”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必然选择。面对武帝时期王国割据的局面,提出了要“强干弱枝,大本小末”的应对措施,提出“立义以明尊卑之分,强干弱枝以明小大之职”,主张以构建以“义”为核心的尊卑等级秩序,打击地方诸侯势力以加强中央集权。在董仲舒“伸君”的思想之外,从来也没有放弃“保民”的思想,这与儒家一贯主张的“仁”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提出“天子命无常,唯命是德庆”,即天子的主宰地位是不断变化的,唯有“有德”的天子才会得到上天的庇佑;董仲舒借此来表达儒家的仁政理念,主张君主要为政以德,注重人心的向背,不断矫正自己的施政政策。在“君”“民”关系上董仲舒还创造性地提出“君者,民之心也,民者,君之体也”,即君主是民众的心脏,民众是君主的躯体,君主要在政治和思想上对民众起到引领作用,而作为回报,民众要对君主予以全心全意的支持和拥护,亦即“心之所好,体必安之;君之所好,民必从之。”为了进一步规制皇权专制对民众带来侵害,董仲舒还从灾异福祸角度对君主加以限制“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17]君主要时时刻刻为政以德,安乐百姓,否则要受到上天的惩罚,通过“天人感应”来对人世间的君主进行规制引导。这集中体现了儒家知识分子对皇权专制统治下的太平盛世的美好憧憬,但在强势的汉武帝面前,这一愿景的实现不得不大打折扣。
(四)“大一统”思想的哲学合法性依据——“始终转移”
“五德终始”之说来源于战国末期齐国阴阳家邹衍的学说,他根据自然界中物质之所以存在的五种基本元素金、木、水、火、土的各自特性,赋予了各个朝代各具特色的“德”的相生相克的动态演进规律,总结了自黄帝以来各个朝代的历史演进规律:“凡帝王者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螾大蝼。黄帝曰:‘土气胜。’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及禹之时,天先见草木,秋冬不杀。禹曰:‘木气胜。’木气胜,故其色尚青,其事则木。及汤之时,天先见金刃生于水。汤曰:‘金气胜。’金气胜,故其色尚白,其事则金。及文王之时,天先见火赤,乌衔丹书,集于周社。文王曰:‘火气胜。’火气胜,故其色尚赤,其事则火。”由黄帝到汉朝的建德次序依次为:黄帝—土德,尚黄;夏—木德,尚青;商—金德,尚白;周—火德,尚赤;秦—水德,尚黑。自汉高祖起,一直对建德问题迟疑不决,直到汉武帝时才确定下来“太初元年…….夏五月,正历,以正月为岁首。色尚黄,数用五,定官名,协音律。”由此确定汉初为土德,尚黄,以夏五月为一年的开端。与之相对应的董仲舒提出了“三统”说,即“黑统”“白统”和“赤统”,其“统”意为“统领”“统帅”之意。“黑统”代表历法上的正月初一,太阳和月亮交汇于营室位置,北斗星的斗柄在“寅”位,此时万物开始萌芽生长,一切事物开始孕育发端,此时的代表颜色为黑色,所有为政措施要以黑色为尊,同时也要亲近赤色,代表天子开始在天亮之前要接受百官的朝拜;“白统”是指农历十二月初一,此时太阳和月亮相汇于虚宿,北斗星的斗柄在“丑”位,此时万物开始褪去桎梏,初步生长,此时的代表颜色为白色,但要与黑色相亲近,代表天子要在清晨接受百官的觐见;“赤统”在历法上是指农历十一月初一,此时太阳与月亮相交于牵牛之位,北斗星的斗柄位于“子”位,此时万物开始萌芽,此时的代表颜色为赤色,但要与白色相亲近,代表天子在夜半时分要接受百官的朝见。董仲舒的“三统”说分别代表了不同“岁首”时间,在每个王朝体现了不同的运行基调,与邹衍的“五德终始”说遥相呼应,组成了两种朝代更迭的哲学架构,为后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哲学命题(1)参见鲍有为《董仲舒与汉代灾异理论的建构》,载于《衡水学院学报》2017年第6期。。
此外,董仲舒还把时间与“大一统”紧密结合起来,创造性地提出了“王正月”的哲学命题,“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体现了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公羊学家对周文王的推崇,提醒统治者在治理国家时要仿效周文王,努力实现政权的统一安定。然而,因春秋战国时期周王室的式微,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公羊学家所提倡的“王正月”“欲天下之一乎周”已不可能实现。至汉兴,董仲舒提出了以“王正月”来“改正朔”以解决此矛盾,只有“改正朔”才能带来新的开始,董仲舒接着提出要“先言王后言正月”。只有先实行王道,有了“王”的实际之后才能具有“王”的名,接下来才能改正朔、制礼乐。董仲舒接下来对汉兴70年但仍未实现“善治”做了反思,提出了“继乱世者世道变”的观点,指出新王朝往往是在旧王朝的废墟之上建立起来的,如果一味坚持旧王朝的各项制度而不加以变更,其结果必然会重蹈覆辙,因此要对前朝的各项制度进行“更化”,汉朝之所以未达到“善治”就是因为没有对自身制度进行“更化”,汉朝如果想巩固自身的正统地位,则要“退而更化,更化则可善治”。假如一个王朝不实行“善治”,不能做到“继乱世者其道变”,董仲舒主张借以“改制”之名实行类似于“汤武革命”的模式取代他[18]。
(五)“大一统”思想理论的实践模式——“德润四海”
《春秋》的思想精髓历来以“尊君”为核心,主张“王者无外”的“大一统”观,面对汉兴70年,府库充盈、物阜民丰的社会环境,公羊学家们急需提出一种“大一统”理论来为新兴的封建统治阶级张目,由此,董仲舒提出了“夷夏一家”的大一统理念,主张对尊重和仰慕华夏文明的周边民族要加以拉拢和奖赏,将其纳入“华夏”的文敏范畴,对不愿归化的周边民族也要以“仁爱”之礼对待[19]。这一观点符合汉武帝主张以礼仪教化来“德润四海”的政治观点,因而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同时也将中华优秀的礼仪文明声名远播,对后世中华文化圈的形成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董仲舒的“夷夏”观在汉武帝经营西南夷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孔子在《春秋》中认为随着历史的不断发展,中华文明的礼仪教化不断远播熏陶,夷狄地区的文明程度也会随之提高,他创造性地提出了一条夷夏的区分标准,即假如夷狄也可以像中原人一样处事遵循礼义,则可视之为君子。可见,在孔子的“夷夏观”里已消弭了地域和人种带来的种族差异。及至汉武之世,北击匈奴,南并百越,在强势的君权面前,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春秋公羊学家不得不顺应历史潮流,提出了一些符合时代需要的新理论:“洞察王号之大意,其中有五科:皇科、方科、匡科、黄科、往科。合此五科,以一言谓之王……四方不能往,则不全于王。”[14]190-192把四方归顺作为称王的必要条件,主张“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四海之内闻盛德而皆徕臣……而王道终矣。”[14]197-199将施行王道与四海与君主正心联系起来,体现了儒家内圣外王的“大一统”思想,在现实角度也反映了董仲舒对夷夏之辨中夷狄亦可教化的深切认同。
对“西南夷”的发现肇始于唐蒙在南粤对“枸酱”的发现。公元前136年,唐蒙上书武帝欲以西南夷兵力制服南粤,得到武帝批准后,遂开通了通往夜郎的道路。在武帝经略西南夷的过程中深刻体现了“德润四海”和大一统治理思想。董仲舒在武帝打通西南夷的道路过程中,提醒武帝“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内莫不率服,广览兼听…….施于方外。夜郎,康居,殊方万里,说德归谊,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于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20]武帝在开拓疆土的过程中要善待百姓,使之心悦诚服。后来,武帝将夜郎和其周边的小国合并成犍为郡纳入了西汉王朝版图,并征调巴蜀地区的士兵修筑了通往牂牁江的道路,在这个过程中,唐蒙擅自征调郡兵进行水路补给,又不合时宜地处死了不听从其调遣的首领,引起了巴蜀地区的骚乱。汉武帝闻讯后派遣司马相如进行安抚,并作《喻巴蜀檄》,表明了通西南夷是为了“存抚天下,辑安中国”,并对唐蒙进行了严厉斥责。后来由于朝廷对西南夷的经营花费甚巨,从蜀郡到中央均提出了要罢西南夷的论调:“罢三郡之士,通夜郎之途,三年于兹,而功不竞,士卒劳倦,万民不赡;今又接之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业。”“弘为御史大夫,是时通西南夷,东置沧海,北筑朔方之郡。弘数谏,以为罢敝中国以奉无用之地,愿罢之。”[21]认为西南夷为“外化之地”,对中央王朝来说存之“无用”。司马相如由是反驳“必若所云,则蜀不变服而巴不化俗也。”接下来西南夷的数个小国因为仰慕中华文化请求内附,主动向西汉王朝请求置吏、称臣,这一系列事迹表明董仲舒所提出的“以礼、义辨别夷夏,夷可为夏”的观点已为大家接受。为了使西南夷地区更好地融入内地,西汉政府推行了“移民”和“遣官”为主要内容的“大一统”政策,这些移民不仅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方式,同时也把中原地区的礼教文明带入了少数民族地区,不仅有利于加强民族融合,同时对加强华夏“大一统”的文化认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所派遣的官吏在当地也发挥了“民之帅师,所使承流而宣化也”的作用,从而推动了儒家提倡的“大一统”国家观的实现。
四、董仲舒“大一统”思想的时代价值
(一)有利于加强民族认同感,对提升文化自信具有重大意义
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是对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深入发掘和时代展现,是为维护西汉王朝的大一统服务,有利于促进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其中的“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华夷勿分”等思想至今依然闪耀着时代的光辉,中华文明之所以生生不息延续至今,就是靠着儒家思想所提倡的“大一统”思想才得以历久弥新,不断进步[22]。因此,今天我们更应该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不断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推动中华文明走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的康庄大道。
(二)有利于促进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不断提升民族凝聚力和自豪感
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突破了狭隘的民族观,将华夏大一统思想贯穿其中,兼收并蓄、去粗取精,使中华文明成为包罗各种民族精神的百花园,使各民族的文化精髓都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和发扬,不断提升中华文明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大一统”思想始终贯穿于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各个时期,在不同时期均发挥着凝聚人心、共御外辱的作用,不断推进中华文明发展进步,与此同时“定于一”的思想也逐渐深入到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液里,成为中华民族始终昂扬向上、自强不息的文明底色。
(三)有利于不断推动中华文明向前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大一统”思想是中华民族有史以来统一时间远大于分裂时间的文化底色,是中华民族不断发展进步的思想基石,是我国保持团结统一的重要保证。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要始终坚持“大共同体”思想理念,不断从中汲取维护祖国团结统一的时代价值,坚持求同存异观点,尊重各民族的民族个性,努力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3],不断丰富和发展多民族共同发展的中华文明百花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