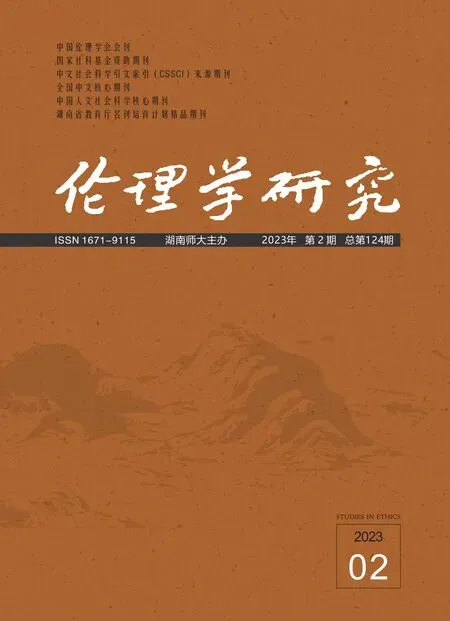墨家伦理学在西方百年译介和接受行旅
刘 松,夏登山
我国伦理学历史悠久,先秦时期即已发达,“儒墨道法,众家并兴”[1](6)。先秦诸子中,墨家建构了一套以兼爱为核心,非攻、节用、节葬、非乐、天志、明鬼为支点的伦理体系。有别于儒家重仁义轻私利、爱有等差的伦理观,墨家提出了“兼相爱、交相利”主张,开启了中国伦理学史上兼爱与泛爱、义利之辩的经典问题域。
自1858 年墨家学说经传教士介绍到西方,其伦理学说备受关注,在不同历史时期被阐释为宗教想象、功利主义、后果主义。墨家伦理学说在西方百年译介和接受之旅深刻揭示出西方不同历史时期对我国古代伦理学说的接受变异和时代性症候,从整体上昭示出西方对中国古代哲学认知方式的嬗变,为重新审视中国古代伦理学的世界意义和当代价值提供了重要线索。
一、宗教想象与借墨攻儒:19 世纪新教传教士对墨家“兼爱”和“节葬”的误读与挪用
1858 年英国传教士艾约瑟(Joseph Edkins)最早将《墨子》介绍到西方,并注意到墨家核心伦理主张兼爱十分契合19 世纪英国功利主义哲学。不过,传教士对墨家伦理学说并没有表现出多大兴趣,他们最关心的是如何借助墨家学说来阐发基督教教义以便更好地在华传播基督教。在墨家诸多学说中,其伦理学说“兼爱”十分契合基督教神学观“博爱”,因此最受瞩目。
艾约瑟将兼爱译为“the doctrine of equal and universal love”(平等与博爱学说),强调墨家兼爱与基督教博爱本质上都是一种泛爱,具有可通约性。他还注意到兼爱提出的时间比基督教诞生还要早五个世纪。他认为这一重要发现表明类似基督教的泛爱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存在,而且儒墨两家在战国时期并称为两大显学,说明泛爱在中国并不缺乏群众基础。站在传教立场,艾约瑟还认为兼爱虽在形式上契合博爱,但存在天然缺陷,无法完成对中国人精神救赎的使命,因为儒家早就精心设计了一套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等级森严的宗法体制,相比于提倡不分等级亲疏、无差别的兼爱,无疑更受统治者欢迎,而基督教博爱则建立在教徒对上帝由衷的信仰和精神上的道德崇敬之上,不仅不会触及统治阶层利益,也更容易获得普罗大众支持[2](165-166)。
艾约瑟在西方历史上第一次论及儒墨耶三者关系,很快就引起了其他传教士对墨家学说的兴趣,其中就包括当时正在翻译儒家典籍的著名汉学家理雅各(James Legge)。为了让传教士对墨家兼爱学说有一个更为全面的了解,1861 年,他在其《孟子》译本中罕见完整翻译了墨家《兼爱》,这是其首次也是唯一一次在儒家经典中介绍其他学派的作品。理雅各进一步对儒墨耶三家伦理观进行了比较。在他看来,儒墨两家都只专注本国(指当时的诸侯国——笔者注)事务,无论是儒家仁爱还是墨家兼爱,他们关爱的对象仅仅是本国国民,不包括其他国家,尤其是敌对国。博爱则是一种跨越地域、超越种族和仇恨、普世无私的爱。因此,基督教具有独一无二的优越性,正好能弥补儒墨之不足。站在传教士立场,他一厢情愿地认定古老中国只有接受基督教洗礼才能迎来新生[3](100-102)。
传教士不仅热衷于在墨家伦理学说中掺入基督教元素,还将其用于批判儒家,因为19 世纪正是儒耶关系最为紧张之际①19 世纪儒家与基督教的关系,可参见刘松:《理雅各〈墨子〉译介成因钩沉》,《中国翻译》2020 年第4 期。,墨家伦理学说便成了传教士批判儒家的工具。传教士对儒家的批判从孟子将兼爱斥为“无父无母,是禽兽也”着手。艾约瑟指出,儒家后学不遗余力攻讦墨家兼爱主要因为兼爱与儒家孝道相抵牾。对儒家而言,对他人之爱无论如何不应超出对父母之爱,但兼爱却是一种不分辈分和阶层的泛爱,是对儒家精心建构的伦理纲常的根本性颠覆。在艾约瑟看来,孟子对墨子的指摘不仅有失公允而且明显有失风度,尽管墨子鲜明提出了“非儒”口号,但墨子及其后学从未对儒家孝道思想提出过质疑,即便墨子反对儒家丧葬之礼并提出节葬之说,但《尚贤》《尚同》等篇章依然反复强调尽忠尽孝是人之义务。艾约瑟认为,墨家被儒家强烈批判的遭遇反倒十分类似基督教因反对儒家祭孔祭祖所遭受的排挤。在他看来,墨家学说可以为新教批判儒家提供新的理论资源和方法论指导[2](168)。
基督教作为一种一神论宗教,只允许教徒信奉耶稣,与儒家在祭孔祭祖问题上一直存在尖锐矛盾。明清之际耶稣会士就指责祭孔祭祖是封建迷信和偶像崇拜,应改信唯一真神耶稣。后来这一问题引发了罗马教廷和与康熙帝的激烈争执,最终这一宗教议题上升到了“中西礼仪之争”,导致康熙帝颁布禁教令。19 世纪新教入华后尽管凭借《天津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获得了传教权,但始终没能找到禁止祭孔祭祖风俗的理据,只能多次将这一议题搁置。后来,荷兰传教士高延(de Groot)发现墨家“节葬”伦理主张可作为批判儒家祭孔祭祖的新证据。1894 年,他在《中国宗教体制》一书中完整翻译了《节葬》,借助《节葬》中对西周丧葬仪式奢靡之风的细致描写来批判儒家丧葬礼仪。墨子指责儒家丧葬礼仪过于铺张浪费,“三年之丧”更是导致劳动力锐减,破坏社会生产。高延认为其当时的中国与墨子所处战国时期一样,战争肆虐、国力羸弱、民生凋敝,中国人应彻底摒弃祭孔祭祖陋习,减少人力和财力的无谓消耗。他还呼吁中国有识之士意识到,自鸦片战争以降,象征基督文明的西方与以儒家为国本的中国交战的结果表明,中国人无法从孔子的教义中找到救亡图存之道。而且,祭孔祭祖本身就暴露出儒家极其虚伪的一面:一面将自己树立成“子不语怪力乱神”的无神论者形象,另一面却为死人操办隆重丧礼,祭拜孔子和祖先。高延认为祭孔祭祖本质上就是封建迷信和偶像崇拜,是野蛮文明的象征[4](674-675)。高延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礼节存在不少误读,其借墨批儒并反对祭孔祭祖,显然是为传播基督教信仰开辟空间。
艾约瑟、理雅各、高延等人将墨家伦理学与基督教教义融会贯通的做法引起了越来越多传教士对墨家学说的兴趣。他们热衷于援墨释耶,将《墨子》想象成一部记载了基督教教义的宗教典籍,出现了《墨翟与基督教》及《海外基督教思想研究:中国哲学家墨翟简介》等一大批专门探讨墨耶关系的著作。传教士对墨家伦理学的阐释带来了双重影响:从正面看,架构了基督教与墨家的桥梁,短时间内使得西方对墨家伦理学的关注度急剧上升;从负面看,墨学伦理学与基督教神学观存在本质区别,传教士对墨家伦理学说的误读与挪用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墨家伦理学的哲学意蕴。
二、从宗教想象到功利主义:20 世纪初西方对墨家伦理学的阐释转型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整个欧洲笼罩在战争阴霾中,主张兼爱非攻的墨家伦理学受到了西方学界的极大关注。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Toynbee)极为推崇墨家伦理观,指出“把普遍的爱作为义务的墨子学说,对现代世界来说,更是恰当的主张……我想只有普遍的爱,才是人类拯救自己的唯一希望”[5](410-413)。汤因比的推介助推了墨子思想在西方的传播。随着对墨家伦理学的进一步了解,西方汉学界逐渐摈弃传教士将墨家学说作为解释基督教教义的工具论做法,而是将其视作西方感到亲切的功利主义哲学。
1914 年,游学西方的日本学者铃木大拙(Daisetsu Suzuki)《中国早期哲学简史》一书最早对墨家伦理学与功利主义的关系进行了剖析。该书第三章专门讨论先秦伦理学。铃木指出,中国人把伦理道德问题作为最值得认真思考的哲学命题,在伦理学领域西方人最熟悉的是儒道两家,但伦理议题并非为儒道两家垄断,先秦时期另一位著名作家墨子亦涉足这一领域。墨家一切学说都是为了达到“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非常类似西方功利主义。铃木分析认为,在儒墨之争中,孟子和荀子等儒家后学正好抓住了墨家功利主义思想的漏洞对其猛烈攻击才导致墨家溃败,使其逐渐淡出中国哲学史视野。铃木详细指出了墨家的漏洞:(1)不能将伦理立场坚持到底。墨子谴责纳妾,因纳妾导致单身男性数量增长,人口繁衍放缓,长此以往不利社会生产。可见,墨子反对纳妾并非出于伦理立场,而是基于经济考量,反映出墨子重功利轻伦理的态度。倘若纳妾有利于社会,墨子或许不会反对,甚至会支持。(2)伦理思想上有明显矛盾之处。在看待丧葬礼仪方面,墨子反对因缅怀逝者就为其操办隆重丧葬礼仪,浪费财富,却又提出“天志”“明鬼”,告诫人们要尊天侍鬼,二者明显相互矛盾。铃木进一步指出,作为功利主义者的墨子目光过于狭隘,尤其注重短期功效,忽略了长期效用。音乐不能创造财富,墨子便反对音乐,他没有意识到音乐作为一种短暂休息方式,能够缓解劳动者长时间劳作的疲惫,反而有助于提高生产效率。铃木认为,墨子往往只考虑行为带来的实际的、短期的功效,是一个“彻底的功利主义者”[6](92-93)。这意味着他不注重长远功效。
《中国早期哲学简史》作为西方最早的中国哲学史著作在欧美产生了深远影响,铃木对墨家伦理学的功利主义阐发推动了西方对墨家伦理学由神学阐释向哲学阐释的接受转型,越来越多西方学者开始将墨家视为功利主义者。譬如,1915 年和1917 年两部先后获得西方汉学界最高奖项——儒莲奖的《宗教和伦理学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Religion and Ethics)和《中国百科全书》(The Encyclopaedia Sinica)都将墨子称作功利主义者。
当然,西方对墨家伦理学的接受转型也离不开中国学者的努力。1929 年,旅美留学生梅贻宝出版了西方首部《墨子》英译本,首次系统向西方介绍了墨家伦理学说。该译本是在梅贻宝博士论文《墨子:备受冷落的孔子对手》基础上修改而成,但他并没有沿用其博士论文标题而是将其命名为《墨子的伦理学和政治论著》,旨在更好地突出《墨子》一书的伦理意蕴。梅之译作付梓后便引起了西方汉学界对墨家伦理学说的浓厚兴趣,也大大提高了墨家哲学的地位。美国汉学家何乐益(Lewis Hodous)称赞“这部优秀译作使我们第一次认识到战国时期与儒家旗鼓相当的伟大哲学家墨子的思想……这部作品对那些想要了解中国伦理学史和哲学史的读者大有裨益”[7](584)。此后西方汉学界对《墨子》的译介和阐释不再囿于神学之维,开始将重点放在对墨家伦理学的探索上,1931 年就发表了两篇专门探讨墨子伦理学的论文:《墨翟与英国功利主义者》和《墨翟的伦理学和社会学说》。前者称:“两年前,梅贻宝博士出版了墨子伦理和政治著作的学术性英译本,在很大程度上方便了欧美读者对这位古老改革家的伦理学说进行评价,正是有了这个译本,我们对墨子哲学思想才有了如此多的解读。”[8](46)
《墨翟的伦理学和社会学说》一文则指出墨家是伦理学家和社会学家,而非有神论者。虽然《兼爱》《明鬼》《天志》等篇章确实能够反映出墨家宗教主张,但墨家从未有建立宗教的意图。墨家伦理学本质上与西方功利主义无异,均为“抽象效用论”(abstract theory of utility)。文章指出墨家功利主义主要缺陷在于其适用范围有限。墨家能解答为什么要建造房屋之类的问题,这类问题通常存在功利动机。倘若追问人们为何要活着,那么就无法再用功利主义来解答了。归根结底,人类生活中的诸多精神需求都无法用功利主义来解释[9](695)。
20 世纪以来,西方对墨家伦理学的接受呈现出从宗教想象到哲学对话的转型,中外学界普遍将墨家伦理学解读为功利主义。美国汉学家牟复礼(Frederick Mote)《中国思想之渊源》一书将墨家伦理学称作“religious utilitarianism”(宗教功利主义)[10](80)。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一书则认为墨家伦理学是“pure utilitarianism”(纯粹功利主义)[11](94)。将墨家伦理学阐发为功利主义刷新了西方人对功利主义的认知,使其意识到功利主义这一概念并非最早起源于19 世纪的英国,更不是西方所特有,而是发轫于中国先秦时期,有力驳斥了黑格尔等西方哲学家长期以来所谓“中国没有哲学”的谬论,提升了中国哲学在世界哲学史上的地位。
不过,由于这一时期仅有梅贻宝一部《墨子》节译本问世,西方对墨家伦理学的了解依然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难窥其全貌,对其义理的阐发也多借用西方哲学概念,有误读和过度阐释之嫌,而且绝大多数研究成果刊登在《教务杂志》《开庭》等宗教杂志上,传播范围和影响有限。
三、从功利主义到后果主义:20 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对墨家伦理学的重新建构
1958 年,美国政府颁布《国防教育法》(The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宣布将外语教育视为维护国家利益的发展战略,西方汉学重镇从欧洲转到美国,墨家伦理学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一些西方哲学家深刻认识到墨家伦理学有其自身独特性而不能完全与功利主义画等号。
1976 年,美国哲学家埃亨(Dennis Ahern)《墨子是不是功利主义者?》一文最早明确反对将墨子视为功利主义者。他将功利主义者分为“强式功利主义者”和“弱式功利主义者”。前者往往鼓吹道德义务论,认为判断行为是否合乎伦理的唯一标准仅仅看该行为能否实现最高的善,即为最多数人带来最大化效益。后者则声称效益最大化只是判断行为对错的标准之一,绝非唯一和最终标准。在埃亨看来,边沁(Jeremy Bentham)和穆勒(John Mill)等19 世纪英国功利主义哲学家便是“强式功利主义者”。要解答“墨子是不是功利主义者”就是要弄清楚墨子究竟是强式功利主义者还是弱式功利主义者,强式功利主义者用公式表达如下:
B1:“x”是一种正确的行为,有且仅当“x 带来效益”。
B2:“x”是一种错误的行为,有且仅当“x 不带来效益”。
埃亨指出,墨子之所以被称作功利主义者,研究者往往依据的是《墨子》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一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将其作为墨子判断言行是否合乎伦理的唯一标准,也从而将墨子看作强式功利主义者。在埃亨看来,这一结论过于武断。墨子在《天志》中构想了一个拥有至高无上权威、人格化的天,其意志凌驾于人类之上。可见,在墨家伦理学中,“天”是除“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外,判断人类言行的另一种伦理标准。墨家伦理计算公式除以上B1和B2以外,还应作以下补充:
B3:“x”是一种正确的行为,有且仅当“x 符合天意”。
B4:“x”是一种错误的行为,有且仅当“x 不符合天意”。
既然存在两套伦理标准,墨子便是弱式功利主义者,也就不能与边沁等强式功利主义者画等号[12](185-192)。而弱式功利主义者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不能算作真正的功利主义者。
埃亨一文发表后在欧美汉学界引起了轰动,开启了长达几十年之久的墨子是不是功利主义者的大讨论。1979 年,美国哲学家泰勒(Rodney Taylor)率先对埃亨作出回应。他认为,埃亨使西方汉学界深刻意识到讨论墨家伦理学不能仅仅局限于其伦理学中的只言片语,而是要将它的主张结合起来看,尤其要重视墨子的宗教世界观。他将墨子比喻成“精神分裂症患者”,一面似乎是有神论者,另一面则是功利主义者。这两张面孔并非完全割裂,彼此存在一定张力。这种张力表现在“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是墨家毕生追求,但为了实现这一点墨家试图借助宗教力量,这便能解释墨家一方面呼吁节葬短丧,却强调尊天侍鬼,而且还能够回答墨家为何回避鬼神存在的本体论问题。墨家没有解释鬼神为何存在、以怎样一种方式存在,仅仅只是不断宣扬鬼神带来的种种好处。可见,墨家根本不在乎鬼神是否真的存在,只要使人确信鬼神能造福于人。因此,墨家虽提倡节葬短丧,却不主张完全废除丧葬,也不反对人们表达对逝者的悲痛,意在使人们相信鬼神存在。泰勒指出,墨家忽略了一旦丧礼过简可能招致鬼神怨恨,最终降下灾祸,反而会使人类遭殃。其结论是,功利主义虽不是墨家伦理学的全部,但却是其终极目的。质言之,墨家不在乎手段,只看重最后结果[13](337-344)。
当然,并非所有欧美汉学家都认同埃亨的看法,美国哲学家沃伦坎普(Dirck Vorenkamp)就是其中之一。他对埃亨墨子不是功利主义者的结论提出异议。他认为仅凭《天志》“天欲义而恶不义”就断定天是伦理问题的最终权威,将人类一切行为诉诸天意明显有误。按照埃亨的说法,人类做什么完全由天决定,这有违人性也不切实际,因为很多人行事完全没有意识到在人类社会还有一个至高无上的天。按照《天志》说法,“天下有义则生,无义则死;有义则富,无义则贫;有义则治,无义则乱”,“治”比“乱”重要,因为“治”在本质上就是好的。既然天意就是“义”,而“义”又会带来“生”“富”“治”,那么天之所以存在就是要造福于人。可见,天的意志就是功利主义的表现,功利主义是墨子处理人、天、鬼神关系的唯一标准。据此,他总结出墨子功利主义标准和天意之间可能存在的多种对应关系:
(1)人应行义,因为这种行为使自己受益,亦遵循天意。此时,人行义既是遵循天意,又带有功利性。天意和功利主义都可以用来判断行为是否正确。此时,墨子不是功利主义者。这是埃亨的观点。
(2)人应行义,此乃天意,而天意就是使人得利。此时,人的一切行为顺从天意。顺从天意便成了人行事须遵循的规则,那么墨子是规则功利主义者。
(3)人应行义,因为这种行为将使自己受益。此时,人考虑的是该行为可能带来的好处,而不在乎这种行为是否顺从天意。此时墨子是行为功利主义者。
沃伦坎普透过对墨家伦理学中“义”和“利”这对极其重要关系的把握得出墨子是功利主义者的结论。在他看来,“天志”就是“义”。对墨子而言,“利”始终摆在第一位,“义”仅仅是实现“利”的途径。在墨子伦理体系中功利主义始终居于首位,天意终究只是墨子实现功利主义的手段罢了[14](433-441)。
实际上,埃亨和沃伦坎普的结论都站不住脚。埃亨将人的行为诉诸天意无视人的主观能动性,而且忽略了另一种可能:倘若天的旨意不符合甚至妨碍人的根本利益,那么人会不会去执行呢?其次,正如沃伦坎普所言,很多人在行事时完全遵照自己意愿,根本没有“天”的概念,其行为也就不可能被天意所支配。同样,沃伦坎普驳倒埃亨的证据亦不充分。他虽意识到“义”“利”关系是墨家伦理学说的核心,但将“利”置于“义”之上则是对墨家伦理学说的误解。墨家强调获利不能违背公平,故“义”和“利”并没有明显的主次关系。
埃亨一文发表后,欧美汉学界对墨家功利主义哲学展开了深入探索。尽管对墨子是不是功利主义者这一问题仍聚讼纷纭,但墨家伦理研究范式摆脱了以往以西释中的印象式点评,研究者开始意识到不能简单将墨家伦理学与功利主义画等号,而是采取和而不同的阐释方法,回归《墨子》文本本身,采取文本细读方式,重新解读墨家伦理学。有趣的是,后来这场讨论也吸引了中国本土学者的关注。2006 年,我国学者郝长墀在当初刊登埃亨论文的《中国哲学》杂志上,同样以“墨子是不是功利主义者?”为题重启讨论,再一次引发欧美汉学界热议。经过30 多年的激烈论争,西方学界基本已经否定了墨家伦理学是功利主义的说法,但未能进一步解答墨家伦理学究竟是什么的问题,最先尝试作出回答的是美国哲学家艾文贺(Philip Ivanhoe)和万百安(Bryan Norden)。
2005 年,艾文贺和万百安合著的《中国早期哲学中的美德伦理学和后果主义》一书把儒墨两家伦理学分别称作美德伦理学(virtue ethics)和后果主义(consequentialism)。他们认为,儒家热衷于道德说教,鼓励人人成为道德高尚之人,其本质是一种精英主义哲学。儒家伦理学另一特征是重义轻利。墨子则批评儒家谈义不言利,没有将伦理问题置于现实世界中考察,是一种空洞不切实际的伦理。墨家不仅谈义,而且将“兼相爱,交相利”视为最重要的伦理标准,其伦理体系不是为了实现某个人、某个家族、某个诸侯国的利益,而是给最大多数人带来最大化的利益。不过,艾文贺和万百安否认墨子是功利主义者。根据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一书对功利主义的定义,“功利原则就是对任何行为表达赞成或反对,都根据这件事的利益相关者的快乐增减趋势,也就是看这个行为是会给他们带来快乐还是痛苦……当每个人的快乐和幸福最大化时,社会实现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15](51)。可见,西方功利主义的计算便是快乐和痛苦的增减。艾文贺和万百安认为,倘若功利标准便是所有相关者主观上的幸福或快乐,显然墨家伦理学不是功利主义。站在功利主义者的角度,音乐是好的,因为它总是给人带来快乐和幸福。倘若墨子也是功利主义者,那么他就会喜欢音乐,实际上墨子极力反对音乐[16](56)。
应该说,艾文贺和万百安对墨家不是功利主义者的分析切中肯綮。我国学者贺麟先生很早就认识到了西方功利主义标准的缺陷并指出其与我国伦理学的差异,“功利主义的一个缺点,是利用计算苦乐、得失、利害的方式来估计人生。中国的儒家,从来就反对计算式或算账式的人生,认为这种生活是最无意义、最枯燥无味的生活。像孟子就是非功利主义的最显著的代表人物”[17](207)。实际上,不仅仅是儒家,墨家伦理标准亦不是西方功利主义那套所谓的快乐和痛苦增减。尽管墨子本人及其弟子多出身贫贱,但墨家从不贪图个人享乐,墨子止楚攻宋的故事和墨家死不旋踵的精神都反映出墨家为了实现《尚贤》中的“国家之富,人民之众,刑政之治”的奉献意识。
墨家与西方功利主义另一个不同之处则是在个人牺牲与集体效益关系看法上的分歧。功利主义者并不反对自我牺牲,但从不将其看作好的行为,正如穆勒所言,“一种牺牲如果没有增进或不会增进幸福总量,那么就是浪费。唯一赞成的自我牺牲,是为了他人幸福或有利于他人幸福而作出的牺牲”[18](42)。换言之,西方功利主义只关心牺牲是否能带来好的结果,而在墨家身上我们看到的则是“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还踵”(《淮南子·泰族训》)的敢于牺牲自我的大无畏精神。
为了进一步揭示墨家伦理学的本质,艾文贺和万百安认为墨家伦理学是后果主义,并将后果主义区分为“规则后果主义”(rule-consequentialism)和“行为后果主义”(act-consequentialism),而且进一步指出墨子是规则后果主义者。在他们看来,墨家提倡兼爱,试图建立一套明确的、能为人们广泛接受的行为伦理评价标准,即“三表法”,根据事物结果来判断行为好坏。例如,衣服的目的是什么?墨家给出的答案是“为了保护我们免受冬天的寒冷和夏天的炎热”。房子的用途是什么?“是为了保护我们免受冬天的风和冷、夏天的热和雨,并防止强盗小偷”。在任何情况下,无论是墨家的提问方式,还是他们给出的答案,都是基于一种后果主义的考虑:利用事物来获得好的结果,抑或事物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给人们带来好处。不过很明显,后果主义所理解的后果,其含义要远远大于传统功利主义所坚持的个人主观上的苦乐及多数人的效益。
艾文贺、万百安的观点得到了香港大学方克涛(Chris Fraser)的回应。方克涛在其2016 年出版的墨学研究专著《墨子哲学:最早的后果主义者》中更是将墨家称作世界上最早的后果主义者。他认为,墨家在《兼爱》中将世界混乱的根源归咎于人的自私及人与人的不相爱。伦理危机出现是整个社会层面的问题,不应归咎于个体。在应对伦理危机时,墨家不像儒家那样教导每个个体成为道德高尚之人,而是试图使上级阶层接受其学说,进而改变整个社会的运作方式,创造良好的社会秩序。墨家伦理学是共产主义式的,而非个人主义的,这与西方古典功利主义强调个人幸福截然相反[19](224)。
方克涛与艾文贺、万百安的分歧在于他认为墨家伦理学并不完全符合规则后果主义或行为后果主义。在他看来,墨家伦理学有时使用规则来评价或指导行为,如《墨子》中反复提及的圣王、仁者、君子的言行似乎就是一种能够约束人们行为的规则或典范。然而,规则并不是墨家伦理学体系最主要的评判标准,因为墨家没有把对一切事物的评估都转换为具体规则,也没有将重点放在制定规则上,有时墨家甚至在评价行为对错时并不诉诸任何规则。墨家伦理学是为了提供一系列可供人们效仿的行为模式,让人们自行选择,而不是制定一整套行为规则,约束人们应怎么做。他还指出,墨家伦理学也不完全符合行为后果主义。譬如,《墨经》中提到这样一种情况:当两种行为都带来不可避免的危害时,危害较小者便是正确的行为,但以行为后果主义来看,凡是产生危害的行为都是错误的[19](267-268)。
实际上,西方规范伦理学视域中的后果主义有两个备受争议的地方。其一,只看重行为是否能够带来好的结果,不关心过程和手段是否合乎伦理。行为合乎道德伦理,有且仅当该行为所产生的结果是最好的。其二,后果主义虽强调集体利益,但忽略了公平原则,即每个个体利益是否都得到了平等对待。英国哲学家肯尼(Anthony Kenny)在《牛津西方哲学简史》一书中就批评后果主义论者过于强调结果,在分配正义方面很少展开讨论,他们仅仅注意到了那些因社会体制不同而有所变化的供给形式[20](244)。我国学者贾凌昌亦批评后果主义要求在每一种情景中的伤害和利益必须以某种方式进行分配,然而这种分配方案由于没有考量人与人之间的差异隐含了具体的不正义[21](50)。墨家伦理学则恰恰弥补了后果主义的两大弊端。首先,墨子在《尚贤》中指出“不义不富,不义不贵”,明确反对通过不正当手段谋利,强调义是获取利的基本底线。当然,这种义利观可能受到了孔子影响。墨子早年“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淮南子·要略》),孔子在《论语·述而》中就有“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的说法。其次,墨子所追求的“利”是一种集体的利,而非私利,正如墨子所言“天下之利,欢”(《大取》),同时也是建立在公平公正基础上,而非满足个体的私欲,即“举公义,辟私欲”(《尚贤上》)。另外,墨子所提倡的兼爱也是一种不分贵贱、辈分、亲疏的平等的爱,“交相利”也强调公平基础上的互利互惠,而不是亏人自利。因此,方克涛将墨家伦理学称作是共产主义式的,既强调集体利益,又强调公平公正,不无道理。这种观点可以说与毛泽东在读《伦理学原理》时写的批注“墨子之兼爱系互助,并非弃吾重大之利益而供他人之小利,乃损己利人而果有利于人也”[22](222)不谋而合。由此观之,墨家伦理学实际上克服了后果主义要么忽略行为过程手段是否合乎伦理、要么忽略公平公正的弊病,这正是墨家伦理学的独特之处,也是其对世界伦理学作出的贡献。
20 世纪70 年代以来,西方汉学界围绕墨家伦理学说产生了激烈争议,墨家伦理学正是在西方汉学界众声喧哗的思想碰撞和论辩驳难中彰显出其独特价值的。墨家伦理学不仅先后出现在像Global Ethics(《世界伦理学》)、A Companion to Ethics(《伦理学之友》)等西方重要伦理学著作中,而且墨子在中国哲学史中的地位也不断提高。英国汉学家、先秦哲学史研究专家葛瑞汉(Angus Graham)指出:“用现代哲学眼光来审视墨子的哲学体系,墨家伦理学不仅仅是关于伦理的指导,更是通过一个批判和质疑价值观念和信仰的过程,同时也是通过寻求可靠证据来支持自己的观点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墨子而不是孔子,应当被称为中国第一位哲学家”[23](618)。艾文贺、万百安认为:“墨子是我们所知道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详细而连贯的世界观的人,这种世界观是对儒学的系统批判和替代。墨子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判断正误的通用算法,以公正地最大化利益为目标,用以取代孔子培养出来的伦理学家”[16](116)。方克涛则称墨家的伦理学说是最早的结果论,同时也有可能是最早的系统规范伦理理论,比边沁和穆勒的功利主义早了近2000 年。因此,墨子称得上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真正的哲学家,他系统提出了伦理、政治和认识论理论,并给出了清晰的、合乎逻辑的论据来证明他的观点[19](vii)。
余论
墨家伦理学跨越了一个多世纪的跨语际译介之旅,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三种迥然不同的历史面相:宗教想象、功利主义与后果主义。19 世纪新教传教士致力于对墨家伦理学说的神学化阐释,致使墨家伦理学说被严重误读,成为解释基督教教义的注脚。到了20 世纪上半叶,西方对墨家伦理学的阐发逐渐挣脱神学桎梏,开始将其与西方功利主义相比附。20 世纪下半叶以降,西方汉学界开始质疑墨子功利主义者的身份,围绕墨子是不是功利主义者爆发了两场持续几十年之久的激烈讨论,西方汉学界普遍意识到墨家伦理学不能与西方功利主义哲学画等号,一些学者倾向于将其解释为后果主义。
墨家伦理学在西方的跨语际旅行跨越了西方汉学发展的三个重要时期——传教士汉学时期、专业汉学时期和美国汉学时期,与此对应的是神学化阐释、以西释中阐释及和而不同阐释。这三种不同阐释范式深刻反映的是三个不同时期的时代症候,从整体上昭示了西方对墨家伦理学认知方式的嬗变以及中国古代哲学在西方文化话语场中话语力量和话语策略的变迁。在神学化阐释期,传教士们将中国儒道墨等古代哲学典籍想象成记载了基督教义的宗教文本,并将这种想象演变成一种集体狂欢,这也成为西方普通读者接受的重要参照物。在以西释中阐释期,一大批专业汉学家登上历史舞台,开始与传教士争夺话语空间和文化资本,试图重新解析中国哲学典籍的哲学价值,使其自身所包含的巨大阐释效能和理论资源得以释放,但由于在阐释过程中往往是借用西方哲学话语和概念,因而中国古代哲学的内在话语谱系也被置换、被稀释,话语功能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变异。这一时期西方学界普遍将墨家伦理学思想解释为功利主义哲学,其本质就是以西方哲学固有的理论范式和概念话语来图解中国哲学。这种做法非常类似佛教传入中国伊始所采取“格义”策略,“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为生解之例”(《高僧传·竺法雅传》),即借用中国传统哲学话语来阐释佛经中的微言大义。这种做法在两种异质文化接触之初的确能够有效减少文化间的抵牾,使受众更容易接受异域文化和外来思想。诚然,借用西方哲学概念、术语或理论来阐释中国哲学凸显了中西哲学的共通之处,但也遮蔽了中西哲学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的不同,中国哲学自身的独特的精神内涵、思维范式和价值取向就无法得到彰显,久而久之就会造成中国哲学在世界哲学话语场的“失语”。
到了和而不同阐释期,研究者们开始摈弃时代性历史短视和阐释偏见,试图将中国古代哲学的对话空间进一步打开,开始采取一种批判、吸收和超越立场,形成了立体化、多声共振的多元阐释格局,在众说纷纭的思想碰撞和论辩驳难中,重新审视中国古代哲学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意蕴。从这个意义上说,墨家伦理学在西方的译介和接受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中国古代哲学在西方接受传播的缩影。这一过程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西方如何解读中国哲学知识、如何创造标识性概念、如何传播中国哲学话语,而且对于我们重新审视中国古代哲学的世界意义和当代价值,深入挖掘中国古代哲学的思想理论体系和知识话语体系,凝练中国古代哲学独特的标识性概念和表达方式,构建融通中外的哲学话语体系提供了历史借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