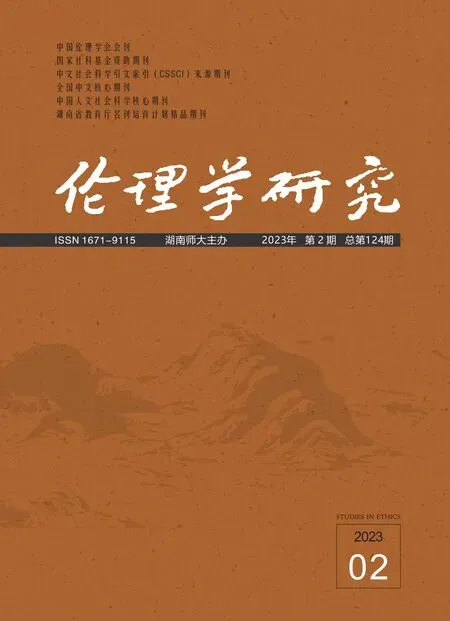从五伦向三纲五常演变的文明轨迹
唐代兴
1927 年10 月,陈寅恪为王国维投湖自尽作的挽词中写道:“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Eidos 者。”[1](12)1940 年5 月,贺麟在《战国策》第3 期上发表《五伦观念的新检讨》,指出“五伦观念之最基本意义为三纲说,五伦观念之最高最后的发展,也是三纲说。而且五伦观念在中国礼教中权威之大,影响之大,支配道德生活之普遍与深刻,亦以三纲说为最”[2](237)。贺麟以不同话语方式表达了与陈寅恪相同的观念:三纲五常实质性地定义了中国文化。但学界对此也存在异议,比如张岱年就指出,“三纲六纪之说不见于先秦儒家的典籍,乃是汉儒的观点”,并且,从文化发展观,“三纲否认了臣对于君、子对于父、妻对于夫的独立人格,加强了君权、父权、夫权,实为专制主义时代束缚人民思想的三大绳索”[3](33)。陈、贺二人对“三纲五常”的研判,属事实判断;张岱年对“三纲六纪”的研判,属价值判断。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有根本区别:前者要求尽可能去主观先见地客观陈述“事实本来是这样的”,后者主张可以从主观先见出发去突出“事实应该是这样的”。如果从“事实本来如何”观,秦以降的中国文化确实可用“三纲五常”来定义,因为它贯通文化思想的各个领域,成为表彰汉以来两千多年文明历史的核心范畴。由此,澄清血缘五伦如何向三纲演进并发明出“三纲五常”思想范式和规训体系所透露出来的中华文明的演变轨迹,有可能对20 世纪初以来有关“三纲五常”思想起源的浅表论争予以正本清源。
一、血缘五伦向宗法五伦演变
思想的产生,始终基于时代存在危机或生存困境而谋求解决之道的认知努力,始终呈现“过去、现在、未来”三维视野并敞开立足“现在”、从“过去”指向“未来”的历史进程。以此观之,“三纲五常”实是经历了“五伦”向“三纲”的历史性生成。
1.“伦理”的存在论释义
“三纲五常”,实际上是由“五常”衍生出“三纲”。理解此进路的认知起点,应该是“五伦”之“伦”,它是汉语“伦理”的最初表述。“伦理”中,其“伦”主要指一种结构,一种秩序;其“理”却指这种“结构”“秩序”何以可能如此的内在规定性。这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中何以将“理”字派给哲学却将“伦”字派给伦理学构成凝聚社会结构和建构人际秩序功能的根本原因。
伦理的社会结构与秩序功能通过“伦”字得到呈现。《说文》定义“伦,辈也”,意为“伦”的本义是辈分,辈分源于血缘。所以,血缘乃辈分的内在规定的本质定义,辈分构成血缘的外在规定。血缘和辈分,从内外两个维度既将人先天地安排在各自该居的关系位置上使之获得等级性存在,也规定了人与人界限分明的类聚关系:血缘之内是一类,血缘之外是另一类。由此,血缘、辈分、类聚此三者构成人间的完整人伦。
人伦,是一种人道,但却原发于自然,是自然使然。血缘、辈分、类聚均属于自然:血缘既是族种性质的,更是物种性质的,均不由人选择;辈分是天赋于人,当生命的种子在母体中播下,辈分由此产生,它不由人来选择;由血缘和辈分规定所形成的原初意义的类聚,既是自然的,也是天赋的,同样不具有自由选择的可能性。
人伦,更是一种结构关系,但同样是自然使然。从根本上讲,血缘体现自然生育法则,辈分和类聚蕴含大千世界中存在物如何存在的天理(“自然之理”的简便说法)。遵循“血缘”这一自然生育法则和“辈分”“类聚”这一存在天理向外拓展,就产生家族,形成民族,建立国家。亚里士多德《政治学》指出,个人不能单独存在和延续种类,男女因为生理需要才组成家庭,生育亦属生理的自然。生育的繁衍使家庭横向扩展成为村坊,村坊的横向联合产生城邦[4](5-6)。这一超越血缘和辈分的结构关系向社会结构关系的创建,既是对自然生育法则的遵循,也发挥了辈分和类聚的“自然之理”功能,这是“伦”与“理”字结成“伦理”的内在依据。
2.上古五伦的血缘主义性质定位与价值取向
明晰“伦”之语义及结构内涵,重新审视上古五伦,既呈现五种群化存在的结构性关系,也蕴含发生学意义的血缘主义取向。
浚咨文明,温恭允塞,玄德升闻,乃命以位。慎徽五典,五典克从。[5](125)帝曰:“契,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5](130)
这是五伦的最早记载。五典,指五种可普遍的且可作为标准、准则的东西;以五典为内容展开教化,就是五教;实施五教所形成的主体性成果,就是五品。理解“五教”和“五品”的前提,是理解“五典”之“典”字。“典”之甲骨形态、、,从册、从双手、从二,形“象双手捧册于基上之状”,意双手捧“献典册以祝告”。《说文》释曰:“典,大册也。”《尔雅·释言》释曰:“典,经也。”《尔雅·释诂上》释曰:“典,常也。”综上,“典”既有“标准”义,也有“常法”义。以此观之,五典,是指五种群居的行为标准或伦理准则,它构成规范、评价人的群化行为的常法。
五常即五典,谓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5](1182)
使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5](1862)
作为常法的五伦,其具体内容是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它构成“五常之教”。《左传》揭示此五常之教具普世性,即使“诸夏夷狄,皆从其教,是谓内平外成”[5](1862)。以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为基本内涵的五伦,属于家族(和家庭)血缘伦理,它构成前国家时代的群居行为规范,是部族内部和谐生存以及部族联盟之间共生共在必须遵循的常法。它“要求把部落的同一性相对化和建立一种抽象的同一性,这种抽象的同一性不再把个人的成员资格归结为共同的血缘关系,而是归结为对一个领土上受限制的组织的共同的从属关系”[6](23)。这是血缘主义五伦需要统治者组织教化而使之生成五品的原因。
3.血缘五伦向宗法五伦的过渡
构建上古社会结构的五伦表现出来的群居行为准则和边界约束规范,堪称是经历了氏族社会向部落社会再向部族社会进发[7](58-64)而形成的成熟伦理常法,它自具结构的完整性,并构成能够涵摄血缘性群居生活世界的方方面面。后来,“监于二代”的周,对其予以系统地礼制规范,建构了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的双向运作体系。以一生致力当世道德重建的孔子,在内涵上对血缘五伦予以充实或丰富。比如“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8](148),意在于揭示周代以“礼”为规范的血缘五伦,却在春秋晚期滑向了形式主义,孔子为此提出以仁来充实礼的补救措施,使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仁”化。客观地看,血缘五伦呈三重结构取向:一是上对下的父义、母慈;二是下对上的子孝;三是平辈的兄友。在这三维伦理向度中,最容易出问题的是子孝,因为父母之爱子女属本性使然,没有利害考量;儿女孝父母,却有可能淡化或丧失本性而以利害取舍之,由此使“子不孝”成为普遍现象。《论语》中许多讨论子孝的内容都是强调仁与孝的关系,突出仁对孝的作用,并揭示以仁为本的孝的实质不是“能养”,而是“父母,唯其疾之忧”[8](29)。
孔子基于当世的伦理状况而对血缘道德予以内涵的充实和丰富,没有突破五伦框架,也没有修改五伦结构。这表明五伦内容的修正及其结构框架的更改,只可能发生在孔子之后的战国时期。
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9](125)
孟子的“五伦”体现两个特征。一是突破了血缘伦理结构和框架,将其修改为政治、家庭、社会三维,即政治层面“君臣有义”,社会层面“朋友有信”和家庭层面“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二是从两个方面强调伦理的政治等序性:一方面,排列出伦理的“自然→社会→家庭”三级等序结构,强调先自然,次社会,后家庭。另一方面,排列出家庭等序结构:先血缘,后两性,突出血缘重于两性,两性依附于血缘,并且血缘之纵向坐标支配两性横向坐标。在血缘坐标上,先父子,后兄弟,因为有亲的父子象征血缘生殖的时间进程,长幼有序的兄弟象征血缘拓展的空间敞开维度。
孟子之前,五伦属血缘主义的私域道德。到了孟子这里,五伦成为公私论域混合的道德,它虽然以“父子”为首,但却突出君臣主导以统摄家庭和社会,所以孟子的五伦属于政治宗法主义的伦理常法,呈现伦理道德政治等序化和君权主义倾向。这一倾向在荀子那里得到了强化:
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三者偏亡焉,无安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10](349)
荀子的“三本”说体现自然主义和血缘主义。天、地、人三者,属自然存在之生育关系:人由天地所生,必然负载天地的本性,受纳天地的律令而存在。在“天、地、人”三本中,“人”之一本演绎出“祖、君、师”。这一思想出自与孔子同时代的左丘明:“民生于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师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长,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壹事之。”[11](166)它强调血缘主义生育、经验主义教化、君权主义统领与治理。荀子首先将“父”之一伦改造成“祖”,突出“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然后将“天”“地”纳入其中,构成“天、地、祖、师、君”五伦。
荀子的五伦结构中,天、地是自然伦理,祖是“追远”的血缘伦理,君、师是当世的政治伦理。整合观之,天、地、祖分别从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为君、师伦理提供背景和依据,这是因为荀子五伦要突出君、师,一是君对人间伦理的统领、规训与治理的作用,二是师在人间伦理生活中发挥教化作用。韩非子发展了前者,并为汉代“三纲”出笼奠定了更为坚实的基础:“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12](510)董仲舒发展了后者,为“三纲五常”提供了形而上学基础和调节、引导机制。
二、五伦催生三纲的思想源头
自20 世纪初始,“三纲五常”问题引发许多知名学者围绕它展开讨论,并形成两大倾向:一是其讨论大多停留于挖掘材料、引经据典、就事论事,缺乏结合思想发展和社会演变的互动敞开史视野;二是其讨论虽涉及广泛,但面对一些根本问题却难以深入。下面先概述其主要说法,然后简要分析这些说法的片面与局限之处。
1.有关“三纲”思想来源的各种说法概要
有关“三纲”思想渊源的众多说法可概括为五个方面。
一是“先秦儒家”说。其首倡者东汉马融将孔子“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中的“所因”注释为“三纲五常”。邢昺发挥马融之说为“此夫子答可知之事,言殷承夏后,因用夏礼,谓三纲五常不可变革,故因之也”[13](25-26)。将三纲的思想源头溯及孔子这种做法为后世者所悦纳,比如虞生沿马融、邢昺的思路,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中的“为”字训为连词“与”,由此译三纲为“君与臣为一纲,父与子为一纲,夫与妻为一纲”[14](27)。方朝晖亦承马融之说,并以孔子作《春秋》来证明孔子倡“三纲”说[15](48-49)。任继愈亦认为“董仲舒根据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纲常和仁义道德思想,提出了一整套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三纲五常说”[16](195)。
二是“法家”说。范子美于1929 年在《青年进步》(第122 期)发表署名“皕诲”的《“三纲”出于法家》一文明确指出,“三纲”起源于法家而非儒家。张岱年亦持类似看法:“《韩非子》书的《忠孝》篇……强调臣对君、子对父、妻对夫的片面义务,可以说是三纲观念的前驱。”[17](109)朱法贞亦持此观点,指出“‘三纲’源于韩非,而非孔子,此理明矣”[18](109)。孙景坛也明确指出“‘三纲’的发明权在韩非”[19](144)。牟钟鉴将此观念写入《中国儒学百科全书》“纲常”条目:“孔子、孟子未明言三纲。而《韩非子·忠孝》认为‘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的顺逆是天下治乱的关键,故称其为‘天下之常道’。这是三纲观念的萌芽。”[20](105)
三是“儒法合流”说。《中国儒学百科全书》“三纲”词条指出,“就思想渊源而言,董仲舒宣扬的三纲之说,来自先秦孟荀儒家和韩非法家”[20](469)。李宗桂亦认为“儒家代表人物荀子明确论述了君臣、父子、夫妇间的尊卑主从关系”[21](764-765)。
四是“汉儒”说。其说以景海峰为代表,他指出“‘三纲’的系统化应该是在汉代,是汉儒革故鼎新的产物”[22](47)。刘明武亦认为“‘三纲’是源于西汉的董仲舒,其最初是出自董仲舒《春秋繁露·基义》一文”[23](35)。
五是“多源头”论。李锦全认为“‘三纲’并非由哪一家或由谁发明,出现这种人际关系的社会现象是从父系氏族公社到宗族奴隶制国家这一社会进化过程中形成的”[24](5)。李存山认为“‘三纲’思想来源于黄老及法家,是秦汉大一统政治格局的需要”[25](29)。所以,“‘三纲’是汉儒为了巩固当时君主专制的大一统帝国,在吸收了儒、道、墨、法、阴阳等各家思想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新政治伦理体系”[26](125)。
2.五种“三纲”来源说法存在的问题
关于“三纲”思想始于何时的如上说法,存在着与客观史事不符或不完全相符的情况。
其一是“多源说”,忽视了思想史上任何一种思想萌生、孕育、诞生、发展,都具体地因时因势因地因人而展开的这一事实,这种抛开时势、环境和思想家本人返本开新而努力的说法,体现了一种缺乏独立思考的“和稀泥”论调。
其二是“汉儒论”,违背了思想发展史常识。在人类精神探索和思想发展史上,任何一种思想和学说的产生,都客观地存在源流和承传的问题,以此观之,“三纲”的产生也不能例外。
其三是“儒法合流说”,也存在三个方面的认知局限。一是这种说法截断了三纲思想与孟子的本来关联,人为斩断了五伦催生三纲的链条。二是对以荀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和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思想为何会相继地共育“三纲”思想的问题没有回答。三是对由儒法共育出来的“三纲”思想怎么可能最后由“儒家”命名并由儒家独揽的结果没有解释。
其四是“法家说”。这种说法如同“汉儒论”一样,违背了思想发展史常识,主观想象地割断了韩非子“三纲”思想形成的源流。从其思想形成的源头讲,孟、荀“五伦”中的“君臣”思想孕育了韩非子的“三纲”思想;从其思想展开的流向言,汉代的“三纲”思想是对韩非子的“三纲”思想的定型、发展、运用。
其五是“先秦儒家论”。此说问题最大,因为这种将孔子定义为“三纲”思想的始祖的说法,虽然始于马融对“殷因于夏礼”一章中“所因”想当然地释为“三纲五常”,但人们坚信马融之说得以成立的根本依据,却是孔子之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要破解此说之谬,需恢复此章内容的正确句读,然后还原其语境,以达于对其本义的理解。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8](284)
公元前547 年,年幼的齐景公继位,其后在公室权力争斗中唯命是从地做了26 年傀儡君主,最后通过杀戮掌握了君权,并意欲励精图治恢复祖上齐桓公的荣光。正值此际,年轻的孔子适齐求仕,于是齐景公向孔子询问治邦强国之策,孔子只给他“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八字方针。这不仅基于齐国内政混乱现实,更因为春秋晚期的整个政治生态。《论语》“微子”篇中,孔子对这一政治生态状况予以了全景式描述。在孔子看来,他所生活的当世是一个君臣失道的时代。孔子经历了“陈成子弑简公”[8](334-335)和卫庄公、卫出公父子争国[8](160)事件。面对“陈成子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请求鲁哀公出兵讨伐之;但对卫庄公、卫出公父子争国,孔子却断然拒绝卫出公蒯辄之邀参与卫政。孔子如此动静分明,是因为在他看来,世道衰微的表面原因是礼崩乐坏,但其实质却是君臣均因横流的利欲鼓动而丧失“责”“德”“道”的约束。孔子认为,要结束这种状况须从个人与治理两个方面着手:应对前者,孔子提出“克己复礼以为仁”的治身主张;针对后者,孔子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治邦方策。
对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一章内容,历代注解各有不同,但孔安国所注最为客观地概括了齐景公问政的特定处境以及由此形成的具体语境:“当此之时,陈恒制齐,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故以此对之。”[5](2504)孔子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为方策,意在指出富强邦国的首要问题是根治内乱,其根本大法是君、臣、父、子各在其位担责、行德、守道。以此观之,孔子应对齐景公问政的八字治邦方策,呈现如下普遍意义。
首先,孔子提出邦家一体的整体论思想,指出要富强邦国,必须邦家齐治。
其次,孔子提出富强邦国必须正定名实的思想。这一思想呈现两方面的自身规定:一是正定名分,这就是“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8](297)。二是正定名实,即有其名分,必要有其实。只有名分,无有其实,就是伪,就会在家乱人伦,在邦乱秩序。这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何以会成为治理邦国内乱的根本方策的理由,因为正定名实的本质,是各遵其道、各正其位、各担其责。
再次,治理邦国的基本任务是构建以权责对等为导向的良性人际关系,孔子将其概括为君以臣为参照、臣以君为参照和父以子为参照、子以父为参照的四种关系。在“君→臣”关系中,只有君遵守君道,担当为君的职责,体现君德的表率,为臣才可真守臣道,担当为臣的职责;在“臣→君”关系中,臣必须以君为榜样,对等地遵守臣道,担当为臣职权范围内的责任;在“父→子”关系中,只有父遵守父道,担当为父的职责,作出父德的表率,子才可真守子道,担当为子的职责;在“子→父”关系中,子必须以父为榜样,诚实地遵守子道,担当为子的责任与义务。
最后,在如上四个关系中,父子是血缘关系,遵循的是无可选择性的血缘律(或曰自然律)。所以,父遵守父道而担当为父的责任和子遵守子道而担当为子的责任,属先天契约规定,是一种天职责任。与此不同,君臣关系是一种后天契约关系,遵循的是具可选择性的社会律,或可称之为等级平等的权责原理和自由权界原理。孔子强调君必守君道担君责,其为政必须遵从明确的边界约束,并提出三个基本主张:一是“以道事君,不可则止”[8](261);二是只有先“君使臣以礼”,然后才有“臣事君以忠”;三是一旦君不守君道,打破君臣之间的边界约束,臣则可“邦无道如矢”[8](362),因为“邦无道如矢”的实质是“君无道如矢”。
综上,孔子应对齐景公问政,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八字方针,是从契约关系、权位与职责、名实与边界约束等不同方面规定君、臣、父、子“既然是这样”,就“必须如何做”。而且,就邦国治理言,对君的职责要求和权力的边界约束是首要的,它构成臣担当职责和接受边界约束的绝对前提,也是家庭父子之间有职责担当和权利边界约束的根本保证。以此观之,孔子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说,与“君为臣纲,父为子纲”没有任何关联性。
三、五伦催生三纲的实质社会走向
1.“三纲”思想的实质诉求与取向
贺麟在《五伦观念的新检讨》中指出,“三纲说实为五伦观念的核心……三纲的明文,初见于汉人的《春秋繁露》及《白虎通义》等书,足见三纲说在西汉的时候才成立。儒教之正式成为中国的礼教也起源于西汉”[2](237),并指出“三纲说在历史上的地位既然如此重要,无怪乎在新文化运动时期,那些想推翻儒教,打倒旧礼教的新思想家,以三纲为攻击的主要对象”[2](238)。三纲思想在新文化运动中遭到批判和遗弃,是它的宿命;但在非运动时期,它又总会发挥其特别功能,因为它既有发挥自身强大功能优势的历史性资本,更有使自己死而复生的文化土壤。比如,自武高寿的《论社会主义契约文化的“三纲五常”》(1995)发表以来,学界不断地“推陈出新”三纲五常思想,并致力使它成为当代的“普遍伦理”。对“纲”做词源学论证,“‘纲’的字义本是网的大绳,网上其他的绳子都连到‘纲’上,因此,国君是臣民的纲”[27](172)。当用如此本义的“纲”来表述君臣、父子、夫妻关系时,其“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纲”被赋予了“规范”“章法”“尺度”等语义,进而可对君臣、父子、夫妻关系予以两个维度的定义。其一,根据“×为×纲”的表述结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实质定义是“君是臣的规范,父是子的规范,夫是妻的规范”。所谓“规范”,是指对行为(或生活)的刚性规定和约束,它构成人人必须服从的章法,必须遵守的尺度。其二,根据“君臣→父子→夫妻”的排序结构,夫妻关系必须以父子关系为准则,父子关系必须以君臣关系为准则,由此排序所表达的根本规范是:国大于家,家重于人,男人重于女人。或曰:女人必须无条件服从男人,个人必须无条件服从家,家必须无条件服从国,国必须无条件服从君。
如上两个方面的规定构成“三纲”的等序结构:居此等序结构顶端的是君,他是一切的来源和理由,也是一切的依据和法则,更是一切的准则和尺度;居此等序结构底端的是女人,她没有个人权利,生下来就是权力、男人、父子的工具或玩物;居此由顶端的君与底端的女人构成的金字塔结构中的其他人,既是奴才又是主子,每个人既是居于上一个等级阶梯上者的奴才,又是处于下一个等级阶梯上者的主人。在“三纲”统摄下,每个人既被彻底异化为没有自由和个性可言的奴才,又拥有通过奴役比自己更不幸者的方式享受自由和展现个性。这既是人们痛恨“三纲”的原因,也是人们留恋“三纲”的缘由。
2.五伦催生三纲的社会变局
真正理解“三纲”的思想实质和功能诉求,就可明白五伦向三纲生成的巨大历史意义和文明代价。
孙宝瑄于1907 年在《忘山庐日记》中写道:“要之,三纲可去,五伦必不可废,何也?五伦者,人生自然之秩序也,本无弊害;害五伦者,三纲也。”[28](473)既然三纲害了五伦,那为何五伦会催生出三纲呢?这种催生是必然的吗?“因为三纲说是五伦观念的必然的发展,曾尽了它历史的使命。”[2](240)贺麟关于五伦催生出三纲是思想发展的必然的判断依据,是五伦催生出了三纲这一思想史实。但是,思想的事实本身并不必然是思想产生和发展的原因和动力,任何一种思想,从其萌生到孕育生成,再到成长发展,其间要经历许许多多的或然和可能,五伦催生三纲同样如此。
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此上古血缘五伦,其功能发挥至于春秋晚期也没有根本性质、内涵以及结构和框架的改变。生活于春秋晚期的孔子在尊重五伦传统基础上特别强调孝的根本性,并努力于解决如何更好发挥血缘五伦的主体德性(仁)与践履相一致的问题。但在政治学领域,孔子却更关注一邦之君如何有道、有德、有责地为君的问题。在孔子看来,第一,只有君有道,它所经营的邦国才有道;第二,只有君有道,才可有德;第三,只有当君以道统德时,才可有责、担责。怎样才能使君有道、有德、有责?孔子提出了两条:一是邦君“为政必正”,这是因为“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8](287);二是应该打破君权世袭制,一切以德才为准则,哪怕是邦君,也应该是德才者任之,这就是孔子论“雍也,可使南面”[8](126)的政治学本质。
孔子生活的春秋晚期虽然出现道术分裂,但周天子仍然是共主;“周监于二代”所形成的分封制社会结构框架和以礼乐为约束方式的精神价值体系,虽然有所破损,但仍然在运转并发挥其功能。整个社会还没有出现周制根本崩解的迹象,诸侯的争霸,也仅是为扩大地盘和拥有更多或更强硬的话语权,还没有产生出推倒或消灭共主自为天下王的野心和想法。在孔子看来,这种有些近似于现代联邦制的分封制文明,应该是最好的文明形态,理由是分封使诸侯不能独裁,政在朝堂。邦国的朝堂,有些近似于欧洲的议会,邦国政务,都要通过朝堂大夫共议,达成共识,邦君才可行其君权。这种“朝堂共议”的决策方式能得到根本保证的前提,是邦国执政的大夫由天子委任。所以,以天子为最高权威、以邦国为实体的二元结构的封建制体现了一种原始性质的民主,给社会和个人留下了巨大的自由空间。春秋开始形成诸侯争霸的格局,从两个方面进一步扩大着社会的自由:一是“天子失官”推动诸侯争霸加剧,对人才的需求加大,人才成为最紧缺的资源,由此形成二元结构的政治并进一步开放自由空间;二是“学在四夷”加大了人的社会性流动,推动了社会自由空间的不断扩展。正是这两个方面的社会风气与扩散态势催生出孔子的政治自由主义。孔子的政治自由主义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突出了人的自由选择与边界约束。孔子将其表述为四个方面。一是“为政以德”。二是“以道事君,不可由止”。三是“邦有道如矢”和“邦无道如矢”,并且“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8](191)。四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只有先“君使臣以礼”,然后才可要求“臣事君以忠”。
综上,孔子不修改五伦,更无君纲思想,是因为他所处的时代社会虽然已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总体取向仍然是在维持“天子和诸侯”二元政治结构的框架下展开利益争夺,并且这种争夺进一步扩大了社会的自由。
孔子逝世170 多年之后,孟子诞生。孔子和孟子所生活的“当世”是两个不同的时代:孔子生活于春秋晚期,虽诸侯国也不断发动战争,但和平是常态,追求和平是基本的社会取向。孟子生活于战国中期,战争已成为常态,大小诸侯邦国或主动或被迫地卷入其中,由此形成自保或图强两种取向,并且自保和图强的努力又成为战争的动力。为更大程度地实现自保或图强,邦国必须变法;变法要富有成效,必须强化君主的权力。在战争频仍的孟子时代,君主集权越彻底,战争取胜的可能性就越大。并且,变法打败世袭获得了彻底性,君主集权的制度和机制真正建立。孟子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社会趋势下将孔子一般意义的仁学思想发挥为仁政思想,并寻求一种心理学和人性论的依据,然后在此基础上重构五伦,将血缘五伦修正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新五伦。上古形成的血缘五伦,强调血缘责任和义务,孟子的新五伦虽也强调责任,但更突出宗法等级和规范。而且,孟子的新五伦突破了血缘框架,将伦理向政治融会,将私德向社会贯通,前者表述为“君臣有义”,后者表述为“朋友有信”。
在孟子的新五伦中,“君臣有义”的“义”,被认为是接着孔子讲,但它实际上与孔子之“义”有根本区别。孔子讲“君臣义道”之义,是公义,是需要君臣共守的道义,其理想内容是“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和“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8](304-305);其实践内容是“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和“修己以安百姓”[8](352-353),为此而必须“庶之”、“富之”和“教之”[8](303);其实现方式是“为政以德”[8](21),即正己以正人,正己以正事,正己以正邦。与此不同,孟子的“君臣有义”之“义”,却是“私义”,孟子将之阐释为“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臣之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之视君如寇仇”[28](186)。孟子将孔子公义性质的君臣“义道”变成私义性质的君臣“义气”,使君臣关系性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孔子那里,君与臣之间完全是一种职业契约:“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8](267)所以“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8](67),并且,“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8](191)。与此不同,孟子的“君臣有义”完全锁定在君对臣的情感好恶和利益取舍方面,没有了社会公“道”的要求与规范。孔子那种唯有“君使臣以礼”,才可“臣事君以忠”的浩然正气和“守死善道”的精神,在孟子那里完全丧失掉了,臣完全可以因为对君的私义而不讲社会公“道”、不求人间正“义”。所以,孟子的宗法五伦为“三纲”铺下了第一块基石,虽然这块基石往往并不为人们所关注,但它却特别根本和紧要。
孟子为三纲铺垫起第一块基石,紧随其后的荀子为三纲铺垫了第二块基石。比较而论,孟子为三纲铺垫的第一块基石,是从君的主体性入手,其直接方面是建立新五伦,突出君的权威;其间接方面是构建仁政理论,强调君的能力和作为。荀子为三纲铺垫的第二块基石,重在突出天赋其君在人间社会的统领地位和主宰功能。为此,荀子首先直接构建起“三本五伦”,强调君权的神圣性,为董仲舒对三纲予以形而上学和神学的论证,提供了思想的土壤和认知的理路。其次是探索重建以神圣性的君权为主导、以礼为基本框架的制度结构。
在为三纲铺垫基石方面,荀子不同于孟子的一个重要方面,仍然是其所生存的时势及取向不同所造就。孟子生活于战国中期,荀子却生活于战国晚期。战国经历中期自保与图强的拉锯性(合纵或连横)兼并战争,完成对各弱小邦国的并吞,其后展开大国之间的深度并吞的拉锯战造就强者更强、弱者更弱的态势迅速明朗,自然产生出一种求取一统的冲动,这种冲动最终构成强者的战争动力,推动战争向更加深广的领域展开。由此不难发现,孔子时代那种希望重建返本开新周道的社会梦想在孟子时代已经泯灭了,孟子时代的思想家大多卷入了为君保国或强邦的大争之势中,已经没有了孔子时代那种可以“守死”的独立于君权君势之道,或者说,孔子时代的君必须有君道,才可有邦道,而君道、邦道却是来自君权之外的体现人性和自然双重律令的社会大道,这就是孔子所盛赞的“唯天为大,唯尧则之”[8](196)之天道(或曰自然法则)。以此观之,孟子时代是真正失道的时代,其失道的普遍化导致了社会对普遍性的道的重新寻求与探索,但已经消解掉了孔子时代的那种主观激情而进入了实利理智的历史进程,这一历史进程最终造就了荀子的礼法并举。进一步讲,孔子时代的思想家探求重建、弥合分裂了的道术的各种社会拯救方案,都体现了思想家们的个性风采;但进入荀子时代,冷酷的战争和寻求与周制完全不同的大一统努力,必须是务实地张扬以君权为导向、以礼为结构框架的制度思考和设计,必须有法的维度、法的思想、法的眼光、法的精神,并寻求“礼法并举”的最终依据和合理解释。这是荀子抛弃孟子“新五伦”路子另建“三本五伦”的社会原因。荀子将孟子的主观性的君主权威赋予客观的内涵,并为具有神性权威的君如何理智地运用这种权威提供一种引领和督导机制,这就是其“三本五伦”中的“尊先祖”和“降君师”,它为汉代董仲舒一方面论证确立君权神授,另一方面又以天人感应的形而上学方式构建限制君权的路径和方法提供了启发。
梁启超曾说:“自秦汉以后,政治学术,皆出于荀子。”[29](261)梁氏之论虽有片面之嫌,但却道出自汉建立起来的文化思想传统和大一统制度的内在秘密。第一,对于中国社会及其文化、思想和教育来讲,秦应该是一个分水岭。秦之前,是血缘部族主义,伦理呈现以家族为核心的血缘亲情取向,政治只是并不严酷的等级主义和相对自由主义,制度虽然是世袭主义的,但却同时体现原始性质的二元结构化的等级民主取向。秦亡汉兴的根本标志,是汉全盘接受了秦制并全面发展了秦制的精髓,即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废除贵族和世袭,行郡县制;厉行严酷的刑罚治理,实施绝对暴虐的思想控制。第二,汉代创建起来的政治、伦理、制度、文化传统的直接思想资源,是荀子的学说和思想,这是因为荀子思想融会贯通了西周的礼制和春秋自管仲始的历代法家从理论和实践操作两个方面建立起来的法制制度及刑罚机制,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尊君师、赏刑法、隆伦礼的体系。第三,汉代重建政治、伦理、制度、文化传统的另一思想资源是孟子的思想。孟子和荀子的思想构成汉代政治、伦理、制度、文化传统的表里:孟子的思想裱其外,主导汉以来的学术、文化、教育;荀子的思想固其本,主导汉以来的制度、刑罚治理和意识形态的专制。
历史地看,真正了解荀子的人除了帝王,就是其弟子李斯和韩非子。李斯从思想的制度实践方面发挥了荀子的思想,使之成为帝王心目中的“圣人”;韩非子从理论的建构上发展了荀子融礼法于一体的“三本五伦”思想,建构起完整的“三事”(“三纲”)思想体系。这仍然是时代给予他的机会、舞台、条件,因为略晚于荀子的韩非子与其师一样,敏锐地把握到时代的趋势和社会的走向,并为分裂数百年之久的天下重新统一设计“只能如此”的大一统奠定理论基础、设计治理方案。这个方案中最精粹的那一部分,就是大一统的社会何以可能的主体条件和客观基础。这个主体条件就是君权如何才可获得超越时空的权威;这个客观基础就是社会必须建构怎样的基本结构框架才可排除任何例外而真正确保天下一统。韩非子通过考量这两个核心问题而建构其解决之道的永久性方案,就是“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的“三事”思想和实践框架。从这个角度看,韩非子为汉代董仲舒全面建构“三纲六统”体系,铺垫起第三块基石。
在五伦向三纲生成的历史进程中,最伟大的人物应该是董仲舒。董仲舒的伟大主要由两方面构成。
一方面,董仲舒发现了作为构建大一统政治、伦理、制度、文化传统的荀子思想资源的务实主义,同时也发现了作为构建大一统政治、伦理、制度、文化传统的孟子思想资源的务虚主义,并将两者虚实有机地统一起来形成以法为本、以德为表的治理体系。采取的具体方式是,基于孟子和荀子都分别自我标榜是孔子的正宗传人,而以孔子为名号来统摄孟、荀,来号令百家,这就是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提出的“推明孔氏,抑黜百家”。
另一方面,董仲舒融统孟、荀思想而创建起“三纲六统”(后来通过白虎观会议订正为“三纲五常”),为全面实施政治统摄伦理和帝王专制天下的独尊主义提供了神学主义、自然主义和人性主义的三重合法性证明,将汉代大一统对周“监于二代”而建立起来的相对自由的二元结构制度被武断弃置后所形成的巨大鸿沟予以形式上的填充,同时也将汉代大一统对先秦以民生主义、原始民主、相对自由主义为本质内涵的传统予以暴虐否定所形成的思想、精神以及心灵、情感上的深度裂口和伤痕,予以形式上的填充性修复。这种形式上的填充性修复,通过“推明孔氏”方式展开。于是,孔子成了汉代帝王专制制度及其政治、伦理、文化传统的象征,“三纲五常”的始作俑者,也必须安排给孔子。所以,孔子在后世既是圣人,更是受难者。孔子作为圣人和受难者的双重历史待遇,虽然与孟子和荀子分别自诩为其思想的正宗传人相关,但最终却成就于董仲舒的伟大智慧和运作。以此观之,孔子被后世再造的圣人史和受难史,谱写出孔子身后的中华政治、伦理、制度、文化演变发展的轨迹。更具体地看,孟子、荀子、韩非子、董仲舒以及整个汉唐经学家和宋明道学家创造、发展、实施、完善“三纲五常”的艰苦卓绝的历史,有条件地以“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方式敞开了中华文明的真实轨迹和实质取向,也为我们如何在今天更客观地对待“三纲五常”提供了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