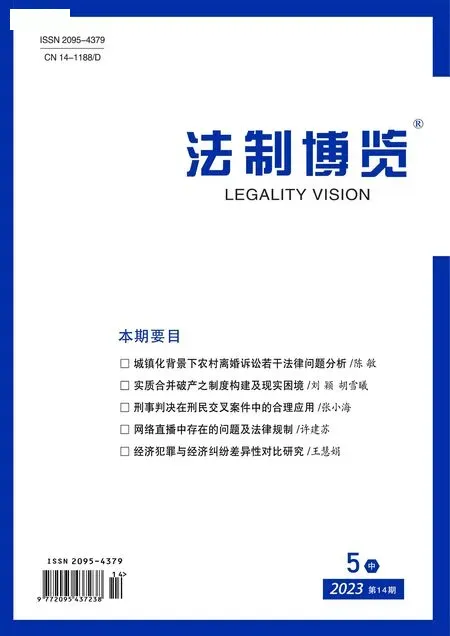未成年子女权益在离婚案件中的保障及完善
何昌莉
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广东 广州 510620
现行《民法典》对离婚后未成年子女抚养问题进行修订和完善,改变过去父母本位思想,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对探望权、抚养权、归属权进行了重新划定。基于此,文章以具体案例为分析,总结未成年子女归属与抚养权存在的实际问题,并给出相关解读。
一、子女抚养权归属原则和影响因素
根据《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规定,当夫妻双方可以对子女抚养权归属问题达成一致,离婚时应该按照双方意见进行裁决[1]。并且在此基础上主要考虑以下影响因素:
(一)父母双方抚养能力
通常情况下,如果夫妻双方经济实力相差悬殊,考虑到今后子女升学、生活、成长问题,未成年子女归属权和抚养权,极大可能归由经济条件较好的一方。
(二)子女年龄因素
首先,如果是不满2 周岁的子女,由母亲直接抚养(特殊情况除外,例如,有条件但是不尽抚养义务,或者有其他传染性、重大疾病),如果子女超过2 周岁,并且夫妻双方共同争夺子女抚养权,此时法律应该根据子女利益最大化原则,考虑双方情况,从情感、时间、陪伴、经济、教育、成长环境等多方考量,决定未成年子女归属问题。其次,当子女超过8 周岁,孩子的意愿也会影响法官判决(法官对子女意见进行考虑,但子女意见不是决定性因素)。
(三)隔代影响因素[2]
祖父母外祖父母协助照顾孩子的意愿和能力,孩子对他们有依赖关系和感情。如果夫妻一方的父母可以帮忙照看孩子,在子女归属问题上可以优先考虑,将隔代抚养纳入子女归属权影响因素中更加符合我国生活实际,因此在抚养权归属问题中占据重要作用。
(四)父母利益因素
离婚案件中,如果夫妻双方已经绝育或者没有生育能力,在未成年子女归属问题上,具有优先权,这符合我国国情,同时也能凸显出法律柔性与人文关怀。
(五)其他可供参考的因素
二、基于离婚案件,解读未成年子女抚养权归属法律问题
为了探究未成年子女抚养权归属在离婚案件中存在的法律问题,文章以具体案例为视角,进行解析。
(一)案例一:沈某与夏某离婚纠纷案① 以下案例摘自于广东高法民法典适用典型案例。
原告沈某(女)和被告夏某(男)于2010 年登记结婚,在2012 年生下一女夏某某,但是在2012 年起原被告双方多次发生摩擦与争吵,被告对原告大打出手,至2014 年夫妻感情彻底破裂,于是在当年6 月,沈某诉讼离婚,经法院调解夏某同意协议离婚,但孩子抚养权由法院判决归沈某。夏某不服提起上诉,认为自己无论从经济条件、住所、家庭情况等各个方面更加有利于其子女的健康成长。沈某辩称夏某所说与事实情况不符,双方分居后孩子一直由沈某独自照看,其幼儿园的工作性质也可以很好地兼顾到照看孩子与工作,且有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她并没有拒绝夏某探视孩子,是夏某自己没有安排好时间。因此,夏某没有新的事实与理由,也没有新的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应该维持原判。
案件裁决: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并无不当,判决维持原判。原审法院判决如下:关于子女抚养问题,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可以认定双方对子女有极大的责任心和爱心,但抚养权的选定应以有利于子女的成长为依据。因双方所生育子女夏某某年龄较小,随母亲生活更有利于其健康成长。又因沈某、夏某分居后均由沈某携带抚养子女并共同生活,为保持子女的生活环境稳定以利于其健康成长,也应随沈某共同生活为宜。且沈某本人从事教育工作,对于教育抚养子女有一定的优势。综合上述情况,原审法院认定双方所生育子女夏某某应由沈某携带抚养。关于子女抚养费数额及探望权方面,依照原《婚姻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离婚后,一方抚养的子女,另一方应负担必要的生活费和教育费的一部分或全部,负担费用的多少和期限的长短,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之规定,根据夏某某的实际需要、双方的负担能力和当地的实际生活水平,原审法院酌情认定夏某每月负担抚养费为**元。夏某对女儿夏某某享有探望权,在不影响女儿正常生活、学习情况下每周末可以探望两天,具体时间和方式由双方协商。离婚之后,父母双方均具有教育、抚养、保护的权利和义务。
(二)案例二:刘某某与陈某某离婚后抚养权纠纷案
刘某某与陈某协商一致于2016 年3 月1 日离婚,双方签订离婚协议,并在民政局办理了离婚手续。协议约定离婚后婚前唯一一套房屋归陈某所有,陈某补偿李某某人民币30 万元,孩子抚养权归陈某,刘某某不需支付抚养费。
但实际情况是,离婚后陈某因为各种原因,无法照看孩子,致使孩子不愿意和他住在一起,而是常年和刘某某及其父母一起生活,在刘某某户籍地上学,由刘某某父母帮助接送照看。陈某因为下岗经济窘迫,不仅没有支付刘某某房屋补偿金,也没有支付孩子生活费。不久陈某组建新的家庭,经多次交涉无果,为了更好照看孩子,刘某某决定更改孩子的抚养权,遂诉至法院。
庭审前法院主持调解,刘某某理由充分,事实证据确凿,要求变更孩子抚养权。陈某坚称自己只是一时困难委托刘某某帮忙,坚决不同意更改孩子的抚养权,并申请要求庭审的刘姓法官和原告代理人回避。后经法庭调查,择日宣判变更孩子抚养权给刘某某,理由如下:首先,从原、被告个人基本情况出发,原告现从事销售服务,工作自由度高,收入稳定,具备抚养子女成长的经济基础和条件;其次,从原、被告家庭成员出发,原告父母及亲属均在广州地区工作生活,有稳定住房及退休金,且均表示出强烈的意愿,愿意协助原告抚养子女,在稳定的家庭环境下更有利于子女的健康成长,被告现居住在成都市,被告的其他家庭成员在广州地区生活,难以协助被告共同抚养被抚养人的生活起居;最后,从被抚养人本身出发,原、被告婚生女陈某某现已年满7 岁,心智基本成熟,属于小学学生,且已经在广州上学,而被告在成都地区生活,在教育质量等相关方面广州地区更具优势。故结合上述分析,本院认为,现被抚养人陈某某由刘某某携带抚养更有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发展。故对于原告要求将婚生女陈某某的抚养权变更,本院予以支持。
后被告没有对判决提出上诉,判决生效。但是此事并没有画上完美的句号,上述判决生效后1年被告都没有支付过陈某某抚养费。多次沟通无效,刘某某只有代理孩子再次提起诉讼。
(三)综合分析以上案件,虽然最后孩子的抚养权都判给了女方,但实践中仍然存在如下实际问题
1.抚养协议审查问题。在协议离婚中,夫妻双方只要签订离婚协议,就房屋财产、孩子抚养权协商一致,就可以办理离婚手续,而抚养权争议的审理,是在夫妻双方抚养权存在争议时诉至法院的基础上才能进行,如果夫妻双方就此达成一致协议离婚,那么未成年子女归属问题不会成为法院审理内容。可见在协议离婚案件中,未成年子女利益是否得到保障,是否达到最大化,是未知的。这也为以后的变更抚养权纠纷、支付抚养费纠纷埋下了隐患。
2.夫妻双方经济问题。一般来讲,如果夫妻双方实力相差悬殊,孩子大概率会归属到经济较好的一方,但同时也应该注意到女方由于对未成年子女,尤其是不满3 周岁(目前大多幼儿园都只招收年满3 周岁的孩子)的子女投入的时间过多,因此在工作、经济能力和抚养能力上不如男性,在子女归属权问题上处于弱势地位,往往因此得不到孩子的抚养权。而低幼年龄段的孩童对母亲的感情依赖很强,这势必影响到孩子的心理健康。
3.家庭暴力因素问题。在部分离婚案件中,未成年子女抚养权裁决对家庭暴力的考量不够深入,在《民法典》施行以来,在离婚案件中可以保护妇女权益,但是未能充分考量家庭暴力对子女的影响。
4.抚养费确定及支付问题[3]。部分案件中,抚养费给付标准不具体,多数情况下法院不能查明父母双方真实收入,因此不能充分体现儿童最大利益原则,且存在给付执行问题,目前一般都是裁决每月支付,但是没有第三方银行扣划保障,给付方不及时或拖延的情况时有发生。于是往往抚养权案件才了,追讨抚养费案件又起。
三、基于案件引发的思考——未成年子女抚养权归属法律完善路径
(一)审查抚养协议
从司法层面来讲,法院给予离婚双方对子女抚养权协商的权利,以家庭自治为由,使得立法干预和家庭之间达成平衡。但是,未成年子女的抚养成长问题又不仅仅是家庭问题,社会也负有重大责任。因此,在协议离婚时,应该对抚养协议进行全面审查,从子女最大利益原则出发,如果协议不符合子女最大利益,应该给予协商和协调,使得离婚双方重新达成协议,在必要时给予驳回处理,之后由法官做出裁决。审查内容主要为:存款、房屋、债权债务、其他财产、经济帮助等,尤其对于未成年子女的抚养问题,应该写明孩子属于哪一方,携带抚养关系直至子女年满18周岁,并且在携带抚养期间给予其教育、安全、生活等方面的监护,不承担携带抚养的一方应该每月支付抚养费,并标明抚养金额,之后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抚养费金额应该由双方另行商量。未享有抚养权的一方应该予以探望权,探望频次由双方协商[4]。以明确责任的书面模式,双方签字确认。通过这一方法,既维护了家庭自治,又可以在夫妻双方达成一致的前提下,让民政部门出于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对未成年子女抚养权归属问题予以审理。
(二)建立抚养权属经济评估制度
相关法律规定从有利于子女身心健康出发,结合父母双方抚养条件和抚养能力等具体情况,妥善解决未成年子女抚养问题,由此部分离婚案件当事人可能片面地认为哪一方经济条件好,就可以获得孩子的抚养权,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出于保护未成年人基本权益,从孩子身心健康考虑,父母经济情况并不是决定因素[5]。而是应该综合考量其教育能力、监护能力、思想品质、权利义务、付出感情、感情亲疏、子女本人意愿等多种情况,因此对于子女抚养问题,其判定是较为复杂的。尤其在经济评估这一方面,对于8 周岁以下的子女,其母亲在生活、工作方面与父亲相比大多处于劣势,因此,在抚养权归属问题上,法律应该向女方倾斜,即使女方经济条件不如男方,也应该在审判中酌情考虑。
(三)增加家庭暴力的可推翻假定
如果法院发现可以证明家庭暴力的证据,并且这一行为已经对儿童身体和精神造成伤害,那么就成立了可推翻假定,出于子女最大利益原则,实施暴力方不可能被判有抚养权,或者在离婚诉讼期间该种暴力行为仍然存在,也不会拥有未成年子女抚养权。但是如果曾经有过恶习的父母,已经改变酗酒、吸烟等恶习,或者已经完成了整个心理疾病康复治疗程序且有证据证明完全康复的,也可以与另一方争夺子女抚养权归属,但最终法官如何判定,应该依据具体情况综合裁决。
(四)优化抚养费确定模式
对于抚养费确定,除了之前文中提到的事前审查抚养协议这一方面,相关部门还应该重新拟定科学化的抚养费标准,供法院和司法人员参考,例如按照当前规定,应该根据当地实际生活水平确定最低抚养标准,但是当前人口大规模流动,现行户籍制度不能使得儿童利益最大化,家庭经济能力不同参照标准就不会统一,因此,这一抚养费确定标准显失公平。笔者认为,应该按照子女不同年龄段计算抚养费数额,建立抚养费给付事前保障机制,通过扣减薪水、按期支付、定期给付、设置担保金等措施,避免后续出现纠纷,增加诉累。同时应该完善抚养费给付事后保障机制,在抚养费执行方面,如果不能按照前期约定给付未成年子女抚养金额,可以参照惩治“老赖”的手段,通过禁止乘坐高铁飞机、执行唯一住房等措施,加大执行力度,最大化保护未成年人的利益。
综上所述,当前在未成年子女抚养权归属方面还存在一些法律问题,相关部门应该为今后立法和司法指明方向,以儿童利益最大化为原则,建立抚养费给付事前、事后保障机制,按照子女不同年龄阶段计算抚养费数额,审查抚养协议,建立抚养权属经济评估制度,增加家庭暴力的可推翻假定等,从而在司法实务中可以依据具体制度规定,使保护未成年人的利益最大化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