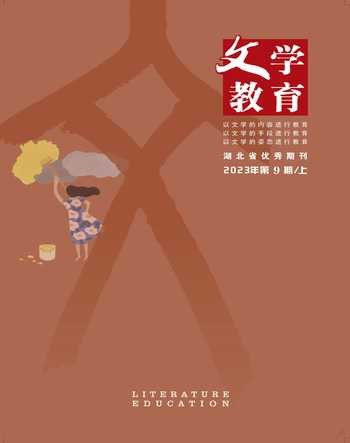论余华《文城》中的“文城”意象
李贤 徐文娟
内容摘要:《文城》是余华的长篇小说,在叙述的过程中,以大量的具象形成抽象的意象。“文城”作为一个观念意象,有三重涵义:首先表现在林祥福这个形象上,这一形象隐含了作者对当下人们生活状态、价值观念的思考,以及对理想人格的肯定。其次,表现在它隐喻了人类的一个永恒的主题,即理想和现实的纠结,文城象征着诗意与远方。第三,文城也是爱与美的象征,探讨了非血缘关系的爱,以及爱与美的关系这一大多数现代人面临的心灵之问。
关键词:余华 《文城》意象 隐喻
余华的每一部长篇都有不同的风格,他小说中的现代主义叙述手法、苦难叙事、表现人性的微妙等似乎成了他的写作风格,在这阶段性的创作嬗变之中蕴含着作者不变的参照对象,即对人的生存状态及人生境界的思考。相比较之前的作品而言,2021年出版的《文城》似乎是一个总结性的书写,以讲故事的方式剖析人性,善良有回报,作恶受惩罚,失去的以另外一种方式得到,寻找、漂泊、终将回归于永恒。文本中的“文城”是一个虚幻的地名,但它推动着情节的发展,影响着林祥福的命运,所有的故事都与 “文城”有关。在此意义上,“文城”是一个意象。它的隐喻首先表现在林祥福这个形象上。他既是文本中的主要人物,也是一个富有意味的“符号”,无论从哪个角度审视,他几乎符合所有的道德要求。然而就是这样完美的一个人却有着不够完美的一生,他的人生似乎注定就是由一场场考验构成,他需要不断地闯关,不断接受环境的变化及挑战,经历了混沌、圆满、澄明三种状态。其次,表现在它隐喻了人类的一个永恒的主题,即理想和现实的纠结。第三,探讨了爱与美、真善美的关系这一大多数现代人面临的心灵之问。
一.人生:成长的轨迹与境界
尼采在《论三种变形》中用骆驼、狮子和婴儿来比喻人的三种境界,其中骆驼汲取和积累知识;狮子表现自己和创新;婴儿随性自由。冯友兰把各种不同的人生境界划分为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四个等级。“人的境界,即在人的行动中”[1]553。这其实也是一个人成长的轨迹,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行为,人的种种行动构成了人生。
《文城》中的林祥福出生于一个富裕的地主家庭,他勤奋好学,读书、种田、做木工,没有地主家少爷的脾气。五岁时丧父,和母亲相依为命;十九岁时丧母,他一夜间长大,他成了一个家庭的支柱,学习父母的样子积攒家产,固守家业。如果没有小美的出现,他会重复父辈的生活、延续家风,做一个知书达理、仁义的地主。可以说在小美出现之前,林祥福像骆驼一样学习各种知识,顺着当地的人情风俗和习惯做事,人们看到他就会想到他的父母,并对他格外关爱。这是他人生的第一个阶段,即人生的自然境界。“在此境界的人,其行为是顺才顺习的”。[1]551他从未想过会离开这片祖辈生活的土地,他自觉意识到自己有责任守成这份家产、不做愧对父母的事。小美的到来打破了他平静的生活,也给他的人生带来转折。小美第一次离开带走了他一半的家产,“祖上积攒的金条”,他依然坚守着那片土地,原谅了她的行为;小美的第二次离开,留下了他的孩子,他开始了漫长的漂泊。他要替孩子找妈妈,这个最朴素的念头和“文城”共同推动着他离开熟悉的家乡和祖传的家业。到文城去是一个艰难的选择,对他有限的人生经历和当地的民俗而言,有着“反叛”的意味。历经艰险,没有人回答他“文城在哪里”,他以“垂柳似的谦卑和田地般的沉默寡言”[2]4留在了溪镇。溪镇的龙卷风和雪冻给了他发挥木工手艺的机会,他和陈永良挨家挨户修理被风损坏的门窗,不计较报酬,甚至是免费修理,“几乎走遍溪镇人家,没有发现小美的痕迹”[2]72,在这一过程中,他所做的一切行为的后果都是利他的,但也有着利己的动机,他潜意识中希望以此方式找到小美。精湛的木工手艺让他立足于溪镇,有了陈永良和顾益民的支持,他的木器社开张了,离开故乡的他再次以善良、仁义立足于异乡。寻找变漂泊,异乡成为栖息地,此后数年,他并没有停止对小美的寻找。小美的离去归来再离去扭转了他的整个人生,这一阶段他不自觉地进入了人生的第二个境界,即功利境界。在此境界的人,“其行为是为利的”,[1]552他的为利表现在:一是为寻找小美而出走,二是为了在溪镇更好地生存而像狮子一样表现自己和创新。他的木器社逐渐在方圆百里闻名,财富日益增多,与顾益民的交往以及自幼熟读的古籍经典,共同引导着他进入了人生的另一个阶段。他由以土地为生变为以商业为生,他与溪镇是一种地缘,地缘是从商业里发展出来的社会关系[3],意识到生活是一个整体,溪镇是一个整体,他是这个整体的一部分。他积极参与溪镇的各项公益活动,这期间他的所言所行都是符合道德意义的道德行为。他冒着生命危险营救被土匪绑架的顾益民,明知道一去不复返的可能性很大。这是他成长中的第三个境界,道德境界。“求社会的利的行为,是行义的行为”[1]553。這也是一次寻找,寻找被作为人质的顾会长,这次寻找是为“义”,为了整个溪镇的利益,最终他以自己的生命换回了顾益民。他的寻找历程就是他的成长轨迹,他的成长轨迹就是他的人生境界不断提升的过程。从最初离开故土的混沌状态,到把溪镇当文城而驻足,并在此奋斗十多年,家产丰厚,名誉一方,终至“明理哲人,神识周运,深悉苦乐,皆属空华”[4]的境界。
《文城》中的众多人物在溪镇相聚,他们的出现以及溪镇的地理特征共同丰富了林祥福这一形象的意蕴。他的每一步都是对既有人生经验的突破,是对之前的否定,寻找小美是一场苦行僧般的修行,一次突破意味着一次蜕变。联系起来看,现实生活中的个人成长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人生就是一个不断寻找的过程,从自然属性到社会属性,历经数次精神的或现实的漂泊才能体会生活的多重境界。
二.理想:可及与不可及的悖论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漂泊于溪镇十多年后,林祥福醒悟到 “既然文城是假的,小美和阿强的名字应该也是假的”[1]153,甚至也怀疑小美和阿强是夫妻而不是兄妹,却依然没有对小美有怨言,也不愿意相信他们骗了自己。这意味着什么呢?是美丽的谎言在大爱中开出了人性最美的花还是对美好的向往促进了一个人的新生?在这一语境下,文城意味着人们对遥远未知的向往,意味着对远方的诗意想象,阐释了理想的可及与不可及这一悖论。
小美和文城是他离家出走的缘由,初到溪镇,林祥福是走在街道边、沉默的流浪汉;十多年间他取得的成就足以让任何一个人骄傲。他寻找小美的念头从未消失,但注定找不到她;对他来说,有小美的地方就是文城,他找到了小美的所在地溪镇;小美期盼他能离开,但他却在此驻足,也许正是他的到来,小美才会永远的离开;文城就变成了一个永远解不开的谜。当他不再去寻找文城,他的生活有了新起色。抽离故事情节可以看出这样一条线:得到即失去,失去的会以另外一种方式补偿。他决定离开故土时,是一种自发的意识,在寻找漂泊的过程中,他见到了形形色色的人和事,打开了一个不同于以往的生活局面。在溪镇,他就有了规划和为实现目标而进行的努力,到后来送女儿到上海读书,解救被土匪绑架的顾益民,这些是他的自觉意识。这里有一个悖论,他的人生实现了质的变化,可他出走的初衷或者说愿望实现了吗?文本中有明暗两条叙事线索,表层来看,他既没有找到文城也没有找到小美,但在寻找文城的過程中改变了固有的生活轨迹;隐藏的叙述线则是小美知道他和女儿漂泊在溪镇,并且还送了婴儿服和鞋帽,而他并不知道是小美送的,他不知道小美冻死在那场雪灾中,他还在为未能找到文城而遗憾。之所以无法见到小美,是因为小美和阿强受到命运的惩罚,就在他到来的那个冬季,双双冻死在祭拜苍天的仪式上。文本中有一个细节描写,小美和阿强知道林祥福找到溪镇了,他们不敢白天出门,一方面惊诧于他的千里之行,另一方面又盼望他赶紧离开溪镇去往别处,阿强问小美“他为什么不去文城”,小美回复“文城在哪里”。这里的悖论就是:他去或不去,都注定找不到小美。若不去寻找,小美已经离开他和女儿了,他不知该如何面对一个婴儿;父爱促使他不得不去找小美,他留在溪镇是为了等小美,小美却彻底消失了。他寻找的意义体现在哪里呢?文本中所有的人都不知道文城在哪里。从道德的角度来看,或许无法把小美视为“美”与“理想”的化身,但不能否认小美是打开他人生的一把钥匙,把他带到了远方,文城可期待而不可至,可至的又非文城。
在《文城》(补)中作者详细讲述了小美和阿强的故事,来自贫寒家庭的小美以童养媳身份进入溪镇,那时的小美对溪镇充满了向往。阿强家在溪镇上做织补生意,心灵手巧的小美跟着婆婆很快就学会了祖传的织补技艺。因为家事,小美和婆婆产生了矛盾,阿强带她私奔到上海,后又到了北方,辗转中钱财耗尽。留在林祥福家是无奈的选择,他们见他家境殷实,父母双亡,就以兄妹相称欺骗了他。小美拿走金条是为了她和阿强,为了爱情;返回是发现有了林祥福的孩子,她想以这种方式感谢他,孩子满月后,她又果断的离开,依然是为了她和阿强的爱情。这里的悖论是:表层看上小美得到了想要的爱情,可是从北方逃回溪镇以后的他们生活在内疚和自责中,并不快乐。他们三人之间有一种不对等的关系,或者说是一种残缺的爱。林祥福心向小美,为她而漂泊;小美心向阿强,为他而漂泊;小美和阿强一块在溪镇度过余生,而她又心系林祥福,活在忏悔中。他们都有自己的文城,都找到了自己的文城而不知,都带着遗憾离开。
三.爱与美:心灵的归宿
文城是虚幻的,但它作为一种强烈的精神支柱和心理暗示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象征着诗意与远方,也是爱与美的象征,这是这一意象的第三个寓意。或者说作者将爱与美的理念赋予了“文城”这样一个地名。
《文城》着重书写的是非血缘关系的爱,邻里之间的友情和错位的爱情。林的父亲出于同情心收留了逃荒的田大父亲,田大兄弟四人在林家长大,田大后来成为管家,林福祥离家出走前把所有的家产都交给他管理,林一走数年,直到生命结束,田家四兄弟带着多年的收成拉着板车行走千里到溪镇,“他与田大平躺在一起,踏上了落叶归根之路”。[1]235这种不是亲情却胜过亲情的爱,再现了人间最质朴、最温暖的一面。林到了溪镇以后,顾益民的仁义之爱,陈永良一家的善良之爱,同样演变为互相信任、超越了友情之爱的爱,陈永良让自己的儿子替代林百家做人质,林福祥为救出顾益民而失去生命。再回到错综不复杂的三个人之间的关系来看,他们三个所有的行动都是以爱为初衷,阿强和小美的行为不符合正常的伦理道德标准;林祥福与小美之间更难以用爱情一词来界定,但这三人之间的爱却体现了一种哲学意义上的爱,他执着于寻找变为了柏拉图式的永恒之爱。“爱经常使自身被缩小,甚至消灭,从而使对方获得新生。可以说这就是爱的本质,或者说爱的本质之德就是自我牺牲。”[5]在这场残缺的爱中他们都失去了自我,惟有代表着“善”、一直向善的林祥福获得了新生,表层上是佛家的因果报应,实质上是受惠于他始终保持仁义礼智信的品格。“文城”是美的象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体现在人性因向善而产生的美的行为中,二是它作为一个虚幻的存在,包含了美好的想象,找到文城就找到了爱情和亲情。
书写真、善、美有不同的方式,《文城》以荒诞的手法营构意象表现了这一文学主题。故事发生在上个世纪初,故事中人的行为具有代表性,隐含了作者对当下人们生活状态、价值观念的思考,以及对理想人格的肯定和塑造。在自媒体时代的今天,新的观点层出不穷,传统的道德价值观念受到了一定的冲击,我们该秉持积极向善的人生观。文本中的每一个人出现的时间、地点、每一个场景的发生都有其特定的意义。小美初次借住在林家时,一场“木盆那么的大冰雹”促成了两人的结合;林福祥和女儿经历了一场夺命的龙卷风后竟安然无恙;就在林祥福到达溪镇的那个冬天,溪镇下了一场百年不遇的大雪,冻死了小美和阿强。这些自然灾害的细描可视为象征情境的书写,推动着故事的发展和人物性格的充分展现。在讲故事的过程中,以大量的具象形成抽象的“文城”意象。
《文城》中的“文城”意象有其多面性,“文城”充满了残缺的爱与美,以及太多的不确定性。它是真实又是虚幻的;它充满了善意又带着欺骗;它给予了希望又隐藏着失望。于林祥福而言,寻找文城改变了他的命运;于小美和阿强而言,文城是他们为骗局而编织的谎言;对于出陈永良以外的溪镇人来说,文城是一个遥远未知的存在。小美口中的“文城”本是虚幻,林祥福为爱去寻找注定无法找到小美;当南方的溪镇成为林祥福认定的文城后,他不再漂泊,凭自己的聪明才智再次成为一个有千亩良田和木器社的人,由外来的“流浪者”成为本地人的主人,成为众人眼中有社会责任感的人。“文城”就是溪镇,他在这片土地上立业、生活,却又在生命的尽头叶落归根于北方的故乡。从某种意义上说,林祥福的“文城”找到了,并获得了丰厚的回报,林百家受到了更好的教育。从来处来,到何处去?又回归来时路。也许每个人的一生都有向往的“文城”,每一个“文城”都充满了想象的诗意和温暖,不停的寻找却可能永远无法到达,也可能身处其中而不知。作为意象的“文城”阐释了当下人的精神状态和生存方式,以及人们对美和爱的追求。
参考文献
[1]冯友兰著,《三松堂全集》4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版。
[2]余华著,《文城》,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1版。
[3]费孝通著,《乡土中国》,人民出版社,2008版,第94页。
[4]林同华主编,《宗白华全集》第1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8页。
[5](日)今道友信著,《关于爱和美的哲学思考》,王永丽、周浙平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版,第140页。
项目基金:安徽省高校优秀青年人才项目“新世纪以来小说创作研究”(gxyqZD20220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