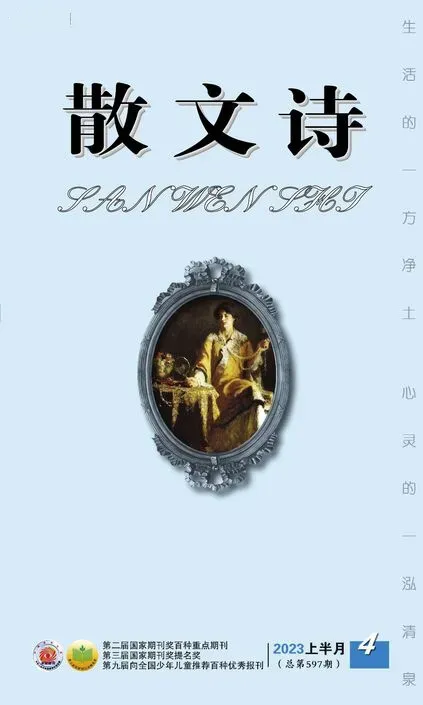新诗谱(节选)
◎胡 亮
刘半农
周树人和周作人兄弟, 都有谈及刘半农。周作人曾说:“那时做新诗的人实在不少, 但据我看来, 容我不客气地说, 只有两个人具有诗人的天分, 一个是尹默, 一个就是半农。”所谓 “那时”, 是指“1919 年前后”。1920 年2 月7 日, 刘半农赴伦敦大学, 妻子朱惠、女儿小惠随行——8 月6 日, 诗人将小惠的话,直接辑录成散文诗《雨》, “妈!我要睡了!你就关上窗, 不要让雨来打湿了我们的床。你就把我的小雨衣借给雨, 不要让雨打湿了雨的衣裳”, 堪称吾国最早且最好的白话儿童诗。是年3 月15日, 诗人一家到达英国。那时女性第三人称, 还用“他”, 某个小范围则用“伊”。妻子, 女儿, 踏入了人称完备的英语世界, 会不会念及这样的语言学漏洞呢? 6 月6 日, 诗人写出《她字问题》,将此前与周作人私聊过的一个问题, 上升为一个公开的语言学提案——应该创造一个字, “她”, 作为女性第三人称。“诗人的语言区分不开帝国和共和国, 区分不开他和她。”西思翎(Jan Laurens Siesling)接着说:“这需要修复:所有革命中最小的, 但最重要的一次。”8 月1 日, 朱惠产下一对龙凤胎:一个叫“育伦”, 一个叫“育敦”。诗人用“你们”迎接了这对儿女;当他转头看向妻子, 就用“他”来代指儿子, 用“她”来代指女儿。一个最古老的代词, 一个最年轻的代词, 琴瑟和鸣, 就此分担了不同的语言学使命。西思翎还曾说:“创造这个字是诗人的无与伦比的职责。从字的所有意义来构想它。一首诗必须将这个字介绍到言语中,通过用它、重复它, 必要时重复它四次以给聋子的耳朵, 最终即使聋子的耳朵也会接收到。”9 月4 日, 诗人写出《情歌》。民谣有所谓“四季歌”, 绘画有所谓“四条屏”, 大都分述春夏秋冬情景。《情歌》也如此, 来读第一节:“天上飘着些微云, /地上吹着些微风。/啊!/ 微风吹动了我头发, / 教我如何不想她?”叙及春季相思, 或云早晨相思。来读第二节:“月光恋爱着海洋, / 海洋恋爱着月光。/啊!/ 这般蜜也似的银夜, / 教我如何不想她?”叙及夏季相思, 或云银夜相思。来读第三节:“水面落花慢慢流, /水底鱼儿慢慢游。/ 啊!/ 燕子你说些什么话? / 教我如何不想她?”叙及秋季相思, 或云午后相思。来读第四节:“枯树在冷风里摇。/野火在暮色中烧。/ 啊!/ 西天还有些儿残霞, / 教我如何不想她?”叙及冬季相思, 或云傍晚相思。从春季到冬季, 从白昼到黑夜, 无论何所睹, 无论何所听, 无论何所触, 百折千回, 千呼万唤, 无不曲径通幽于相思。全诗既有画面, 又有音韵, 画面有交替, 音韵有抑扬, 堪称尽善尽美。然则, 诗人在伦敦, 娇妻在怀, 娇女在膝, 谁会是那个“她”? “她”者, “故乡”也, “故国”也。1926 年, 赵元任先生为《情歌》作曲, 颇有舒伯特(Franz Schubert)之风, 很快传唱于四海, 或当留名于千古。可能正是赵元任, 将《情歌》改题为《教我如何不想她》。刘半农亦擅旧体诗, 1918 年, 他写出《听雨》:“我来北地已半年, 今日初听一宵雨。若移此雨在江南, 故园新笋添几许?”1925 年, 又写出《苏彝士运河》:“重来夜泛苏彝士, 月照平沙雪样明。最是岸头鸣蟋蟀, 预传万里故乡情。”刘半农诗集, 除了《扬鞭集》, 尚有《瓦釜集》。后者乃是依照江阴“四句头山歌”声调, 以方言创作的“拟民歌”。不但白话可以作诗, 方言也可以作诗——诗人以这种极端的试验, 交臂于胡适, 投身于白话诗运动, 被赵景深先生称为“中国Robert Burns(罗伯特·彭斯)”。诗人曾编成《初期白话诗稿》, 付梓于1932 年, 却没有收入自己的任何作品集。他的胸襟, 磊落如此。前面提到的周树人——也就是鲁迅——曾说:刘半农“是《新青年》里的一个战士。他活泼, 勇敢, 很打了几次大仗”。须知, 刘半农早年只读过中学, 却于1912 年扬名上海,1917 年执教北大, 1918 年参与成立 “小说研究所”, 收集 “歌谣”, 1919 年参与倡用“新式标点符号”, 1920 年命名“鸳鸯蝴蝶派”, 进入伦敦大学攻读“实验语音学”, 专文指导李大钊编排北大图书馆“新目录”, 1921 年转入巴黎大学, 向蔡元培提出《创设中国语音学实验室的计划书》, 1924 年出版 《四声实验录》,1932 年出版《中国文法讲话》和《中国俗曲总目稿》。所译《猫探》《黑肩巾》《欧陆纵横秘史》, 所辑所校所印《何典》《西游补》《太平天国有趣文件》, 林林总总, 大都风行士林, 甚而惠泽学界。1934 年, 诗人为绘制《中国方言地图》, 亲赴绥远, 魂断塞北, 诚可谓以身殉学者也。
郭沫若
郭沫若的第二部诗集《星空》, 出版于1923 年。诗人曾在卷首引来康德(Immanuel Kant)的名言:“有两样东西, 我思索的回数愈多, 时间愈久, 他们充溢我以愈见刻刻常新, 刻刻常增的惊异与严肃之感, 那便是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如果说“头上的星空”意味着神的秩序、外在的秩序;那么“心中的道德律”意味着心的秩序、内在的秩序。然则对这两种秩序, 郭沫若却似乎并无敬畏。他的第一部诗集《女神》, 出版于1921 年, 或可视为对“头顶的星空”的冒犯;第三部诗集《瓶》, 出版于1927 年, 或可视为对“心中的道德律”的冒犯。《女神》所录新诗, 起于1918年, 讫于1921 年, 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泰戈尔(Tagore)阶段、惠特曼(Whitman)阶段和歌德(Goethe)阶段, 可对应“五四运动”的前期、中期和后期。该书呈现了狂飙主义的萌动、勃发和低回, 其最高价值, 则在狂飙主义的勃发。“我虽然不曾自比过歌德,”诗人曾说,“但我委实自比过屈原。”屈原是个什么情况呢? 先读其《湘累》:“我知道你的心中本有无量的涌泉, 想同江河一样自由流泻。我知道你的心中本有无垠的潜热, 想同火山一样任意飞腾。”这是女须说给屈原的知心话, 当然, 这个屈原正是郭沫若的化身。再来读《天狗》:“我是一条天狗呀!/我把月来吞了, / 我把日来吞了, / 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 / 我把全宇宙来吞了。”——此之谓对“头顶的星空”的冒犯, 当然, 也不妨解读为对“旧秩序”的冒犯。还可参读《立在地球边上放号》《晨安》和《凤凰涅槃》。狂飙主义的极致, 就是玉石俱焚。接着读《天狗》:“我剥我的皮, / 我食我的肉, /我吸我的血, / 我啮我的心肝, / 我在我神经上飞跑, / 我在我脊髓上飞跑, / 我在我脑筋上飞跑。”这样的“生理学排比”, 这样的夸口, 这样的任性, 这样的失控, 这样的装疯, 这样的寒热病, 读来令人忍俊不禁, 今天或已很难求得诗人所谓“振动数相同”或“燃烧点相等”的读者。然而, 谁也不能否认, 单就新诗而言——早在20 年代初期,郭沫若就是最凶猛的一个先锋派;正如20 年代中期, 鲁迅先生亦是最凶猛的一个先锋派。郭沫若单凭一部《女神》, 就好比一部《巨人传》, 已然呈现出丰富而复杂的若干种形象——如果起用政治史解读, 他是一个嗅觉灵敏的革命者;如果起用思想史解读,他是一个莽撞的启蒙者;如果起用文学史解读, 他是一个从头新到脚的立异者。诗人响应了马克思主义、列宁和日本左派思想,孳生了零传统自觉, 囫囵带来了泛神论(Pantheism)——他用古语集来的一副对联, “内圣外王一体, 上天下地同流”, 可以直接诠释这个术语, 而不必引来他曾提及的“三个泛神论者”, 亦即战国的庄子、荷兰的斯宾诺莎(Spinoza)和印度的伽皮尔(Kabir)。综上可知 《天狗》或 《女神》的意义在于——从 “文体”的角度讲, 首次创造了真正的 “新诗”:一种自由、开放、错落、复沓和华彩的“新诗”;从“主体”的角度讲, 首次创造了真正的“新我”:一个暴躁、凌厉、张扬、冲动和狂热的“新我”。来读《女神之再生》:“姊妹们, 新造的葡萄酒浆/ 不能盛在那旧了的皮囊。/ 为容受你们的新去创造个新鲜的太阳!”也许郭沫若早年的旧句, “神州是我我神州”, 已将个人之“新我”等于中国之“新我”。来读《凤凰涅槃》:“我们更生了。/我们更生了。/一切的一, 更生了。/ 一的一切, 更生了。/ 我们便是他, 他们便是我。/我中也有你, 你中也有我。/ 我便是你。/ 你便是我。/ 火便是凰。/ 凤便是火。/ 翱翔!翱翔!/ 欢唱!欢唱!”单从“诗”的而非“五四运动”的角度来看, 也许, 《炉中煤》和《夜步十里松原》比前引作品都重要;这且按下不表, 却说姜涛先生论《女神》, 认定此书既是“新诗合法性起点”, 又是“生活构想和自我构想的指南”, 似乎已在很大范围内成为一个共识。《女神》的压轴诗, 亦即《西湖纪游》, 就像是预告了《瓶》。《瓶》所录新诗, 起于1925 年2 月18 日, 讫于3 月30 日, 大致也能分为三个阶段——盼信阶段、收信阶段、阅信阶段, 可对应“西湖情史”的前期、中期和后期。该书呈现了洛丽塔情结的萌动、勃发和低回,其最高价值, 则在洛丽塔情结的低回。那时纳博科夫(Nabokov)正在柏林, 还要等30 年, 他才会在巴黎出版小说 《洛丽塔》(Lolita)。郭沫若的“洛丽塔”, 乃是一个女学生, 他们的足迹遍于放鹤亭、抱朴庐、宝叔山(应为宝石山)、宝叔塔(应为保俶塔)、白云庵、孤山及灵峰。因而杭州和西湖, 也便相当于歌德的赛森海姆(Sesenheim)。在此以前, 诗人先娶张琼华, 后乱佐藤富子;在此以后, 诗人再娶于立群。《瓶》乃是组诗, 《献诗》而外,正文有42 首。来读《献诗》:“我爱兰也爱蔷薇, / 我爱诗也爱图画, /我如今又爱了梅花, /我于心有何惧怕?”——此之谓对“心中的道德律”的冒犯, 当然, 也不妨解读为对“旧道德”的冒犯。故事的结局充满了反讽, 这个女学生, 反而执意于对“旧道德”的盲从。来读第42 首, 诗人引用了她的来信:“我今后是已经矢志独身, / 这是我对你的唯一的酬报”。你说, 这不是害苦了人吗?诗人还曾撰有书信体中篇小说《落叶》, 互文于《瓶》, 两者都有受到日本“私小说”的影响, 只不过前者采用了“少女视角”, 后者采用了“中年男性视角”(先后被对方称为“先生”“你”和“哥哥”)。《瓶》之价值, 仅次于《女神》, 两者都演示了歌德的名言:“永恒之女性/领导我们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