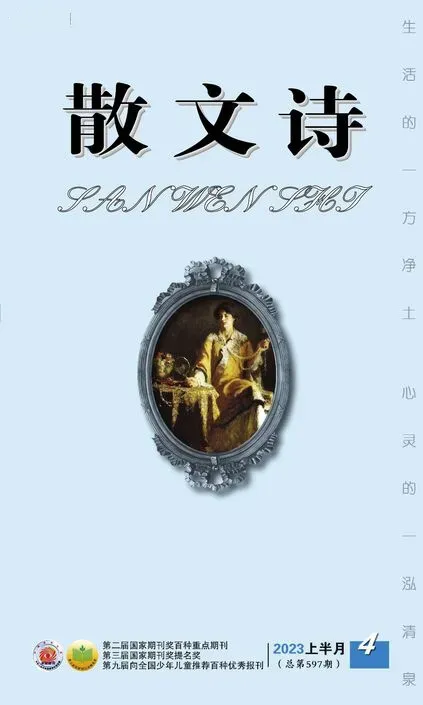但少闲人
◎焱 引
卷 帘
丝绸建起的房子里, 卷帘是最坚实的防盗锁。向微风贡献一些雕纹华饰, 归家的黄雀就不再沉溺于追求月亮。
每一次摇动, 都是对几株伏于墙角的草苗的陪伴。而更多的时候, 一只误入的蝴蝶借着垂帘, 静静地窥视着我。我因此注意到了窗台一角的面包屑, 也因此习得以某种倾斜度, 改变我过分耿直的眼神。
曾经, 那被悬束于高阁的帘角装饰也这样凝视我。它们褶皱出一张沉默的脸。可我长期低头写字, 未必懂得欣赏穿上纱裙的蓝天。
有许多挂扣生锈了。我必须去惩罚吊钟于此的失声。窗边的桂花树也是不能幸免的, 花蕾仍然缺乏坎坷, 没能挽留蒸干水分的花香。
唯有那对经常从窗户外头朝我微笑的老夫妇应当被赞扬——那位靠轮椅行走的老爷爷, 卷帘擦过他眼角的时候, 总有一双手开始流露温柔。
于是, 我决心练习抬头。不仅为了把帘拉成某种值得审美的角度, 更渴望将恰到好处的阳光分享给这个小书房。
独 居
字不见了。我从来舍不得忘记的。但确实不在那个地方了。
所幸月亮还舍不得把灯关上。挂掉忙线的电话, 才听见门被轻轻叩响。恰好二更时分, 不多不少。就像心跳的节奏, 不缓不急。
我们都知道什么叫做无用功。
假如, 春天可以和秋天重叠在一起呢? 当飞鸟躺在花海里吮吸山捻子, 害相思病的爱侣互相为对方准备惊喜。或许, 我也不至于失眠。
邻里昨日捡回来的野猫估计是睡了。我记得他们家的鱼缸摆得很高, 那一尾鱼儿总睥睨地看着我, 优雅地用凤尾扫掉我的想象。
楼下的小孩肯定又闯祸了。最后一声哐当过后, 风停了。
都怪我过分平庸的厨艺, 以及演技。既不敢邀约那个躲在角落里的少年, 也无能逗他开心。逗哏不适合我, 捧哏也是。我斗胆能学习一下如何写剧本。
不必去照镜子。那上面全是尘。
重 读
重读一本书, 不仅是重新命名某个颠沛流离的人物, 更是对某种记忆的删繁就简。倒叙, 推翻, 断裂, 新生。丰满更多的经验, 飘荡更自由的随想情思, 顺便与一个毫不奔疲的灵魂静坐。
甚至不必发言。不必与所谓的作者对话, 不必为进一步表达而陈述。
倾听即可。
听作者, 听主角(假如有), 听自己。听其言语。尽管这依然无从帮你领悟某种崇高的旨意或达地知根的本质, 但你依旧能够抓起一支墨香的笔, 慢慢研磨它的耐心。
某日, 我又试图从古希腊剧院的出口默看起风沙的路。双目虽没陷入光的诱惑, 却依然感到刺痛, 宛如某个彷徨多年的王子,一直不能寻到区分深邃与激情的法则。但彼此依然需要踏上征途。
所有因自己曲折的意义, 所有因自己注释的方向, 都在穹宇的赤黄染色瓶翻倒瞬间, 遮盖住自身赤裸的细节。为此, 我不再寻找更多诠释重复的借口。在某段静谧中, 我只能读出那么一两个字, 不纠结, 也并非荒谬, 我的影子在书内书外反复出逃。
可是, 就算我不去追赶它, 它也会逐渐在徘徊中自我觉醒:伪设糊涂, 并且不对他者罔置一词。
书本渐渐凸起皱痕, 可我早忘了重构一盏幽冷的晚灯。切勿来质询我, 为何出演着昨日的戏, 笔尖却绘着明日的诗。
观影:谢幕
我在那束光线的折返中, 抓住了不一样的形式。有过那么短暂的一瞬, 电影按下了定格键, 某一句台词跳出命运。过程十分简单, 只不过是利用镜片的伤痕, 顺便用绳子绑紧了突兀醉倒的闪光灯。
每一位观众都习得评论的主体性, 证据是前一位布置命题的评论家失联。错误是允许被宽宥的, 或许我也应该习惯于, 在暂停后继续播放之时, 帮某只迷途的小猫合上双眼。我是早就了解的, 生锈的机械韧带, 褪色的银幕斑痕, 只是, 还有一些疑问,在于爆米花融化的时候, 它们选择了怎样的姿态?
所有的眉蹙或微笑都是编织的, 正如所有的粗糙手艺都将被后来者反复革新。但我依然把握住了某一瞬自然的停顿。
——实心的句点。顽固而不肯让步。
终于, 幸存一道迷途的射线, 封堵住了台词最后的字眼:谢。
“谨对以上工作人员表示鸣谢”。
替来者留下命题的时候, 剧情内容早已从我的记忆细胞中分解。推开门, 一道道光开始了它们的交互工作, 过程中, 只留下一些不起波澜的轻尘。
对于某一部电影, 我无从得知那些以往或将至的风骨。我唯能做的, 仅仅只是念着自己的名谓, 并且孑然行走于落日余晖。
木 舟
在这近乎干涸的湖, 划桨成为一种悬念。
游荡久了后, 朽木早已分不清楚, 名曰“航行”的尺度。身旁, 有黑天鹅飞走, 有翎羽揉进淤泥, 还有一个用作坐标的凸物。但并没有一个人, 选择荡舟。
因为翅膀与雨云都是奢侈的, 木头的迟钝便取得了占有一艘舟的合法性。如今, 这片命悬一线的浮叶, 看着这些愚钝的孩子,与残疾的湖面对饮, 与棱角的沉铁比硬, 还肆意地将蠢动的尘屑,一层层剥离。
它所能够尝试的, 只剩下浮荡, 而意义仅仅是维持一副被沾湿的躯干。
毕竟, 这木舟曾如此匮乏重量, 甚至在一尾鱼撞入骨头的时候, 遗落一根穿透咽喉的长钉。
直到一轮月亮, 鳝一般将其捆绑。
于是, 疯狂踉跄。在吹拂的风和树丛间沉默的头颅面前, 它只能借助嘶哑, 来幻想艰难扭转朝向——可这几乎濒临瘫痪。最后, 独剩下一根龙骨, 支撑着一直不见弯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