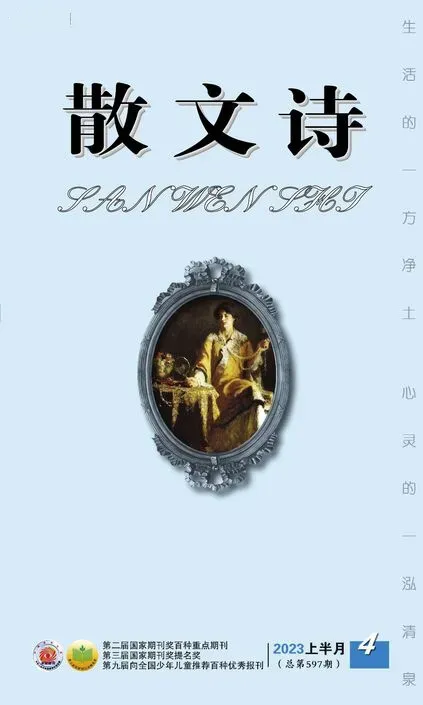润泽路上
◎黎 杰
堵
润泽路是一条短巷。
很短。风从东头来, 摩托车从东头来, 人力三轮车从东头来,共享单车从东头来, 轿车从东头来, 城里人从东头来, 乡下人从东头来, 这些, 全都堵在西头。
西头卷起尘土, 西头在建。
阳光不挤, 阳光是拐角擦鞋摊上方的一块遮阳布。
坐下来歇歇。
米粉店人满为患, 面馆还打着烊, 小五金店摆上了人行道。
行道树叶一枚枚落, 日子一枚枚落, 今天和昨天重复着, 叠加着。
不是每一个脚步都有计步器计着数, 脚步匆匆。
润泽路前身是一个田坝, 我们走过的地方, 就是一条茅草小径。如今道路硬化了, 溪水流不过来, 巷子有些堵了。
门虚掩着
门, 虚掩着。
店铺里寂静无声, 一个安静的正午, 润泽路的店铺都虚掩着。
突然想起乡间午后, 满村只有一只柴犬在吠着, 只有一只蝉在嘶叫着, 其它的都闭了眼, 在睡觉。
很闷的, 我想敲开风的一条缝, 让阳光挤进来。
我突然记不得我要买些什么了。
虚掩的门毫无心机, 此时, 有一只麻雀在店门前下水道口啄食陈年往事。我大概记起我是来买一包盐或打一壶酱油的, 我们的生活总缺点味儿。
店主人去哪儿了? 店门形同虚设。
在门前徘徊, 我不敢上前去, 敲, 或者推, 都将让寂静的润泽路受惊。
事实上, 我不知道被这门拦在外面多久了。
唱歌的小巷
小巷在唱歌。
第一支歌是卷闸门唱的, 店主的哈欠声是长长的过门儿。
第二支歌是洒水车唱的, 一句歌词没唱完, 洒水车就开过了巷子。
第三支歌是清洁工唱的, 扫一下, 唱一句, 直到车流人流盖过来, 歌声才小了, 但从没停止。
清洁工的歌声最嘹亮, 她唱的是山歌, 唱着唱着, 就会把人带到曾经的乡村, 带回曾经的童年, 带去月亮里的外婆桥。
润泽路上的这支歌, 都听得懂。
擦皮鞋摊
拐角处, 有一个擦皮鞋专摊。
一个人走过来, 又有人走过来, 他们在擦皮鞋摊前, 停下,看看自己的皮鞋。
看一个人走过来, 看又一个人走过来, 擦皮鞋的女人, 她的目光, 不看人, 只看路过的人脚上的皮鞋。
拐角处, 人流量大, 总有人停下来坐坐。
不擦鞋也坐坐, 累了也坐坐。
鞋擦起来了, 我注意到, 擦鞋的女人把那么多的阳光都涂在了鞋子上, 鞋擦亮了, 鞋上有光了, 满条街都整洁、光明了。
我还注意到, 鞋亮了, 那双擦鞋的手却黯淡了下来。
我伸出的脚不禁又收了回来。
修 补
润泽路需要修补了。
润泽路从小路变成大路再硬化后, 就不堪承受了。
就如到了春天, 两排行道树都需要修枝。
曾经的小溪堵了, 下水道疏不通夏日暴雨淤积的怨气。
围栏扎起来, 工程车轰轰地响。围栏拆掉, 润泽路就宽了,就如春天把行道树一修枝, 整条路就更亮了。
润泽路一宽, 阳光就跑进来;阳光一跑进来, 生活就沸腾;生活一沸腾, 满巷子就长出春天般簇簇的鸟鸣了。
慢生活
从东头入, 从西头出。润泽路, 短得只有一米阳光的距离。
逛润泽路, 只有慢下来。
就如行走在巷子里的阳光, 在润泽路上没有留下刻度。
行道树中有一棵银杏树, 长得很高, 长得很慢, 叶一直青着,绿着, 我一直都在盼望着秋天叶黄, 就如我盼望迎娶我的新娘一样, 我在巷子东头准备钻戒, 再走到巷子西头准备婚房, 这一来一去, 已然用掉了我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