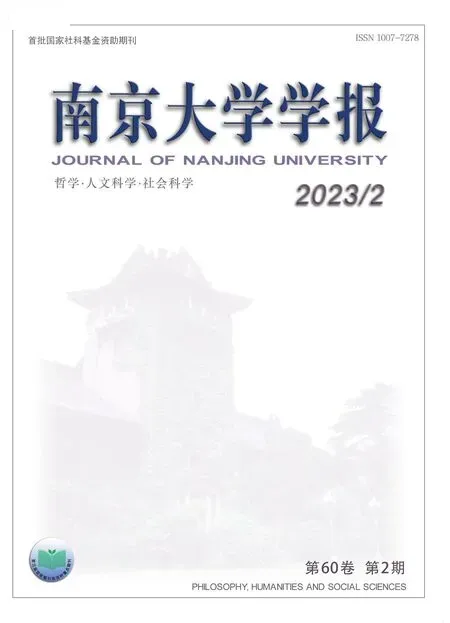“丑感”批判与审美感性共同体实践
——莫里斯的艺术社会主义思想探析
林 瑛 杨金才
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的作家、艺术家、商人、社会主义者的多元身份是积极反思、介入19世纪英国资本主义现代文明危机的结果,其在各个领域的成就沉淀了其匡正成果。作为作家,莫里斯的创作涉及诗歌、小说、散文等多种文类,著述颇丰,皆间接或直接地关切19世纪英国现实。他曾在1877年被牛津大学提名继任“牛津诗歌教授”(Oxford Professor of Poetry);更在1892年丁尼生去世后,被提名继任“桂冠诗人”(他因自己的社会主义信仰拒绝了这一头衔)。作为艺术家,莫里斯被认为是晚期拉斐尔前派的代表人物,创作的作品《美女伊索尔特》(LaBelleIseult)现珍藏于泰特现代美术馆。作为商人,莫里斯先后开办了“莫里斯、马歇尔与福克纳公司”(MMF)与“莫里斯公司”(Morris &Co.),设计生产了大量的墙纸图样、彩绘玻璃等工艺美术作品留诸后世,至今仍给予后人美的灵感与启发,他因之被尊为“现代设计之父”,深刻地影响了欧洲大陆以及美国的工艺美术运动。他还开办了“凯姆斯格特出版社”(Kelmscott Press)并发起了私人出版运动,致力于传承中世纪的传统书籍制作艺术并以之对抗欣欣向荣的现代出版业。作为社会主义活动家,莫里斯活跃于维多利亚晚期的英国社会主义运动之中。1877年莫里斯第一次发表公开演讲,这标志着他的思想开始呈现社会主义转向。1883年莫里斯加入“社会民主联盟”(Social Democratic Federation),正式成为一名社会主义者。因政见不和,他又在两年后退出,在恩格斯的支持下与马克思的女儿埃莱诺(Eleanor Marx-Aveling)、女婿爱德华·埃夫林(Edward Aveling)组织成立了新的社会主义团体——“社会主义者同盟” (Socialist League)。莫里斯不仅是同盟最重要的经济支持者,而且还担任同盟机关报《公共福利》(TheCommonweal)周刊的主编。1890年莫里斯离开同盟,创办“汉默史密斯社会主义协会”(Hammersmith Socialist Society),毫不妥协地继续追求其社会主义理想。
莫里斯的社会主义思想脱胎于英国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暴露的全方位的现代文明危机。19世纪末自然环境的恶化与艺术品位的降低促使莫里斯关注社会主义事业内的生态问题探讨,他透过社会问题探讨力图探触症候背后资本主义现代文明危机呈现的以“丑感”为突出特征的总体性堕落。受19世纪社会主义思潮兴起的影响,在个人化的探索与实践过程中,莫里斯的社会主义思想兼得了文学意识、审美态度与政治表达,致力于以艺术改造社会,以审美重塑共同体,在社会主义思想谱系中独树一帜。然而,本文所用的艺术社会主义概念并不单指他在艺术领域的种种见解与实践,更意在透视他如何通过艺术创作和艺术观念的演进阐释理想社会的面貌。本文试图揭示莫里斯对资本主义现代文明危机反思与匡正的深层政治美学逻辑,论证理想社会之所以理想的马克思主义内核,从而明确莫里斯在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中的历史地位。莫里斯张举“次要艺术”,开启共同体集体感性之重新分配,促成了审美平等。凝结于手工艺中的“日常生活的艺术化实践”,重构了个体与集体的感性世界,通达个体与共同体的自由与解放之境。这既是审美感性共同体实现的一种方式,同时也是莫里斯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兑现。
一、丑感批判:问诊资本主义现代文明
莫里斯所处的维多利亚时代是英国历史发展中的重要转型期,高速发展与社会危机并存。一方面,人们习惯用“进步”来定义这个时代,“人口大量增长,帝国的建立以及社会改革的施行都使得维多利亚人认为他们生活在一个前所未有的进步与变化的时代”(1)Beth Palmer,Victorian Literature: Texts, Contexts, Connections,London: York Press, 2010, p.7.。另一方面,维多利亚时代的伦敦又常被喻为巴比伦、庞贝,“人们或是害怕,或是希望,或是期待这座伟大的帝国之都也终有一天会倒下,化为尘埃。……伦敦也会陷入混乱和永夜,远古的过去将在遥远的未来重现”(2)阿克罗伊德:《伦敦传》,南京:译林出版社,2016年,第486页。。这种矛盾的复杂况味,再现了维多利亚人在经济繁荣表象下心理深层的焦虑与不安。1848年革命星火燎原,席卷欧洲大陆,唯有英国因经济繁荣避免了革命的发生。然而,与经济繁荣伴生的是另一种危机:贫富差距扩大,阶级矛盾尖锐。恩格斯历时21个月实地考察了英国工人阶级的生存状况,认为工人阶级已经被置于“不能生存的境地”,与“谋杀”无异,“英国社会每日每时都在犯这种被英国工人报刊合情合理地称为社会谋杀的罪行;英国社会把工人置于这样一种境地,使他们不能保持健康,不能活得长久;英国社会就是这样不停地一点一点地葬送了这些工人的生命,过早地把他们送进坟墓”(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09页。。面对繁荣与危机并存的时代,19世纪中期的维多利亚知识界百家争鸣,寻求延续国家繁荣以及规避潜在危机的途径。阿诺德(Matthew Arnold)认为,“整个现代文明在很大的程度上是机器文明,是外部文明,而且这种趋势还在愈演愈烈……在我国,机械性已到了无与伦比的地步……世上没有哪个国家比我们更推崇机械和物质文明……对机械工具的信仰乃是纠缠我们的一大危险”(4)马修·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政治与社会批评》,北京:三联书店,2012年,第12页。。莫里斯认同阿诺德对现代文明的批判并沿用了“现代文明”这一用词,在《我怎样成为了一名社会主义者》中,莫里斯直抒胸臆:“我一生最为痛恨的就是现代文明。”(5)William Morris, “How I Became a Socialist,”The Collected Works of William Morris Volume 23,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279.他与“现代文明”第一次有意味的遭遇须追溯至第一届世博会。1851年万国工业博览会在伦敦开幕,全世界的商品汇聚于水晶宫。马克思、恩格斯在《国际述评(三)》中论及博览会,他们认为:“世界资产阶级以这个博览会在现代的罗马建立起自己的百神庙,洋洋自得地把它自己创造的神仙供在这里。……资产阶级庆祝它的这个伟大节日的时候,正是它的整个威严快要丧失,从而将非常明显地向它证明,它所创造的力量如何摆脱它的控制的时候。”(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503页。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博览会的商品拜物教本质,并预言了商品与技术将异化于生产者、创造者的趋势与危机。对于17岁的莫里斯来说,他尚无法在深层逻辑层面对资本主义“水晶宫”进行理论透析。然而,他却以艺术家对于审美的直觉,同样对水晶宫做出了总体性的把握。在莫里斯看来,水晶宫是维多利亚时代现代文明的整体视觉性呈现,他直观感受到了一种“绝妙的丑陋”(wonderfully ugly),并因之以拒绝进入表达个人态度。“丑陋”,不仅是莫里斯对于现代文明的直观感受,也是其对于现代文明后果的论断与批判。艾柯指出:“整个19世纪都被两种力量的冲突搅动着:一边是为工业革命兴奋的人,革命激发出铁和玻璃的新建筑;另一边的人既以传统价值之名,又以新审美鉴赏之名,拒斥这些技术革新。”(7)翁贝托·艾柯:《丑的历史》,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第346页。在这两者之间,莫里斯倾向于后者。莫里斯尚无法理论性地把握博览会背后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性问题,却由艺术家的审美直观,以感性拒斥表达了对于现代文明之“丑陋”后果的激进态度。莫里斯这一意味深长的逸事也预示了其未来一以贯之地将审美追求与政治探索相统一的行动路径。丑感批判是莫里斯现代文明反思的起点,是其政治美学实践的发轫之处。
莫里斯清晰地界定了“丑陋”。在《今日的艺术与工艺》中,莫里斯指出:“如果没有艺术,人类劳动所生产的产品都是丑陋的。我使用丑陋时,使用的正是它在英语中最最简单的词义。”(8)William Morris, “The Arts and Crafts of To-day,”The Collected Works of William Morris Volume 22,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357.莫里斯意在使用日常的、去形而上的词汇与词意表达对于现代文明的感受。莫里斯又随之以“对美的否定”(negation of beauty)、“无艺术的人类劳动”(non-artistic human work)扩大丑的内涵,意图在树立丑与美的直接对立、非此即彼之中激发感性,并借由感性唤起大众的反感共鸣,构建批判的集体感性域。丑感批判既是对以水晶宫为象征的公共空间之丑陋的反感共鸣,也下沉至日常生活空间,由之展开了一个关涉日常生活方式的文化向度的批判。在《生活中的次要艺术》中,莫里斯批判了如陶器、玻璃制品、布料等日用之物之丑陋。莫里斯认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一半乐趣已经丧失了,“生产丑陋的陶器是我们文明最杰出的发明”(9)William Morris, “The Lesser Arts of Life,”The Collected Works of William Morris Volume 22,p.242.,丑感以具体的存在方式充斥着维多利亚时代的日常生活空间。
在莫里斯看来,如果艺术与工艺不美,即是“蓄意的丑陋”(actively ugly)。“蓄意的丑陋”激发出了莫里斯丑感批判由表及里的纵深度。在莫里斯的理解中,“丑陋”是作为表征的丑陋,其背后是19世纪英国资本主义现代文明危机的深层动因。在《纹样设计的启示》《财阀统治下的艺术》中莫里斯都将“不道德”与“丑陋”并用(base and ugly)。丑陋所联通的不道德,并不仅仅是个人的行为规范,还是维多利亚时代的总体性问题与结构性堕落。莫里斯认为:“现代工业所生产的皆是丑陋。”(10)William Morris, “The Revival of Handicraft,”The Collected Works of William Morris Volume 22,p.336.在他看来,如果劳动无法使工人产生感恩之情与愉悦之意,就等同于对工人的压迫(11)William Morris, “Art, Wealth and Riches,”The Collected Works of William Morris Volume 23,p.151.,因而必然生产丑陋的产品。故而,“蓄意的丑陋”在根本上源自资本主义下资本家与工人间不道德的阶级剥削与压迫。
莫里斯并未将维多利亚时代的丑感批判止步于现代文明,而是追根溯源,在现代文明呈现的丑感图景背后看到了阶级压迫,因而更加深刻地把握了维多利亚时代繁荣与危机并存的社会表征。莫里斯在《艺术与社会主义》中对维多利亚时代做出了“艺术饥荒”(famine of art)的诊断:“现代文明世界,由于急于获得一种分配不公的物质繁荣,完全压抑了人民的艺术;或者换句话说,使大部分人民享受不到艺术……人民在现代文明世界……失去了为人民所创造并为人民所享受的艺术,并因而失去了劳作的天然慰藉。”(12)William Morris, “Art and Socialism,”The Collected Works of William Morris Volume 23,p.192.“饥荒”是大部分人的饥饿,是人民大众对于艺术的匮乏与缺失。如此一来,“艺术饥荒”之本质即为维多利亚时代阶级不平等的政治问题蔓延至艺术领域的结果。因而艺术饥荒不只是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问题,还是资本主义所必然携带的政治问题的美学表征。1883年莫里斯在写给《曼彻斯特观察家》(TheManchesterExaminer)编辑的信中说道:“如果我们不去弥合贫富之间的鸿沟,大众艺术不会带来健康的生活状态。”(13)Norman Kelvin,The Collected Letters of William Morris, Volume Ⅰ 1848-1880,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p.173.在此时,莫里斯已经明确地将政治关切与美学主张等而视之,延伸出了艺术中的政治批判与实践维度。莫里斯的政治观与其艺术观共享相似的共同体意识与革命性。正是在艺术中,莫里斯寄寓了匡正维多利亚时代丑感图景的政治理想。
二、从“艺术家”到“手艺人”:正名次要艺术
艺术史研究通常认为在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阶层才真正产生。“在古代和中世纪,绘画、雕塑和建筑及其从业者的文化和社会地位通常都很低下。三门艺术不仅被归为技术性和体力性的技工艺术,且附属于其他主要技工艺术,在知识体系中缺乏独立的位置。相应地,画家、雕塑家和建筑师也通常被视为卑微的体力劳动者和手艺人,处于社会等级的底层。”(14)刘君:《从手艺人到神圣艺术家: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艺术家阶层的兴起》,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363页。然而,莫里斯在1877年的第一次公开演讲中却说:“曾经一度,世界熟知手工技艺的神秘与神奇,人们制造的东西中充满想象力;在那个时代所有的手工艺人都是艺术家。”(15)William Morris, “The Lesser Arts,”The Collected Works of William Morris Volume 22,p.9.莫里斯刻意否认了艺术史事实,认为在中世纪时手艺人都是艺术家,旨在解构艺术家与手艺人的二元对立,从而颠覆社会阶级观念,促成共同体的审美感性交织,表达了融合于其艺术主张中的激进的政治美学观。
在莫里斯看来,“真正的艺术是人在劳动中的愉悦之表达”(16)William Morris, “The Art of the People,”The Collected Works of William Morris Volume 22,p.46.,在《生活中的次要艺术》中莫里斯又说,“我所指的艺术是人通过调动感官,诉诸情感与思想的创造”(17)William Morris, “The Lesser Arts of Life,”The Collected Works of William Morris Volume 22,p.235.;因而,“艺术的目的即为增加人的幸福感”(18)William Morris, “The Aims of Life,”The Collected Works of William Morris Volume 23,p.81.。莫里斯关于艺术的定义强调了“人”与“感性”。事实上,这一对于艺术的定义是最为正统的对于美学的定义:鲍姆嘉通美学自发端之时便是以张扬感性为其定位,“审美对象不是别的,只是灿烂的感性。规定审美对象的那种形式就表现了感性的圆满性与必然性,同时感性自身带有赋予它以活力的意义,并立即献交出来”(19)米盖尔·杜夫海纳:《美学与哲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28页。。
在莫里斯看来,“次要艺术”(the lesser arts)是能够承载审美感性的艺术形式。次要艺术以陶艺、玻璃制品为最重要的形式,主要包括造房工艺、木艺、铁艺、陶艺、编织技艺等起装饰、美化与完善作用的艺术形式。次要艺术多以手工完成,因而是“审美愉悦的表达”(20)William Morris, “The Lesser Arts,”The Collected Works of William Morris Volume 22,p.8.。鲍桑葵(Bernard Basanquet)认可莫里斯对于次要艺术与感觉的关联:“生活中日用的次要艺术在一个小的规模上提供了答案,然而这个答案却是正确而深刻的。内容所以能进入制作品中,是因为它存在人身上,而且是深深地存在人身上。”(21)鲍桑葵:《美学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583页。译文有修改。在莫里斯看来,次要艺术因手工艺的使用而直接地联通了感官,张扬人之主体性,实现了以艺术再现感性之美的审美理念,手工艺人也在这一纯粹美学的意义上应当被视为艺术家。
然而,令莫里斯担忧的是次要艺术在维多利亚时代已经堕落。莫里斯认为维多利亚时代的次要艺术“渺小、呆板、愚钝,无力抵抗时尚与欺诈的压制”(22)William Morris, “The Lesser Arts,”The Collected Works of William Morris Volume 22,pp.3-4.。“时尚”与“欺诈”影射的是维多利亚时代的机器生产与艺术品复制的历史语境。维多利亚时代艺术品已经进入了机械复制时代,艺术受到了来自摄影技术的竞争,“19世纪中期产生了一个真正的革命现象:由于技术和科学发展,创造性艺术的某些作品有史以来首次可借由技术手段进行复制,不但价格低廉,而且规模空前”(23)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资本的年代:1848-1875》,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331页。。产品的生产境遇与此相仿,机器制造以其绝对的价格优势压制传统手工制作,艺术品的光环渐渐褪却。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莫里斯将手工艺人提升为艺术家,呼唤艺术家回归手艺人的审美初心,具有了更为迫切的现实意义。
莫里斯认为“手工艺的堕落是生活的堕落”(24)William Morris, “The Revival of Handicraft,”The Collected Works of William Morris Volume 22,p.336.,因而他对次要艺术寄予厚望。“次要艺术”的命名沉淀了莫里斯的批判立场和革命态度。莫里斯在第一次公开演讲中就以“次要艺术”为主要论题。这篇演讲在莫里斯全集中被取名为《次要艺术》而传世。事实上,这篇文章最初以小册子传播时名为《装饰艺术》。莫里斯在这篇文章中也多使用“装饰艺术”,而尚未形成次要艺术的完整表述。“次要”一词多作为形容词,用以描述装饰艺术的“次要”处境并予以批判。在1882年《生活中的次要艺术》中,莫里斯开始广泛使用“次要艺术”这一提法。莫里斯将政治追求与艺术实践统一的政治美学实践使其在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对立中捍卫被压迫的工人阶级;也使其在建筑、雕塑、绘画等辉煌的“大型艺术”的光芒之外,将弱势的次要艺术挖掘出来,“在很多时候或者说在绝大多数时候,我们对装饰艺术熟视无睹,我们认为它们是自己生长起来的,就像我们用木棍生火而毫不留意木棍上的青苔”(25)William Morris, “The Lesser Arts,”The Collected Works of William Morris Volume 22,p.4.。莫里斯的艺术社会主义立场使其认为工人阶级中蕴含着巨大的能量,也使得他相信在次要艺术中蕴含着美学的抵抗与解放能量。次要艺术凝结着劳动者的主体性与自由意志,是民主政治秩序的呈现方式,次要艺术又因其在日常生活中的使用,可以让艺术之光照亮为数更众的普通人民,是社会主义政治实现的一种方式。这样一来,莫里斯打破了大型艺术与次要艺术或者说纯艺术与实用艺术之间的审美体制,搅动共同体的集体感性之重新分配。只有当艺术家成为手工艺人时,才能够实现审美感性的复归,抵抗机器制造的奴役,让艺术进入人民大众的生活方式之中,从而实现艺术为人民的目的,艺术家也回归于人民大众之中。
三、人人都是“艺术家”:重构感性世界
莫里斯的次要艺术所蕴含的政治美学价值不仅仅在于审美平等的达成,更在于其对个体感性世界的激活,以及其间蕴含着建构审美感性共同体的可能性,其艺术观在席勒游戏说基础上,内蕴马克思感性活动的人的主张,呈现了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底色。
席勒的审美游戏观中蕴含着日常生活中艺术乌托邦的超脱之境。席勒认为,人性具有感性冲动与理性冲动之分,然而现代文明“不仅使社会与个人、而且使个人本身发生了严重的分裂。一方面是科学技术的严密分工,另一方面是复杂的国家机器造成职业和等级之间的严重差别,从而使人性发生分裂,人失去了内心的和谐与完整性”(26)蒋孔阳:《德国古典美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81页。。为了复归感性冲动与理性冲动的统一与和谐,达到理想的人性,席勒提出了“游戏冲动”,他认为:“只有当人是充分意义的人的时候,他才游戏;并且只有当他游戏的时候,他才是完全的人。”游戏冲动平衡了感性冲动和理性冲动,并在这种过程中创造了美,“事物的实在性是(事物)自己的作品,事物的外观是人的作品;一个欣赏外观的人,已经不再以他所接受的东西为快乐,而是以他所创造的东西为快乐”。因之,席勒的审美游戏观中蕴含艺术乌托邦的超脱之境:“在力量的可怕王国的中间以及在法则的神圣王国的中间,审美的创造冲动不知不觉地建立起第三个王国,即游戏和外观的快乐的王国。在这个王国里,审美的创造冲动给人卸去了一切关系的枷锁,使人摆脱了一切称为强制的东西,不论这些强制是身体的,还是道德的。”(27)席勒:《审美教育书简》,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年,第48、85、95页。在席勒看来,正是在审美的游戏实践中蕴含着挣脱现代性束缚的解放力量。莫里斯推崇的“次要艺术”与“手工艺”的自由之境与席勒这一审美现代性观念高度契合。莫里斯的艺术观同样扎根于日常生活,在莫里斯看来艺术应像食物一样日常、一样必需。事实上,莫里斯主张艺术进入日常生活,重塑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文化并非仅仅是“日常生活的艺术化”,而且更深入地呈现为“日常生活的艺术化实践”。
莫里斯“日常生活的艺术化实践”在实用与审美之中连接了实践的维度,是马克思哲学新世界观在日常生活中的政治美学实现路径。正是在日常生活的艺术化实践中,人人都可以是艺术家。与传统形而上学只追求现象背后之超感性领域的思考路径不同,马克思哲学不再在观念与观念的逻辑推演中将哲学困于纯粹思辨的领域,而是回归实际生活,由之提出了实践的思维模式,将社会、历史、实践和现实的人等因素并置于研究视野中。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马克思由此把思维从彼岸世界拉回至此岸世界,强调在现实实践中把握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强调行动对人之认识与把握世界的意义。因之,马克思哲学所关注的人既不是以往哲学中抽象的、思辨的人,也不是费尔巴哈“抽象着存在”的感性的人。马克思说:“费尔巴哈不满意抽象的思维而喜欢直观;但是他把感性不是看做实践的、人的感性的活动。”(2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00、501页。故而,马克思关注的“人”是“感性活动”的人。在莫里斯看来,手工艺之所以能够成为对抗时间的艺术品,正是由于其创造过程凝结了劳动者的感性生命,“因为从一开始,它们内部即具有灵魂、人的思想”(29)William Morris, “Art and Socialism,”The Collected Works of William Morris Volume 23,p.197.。每个感性生命都是唯一的、各异的,艺术的价值正在于它闪耀着劳动者差异化的感性实践。这一蕴含马克思主义解放与自由思想的艺术观呼应着马克思的政治美学观,威廉·莫里斯等人“已比康德、席勒、谢林、荷尔德林和黑格尔更清楚地认识到,真正的革命不光是宪政和治理形式的转变,更是对感性世界的重构,而后者要求我们将艺术的形式转化为生活的形式。对于他们而言,艺术革命中隐含了更彻底的政治革命”(30)陆兴华:《艺术—政治的未来:雅克·朗西埃美学思想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3页。。在莫里斯看来,除了重构个体感性世界,次要艺术的政治美学价值蕴含着建构审美感性共同体的可能性。莫里斯认为,次要艺术无法摆脱与艺术传统的关联,“一个人,无论多么具有创新精神,当他坐下来想要绘制一幅桌布纹样,一个器皿的器形,或者设计一件家具时,也不过是数百年前纹样的一种发展或者倒退”。然而,置身机械复制时代手工制品面临的生存危机之中,莫里斯哀叹道:“这些纹样在过去或许是某种崇拜或者信仰的神秘象征符号,只不过现在已经鲜少被人们记得或者已悉数尽忘。”(31)William Morris, “The Lesser Arts,”The Collected Works of William Morris Volume 22,pp.7-8.莫里斯因而呼吁复兴手工艺,回望手工制品自身传承的制作技艺,保护并延续寓于其中的文明传统。莫里斯将视野完全打开,跨越了民族、国家的藩篱,站在人类历史的总体性高度,阐发了次要艺术对于感性世界重构而通达的审美感性共同体:
这些艺术,如前所述,是人类伟大的美之愉悦表达系统的一部分:所有的人在所有的时代都曾使用过它们;它们曾给自由的国家带来快乐,也曾给被压迫的国家带来安慰;它们被宗教使用过,升华过,也曾滥用过,堕落过;它们与整个历史紧密相连,并且曾为其明师;更重要的是,它们是人类劳动的甜味剂,不仅是对于将生命投注到其制作中的手工艺人来说,亦对于广大人民。广大人民在一日劳苦之后看到这些装饰艺术便将受到影响,它们使得我们的劳作可得幸福,我们的休息可得充实。(32)William Morris, “The Lesser Arts,”The Collected Works of William Morris Volume 22,p.8.
概言之,在次要艺术中,手中制作的艺术之“物”得以显现,并以其显现牵连、映射出创造者的感性生命,因而在次要艺术中交织着的是融汇感性生命的历史,是“鲜活”的人类历史。21世纪的物质文化研究在鲍德里亚、法兰克福学派的声音之外,发现了物与人的另一种关系,手工制品中能够承载人与物的亲密关联,“手工业文化的产品以中间人、斡旋者的面貌出现,这些产品超越了直接实用性,具有自身的份量,自身的生命,自身的含义。它们具有自身的属性。这些属性使它们能够成为具体时空的结晶体,成为充满着意义和感性的结构,可以栖息之所”(33)阿尔布莱希特·维尔默:《艺术与工业生产——论现代和后现代的辩证法》,周宪编:《文化现代性读本》,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33页。。莫里斯已经超前性地让“物”或手工制作之物显现,试图摈弃商品内蕴的资本主义商业逻辑,尽可能使商品以“物”的形式显现,重构了物与人之间的体贴关联。于是,次要艺术便借由“物”的共同体之表象呈现了一个审美感性的共同体。
无独有偶,朗西埃继莫里斯之后仍在关注审美共同体的形构。他的着眼点在于建立某种艺术审美体制,即发现人民这一主体。这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莫里斯的审美共同体思想。莫里斯早就说过:“我不想要只为少数人的艺术。”(34)William Morris, “Art and Socialism,”The Collected Works of William Morris Volume 23,p.197.在莫里斯审美感性共同体的政治美学实践中,每一个感性活动着的实践的人都是艺术家。次要艺术的审美体制构建了审美感性共同体是莫里斯对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想象方式与实践路径。正如朗西埃所指出的:“一座缺损的雕像,如何成为一件完美的作品……一件家具,如何被尊为一座神庙……这种种的转型,并非来自一些个人的凭空幻想,它们的逻辑,从属于一个认知、情感、思考的体制,这个体制,我便称其作‘艺术的审美体制’。”(35)雅克·朗西埃:《美感论:艺术审美体制的世纪场景》,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12页。
在《浪漫主义者到社会主义者》中,汤普森提到一个细节,在莫里斯演讲过后,来自另一党派的一位女士问谁是莫里斯,福克纳礼貌地答复了她,她继而反问道:“是诗人吧,我想,不是社会主义者?”福克纳这次厉声地回复道:“莫里斯如果不是社会主义者怎么可能是诗人?”汤普森评论道:“直到莫里斯去世时,他的政敌与批评家仍然坚持把作为诗人的莫里斯与作为社会主义者的莫里斯区分开来看。”(36)E. P. Thompson, William Morris: Romantic to Revolutionary,New York: Pantheon, 1976, p.360.事实上,只有把作为诗人、艺术家与社会主义者的莫里斯等而视之,莫里斯寓于艺术中的抵抗活力才能够得以发现。莫里斯接受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并以乐观的态度预见未来,莫里斯希望艺术能够在革命中承担它的责任,因为艺术可以“拯救无知与少智带来的损失……艺术可以复活一些传统,拯救过去的记忆,从而不至于当新生活到来时,人们要为新的时代精神创造全新的艺术形式”(37)William Morris, “The Lesser Arts,”The Collected Works of William Morris Volume 22,p.26.。
1932年徐朗西在《艺术与社会》中指出“改造社会的方法,可概别为三类:(一)道德的改造,(二)科学的改造,(三)艺术的改造”(38)徐朗西:《艺术与社会》,上海:现代书局,1932年,第1页。,并在“艺术社会主义”一章介绍了莫里斯。莫里斯一生的多元身份与多元实践始终关切艺术与社会这一议题,致力于以艺术改造社会,以艺术创造美好生活。然而,“要真正理解‘艺术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必须克服两元对立的认识论或反映论的传统思维方式。从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思维方式出发,将人、历史、社会、文化、艺术(在本质上)理解为一种实践的存在——亦即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存在论的视域和立场出发来看待、理解和解答‘艺术与社会’的问题,才可能真正凸显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的革命性意义”(39)宋伟:《艺术与社会:重新关照百年中国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的总体性与问题域》,《艺术百家》2021年第2期。。莫里斯正是在这一现代性批判与人类自由解放的哲学与美学境域中发挥了艺术介入社会的功能。
维多利亚时代令莫里斯忧心忡忡,他担忧“荷马的位置要被赫胥黎取代”,担忧资本主义文明使工人沦落为“骨瘦如柴的可怜存在”。然而,莫里斯并不认为艺术是一个被动的客体,在他看来“在艺术的疆域里,人们能真正实现一种充实的、公道的理想生活。一种可以欣赏美、创造美的生活,享有真正的愉悦。这些对于人来说本来就应该像日常食用的面包一样必需”(40)William Morris, “How I Became a Socialist,”The Collected Works of William Morris Volume 23,p.281.。莫里斯从丑感批判到审美感性共同体实践的过程,是对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批判以及其社会主义政治理想的实践过程。莫里斯激进的政治思想沉淀于凝结了日常生活的艺术化实践的次要艺术与手工艺中。每一件由手工制成,凝结了劳动者感性活动的物品都是艺术品,故而,人人都可以是艺术家。次要艺术中无阶级差别的实践实现了莫里斯的审美感性共同体,兑现了其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马克思的同时代人,莫里斯内化了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思维模式,其艺术社会主义思想响应了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是对于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的历史性实践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