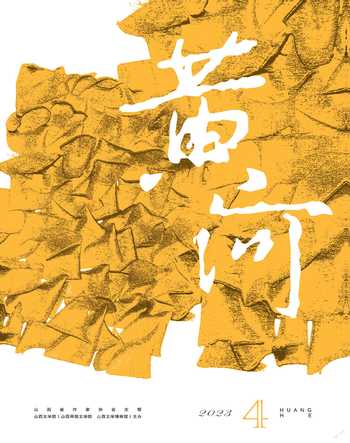一朵秘色花
草白
缘起
很多年前,我在一间叫“南方嘉木”的茶馆里第一次听闻“秘色瓷”。它让我想到的不是瓷器,而是某种模糊、氤氲的色彩,由于年代久远,其来源、配方均无从考证。由此,我想起桃花水母,想到一種叫朱的吉祥鸟以及《山海经》里远古时代的动物。直到有一天,我来到浙江松阳,站在一个研制秘色瓷的工匠面前———他叫刘法星,这也是北斗七星第二星天璇的别名。这位以星为名,学过木雕、黑陶,曾走街串巷卖过画,也给寺庙做过佛像的手艺人,有一天忽然跑到龙泉,成为工艺美术大师徐朝兴的关门弟子,一门心思做起青瓷来。
在龙泉,有人和刘法星谈起一种叫“秘色瓷”的东西,他被图片里器物青绿莹润的光泽所打动,耳边好似响起山涧清泉,声清冽而朗润。
谁也没想到这位生活于二十一世纪的工匠,毅然离开黑陶和青瓷,去研制这种流传于九至十一世纪的器物,为着那种内部空寂、注定会破碎的东西,日日夜夜,好似入了魔怔。
雨过天青,秘色归来
“那一刻,我感到自己的身体好像要蹦起来———”2022年6月的某一天,年届花甲的陶瓷艺人刘法星讲起2017年1月7日那个遥远的早晨,忍不住嘴角上扬,深黝的脸庞浮现出泉水般清澈的笑容。
他的家乡丽水松阳县,古属处州。彼时,龙泉青瓷窑也在处州境内。宋人庄绰编著的书目中记载,“处州龙泉县多佳树,地名豫章,以木而著也……又出青瓷器,谓之‘秘色”,———尽管龙泉也出秘色瓷未必可信,但由此似可推测出龙泉窑也烧制过胎质细密、釉色翠碧的越窑青瓷。
刘法星记忆中的2017年1月是个罕见的暖冬。冬至过后已十七天,最低气温仍维持在十度以上。近似深秋。晚唐时,匠人烧制秘色瓷的主要时间也在秋天,“九秋风露越窑开”,气候干燥、柴禾充足,正是烧窑好时节。那天,刘法星像往常那样来到成型车间准备开窑,经过一天一夜的冷却,窑温已降至可开启状态。不知为何,这一次,他竟有些莫名的紧张与慌乱。当他打开窑门,往里张望一眼,瞬间懵了。那一刻,他脑子里一片空白。棚板上的瓷器居然呈现出日思夜想的光泽,神秘,幽远,恍惚,一种失传近一千两百多年的颜色就在眼前,就像湖底沉睡千年的宝物忽然浮上水面。
几分钟后,他以十二分的小心拉开窑车,动作缓慢、轻柔,生怕眼前的器物不翼而飞。但这一次与以往任何一次都不同,他唤醒了它们———那些诞生于晚唐五代时期的陶瓷,釉色温润、静穆雅致,就在他触手可及处。那一刻,他错以为它们来自同一片晚霞与星空。过去十几年里,梦里梦外,他无数次地见过它们,脑海里全是那青色恍惚的身影。吃饭、睡觉时,他都在琢磨着如何接近它们。为了那件出土于黄岩灵塔寺的越窑青瓷熏炉,他在浙江省博物馆待了足足一个礼拜;至于临安博物馆,更是去过无数次,闭着眼睛也能想起那只越窑青瓷褐彩云纹熏炉,它出自钱之母水邱氏的墓地,炉内仍有残存的香灰,似乎还能闻到晚唐空气里那一缕神秘的幽香。这些博物馆里的旧魂灵一度成了他魂牵梦萦之物。
现在,雨过天晴,它们循着火光回来了。刘法星取出窑腔上层、离他最近的那只天青色茶盏,瞬间,温热的气息在掌间蔓延。他放下这件,又拿起另一件,双手在杯、盏、盘之间勾留。眼前出现一片氤氲的湖面,烟云弥漫,他想起家乡境内穿城而过的松阴溪,也想起大木山和双童山。“湖山蔼蔼旧相识”,如今,它们都落在这一件件新出炉的器物上。
这一天,距离2003年第一次烧制越窑秘色瓷,已过去十四个年头。五千多日夜,六百多道配方,千余次试验,诞生了六万余件、堆积如山的废弃胚体。其间,他卖掉五套房子,每天除了六小时睡眠,便是夜以继日的工作;当身体陷入魔怔状态,他早已与手中的瓷泥合二为一。他不去想过年的餐桌上有没有肉,也不去想那些怎么也无法还清的债务,任脑子里装满釉水配方,无数种组合就像沸腾的茶汤,随着时间流逝不断有东西析出。他既是手艺人,更是冒险家,世间万物都要经过严格淬炼才能呈现耀眼光华。秘色瓷从原料、素胚到上釉后的瓷体,要经历三次烈焰烧灼。最后一次,更要从0度升至1300度左右,历经脱水期、氧化期、玻化期与保温期,这既是泥与火的艺术,也是毁灭与重生之旅;是天人合一,是物之生生不息的轮回。对此,人们只能做笼统而抽象的概述,具体的成型过程,与火焰有关的秘密,谁也无法说清。任何微小的纰漏,偶然的过失,不经意的动作,都可能功亏一篑;而结晶、缩釉、气泡、开裂等等,更是寻常事件。
很多时候,刘法星感到秘色瓷就隐藏在眼前的火焰中,窑火灭后,便会自动呈现。夜深人静,家人早已熟睡,他还坐在窑门前守望。无论窗外是冰天雪地,还是凉露侵衣,在烧制车间,一年四季都闷热如煮,都是夏天。
在遇到秘色瓷之前,刘法星迷的是良渚黑陶,那是另一段没日没夜的烧制之旅。他感到自己的身体里有火焰,也有水。他不断取出体内的火焰,又取出水。饶是如此,也无法平息内心的风暴。他的双手停不下来,需要不断地去制作什么来获得平静与满足。行家对他黑陶作品的评价是:沉静洗练,高古幽远,意境苍远而不阴晦,手法老练而不失新润,堪称一绝。
他毅然从黑陶的七彩光芒中走出,去寻找处州大地上的秘色之光,他相信那种东西的存在,就像相信晚唐的天空里一定有鸟飞过。
痴人与梦
相传宋徽宗做过一个梦,梦到“雨过天晴云破处”,梦醒后,他下令工匠烧制这种颜色。这便是汝窑瓷器天青色釉的由来。秘色瓷的诞生是否与梦境有关,我不得而知,但后人孜孜不倦地研制这项失传技艺的行为本身,倒近乎痴人与梦的关系。
松阳县处州古窑瓷研究所,一处位于松阳县郊的院落,既是陶瓷匠人刘法星的工作室,也是他的家。当传说中的秘色瓷摆在眼前,我几乎有些不敢相信。如果说秘色瓷的颜色是天空与湖水的颜色,那么世人所见的湖水与天空,原本就各不相同。刘法星研制出的秘色瓷,色呈青、黄、灰,胎质细密如玉,釉色温润似璧,通体洋溢出一股氤氲的气息。
随着1987年法门寺地宫的开启,消失了上千年的秘色瓷重见天日,玲珑的器形与釉色让人惊叹。人们随即发现,即使对照博物馆里的馆藏,唐代诗人徐夤在《贡馀秘色茶盏》里的描述也是如此精确。诗歌讲述的不过是诗人某日偶得一只秘色茶盏,且是进贡所余之物,但在他眼里,那一只被挑剩下的秘色茶盏已然是“明月染春水”“薄冰盛绿云”之类的尤物。
“贡馀”之物尚且如此,又遑论真正的进贡之品。唐代文学家陆龟蒙更以秘色瓷器来抒写胸中块垒,“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如果夜半之时,在秘色瓷碗中盛上浅浅的露水,便可以陪着嵇康将杯中的残酒饮尽了。诗人让秘色瓷碗与竹林七贤的酒杯遥相应和,此情此景,又该是何等销魂。
一千多年来,人们对何为真正的秘瓷之色浮想联翩,刘法星于反复烧制中形成了独特的秘色谱系,“我不让它偏离青、灰,青灰既是主题,也是感觉”。青灰色调中,青为冷色系,灰是中色调。淡淡的灰中似藏有七彩虹霓,而青之所指似乎更为复杂———苍、蓝、碧、翠、绿等都可归为“青”之囊中。青为东方之色,是《千里江山图》的颜色,更是江南三月江水的色。
刘法星研制的秘色瓷为纯哑光釉,青灰色调———青中泛灰绿,绒光,玉质感,低饱和度,让我想起乔治·莫兰蒂的画。没有大亮大暗之色,是晴朗天气里的晨曦照耀,也是旧时纸窗里透出的曲折微光。
这样的哑光,含蓄蕴藉、沉静内敛,不以大面积反射自然光线为目的;这般器物自出窑那一刻起,便像是从光阴深处走来,宛如古玉之五色宝光———那是来自时间深处的包浆。
成功研制出哑光秘色瓷后,刘法星又千里迢迢赶去西安法门寺博物馆,得以抚触千年前的秘色瓷器,尤其是那只玲珑剔透的葵口盘,灯光照射下,盘内似含着一汪清幽的泉水。最终,由这汪“清幽的泉水”,他研制出半哑釉色。
刘法星认识到所有釉色都为生命之色,它们是流动的,鲜活的,就像奔泻的山泉。不同光线下,它们会产生迥异的色泽,以至于当同一器皿出现在不同天气、时辰里,就像出现无数个分身,让人惊叹。
西安法门寺内“触手可及”的秘色瓷记忆,一直留存在刘法星的脑海里。关于手与眼,到底哪个才是创作的主人,他说不清。他只知道那些来自唐朝的器物并非全无瑕疵,比如有些器物的底部有缩釉,或青或白,色泽不一;如果以放大镜视之,还能发现局部釉内有大小不一的气泡。或许,正是这些瑕疵打动了他,好像只有如此才能表明它们也是由人创造出来;一千多年前的无名工匠与他一样都是凡胎肉身,他们在青山绿水间练泥、修胚,轻揉慢捻,夜以继日地工作。千年前的秘色瓷入乎自然草木之中,又超乎其上,通体清亮,气息雍容,给人以古玉的温润华滋感,好似刚刚离开工匠们的柴窑,晶莹的釉面中还隐藏着自然的幽微与宁静。
法门寺回来不久,刘法星去了慈溪上林湖后司岙秘色瓷窑址。在那里,他捡回一些唐、五代時期的瓷片。让他颇感意外的是,遗址内的秘瓷之釉色居然如此丰富,有天青、月白、象牙、金褐等色,细腻光滑,呈半透明状,且器型不一。走在布满瓷质匣钵和碎瓷片的湖畔之路,他常有一种穿越之感,己身化作千年前烟熏火燎的窑工,在上林湖畔沉思与劳作。随着湖面上升,当年的部分窑址已没入水中;潺潺溪流之中,碎瓷布满溪底,泛着玉石般莹润致密的光泽。而未没入水中的部分,也已被荒草树木所覆盖。
陆羽选茶具,认为如冰似玉胜过类银似雪。刘法星的秘色瓷虽为一次施釉,但釉层厚薄适宜,釉面气泡小而密集,呈现润泽如玉的质感。玉质感的产生还与釉料配方有关。无灰不成釉。北方的汝窑以玛瑙入釉,但无具体工艺流程传世;而越窑釉灰的炼制工艺虽有详细记载,但近代匠人很难完全复原其中精粹。
刘法星所研制的秘色瓷,其釉料成分就有岭根釉土、紫金土、草木灰、谷糠灰等数种配料,整个烧制过程可谓“千锤百炼”。尤其是不可或缺的草木灰,最好选有机草木灰、茶秸秆草木灰等传统配釉材料。即使同为紫金土,也要根据颗粒粗细、是否耐高温、与素胎是否吻合等情况,一一试验烧制,来选出最优组合。单一材料尚要经如此精挑细选,遑论组合之后的调整、删选、优化,以及与具体瓷土的结合,无数种可能性都要一一排演,依次试验,可以想见其中的繁复与艰难,类似于科学家所做的试验,千回百转,山穷水复。
为了寻找适宜的原矿粉料和釉料,刘法星的足迹遍布景德镇、龙泉、宜兴、佛山、淄博等地。他经常在找到原矿釉料后,组织工人上山开采与搬运。从材料到成品,从瓷土、原矿釉料到釉土矿粉,多少道工序,多少次配釉、试釉烧制,以及无数次的高温保温氧化还原,才最终烧成那一只只釉面青碧、晶莹润泽的秘色瓷器,宛如一面宁静的湖水,或一方幽深的湖泊。
这一个个秘色瓷碗,看上去如此孤寂,宛如从时空深处穿越而来,需要一个人以全部心力去聆听、凝望与审视。
盲盒开启,波诡云谲
对刘法星而言,每次开窑,宛如开启盲盒,也像等待彩票开奖。在窑门打开之前,一切都是未知。这份未知,年复一年地吸引着他。每一次,于他都充满期待,都像是第一次。
晚唐、五代时期,秘色瓷在烧制时并不直接接触炉火。一器一匣,被装入瓷质匣钵中,并以釉浆密封,使之受热均匀,避免釉面被二次氧化成偏黄色调。窑门打开的刹那,并不能即刻看见,需敲开匣钵,才拨云见月。那是古老的柴窑时代。现代气窑因能准确地控制烧成曲线,保证了窑温的可控型,使得秘色瓷的烧制工艺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中之一便是匣钵的弃而不用。
刘法星并不神秘化柴窑,他知道柴窑的好处,更明白它的局限。他使用气窑已经多年,用着也顺手,关键是可以提高效率,一个人守着也不累。五六天一循环。今日入窑,要后天早晨才能等到窑熟。窑门打开的刹那,他的心脏总会按捺不住地多跳几下。与别的瓷器相比,秘色瓷胎釉结合紧密,少有开片现象。如果开窑后,听见一记细微的“叮”声,八成是某处瓷裂了。那时候,他的心头就会紧一紧,又多了一件瑕疵品。可也有意外之喜,如果“窑变”恰到好处地发生了,便能将普通器物上升为艺术品。它是水土所合,也是时间与温度魔力的体现,非人力之巧所能为。这样的情况刘法星遇到过几次,但可遇而不可求。问他如何解释窑变结晶现象,他想了想说,“这有点像煮米饭,煮熟后再焖一会儿,可能就发生了。”可是,需焖多久,气压及火力如何掌控,都无确数。也有可能,焖了也不成,或干脆焖坏了、烧焦了。宋瓷中的冰裂、蟹爪、牛毛、鱼子纹就是窑变的产物,尤其是冰裂纹,多么美,让人想起诗人北岛的一句话,“如今,我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梦破碎的声音。”陶瓷史上,哥窑的开片是绝唱,不断发生的碎裂声就像河面破冰、树木生长。在古时,窑变一度被视为不祥之兆,后来才被引为缺憾之美,获得文人艺术家的青睐。
秘色瓷的结晶窑变有点类似摄影师的失焦拍摄,没有固定焦距,成像后全然模糊。如此,或可成就一段意外之美,就像一次美妙的邂逅。选料、练泥、制坯、上釉、烧造……窑变的种子或许就藏在这其中任何一道工序里。刘法星给我们展示过他的“得意之作”,一只褐色八角盏,八个面,面面俱有风致,釉色好似自然流淌而成,有种水墨的氤氲感。釉俱五色,褐色之中藏着红、黄、蓝,藏着万千变化,宛如流动运行的水、轻盈缭绕的雾。若隐若现,灿若烟霞。再看,分明是波诡云谲,难怪朋友们都说,“可真是美啊,幸亏发生了窑变。”
刘法星热衷于试验与收集意外之喜。每一窑中,总有几样是他的试验品———瓷泥经过调整,釉料配方也是全新。他记下它们的耐温性、发色情况,以及烧制过程中形成的升温与降温曲线。那是一组神秘的线条,宛如数学中的抛物线,每一弧度都蕴藏着万千变化。他已成功试验出一百五十多种配方。整个烧制过程,便是不断发现秘密、并揭开秘密的过程。
从无到有,再到隐匿不见,任何器物的诞生,都遵受空寂之道,并因此而涵纳万物。秘色瓷来过了,消逝了,如今又被人试了出来。就如上林湖的水下遗址被淹了,退回到历史的深渊里,谁也不知哪一天又将重见天日。
开出一朵秘色花
它们是一朵朵花。看着这些造型不一的秘色茶盏、杯子、碗碟,就像看着自然中的各色花卉。不是浮花浪蕊,是葵花、菱花、荷花以及海棠花,属古典中国里的二十四花品。这些花口杯盏,造型古雅,气息淳朴。面对如此茶器,宛如面对山河故人。一室一物,一边一隅,取其精华,慢慢融于现代空间之中。如此,日常生活才生出隽永之心、缱绻之心。既有茶香之美,也有器物之美,前者源于云雾山涧,后者采自草木矿物,千锤百炼而成。
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秘色器大都为圆器,雍容、古雅、大气,为唐人审美典范。而刘法星所研制的秘色瓷,造型多变,多为花口杯盏。那几乎是另一种圆,是“圆”上所作的增与减,虚实凸凹,似断实连,最终拢成一个浑然、质朴的器型。
清茶一盏,知己二三;室内洁净无尘埃,茶器温润无贼光;看杯中峰峦叠翠,听耳畔山风浩荡。这便是最良的辰、最吉的日,也是最好的清供。
那一只只师法自然的茶盏、茶杯与碗,既可品茗,也能饮酒。既可日用,也能珍藏。刘法星的故乡丽水松阳———有卯山、大木山、双童山,产卯山仙茶、银猴、玉峰,鲜碧的叶子藏于山谷深处,藏在“云深不知处”里。
独山是松阳城里唯一的山,远归的游子一旦看见它,便是回了家。松古盆地之上,松阴溪一脉穿城,水绿如蓝,它就是王维口中的“清江”。那个叫“山·醺”的茶酒空间四面环水,可观云,可远望独山。白日饮茶,夜里对酌。同一空间,腾转挪移,合二为一。茶品有三,酒品不详。茶有山兰、山香和山红三种。其中,山兰为白茶,汤色黄亮,口感淡雅,平淡持久;山香为绿茶,汤若五谷之甘醇,山民常自饮之;而山红为红茶,汤色鲜亮,似有草木花香。
刘法星希望秘色瓷能走出典籍史料,走进寻常百姓人家,当茶盏、花器用,作日常陈设观赏用,也能在“山·醺”里供茶客品茗赏玩用。器物不仅是茶空间中的陈设品,更是口唇与手的触碰物,触感要细而润,上手摩挲时不感到棘或绊。那独特的秘色及花瓣造型,就像来自一个空灵世界。那个世界里的人,闲时松花酿酒,忙时春水煎茶,喝一口茶,看一眼云。山中一日,世上千年。秘瓷之色,实为山林之色,湖水之色,自然之色。想要获此色,似易实难。无数匠人于山水湖畔之中殚精竭虑,也未必能得,即使得了,总也差了那么一点意思。
刘法星以自然为灵感,大地为原料,不断试写新的釉料配方,以期接近那座真正的秘色宫殿。五代的盘子,唐宋的茶盏,上林湖畔的碎瓷片,他于残缺中寻求完整,在截面里发现真相。他就像一名心不在焉又踌躇满志的漫步者,不断寻找通往秘色王国的林间小径;它们荒废已久,又历时弥新,一切都让他感到有趣。
在松阳,像刘法星这样的陶瓷匠人并不多。这块土地,自古以来,多的是茶人。他们自己采茶、做茶,无事时相约一起喝茶;或以茶叶做菜、酿酒。在松阳,有个叫吴美俊的茶人,她采撷、收集高山上的古茶树叶,在自家后院的工作室里,手工揉捻、发酵、干燥。每次做茶期间,有邻人路过其家,总能闻到一股神秘幽香,还以为是茉莉、桂花或栀子的气味。他们不相信普通的茶叶能散发出如此幽香。吴美俊总是说,要顺着茶叶的性子来做茶,香味自然就出来了。经反复实践,她终于研制出属于自己的“仙芽”与“甘露”,其中有一款“宝珀玉露”,便是由松阳高山野茶发酵而成,色似琥珀而镶金边,清亮通透,口感醇厚,有草木清香。
如果将此琥珀色茶汤盛于莲花形秘色瓷盏之中,大概与古诗中所说的“玉碗盛来琥珀光”非常接近了。茶叶鲜叶在经杀青、揉捻、干燥等步骤后,于沸水中重新绽放。它活了过来,叶脉依稀、似隐若现,宛如春天山林的模样于茶汤中再度浮现。
刘法星所制的秘色瓷盏恰似一朵朵花,是葵花、菱花、荷花以及海棠花,叶与花俱为自然的面相,也隐藏着自然的密码。作为松阳人,刘法星喜喝本地土茶,拉胚、施釉之余,喝茶是唯一消遣,也是一天中最为惬意之时,万事万物都在脑海里自动遇合,或聚或散,无需理会。伴着茶汤写下的配方,宛如骤现的灵感。
与诗人、艺术家对灵感的处置方式同,手艺人的想法也需经过时间与火焰的双重检验,或许是更为苛刻的检验。晚唐、五代时的秘色瓷被工匠们小心翼翼、殚精竭虑地烧制出来,稍有瑕疵,便悉数尽毁。上林湖畔堆积如山的瓷片废墟便是明证。一千多年了,五彩碎瓷還铺满整条河床,那些明亮的锐角仍在持续不断地反射秘色之光。
事物的意义从来都是因破碎而彰显。真正的秘色瓷,那种流传于九到十一世纪的器物,其实很难被完全复制。天空、土壤、空气,都已不复当年,古老的河流也不可能流到今日的河床之上。
对于青瓷,我们总可以说出它的颜色———什么天青、豆青、粉青或梅子青,不过是表面施有青色釉的瓷器;只有焙烧不当时,才烧出黄色或黄褐色。但秘色瓷不同,人们很难说出它的真正颜色,秘色,还是蜜色?抑或蜜草色?蜜草大概就是甘草吧,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说它呈鲜绿或淡绿色。
刘法星认为秘色瓷是青灰色调,是青色大于灰色,还是相反?如今,那些制作秘色瓷的人早已将二十一世纪的气候、天色、心情都烧了进去,染上了今日之色。尽管法门寺地宫的“无中生水”可以得到复制,但属于唐朝的明澈与清亮感,早已一去不复返;这世上尽管也有“做旧感”这种工艺,但人们无法把古老的时间像金箔一样贴在器物表面。
这几日,院子里的荷花开了,闻着有股木头的清香,很像古老寺院里散发出的气味。我想起刘法星的莲花盏,也想起若干年前的夏天。此前,我一直琢磨着,何为秘色之光,此刻闻着荷花的气味,似乎有了模糊的答案。
很多年前,我去苏州博物馆,看到秘色瓷莲花碗,也只是看看,并没往心里去。
那时,我还不认识它,也没有留意“秘色”二字。如今再次想起,似乎有一种气息隔着几年前的玻璃展柜,准确无误地击中了我。书上说,我们所看到的星光可能是几万年之前的光———我不知这话想要表达什么,但莫名地被那种语气感动。
在广阔、无垠的时空里,有些东西因承载了世上一切美好之物而变得轻盈,它们会传播得很远,比我们想象中远。
责任编辑:李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