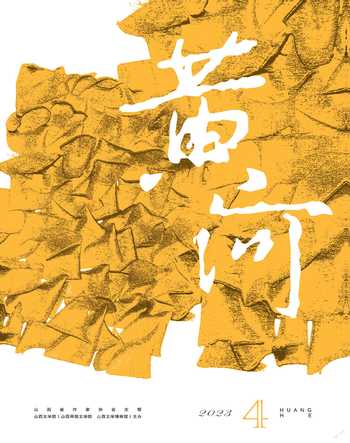风调雨顺的煎熬
王安琪
1
两户村的人谁也没想到豆瓣儿会做下那种事。
事情发生在一个风调雨顺的秋天。塬上很少有这种风调雨顺的时候,那一年偏偏就这么风调雨顺。
早些年,两户村实行了责任制。一觉醒来,土地分了,农具分了,牲口也分了,凡是原来集体的东西统统分到各家各户。当年被合作化的风刮走的东西,一夜之间又被相反的风刮回来。人们守着各自的土地,就像刚娶媳妇的汉子,不要命地摆弄它们。土地像受孕的女人,可着劲给人们生粮食———夏粮丰收了,秋粮丰收了。粮食顺着人们下地干活的那条路,排着长队回到人们的地坑院里,像一群识路的羊。
擀面条。人们说。
烙油馍。人们说。
白面条就油馍。他们说。
有几年,两户村的人生活得像天上的神仙。八碗一火锅,热腾腾的白蒸馍,神仙也就是这种日子吧。
突然有一天,吕满升他娃从城里回来,说,城里的钱就跟飘落的树叶儿一样,遍地都是,只要你肯弯腰,挣钱跟拾钱一样容易。走啊,跟我进城,拾他们的钱,就当是给城里打扫卫生呢。有人跟吕满升他娃进城了。很快,他们就知道城里人才真真是神仙呢,人家不光吃香喝辣,还穿金戴银,还有香车宝马,还住高楼大厦,人家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越来越多的人进城了。城市像个大风箱,吸走两户村的年轻人,旱塬上的地坑院像一个个破布袋,只剩下一些老得掉渣的人。
豆瓣儿还不算太老,可她是个寡妇。
村里人都还记得豆瓣儿她男人死时的情景。那年她家修院子,一块土坯从窑垴上塌下來,把她男人砸了进去。等人们把他扒出来时,人倒是囫囫囵囵的,却没气儿了。
豆瓣儿成了寡妇后,不少人打过她的主意,有人劝她改嫁,有人想占她便宜,但豆瓣儿却坚定地守着男人留下的破家烂院和不满周岁的女娃,磕磕绊绊地走在两户村的岁月里。白天,她和别的女人一样干活,到了晚上,便把是非闩到门外。所以,孤儿寡母十几年,却从没跟任何人生出过一枝一桠。可男人如天,豆瓣儿的天塌了,日月压着她,把她的身体和精神一天天压垮了。
2
刚过了霜降,接着就是一场连阴雨,墚墚峁峁都憋足墒气,等着人们种小麦。可风调雨顺却让豆瓣儿感到深深的熬煎———犁地种麦的时候,她发现她家没有牛。
分产到户时,集体的东西统统分了,只有牛没分。牛不是土地,不能切成一块一块的牛肉。所以,队里把牛作了价,谁家想要牛,就得把差价补出来。豆瓣儿拿不出那些钱,没有分到牛。有几年,她总是求爷爷告奶奶四处借牛,可今年连着好几天,她跑来跑去,连一根牛毛也没有借到。
年轻人都进城了,留守的人都忙着种自家的庄稼,谁还顾得上别人?
“刨吧。”豆瓣儿跟她女子小麦说。
“活人不能叫尿憋死,咱没牛,咱拿镢头刨。”她说。
这样,豆瓣儿就领着小麦上了鸡冠峁。
鸡冠峁上长着许多柿树,可豆瓣儿家的地头却长着一棵榔榆,没有叶子,就光秃秃的一个树干,像根棒槌插在那里,挂着一身脏不拉叽的干皮,远远看着,像一棵死树。可它不是死树,说不定哪一场雨后,就会冷不丁挤出几片叶子,炫耀似的顶在树干上。但现在什么也没有,毕竟时令已经是深秋了。
嗵,嗵,豆瓣儿和小麦在地里刨着。她们撅着屁股,像两头上坡的牛。有一些玉米秆被她们刨下来,还有一些,还有一些———它们愣乎乎地对着天空。
太阳在天上挂着,像一块风干的红薯,已经没有多少光气了。可人一干活儿还是会觉得热,汗水在她们屁股和背上溻出几片湿印儿,像补了几块深色的补丁。开始的时候,母女俩还并排刨着,后来小麦就落在后边。
小麦在看土里的一样东西,那是她弄断的一只蛾蛹。她知道这东西到了夏天就会变成蛾子,可现在它却像虫子。她把蛾蛹弄断时,似乎听到响了一声,脆脆的,像是折断一段草根。她看见半截蛾蛹在镢头处很痛苦地扭动着身子,冒着湿乎乎的血,像是谁往那地方吐的一口唾沫。看不清血的颜色,可她知道那就是蛾蛹的血。还有半截埋在土里,看不见,她知道土里头肯定还有半截。
人就像蛾蛹。小麦想,并不是所有的蛾蛹都能变成蛾子远走高飞,有些蛾蛹还没活到时候就被人弄死了,一把镢头,一张锨,碰一下就会把它碰折,像弄断一段草根。这样,它就永远被埋到土里。
这么一想,小麦就不想刨地了。她直起身子,拄着镢头把儿,一条腿绷着,另一条腿弓着,就是这么一种架势。她好像站得很费劲,比刨地还费劲。
豆瓣儿就这一个女娃。女娃生下来时,她男人说,就叫小麦吧。他们本来打算再生个男娃,名字都想好了,叫高粱,可男人早早就殁了,所以就小麦一个女娃。所以,她对小麦娇得不行。塬上的女娃也读书,一般到认得自己的名字就算了,可豆瓣儿却一直供着小麦,从小学读到镇里初中,读到县里高中。本来还要读下去,从县城读到市里,从中学读到大学,可小麦没考上大学,狗日的分数线像绊马索一样把她绊了一下,让她又跌到了两户村。这样,小麦就跟别的女娃很不一样。人读书多了,就会有些不一样,说不清哪里不一样。很多事情都说不清,但很多事情都摆在那儿。
小麦想过进城打工,可豆瓣儿没答应。家里还有几亩地,她拖着病恹恹的身子伺候不了。
他妈的。小麦在心里骂了一句。她不知道是骂谁,就是想骂一句。
后来,小麦看见豆瓣儿往嘴里扔了点什么。她知道那是盐。
塬上的人不吃盐面儿,他们吃那种一坨一坨的青盐。那种盐看起来潮乎乎、脏兮兮的,可他们就吃这种东西。他们说这种盐好,味儿重。别人吃盐是调味,豆瓣儿却是另一种吃法,跟吃炒豆一样,口袋里整天装着一把青盐,隔一会儿往嘴里扔一粒,嘎嘣嘎嘣,她嚼着吃。男人死后,她就开始这么吃盐了。吃多了,胃里泛酸水,噗,吐在地上,土被蜇得虚起老高。她知道这么吃盐不好,可就是管不住自己。
“我早晚要死到这上头。”豆瓣儿说。
“他妈的,我由不得我了。”她曾说,“我心里?惶。人心里?惶,就想吃点什么,随便吃点什么,心里就好受了。”
嗵,嗵,豆瓣儿刨着地。
嘎嘣嘎嘣,她嚼着盐粒。
“你别吃了,行不?”小麦喊了一声。
“我吃我的,又不耽误刨地。”豆瓣儿说。嘎嘣嘎嘣。
“下作样,我看不惯你那下作样。”小麦说。
豆瓣儿没抬头。嗵,嗵,她刨着地。嘎嘣嘎嘣,她嚼着盐粒。
老鼠,小麦想,跟老鼠一模一样的声音。她听不得这种声音,嘎嘣嘎嘣,像老鼠在一下一下啃她的膝盖。她忽然觉得膝盖那儿有些痛。
“老鼠。”她喊了一声。
豆瓣儿还是没抬头。她背了下身子,又摸出一粒盐扔进嘴里。好像有了一些顾虑,她不想跟小麦较劲。嘎嘣,她嚼了一下。过了一会儿,又嚼了一下,嘎嘣。她偷偷摸摸跟做贼似的。
小麦的脸慢慢变红了,变紫了,像熟透的茄子。青筋像几根蚯蚓爬在她鬓角那里,一会儿出来,一会儿进去。她觉得她要做些什么。
后来,小麦走到豆瓣儿身后,把手伸进豆瓣儿的口袋,往外一掏,口袋被带出来,那口袋就像豆瓣儿的胯骨上突然长出一块什么。几粒青盐掉下来,落到潮乎乎的泥土里,还有一些握在小麦手心里。她抡了一下胳膊,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见,但她知道那些盐已经被扔到很远的地方。
“你把我的盐撒了?”豆瓣儿说。她有点不相信她女子会这么做。
“我看不得你那下作样。”小麦说。
“盐又不是种子,你把它撒到地里?”她說。
“盐又不是粮食,你那样吃?”她说。
“我就这样吃。”豆瓣儿说。她从土里拣起几粒青盐,全都扔进嘴里。嘎嘣嘎嘣,她夸张地动着嘴巴,作对似的看着小麦。
“老鼠。”小麦说,“你是一只老鼠。”
“我是你妈,你这么说我?”豆瓣儿说。
“我就说。老鼠,你恶心人。”她说。
豆瓣儿一屁股坐到地上,呜哇呜哇哭起来,一边哭一边看着小麦,说不清是气愤还是难过。
“他妈的,我不干了。”小麦说。
她扔下镢头,朝那棵榔榆走去。树下放着一本书,她把书拾起来,夹在胳肢窝里,朝峁墚下边走去。
豆瓣儿看着小麦,看着她拐了一下,又拐了一下,拐进一条沟。沟沿如刃,一截一截地切着她的身子,那身子越来越短,越来越短,后来只剩下一个脑袋,像漂在河里的一个葫芦。后来,连脑袋也没有了,似乎一个大活人就这么从世界上消失了。
3
小麦回到家,她在窑屋里看了一会儿书,看不进去。书上的字像跳蚤一样上蹿下跳,弄得她身上刺痒。她走到院子里,想把院子打扫一遍。小麦是个爱干净的女子,她家院子从来都是干干净净的。可她发现早上刚刚打扫过,现在根本用不着打扫。再说,也不是扫院子的时候,已经过午了,谁家晌午还打扫院子?
后来,小麦看见窑垴上挂着几捆芝麻秆。芝麻早就收割了,可不知道为什么当时没把它们打出来,它们挂在窑垴上,像几捆黑黢黢的柴禾。
小麦把那几捆芝麻秆取下来,找了一张布单,把它们摊在布单上。不大一会儿,芝麻秆儿就被晒得刺棱刺棱响。她拿了一根棒槌,一下一下捶打它们。芝麻秆儿激动地跳起来,有几根粘在棒槌上,被她高高地举在阳光里。
嘭嚓,嘭嚓,就是这种沉闷干燥的声音,听起来让人心慌。
这日子。小麦心想。
嘭嚓,嘭嚓,她一下一下捶打着芝麻秆儿。
这日子就像这些芝麻秆儿,她想,干干的,没一点指望。
这么一想,就有一种委屈像泉水一样从小麦心里泛上来。她想,过些日子吧,过些日子一定得找个地方好好地哭一场。非大哭一场不可,不然的话,还活个什么意思。不然的话,还不把人活活憋死?
刚有这个念头,她心里那股委屈的泉水就朝着喉咙涌去,涌到喉头那儿,又分成两股,一股涌向鼻子,像醋一样把她的鼻子弄得发酸;另一股涌向眼睛,变成一些泪花花,虫子一样从她眼眶里爬出来。
哧溜,她抽了一下鼻子。
不打了,我一个人打个什么劲。她把棒槌扔到一边,又抽了一下鼻子。她就这么低着头,压抑地哭起来。
当时,偌大的地坑院里就小麦一个人,顶多还有一颗太阳和几捆芝麻秆,顶多还有她哭泣时发出的那种声音。
“有柿饼吗?”
小麦被吓了一跳。一个人正认真地做着什么,忽然听到有人在头顶处跟你说话,不能不被吓一跳。
她抬起头,看见一个男人站在窑垴上。
窑垴上有一棵老柿树,虬虬扎扎的,男人就靠着柿树站在那儿。他的鼻子有些高,而且红红的,看着像他脸上挂着一只辣椒儿。
“有柿饼吗?”男人说,露出两排友好的白牙齿,“我是收柿饼的。”
经常有那么一种人,冷不丁地跑到旱塬,收柿饼,收土槐籽。他们鼓捣这些东西,有时候也鼓捣塬上的女子。
哧溜,小麦抽了一下鼻子。她用手把脸上的泪擦了一下,擦去了一些,还有一些沾在脸上,她又擦了一下。她没有想到竟然流了那么多泪。
“你哭哩……”男人说。
“你看我……”男人很惭愧的样子,“我不知道你正哭哩……”
男人这么一说,小麦的眼睛就像泛泉水一样,又开始往外涌泪水。她本来觉得对着一个外人流泪不好,本来不想哭了,可那人一说话,她就忍不住了。
她不停地抽着鼻子。
“你看,我问有柿饼嘛,我又没咋着你……”男人的脸上有些挂不住。
“我没怪你。”小麦说,“这不能怪你,我自己心里?惶。”
“唉,人人都有一本难念的经。”男人说。
停了一下,男人又说:“我是说,谁都有?惶的时候。”
“你也?惶吗?”小麦说。
“我本来不?惶。你一说,我也有些?惶了……”男人说,“人就是这样,常常看不得别人?惶。”
“你别笑话我。”小麦说,“你看见我哭了,你可别笑话我。”
“我不笑话你。我笑话你做什么?人?惶了,就想哭一会儿。哭一会儿,心里也许就不那么?惶了。”男人说。
“你是好人。”小麦说。
“谁都有?惶的时候嘛。”男人说。
后来,他们都不说话了,就听得见芝麻秆儿被太阳晒得刺棱刺棱的响声。
“你说,人是咋来到这世上的?”小麦说。
“我妈说我是柿树上的看树佬儿变的。”男人说。他说着,抬头朝柿树看了一眼。
霜降已过,树上叶子已经掉干净了,树上的柿子并没有全摘完,还留着三两个,高高地挂在枝头,人们叫它们“看树佬儿”。人们说,树跟日子一样,得有人守着。
“你信吗?”小麦说。
“噢嘛,当时我信了。我去看过那棵老柿树,我想要不是我妈把我摘回家,说不定我早就叫老鸹叼去了。”男人说着,笑了一下,“我跟我妈说过这话,我妈光是笑。我不知道她为什么光是笑。我想我得对我妈好些,可是我妈没等我长大就去世了,我没对我妈好成。”
“你妈哄你哩。”小麦说。
“后来我才知道我妈哄我哩。”男人说,“你妈没哄过你吗?”
“哄过。我妈说我是从河滩里拾来的。”小麦说。
“大人们都这么哄娃。”男人说。
“你也这么哄你娃吗?”小麦说。
“我没有娃。”男人又笑了一下,“我还没有婆娘哩,咋会有娃?”
小麦不说话了,她咬了咬下嘴唇,露出一口又细又白的好牙。
男人看见小麦的牙。他想,干黄干黄的塬上,这女子咋会有这么一口好牙呢?
“你是个好人。你陪我说说话,我心里就不?惶了。”小麦说,“我说你是个好人。”
“噢嘛。”那人说。
“做什么,你说噢嘛?”小麦说。
“你说‘你是个好人,我就说‘噢嘛。”男人笑了一下。
“我不认识你,可我觉得你是个好人。”小麦说。
“你也是个好人。”男人说,“我知道你也是个好人。”
他们又不说话了。刚好有一只花尾巴鸟儿从他们头顶飞过,他们都仰起头看那只鸟儿。花尾巴鸟儿叫了一声,就一声,便箭一般射到远处。天上什么也没有了,只有太阳无声地筛洒着阳光。
“我能去你家喝口水吗?”男人突然说。
“我家里没人。”小麦说,“你别下来,你下来了,你就不是好人了。”
她说得很快,好像她不快些说出这些话,男人就会走下窑垴,进到她家院子里。
“你去别人家喝水吧。”小麦说。
男人的脸上有些失望,他站了一会儿,终于缓缓吐了一口气,慢慢转过身去,走了。窑垴像刀刃一样,一截一截地截着他的身子,很钝,但最后还是慢慢地把他截完了。
小麦的心里一下空了,她觉出了一些燥热,像肚子里的东西都变成汗水跑出来。她走进灶火屋,守着水缸喝了一大瓢水。凉水通过她的喉咙流到肚子里,一路行踪清晰可辨。
水缸里映出小麦的眉眼,慢慢地,她觉得水缸里的那个女子实在太亏屈了。
突然,小麦扔下水瓢,风一样地刮出院子,风一样地朝窑垴追去,听到肚子里的水咣当咣当地响。
“哎。”小麦喊了一声。
男人停下,转过身来。他想,说不定她改变了主意,说不定她会请我去她家喝口水呢,他就在路边站着,等着小麦请他喝水。
“你是个好人。你记着,我说你是好人。”小麦说。可她没有请他。
“你走吧。天不早了,你去别人家喝口水,就赶紧走吧。”小麦又说。
男人笑了笑,小麥看见男人也有一口好牙。
“你家有柿饼吗?”男人说。
“噢嘛。”小麦说,“你等着,你在鸡冠峁上等着,明儿个我给你送去。”
小麦一说完,就知道自己这么说不好。这话她刚才就想说了,可她刚才把自己管住了,后来一不小心,这话就像兔子从她嘴里跑出来。人有时候就是管不住自己。小麦不明白为什么她没把自己管住。
男人认真地点了点头,转身走了。他走得很肯定。
4
“嗬嗬。”有人在远处笑了一声。
豆瓣儿扭了一下头,她看见吕满升在笑。
吕满升的地跟豆瓣儿家搭界,当时他正在犁他的地。不是他自己犁,是杠子在替他犁。吕满升养了两头牛,他自己不需要干这些活儿。早年他是两户村的村长,经常有人像狗一样巴结他。后来他不当村长了,还是有人像狗一样巴结他。吕满升他娃在城里开公司,挣钱像飘树叶一样容易。
豆瓣儿哭的时候,吕满升就站在他的地里笑。他笑的样子很难看,嘴张得老大,像个肉窝窝,舌头在里头一闪一闪。他就这么笑,嗬嗬,嗬嗬嗬。
早年吕满升可不是这样,他当村长时经常关照豆瓣儿:把驻队干部往她家安排,让她从队里拿油拿面;她不用下地干活,还能领男劳力一样的工分。他以为这样就有了资本,就可以占豆瓣儿的便宜,没想到豆瓣儿在他脸上咬了一口,差点把他的鼻子咬下来。从那以后,吕满升就不再关照豆瓣儿了。谁也不会把心思用在没用的地方。
当时,吕满升就那么笑着,嗬嗬,嗬嗬嗬。幸灾乐祸的样子。
吕满升一笑,豆瓣儿就不哭了,她知道吕满升在看她笑话。
他妈的,我不叫你看笑话。豆瓣儿心想。
她从地上站起来,拍拍屁股上的泥土,“回呀,不干了。”
“他妈的,我干个啥劲?”她说。
5
当天晚上,豆瓣儿就做下了那事。
如果不是白天在地里看见吕满升,如果只是看见了吕满升而没有看见他的牛,豆瓣儿也许会睡个好觉。可她都看见了,看见了就睡不着了。白天的事儿让她心里来气,人一来气就睡不着,越睡不着越来气,越来气越睡不着。就是这么一个圈圈,跟驴拉磨一样。
这不能怪我。豆瓣儿想。
她这么一想,就把一件事想清楚了。那件事像跳蚤一样弄得她浑身发痒,她把脊背在炕上蹭了几下,不是背上痒,是心窝那里痒。她又在心窝上抓了几把,才知道也不是心窝痒,是心里头痒痒。这她就没有办法了,人又不能把手指头伸到心里头抓挠,谁的手指头能伸到自己的心里头呢?
小麦睡得很死,隔着窗子能听见她嘎嘣嘎嘣咬牙的声音。
豆瓣儿心想,女娃咬牙恨爹娘,男娃咬牙恨学堂。她想,小麦从小就咬牙,她喜欢读书,就是老跟她作对,书读得越多,就越跟她作对。她又想,要是能把心掏出来,让那牙嘎嘣嘎嘣咬两下,也许就不痒了。她突然想去隔壁窑屋,掀开小麦的嘴唇,看看她咬了十几年的牙是不是给磨下去了一些。可她没那么做。黑灯瞎火的什么也看不见,她又不想点灯,为这点儿事也划不着点一次灯。
何况……豆瓣儿想。
这不能怪我。她想。
豆瓣儿掀开被子,从炕上坐起来。被窝里黏乎乎的,有一股汗腥味儿。刚才被子捂着,闻不到;现在被子掀开了,它们就跑出来,像拐线虫一样,一拐一拐钻到她鼻子里;还拐,还拐,一直钻过她的喉咙,钻到她心里头,那痒就有些忍无可忍了。
这不能怪我。她想。谁叫他吕满升笑话我哩?我去刨自家的地,他凭什么笑话我呢?
她这么想着,走到院子里。
“哗啦。”头顶上响了一声,她知道是窑垴上掉下的土。这几间窑屋太老了,像人老了要掉牙一样,窑垴上总是冷不丁往下掉土。
小麦睡得很死,窑屋里传出她咬牙的声音。
这不能怪我。豆瓣儿心想,要是吕满升不把地分了就好了,那样我就不用操恁些闲心。可吕满升把地分了,我不能叫我的地荒着吧?
这么想着,豆瓣儿竟没忘拐进灶火屋,从盐罐里抓了一把青盐装进口袋,顺手往嘴里扔了一粒。
嘎嘣,盐粒在她嘴里响了一声。
小麦咬牙的声音突然停了,豆瓣儿吓了一跳,她以为小麦醒了,停下脚步,也停下咀嚼。这是她一个人的事,她不想让小麦知道她的事。
静了一会儿,见小麦再没动静,豆瓣儿放心了,她用舌头裹着盐粒,蹑着脚朝院门走去。
门楼上有一个光屁股月亮,昏黄昏黄的,像一张人脸;还有几颗星星,像按在娃们弹弓上的泥蛋蛋,一拽一拽的,忽儿远了,忽儿近了。谁家的狗叫了两声,就叫了两声,像老汉吸过旱烟后的咳嗽,闲适而慈祥。狗声融进月光里,成了寂静的一部分。豆瓣儿一点儿也没有在意。都在两户村住了一辈子了,谁会跟谁过不去呢?
6
后来,豆瓣儿就把吕满升家的牛弄上了鸡冠峁。
好牛。豆瓣儿心里说。
她抚摸着牛的皮毛,就像摸着一块好匠人搟出来的好毡,能感到牛皮下一坨一坨结实的牛肉,好像牛的气力多得盛不下,快要把牛皮胀破了。
真是一头好牛。她想,要是我家有这么一头牛就好了,那样就不用受小麦的窝囊气了,那样吕满升就不会笑话我了。
满升哥,你可不能怪我。她心里说,谁叫你把地分了呢?谁叫你笑话我呢?你给我分了地,就是要看我的笑话吗?他妈的,我使你的牛把地犁了,我不能叫别人看我的笑话。
她想着很解气。
豆瓣儿套牛时被自己吓了一跳,这时候,她发现她不会套牛。犁、撇绳、梭头,所有的东西都齐了,可她没法把它们弄到牛身上。她去吕满升家牵牛时,根本没想过这些问题,这时候这些问题却一下子都冒出来。她不能把它们弄到一起,牛再好也是一头猪,还不如一头猪哩,猪会用嘴拱地,牛不会,牛戴着鼻圈儿哩。
牛眼一眨一眨。
天上的星星也像牛眼一样,一眨一眨。
都是很着急的样子。
呼哧呼哧,牛喘着粗气。
呼哧呼哧,豆瓣儿也喘着粗气。
都是气急败坏的样子。
峁墚上静悄悄的,连一只鸟儿也没有,连一声虫叫也听不见。时辰已经是后半夜了,鸟儿肯定是钻到什么地方睡觉去了,可应该还有虫吧?霜降刚过,虫怎么也不叫了呢?有一丝风,但风只有碰到树叶才能发出响声,在这光秃秃的峁墚上,风什么也碰不到。虽然地头有一棵榔榆,可那棵树光秃秃的像一根棒槌。满世界就这么静着,静得连峁墚丢了也没人知道。
他妈的。豆瓣儿骂了一声,把手里的牛套扔到地上。
跟着,她也像牛套一样坐到地上。心里头有一种东西慢慢往上泛,泛着泛着就泛到喉咙眼儿,那地方就有些痒痒,好像有几条虫子急着要从那里爬出来。她紧了紧喉咙,使劲咳了几下,到底还是没把那虫子咳出来。她想,要是把牛缠绳穿喉咙里,上下拉一拉就好了。
后来,豆瓣儿听到了哭声,好像有人在很远的地方哭,开始的时候听不清,过了一会儿就听清了,是她自己在哭。刚开始她在心里哭,所以她听不到;后来是小声哭,所以觉得有些远;再后来她哭的声音大了,才知道是自己在哭。
“唉……我这可怜的我,唉……”豆瓣儿哭着说。
“唉……你个狠心的你,唉……”她想起她死去的男人。
“唉……你把可怜的我,唉……”她就这么哭。
豆瓣儿反反复复地哭诉着这些话,好像一块湿淋淋的布条子从她喉咙里抽出来,绵绵不绝。一些泪蛋蛋从她眼窝里滚出来,顺着颧骨往下流,在她下巴那儿挂了一会儿,吧嗒,落到地上。吧嗒,吧嗒。
这时候,有一阵脚步声传过来,豆瓣儿没有听见,她被悲伤埋住,只能听见自己的哭声。脚步声越来越近,后来停在豆瓣儿跟前。
“你哭哩。”那人说。
豆瓣儿被吓了一跳。三更半夜的,突然有个人站在你面前,谁都会吓一跳。她看了看那人,虽然有月光,可还是看不清那人的眉眼,只看见几个黑乎乎的小坑,像石头在湿地上砸出来的几个印印,但她知道是个男人。
“我正赶路哩,听见有人在哭。”男人说。
豆瓣儿不哭了。
“我本来不想过来,可三更半夜有人在野地里哭,肯定是遇到了难处。这样我就拐过来了。”男人说。
豆瓣儿这才知道那人是走夜路的。人活在世上,总有这样那样的事情,有些事儿白天办不完,就得赶夜办。那人不是两户村的,她不认得,但她知道他是走夜路的。
“你做啥哭哩?”男人说。
“我心里?惶。”豆瓣儿说。她用手在鼻子上捏了一把,哧,就那么响了一声,随手一甩,指头上的鼻涕就被甩出去,像一粒蜘蛛,挂在一棵玉米秆上,一弹一弹的。
“你做啥心里?惶?”男人说。
“我以为我会犁地。可牛弄来了,我才知道我不会使唤……”她说。“我从来没使唤过牲口。”
“女人家……”男人说,“我是说,这不是女人做的活儿。”
男人说着,看了看那头牛。
牛低着头站在那里,一副灰心丧气的样子。牛套、撇绳、梭头之类的东西胡乱地搭在牛背上,还有犁也歪在一边。
男人从豆瓣儿跟前绕过去,走到牛的身边,好像他什么也没有做,那些东西就跟牛弄到了一起。
“哦。”男人吆喝一声。
牛乖乖地拉着犁往前走,身后留下一道黑油油的犁沟。
好人。豆瓣儿心里说。
她站起来,拍了拍屁股上的土。这样,她的手碰到口袋里的那些青盐,她把身子靠在榔榆树上,顺手往嘴里扔了一粒盐,于是就有了有滋有味的声音———嘎嘣嘎嘣。
好人。她心里说。
7
这时候,两户村有只鸡叫了一声,接着,又有一只鸡叫了一声。不大一会儿,全村的鸡叫就连在一起,像那片刚刚犁出来的土地。天上的星星一颗颗隐了去,像一盏盏被人吹灭的灯。可天和地却一下子明亮起来。其实,天和地早就亮了,它们亮得很慢,所以察觉不到。等察觉到的时候,好像突然就那么亮了。
“嗬嗬。”豆瓣儿听见有人笑了一声。
她转过身子,看见几个人站在她的面前:吕满升,吕满升的婆娘,杠子,还有另外几个人。她知道他们迟早会来,可没想到他们来得这么早。还剩下一个地角没犁呢,这么早他们就来了。
“满升哥……”豆瓣儿说。
她说话时,对吕满升笑了一下,她以为吕满升也会笑一下,可吕满升没有笑。那些人谁都没有笑,豆瓣儿的笑僵在脸上。她觉得有人揪着她的头发把她往上提了一下,她一下子就悬到空中,头皮有些发麻。后来她才知道,并没有谁往上提她,是她的心往上蹿了一下。
“我的牛好吗?”吕满升说。他说话的样子一本正经,好像他是一个牛经纪。
“噢,我使使你的牛……”豆瓣儿说。
“使使?”吕满升回头对众人说,“都听听,她说得多轻巧,她说‘使使。”
“贼。”吕满升婆娘从背后闪出来,“我说你是个贼。”
吕满升的婆娘有些矮,像个胖乎乎的麻袋,说话时身子一摇一摇的。
“啐!”
豆瓣儿听见这么一声,她看见一团东西从吕满升婆娘的嘴里飞出来,粘到她脸上。她知道那是一种脏东西。吕满升婆娘为了让那东西有点儿准头,吐的时候往上蹿了一下。
“你唾我……”豆瓣儿说。她看见吕满升婆娘的嘴巴又想动,就抬起胳膊挡了一下,“我不过就使使你家的牛……”
“贼。”吕满升婆娘说。
“有借有还,我又不会匿了你家的牛。”豆瓣儿说。
“贼贼贼贼贼。”吕满升婆娘说,“啐!”
豆瓣儿赶紧用胳膊一挡。可这次吕满升婆娘没有往她脸上唾,人家把一口痰吐到刚刚犁过的地里。犁沟里有一条被翻出来的蚯蚓,那口痰正好落在蚯蚓身上,蚯蚓很难受地扭动着身子。
“你说,”吕满升对豆瓣儿说,“你说这事儿咋弄吧?”
“我不过就使了使,你不叫使就算了,你把牛牵走。”豆瓣儿说。
“嗬嗬。”呂满升笑了。
“要不我给你送回去。”豆瓣儿说。
“她说算了,都听听,她偷了我的牛,她说算了。”吕满升对众人说。
又有一些人来到这里,他们跟先前的人聚在一起,互相询问着,互相告诉着,叽叽喳喳,很兴奋的样子。
吕满升把杠子他们叫到一边,开始商量什么。他们的言语黏乎乎地搅动着早晨的空气。
过了一会儿,吕满升走过来对豆瓣儿说:“看你寡妇失业的,我不跟你一样,偷牛的事儿就算了。”
“我没偷,我就是没跟你言传……”豆瓣儿有些急了。
“没言传,那就是偷。”吕满升说,“可我不能叫你白使我的牛犁了恁些地。”
豆瓣儿看了看犁过的地,阔阔的一片,很壮观。
“你过来。”吕满升叫那个犁地的人。
男人慢慢地走过来。吕满升他们一到,他就不再犁地了,虽然还剩下一个地角。他圪蹴在地头,听他们说话。一开始他听不明白,后来听明白了,但他没有走。他想有些事儿他得说清楚,如果他走了,这些事儿就说不清楚了。听见吕满升叫他,他慢慢地走过来。
“你犁的?”吕满升说。
“噢嘛。”男人说,“我可没偷你的牛。”
“活儿干得不赖,垄是垄,耥是耥。”吕满升笑着说,好像那人帮他犁了地。
“可我没偷你的牛。”男人回了一个笑,露出两排友好的白牙齿,“我是收柿饼的,正走夜路哩,听见她在这儿哭,我就过来了。我不知道她偷了你的牛。”
“我没说你偷了牛。”吕满升说,“可这些地是你犁的不是?你犁了,你就得想法把这地弄瓷实。我不能叫她白使我的牛犁了恁些地。”
“我不弄那事儿,坏良心嘛。”男人说。
“你犁的,你不弄?”吕满升说。
“偷牛不好,把地弄瓷实也不好。”男人说,“你知道我没偷你牛就行了。”
说完,男人就走了。人们看着他朝远处走去,越走越远,越走越远,慢慢就看不见了,只剩下一条干黄干黄的土路。
“人。”吕满升说。
“杠子,他不去,你去。”吕满升又说。
杠子看了看吕满升,又看了看豆瓣儿。后来杠子就赶着牛下了鸡冠峁。
太阳升起来了,就挂在鸡冠峁的尖尖上。这是一天里头一拨阳光,洁净得像刚从井里打上来的凉水。等到阳光越过一座座峁墚,越过一个个地坑院,从村东走到村西的时候,就会沾上很多烟尘、饭香、汗腥、尿臊粪臭味儿,就会变成一堆恶俗的东西。现在太阳才刚刚升起来,所以那阳光洁净得像刚从井里打上来的凉水。阳光照耀着人们,在他们的脸上身上粉了一层金子样的亮色。
过了一会儿,杠子来了。他用牛拖来一个大碌碡,就是夏天打麦用的那种东西。
“碾,碾,你给碾成一块石头。”吕满升婆娘一蹿一跳地说。
杠子看了看吕满升。
吕满升说:“开始吧。”
杠子又看了看豆瓣儿,豆瓣儿什么也没说,眼睛迷离得像两片无所适从的枯叶。
杠子说:“嫂子,你可不敢怪我。”
“我不怪你,我怪你做啥呢?”豆瓣儿说。
“你也不敢怪人家满升哥。”杠子说,“要怪就怪你自己。你使人家牛,你得跟人家言传一声。”
“我不怪,我谁也不怪。”豆瓣儿说。
杠子就把牛赶进地里。牛拖着碌碡在地里来来回回走,跟刚才犁地一样。但刚才牛拉的是犁,现在它拉的是碌碡,碌碡碾过去,刚才犁起来的虚土重又变得瓷实。不大一会儿,那块地就变成一个光溜溜的打麦场。
后来,人们都走了。
豆瓣儿一个人站在地头,看着那块瓷瓷实实的土地,像做了一场梦。许久,她觉出脸上有些别扭,抬起手抹了一把,才知道是吕满升婆娘留在她脸上的一口痰。
啐!豆瓣儿朝着远去的人们唾了一口。她想,要说这事儿还是得怪吕满升,要是他不把地分了,也许就不会有这些龌龊事儿了。
这么想着,豆瓣儿觉得眼窝里有几颗泪蛋蛋要往下掉。她吸了吸鼻子,把脖子仰起来,远远地看着鸡冠峁的尖顶———
这时候,她看见峁顶那边走来一个人,走得很快,很快就到了跟前,是小麦。小麦的身上背着一个背包。
豆瓣儿吸了一下鼻子,没让那泪蛋蛋掉出来。
小麦也吸了一下鼻子。
责任编辑:柏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