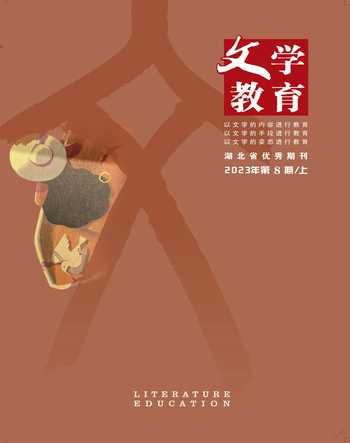莫言《酒国》中对酒神精神的消解
裴国江
内容摘要:酒神精神是尼采对古希腊悲剧的解析,即一种狂乱迷醉乃至癫狂的精神状态,尼采希求通过赞美这种迷醉的非理性精神,从而论证重估悲剧、重估人生价值的哲学内蕴。莫言的《酒国》是一部基于酒神精神而创作出的作品。小说围绕酒展开,文本整体弥漫着癫狂迷醉的魔幻酒神氛围,莫言在作品中展现出自己对尼采的非理性带来欲望扩张的必然悲剧性的思考,并在创作中虚构了酒国这一酒神精神的载体,实现对酒神精神的消解。
关键词:酒神精神 莫言 《酒国》 消解
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通过对古希腊艺术的分析,从中提取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他认为这两种精神是在相互制约中达到一种协调,并由此产生完美的艺术形式悲剧。酒神精神即狄奥尼索斯精神来自于丰收神、酒神祭祀,希腊人为了庆祝收获,在酒神祭上饮酒狂欢,酒醉使他们且歌且舞,冲破禁忌,并在酒精的催发下进入癫狂的状态,获得一种精神上颠覆的快感。尼采认为这是音乐艺术产生的前提,这种精神沉淀于艺术乃至文学创作中便成为文学创作的一种内在精神动力,其本质上是对现实苦难的精神消解,通过这种狂欢的状态暂时忘却世俗烦恼,用酒精带来的迷醉遮掩现实人生的本来面目,从而实现暂时的、精神的、形而上的解脱,使人与人的关系更加紧密融洽。由此可以看出酒神精神本质上仍是一种肯定人生的态度。作为个体存在的人必然是矛盾且痛苦的,通过酒神精神,暂时消解人的现实痛苦,给人以信念去忍耐突破痛苦,从而以更积极的心态面对人生。
莫言捕捉到了酒神精神中双重性,即生命力的释放与欲望无限膨胀的双重性存在。并抓住欲望这一酒神精神中的非理性因素,创造了“酒国”这一充斥欲望膨胀的酒神精神的虚拟世界,通过各种荒诞与糜乱的刻画,实现对于酒神精神的消解,即酒神精神中隐含的必然毁灭的悲剧。莫言的《酒国》创作有着强烈的现实因素,其创作目的在于揭露物欲横流下人性的丑恶。
一.“酒国”——酒神精神的“乌托邦”
(一)“酒”作为载体串联起了一个非理性的世界
莫言在作品中塑造了酒国这一酒神精神的乌托邦。《酒国》以酒为载体,串联了三个脉络不同却相互联系的故事,一是高级侦察员丁钩儿到酒国调查食婴儿一案,在酒国的酒权钱色的羁绊下,一步步堕落,最终堕入欲望的深渊。二是作家莫言与酒国作家李一生就文学探讨的书信往来。三是李一生寄给作家莫言的九篇以酒国的故事为题材短作。三条线以酒为链条,相互补充串联之间,构塑了酒国这一迷醉的世界。这种三条线索之间的来回穿插提供了双重的叙事空间,即以丁钩儿经历的现实空间和以书信小说构成的文本空间。两个叙事空间在读者阅读的层面而言相互打断了彼此的叙事时间轴,文本空间与现实空间不断相互补充和佐证,虽然打断了小说的正常叙事顺序,但这种虚虚实实的叙事方式中,在阅读中却给予读者一种穿插带来的酒后迷醉。
酒最初作为祭祀用品而产生,酒神精神也发轫于酒神祭,这种祭祀的前提就是人类的物质生活的丰富,只有物质上的丰富人类才有多余的酒食进行祭祀乃至祭祀后的狂欢。酒国的背景被置于90年代商品经济迅猛发展的中国,经济的野蛮增长带动了权力与金钱的膨胀。而酒国的财富却来源于采矿这一原始且直接的方式。这种原始直接简单获取财富的方式更容易造成人的暴发心理,消解人的危机意识,对金钱不珍惜陷入到原始的享乐主义中,而酒这一与权力金钱享乐纠缠不清的饮料就很自然的成为直接的纵欲方式,整个酒国弥漫着酒精、金钱与權力的狂欢。“可以说酒在酒国是一生万物的原始之道,也是推动叙事的行动元,由酒开始,有了酿造大学,有了酒肉之宴,也有了口腹与纵欲的极致狂欢。”[1]小说中的人物逐渐迷失在虚幻的金色泡沫之中。
(二)“酒国”的物欲横流下道德的消解
财富的暴发会引起人对于原始欲望的追求,产生对于食色的放纵。这一点酒国与古希腊极其相似。农业社会时期的丰收和酒国的矿业的发展,都是财富的急剧扩张,进而产生食色的狂欢。希腊人是对丰盛祭品的享用,而酒国则是突破道德底线,对食材病态追求。对于食材的病态追求,突破的是常规的饮食经验,追求的不是这种食材本身,而是追求其背后的特殊意义,通过彰显自己的权力、财富带来的越界行为获得精神上的满足与快感,这本身就是与人的道德相违背的。 “吃人”是作家对于病态社会的一种常用的描写,而莫言在酒国中更是突破生理道德极限来刻画食婴。主角丁钩儿来到酒国的机缘,就是调查“红烧婴儿”案。莫言不吝笔墨详尽的刻画了食婴的情景“圆盘中的金黄色遍体流油、异香扑鼻的男孩”,用刻画美食的笔法去描绘食婴,更凸显食用者突破道德底线带来的冲击力。在酒国,被食用的婴儿被反复强调称为“人形小兽”,婴儿被剥夺了作为人的权利成为食材,而这种反复的遮掩更凸显了酒国人的心虚,而收购站的女守门人更是直接点破,咒骂道“总有一天会有人出来收拾你们这些吃人的野兽”[2](96)。在酒国所有人在利益的裹挟下集体遮掩这个“人形小兽”的谎言,售卖者惦念卖出的钱,食用者贪恋这种畸形的享受。在这种集体道德堕落下,婴儿像食材一样畜养,精心的照顾只为了多卖点钱,收购者建立收购等级,双方如同售卖猪仔一样讨价还价,甚至产生了畸形的攀比心,父母忧虑自己的孩子没有别人卖的价高。而作为揭破这个罪恶的正义使者丁钩儿,却也在酒精的麻痹和矿场领导辩解下食用了婴儿,酒国在无法挽回的走向进一步的堕落。
而这种对于变态食欲的追求还体现在酒国食驴的狂热,酒国有一条专门食驴的驴街,在驴街上,人们追捧的美食却是驴的生殖器。“将公母驴的生殖器在清水泡三遍,血水浴三遍,碱水煮三遍,油锅熘一遍,砂锅闷一遍,高压锅里蒸一遍,再以精细刀工,切出各种花纹,配上名贵佐料,点缀上鲜艳菜心……”[2][117]这种变态吃驴方法在对于食材的求新猎奇的畸变中滋生出来的。将公母驴的生殖器做成的菜冠以龙凤之名,进一步美化低俗,在这种饮食无禁忌的习俗滋养出了酒国一种道德失格的无耻感,对于生殖器的迷恋与漠然进一步的助长了酒国对于男女之间的道德感缺失。
酒国的堕落事实也导致了传统道德消散,造成了理性者无可避免的走向死亡。酒国中烈士陵园看守老革命是作品中少数的正面人物,在丁钩儿的第一次因酒堕落后再次给了他继续追查的信念,而作为一个革命者却在道德沦丧的酒国无可避免的遭到挤兑最后悄无声息死亡被老鼠啃食,这一悲剧彻底击溃了第二理性者丁钩儿的心理防线,使他彻底失去理性和自我逐渐堕落。
二.酒国中隐含了酒神精神悲剧的必然性
酒神精神是一种突破道德和约束的非理性的精神,而酒国就是对人内心世界和人性本能冲动的非理性刻画,是一种集体性的非理性的狂欢的世界,而这中狂欢背后却已经隐含了悲剧爆发的必然性。
(一)酒国底层社会贫穷
由于酒国中的百姓生存艰难,乡村的贫户被迫将自己孩子卖给权贵当作餐食,满足权贵的畸形饮食需求。丁钩儿初到酒国就来到作为酒国财富生产的中心矿区,而作为财富来源的矿区却是破败不堪“已经十点一刻,煤矿的铁栅栏门依然紧锁着。那只挂在门鼻子上的乌黑大铁锁,宛若一只黑盖的大鳖。安全生产庆祝五一,八个色彩消褪的红漆大字拘禁在圆形的铁片里,电焊条在很早的时候把它们焊在了铁栅栏上。”[2]6与之相对应的是矿区招待贵宾的餐厅却是富丽堂皇。丁钩儿在落魄时去吃路边卖馄饨大爷的馄饨,大爷看穿了丁钩儿的落魄没有收钱,却在得知丁钩儿的身份后惶恐起来:“不敢呐,不敢呐,首长,几碗烂馄饨,算得了什么?碰上您这大仁大义的人,是小老儿三辈子前修下的福气,不敢呐,不敢……”[2]148底层民众深受压迫,生活与酒国上层的纸醉金迷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而这种反差也是酒国悲剧的最集中的体现,最终整个酒国将会在矛盾的激化中覆灭。
(二)知识分子的堕落
酒国的堕落也侵染了酒国的知识分子,本应清高的知识分子也堕落在了酒国的酒色欲望之中。在酒国的大学里,教授不以科研为务,而是钻研酿酒技术和烹饪婴儿,成为了酒国欲望的帮凶。教授袁双鱼因为一个传说甚至愿意抛家舍业去深山里向猴子学习酿酒。而他的女婿李一生,一个追求文学的酿酒博士,在与作家莫言的通信中一方面以作家和文人的身份标榜自己,另一方面却表示为了作品发表不惜行贿。面对流氓富商余一尺,极尽谄媚之色。作为袁双鱼的学生和女婿,却对自己的妻子极其厌恶,把婚姻视作追求名利的工具,并粉饰对岳母进行的意淫。而看似清高的莫言,终于也没有经得住李一斗以”金钱“和”美酒“为名的反复邀请,不仅接受了猿酒节的邀请并答应为无赖侏儒富商写自传。并且一到酒国市就开始了类似丁钩儿的轮回体验,不仅对酒店的美女产生情欲的冲动,更在美食与酒香之间不能自拔,开启了沉醉之旅。知识分子本应是作为社会的清醒者而存在,而李一斗等却陷入在酒国中的堕落泥淖,失去知识分子的风骨沦为酒国堕落阶层的一份子。
三.《酒国》中酒神精神的消解
莫言塑造了一个作为酒神精神载体的酒国,并在小说中埋伏了酒国悲剧爆发的种子。而酒国与酒神精神内在的一致性也指明了酒神精神悲剧的必然性。而这种悲剧必然性也正是由于酒神精神内在的哲学层面的缺陷,尼采的酒神精神自身就是一种悲剧性的存在,由于酒神追求非理性的欲望释放,其必然引导个体走向毁灭,而酒国的悲剧性也正是发端于此。
(一)《酒国》对酒神精神的反解
在尼采的哲学思想中,酒神精神所代表的迷醉与狂欢是人的生命力的释放,而在酒神精神的发源地酒神祭来看,酒神精神带来的迷醉与狂欢对于维护城邦的稳定具有重要意义。酒神祭作为一个宗教意识,一方面作为物质与肉体的狂欢,其可以成为城邦统治者获取公民支持和拥护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祭祀作为一种宗教意识,其体现的也是一种的意识形态,祭祀作为城邦意识形态的展示,可以起到统一城邦思想的作用,并且丰盛的祭祀仪式可以展示城邦的强大物质力量,从而推动城邦意识形态乃至思想文化的传播与交流,成为古希腊人统一思想、共御外敌的思想武器和共建和谐社会的思想基础。
并且古希腊人在酒神祭祀上体现出酒神精神实际上是物质不丰富的条件下的有限纵欲,通过短暂的迷狂暂时忘却现实的痛苦,是欲望的有限满足。,并且是一种积极的存在。此外,酒神精神虽然本质是一种贵族精神,但从古希腊的条件客观来看,它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一种平等的狂欢,所有的参与者抛弃了理性的存在,进行无差别的放纵。因此这种狂欢是可以提高城邦人的认同心理,缓和城邦的内部矛盾从而起到维护城邦的稳定性的作用,体现为一种积极性的存在。
而莫言对酒国精神进行了反解,创造了一个追求无限享受,无限欲望满足的酒国世界,去凸显酒神精神本质上的非理性与个人主义贵族主义,反馈酒神精神背后深层次的消极性存在。《酒国》剥离了酒神精神狂欢的外衣,直指其本质——无理性约束下无限扩张的欲望,进而构建一个没有理性和克制的酒国世界,而正是无节制的欲望所代表的非理性,造就了酒国中所有人堕落的悲剧,这本质上也就是酒神精神的悲剧,脱离了日神精神的制约,酒神精神带来的就不是生命力的舒展,而是欲望的膨胀,而这种欲望的膨胀必然导致毁灭,因此无论是酒国中的每一个体亦或是酒国这一整体性存在,莫言都是用一种讥讽批判的手法进行建构,其暗含的就是对于这种酒神精神的批判,更具体来说,就是对上世纪80、90年代经济野蛮发展的部分堕落者的批判。
总而言之,莫言既塑造了一个酒神精神畸形体现的酒国,同时也在小说中埋伏了酒神精神内在的哲学层面缺陷,即非理性带来的无限欲望扩张和贵族主义、个人主义,对酒国堕落路上的狂奔的描写暗示了酒国的悲剧,也是酒神精神悲剧,实现了对酒神精神的反解。
(二)酒神精神的反解服务于反讽批判
酒国的创作并不是针对酒神精神的批判,而是通过酒神精神的反解来揭示露物欲横流下人性迷狂。对于酒神精神的反解是为了讽刺欲望的放纵使人性走向畸形,是对人性以及现实的批判。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一段经济野蛮生长的年代,一方面经济的快速发展,一部分人迅速获得了大量的财富,整个社会沉浸在发展带来的经济效益中,而由于思想和管理没有跟上经济的发展形成了相对滞后,与之同时也产生了时代的弊病,一些发展中的问题也体现了出来。可以说那个时代也陷入了酒神精神的狂欢,一方面是物质上的突然丰富,正同希腊人的丰收与酒国人的矿业,都是一种直接简单的获得的财富;另一方面是则是约束的滞后,如同脱离理性日神精神束缚的酒神精神,必然会导致一系列社会问题的产生。
基于此时代莫言于1989年创作开始《酒国》,并在1992年完成。莫言在后记中阐释了自己的创作动机,从酒与自己的渊源谈起,谈到了自己的家乡,谈到了自己的体验,也谈到了当时社会的问题。莫言从酒讲到了当时社会的造假问题,“报章上不时揭露用工业酒精勾兑假酒喝坏了人的事件,读之令人心怵。假酒制造者遍布各地,手段卑劣,令人发指。大批的假酒制造者和销售者发了横财,被揭露者不过千万之一……”[2]364而直接刺激莫言进行创作的,则是一个报道:一位右派青年在特殊时代抑郁不得志,买了八斤酒想醉死自杀,寻死失败却意外发现自己有千杯不醉的能力,从而如鱼得水成为一个矿山陪酒员,得到了领导重用,名利色兼收获得了“成功”。莫言敏锐地捕捉到时代的问题,并应时应世创作出作品,在简短的后记中展示对时代的担忧。
莫言面对这些社会问题,将夸张讽刺的手段囊括入作品,进而实现对时代弊病的批判。“原想远避政治,只写酒,写这奇妙的液体与人类生活的关系。写起来才知晓这是不可能的。当今社会,喝酒已变成斗争,酒场变成了交易场,许多事情决定于觥筹交错之时。由酒场深入进去,便可发现这社会的全部奥秘。于是《酒国》便有了讽刺政治的意味,批判的小小刺芒也露了出来。”[2]366在后记中莫言点名了《酒国》的创作价值在于讽刺、批判。文学作品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对时代的记录,更体现为作家对于社会问题的态度,体现为作家的社会责任感。莫言借助小说对于時代弊病的批判,正是其作为优秀作家的优秀品质的展现。
参考文献
[1]赵坤.《酒国》中的精神现象浅析[J].小说评论2016,(04):87.
[2]莫言.酒国[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7.
[3]王晋生.论尼采的酒神精神[J]. 山东大学学报,2000:03.2000,{03}:13.
[4]尼采.悲剧的诞生[M].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