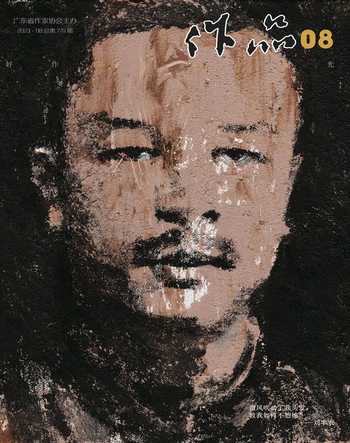马里奥和一枚爱恨交加的钻戒
刘荒田
一
1995年底,马里奥和我一起进旅馆的宴会部当侍应生。属于内部更换岗位,他来自意大利餐厅,我来自送餐部。这一年他四十八岁,我四十七岁。马里奥爱和我聊天,当同事才一个月,他就把身世没有保留地告诉了我。本来,我对他私下的评价是平庸,什么都是“中不溜儿”——中等的身架,不过不失的容貌,流利但词汇偏少的英语,思想肤浅,谈半天也难得听到一句具深度或幽默感的话。也难怪,他压根儿不想“出众”,除非天冷,他上街总趿一双热带居民穿的大拖鞋,而他旁边的太太,比他年轻十多岁,花枝招展,格外衬出他的老和懒散。但我了解他前半生的经历以后,印象全变,下了这样的结论:他是难得的好男人。
马里奥出生于菲律宾群岛中的班乃岛,家境贫困,在家乡念完高中,就去马尼拉闯荡。在远洋轮当了十多年水手,跑遍全世界的大港口。三十岁那年,他厌腻了起伏不定的大海,和旧金山一位拥有美国籍的菲律宾女子结婚,就此取得居美身份。那时,他在旧金山金融区一家大企业里头的“维克多”餐厅当服务员。他生性勤快,一个人干活,养太太和两个儿子。他太太却不是规矩人,在家带孩子嫌闷,找了情人。和情人打得火热之后,干脆“净身出户”,和情人私奔到外州去,就此断了音讯。两个儿子,一个一岁多,一个六个月,撂给马里奥。马里奥在旧金山并没亲人,不上班就连房租也交不出。他咬牙忍了,每天一早给小的喂了奶,让大的吃了麦片粥,就用背带背一个,怀里抱一个,送往保姆家。晚上下了班再领回家。雇请上班时间超长的全职保姆开销大,马里奥只好把额外的送餐服务也包下,好多赚点钱。
既当妈又当爹的艰难日子,过了十二年,到两个儿子上了高中,他才松了口气,思量娶妻。这一次,他以美国籍民的身份,和从菲律宾首都马尼拉来美国找对象的女子认识,结了婚,次年生下一个女儿。这一年,他从供职十多年的“维克多”转到游艇俱乐部的餐厅。游艇俱乐部的会员都是有钱人,舍得付小费,马里奥的收入增加了一倍。太太也被梅西百货公司化妆品部聘为销售员。两个儿子进了学费廉宜的社区大学。这个前半生坎坷的好男人,从四十五岁那年起,像童话的结尾一样:过上幸福的生活。
他和我聊天时,不时满怀神往地谈起游艇俱乐部:每到周末,游艇的主人们带上一家子或伴侣,在旧金山湾内升起雪白的帆。湾内不同于外海,浪总是柔和的,晴空万里下,数百只价格从数十万到上千万美元的游艇散布在碧蓝的海水上,犹如天鹅群。游了半天以后,他们把艇停在码头,进餐厅就餐。
“一群老寡妇,最喜欢的侍应生就是我,指名要我侍候她们,饭后抢着给我的制服口袋塞小费,最少二十美元。”他得意地炫耀。我算算,不计每小时超过二十二美元的工资和正规的小费,单是这一类外快,他一天也赚上百美元。
“这么好的工作,你不做,宁愿降一级,来这里的意大利餐厅当练习生?有点不合常理。”我说。不知何故,他的脸唰地变色,沉默了一阵,拧头向别处,似乎被我挑起了隐秘的心事。
我为了打圆场,替他做解释:
“你要求转来宴会部,就是为了当侍应生,算来你当侍应生该有二十多年了,没理由回去打下手。”
“其实我离开游艇俱乐部,是不得已。”他叹口气,说。
二
原来,马里奥辞掉游艇俱乐部的美差,是为了一枚钻戒。经过是他在上班的间隙断断续续地告诉我的。看來这已成他必欲吐之而后快的“块垒”,一如少男少女满得要溢的情欲,“向谁倾诉”不是首要问题;非要“说出来”不可,碰巧我是唯一爱听他说话的同事。
两年前,他在游艇俱乐部餐厅上班那阵,发生了这样的事:
马里奥从游艇俱乐部的餐厅下班回家,已经是深夜十二点。他经过儿子的房间,轻轻推了推,门在里面关上了,这意味着二十三岁的宝贝已经回家,入睡了。他走进自己的卧室,关上房门。
他还在亢奋中,衣服没脱,打开床头柜的灯,把口袋里的东西掏出来,那是用餐巾裹着的小玩意。他的手微微发颤,把它捏起,贴近灯光。是一枚镶嵌钻石的戒指,钻石内部折射出粉红的幽光,他旋一下,光对准灯泡中心,闪电一般,眼前一片空白,他眯一会眼,再睁开,周围寂静依旧。他试图把戒指戴上,直径太小了,是女性专用的。他戴在右手小指上,左看右看,哈哈大笑起来,抱着被子打滚,太妙了!今晚他怎么胡闹都行。妻子一个星期前回马尼拉看望父母去了。
他睡不着,干脆走进厨房,倒了一杯红葡萄酒。开灯前,尾指上的一朵红光晃着。
他端着酒杯,回到卧室,坐在单人沙发上。刚才的一幕在脑际泛现。今晚,他在游艇俱乐部的餐厅,为一个生日宴会服务。今天是史蒂文森先生的七十大寿,史蒂文森太太是宴会的发起人。一切按部就班——首先是主人致欢迎词,再是就餐,三道菜——沙拉,煎牛排或金枪鱼,甜点。他在这里已当了五年侍应生,客人基本上是俱乐部的会员,叫不出名字也认得脸孔。轻车熟路地侍候客人进餐,接下来,送上生日蛋糕,史蒂文森先生吹蜡烛,许愿,宾客轮流上台,说笑话。舞会开始,侍应生和练习生们除了收拾餐具,没什么活干,都在舞池旁边站着,聊几句闲天。
马里奥是勤快人,总乐意为客人多做点事,他轻声问跳舞跳出了汗,在舞池旁边坐下的太太们,要不要喝饮料。这些会员,绝大多数是有钱人,家底不丰,怎么买得起起价动不动要十来二十万美元的游艇,还得付停泊专用码头的费用,以及俱乐部会员费?
在五人爵士乐队伴奏下,舞会进行了两个小时,宾客们都上了年纪,跳累了。坐的比跳的多起来。一位穿红裙子的女士从座位上蓦地站起,嚷着:“我的戒指呢?我的天,我的戒指丢了!”她旁边起了骚动,绅士淑女们都站起来,挪动椅子,低头看地下。红裙子女士嚷得更响了:我的婚戒呀!不见了不得了呀!马里奥认识她,是老会员凯莉,七十多岁了,去年先生去世,出殡以后也是来这里招待宾客的。凯莉是圈子里的名人,以张扬出名,过了六十岁,每三年拉一次皮,丰唇手术不知做了多少次,如今猩红的嘴唇活像两条蚕虫。马里奥刚才和同事们说悄悄话,还拿凯莉开涮:“看吧,再拉三次皮,嘴巴恐怕要长胡子了。”同事听不明白这黄色玩笑,一个劲问为什么?马里奥问:“哪里的毛最多?”说着,指了指裤裆部位。同事恍然大悟,笑得差点岔了气。
“是亨利给我的啊!我的天,可怜的亨利,原谅我……”凯莉嘤嘤而泣。宾客们都知道凯莉爱咋咋呼呼,以为她夸大事态,不怎么当回事,在旁的人代她找,也是装模作样而已。首先紧张起来的是宴会主人史蒂文森太太,她过来问凯莉:“怎么回事?”凯莉说,她肯定进门时钻戒还戴着,现在不见了。史蒂文森太太不敢问钻戒的价值,因为太俗气,人家结婚五十多年,丈夫已辞世,单从纪念意义上说,哪怕是镀金的、银的,也不可小看。凯莉呜呜地哭起来。马里奥把一盒纸巾放在她身前的桌子上。
史蒂文森太太以主人的身份,通知乐队停下来,舞会中止,又吩咐一位女士去洗手间检查,同时,要经理把天花板下的水晶吊灯旋到最亮,请全体侍应生帮忙,一寸寸地检查地板和舞池,特别是缝隙。闹腾了二十分钟,并无所获。史蒂文森太太皱着眉头,看了看窗外黑幽幽的海水,摇头,自言自语:“莫非给扔进水里了?”凯莉不肯罢休,说:肯定是在餐厅里头掉的。史蒂文森太太扫视全体侍应生,话里有话地问:“大家听好了……”她指望有人说:“我捡到一只,看是不是……”可是经理、领班和侍应生们都沉默。“以后如果找到钻戒,千万送回来。”史蒂文森太太最后说。这位主人曾闪过一个念头:请俱乐部的保安来逐个搜身。可是,这样做太不文明了,犯不着为了爱炫富的寡妇开罪所有人。有心拿走的人早就藏好了,小小钻戒,塞进哪里不行?何况,非法搜身,会不会侵犯人权,心里没底。
马里奥从头到尾在场,却没有动作。直到史蒂文森太太大声问“有没有人拾到嘛?”他才隐隐感到事情“似乎”和他有关,从而下意识地按按裤袋,硬硬的小玩意在。
原来,舞会开始不久,他收拾散落在舞池边沿的鸡尾酒杯,无意间看到地上有一个发红光的点,以为是小孩子的玩具,弯腰拾起,哈,是戒指呢!他对首饰是“八窍已通其七——一窍不通”,根本没想到有多珍贵,随手放进口袋。因为这是“举手之劳”,很快忘掉了。及至事情闹大,他想交出,却没有勇气。因为史蒂文森太太问了三遍,语气越来越严厉。他怕被质问:“刚才为什么不交?”经理在旁,一定怀疑他手脚不干净。一迟疑,错过了时机。
宾客们纷纷回家去,气氛很坏。最后离开的是被史蒂文森夫妇陪着的凯莉。凯莉不甘心,老要找。连吸尘机搬来,把围绕舞池的地毯吸了一遍,也没有结果。凯莉一路说:“心疼啊!”恋恋不舍地走出去,上了来接她的车。
马里奥找个空隙,溜进洗手间,关上门,把钻戒拿出来,看了看,用餐巾裹好,塞进内裤里面。他走出俱乐部专供员工出入的门口,有点鬼祟地左看右看,同事们有说有笑地经过。他老觉得被人怀疑上了,冷汗涌出。
“那一刻,我后悔死了!捡起钻戒时立刻交出去多利落!一秒钟举棋不定,祸害无穷。”马里奥说到这里,痛心疾首地顿脚。
“不过,你发横财了啊!”我拍了拍他的肩膀。
“我后来也是这么说服自己的,前妻走了以后,我受那么多苦,上帝知道,给回报了。”马里奥把手交叉在胸前,但语气没有欢欣,相反,拧着眉毛,不胜痛苦似的。看来,事情不简单。
三
“接下来怎么办?”我问马里奥。他摇摇头,不大愿意直说。几天以后,我和他在员工食堂喝咖啡,看他的脸皮没那么紧绷,又不经意地问起,他说了,尽管不够爽快。
马里奥拾到钻戒的第二天,是休息日。当务之急是了解钻戒的价值。他知道凯莉的为人,为了面子,爱吹自己多有钱。有一回,她挎的手袋,被和她有过口角的女会员揭了老底:不是真LV,而是从渔人码头一家中国人开的店买的假货。天知道钻戒谁真谁假?去哪里检验?旧金山的珠宝店万万不能去,怕凯莉给所有检验员发了通知。想了半天,他决定去太浩湖赌城,那里,全球的赌客、游客云集,任谁也查不出来。
马里奥从他居住的旧金山郊区戴利市驾车到太浩湖,走了五家赌场,每一家,都先打听有没有珠宝店,如果前台经理说有,他便进去,假装买珠宝,低头看厚玻璃柜台内的货色,顺便对照自己揣在夹克内袋的宝贝。珠宝店的店员都是年轻女子,她们是被雇来卖货的,却不懂得什么钻石最高级别是“无色”。
马里奥到了“喜乐时”赌场里头的商场,踱进一家金铺,看旁边没有人,便向柜台后头工作台前戴单眼放大镜的老师傅打招呼。老师傅年过60,白人,问马里奥有什么需要帮助,马里奥从口袋里掏出一块丝质手帕,放在柜台上。师傅问是什么。马里奥又转身把四周看了一遍,打开折了三层的手帕,里面就是钻戒。他请师傅看看钻戒是真是假,价值多少。
老师傅看他鬼祟的模样,以为是来销赃的,不大情愿。马里奥把一张百元美元钞票从钱包抽出。老师傅说,稍等。他回到工作台,戴上放大镜,对着台灯看了一会,边看边点头。马里奥知道“有戏”。师傅说,是真货,正式鉴定要收费。马里奥把放在柜台上的钞票推过去,问够不够。师傅没正面回答,只问,信任我不?如果信任,我就去里面使用专门设备。马里奥毫不迟疑地说,当然。他知道,赌场里的店铺不会乱来。
师傅把钻戒拿到显微镜下,看了又看,相知相惜的微笑像一朵菊花,在脸上徐徐展开。他是本地人,在赌场开珠宝店二十多年了。见多了输红眼的女赌客把戒指、项链从身上脱下,托他估价或出手,拿了钱再度进场搏杀,交到他手里的不是没有上品,但像眼前这般华贵的,一年也就看到一两枚。
师傅撩开门帘走出,马里奥上半身伏在柜台上,似乎在看厚玻璃下的各种廉价珠宝,但脸憋红了,心里急得要命。师傅不急,端来两杯咖啡,一杯自喝,一杯给马里奥。
“我叫亨利,你忙不忙?不忙就听我说说。”师傅呷了一口,马里奥哪有心情品咖啡,上半身更往前傾。
亨利先给他启蒙:“钻石的品质,和颜色、重量、净度、切工,四个词都以C开头,叫4C……”
“算了,你直接说好不好?”
“急不来的。”亨利提高嗓门,眼神威严,意思是:你催我就不说了。亨利这个自命为内华达州“行内翘楚”的工匠,一辈子和钻石打交道,学问有的是,遗憾的是没几个人愿意学。和他打交道的赌客,和马里奥一样,只想知道权威的数据:值多少钱?亨利积累下来的发表欲,今天非要发泄不可,但他怕迫不及待的客人掉头而去,连鉴别费也拒付。
“好,简单说。”亨利做了一次深呼吸。
“你这个钻戒,是I级。”亨利要说下去,被马里奥打断了——“I级是第几级?”
亨利终于明白,对这位客人普及钻石ABC是瞎子点灯,简单地交代了:
“三卡拉,价值在九万至十一万美元……”
马里奥问,请再说一遍。亨利照办了。这次的语气带着鄙夷——好菜给猪拱了!
马里奥差点扑过柜台,去拥抱素昧平生的老头子。
“发了!发了!”马里奥在心里欢呼。他在游艇俱乐部,小费的丰厚令同行眼红,但一年下来,工资连小费税前也就四万五千到五万美元,那一次弯腰捡起的“闪光的玩意”,价值等于他两年的辛劳,两年!早起晚睡,忍受多少次挑剔的客人使唤,赔多少笑脸!
亨利的脸偏到一边,避开马里奥兴奋到极点时喷出的口水,再做解释:这个价格之所以有上下限,是因为到了这个价位,全凭买者和钻石的缘分,人家要是一见钟情,出到十五万美元也说不定;否则,人家出到九万美元你也要割爱。
亨利多么希望和一个“钻石迷”互动一番,单是这一枚的光泽,就够讨论一个小时,但马里奥并非合适人选。亨利开了一张鉴定钻石的收据,手续费为一百二十美元。马里奥有点心疼,他要赚这点钱,非得干两个午餐,但爽快地付了。
马里奥没有离开,他要榨取剩余价值,继续问:亨利,我把这颗钻石切割为两枚,你说好不好?
“天啊!万万不可!你看,”亨利把马里奥手里的钻戒拿过来,拧亮柜台上专为顾客看货而设的聚光灯,“这颗钻石,质地虽说上乘,但更值钱的是切工。知道吗?切割功夫好的钻石,能把所有吸入的光线反射出来,从哪个角度看都那么夺目。”亨利边说边旋转钻戒,缤纷的闪光炫得马里奥眼花,他眯上眼,更加陶醉。
“可是,我要割成两枚。”马里奥不在乎。
亨利生气了:“这活我不接,多少钱都不行。”
马里奥已经嫌他收费太高,没勉强,兴冲冲地驾车回家。
四
说话就过了一年多,作为话题,这枚钻戒已陈旧,我失去了兴趣。反正,悬念没有了,这位头脑简单的蓝领工人,持有一枚价值超过一辆最新款550系列奔驰轿车的钻戒,并不影响地球的运转,他所过的日子是“外甥打灯笼”。
1998年圣诞节前,马里奥的大儿子马克对老爸说,他打算在平安夜向相恋三年多的女友求婚。马里奥当然支持。儿子说,人生大事马虎不得,要给女友买一个“过得去”的钻戒。然而,马克只是一家快递公司的仓库工,时薪才十三美元,钻戒动不动开价一两万美元,哪里出得起?他知道老爸养大他兄弟俩有多艰难,不忍心让他百上加斤,而后母一直偏心眼,对亲生女儿比对他们兄弟好得多,他不愿向她伸手。于是打算向银行贷款,好买一枚两万美元左右的钻戒。
马里奥自从去赌城摸清钻戒的底后,把它放进银行的保险箱,什么都没做。这一次,他把钻戒拿出来,驾车一个多小时,到了沙加缅度市,走进从网上搜索到的金铺,找一位从事钻石切割、镶嵌的行家,请他一分为二。
“你什么也不必问,也不要告诉任何外人。”马里奥付保证金时告诫师傅。这师傅是中国人,姓全,他并没有切割钻石的刀具,但他朋友有。沙加缅度离旧金山一百五十公里,马里奥舍近求远,理由和从前一样——免得被追究,尽管离拾到钻戒的1993年已有五年。
马里奥付了一千五百美元,把钻戒变为两枚。从此,原先带上产地认证证明的钻戒彻底消失。一枚送给大儿子,一枚送给太太。
五
钻戒送了出去,心事该已了结。而且,马里奥已从与他一起在游艇俱乐部餐厅共事的领班口里知道,丢失钻戒的老太太凯莉,钻戒早就买了保险,保险公司赔偿五万美元,虽然没赔足额,但也够她买一枚蛮不错的“鸽子蛋”,何况,她有的是从丈夫那里继承的遗产。马里奥久久被折磨的心,自此感到轻松一点。
马里奥告诉我,他太太接过钻戒时,生日已过了,她想不起老公这么慷慨出于什么理由。当然,马里奥从来不透露他曾拾到钻戒。被太太知道,“模范老公”的形象就全毁掉。太太并没有心机,把钻戒套进手指,不经意地问:“是真的吗?”马里奥顺水推舟:“管它真假,你收下就是,可不要丢掉啊!”太太无意探究,把钻戒锁进抽屉,反正她不爱打扮,从来只戴价值三百美元的14K婚戒。
大儿子马克呢?他从父亲手里接过钻戒,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不敢多问,一个劲道谢。他乐昏了,好可爱的老爸,把他最大的难题摆平了。他后来偷偷拿去权威的首饰店,请专业人士评估,人家说,这一枚值四万美元,小小的遗憾在切工不大理想,不然可以卖6万美元以上。他放心了,平安夜,家里的圣诞树,灯饰闪着彩光。马克单膝下跪,给女友送上小盒子。
女友打开,只见一枚闪着迷幻粉红色光的戒指,她又惊又喜,拿起来捂在胸前。马克说:“你愿意嫁给我吗?”女友的眼睛、泪花和钻戒一起闪耀,说:“愿意!”
马里奥告诉我,这一幕上演时,全家都在场,他的心情颇为奇特,本来,负罪感怎么也甩不掉,目睹这一幕,他突然感到,前妻私奔以后,他的使命就是把孩子养大成人,为此,做什么牺牲都是值得的。从这点出发,从有钱人那里拿到一枚钻戒,也没什么大不了。他感到的轻松,这几年从来没有过。
六
半年以后,我问马里奥:钻戒的故事到此为止了吧?
他摇摇头,一言难尽的模样。
他说:这枚钻戒害得大儿子马克差点和未婚妻罗斯分手。
我说:怎么可能?
他说:罗斯是虔诚的基督徒,论人品是没得说的。她知道钻戒的价值以后,起了疑窦,问马克,这么大笔钱谁出的?她晓得马克没这个能力。马克说是爸爸送的。他们俩都明白,以父母的收入和积蓄,买它完完全全超出能力,唯一的可能是从银行借钱。若然,银行需要的抵押品呢?抵押的只能是房子。
罗斯是通情达理的,她对马克说:为了体面,置这么贵的钻戒,无端增加生活压力,弄不好连房子也被银行没收,完全没必要,我宁可不要,告诉你爸爸退回去。小两口吵起来。最后,罗斯扬言,不解决这钻戒,婚期要无限拖延。
马克只好把钻戒还给老爸,另买一枚价格为一千美元的订婚戒指,送给罗斯。
从此,马里奥已被化解得差不多的心事回来了,吃不好,睡不香,不敢见未来的媳妇罗斯,生怕她问起:“钻戒退回去没有?”
七
一个月以后,马里奥给我打电话,说:钻戒的事情,这一回总算了结!那语气透出前所未有的解脱。
事情是这样的:罗斯给未来的公公送了一本《圣经》,还告诉他,马克也受洗了。
马里奥平日不读书,看报只读马经和体育版。但这一次拗不过未来媳妇的热心,用心读起《圣经》。
里头两段话,有如重锤撞上心口:
耶和华对该隐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它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它。”
“若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剜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百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
马里奥一夜翻来覆去,半夜里叫醒太太,把事情和盘托出。太太听完,说,我可不要这不明不白的玩意,还给人家嘛!她起床,打开抽屉,拿出钻戒。
次日上午,馬里奥开车去游艇俱乐部餐厅,找到领班,请他打开电脑,找到钻戒的主人凯莉太太的地址。领班说,凯莉太太去年已去世。马里奥说,没关系,我有事向她的后代说清楚。
马里奥带上两枚钻戒,到胡桃街2999号,按了一座大宅的门铃。佣人开门,马里奥说要找主人,有要紧事。佣人便进里头向凯莉太太的女儿通报。
凯莉太太的女儿和马里奥在客厅落座。马里奥把盛着钻戒的盒子递过去,原原本本地说了经过,做了诚恳的道歉。凯莉的女儿通情达理,不为难马里奥,没提赔偿损失的事。友好地谈了一会,马里奥喝了佣人送来的咖啡,对凯莉太太的遗像深深地鞠躬三次,才告辞。
从那一天起,我和马里奥一起干活,第一次发现他如此开朗、快乐。
责编:胡破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