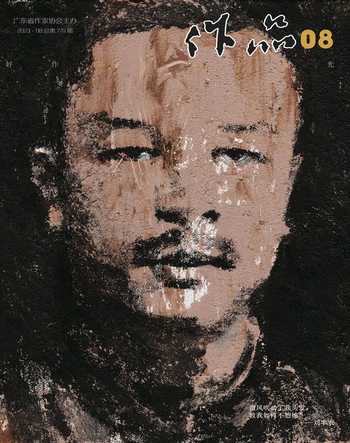“爱的绝望的气息”
行超
在大多数初习写作者的作品中,我们很快就能读出作者成长经历的蛛丝马迹,性别、地域、家庭关系、过往经历,如此等等。然而这一切,在王子健小说的阅读过程中几乎全然失效。他的小说,既有男性视角,也有女性视角;既有家乡,也有异国;既有青春少年,也有中年妇女;既有现实人生,也有幻想世界……王子健小说的多样性,不仅超越了许多由个体经历、回忆开始写作的同龄人,更显示出一种复杂而独特的美学风貌。唯一可以确定的是,这是一位具有超常想象力与虚构能力的作家,对他而言,写小说就像是建造一个王国,在那里,他便是唯一的国王。
小说《小披头的恋情》的结尾写道:“那么我也有理由相信,作为小披头最好的朋友,我也同样沾染了爱的绝望的气息——也许我也将爱李娅,至死不渝。”在这篇小说中,“爱的绝望的气息”是作者赋予“我”以及逝去的好友小披头等众多人物的共同特征,然而在我看来,这其中也刚好囊括了王子健小说的三个关键词,即爱、绝望、气息。
首先说“爱”。在早前的一篇人物专稿中,作者马兵曾经写道:“写作的母题,子健认为是‘爱。假若人与人之间一定有链接,那没有什么比爱更适合。”(马兵《王子健:大美不言,小美多话》)。的确,“爱”是王子健作品的共同主题,更是他小说共同的叙事动力与起点。《巴丹吉林遗书》中,主人公吴忌多年难以忘怀自己钟爱的姑娘楠米子,为了验证两人曾经许下的爱的誓言,吴忌一路追随楠米子的生活轨迹,终于在期待落空后,独自葬身巴丹吉林的沙漠之中;《塔克拉玛干沙漠里的游吟诗人》中,韦女士为了破解她的爱人巴依阿吉死前留下的谜语,邀“我”一同前往塔克拉玛干沙漠,在那里寻找巴依阿吉的遗骸、追忆逝去的爱情;《小披头的恋情》中,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发现在互联网的云祭祀平台上,自己离世的朋友小披头原来一直被一个女孩默默地、长久地深爱着……王子健笔下的爱情多是这样“无中生有”的,而从写作技巧上看,正是这样的“无中生有”,让王子健的小说人物得以相遇,他们在爱情中泥足深陷,又最终分道扬镳,甚至以殉情的方式铭记彼此。
小说《东方蛭蚓审讯笔录》具有科幻文学的外壳,所谓“东方蛭蚓”,乃是小说中编号13698的雇主为性爱仿生人所起的名字。年轻时的13698曾与女诗人“零余者”相爱,《东方蛭蚓审讯笔录》即是她写给这段爱情的诗作。女诗人英年早逝,13698则经历了漫长的余生,直到迟暮之年,依旧对曾经的恋人念念不忘,于是他找到了仿生人,依靠自己的想象和仿生人的配合,一次次共同创造着老去的女诗人形象。这是小说中的第一重爱情,也是其中显在的叙事线索。与此同时,小说通过“审讯录”的形式,呈现了作为小说特殊“人物”的性爱仿生人的遭遇。因为这项特殊的“工作”,它结识了“恋老”的13698、虔诚告别奶奶的13266,更与19号雇主保持关系长达十年之久。与其他所有雇主不同的是,19号愿意仿生人随意变成它自己喜欢的样子,从来不加干涉,仿生人因此逐渐爱上了这位雇主。小说最后,或许是受到13698与女诗人爱情的感染,仿生人在19号面前变成了年轻的女诗人——伴随着爱的诞生,仿生人也似乎变成了“人”,她再也无法任意改变自己的形象,以至于再见到年轻女诗人样貌的13698惊惧而死——像所有死去的爱人一样,小说最后,仿生人因“损耗严重”被强制收回,并且清洗了包括爱情在内的全部记忆。
其次说“绝望”。德国导演法斯宾德有一部著名的电影,名叫《爱比死更冷》,我猜想,王子健的爱情观大抵如此,他笔下的“爱情”故事总是死亡意象紧密缠绕,死去的爱人、为爱而死的人,仿佛唯有死亡才是爱情唯一的结局与归宿。这当然令人伤感,但如果死亡可以凝固爱情的美好,那么便不至于绝望。真正令人绝望的是没有结局的爱情,比如《东方蛭蚓审讯笔录》中的仿生人,它在临“死”前最想知道的是,如果自己被清除记忆,19號雇主是否会觉得惋惜和不舍。答案当然是否定的,19号甚至否认了与仿生人的十年交往。在这个故事当中,人比机器人更无情,而机器人真正成为了绝望的爱的主体。又比如,在小说《小披头的恋情》中,小披头绝望地爱着一个女生,这个女生的好友渡渡鸟却一直绝望地爱着小披头,而“当一个人绝望地爱着另一个人,同时其他人也绝望地爱着他,他们的绝望是不可能相互拯救的”。与小披头阴差阳错的爱情类似,小说中的“我”在网上结识了一个名叫李娅的女生,就在两人逐渐步入爱情时,李娅却告诉“我”,自己原本是个男生。“我”失望至极地离开了她,但更令人绝望的现实是,此后的“我”再也无法爱上他人,原来那个擦肩而过的爱人,就是自己一生再难找回的挚爱。
最后说“气息”。如此,当我们一一列数王子健小说中的爱情,不难发现,这种无限接近于无的情感驱动,与其说是具有实感的爱情,不如说是一种氛围,一种气息。如果为其寻找一个比喻,我以为,那便是蛇的气息——阴暗、湿冷、滑腻、纠缠不清。即便王子健的几篇小说都置身于艳阳高照的、干燥明亮的沙漠,但其中人物在爱情中的绝望,以及那种充斥着死亡意味的“蛇”的气息依旧十分浓烈。小说《摩洛哥猫首杯》集中体现了这一特征。这是一篇具有明显象征主义与颓废主义特征的作品,其核心意象“摩洛哥猫首杯”并不是什么来自异域的艺术品,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用死去的猫的头颅做成的水杯——“当时挖出来后,头骨上残余的果冻状组织、安静蠕动的蛆,和恶臭、深粉的土一起,都被我细细擦掉了。擦啊擦,月亮下,当我看见先前杨梅果冻般的红与蛆肉留下的、黏腻的白中和时,我甚至忍不住亲了它一口;还没擦干净,凑得太近就会看见剩下的蛆;我用食指插进它的眼眶,把它架在空中,享受那些依然活着的、顽强的蛆温柔的舔舐,就是气味太差了——像和不爱干净的人,做那个。为让它好闻些,回来后我还一遍遍淋上小姨给我的香水。”“猫首杯”及其制作的过程,突出显示了一种极端恐怖的、充满死亡的腐朽气息的审美价值与主观情绪。与这一意象构成互文的,是小说人物病态、扭曲的精神世界,“我”出生在一个有着精神疾病家族史的家庭,受姥姥的遗传,小姨从小性格古怪、歇斯底里,最终在摩洛哥当着男友的面自杀;好友漾子冷酷、乖戾,不仅与许多男生纠缠不清,更当着“我”的面,亲手打死并埋葬了一只小猫。小说不惮于描写那些恐怖的、令人作呕的细节,并由此呈现了人性之恶,但作家显然无意于批判这种丑恶,就像波德莱尔笔下的《恶之花》一样,王子健试图在一个充满罪恶的世界中寻找价值,在恶中发现美。
以《摩洛哥猫首杯》为代表,王子健的写作具有一种明显的唯美主义倾向,去道德化的立场、死亡体验、颓废美学等,在他的小说中均得到了极大的张扬。我们知道,在古典美学中,“美”与“善”常常是紧密联系的,所谓“真善美”“里仁为美”等等,背后无疑都包含着明确的伦理标准、价值判断。而到了以《恶之花》为代表的现代派,“美”与“善”逐渐分离,波德莱尔在废墟中、在垃圾堆里、在骷髅和流浪汉身上发现了美,或者说,他重新定义了美。于是,现代美学中,“什么是美”成了一个越来越复杂的问题,“美”的多元性也由此被彰显出来,而这种对美的极致追逐,在19世纪末的唯美主义者那里逐渐走向顶峰。在这个意义上,王子健的小说无疑具有明显的现代特征,病态、扭曲、凶残、冷酷,正是他小说的核心美学。毫无疑问,王子健是一个享有极高文学才华的写作者,奇崛的想象力、诗性的语言、对美的敏锐感知与建构,在他笔下自然地渗透、融合,他的小说由此自成一格。但是,正如“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所遭遇的困境一样,王子健的小说在极力彰显美的同时,也多少被美所拘囿、所束缚。
即便唯美主义始终否认艺术与现实之间的关系,但是,毋庸置疑,唯美主义的出现,恰恰来源于19世纪的工业化以及资本主义兴起这一重要的历史现实。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方面,新兴资产阶级急于摧毁旧的道德与旧的伦理,进而创造以自我为中心的新的价值;另一方面,工业化城市的出现,让人们时刻感知着一种全新的都市生活,并且在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现实中产生了种种精神畸变。也是因此,波德莱尔、兰波、马拉美以及王尔德的作品才具有开创性的艺术价值。然而,在今天,在我们所身处的现实世界之中,曾经为19世纪艺术家们提供“震惊体验”的那种生活,究竟还能给我们带来多少新意和创造性?或者说,我们该如何发现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震惊体验”?在这一意义上,一味地回返乃至模仿19世纪晚期的唯美主义,在今天不仅空浮,甚至显得过于机巧。作为一個初学写作的年轻人,王子健找到了自己钟爱的艺术路径,以此确立了自己独立的美学风格,这当然是一件难得的好事,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如果仅仅以此作为今后写作的唯一信仰,那便很有可能限于狭隘。
或许小说《蒜薹女的华丽人生》正是王子健试图突破唯美主义,进而为自己的写作寻找新的可能性的一次尝试。小说的开篇颇有意味:“我母亲过去常说,一个女人一生中总会有那样一个时刻:知道今天的蒜薹多少钱一斤,比昨天便宜多少,或者贵多少。当然,不一定是蒜薹,也可以是萝卜、白菜、韭黄或者猪肉。”与王子健的大多数小说不同,这篇小说很大程度上放弃了美学的雕琢,显示出生活的经验、现实的智慧。小说主人公是一个四十岁就经历了两次丧偶的中年女性,她长年照顾年迈的母亲,儿子远在他乡、负债累累,好友王姜癌症去世,曾以为可以共度余生的老墨也离她而去。在小说中,王子健努力书写着女性的艰难、凄苦、孤寂,他敏锐捕捉并且描绘了一种极端的个体处境。我们不难感知作家对这一现实乃至群体的关怀,但也正是在这篇小说中,年轻写作者的短板更为直接地表现了出来。在这样一个现实题材作品中,在小说中这些相对远离作家个人生活经验,又很难通过单纯的想象完全支撑起来的人物形象上,作家难以提供真实的、令人信服乃至使人共情的生活细节,而一旦缺乏这样毛茸茸的细节,小说就仅仅是“虚构”,写作者的关怀、理念乃至美学,最终也只是想象的空中楼阁。与这篇小说精彩的开篇相呼应,“蒜薹女”本应是极具生活质感和现实意义的人物形象,“蒜薹女”与“华丽人生”之间的冲突,更是包含着一种文学的内在张力,然而让人略感遗憾的是,在最终呈现的文本中,“我”这个平凡的中年女性,究竟是如何日复一日地与“蒜薹”打交道,又是为何收获了“蒜薹”这一人物身份的等等,这些问题在小说中并未得到深入展开,她的人生因何“华丽”、有何“华丽”也未及细致刻画,因而,这个人物显得有骨架却缺血肉,总体上不够立体和丰满。
与唯美主义的主张略有分歧,我相信,所有的艺术感受都来源于生活的赐予,一个只有天赋而没有生活的作家,他的作品就像是断了线的风筝,即便工艺再精美,却始终没办法飞向天空。在这个意义上,小说也是时间的结晶。文学史上从不缺乏才华横溢的作家,但若想拥有更为持久的创造力,就必然要经历真实的生活,而这一点,恰恰是年轻的王子健所欠缺的。我想,对于今后的王子健而言,写作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他更需要去生活、去尝试,去耐心等待漫长的未来。
责编:郑小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