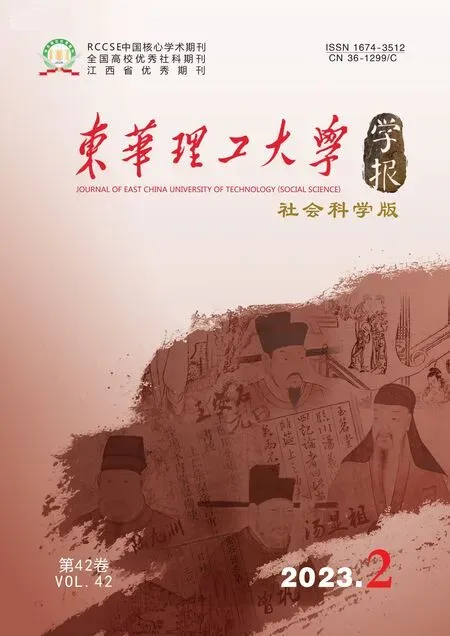论21世纪长篇小说中的农民“返乡”题材
杨超高, 王梦想
(东华理工大学 文法与艺术学院,江西 南昌 330013)
一般而言,返乡是指回到家乡,在本文中,返乡特指由城市回到乡村。21世纪以来,伴随着城市发展与乡村建设进程的加快,农民进城与返乡越来越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以之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也日渐增多。如果说20世纪80至90年代的乡土小说(也包括21世纪以来的不少作品)更多是写农民进城的苦难遭遇,那么近年来涌现出来的农民“返乡”书写则成为一种与之相关却又很不相同的叙事潮流。有相当多的作品如关仁山的《金谷银山》《天高地厚》、周大新的《湖光山色》、苗秀侠的《皖北大地》、尹马的《回乡时代》等关注乡村现实与变革,表现农民返乡后的经历与命运,他们塑造了一批新农民形象,讲述了一系列属于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1 农民“返乡”书写的历史与转向
要分析21世纪长篇小说中的农民“返乡”书写,发现其独特意义与价值,就有必要对之前小说中的返乡农民书写做一梳理。
由城返乡的一个前提是城市的出现。中国现代城市文明大概是从20世纪初才逐渐兴起,与之相应,中国文学中的农民进城与返乡书写也差不多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如鲁迅的《阿Q正传》等作品。然而,这一时期作家的意图更多的是揭露传统农民身上的文化痼疾,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1]84。对国民性揭露与批判的执着,却也遮蔽了农民作为个体在城乡两种文化语境之下的生存境遇。此后,洪灵菲的《归家》、赵树理的《李家庄的变迁》、梁斌的《红旗谱》、浩然的《艳阳天》也谈及了农民返乡,但他们更多的是从革命维度来表现农民被压迫及走向觉醒、反抗的过程,缺乏对返乡后农民心灵变化过程的表现。事实上,至少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农民“返乡”书写是比较匮乏的。
步入20世纪80年代,中国城乡格局发生了变化。一方面,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城市化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国家逐渐放宽了户籍管理政策,农民开始成规模地进城与返乡。这在新时期小说中也有充分表现,如高晓声笔下的陈奂生,可作为农民进城与返乡的一个典型代表。然而,由于作者仍旧是以国民性批判为视点,“是在历史发展的纵向上,对中国农民的命运历程做系统剖析”[2]236,由此对陈奂生的进城叙述主要是在物质方面,他并未真正触摸到城市的肌理。对于陈奂生来说,乡村比城市更有吸引力,因此他既没有想过,也不会在城市生活,“陈奂生骨子里流淌的仍然是中国传统农民的血液”[3]238。相比之下,《人生》中的高加林和城市的关系更加深厚、复杂,他渴望进城的同时更希望能够获得城市的认同,城市的拒斥让他无奈返乡,真实呈现出了农民进城的困境。城市之行对于高加林来说更像是黄粱一梦,梦醒之后各归其位。为了表达自己的乡村立场,作者设置了高加林返乡之后,得到了乡村的宽宥与救赎。然而,用乡村拯救的传统命题来表达城乡分治对人命运的戕害,过于简单地把人物命运归为生不逢时、命运不济,这在无形之中消解了作品对现代性本身的批判与反思。总之,20世纪80年代的农民“返乡”题材虽触及农民返乡的事实,但限于各方面的因素,并未有真正的突破。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早期进城返乡的农民带来了城市繁华的想象。无数的农民怀着美好的愿望向城市挺进,渴望在城市获得一席之地,但城市给予他们的往往是“否定性”的体验,农民进城遭遇现实生存与身份认同的双重困境成为作家书写的重点内容。譬如尤凤伟的《泥鳅》、鬼子的《瓦城上空的麦田》、孙惠芬的《吉宽的马车》、陈应松的《太平狗》、方方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曹征路的《那儿》。这些作品都写到了进城农民所经受的物质生存和精神压力上的双重苦难。
遭逢进城失败后,返乡自然成为农民的最后选择,但实际上,返乡的结果往往是“无乡可依”。不同于80年代陈奂生、高加林的命运,90年代后的乡村并未像“地母”一样包容、接纳返乡农民,反而以传统道德为借口对他们进行羞辱和审判。在关仁山的《九月还乡》中,曾在城里做风月生意的九月和孙艳返乡后,文本用兆田村长的眼光审视她们,“没发现她俩有一点羞耻的意思”[4]20。为了拿回被开发商霸占的土地,村长鼓动九月以身换地,其原因无非是九月在城里失过身,这次献身也算不上什么。女性身体的随意征用所隐含的话语,正是乡村对返乡女性的道德审判与惩罚。贾平凹的《高老庄》同样也揭示了返乡农民的困境,乡村用暴力的方式完成了对返乡女性的道德处决。苏红返乡后遭到以蔡老黑为首的乡人的欺辱,他们对苏红曾经的“职业”冷嘲热讽,在光天化日的械斗中蛮横地扯光了苏红的衣服。文本的深刻之处是作者不仅批判了乡村道德对返乡女性的外在伤害,还对返乡女性个体内心深处潜藏的自我道德审判进行了批判。苏红对乡人的侮辱不但毫无反抗,而且任凭处置,把道德审判当作是一个必经的过程。这种内在的自我道德审判展现出来的不仅仅是农民尊严的失却,更是农民主体性的丧失。除了这两部作品外,罗伟章《我们的路》中的郑大宝和春妹,刘继明《送你一束红草花》中的樱桃,陈应松《夜深沉》中的隗三户,孙惠芬《民工》中的鞠福生父子等,也有相似的命运和遭遇。从整体上看,这类作品构成的“返乡”书写模式,将重点放在揭示农民的生存艰难与精神痛苦上,存在着强化城乡对立(甚至丑化城市)的弊病。
近年来,文学创作中苦难化的返乡农民书写有所改观,作家不再执着于农民“苦难”的渲染,而是“以建设性的姿态思考着中国乡村的未来,并试图提出乡村重建的方案”[5],塑造出了一批返乡建设者。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当下的乡村建设与发展,吸引了不少进城农民主动回到乡村,这种社会现实构成了作家们新的写作内容。此外,一些作家也开始有意识地反思、纠正20世纪80年代以来“进城—返乡”农民书写的偏颇,比较客观地书写返乡农民,这都促进了21世纪返乡农民书写的转型。长篇小说由于篇幅较长、叙事自由,可以充分展开农民返乡后的故事,因此返乡建设型的农民形象塑造在长篇小说领域尤为明显。其中比较典型作品有周大新的《湖光山色》、关仁山的《金谷银山》《天高地厚》《日头》、苗秀侠的《皖北大地》、尹马的《回乡时代》等。这些作品不仅将叙事重心从“进城”转向“返乡”,而且对既往的城乡对立模式与农民“苦难展览”式的书写方式进行了反思与改写。他们相当正面地叙述了返乡农民的经历与命运——农民返乡后扎根乡村,并致力于乡村发展。在这个过程中,返乡农民不仅表现出对乡村身份的认同,而且展现出具有现代性的主体形象,从而为新时代农民形象的塑造构画了新谱系。
2 乡村身份认同与现代性主体建构
21世纪长篇小说中,农民“返乡”题材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返乡农民对乡村身份的认同。身份认同问题是“苦难”型进城与返乡农民书写长期以来都没有解决的问题。在“苦难”型叙事中,农民常常陷入身份认同的困境之中——他们拒绝(否定)乡村,又不为城市所接纳,返乡也无法重新融入乡村,因而无法确证自我身份。然而,“身份确认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个内在的无意识要求。个人努力设法确认身份获得心理安全感,也设法维持保护和巩固身份以维持和加强这种心理安全感,后者对于个性稳定与心灵健康来说,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6]332。身份认同问题导致“苦难”型书写笔下的农民遭受着身体和精神双重伤害。不同于“苦难”型农民在身份认同上的“左右为难”,21世纪长篇小说中的返乡农民最终以乡村身份的认同,维护了自身的心理安全。
例如,《金谷银山》里的范少山就以认同自身的乡村身份来拯救自己心灵的失衡。最初范少山“觉得自己在北京就像一滴油花,漂在水面上,看似光亮,却总也融不进水里。而一滴油花能做什么?反而把水弄脏了。范少山是个啥人?城里人认为他是乡下人,乡下人认为他是城里人。他就像画好油彩扮上妆的演员,一登台,却被观众轰了下来”[7]55。城市和乡村的双重拒斥,身份的尴尬一度让他怅然若失。而在他返乡后,目睹昔日生活的乡村沦落到几近要搬迁的地步,内在的乡村情感燃起了他身为乡村之子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他觉得自己有责任、有义务拯救乡村。这种行为背后隐含的正是范少山对自身乡村身份的认同,也正因为如此,范少山最终决定“就是碾成一颗钉,也要钉在白羊峪!”[7]63
《皖北大地》也塑造出了一个对自身乡村身份认同的返乡农民——安玉枫。作为“一个背井离乡多年,早已把异乡当作故乡的人,突然被故乡拽了一把,就拽醒了”[8]98。多年的城市生活依然改变不了他内心深处对于自身乡村身份的认知。他对从家乡带出来的马灯视若珍宝,妻子失手打碎后,从未和妻子有过争执的安玉枫,竟和妻子大吵。在城市里稍微有些积攒后,他立马想到的是投资家乡,即使首次投资家乡陷入骗局,仍无悔地选择再次投资,这些行事背后潜藏着的即是他对自身乡村身份的认同。《回乡时代》里的周楚阳也属于这类人物。时常涌起的乡愁,让他在城市里若有所失,就连晚上做梦也是关于家乡的场景,投资首先考虑的也是家乡,这些都表明他从未忘记自己的乡村身份。范耀华认为“人的主体身份意识的确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体对自我主体身份的认识与定位”[9]36,无论是范少山、安玉枫还是周楚阳,他们对自己身份的定位就是乡村,乡村身份认同缓解了返乡农民因身份尴尬而产生的紧张焦灼情绪,让他们失落的心理重新找回了平衡。
在乡村身份认同的基础上,返乡农民凭借城市经验在投身乡村建设的过程中确证了自我主体的意义。这就构成了21世纪长篇小说中农民“返乡”书写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即农民现代性主体的建构。有学者指出:“农民的现代性主体建构既是一个外在的前现代的‘农民’身份制废除的过程,也是一个内在人格蜕变的过程,这种人格蜕变具体地说就是挣脱传统乡土社会所塑造的文化心理、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实现由‘受外在权势支配’的依附性人格走向现代自由人格的过程。”[10]费孝通的《乡土中国》认为,传统的中国乡土社会是阿波罗式的,农民依附于土地而生,在“恒居不动”的乡村社会中培养出来的农民也是阿波罗式的,无论是思想还是行为都偏安于现状,追求生活安稳,这也成为传统农民最显著的符号特征;与之相反,城市文化培养出来的是浮士德类的人物,为了能在奔涌激变的城市波涛中生存,他们必须不断更新自己的思维,调整自己的行为方式,以适应城市的快速发展。城市环境的多变促成了城市中的人不满足于现状,具有不断挑战新事物的冒险精神。这些特征在21世纪长篇小说中的返乡农民身上有着突出表现,展现了具有现代性的农民主体。
为了使返乡农民现代性主体建构具有合理性,作者首先对他们的教育水平做了强调,他们大都接受了一定的教育,建立了现代文化人格。比如《湖光山色》里的楚暖暖初中毕业,《金谷银山》里的范少山、《皖北大地》里的安玉枫、《天高地厚》里的鲍真、《回乡时代》里的周楚阳都是高中毕业,《日头》里的金灶沐甚至上过大学。接着作者又对他们在城市获得的现代经验做了重点勾染,这种以“现代”为核心的“城市经验”恰恰改造了他们[11]——楚暖暖、范少山获得了现代意识,安玉枫、周楚阳积累了资本,还有许多返乡农民在城市生活中开阔了眼界,在文化思想方面得到了更新……显然,他们与传统农民有别,他们不再像祖辈那样保守、落后。知识文化的储备及城市经验的取得使得他们能够运用现代理性来建立自我主体性。
范少山就是一个运用现代经验与自身主体性,最终帮助白羊峪脱贫的人物。他先是不辞辛苦地寻找“金谷子”发展特色农业;同时考虑到仅靠“金谷子”作为村民的收入来源又太单一,于是租用农场种植绿色蔬菜;为了提升农产品的竞争力、满足高档消费者的需求,在孙教授的指点下,他号召村民栽培无公害的“金苹果”;村里交通不便影响到农产品的出售,范少山带领村民开山修路;为了解决乡村孩子上学难的问题,他出资重建学校;村子供电不足,影响村民的日常生活,他联系并引进外来公司为村子发展光伏发电;村庄发现溶洞后,他又提倡边保护边发展……物质上的提高还不能满足范少山对于“新乡村”的想象,他找到了刻着白羊峪村训的石碑,将其立在村口,希望村民把乡村精神传承下去。此外,范少山积极学习现代互联网知识,发展互联网农业,让农业与现代接轨。在范少山的努力下,白羊峪从一个贫穷落后甚至要搬迁的村庄发展成了示范村,引得报纸、电视争相报道。范少山返乡后的一系列行为,展现出来的是一个不断转变思想、更新观念,具有现代思维方式与行为观念的农民主体形象。
《湖光山色》里的楚暖暖亦是如此。楚暖暖返乡后因给母亲看病花光了全部积蓄,面对一贫如洗的家庭现状,她没有坐以待毙,而是想尽各种方法贴补家用。在婚姻方面,她敢于反抗父母的包办婚姻,和抢亲的村主任斗争,争取婚姻的自由与自主,婚后帮助丈夫成功竞选了村主任。楚暖暖作为接受城市“现代教育”的归来者,她不断启蒙丈夫摆脱落后、守旧的小农思想。在谭教授的点拨下,她利用楚王庄现有的楚文化资源开办民宿,成立南水美景旅游公司,她和五洲公司合作共同开发楚王庄,建立赏心苑,拉动当地村民就业。当丈夫矿开田陷入权力崇拜几近丧失人性,勾结薛传薪损害村集体利益的时候,楚暖暖展开了与丈夫及薛传薪的斗争,并最终取得了胜利。在楚暖暖身上,作者呈现出的是一位具有现代思想与主体性的新农民形象。
《皖北大地》里的安玉枫同样如此。他从城市回到了似乎被现代化抛弃的安大营,凭借着敏锐的市场意识及现代管理经验,选择大棚蔬菜种植,动员当地农民入股,获得收益。在村霸红绿灯使出各种手段阻挠安玉枫,使大棚种植遭受巨大损失,入股农民也对安玉枫产生强烈不满时,安玉枫没有畏缩,而是运用才智与其对抗,抓住其把柄,并一举获得了胜利。另外,就黑麦种植产生的秸秆问题,安玉枫向农学博士朱宝山请教,促成了农业生态链的循环发展。再如《天高地厚》中的鲍真,她建立奶牛场、酱菜厂,实验水稻田养蟹,经营棉田,利用土地承包转身变为种粮大户,探索绿色农业,开办农民协会,勇闯北京建立自己的农产品品牌,最终完成了其所在乡村的蜕变。《回乡时代》中的周楚阳亦是如此,他不仅懂得运用自身的影响力,还深知和官方合作对于促进乡村发展的重要性。在返乡后,随着对家乡了解的深入,周楚阳逐渐摆脱了传统的商人思维,心系乡村发展,真正致力乡村的脱贫攻坚工作。
总之,在这些返乡农民身上,展现出来的是一种“接受社会的可变和开放的形式……不去怀念存在于真正的和幻想出来的过去之中的‘固定的冻结实了的关系’,学会变动,学会依靠更新而繁荣”[12]479的精神,而这正是现代城市文化所培养出来的浮士德精神,是返乡农民在经过城市洗礼后,逐渐抛却传统守旧的思维模式与行为观念,形成了与“城市生活相适应的价值观念、生活态度和社会行为模式”[13]。相较于那些盲目被动承受命运安排、在现实苦难面前退缩的传统农民,这类返乡农民在城市现代“教育”中认识到了主体的力量,并主动选择去改变现实生存困境,而广阔的乡村正好为他们提供了展示主体力量与现代经验的场地。返乡农民正是在致力于乡村发展、投身乡村建设过程中实现了现代性主体的建构。
3 农民“返乡”题材转向的艰难
21世纪长篇小说中返乡建设型农民形象的塑造,体现出作者试图对惯有的农民形象(典型如鲁迅笔下愚昧麻木的阿Q、祥林嫂;沈从文笔下静美纯良的翠翠、老船工;赵树理笔下思想落后迷信的二诸葛、三仙姑;贾平凹笔下苦难悲惨的刘高兴、五富等)进行改写的一种努力。就文学本身来看,这种尝试确实使得新世纪返乡农民呈现出别样的面貌,构建了新时代农民形象谱系。但也应该注意到,农民“返乡”题材的书写仍存在一些不足,甚至在作者极力建构的乡村身份认同与现代主体性方面也不无问题,这也可以看出农民“返乡”题材书写转向的艰难。
一是乡村身份认同存在悖论。为了呈现农民返乡建设的合理性,21世纪农民“返乡”题材的长篇小说中不断以乡愁、乡情强化返乡农民对乡村身份的认同,但在细微处我们还是能够发现这些认同存在罅隙。比如《天高地厚》中鲍真对城乡的态度:“鲍真自己也明白,城市是别人的,不是她们的。”[14]99她内心深处认为终归要返乡。从表面上看,她是认同自身的乡村身份而返乡,但实际上这种认同是基于乡村身份使她无法融进城市,无法获取城市身份而做出的妥协,“这是一种身份无法认同之后的身份强化——无法得到认同的是城市身份,强化的是乡村身份”[9]55。那么,她返回乡村旋即搞投资建设的初衷,表层看是强化自身的乡村身份,实际却是“无法融入城市、获得城市身份确认后的自我暗示,是挑战式的宣告,也是身份‘悬浮’中的自救焦虑与艰难确认,能逐渐演变成一种将计就计的、与城市相抗衡的武器”[9]55。因此,她的乡村身份认同,其实是为了消除身份悬浮、焦虑、紧张状态而采取的退步策略,这使得鲍真类人物表现出的乡村身份认同多了一份刻意,其投身乡村建设的崇高感也在一定程度上被消解。
又如《湖光山色》里的楚暖暖,她对自身的乡村身份认同感并不强烈,返乡的原因也并非乡愁的指引。返乡之后,她并不是不想再次进城,而是囿于家庭方面的原因不允许她再次进城,她对此也不无遗憾。随后进城培训时,当看到“店内五彩缤纷的灯光,窗外连绵不断的车流,四周热闹喧嚷的市声一下子想起了当初打工见识过的北京城。在这一瞬间,她再一次感受到了城市对自己的吸引力,做一个城市人真好呀!”[15]224楚暖暖对城市的无限向往,也不免让人质疑她扎根乡村、推动乡村致富的决心。
同样,《回乡时代》中的周楚阳对自身乡村身份的认同也存在问题。作品中虽然多次写到了周楚阳的乡愁,然而他投资的初衷却并不是致力于乡村的建设与发展,而是为自己城里的事业安排后路,是一名商人逐利的需要,这就使得他的乡村身份认同存在矛盾。尤其是周楚阳在投资建设乡村的同时,主动邀请律师界翘楚在南广建立分公司,试图用法律维护乡村的营商环境。中国传统的乡村社会是礼治社会,习惯靠礼治维持秩序解决争端。律师、律师事务所作为“现代文明”社会的典型象征,它们的引入意味着乡村礼治功能的失效。南广的发展前途已不是乡村,而将是一座名为南广的城市。那么,他对自己乡村身份的认同,也就失去了实际的意义。
二是作品建构的现代性返乡农民主体本身也存在裂痕。21世纪农民“返乡”题材小说中设置了诸多返乡农民抛却乡村老旧传统,用现代性思维方式与行为模式处理各种关系与事件的情节,然而具体叙述却存在着各种悖论。返乡农民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犹疑与困惑,直接影响了其现代性主体的建构。如《皖北大地》中的安玉枫,他在返乡投资建设的时候,展现出的是一个具有杀伐决断气质的现代经营者,然而在面对个人感情的时候,他又回归了传统。他在都市妻子温晓莉和乡村玩伴之间游移不定,这种游移正显示出了他对于现代与传统的矛盾。安玉枫对杨二香的选择,某种程度上暗含了他对传统的服膺。再如《湖光山色》中的楚暖暖,她用现代文明眼光审视乡村传统的时候,会对奶奶光着膀子的行为深感不适,会惊讶于村子竟还存在着“阴亲”恶俗。然而,在现实生存“屡遭挫折”后,她的“拜神求佛”行为又复活了传统社会塑造出的文化心理。为了获得扩建旅舍所用的宅基地,楚暖暖再次以身体为资本进行交易,这种“商业交易”行为也是对其现代性主体的破坏。尤其是在“以身救夫”成功后,面对险恶的社会,楚暖暖又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变回了“小女人”,完全依附于丈夫,呈现出传统社会中女性对男性的依附。总之,在文本的细节叙写中,我们仍能发现返乡农民主体性建构存在的缺陷。
除此之外,文本就返乡农民现代性的获得,陈述得过于简单甚至并不具备说服力,这也使得返乡农民建设乡村的行为本身并不能使人信服。比如楚暖暖,她的现代性思想及发展乡村的凭借主要来自城市经验。然而,一方面,她主动抛弃了传统乡村经验,已不再是一个典型的农民;另一方面,也存在以下疑问:在城市里她一直处于社会的底层,如何能接触到城市现代化发展的“秘诀”进而从事乡村建设?难道仅靠后来的一次进城培训,就能够脱胎换骨而成为具有现代商业思维模式与行为方式的现代性主体?这显然并不真实。因此,楚暖暖的返乡行为更像是作者为了完成乡村建设的“命题作文”而强行从城市里拉回的一个“工具人”(她已经不像是一个农民了),这也就无怪乎一些评论家对楚暖暖人物塑造的合理性提出质疑与批评。《天高地厚》里的鲍真只是在城里打零工、做保姆,又如何能够在返乡后摇身一变成为不断在乡村实验、探索乡村走上现代化发展之路的建设者。《金谷银山》里的范少山在城里也只是一个卖菜的小商贩,如何凭一次返乡看到乡村的贫瘠及老德安的死亡就决心要扎根乡村,并依靠自己的力量完成建设现代化乡村这一庞大工程。显然,作品对他们现代性的获得缺乏令人信服的描写,那么,他们的返乡建设的行为也就缺乏足够的支撑力。
三是这类作品表现出的浪漫传奇风格,也反映出21世纪长篇小说中农民“返乡”题材书写转向的艰难。譬如,《金谷银山》里范少山的经历充满着奇幻、理想化色彩,“金谷子”“金苹果”“溶洞”的发现都充满着偶然性,但又像是为他量身定做的。每次遇到困难,范少山都能够靠自己的智慧和力量解决,在每次困难的解决中,他的品格和毅力都得到了锻炼。很显然,这种情节设置过于理想化、传奇化了。同样,《湖光山色》里楚暖暖的发家也是偶然发现楚长城,碰巧和谭教授相遇,并在其点拨下开办楚地居。又恰巧和薛传薪相逢,并与其合作开发楚王庄。对楚王河过于神秘的描绘,都增添了作品的传奇色彩。而在《皖北大地》中,主人公安玉枫的形象则更像是一个救世主,无所不能,这样的人物形象塑造缺乏合理的逻辑,叫人难以信服。《回乡时代》里的周楚阳更是一个带有主角光环的人物。几乎所有的人都围绕在他身边,如县政府极力拉拢他,并把吸引返乡投资的重任放到他肩上,他也不负众望,在其努力下越来越多的人返乡投资。事实上,无论是范少山、楚暖暖、鲍真还是安玉枫、周楚阳,这些返乡农民都有类似的特征,他们带着英豪的气质,在一片荒地展开自己的英勇事迹,困难、挫折是他们光荣的印记,而他们最终都完成了英雄的事业。在这些返乡农民身上甚至能窥见“十七年”文学的某种痕迹,相似的叙事模式与形象塑造,使得返乡农民书写带有概念化的弊病,这也是农民“返乡”题材书写转向艰难的一个重要表现。
造成农民“返乡”题材书写转向艰难的原因有很多。首先,就现实社会发展而言,当前城市仍然是“现代化实践和现代性文化构想中的核心目标,甚至是唯一目标。在现代性的时间序列中,城市处于先进的、新的、未来的一端,而乡村相反”[9]127。这种客观大环境势必影响作者的创作,造成作者主观情感上着意于塑造出能够代表这个时代的新返乡农民形象,但在客观书写时,又往往受到“城市中心论”的影响,从而造成了作品中返乡农民在现代与传统之间的撕裂,影响了农民“返乡”题材书写的转向。
其次,从作家身份角度来看,书写这类作品的作家大都出身于乡村,这使得他们对乡村具有本能天然的亲切感,情感上更倾向于乡村。但他们成名之后又普遍生活在城市,目睹了现代化所带来的社会巨变与生活便利,再加上城市化、现代化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他们对此也持肯定态度,这使得作家们在处理乡村身份认同问题时“普遍存在激情有余、理性不足的问题”[16],即在传统乡村与现代城市之间徘徊不定、难以抉择。而这种创作观念投射到文学创作以及人物塑造身上,就出现了返乡农民一边认同乡村身份,一边又渴望城市身份;一边秉持着现代观念,一边又不由自主陷入传统当中,进而阻碍了农民“返乡”题材书写的转向。
最后,从农民本体角度来看,农民本身就背负着传统的重荷。几千年所形成的文化心理、思维方式与行为模式已经积淀为一种恒久的乡土基因,在农民身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反观中国的现代化历程也只是百年左右,何况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社会一直处于动荡之中,真正的城市现代化过程也不过几十年,在如此短的时间就让农民完全卸下传统的重担,淘洗干净传统的乡土基因,显然也并不现实。
4 结语
过去,研究者常用“城市异乡者”“流动”农民、“游民”等称谓描述进城农民的生存境遇与精神状态,无论是哪种称谓,展现出来的都是农民身份与灵魂无法安置的问题。21世纪长篇小说中展现出的返乡农民对乡村文化与身份的认同,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进城农民身份焦虑所带来的心灵失衡与人格异化,这既是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持续的农民苦难书写的纠偏,也丰富了21世纪以来农民形象的塑造。借用郭艳在评价苗秀侠作品《皖北大地》中的一句话——“作家无疑试图重新建构中国现代农民的主体性,期待这些曾经低到尘埃里的大多数‘沉默者’能够获得作为一个现代人的尊严。”[8]7尽管返乡农民乡村身份认同与现代性主体建构细节处仍存在缺陷,但是这正表现出农民“返乡”题材书写转向的艰难。农民返乡本身就是一个复杂、动态的社会现象,简单地以一种评价方式去归纳人物形象特质显然不合适;同时,返乡农民也是一类复杂立体的人物形象,需要在时代动态中把握,才能更好地分析出返乡农民形象的时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