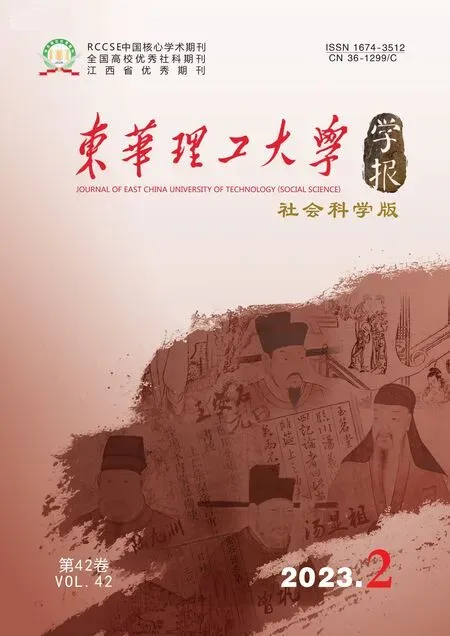王安石与二程天道论新探
关素华
(南京中医药大学 医学人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关于王安石新学与二程理学的比较研究,学界已有不少(1)较早如肖永明的《北宋新学与理学》,作者分别从为学方法、社会政治思想和本体论建构的特点对两者进行比较研究。尤其是在本体论建构方面,肖永明的分析可谓客观深入。参见肖永明.北宋新学与理学[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57-215.类似的研究还有王书华在其博士论文《荆公新学初探》中讨论王安石与二程对待《周礼》《孟子》、佛老态度的异同及二者政治思想的分歧与对立。相比肖永明先生,王书华的比较研究更为细化,但是两者都未深入到王安石的道论研究之中。。目前,学界影响较大的是余英时先生从“内圣外王”的角度比较两者的观点,他认为王安石新学和二程理学都主张“内圣”与“外王”并重,只是在“内圣”的具体内容方面两者发生了重大分歧(2)余英时先生认为,他们都处在北宋重建秩序的政治文化背景之下,主张“内圣”与“外王”并重;只是在“内圣”的具体内容方面,两者发生了重大的分歧,二程批评王安石的“道”因杂入佛老而不纯。参见余英.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M].北京:三联书店,2004:48.。卢国龙先生从政治变革和儒学复兴的角度,分析了王安石新学与二程理学的承接关系,认为王安石新学在理论上表现为天人二分、人道人文服从于自然天道,在实践中表现为难以避免独断论,这正是蜀学和二程理学所要匡正的(3)卢国龙分析认为,正是因为王安石新学“不能把理性精神与人文情怀两个方面有机地结合起来,自然理性被作为第一义的,人文情怀被作为第二义的,在理论上就表现为天人二分,人道人文服从于自然天道,在实践中则难以避免独断论……这是新学派的一大思想盲点,有待于蜀洛学派予以匡正。”参见卢国龙.宋儒微言:多元政治哲学的批判与重建[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24.。我国台湾学者夏长朴先生主要从文本出发,全面分析了二程批评王安石之学的原因、重点和影响(4)就二程批评王安石新学的重点方面,夏长朴先生主要列举了介父之学支离、介甫不识道、介甫不知臣道、介甫坏人主心术等方面,基本囊括了二程对王安石之学的正面批评。参见夏长朴.介父之学,大抵支离——二程论王安石新学[M]//王安石新学探微.台北:大安出版社,2015:209-249.。以上研究基本涵盖了学界对王安石新学与二程理学比较研究的主要方面,但是仍然存在不足之处。第一,学界鲜有专门从二者的天道论层面进行深入比较研究。第二,多数研究仍然是以二程理学为立场,对王安石新学进行批评,从而忽视了王安石新学自身的理论架构及其合理性,没有给予王安石新学一个合理的学术地位。第三,学界忽略了王安石与二程关于“气”的比较研究,气论不仅是北宋儒家学者关心的重要主题,也是王安石和二程天道论的重要内容,因而应当给予充分关注。
在《二程集》中,二程(5)虽然程颢与程颐的思想有些许不同,但是基本观点、理论框架、思维模式都是一致的,故本文不对二者做具体区分,而是把两者合而言之。对王安石的批评多达40多处,对其天道论的批评占据多半。综合以往研究,笔者主要从“佗不知道”“以气明道,气亦形而下者”“介父之学,大抵支离”三个方面来考察二程对王安石天道论的批评,进而揭示二程对王安石批评的不当之处,还原王安石天道论的本来面目。
1 “佗不知道”与“道非物也,然谓之道,则有物矣”
在《河南程氏遗书》中,二程的弟子记录了一段程颢评论王安石之“道”的话。他说:
先生尝语王介甫曰:“公之谈道,正如说十三级塔上相轮,对望而谈曰,相轮者如此如此,极是分明。如某则憨直,不能如此,直入塔中,上寻相轮,他勤登攀,逦迤而上,直至十三级时,虽犹未见相轮,能如公之言,然某却实在塔中,去相轮渐近,要之须可以至也。至相轮中坐时,依旧见公对塔谈说此相轮如此如此。”介甫只是说道,云我知有个道,如此如此。只佗说道时,已与道离。佗不知道,只说道时,便不是道也。有道者亦自分明,只作寻常本分事说了。孟子言尧、舜性之,舜由仁义行,岂不是寻常说话?至于《易》,只道个“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则和性字由字,也不消道,自已分明。阴阳、刚柔、仁义,只是此一个道理[1]5。
就这一段话,不同学者的解读略有不同。余英时先生认为,这段话表明二程批评王安石的“道”是佛而不是儒[2]50。夏长朴先生则认为,此处表达出程颢批评王安石论道只是停留在语言描述,将己与道分离。另外,王安石论道缺乏身体力行的实践,总归是无法真正体悟道。程颢认为自己所论的道,则是脚踏实地去践行,工夫看似笨拙,实际上却从未离道,而是逐渐地接近道[3]218。余英时先生和夏长朴先生的解释各有道理。除此之外,程颢对王安石论道的批评应当还有一层意思,即程颢认为王安石所论之道本质是“虚无”,故而他才会说王安石的道如“捉风”。
荆公尝与明道论事不合,因谓明道曰:“公之学如上壁。”言难行也。明道曰:“参政之学如捉风。”及后已逐不附己者,独不怨明道,且曰:“此人虽未知道,亦忠信人也。”[1]255
王安石批评程颢的道因工夫太繁琐而难以实行,程颢则批评王安石的道犹如捕风捉影,根本不切实际。正如夏长朴先生解释说:“他(程颢)认为安石所谓的道,其实是无中生有,既不可能实践,也无从捉摸,只是虚幻不实的概念。”[3]219这也印证了前文所述,二程认为王安石的道本质上是“虚无”,而非实有,所以总归不是道。二程之所以有如此的批评,也在于王安石论道基本上承袭《老子》,故而使人认为他不过是继承道家的“无为之道”“有生于无”的思维模式。但在“道”之有无这一点上,程颢确实误解了王安石。
王安石论道借鉴了《老子》的思想,这确是事实。王安石说:“道非物也,然谓之道,则有物矣,恍惚是也。”[4]46一方面,道不是有具体形体、具体方位的存在物;另一方面,道又不是虚无,而是实有,它是“有物”,这个“物”即是“恍惚”“混成之道”“道一”“元气”,只是它不可见、不可言说而已。所以王安石在《老子注》的第一章就说:“道本不可道,若其可道,则是其迹也。有其迹,则非吾之常道也。”“道本无名,道有可名,则非吾之常名。”[4]13“迹”“名”便是具体的“体”“方”,但它们都不能用来规定“道”。“道”的性质要求它不能有一个类似于西方哲学中种加属差式的定义,它只能被描述,而无法被定义。例如,“道”的存在超越时空,它先于天地万物而存在,它不生不灭。
吾不知道是谁所生之子,象帝之先。象者,有形之始也。帝者,生物之祖也。故《系辞》曰“见乃谓之象”,“帝出乎震”,其道乃在天地之先也[4]24。
天之所法者,道也。故曰“天乃道”。道则无古无今,故曰“道乃久”。夫道,至于久而可以没身不殆,其孰能至于此哉?[4]41
惟道,则先于天地则不为壮,长于上古而不为老[4]77。
除此之外,它也具有绝对性,它不依赖于任何事物而独立存在。正如王安石在对《老子》第二十五章进行注解时所说的:
人谓王也。人法地之安静,故无为而天下功。地法天之无为,故不长而万物育。天法道之自然,故不产而万物化。道则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无所法也。无法者,自然而已,故曰“道法自然”。此章言混成之道,先天地生,其体则卓然独立,其用则周流六虚,不可称道,强以大名。虽二仪之高厚,王者之至尊,咸法于道。夫道者,自本自根,无所因而自然也[4]50。
“道”本身是自本自根、自然无为的。“道”不仅仅是天地万物存在的最终依据,也是天地万物运动变化所要遵循的规律和原则。王安石也说过“天与道合而为一”[4]41,所以说,“道”即是“天”,也是“天道”。
以上是王安石对“道”的一般属性的认识。除此之外,他也认为:“道一也,而为说有二。”[4]15“道”本质上是“一”而非多,“道”分而言之则有二,也即王安石常说的有无、本末、体用。
所谓二者何也?有、无是也。无则道之本,而所谓妙者也;有则道之末,所谓缴者也。故道之本,出于冲虚杳渺之际;而其末也,散于形名度数之间。是二者,其为道一也。而世之蔽者常以为异,何也?盖冲虚杳渺者,常存于无;而言形名度数者,常存乎有。有无不能以并存,此所以蔽而不能自全也。夫无者,名天地之始;而有者,名万物之母。此为名则异,而未尝不相为用也。盖有无者,若东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无也。故非有则无以见无,而无无则无以出有。有无之变,更出迭入,而未离乎道[4]15。
同样,王安石也在《老子》一文中,论述了他对道之本末、有无的理解:
道有本有末。本者万物之所以生也,末者万物之所以成也。本者出之自然,故不假人之力而万物以生也;末者涉乎形器,故待人力而后万物以成也。夫其不假人之力而万物以生,则是圣人可以无言也,无为也。至乎有待于人力而万物以成,则是圣人之所以不能无言也,无为也。故昔圣人之在上而以万物为己任者,必制四术焉。四术者,礼乐刑政是也,所以成万物者也[5]1230。
王安石以无为道之本,以有为道之末,似乎与老子的思想别无二致,但事实上却存在着极大的差别。首先,在王安石看来,作为道之本的“无”并非老子之虚无,也非佛教之空无,而是无形无象、无体无方之“无”。因为它“出于冲虚杳渺之际”,隐而不发,所以世人无法像认识具体事物一样去认识它。在王安石看来,作为道之本的“无”不仅不是虚无,它还是天地万物之始,是万物之所以生之无。其次,王安石从形而上者与形而下者的角度来区分无和有,“无者,形之上者也,自太初至于太始,自太始至于太极,太始生天地”“有,形之下者也,有天地然后生万物”[4]14。在王安石看来,道贯通有无、形上形下,两者同出于道,并非如老子重无而轻有、重形之上者而轻形之下者,亦非如世之学者“以无为精,有为粗,不知二者皆出于道”[4]15。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知道,王安石已经对老子的“道”进行了改造,“道”不是“虚无”,而是实有,具体表现为“元气”。因此,程颢认为王安石的道“如捉风”,着实是一种误解。而程颢“未知道”,则缘于王安石认为至高无上的天道只有圣人才能够体认和掌握,并非所有人。王安石的批评,除了指明其道难行之外,也否定了人人都能够通过做工夫而达到道的可能性,这确实是一个让人有点沮丧的观点。
2 道气一元与“以气明道,气亦形而下者”
正如前文所述,程颢对王安石的批评是一种误解。王安石所论之“道”不仅是实有,而且表现为“元气”。王安石说:“道有体有用,体者,元气之不动;用者,冲气运行于天地之间。其冲气至虚而一,在天则为天五,在地则为地六。盖冲气为元气之所生,既至虚而一,则或如不盈。”[4]23“元气”是“混成之道”的原初状态,是阴阳未分之气,“冲气”则是阴阳已分之后的“冲和之气”;“元气”和“冲气”都是“气”,只不过一个是体,一个是用。因而,王安石所说之“气”就是“道”,“气”与“道”为一。有学者认为:“王安石的道以元气为体,冲气为用的哲学理论,把老子的道生万物的天地演化论发展为道有体有用的哲学本体论。”[6]338王安石所说的“元气”相当于张载的“清虚一大”“太虚之气”,正如马振铎先生所指出的那样,王安石所提出的元气一元论和宇宙气化论与张载的“元气本体论”思想是基本一致的[7]50-89。
另外,王安石的宇宙生成论也是以“气”为核心而展开的。王安石融合了《周易·易传》《老子》和《尚书·洪范》的思想认为:“人之精神与天地同流,通万物一气也。”[8]367气不仅贯穿于天地万物之中,也贯通于人的精神之中。关于气的这一贯通过程,王安石运用太初、太始、太极、元气、冲气、阴阳、五行、万物等一系列概念范畴,构建起了一幅生动的宇宙生成演化图景。
王安石在《老子注》第一章就对宇宙生成演化做出了较为清晰的说明。他说:
无者,形之上者也,自太初至于太始,自太始至于太极,太始生天地,此名天地之始。有,形之下者也,有天地然后生万物,此名万物之母[4]14。
无名者,太始也,故为天地之父。有名者,太极也,故为万物之母。天地,万物之合;万物,天地之离。于父言天地,则万物可知矣。于母言万物,则天地亦可知矣[4]14。
所谓“太初”便是“道一”之“道”“混成之道”;“太始”是道之本,是无,是形之上者,是天地之父;“太极”是道之末,是有,是形之下者,是万物之母。万物生于太极,天地生于太始,也就是太极生于太始,“天地”与“太极”同义。简单勾勒这一生成结构:太初/道一/混成之道—太始—太极/天地—万物。接下来王安石又进一步丰富这一结构。他说:
道有体有用,体者,元气之不动;用者,冲气运行于天地之间。其冲气至虚而一,在天则为天五,在地则为地六。盖冲气为元气之所生,既至虚而一,则或如不盈[4]23。
道无体也,无方也。以冲和之气,鼓动于天地之间,而生养万物;如橐籥虚而不屈,动而愈出[4]26。
道之体用,也即道之本末、无有,体用、本末、无有三者是相对应的。道之体是元气,道之用是冲气,太初的内涵便是元气,太极则是冲气。冲气为元气所生,同时又生养了万物。从道之体用的层面,我们可以将这一生成结构归纳为:道—元气—冲气—万物。把两者结合起来便形成了如下结构:太初/道/混成之道—太始/元气—太极/天地/冲气—万物。“元气”是气的原初状态,是混沌未分之气;何为“冲气”?王安石解释说:“冲气以天一为主,故从水;天地之中也,故从中。又水平而中,不盈而平者,冲也。”[4]24除了从文字学的角度之外,王安石进一步把“冲气”与“阴阳之气”结合在一起。
“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则冲者,阴阳之和也[4]66。
一阴一阳之谓道,而阴阳之中有冲气;冲气生于道,道者,天也。万物之所自生,故为天下母。夫物芸芸,各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则得以返其本也,故曰复守其母[4]73。
王安石认为“冲者,阴阳之和”“阴阳之中有冲气”,即认为“冲气”是元气区分之后形成的阴阳之气。他不仅把汉代以来盛行的阴阳学说融入到道家的宇宙生成模式中,还把“五行”之说纳入其中。王安石说:“夫太极者,五行之所由生,而五行非太极也。……夫太极生五行,然后利害生焉,而太极不可以利害言也。”[5]1234太极生五行,也即阴阳生五行,五行生万物。综合以上分析,完整的宇宙生成论结构应是:太初/道一/混成之道—太始/元气—太极/天地/冲气/阴阳—五行—万物。具体的万事万物都处于生灭变化之中,阴阳五行之气相交变化凝聚以形成万物;万物灭亡,凝聚之气消散,复归于元气。所以王安石说:“夫物芸芸,各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则得以返其本也,故曰复守其母。”“复命”“反本”“反朴”即指气回归到道之本、太初、“元气之不动”的状态。依此循环,以至于万物生生不息。故而,王安石的宇宙生成论实际是一种宇宙循环论。这一点与张载的气化宇宙论极为相似,同样备受二程及其后学的诟病。
二程关于气的论述主要体现在对张载的批评之中。二程的“洛学”与张载的“关学”自成体系,但又相互影响。二程对张载的理论多有赞赏之处,但也批评张载学说最大的问题是把“气”作为世界万物的本原[9]213。概括言之,二程对张载气论的批评主要可以分为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对其“气本论”的批评;第二层面是对其“气之聚散”宇宙循环论的批评。
就“气本论”层面,可以具体区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从天道本体的层面进行批评。二程通过区分形而上者和形而下者,将阴阳与道、器与道、气与道做出了区分。二程认为,阴阳乃气,也是形而下之器,道则为形而上之理。他说:
形而上为道,形而下为器,须著如此说。器亦道,道亦器,但得道在,不系今与后,己与人[1]4。
《系辞》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又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又曰:“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亦形而下者也,而曰道者,惟此语截得上下最分明,元来只此是道,要在人默而识之也[1]118。
离了阴阳更无道,所以阴阳者是道也。阴阳,气也。气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形而上者则是密也[1]162。
阴阳、器和气都是形而下者,道不同于阴阳、器和气,但又不离于阴阳、器和气。二程说:“以气明道,气亦形而下者耳。”[1]1128作为形而下的气,如何能够成为世界万物的本原呢?二程进一步批评张载“以清虚一大名天道,是以器言,非形而上者”[1]1174。王安石的气论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即“以气明道”。
第二个部分是从人性本体层面进行批评。二程从逻辑上区分了形而上者和形而下者,只有作为形而上者的道、理,才能够成为宇宙万物的本原,也才能成为儒家仁义道德的根源。作为形而下的气不仅不能成为世界的本原,更不能作为人性善的价值依据。在张载的理论体系中,气质或气质之性是恶的根源,因而其无法成为人性善的根源。所以在这一点上,二程对张载的批评是完全合理的,这正是张载哲学体系存在的理论漏洞。但是对于王安石来说,这一批评却不能成立。因为在王安石的理论体系中,他没有从恶的来源的角度认识气,气只是一个自然的、客观的存在,它并不具有任何的价值意义。因而在涉及道德修养的问题上,他也并没有将气作为消极的东西而加以“变化”“治理”,而是强调“保形”“育气”(6)王安石在《礼乐论》的开篇就论述说:“气之所禀命者,心也。视之能必见,听之能必闻,行之能必至,思之能必得,是诚之所至也。不听而聪,不视而明,不思而得,不行而至,是性之所固有,而神之所自生也,尽心尽诚者之所至也。故诚之所以能不测者,性也。贤者,鞠以立性者也;圣人,尽性以至诚者也;神生于性,性生于诚,诚生于心,心生于气,气生于形。形者,有生之本。故养生在于保形,充形在于育气,养气在于宁心。”参见: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M]//王安石全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1199.。
二程对张载气论批评的第二个层面是“气之聚散”的宇宙循环论。二程说:
若谓既返之气复将为方伸之气,必资于此,则殊与天地之化不相似。天地之化,自然生生不穷,更何复资于既毙之形,既返之气,以为造化?近取诸身,其开合往来,见之鼻息,然不必须假吸复人以为呼。气则自然生。人气之生,生于真元。天之气,亦自然生生不穷。至如海水,因阳盛而涸,及阴盛而生,亦不是将已涸之气却生水。自然能生,往来屈伸只是理也。盛则便有衰,昼则便有夜,往则便有来。天地中如洪炉,何物不销铄了[1]148。
在二程看来,宇宙在本质上并非循环往复的,而是日新日益、生生不息的。这种生生不息的力量来源于“道”“理”,所以二程说“道则自然生生不息”“道则自然生万物”。二程对张载宇宙循环论的批评,可以等同于对王安石宇宙循环论的批评。
关于“气”的认识,王安石与张载一样,一方面继承了汉代以来的气化宇宙论,另一方面也把“气”提升到了本体论的高度,并将其等同于“道”。但对二程而言,“气”不仅不能等同于道,并且宇宙运动也不是气的循环往复,而应是日新日益、生生不息的。就二程日新的宇宙论和张载、王安石循环的宇宙论而言,正如徐洪兴先生所评价的:“就其(二程)批评本身而言,在理论上却还是能够自圆其说的。”[9]215
3 “介父之学,大抵支离”与天生人成
上文已经分别澄清并还原了王安石的道本论和气化宇宙论思想,接下来将进一步比较、探讨王安石与二程就天人关系的不同认识。
二程除了批评王安石所论之道虚无以外,另一个批评便是认为王安石之学“支离”。程颐说:“介父之学,大抵支离。伯淳尝与杨时读了数篇,其后尽能推类以通之。”[1]28“支离”既体现了王安石为学的思维方式,即“事事分作两处”,也体现了王安石天道论的理论特色,即区分天道与人道。王安石关于区分天道与人道的地方处处可见,尤其展现在《三经新义》当中(7)例如,王安石在《诗经新义》中说:“人之行莫大于孝,此乃人道,未至于天道。”“刑于寡妻为形上者,则有道存焉;以御于家邦为形而下者,则有度数存焉,是故谓之御也。”参见:王安石.诗经新义[M]//王安石全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438,638.。王安石在《尚书新义》中说:
尧行天道以治人,舜行人道以事天。《尧典》于舜、丹朱、共工、驩兜之事,皆论之,未及乎升黜之政。至《舜典》,然后禅舜以位、“四罪而天下服”之类,皆尧所以在天下,舜所以治[8]47。
程颐针对这段话有一段较长的评论文字,他说:
介甫自不识道字,道未始有天人之别,但在天则为天道,在地则为地道,在人则为人道。如言是何义理?四凶在尧时亦皆高才,职事皆修,尧如何诛之?然尧已知其恶,非尧亦不能知也。及尧一旦举舜于侧微,使四凶北面而臣之,四凶不能堪,遂逆命;鲧功又不成,故舜然后远放之。如《吕刑》言“遏绝苗民”,亦只是舜,孔安国误以为尧[1]282。
程颐直接批评王安石“不识道”,因为他将天道与人道区分为二,将天人相分(8)二程类似的批评还有如:“或问:‘介甫有言,尽人道谓之仁,尽天道谓之圣。’子曰:‘言乎一事,必分为二,介甫之学也。道一也,未有尽人而不尽天者也。以天人为二,非道也。子云谓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亦犹是也。或曰:乾天道也,坤地道也,论其体则天尊地卑,其道则无二也。岂有通天地而不通人?如止云通天文地理,虽不能之,何害为儒?’”参见程颢,程颐.二程集[M].北京:中华书局,2014:1170.。二程始终认为“天下只有一个理”[1]196“上下、本末、内外,都是一理而已,方是道”[1]3。“理”便是“道”。所以在天人关系上,二程认为天人无间。
有道有理,天人一也,更不分别[1]20。
除了身便只是理,便说合天人。合天人,已是为不知者引而致之。天人无间[1]33。
天人本无二,不必言合[1]81。
二程从本体论的角度打通天人,将传统的“天人合一”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在他们看来,讲“天人合一”的逻辑前提依然是“天人相分”,但天人本来就是一,因而不必言合,说“天人合一”只是为了让不知道的人了解而已。如此看来,王安石区分天人、区分天道与人道的做法,着实与二程的理论体系不合。
王安石天人相分的观念来源于他对汉代以来“天人感应”的批评。“天人感应”认为,天是有人格、有意志的天,它与人事交相感应;天能够通过天象预示灾祥从而影响人事,而人事运行的好坏也能感应上天。汉代的董仲舒融合《春秋》中的灾异说、当时流行的阴阳五行说和《尚书·洪范》中的五行学说,最终形成其特有的“天人感应”理论。直至唐宋时期,士人对《洪范》的注释仍陷入在“天人感应”的窠臼之中。王安石有感于此,批评说:
予悲夫《洪范》者,武王之所以虚心而问,与箕子之所以悉意而言,为传注者汨之,以至于今冥冥也,于是为作传以通其意。呜呼!学者不知古之所以教,而蔽于传注之学也久矣。当其时,欲其思之深、问之切而后复焉,则吾将孰待而言邪?[5]1284-1285
后世学者囿于汉儒章句训诂之学,严守“天人感应”的传统,丢失了《洪范》作为教化之学的真实内涵。于是,王安石决定重新为《洪范》作传,以启后学。王安石作《洪范传》的另一个原因,是他认为“《书》言天人之道,莫大于《洪范》”[5]1202。
在王安石看来,首先,天(9)对王安石来说,天等同于道,“天与道合一”。不具有人格意志,天是自然无为的,它经由元气、冲气、阴阳、五行而生成万物,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并非人的意志所能左右。故而,“天人感应”不能成立。其次,《洪范》的第八畴言“庶征”,很多人认为这是“天人感应”、灾异说的最好说明,王安石则对此提出明确的批评:
孔子曰:“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君子之于人也,固常思齐其贤,而以其不肖为戒, 况天者固人君之所当法象也,则质诸彼以验此,固其宜也。然则世之言灾异者,非乎?曰:人君固辅相天地以理万物者也,天地万物不得其常,则恐惧修省,固亦其宜也。今或以为天有是变,必由我有是罪以致之;或以为灾异自天事耳,何豫于我,我知修人事而已。盖由前之说,则蔽而葸;由后之说,则固而怠。不蔽不葸,不固不怠者,亦以天变为已惧,不曰天之有某变,必以我为某事而至也,亦以天下之正理考吾之失而已矣,此亦“念用庶证”之意也[5]1190。
由此可以看到,王安石对天人关系的认识非常理性。一方面,他反对天人感应说,因为天道自然,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另一方面,他也反对将天与人彻底割裂的做法,并且批评了天人毫不相干的认识,因为人应当效法天道(10)朱熹在评价王安石时认为,汉儒灾异说太绝对,但是王安石又割裂了天与人。朱熹评价说:“《洪范》庶征固不是定如汉儒之说,必以为有是应必有是事。多雨之征,必推说道是某时做某事不肃,所以致此。为此必然说之,所以教人难尽信。但古人意精密,只于五时上体察是有此理。如荆公,又却要一齐都不消说感应,但把‘若’字做‘如似’字义说,做譬喻说了,也不得。荆公固是也说道此事不足验,然而人主自当谨戒。如汉儒必然之说固不可,如荆公全不相关之说,亦不可。”从以上分析可以明显地看到,在割裂天人这一点上,朱熹实际上误解了王安石的意思。参见:黎靖徳编.朱子语类:卷七十九[M].北京:中华书局,2015:2048-2049.。
概括言之,王安石一方面强调天与人之间应当有所区别,另一方面又强调人应效法天。这一天人观,体现在他的“天生人成”的观念之中。王安石说:“始而生之者,天道也;成而终之者,人道也。”[5]1139这一观念在《老子注》中体现得更加淋漓尽致。
盖天之体不能生生,而生生者,真君也;而真君未尝生。地之体不能化化,而化化者,真宰也,而真宰未尝化。则出显诸仁,故凡在天地之间,形、物、声、色也,皆制于我,而物不得以疏;及夫已生已化,则入而藏诸用,故物有分之类有群,各以附离而忘于我,而物不得以亲。虽然,天能生而不能成,地能成而不能治,圣人者出而治之也[4]26。
王安石认为,天生、地成、圣人治三者缺一不可。圣人治人事,推而上之,可以至于天道,也惟有圣人能够“合同天人之际,使之无间”[8]55,最终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对于王安石来说,虽然天道与人道是相分的,但圣人能够修人道以至于天道,从而实现天道与人道的合一。“天人合一”是就修养论层面而言的,并非就本体论层面而言,这一点与二程的“天人本无二”有根本的区别。
二程认为,万物只有一个理,“天人本无二”“天人合一”不仅是就修养论层面而言,更是就本体论层面而言。故而,即使王安石也承认“天人合一”,但终将是“支离”天道与人道。如果王安石仅仅从修养论的层面理解“天人合一”,那么他便无法回答圣人通过人道推至天道从而使“天人合一”何以可能的问题,即王安石不能给予“天人合一”一个最终依据。这种“支离”体现在人事上,则表现为割裂本体和工夫、知和行;在政治改革方面,则表现为一味强调“自然理性”,而忽视“人文情怀”[10]24,等等。
但回到王安石自身的天道论体系中来,王安石的天人关系论与其道本论、宇宙生成论是一致的,即他的思想体系是自我融洽的。在王安石看来,道是一,只不过道有体有用、有本有末。具体而言,天道是本是体,人道是末是用,天道高于人道,人道效法天道。圣人能够推人道以至于天道,从而达到“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即“道一”“道全”的最终状态。落实到人事层面,“天生人成”的观念为王安石积极有为、改革变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所以从王安石自身的理论出发,区分天道与人道,是合理的。
4 余论
王安石的天道论主要包含了以道为本体的道本论、以道/太初—太始/元气—太极/冲气/阴阳—五行—万物为结构的宇宙生成论、“天生人成”的天人关系论三个方面。王安石天道论的特色融合了儒、道思想,且自我圆融。二程极为敏锐地抓住了王安石天道论的理论特点,并从“支离”“以气明道”等方面对王安石进行了批评。但二程的批评带有鲜明的“理本论”立场,而非针对王安石思想的内部逻辑展开,故而有隔靴搔痒之嫌。
二程的“理本论”认为,天下只有一个理,理不仅是宇宙万物的本原,也是社会伦理道德的依据,它贯穿了宇宙、社会和人本身;“性即理”“命、理、心、性都是一”;“天人本无二”。从“理本论”的角度看,二程自然不能容忍王安石把“道”仅仅停留在自然的层面而不具有道德价值;“以气明道”的道气一元论也不符合二程对“道与气”“形上与形下”的区分;在天人关系问题上,他们也不能接受王安石将天与人割裂开来。然而从王安石自身的理论体系来看,天与人的关系是双重的,两者既相互分离,又具有统一性,这与他在人事方面强调积极有为、经世致用的观点是一致的。他的自然天道论也为其社会政治层面的“礼乐刑政”提供了客观的形上基础[11]。所以,王安石的理论从天道到人事是相互融贯的,并非“支离”。所不同的是,二程理学主要关注儒家道德建构形而上学基础,王安石新学则主要关注儒家“礼乐刑政”奠定形而上学基础。
王安石和二程同处于北宋儒学复兴的文化背景之下。儒学复兴的主题多元并存,以至于王安石新学盛行于世六十多年。南宋以后,王安石新学衰落并成为众矢之的,理学则逐渐成形并且成为学术主流,直至确定为一尊。故而后世所论宋代儒学复兴便无不以理学为宗,将王安石新学贬斥为“异端”。即使是研究王安石思想的现代学者,也大多指出王安石新学不符合北宋儒学复兴的要求[12]。笔者认为,这种后设的“儒学复兴”观不仅不符合历史事实,还大大缩小了宋代儒学复兴运动的范围,更局限了儒学的全面发展。因而,重新确立王安石新学的历史与学术地位,并进一步揭示其现代意义,就成为当前王安石思想研究的重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