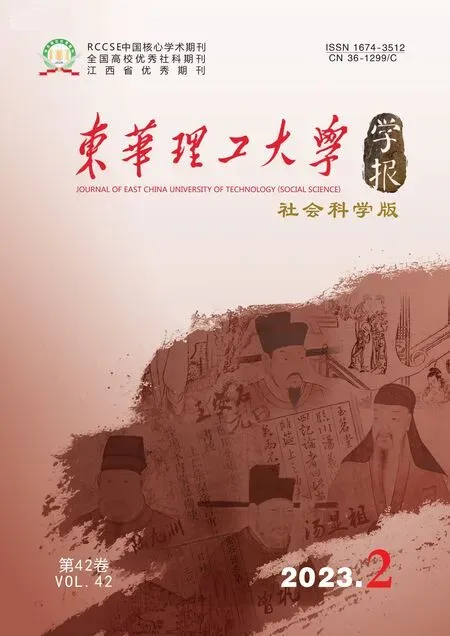朱熹“心统性情”说的孟学诠释
张宏锋, 王建军
(盐城师范学院 文学院,江苏 盐城 224002)
“心统性情”一语最早由张载提出,后经朱熹发展,成为一个具有“心主性情”和“心兼性情”双重内涵的系统学说。这一学说在朱熹哲学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是“朱熹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他心性学说的纲领”[1]。学界对朱熹“心统性情”说多有探讨,其中关于“心主性情”这一层内涵,学者们的观点有所不同。钱穆说:“谓之一者,如谓‘心即理’;谓之二者,如谓当使此心主宰始得理,是也。”[2]128-129他认为朱熹“心统性情”说的目的是讲“心即理”,“心”是真正的主体,涉及本体层面。但牟宗三却说:“‘心之理’是心认知地所摄具之理……性情之主,‘主’是绾摄义,是管家之主,而不是真正的主人之主。真正的主人之主当在性,不在心。”[3]249在牟宗三看来,“心”对“性”“情”的主宰作用仅限于功夫层面,不涉及本体层面;在本体层面,“性”才是真正的主体。继钱穆、牟宗三之后,学者对“心统性情”的探讨皆不出其囿,但更加倾向于牟宗三之说。如蔡方鹿指出:“朱熹心主宰性情的思想主要涉及伦理学的问题,无论是心主宰性……还是心主宰情……都讲的是伦理道德问题,而不涉及本体论问题。”[4]蒙培元亦认为:“心是性情得以存在的主体,但不是认识主体或主要不是认识主体,而是德性主体。”[5]554-569然而,“朱熹哲学和它的许多重要部分都不是一下形成的静止结构,而是有其自身提出、形成并经历复杂演变的动态体系”[6],故仅从静态角度研究朱熹的“心统性情”说容易出现理解上的分歧。部分学者注意到这一点,侧重考察朱熹“心统性情”说的形成过程。陈来指出,朱熹“心统性情”说中的“心兼性情”主要按照二程“易(体)—道(理)—用(神)”[7]的方法论模式展开。刘述先则认为,朱熹的“心统性情”说“隐涵(含)在他的中和新说的后面,在有关仁说的论辩之中显现出来。晚年之思想更进一步加以繁演。”[8]193
纵观前人之说,仍有如下研究空间:一是朱熹在论述“心”“性”“情”的同时,经常将“才”纳入其中,说明“才”也是“心统性情”说一个很重要的范畴,但无论是静态研究还是动态研究,学者仅局限于“心”“性”“情”关系的探讨,却没有讨论“才”;二是部分学者虽然对朱熹“心统性情”说的形成过程有所关注,但并没有将这个过程完整揭示出来。朱熹理学思想的核心在《四书》,而关于“心”“性”“情”关系的探讨,却多集中于《孟子》。孟子思想以“心”“性”为主,“《孟子》一书,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养性,收其放心”[9]244。因此,朱熹的“心统性情说”是在诠释孟子思想基础上逐渐形成。朱熹的孟学著述丰富,主要有《胡子知言疑义》(1)学界普遍认为《孟子精义》是朱熹的第一部孟学著述,其实胡宏《知言》的大部分内容都与《孟子》相关,尤其是心性论部分。《胡子知言疑义》成书于乾道七年(1171),因此在讨论心性论的时候,将《胡子知言疑义》视为其最早的孟学著述较为妥当。《尽心说》《孟子精义》《孟子或问》《孟子纲领》《孟子集注》,以及《朱子语类》中的《孟子》部分。这些著述成书的先后顺序,恰巧反映了朱熹建构“心统性情”说的过程。本文拟在前人基础上,以朱熹孟学著述为中心,考察其如何在诠释孟子思想基础上建构“心统性情”说,以补研究之阙如。
1 “心统性情”说发端:“心主性情”
朱熹首次提出“心统性情”说是在《胡子知言疑义》中。
《知言》曰:“心也者,知天地,宰万物,以成性者也。”……熹谓:“‘以成性者也’,此句可疑,欲作‘而统性情也’,如何?”栻曰:“‘统’字亦恐未安,欲作‘心主性情’如何?熹谓所改‘主’字极有功。”……熹谓:“论心必兼性情,然后语意完备。”[10]3555
朱熹与胡宏心性论的分歧之一在于对“情”的处理。按照胡宏“心以成性”说,“情”则无处安顿;但在朱熹看来,“论心必兼性情,然后语意完备”,故欲将其改作“心统性情”。虽然在“心统性情”这一架构中,“情”得到了较好的安排,但张栻却认为“统”字仍无法准确描述三者之间的关系,欲将其改作“主”字。朱熹随即认可张栻的说法,称赞“改‘主’字极有功”。这不免带来两个疑问:一是朱熹为何坚持论心必兼情?二是朱熹此时所说的“心统性情”是否承袭张载而来?
朱熹坚持论心必兼情,有两点原因。首先,在“中和旧说”时期,朱熹主张“已发”是“心”,“未发”是“性”,“性”是心之体,“心”是性之用,强调在“未发”处下功夫。但“未发”时心该如何涵养,始终让他觉得“无立脚下工夫处”[11]1392。为了寻求这一答案,朱熹遂转向程颐之学。程颐主张“心一也,有指体而言, 寂然不动是也;有指用而言者, 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12]1183,这让朱熹认识到从体用角度而言,“心”只有一个,不能将“心”“性”二分。因此,他在程颐之说基础上,以“心”贯穿“未发”“已发”两个阶段:“未发之心”指当“心”未接触外物时,无法发挥其思维作用,属于静的状态,这种状态的“心”就是“性”;而“已发之心”则指“心”在接触外物时,其思维作用得以发挥,属于动的状态,这种状态下的“心”即为“情”。朱熹将“情”作为“心”的已发状态,使“心”有所主,这样就可以在“已发”处下功夫,从而解决之前的困惑。简言之,朱熹为了寻找下功夫处,就一定要引入“情”。其次,“情”在孟子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朱熹为了契合孟子之说,必然要为“情”找到合适的位置。孟子论性善,从“心”言“性”,从“情”言“心”。人性善的依据在于人有“四心”,而人之所以有“四心”在于有“四端”,“四端”即是“情”。如果缺少“情”,孟子“性善论”无法成立,朱熹“心性论”更无法建立起来。《朱子语类》云:
旧看五峰说,只将心对性说,一个情字都无下落。后来看横渠“心统性情”之说,乃知此话有大功,始寻得个“情”字着落,与孟子说一般。孟子言:“恻隐之心,仁之端也。”仁,性也;恻隐,情也,此是情上见得心[13]226。
朱熹发现胡宏“心以成性”说存在“情”无处安顿的弊端。而朱熹这样说的依据就在于孟子言“恻隐之心,仁之端也”,说明“心”包含“性”与“情”两个部分,若“情”无处安顿,则与孟子之说相戾。因此,朱熹得出“言心必兼性情”的结论。此外,这则材料还解决了另一个疑惑。从朱熹表述来看,他此前似乎并不知晓张载的“心统性情”说,而是通过发现胡宏“心以成性”说忽略“情”之弊端,才得出“心统性情”的结论,与张载的观点不谋而合。
朱熹根据自己的体悟得出“心统性情”的结论,但在张栻提议下改作“心主性情”,这又引发一个疑问:朱熹为何如此赞许“心主性情”呢?在《胡子知言疑义》中,朱熹并未做出明确回答,但在同一时期的《尽心说》中却做了隐性回答。《尽心说》云:
盖天者,理之自然,而人之所由以生者也;性者,理之全体,而人之所得以生者也;心则人之所以主于身而具是理者也。天大无外,而性禀其全,故人之本心,其体廓然,亦无限量,惟其梏于形器之私,滞于闻见之小,是以有所蔽而不尽。人能即事即物,穷究其理,至于一日会贯通彻而无所遗焉,则有以全其本心廓然之体,而吾之所以为性与天之所以为天者,皆不外乎此,而一以贯之矣[14]3273。
朱熹为了契合孟子“尽心”说,以“理”贯穿“天”“性”“心”三者。“天”是“理之自然”,是人产生之依据;“性”是“理之全体”,是人生来所获得的本能;而“心”则是性理主于人自身之处。因为“天”广阔无形,包含万理,作为“理之全体”的性自然也包含万理,所以将性理主于自身的“心”,同样具备万理。但“心”作为能思之官,有其弊端,容易“梏于形器之私”“滞于闻见之小”,从而遮蔽了其原本所具有的性理。如何恢复“心”之所具之理呢?这就必须将“心”放到主体地位,只有让“心”主宰“性”,才能通过“即事即物,穷究其理”,以“尽心”的方式,达到“心”“性”“天”三者合一的境界。若“心”不能主宰“性”,性理无处安顿,“心”也无所主,势必会导致“心”被物欲所蔽,原有的性理也就无法恢复。这一时期,朱熹受孟子“尽心”思想的影响,侧重“心”对“性”的主宰作用,故称张栻“改‘主’字极有功”。同时,这也表明“心”对“性”的主宰作用,仅限于道德层面,而不涉及本体。
2 “心统性情”说的双重内涵:“心兼性情”和“心主性情”
继《胡子知言疑义》《尽心说》之后,朱熹开始全面阐发孟子思想,先后形成了《孟子集注》《孟子或问》《孟子纲领》等一系列孟学著作,“心统性情”说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全面发展。在《孟子集注》中,朱熹正式提出“心统性情”说:
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情也。仁、义、礼、智,性也。心,统性情者也……此章所论人之性情,心之体用,本然全具,而各有条理如此[9]289-290。
此处所说的“心统性情”中的“统”字并非“主宰”之意,而是“兼包”之意。因为朱熹明言“此章所论人之性情,心之体用,本然全具”,所以从体用角度论“性”“情”,显然是在说“心兼性情”。这一点,在《孟子或问》中有着更明确的表述:
心之体无所不统,而其用无所不周者也。今穷理而贯通,以至于可以无所不知,则固尽其无所不统之体、无所不周之用矣[15]994。
未发者,其体也,已发者,其用也。以未发言,则仁义礼智浑然在中者,非想象之可得,又不见其用之所施也。指其发处而言,则日用之间,莫非要切,而其未发之理,固未尝不行乎其间[15]1000。
“心”有体用之分,其体“无所不统”,其用“无所不周”。“体用”即指“性”和“情”。虽然心体无限量,但“心”包含“性”和“情”,故通过“尽心”“穷理而贯通”,则能“尽其无所不统之体、无所不周之用”。不仅如此,“心”还有“未发”和“已发”之分。“未发”是体,“仁义礼智信”之性存于“心”中,无法显现,也无法“见其用之所施”;“已发”是用,“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情在日常应用之间,“莫非要切”,但未发时的性理从未断绝,而是行于情之中。可见,“性”“情”是“心”的两种状态:未发时,“性”存于“心”中,处于“静”的状态,性理无法显现,其用也无处施发;已发时,处于“动”的状态,“性”随之变为“情”,“仁义礼智信”等性理得以显现,发挥其用。其实,孟子并不讲“体用”和“未发已发”,但孟子的“四心”“四端”说,却为朱熹建构“心统性情”说在理论上提供了依据,这也是朱熹按照诠释孟子思想的路径来建构“心统性情”说的原因之一。
此处仍有一个疑问:朱熹为何不再提及“心主性情”,而是改回“心统性情”呢?有两点原因:一是朱熹很可能此时已经注意到了张载也有“心统性情”说,而这一提法与他最初的想法一致。因此,朱熹更倾向于用“心统性情”来表述三者之间的关系。二是朱熹对“心”的理解发生变化。在《孟子集注》之前,朱熹重在凸显“心”的主宰性,但这一时期,其认为:“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9]425“心”乃“知觉虚灵”(即“神明”)之物,包含万理,凸显了“心”的包容性。此时的“心”已经具备“兼包”和“主宰”两种特质,仍以“心主性情”来描述“心”“性”“情”之间的关系,显然不再适合。这一点在《孟子纲领》(2)《孟子纲领》的完成时间各类《年谱》皆无记载,但《孟子纲领》云:“程子之言之要,皆已见于《序说》矣。”其中的《序说》便是指《孟子集注》开篇的《孟子序说》。又《孟子或问》云:“谢氏充扩得去者得之……其以心专为发用,则吾于《纲领》之篇已辨之矣。”所以,这可推知《孟子纲领》当在《孟子或问》之前或者与之同时完成。中有明确表述:“性,本体也,其用情也,心则统性情,该动静而为之主宰也。”[16]3584
在朱熹看来,“理内具于人心,但心并非属于理的层面,而是属于气的层面,是‘气之精爽者’。心中有性与情,性为心之理,而情为心之用”[17],故“该动静”中的“该”有“包括”之意,“动”指“情”,“静”指“性”,故“该动静”即指“心包括性和情”;“而为之宰也”语义明确,即指“心主宰性和情”。“心”既包含“性”“情”,又主宰“性”“情”,以“主”字无法完全概括它们之间的关系,故朱熹有意将“心主性情”改回“心统性情”。自此,“心统性情”形成了“心兼性情”和“心主性情”的双重内涵。
晚年,朱熹将“心统性情”说的来源、内涵、目的表述得更加明确。《朱子语类》云:
横渠说得最好,言:“心,统性情者也。”孟子言:“恻隐之心,仁之端;羞恶之心,义之端。”极说得性、情、心好。性无不善。心所发为情,或有不善。说不善非是心,亦不得。却是心之本体本无不善,其流为不善者,情之迁于物而然也。性是理之总名,仁义礼智皆性中一理之名。恻隐、羞恶、辞逊、是非是情之所发之名,此情之出于性而善者也。其端所发甚微,皆从此心出,故曰:“心,统性情者也。”性不是别有一物在心里。心具此性情[18]227-228。
此条语录透漏出三条信息:首先,朱熹的“心统性情”说源于张载与孟子,而张载与孟子之说相一致,故朱熹称赞张载、孟子“极说得性、情、心好”。其次,朱熹借孟子“四心”“四端”说解释了“心统性情”的内涵。孟子言“恻隐之心,仁之端”,其中“恻隐之心”是“已发之心”,此状态下的“心”称为“情”;“仁”即“未发之心”,此状态下的“心”称为“性”,故此句可解释为“情,性之端”。但无论是“性”,还是“情”,都由此“心”发出,故曰“心,统性情者”。再次,朱熹解释了“心统性情”的目的是契合孟子的“性善论”。“性”本至善,“心”之本体也无不善,为何还会出现不善呢?朱熹将不善归根于“情”。但这不代表朱熹认为“情”是不善的,恰恰相反,“情”作为“性之端”,源于“性”,“性”善“情”亦善。关键在于,“情”只是“性”之端绪,在“情”刚发出时,它本身具有善性,但发出后,则会“迁于物”而流于不善。如何防止“情”流于不善?这就需要“心统性情”,当“情”发出后,用“心”钳制“情”,“情”就会顺着其原本的善性发展。
3 “心统性情”说的演进:“才”与“心”“性”“情”
孟子在论述“心”“性”“情”的同时,还经常涉及“才”。《孟子·告子上》云:“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9]399“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尔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9]400“人见其禽兽也,而以为未尝有才焉者,是岂人之情也哉?”[9]402孟子认为,上天赋予人之“才”在本质上相一致,皆为善,若流于不善,则是因为受外界环境的影响,导致人们迷失了本心。孟子强调,“才”本身至善,目的是让人们通过修养来充分发挥人原本所具有的善资。而这一思想在朱熹那里得到了充分发挥,“才”成为了一个与“心”“性”“情”不可分割的范畴。
朱熹对“才”的理解,可追溯至《孟子精义》。在《孟子精义》中,朱熹辑录众人对“才”的理解,其中张载、程颐的观点对朱熹影响较大。《孟子精义》云:
横渠曰:“人之刚柔缓急,有才有不才,气之偏也。天本参和不偏,养其气而反其本,使之不偏,则尽性而天矣。”[19]769
横渠曰:“孟子之言性、情、才,皆一也,亦观其文势如何。”[19]774
张载将人之“有才有不才”的缘故归根于“气之偏”。气正,人则有才;气偏,人则有不才。无论是“有才”还是“有不才”,皆属于“气”。在张载的心性体系中,“气”即“气质”或“气质之性”。质言之,“才”是“气质之性”中的一部分。人有不才,只需要通过养气反本,使气回归正常,就可以尽性而知天了,故张载认为“孟子之言性、情、才,皆一也”。张载重构孟子之说,使“心”“性”“情”“才”处于一个思想体系中,这对朱熹影响甚大。朱熹在之后的《孟子集注》中,便将“才”的性质和范畴归属于“性”,并以“气禀之说”解释“才”的差异性。
程颐对“才”的认识与张载不同。《孟子精义》云:
(伊川)曰:“才乃人之资质,循性修之,虽至恶可胜而为善。” ……又曰:“性出于天,才出于气,气清则才清,气浊则才浊,譬犹木焉,曲直者性也,可以为梁栋,可以为榱桷者才也。才则有善有不善,性则无不善。”[19]774
程颐对“才”的理解有以下两点。一是“才”乃人的“资质”。如木之“曲直”的特质是“性”,而能够被用来做成“轮辕”“梁栋”“榱桷”,就是“才”。这说明“才”具有可塑性,只要“循性修之”,即使“不善之才”也可转为“善之才”。二是“才”不同于“性”。“性”源于“天”,“才”则源于“气”。这与张载“才”属于“气质之性”的观点不同。在程颐这里,“性”“才”属于不同的体系。“才”源于“气”,会受到“气”之清浊的影响,故“才”有善有不善;而“性”源于“天”,“天”纯然至善,故“性”无不善。程颐“循性修才”“才出自于气”等观点都被朱熹所继承。
与成人重度窒息所致脑灰质弥漫性受损表现不同,HIBD对新生儿脑组织损伤位置具有很强选择性,且不同成熟度的新生儿脑损伤位置也呈不同的特点。这与新生儿脑组织各部位对能量需求强弱、缺氧缺血发生时间、性质及脑血管解剖生理等有很强相关性[6-7]。Logitharajah等[8]研究表明机体发生急性缺氧缺血性窒息时,脑内血流再分布代偿机制会失效,常易发生在代谢能量需求最旺盛基底节、丘脑等部位脑损伤。本研究发现新生儿窒息的病例MRI双侧苍白球区呈稍短T1WI异常信号,考虑为缺氧缺血性脑损伤和高胆红素血症脑损伤所致[9]。这也是本研究将轻度缺氧缺血性脑损伤病例的感兴趣区放置于双侧基底节的苍白球区原因。
在《孟子精义》中,朱熹虽然辑录众家之说,并未表达自己观点,但所辑录的学说都是阐释孟子思想的“精义”。因此,朱熹在《孟子精义》成稿后,便开始着手撰写《孟子集注》。在《孟子集注》中,朱熹整合张载、程颐之说,表达了自己对“才”的见解:
才,犹材质,人之能也。人有是性,则有是才,性既善则才亦善。人之为不善,乃物欲陷溺而然,非其才之罪也……程子曰:“性即理也,理则尧、舜至于涂人一也。才禀于气,气有清浊,禀其清者为贤,禀其浊者为愚。”[9]399
朱熹对“才”的理解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才”是“材质”,即人的才能。其次,“才”属于“性”。“人有是性,则有是才”,一方面突出“性”对“才”的决定作用;另一方面表明“才”与“情”相同,皆属于“性”,即“性兼情才”,这是对张载之说的进一步发挥。既然“才”属于“性”,其便带有“性”的特质——“善”。故不善“非其才之罪也”,而是因为“物欲陷溺”。再次,“才”具有差异性。“才”虽然本善,但每个人禀气的情况不同,“才”自然也不尽相同,正如程颐所说:“才禀于气,气有清浊,禀其清者为贤,禀其浊者为愚。”
在《孟子或问》中,朱熹对“才”的理解更具有代表性:
才则性之具而能为者也……盖性不自立,依气而形,故形生质具,则性之在是者,为气所拘,而其理之为善者,终不可得而变。但气之不美者……才亦有时而偏于不善,若其所以为情与才之本然者,则初亦未尝不善也[15]981-983。
朱熹创造性地提出“才则性之具而能为者也”的观点,既将“才”归属于“性”的范畴,又明确“才”的内涵是“能为者”,这与《孟子集注》“有是性,则有是才”的观点一脉相承。不仅如此,朱熹还从理气关系来探讨“才”,这与孟子的气论相关。孟子“不仅以‘气’论‘性’,而且以‘性’证‘气’”[20],阐明了性、气之间的逻辑关系。基于此,朱熹认为,“性”无法脱离“气”而存在,只能“依气而形”,当“形生质具”时,“性”就会“为气所拘”,但“理”是形而上的存在,故“其理之为善者,终不可得而变”。因此,属于“性”范畴的“才”,同样受到“气”的影响而流于不善,但其“初亦未尝不善”。程颐以“气”论“才”,说明人有贤愚之别。朱熹则深刻地认识到“才”与“性”“理”“气”之间的关系,较程颐说更为精深。
晚年时,朱熹对“才”的理解更加深刻。《朱子语类》云:
才,则可为善者也[18]1881。
或问:“《集注》言:‘才,犹材质’,‘才’与‘材’字之别如何?”曰:“‘才’字是就理义上说,‘材’字是就用上说。孟子上说‘人见其濯濯也,则以为未尝有材’,是用木旁‘材’字,便是指适用底说;‘非天之降才尔殊’,便是就理义上说。”[18]1883
恻隐、羞恶,是心也。能恻隐、羞恶者,才也[18]1887。
“才”是“可为善者”,即人为善的一种能力。具体而言,才是可以做到“恻隐”“羞恶”“辞让”“是非”的一种能力。与之前的孟学著述相比,此处对“才”的理解显然更加明确和具体。朱熹又进一步区分《孟子集注》“才,犹材质”中的“才”与“材”,认为“才”是以“理义”言之,而“材”是以“用”言之。可见,“才”包含“理义”和“用”两个层面:前者指先天为善的能力[21],即天赋予人的一种为善的能力,如孟子所说的“非天之降才尔殊”,这种“才”人人都具有,没有差异,故一个人不善,“非才之罪”,而是因为“不能尽其才”;后者指由道德之心生发而成的善资,如孟子所说的“人见其濯濯也,则以为未尝有材”,但这种“才”并非人人所具有,而是具有差异性,故一个人若想要拥有这种善资,只能通过后天存养来获得。
综上,无论是张载、程颐,还是朱熹,他们在论述“心”“性”“情”之间的关系时,都无法忽略“才”的存在。在《孟子集注》《孟子或问》中,朱熹只讨论了“性”与“情”“才”之间的关系,即“性兼情才”“性决定才”,但“情”与“才”又是什么关系呢?“心”与“才”又是什么关系呢?这一问题直至朱熹六十岁以后才有所探讨。《朱子语类》云:“情是这里以手指心。发出,有个路脉曲折,随物恁地去。才是能主张运用做事底。”[18]1888“情”是“性”所发之“路脉”,“才”是“能主张运用做事底”。“才”在“性”“情”之间属于一种推动力,它推动着“情”从“性”发出,没有“才”,“情”也就无法从“性”自然发出。朱熹不仅讨论“情”“才”之间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将“才”放到“心统性情”这一架构中探讨。《朱子语类》云:
性者,心之理;情者,心之动。才便是那情之会恁地者。情与才绝相近。但情是遇物而发,路陌曲折恁地去底;才是那会如此底。要之,千头万绪,皆是从心上来[13]233。
朱熹以“心”为主体,强调“性”“情”“才”皆“从心上来”,再次印证了“才”也是“心统性情”说的一部分。其中,“才”与“情”的关系最为密切,没有“才”,“情”也就无法存在。如果这条语录未将“心统性情”中的“才”阐释清楚,那么下面这条语录所用的比喻,则将几者关系表述得十分明确。《朱子语类》云:
才是心之力,是有气力去做底。心是管摄主宰者,此心之所以为大也。心譬水也;性,水之理也。性所以立乎水之静,情所以行乎水之动,欲则水之流而至于滥也。才者,水之气力所以能流者,然其流有急有缓,则是才之不同。伊川谓“性禀于天,才禀于气”,是也。只有性是一定。情与心与才,便合着气了。心本未尝不同,随人生得来便别了。情则可以善,可以恶[13]233。
在“心统性情”的架构中,“心”是主宰,若“心”为水,则“性”“情”“才”皆属于“水”的一个方面。“性”似水之静,“情”似水之动,但水如何能流动呢?这就需要“才”。能使水流动者,即是“才”,故朱熹说“才是心之力”。水之流有缓有急,这是“才”不同的缘故。朱熹不仅阐释四者之间的关系,而且还暗示着“心统性情”说与其“性二元论”密不可分。朱熹将“性”二分为“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并以此解释性之善恶的情况。在“心统性情”说中,朱熹强调“性”源于天,故“性”纯然至善,始终不变,而“心”“情”“才”虽然都受到“气”的影响,但心本体至善,只不过“心”遇物而发时,则为“情”。“情”受到“气”的影响,则有善有不善。质言之,“情”是“气质之性”,而这表明朱熹的“心统性情”说与其“性二元论”相一致。
4 结语
通过梳理这条路径,朱熹建构“心统性情”说的特点和过程可归纳如下。
朱熹受孟子“四端”“四心”“尽心”说的影响较大。他早年将“心”“性”分开,导致“心”无所主,无处下功夫,遂转向程颐之学,认识到“心”“性”是一体的,不可分割,遂将“性”作为“心”未发的状态。既然“心”的未发状态是“性”,那么已发状态是什么呢?孟子的“四端”“四心”说给出了答案。孟子言“恻隐之心,仁之端也”,这句话用“心”“性”“情”代替,可改作“情之心,性之端也”。“情之心”表明“情”是“心”的一种状态,“性之端”表明“情”是“性”的发端。因此,朱熹说孟子言心、性、情极好,遂将“情”作为“心”的已发状态。在此基础上,朱熹批评胡宏的“心以成性”说忽略了“情”的存在,并在《胡子知言疑义》中,首次提出“心统性情”的观点,但在张栻的提议下,改作“心主性情”。虽然在《胡子知言疑义》中,朱熹并未言明这样改动的原因,但由《尽心说》可知其受孟子“尽心”说的影响较大。孟子强调,“知天”的前提在于“知性”,而“知性”的前提却在“尽心”。因此,朱熹以“心”主宰性、情,一方面契合孟子“尽心”说的路径,另一方面,以“心”钳制“情”,防止“情”流于不善,也有下功夫之处。
继《胡子知言疑义》《尽心说》之后,朱熹开始深入阐发孟子思想,前后撰写了《孟子精义》《孟子集注》《孟子或问》《孟子纲领》等著述。这一时期,“心统性情”说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一方面,“心统性情”说形成了“心兼性情”和“心主性情”的双重内涵;另一方面,朱熹还开始探讨“性”与“才”之间的关系,主张“性兼情才”“性决定才”,出现了将“才”纳入“心统性情”说的倾向。
晚年时,朱熹开始全面深化和拓展“心统性情”说,并在《朱子语类》中正式提出“才”属于“心统性情”说的一部分,并阐释“才”与“心”“情”之间的关系,提出“才是心之力”“才是能主张运用做事底”等创造性观点。不仅如此,朱熹还将“心统性情”与“性二元论”相互融合,强调“性”无不善,不善是因为“情”受气的影响,容易被物欲所蔽,而“才”同样会受到气的影响,导致人有贤愚之别,这样“情”“才”皆属于“气质之性”,从而与“性二元论”相贯通。
综之,孟子思想是心性之学的源头。朱熹自幼接触《孟子》,对《孟子》一书用力甚勤,故在研究朱熹“心统性情”说时,不能仅以《朱子语类》《文集》等材料为据,而应充分关注其所有的孟学著述。此外,朱熹的学说并非静止不变,而是随着体悟的加深不断变化。这决定了在研究朱熹“心统性情”说时,还要用历时性的眼光对待,不能局限于静态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