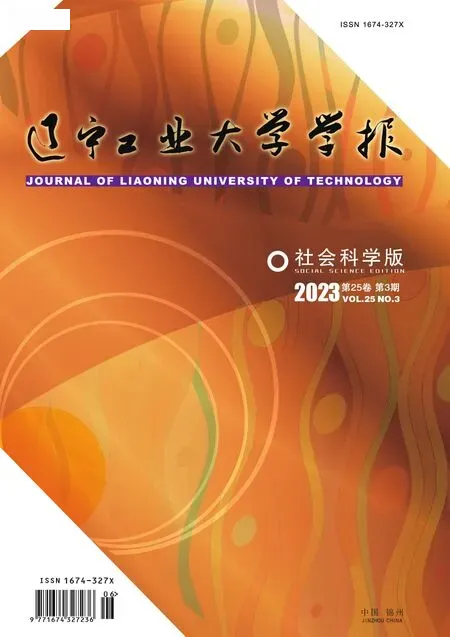《说文解字》从“贝”诸字归部理据探索
翟雪明
(陕西理工大学 人文学院,陕西 汉中 723001)
我国最早研究古文字字形字义的是许慎(约58—约147 年)的《说文解字》,该书创建540 个部首系统,按照“据形系联”的理据将全部收录的字进行归部,用“凡某之属皆从某”的原则标注每一个部首字,让所有字都有部首可依。这种部首及部内归字的理据对于文字的规范和统一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为我国字典辞书的编纂提供了参考,也为后代学者的阅读和研究提供了便利。
以往的研究表明,《说文》中形声字或会意字所包含的义符的多少影响着归部,根据义符的多少可以分为只包含一个义符或是两个及两个以上义符的情况。针对多义符字如何归部的问题,薛克谬提出:“形符都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因而归部也就相应地具有多种可能性,这就需要有一个归部的标准,以便从众多形符中恰当地选择其部首,但这个标准,《说文》却未加指明。”[1]在此以从“贝”诸字的归部为例,可以看出,“败”“浿”“员”三字均从“贝”,且含有“贝”这一义符,但都没有归入“贝”,而分别根据其他形符归部,归入“辵(辶)”“水”“员”三部。可以得出,“败”“浿”“员”三字并未因从“贝”就归入“贝”部,反而因另外义符被归入其他各部。
由此观之,薛克谬指出了在归部问题上遇到的情况,由同一义符构成的文字进行归部时却没有明确的准则,或归入该部,或据其他义符进行归部,有的则另立他部。因此选取哪个义符进行归部,是我们根据《说文》实际归部材料进行研究所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一、《说文》归部理据研究
段玉裁(1735—1815 年)指明,会意字的归部理据即为“义有所重”。在此基础上,王筠强调了“义有所重”的使用范围,将其扩大到整个会意字归部的问题上。但字义的轻重程度都不是绝对的,在特殊情况下,彼此间的界限,重轻主从想要划分清楚非常困难。比如,“则”,从刀从贝,意为法则,准则,指古时人们用刀将条文刻铸在钟鼎器具上,分辨不出哪个义符重哪个义符轻,《说文》将其归入“刀部”;“贯”,从毌从贝,是指穿钱的绳子,毌是贯通的意思,贝意为钱币。这里,同样分辨不出义符的轻与重,但《说文》将其归入“毌部”。因此,这个标准的不确定性使其不适用于全部会意字。
针对“义有所重”说的片面性,刘忠华先生指出,部首的排列以及部内汉字的编排顺序会影响会意字的归部,并提出:“考察《说文》会意字的归部,要着眼于字与字的关系及字义特点,而非偏旁与字义的关系。”[2]即在分析时,紧密结合该字周围的一组字的特点和意义,分析该书编排的依据,着眼于相邻两字在字义上的相同之处,在多义符合体字的多个义符中,选择其中一个义符进行归部,而不是过分关注该字义符的孰轻孰重。若纠结于单个汉字义符意义的轻重,那么在不同的语境下,义符的轻重程度也会发生变化,具有不确定性。刘忠华先生同时指出:“考察《说文》会意字的归部,应该着眼于字与字之间的关系,会意字归部的通例是‘以类相从’而非‘义有所重’。”[3]这一说法不仅指出了“义有所重”的局限性,同时肯定了“以类相从”在辨别汉字归部方面的重要性。
本文正是基于刘忠华先生的观点,对其中从“贝”字的归部理据进行探究,主要从贝部会意字、从“贝”却归入他部的会意字,以及“贝”部亦声字的归部理据举例分析。
本文对“贝”部字作研究,凡以部首编辑的字书都立有“贝”部。《说文解字》创立,后多从之,但收字多少不等。《说文》收正文59,重文3;《康熙字典》收279 字(含异体);《汉语大字典》收361字(不包括简化字),收字呈上升趋势。《说文解字注》对“贝”作了详细的解释,讲述了货币的发展阶段,古人早期是以贝壳充当通行货币,到了周朝“泉”币通行,秦朝则废贝而行钱币。段玉裁解释“贝”即“象其背穹隆而腹下岐。”[4]本文所谈的贝部字,是指含有“贝”,而不全是归入“贝”部的字。
据统计,《说文》中从“贝”的字共有164 字,大部分归入“贝”部,但也有少数特殊情况。有研究价值的仅有15 字:7 个贝部会意字,7 个从“贝”却纳入其他部的会意字,以及1 个从“贝”的亦声字,下文依据这15 个字的先后排序进行探究。
二、贝部会意字的归部理据
贝,海介虫也,象形字。贝字多与货币、财务、贸易相关。贝部会意字,有“赞负赘质买賏赗”七字,其归部理据分析如下:
1.“赞”(见也。从贝从兟),徐锴(920—974年)注,“进见以贝为礼也。”[5]意思是呈献财物以求谒见拜见,与形声字“赆”(会礼也。从贝㶳声)、“贡”(献功也。从贝工声)排列在一起。三个字都具有向上进贡财物表尊敬的含义。其中“赆”“贡”两字都是形声字,依其义符只能归入贝部。把“赞”同时也归入贝部,与“赆”“贡”类聚,遵循“以类相从”的原则。
2.“负”(恃也。从人守贝,有所恃也),表示凭仗、依仗、具有的意思。与形声字“贮”(积也。从贝宁声)顺序连在一起,都具有享有某物的意义,形声字“贮”依其义符归入贝部。把“负”也归入贝部,与“贮”类聚,遵循“以类相从”的原则。
3.“赘”(以物质钱。从敖、贝)“质”(以物相赘也。从贝从斦)二字都有抵押品的含义,与形声字“贸”(易财也。从贝卯声)顺序连在一起。同有物质抵押、物品交易的意义,其中“贸”是形声字,根据其义符归部,只能归入贝部。把“赘”和“质”也归入贝部,与“贸”类聚,遵循“以类相从”的原则。
4.“买”(市也。从网、贝),表示买进,购进,与形声字“贩”(买贱卖贵者。从贝反声)排列在一起。同有物品交易的意义,其中“贩”是形声字,根据其义符归部,只能归入贝部。把“买”也归入贝部,与“贩”类聚,遵循“以类相从”的原则。
5.“賏”(颈饰也。从二贝),表示脖颈上佩戴的配饰、装饰品,与形声字“贶”(赐也。从贝兄声)排列在一起。都与钱物有关,其中“贶”是形声字,根据其义符归入贝部。把“賏”也归入贝部,与“贶”类聚,遵循“以类相从”的归部原则。
6.“赗”(赠死者。从贝从冒。冒者,衣衾覆冒之意),意思是用马车帮人办丧事,与形声字“贶”(赐也)排列在一起。都是与帮助他人,给予他人援手有关。而“贶”是形声字,根据其义符归入贝部。把“賏”也归入贝部,与“贶”类聚,遵循“以类相从”的归部原则。
据此可知,贝部“赞负赘质买賏赗”7 字的归部原因,都符合“以类相从”的原则。
三、从“贝”而归入他部的会意字的归部理据
对只包含一个义符的形声字而言,其归部向来根据其义符归部。如从“贝”而归入他部的形声字“䢙浿䟺宝员”,依据形声字据义符归部的原理可得,䢙,从辵贝声,同“败”,毀坏。归于辵部。浿,从水贝声,水名。归于水部。䟺,从足贝声,步行猎跋也。归于足部。“宝”(珍也。从宀从王从贝,缶声),归入宀部。按,部首字“宀”(交覆深屋也。象形。凡宀之属皆从宀),表示深屋、覆盖的意思,而“宝”表示的是房屋里有珍宝,两个字都包含有房屋覆盖的含义。因此“宝”归入宀部,符合“以类相从”原则。“员”(物数也。从贝口声),本义是指物品的量或是人的数额。归入员部。
不同于上述举例的只包含一个义符的形声字,一些会意字存在有多个义符,并不能根据其中一个义符归部的情况,需要依据“以类相从”的归部。从“贝”归入他部的会意字有7 个,“贯(毌部)贙(虤部)则(刀部)贞(卜部)㕢(部)败(攴部)具(廾部)”,现详细分析这7 个字的归部依据:
1.“贯”(钱贝之贯。从毌、贝),归入毌部。前文中谈到,若是依照义有所重的归部原则,归部则比较模糊。按,部首字“毌”(穿物持之也),“毌”是贯穿的物品。本义指穿钱的绳字,表示贯穿、贯通。而“贯”表示的是贯穿,贯通,用绳子穿联成串。两个字都表示穿通的含义。可见“贯”归入毌部,基本符合“以类相从”这一原则。
2.“贙”(分别也。从虤对争贝),归入虤部。按,部首字“虤”(虎怒也。从二虎),意为两只老虎因为相争而发怒的样子。而“贙”表示的是一种似狗的野兽。部内辖“䖜”字,《说文》:“两虎争声。从虤从曰。”[6]这三字都有两虎相争之义。可见“贙”归入虤部,基本符合了“以类相从”的归部原则。
3.“则”(等画物也。从刀从贝),归入刀部。按,部首字“刀”(兵也),表示一种兵器;而“则”表示的是法则理据,古人用刀将一些条文刻铸在钟鼎上,使人遵循。部内辖“刻”(镂也,从刀亥声)雕刻,在木头上雕刻,“剖”字(判也,从刀咅声),本义是破开,中分。这些字都有表示兵器在某物上雕刻之义。把“则”归入刀部,基本符合“以类相从”的归部原则。
4.“贞”(卜问也。从卜,贝以为贽),最初作“鼎”,后来改为“贝”归入卜部。因为部首字“卜”(灼剥龟也,象灸龟之形),表示古人灼烧龟甲或野兽的头骨,根据其裂纹判断事情凶吉的风俗;而“贞”有占卜,问卦的意思。两个字都表示有旧习俗的含义。把“贞”归入卜部,基本符合“以类相从”的原则。
6.“败”(毀也。从攴、贝。败、贼皆从贝),归入攴部。部首字“攴”(小击也。从又卜声),表示轻轻地击打。而“败”的含义是毁坏,以手持杖,敲击的意思。两个字都表示打击破坏。把“败”归入攴部,遵循了“以类相从”的原则。
7.“具”(共置也。从廾,从贝省),归入廾部。部首字“廾”意为棘手竦手,表示两手捧物。今作“拱”。而“具”的上面是“鼎”,下面是双手,意为双手高高捧着盛有食物的器具之义。“具”和其部首字“鼎”都表示用双手高举某物。可见“具”归入廾部,遵循了“以类相从”的原则。
分析可见,“贯(毌部)贙(虤部)则(刀部)贞(卜部)㕢(部)败(攴部)具(廾部)”的归部,均遵循“以类相从”的归部原则。
四、结论
对于亦声字的归部,刘忠华先生表示:“取亦声偏旁归部,或是为了避免空部首的存在,或是因为某个亦声字的义符不是《说文》部首,该字只能按亦声偏旁归部,多数则是‘以类相从’的原则决定的。”[7]《说文》中贝部有一个亦声字,“贫”(财分少也,从贝从分,分亦声),表示缺少财务,贫困。归入贝部。按,与其排列在一起的“赁”(庸也)意为穷困,平庸。两字都含有缺少财务,经济困难,穷困的意义。把“贫”归入贝部,符合“以类相从”的原则。
“以类相从”是把字义关系紧密或者意义相似的一组字,取两者相同的义符归部。本文举例分析了15个从“贝”作义符的字,包括从“贝”会意字、从“贝”却归入他部的会意字,和从“贝”亦声字的归部,可见《说文》从“贝”作义符的会意字和亦声字,大多是依照“以类相从”的原则归部。可证“以类相从”是《说文》的编排依据和体例。
一个字如何归部,主要取决于该字与部内周围字之间的关系,它们具有一定的共同特征和意义。由此可以得出,“以类相从”是《说文》中汉字归部所依据的基本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