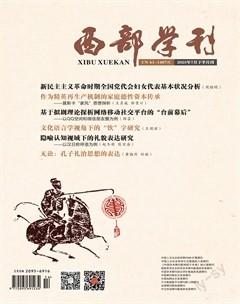浅析通报批评与警告的界限
摘要:自2021年新修订的《行政处罚法》第九条第1项新增行政处罚种类通报批评以来,学界普遍认同应以通报批评统括实质上具有相同法律效果的声誉罚,而统括观点的一个重要矛盾即是与通报批评并列之警告势必不能纳入通报批评的涵射范围。为了厘清两者的边界,通过比较通报批评与警告的性质和界限范围发现,两者虽具有一定共性,但在性质倾向、适用对象、制裁力度、处罚方法方面均有一定差异,同时,以处罚方法上的差异为核心界限使得两者得以明确区分。
关键词:通报批评;警告;声誉罚;行政处罚种类;界限
中图分类号:D922.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3)14-0091-05
A Brief Analysis of the Boundary Between
Name and Shame and Warning
Wu Jianyuan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Wuhan 430000)
Abstract: Since the introduction of name and shame,a new type of administrative penalty, in Item 1, Article 9 of the newly revised Administrative Punishment Law in 2021, the academic community generally agreed that it should include the reputational punishment which has the same legal effect. And an important contradiction in the view of inclusion is that warnings, which are listed alongside with the circulation of notice of criticism, will not be able to be included in its scope. In order to clarify the boundary between the two, this paper contrasts the nature and scope of name and shame and warning, discovering that the two share some similarties but differ in the nature tendency, suitable object, sanction and punishment method. At the same time, the two are distinguished clearly by the differences in punishment method as the core boundary.
Keywords: name and shame; warning; reputation penalty; types of administrative punishment; boundary
2021年新修的《行政處罚法》在第九条第1项中新增“通报批评”这一行政处罚类型并与警告并列。学界主流观点认同应以作为一般种类行政处罚的通报批评统括声誉罚,将实质上具有相同法律效果、形式上以公开为处罚方法的处罚种类纳入通报批评的范畴,进而通过《行政处罚法》予以统一规制。然而,新《行政处罚法》将“警告”与通报批评并列意味着两者虽具有一定的共性,但却是两种彼此独立的行政处罚种类。因此,若将同属声誉罚的警告纳入通报批评的涵射范围加以统括显然是有失妥当的。所以,区分通报批评与警告,厘清两者的边界就变得非常重要,对通报批评的内涵解析和正确适用都有重要意义。
一、通报批评之内涵明晰
2021年新修的《行政处罚法》第二条对行政处罚的概念作出了规定,“行政处罚是指行政机关依法对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以减损权益或者增加义务的方式予以惩戒的行为”。这一定义涵盖了行政处罚的主体、对象、法律效果以及惩戒性四个层面的含义,而通报批评作为一种行政处罚当然具有这四个方面特征。此外,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在《行政处罚法释义》中对通报批评的概念作出了阐释,“通报批评是指通过书面批评加以谴责和告诫指出其违法行为,以避免其再犯,从而达到立法目的”[1],这一定义在行政处罚内涵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通报批评的形式、内容以及目的。由此,结合行政处罚的一般含义和通报批评的形式、内容、目的三方面要素,通报批评是指行政机关依法对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人采取的、在一定社会范围内以书面形式公开违法行为人的基本信息、违法事实并对其行为作出否定性评价,以减损其名誉、避免其再犯的惩戒性措施。
(一)通报批评的性质
顾名思义,通报批评由“通报”与“批评”两层面含义组成,传统的“通报”一词更多地聚焦于上下级机关之间的书面通告《现代汉语词典》将“通报”的词义解释为“上级机关把有关情况以书面形式通告下级机关”,主要局限于国家机关内部的文件通告。,常表现为一种机关内部行为。随着社会发展变化这一释义已不能完整涵盖通报一词的范围,尤其是在行政处罚法领域,通报更强调的是行政处罚的外部性。通报批评中通报的含义是在一定社会范围内,对违法行为人基本信息、违法事实以及相应的否定性评价予以公开,从而使其他社会个体得以知悉。至于“批评”,则是指“对缺点和错误提出意见”《现代汉语词典》将“批评”解释为“评论是非好坏。通常针对缺点、错误提出意见或加以攻击”。,在通报批评中即是对违法行为人的否定性评价和训导、劝诫等。通报、批评这两层面含义分别赋予了通报批评声誉罚和申诫罚属性。
1.声誉罚属性
“通报”的方式多种多样,包括通知单位、行业内公开、网上发布等,概括而言即是通过将违法行为人的基本信息、违法事实公开于其所处的一定社会关系环境中,并对其违法行为进行谴责,从而“通过实际影响当事人的声誉或者严惩影响当事人的声誉、名誉的方式,以社会影响和社会压力来达到制裁的效果和目的”[2]。这种在法律效果上直接减损违法行为人名誉、降低其社会评价的处罚方法使得通报批评具有明显的声誉罚属性。
2.申诫罚属性
单纯的“批评”与警告、训诫在内容上基本无异,都是对行为人实施违法行为的谴责、规劝,主要包括对行为人身份信息的确认、违法事实以及违法结论之依据的描述、否定性评价等内容。如绍兴市消防救援支队对邢录安的训诫嵊消行罚决字〔2022〕第0260号。、重庆市巴南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对重庆巴南刘坤诊所的警告巴卫传罚﹝2022﹞26号。、深圳市生态环境局大鹏管理局对深圳鹏信达环保水保科技有限公司的通报批评深环(大鹏)罚字〔2022〕7号。在批评内容上都主要包含了这些要素。因此,纯粹的批评与训诫、警告等处罚在申诫罚属性上是一致的,都含有否定、劝诫之义。
(二)通报批评的界限范围
从通报批评作为一种行政处罚的角度来看,应将一些看似“通报批評”的情形排除在外。首先,基于行政处罚的外部性,应排除内部管理关系中的“通报批评”。诸如军事机关内部的通报批评、具有上下级关系的行政机关内部通报批评等都不属于行政处罚之通报批评。其次,应排除非法定行政主体作出的“通报批评”,如学校、行会团体作出的通报批评[3],在没有行政机关委托或者法律法规授权的情况下,其作出的通报批评不属于作为行政处罚的通报批评,如上海期货交易所办公室给予孙凤霞、何煜民的通报批评上期办发(2017)54号。。此外,还应排除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设定的“通报批评”,根据新修的《行政处罚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只有法律、法规、规章方可设定行政处罚,因此其他规范性文件(如行业协会规范)设定的通报批评并非行政处罚的范畴。排除了前述情形,明确通报批评的外部辨析后,可从形式与实质两个方面明确通报批评的内部范围。
1.形式意义上的通报批评
目前,我国现行行政法律、法规以及规章明确规定了通报批评行政处罚的有“慈善法等近10部法律、船舶和海上设施检验条例等约20件行政法规、广告语言文字管理暂行规定等近10件部门规章、浙江省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等10多件地方性法规规定了通报批评的行政处罚”[4]。从量上来看,直接从文字上明文规定通报批评的法律规范并不多,且大多聚焦于远离人们日常生活的领域,零散的分布于单行法之中。
2.实质意义上的通报批评
如前所述,形式意义上的通报批评较少且往往远离日常生活、零散分布于单行法,若将通报批评的范围局限于此类形式上之通报批评,那么其就无法成为行政处罚中的一般种类,而应纳入《行政处罚法》第九条第6项中“其他行政处罚”的范围并以单行法特别规定的形式存在。然而,新《行政处罚法》却将通报批评设定为一般种类并与警告并列,这意味着其应具有与警告相似的特征,也更贴近于日常社会生活。故此,对通报批评应作实质意义理解而不应局限于文字形式。此外,“考察《行政处罚法》第九条时,需要认识到的一个前提是,行政处罚种类的规定,本身就是采用实质主义的立场。该法律第九条规定的行政处罚种类,并不是以形式用语为规范对象,而是着眼于概念所表现法规范效果的实质方面”[5]。如作为一般种类的“吊销许可证件”,吊销的对象并不局限于所谓“证件”,更强调的是实质意义上剥夺违法行为人从事某种活动资格的处罚,文字称谓上也不尽然是证件、执照,如机动车驾驶证。如此,以通报批评统括实质上具有相同法律效果,即通过向一定社会范围内公开违法信息从而减损行为人名誉的声誉罚是较为妥当的,典型者如公开谴责、列入失信名单、公布违法事实等皆可纳入实质意义上的通报批评范畴。公开谴责与列入失信名单都能够直接产生违法行为人名誉受损、社会评价降低的法律效果,值得注意的是公布违法事实。由于其内容主要是对违法事实的客观表述并不涉及否定性评价,理论上不会产生权益减损或者义务增加的法律效果,行政机关在作出该行政处罚时亦无希望发生某种法律效果的意思而仅是客观表述事实,因而其是否属于法律行为或行政处罚存有争议。然而,“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而不在于逻辑”,于一般人而言公布违法事实本身即蕴含着浓厚的否定之意,并且伴随违法事实的公布必然引发社会性制裁,这无疑也是立法者预设的惩戒效果,应纳入公布违法事实的法律效果范畴。
二、警告之内涵明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释义,“警告是指行政机关对有违法行为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出告诫,使其认识自己违法所在和如何改正的一种处罚种类”[4]。这一定义表明警告之内容主要是对违法行为的指正以及对行为人的劝诫,实在是惩戒性最轻的一种行政处罚,主要是针对轻微违法行为而设定的。
(一)警告的性质
根据五分法,行政处罚可以分为人身罚、财产罚、行为罚、资格罚和名誉罚,主流观点认为警告也是通过对行为人的名誉造成损害以实现制裁目的的处罚方式,应纳入名誉罚的范畴。但是也有不少反对观点认为,警告并非声誉罚,“因为警告一般只是向行政相对人作出,并不涉及向社会的公开,并不能导致其社会评价的降低”[6]。因此,主张增加一类警示罚,将警告纳入警示罚,而将通报批评等纳入声誉罚。另有一些观点认为,根据新修的《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只有当行政处罚具有一定社会影响时才应当公开,并非所有的警告处罚都可能引起行为人社会评价的降低和名誉减损。甚至于当警告局限于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时,其主要是通过劝诫、训导、警示给行为人增加精神压力,从而激起其内在自觉以避免其再犯,并不涉及行为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变动,因而,此时警告或许更多的还体现为是一种行政指导的事实行为。
然而,警告的行政处罚性质毋庸置疑是法定的,实际上也应属声誉罚。无论警告是否公开,在实际效果上往往难以避免处罚事实在行为人所处的一定社会关系环境中流传开来,从而造成其名誉减损,毕竟法律上并无关于警告事实传播的禁止性规定。并且,传播他人受警告的事实或许在道德上可责难,但因其并非虚构事实,难以构成民事上的侮辱、诽谤侵权抑或刑事上的侮辱罪、诽謗罪。违法事实和单纯地受警告处罚事实本身不具有不涉及公共利益或他人利益的私人性,亦不属于隐私,也不构成隐私侵权,当然若传播处罚所涉及的隐私信息部分则另当别论。因而,警告事实的传播在实际上往往难以避免,法律上又未禁止,受警告处罚的相对人几乎必然会受到因警告事实传播而引起的名誉损害,只是相对于通报批评而言传播范围较窄,名誉损害程度较轻而已。
此外,警告还具有明显的申诫罚属性,其主要是通过告诫、警示,指正相对人的违法之处,对其违法行为给予否定评价,是“行政主体给予当事人的一种申斥和告诫”[7]。
(二)警告的界限范围
警告的适用在行政法领域早已趋于成熟并渗透到了社会日常管理的诸多方面,其主要适用于轻微违法行为,因而细碎至占用、堵塞、封闭消防车通道嘉海综执罚决字〔2023〕第000219号。、使用高音喇叭招揽顾客义执法行罚字〔2021〕第12449号。等领域都有警告处罚的身影。根据黄海华的整理,现行行政法律规范中,共有95部法律、267件行政法规以及大量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政府规章规定了警告的行政处罚[8]。警告处罚力度极为轻微,常常涉及的也是最为基础的社会秩序保护,因而法律赋予了大量行政主体关于这一处罚的设定权,法律、法规、规章皆可设定。鉴于其数量之庞大以及现实适用之娴熟,再作实质解释囊括其他处罚难免造成行政处罚体系各种类之间在量上的失衡,且作为最轻的行政处罚种类,几乎所有其他相对较重的行政处罚都具有警告的功能,因而没有必要也无法作实质解释进行统括。
三、通报批评与警告之共性
新修的《行政处罚法》第九条第1项将通报批评与警告并列,意味着两者除了都具有行政处罚的一般特征,还具有某些共性。
(一)声誉罚定位
在性质上,通报批评与警告都属于声誉罚,两者都是通过给行为人人格利益造成损害来实现制裁目的,实质上都具有减损名誉,降低社会评价的法律效果,尽管通报批评对社会评价的负面影响是直接的,而警告对社会评价的负面影响是间接的,即通过警告行为来引起社会性制裁从而间接对行为人名誉造成减损。如前所述,法律上对警告事实之传播并无禁止性规定,实践中也无法避免在一定社会关系范围内流传,“既然明示的意思表示的法律效果无法限定范围边界,且可预测或必然发生,那么,相应的社会性制裁就构成了预设法律制度的一部分,属于默示性的或潜在性的法律化结果”[5]。
(二)保护基础性社会秩序
在通报批评上升为行政处罚一般种类以前,形式上的通报批评的适用范围狭窄而零碎且远离日常社会生活,更多的涉及审计、科技成果转化、慈善等领域程序性义务的保护,其处罚对象也常常是单位。但随着新法的颁布实施,基于通报批评作为行政处罚一般种类统括声誉罚的定位,实质意义上的通报批评极大地丰富了其保护的社会秩序范围,尤其是列入失信名单的加入,使得通报批评与警告一致更贴近于日常社会管理,所保护的社会秩序也更具基础性。例如,根据《上海社会信用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二款第二项的规定,“严重破坏社会正常秩序”即可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再如曾引起轩然大波的高铁座霸男事件,行为人被处罚款的信息即被记入铁路征信体系。
(三)惩戒轻微违法行为
与通报批评并列的警告在实践中的运用早已趋于成熟,相较于新设定为一般种类的通报批评,理论上人们也对其也有更深刻地认识,因而可以警告为突破口,探求立法者将通报批评列入与之并列时,是根据警告所具有的何种属性。新修的《行政处罚法》第九条规定的各种处罚是按制裁力度由轻到重进行排序的,警告无疑是最为轻缓的一种处罚种类,其主要适用于惩戒轻微违法行为。那么,立法者将通报批评与之平行置于新修的《行政处罚法》第九条第1项,显然是承认通报批评也具有该特点。不过,在制裁力度方面,通报批评的浮动上限却是较高的,个别情况下甚至能给行为人的财产权益间接造成极为严重的打击,如根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规定《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规定,“……在政府采购、工程招投标、国有土地出让、授予荣誉称号等工作中,……对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或者严重违法企业名单的企业依法予以限制或者禁入。”,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单或者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的企业将被限制或禁止进入政府采购、国有土地出让等领域。
四、通报批评与警告之界分
尽管新修的《行政处罚法》第九条第1项将通报批评与警告并列表明两者具有一定共性,但并不意味着两者完全相同。既然要以通报批评统括实质上具有相同法律效果、形式上以公开为处罚方法的声誉罚,那么厘清通报批评与同为声誉罚的警告之区别就是极为关键的,毕竟逻辑上,作为独立的行政处罚一般种类的警告是不可能通过法律上与之并列的通报批评来统括的[9]。
(一)性质倾向差异
从理论上来看,警告一般是通过直接向违法行为人送达通知书以实现警示、谴责违法行为人的效果,一般不涉及直接向社会公开从而减损其名誉的情形。如前所述,警告对社会评价的负面影响是间接的。实际上,作为一种典型的申诫罚,对违法行为人作出警告处罚更多的不是依靠降低其社会评价,从而严重影响其名誉以达到制裁违法行为、预防再犯的效果,而主要是依靠警告的批评教育功能引起当事人的内在自觉来实现处罚目的。因而,与直接向行业内乃至社会范围内公开的通报批评性质倾向不同,警告虽同属声誉罚,但更侧重于申诫罚属性。
(二)适用对象差异
通报批评主要适用于单位,即违反行政法管理秩序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而警告的主要适用对象范围则更宽泛,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都有涉及。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或许就在于两种处罚虽然保护的都是基础社会秩序,但在所侧重的领域上略有不同。关于通报批评的规定常见于慈善、审计、传染病防治、防震减灾等领域,公开谴责则主要规定于金融监管领域,列入失信名单则常见于市场监管领域。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基于两者的共性,警告也常常与通报批评出现于同一条文之内,因而两者保护的秩序领域有较大的交集部分。但是,相较于通报批评而言,关于警告的规定更常见于对人们日常社会生活的管理,最典型的体现即警告属于《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条规定的治安管理处罚种类之一,而不论形式上还是实质上的通报批评均不在此列。
(三)制裁力度差异
在制裁力度方面,通报批评应当依法在行业乃至全社会范围内公开违法行为人基本信息、违法事实以及相应的否定性评价,故而相比于依赖社会性制裁的警告,能对行为人造成更为严重的名誉减损和社会评价降低。因此,虽同为新修的《行政处罚法》第九条规定中较为轻缓的处罚种类,通报批评的制裁力度一般是要强于警告的,甚至于个别情况下,同样是惩治轻微违法行为,通报批评却存在过罚失当的风险,尤其是对企业而言,名誉减损所带来的损失往往可能更甚于资格罚。
(四)处罚方法差异
通报批评与警告虽同属声誉罚,但两者的核心界限就在于通报批评之“通报”,即以将违法信息在一定范围内公开为处罚方法,而警告则是直接向相对人作出的并不以公开为处罚方法。也正因如此,通报批评对行为人名誉的损害是直接的,而警告则是间接的,但基于这种对社会评价间接造成负面影响的必然性,这种社会性制裁所造成的名誉减损后果仍应属于立法者预设法律效果的一部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依据新修的《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八条规定而公开警告同样可能会造成名誉减损的后果,但这种公开并非行政处罚的组成部分,更非警告的法定处罚方法,而是为保障公民知情权、监督权而设置的一项行政公开制度。
五、结论
通过比较通报批评与警告的性质和界限发现,两者虽具有一定共性,同属声誉罚,但在性质倾向、適用对象、制裁力度、处罚方法上均有一定差异,其中是否以公开有关违法信息为处罚方法是通报批评与警告的核心界限。纯粹的“批评”与警告在内容、功能上几乎别无二致,都是对违法行为人之劝诫、警示,唯有加之一定范围内的“通报”才能使之与警告构成实质区别。通报批评对行为人名誉减损的影响是直接的,而警告则是间接的,但这种名誉减损后果于警告而言仍处于立法者预设的法律效果范围之内,是默示性的法律化结果。
参考文献:
[1]许安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释义[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21:50.
[2]谢祥为.冲突与选择:通报批评在行政法中的命运[J].行政与法(吉林省行政学院学报),2004(1):91-93.
[3]刘启川.通报批评不应一概认定为行政处罚[N].民主与法制时报,2020-07-12(3).
[4]山西省林业和草原局执法监督处.行政处罚种类和设定(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释义系列之一[J].山西林业,2022(2):6-7.
[5]朱芒.作为行政处罚一般种类的“通报批评”[J].中国法学,2021(2):148-165.
[6]吴叶乾.行政处罚中的通报批评:制度架构及法律规制[J].安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5):76-82.
[7]晏山嵘.行政处罚实务与判例释解[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6:90.
[8]黄海华.行政处罚的重新定义与分类配置[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20(4):31-43.
[9]江国华,孙中原.论行政处罚中的通报批评[J].河北法学,2022(6):46-67.作者简介:吴健源(1996—),男,汉族,广东深圳人,单位为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研究方向为法学。
(责任编辑:赵良)